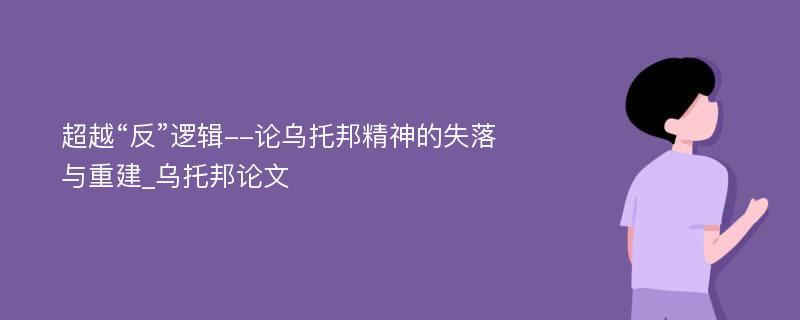
超越“反”的逻辑——论乌托邦精神的失落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逻辑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12-0024-07
雅各比以乌托邦之死来指称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特征。他不无惋惜地写道:“乌托邦精神,即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的这种观念,已经消失了。甚少有人相信未来,它不过是今天的复制品而已,这复制品有时候比今天稍好些,但是一般而言要比今天糟糕。出现了一种新的一致性看法:不存在其他选择。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个政治衰竭和退步的时代的智慧。”[1](P1-2)时代对乌托邦精神的放逐是人类屈从于现实、超越性想像力衰竭的表征,深入挖掘其中的根源与寻求乌托邦精神的重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力图在乌托邦精神与乌托邦主义之间寻求分野,力求从固化的乌托邦主义中拯救出流动的乌托邦精神,既拒斥乌托邦主义对未来社会蓝图具体琐碎的强制性预设,又在乌托邦精神的感召下抗拒具有强大塑造主体功能的现代性社会图景,解放主体的“主体性”。面对乌托邦精神的拯救与重建的重大问题,本文认为,只能在康德与马克思之间寻求“信仰”与“运动”的张力,对这两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实现有效的整合,在“信仰”中点滴地创造“运动”的历史契机,在“运动”中加强“信仰”的力量。
一、乌托邦:“精神”与“主义”的分野
寻求乌托邦精神与乌托邦主义的分野是拯救日益陨落的乌托邦精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作。当各种反乌托邦主义者一致指称“乌托邦”必然导致极权的强势话语之下,以乌托邦“主义”为载体的乌托邦“精神”就必然成为和污水一起泼出的婴儿。反乌托邦主义者总是批判乌托邦主义妄图在人世间建立天堂,却最终只能在现实中建立了地狱。他们一再呼唤此岸世界自身规则的遵守,对彼岸神圣原则的警惕,并一再泣血地告知人们美好的理念决不可僭越“平庸”的现实,他们的分析是深刻的、语词是煽情的、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也是有力度的。不可否认,乌托邦主义曾经给人类造成了巨大创伤,忘记这种创伤是对人类幸福的亵渎,因此必须以哲学的解剖刀加以批判,警醒人们,才不至于再度集体走向地狱。然而当人们不再相信彼岸之理念,而庆幸自己摆脱了恶魔与锁链的同时,却不自觉地抛弃了人类的至宝——乌托邦精神,而乌托邦精神的穷竭必然导致人类历史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终结的结论。事实上,一些目光敏锐的思想家早已开始在价值维度寻求对乌托邦精神的拯救。布洛赫就放弃了乌托邦主义的政治设计,而致力于乌托邦精神的发掘,在他看来,乌托邦精神是人类冲破异化结构的精神动力,它是在此世没有位置的希望,它使人们认识到现存政治结构的不完善性,唤起人们冲破异化结构的自我解救意识。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将乌托邦精神植根于人的本性,从而保存其对现实的批判力度。蒂利希则以同样的立场,将乌托邦精神视为植根人性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是一个“期望的范畴”,“由于人超越一切有条件处境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始终都有一些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无限的可能性”。[2](P169)中国的学者贺来祛除了实证主义对“乌托邦”细节的纠缠,在布洛赫同样的立场上,将“乌托邦精神”置于人类生存价值关怀的维度上,归结为人的价值化的存在方式。[3](P6-8)由此,本文认为,乌托邦精神是人类植根实然世界,追寻应然世界的超越性本性,是人类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力。具言之,它既是植根于人类生存结构与人性根基的自由精神,又是对人类更好生存状态永无止境寻求的超越精神,它支撑着人类的想像力与创造力,是人类超越自身,创造未来无限可能性的潜在力量与永恒智慧。它是一种不在场、却不断趋向更好状态的“意向”,永远不会闭合,总是面向未来、在途中的“尚未存在”,因而也是非确定性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托邦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潜能与“意向”,是作为动词的“存在”,而不是实体化的知识及其建构的“存在者”。与此相反,乌托邦主义恰恰就是这种精神与智慧呈现为整体特征的固化、客体化与知识化,因而也就是存在者。当反乌托邦主义者锋芒毕露地指称“乌托邦”不可实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整体性、实体化的知识。
这种“精神”何以成为“主义”,其内在机理何在?事实上,这内在于人类面对异在的流变世界,既渴望超越有限指向终极,又追求确定性理解的创造性活动自身。面对世界的流变性,人类只有寻求对世界与自身的确定性理解才可把握世界,实现生存。从一开始人类就是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群体存在,正是这种群体存在方式才达到对动物性自然关系的扬弃,由此获得生存的确定性根基——社会文化。个体在社会中确证自身,也生长着自身,个体在以文化为中介与他人的联系和交往中,其本质力量不断被牵引出来,也实现着与他人本质力量的交换,从而吸取他人力量,成为拥有社会力量的个体。这样,人类在相互的交往之中不断添加着作为确定性存在的文化因子,这些因子不断从稀薄的抽象走向丰富的具体。而人们创造的文化系统其最基础的层面在于劳动工具与语言,正是它们的创生使世界不断朝着符合人的目的性要求的方向发展。劳动工具与语言正是承担“为我性”结构的现实载体。“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4](P82)劳动工具沟通了人与自然,它将人的无限抽象目的具体化、有限化,成为客观可行的目的,又使自然的不合目的性通过工具的中介作用于目的,使目的受到对象的规约,从而在工具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了人类自身的目的。而语言的诞生则成为人类“自我意识”产生的标志,它不仅使个体间的交流成为了可能,也使人类内生出自身的“为我性”认识结构。语言的指称容量不仅包含反映当下经验的“所指”,也包括“非现实性”的能指,使语言的认知功能超越当下经验,而指向未来。从共时性维度看,语言的信息承载功能,使人类个体间相互对话、达成相互理解,并共同获致真理;而从历时性维度看,作为书面文字载体的语言成为知识的媒介,从而使人类文明世代相传成为可能。人类在此基础上相继创造出知识、道德、国家、社会制度等各种文化社会规则和形式。这些确定的文化因子不仅是人类创造精神与能力的结晶与外化,同时也在不断生成与提升着人类面向未来的创造精神与能力,人们正是充分运用了这些文化规则与形式后获得发展的。而当这些确定性的文化规则变得僵死而窒息人类非确定性的创造精神时,人类就将对其扬弃与更新,从而寻求更好的生存场域。人类这种“为我性”的生存结构使人不断向未来开创可能性空间,憧憬与规划一个更值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类也正是在这样的开创过程中其非确定性的“乌托邦精神”不断外化、实现着确定性存在,又不断在自身的生长中突破与更新确定性存在。
但人类个体毕竟是一个会死亡的有限性存在,无论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掌控能力,还是在“被抛”世界的自由程度而言都是有限的,从而也是不完美的,人类的创造性本性不断渴望突破这种不完满,这样从一种有限走向另一种有限。然而人的创造本性仍然不甘于这种不完满的有限性存在,必然拥有指向终极价值的冲动。而且面对生死,拥有自我意识的人形成了稳定的生死意识,总是张扬生命,创造一切有利于生命的物质条件、社会结构与思想方式,抗拒一切有助于死亡的东西。人类只有超越个体的有限性,才可以超越恐惧,获得心灵的宁静。在人类的早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使人们产生“万物有灵”的思想,也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观念,个体的肉体死亡并不能断绝人作为“类”与“全体”的存在,已逝者的灵魂追随着祖先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个体生命在现实世界与灵魂世界穿梭与轮回,从而获得生命的自足。同时,人类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力不发达,人类对世界的改造能力有限,时间似乎在生活中凝固,生活的不断空间性重复使人类的思维方式也是空间性的,人类只要认识当下支配宇宙与人类社会的“逻各斯”,这种认识便能成为永恒,借此就能掌握自身的命运,这样人们就将确定性的寻求指向了终极,以期望在全体、终极的“类”生活中寻找一个真实的根基,期望毕其功于一役地来安顿人类。人类由此开创了其生命的另一个维度——圣神与超越的维度,产生了个与类、此岸与彼岸的对峙。前者是形下的、此岸的、经验的世界,后者是形上的、彼岸的、超验的世界。人对死亡的畏惧这一“事实”,在人为塑造的意义世界里,得到了创造性的“价值”转化,个体的“小我”,融入了类乃至于宇宙苍穹的“大我”,以终极的“大生命”化解了个体对死亡的恐惧。“对于个体来说,固有生有死,但对个体所从属的终极存在而言,并没有真正的相对的‘生’‘死’,亦没有真正的‘不存在’(无)。”[5](P143)当这种终极存在的信念注入个体的心灵深处之时,也就成为个体超越生死的“心灵家园”。于是,此岸世界是现象的、不完善的,只有彼岸世界才是本真的、完美的世界,神性世界成为无限的意义世界,成为人类创造力、智慧与潜能的终极源泉,它从而是至真、至善与至美的。作为绝对基础的形而上学也由此产生,它是人既追求确定性又渴望寻求终极关怀的创造本性、渴望超越肉体死亡恐惧安顿生死的本能冲动与空间性的知性思维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形而上学在无限中确立了绝对的根基,以此作为支撑人类的阿基米德支点,但矛盾在于,作为绝对确定性的形而上学存在其必然性与合理性,而它在对人与世界“全体”“本质特征”的客观化、知识化与绝对化,并处于至高无上地位,压制有限之时,也就走向超越意图的反面,从而造成了对人类创造性的封闭,窒息了非确定性的“乌托邦精神”,走向了“乌托邦主义”。
这里的危险还在于,如果人们只是在想像中形成对未来完美社会的期待,这种诗意的构想并不构成对人类生活秩序性的威胁,只有当这种构想以绝对知识、绝对真理的面貌出现在人类社会之中,形成一种话语权,这种绝对真理的在场就意味着谁掌握它就将拥有成为人类的先知与“哲学王”的资格与可能,并且一旦为教会、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等权力实体所掌握,就会形成一种强制性、破坏性力量,窒息个体自由与社会开创其他可能性的机会。反乌托邦主义者不断批判形而上学的独断性,不断否定终极真理的实在性,其用心正在于防止以终极真理作为话语权,形成极权。这种一元决定论所带来的灾难性固然不言而喻,然而被窒息其中的乌托邦“精神”却不能任其随着乌托邦“主义”的陨落而消亡。
二、“类”的缺失与“犬儒化”的社会:乌托邦精神失落的根源
乌托邦精神日益失落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乌托邦主义的推行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是其中一个显在的原因。然而人们终止了形而上学的同时,也陷入了“形而上学”:现实技术化的控制,终止了超越与终极关怀的价值维度,从而陷入“犬儒主义”。与此关联,人们拒绝形而上学对个体的强制与压迫,也拒绝了个体在“类存在”中的心灵安顿。被批判的乌托邦主义与形而上学的退场由此加重了两个结果:一是缺失了“类”的个体,二是陷入“犬儒主义”的社会。事实上,“类”的缺失与“犬儒化”的社会并不是在批判乌托邦主义之后才产生的,毋宁说,在市场化的生活成为支配人类生活的主要方式之时,这一后果就已经凸显了,成为乌托邦精神失落的隐在原因,而乌托邦主义的批判与形而上学的陨落只是使这两个后果变得更加严重而已。
随着市场机制作为人类主要生活方式的确立,利润与效率成为人们的主要追求,货币与商品成为个体与个体交往的中介,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只能存在想像中的物件在科学充分发展的现代社会已随时可以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将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转移到现世的物质追寻。从群体挣脱而出的个体,其主体性大大增强,在市场中名正言顺地逐利。人性被设定为算计的“理性人”与“经济人”,在利益的引诱下不断扩张着其物质占有欲,以利益追求的最大化来标志自身的价值。人似乎占有的越多越能扩张生命,自我实现,但是人越是孜孜以求身外之物,就越是为身外之物所占有不能抽身而出,从而沉沦于物。原本可以补充其内在本质的个体间关系,成为相互利用以求利的外在关系,个体间丧失了同类间的情意,陷入彼此的算计之中,社会关系成为一种异在于个人的关系。个体为求利而越来越眼光狭小,离开群体日渐强大的个体已经淡忘了自身的“类”的特质,忘记了“类”所承载的意义与价值。个体利益占有的最大化生存方式使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那个超验的终极实在了,能够相信的只有现实的物质利益,人类脱离了上帝,认为仅以理性的力量就足以确证自身,上帝就这样被遗弃了。乌托邦精神的失落正是由于人类陷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在物质的狂欢中缺失了“类”的维度,从而使“信仰”难以扎入人心深处。人类总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自身与他人,使其利益的占有成为一种“恶无限”的追寻,目的总在前方,绝对的占有毕竟不能抓住绝对的目的,人的有死性又使个体所占有之物成为“身外之物”,随着自身的死亡而归于幻灭,人的灵魂得不到安顿,由此产生一种末世情结,对死无奈的恐惧、对生极度的眷恋,从而产生一种破坏性力量,摧毁人类道德,破坏社会秩序,只管眼前声色犬马,哪顾身后洪水滔天。物质的追求不能使个体超越自身有限性,寻求到心灵的宁静与现实的幸福;相反激烈的竞争,生存状态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还使人在飘零中感到焦虑,感到孤寂与无助,“无根”成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经典描述。现时代的人不再拥有将自身融入永恒类存在的“大我”,实现个体生命托付,获得人生意义永生的那种凝重与庄严。人以物的逻辑而存在,只能沦陷于物的恶性循环,诚如马克思所言:“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4](P80)只有重新寻回人自身的目的性,重新寻回人早已“异化”的类本质,人类才能得救。
另一个致使乌托邦精神失落的原因是社会日益“犬儒化”,这是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祛除了神与蒙昧的“巫魅”,实现了人对自身的主宰,或者准确地说,是作为人类本质的“理性”对人的主宰。当然这里的理性指的是一种技术理性,它的特征在于只考虑以一定的手段达成特定目的的效果,因而是一种手段与程序的计算理性,它的视野里只有作为“原材料”、“工具”、“物”的事实,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效率。人被放置在这种理性化的制度之中,沦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受着社会制度的塑造,并只能通过它来确证自身价值,这样,本来作为目的的人反而处于手段的地位,整个社会诚如弗洛姆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管理着人所创造的机器技术的复杂的社会机器”。[6](P226)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与个人自由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内在矛盾,期望以“技术理性”凸显大写人的力量的启蒙理想,却在个体丧失自身独立,沦为“铁笼”中“祭品”的结局之下流产了。稳定的社会结构也陷入了一种不断复制自身的境地,缺失了超越的能力和维度,作为人性根基的乌托邦精神在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社会中被窒息了。人的心灵也被物化的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所塑造,从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不再去反思社会现实与自由解放理念的巨大反差。技术与欲望成为社会的绝对权威,每个人都在以“职业”的形式去主动符合技术结构。“乌托邦精神向每一时代的人们展开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并提供着坚定的价值归宿,人们向它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通达这一归宿的‘桥梁’和‘路’。人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自我解放自我发展的。”[3](P8)然而,个体在同质化的社会生存境域之下,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沦为被折翼的天使,损害了其高飞的能力,消减了其超越的愿望,从而屈从于现实的社会,陷入“犬儒主义”的境地。但是,我们绝没有理由由此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沼不能自拔,事实上,人类的本性就是不断突破禁锢的超越性存在,因而社会结构对人暂时的束缚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其创造本性,人类的未来必定在自身的拯救中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乌托邦精神的重建承载着这样的历史使命,因为乌托邦精神不能丧失,如果丧失人类就失去了自我拯救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重建乌托邦精神的重要意义。
三、在康德与马克思之间:乌托邦精神重建的抉择
乌托邦精神的重建面临一种选择,是回到康德,将乌托邦精神植根于“信仰”;还是坚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将乌托邦精神客体化在现实的“运动”中。前者是将乌托邦精神承载在“道德宗教”之中,成为一种对现实的否定性、批判性力量,植根在社会的文化心理之中,不断地鞭策人类不屈从现实社会,从而促使社会进步,但这是一种将乌托邦精神客体化为个体的沉思与实践,从而不能挽救乌托邦精神整体解放意义的消解。而后者是将乌托邦精神具体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使之与事实相勾连,实现事实与价值的动态统一,成为一种现实性力量,是一种否定终极解放的理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承载着乌托邦精神整体解放意义的现实“运动”,这依赖于具体历史情境与条件的生成。但这种乌托邦精神的历史主义构建将希望放置未来历史条件的生成,所能预见的只是科学技术使社会在“量”上的累计,而非社会总体变革与人类精神“质”的进步。本文认为,乌托邦精神的重建只能在康德与马克思之间寻求“信仰”与“运动”的张力,通过对这两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实现有效的整合才能实现,在“信仰”中点滴地创造“运动”的历史契机,在“运动”中加强“信仰”的力量。
康德哲学构建是基于对有僭越冲动理性的重新考量,由此划清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边界,在知识止步的地方正是信仰的地界。理论理性为自然立法,不仅意味着理性提供知识的形式规则,更为重要的在于理论理性对认识对象的创造,这种创造同时也意味着其功能的边界,仅凭纯粹理性运用知性范畴就想去把握终极实在只能是一种理性的僭越,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正如康德所云,“我得扬弃知识,以便给信仰留有余地”,因为对有限世界的超越以期达至无限是人追寻自由的本性所在,这种超越是知识所无能为力的,只能存在于信仰之中。实践理性正是要超越经验,为自身立法,以“自由理念”在“物自体”领域形成“目的王国”,获致自由。如果说道德律令是自由的客观体现,自由则是道德律令的内在源泉。自由即是自律,人的自由意志是道德律令的立法者,构成一切道德律令的最高原则。理性为自身立法表明,人可以脱离经验世界的物质束缚,服从自由意志,担负起作为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确证人自身的尊严。康德由此得出了“本体界”最重要的道德命令:“人是目的”,人如此行为就进入一个“目的王国”。“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必须服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由普遍客观规律约束起来的有理性东西的体系,产生了一个王国。无疑这仅仅是一个理想的目的王国,因为这些规律同样着眼于这些东西之间的目的和工具的关系。”[7](P53)这一目的共同体在“应当”的层面鼓舞着人们在不完美的世界里进行自身的道德努力,不管现实环境怎样,都以这样的方式行事,凸显了理性存在者的尊严和价值,每个人都不以自身的冲动与情感,而以理性确立的普遍原则来行事,形成了个体在主体信念中的责任感。尽管康德在意志自由概念中未说明对生活其中的世界怎样安排,却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了一种确切的道德内容。个体对自由本体的信仰也成为承载乌托邦精神的载体,这种信仰来源于理性存在者在目的王国中的责任,每个人在信仰中直面自身的类本质,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文化心理,它是对物化现实的否定性力量,不断批判着现实的缺陷,使现实世界实现着对自身的超越。信仰绝不是不关照现实的虚妄存在,恰恰是信仰主体在自身的思想信念中向现实回归,在实践智慧中关联现实,不是先验整体的,只是从个体行动形成现实的整体合力与广泛的社会文化心理。这里依然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将乌托邦精神承载于“信仰”之中,实际上是将其客体化为个体的沉思与实践,不能实现乌托邦精神现实的整体解放意义,所以也需要一种整体的力量加以推动与补充。另一个问题是这种信仰它的现实根基在哪里,又以何种方式生发出来?这依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无可置疑的是,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过度泛滥与工具理性的肆虐造成乌托邦精神与价值理想的失落,人已无家可归,人们迫切需要重建精神家园,渴望“类”的回归,在现实道路尚不明了的情况下,便“只有一个上帝可以救赎我们”,这个上帝既是承载人类本质的价值源泉,又是对物化现实的否定性精神力量,这也就是信仰在现代社会重建的需要与希望所在。
而马克思不满康德将理想与现实分置的立场,其历史主义所开启的正是将乌托邦精神在实践中动态现实化的路径,从而澄明其整体解放意义。在马克思那里,价值必须以事实为基础,才能走向“定在”,价值理想不过是植根于人类实践、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相对价值原则,所谓终极价值不过是虚假意识形态。立足于实践即人类感性活动,理想与现实、事实与价值由此实现了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动态统一。因此,马克思不是将价值理想及其规范原则看作历史条件之外的抽象规定而悬浮在彼岸世界,相反地,他认为,不存在超历史的价值理想,只有将价值理想建立在科学认知所能把握的事实性基础之上才是能够理解与掌握的。马克思哲学中承载的乌托邦精神立足现实生活世界,不以超验神圣的“永恒正义”为载体,取消毕其功于一役地实现“绝对自由”的妄念。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生活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人的自由本性正是在对矛盾的否定与扬弃中生长,甚至可以说,人就是一种矛盾性存在,追求无矛盾的自由只能是神的存在方式而非现实中的人的存在方式。现实生活世界还是一个拒绝抽象的具体世界,人的创造性活动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才能展开。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人因此不仅具有不同特征与表现形式,也面临不同问题。人就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又面临新问题的矛盾性境遇中凸显其自由本性,并创造历史,历史性因而不仅是人活动的前提也是人创造的结果。人依据相应历史条件,在人与世界的否定性关系中突破固有性限制,不断否弃着不利于人生存与发展的困境,追求着未来的幸福与和谐,人也因此在环境挑战与回应的生存战略中,超越自身有限性,开启未来无限可能性,不断走向自由与解放。正因为如此,当乌托邦主义者以抽象而神圣的先验教条去演绎未来社会时,马克思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的哲学语境中拒绝一切抽象的终极实体与超人强力,只强调人在生存的具体性中成为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的命运。马克思本人则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去确立未来理想,并希望通过革命结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创造历史条件,超越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从而实现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分裂现实的缝合以及对肢解人性的整合。总之,以马克思哲学重建乌托邦精神,是将其具体化在特定历史情境之中实现事实与价值的动态统一,乌托邦精神的整体解放意义也在实践中化为一种现实性力量,即“现实的运动”。但问题在于,这依赖于具体历史情境与条件的生成,在历史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形下,“运动”便不能成为现实,只能以文化的形态出现在批判的维度中。而这种乌托邦精神的历史主义构建将希望放置未来历史条件的生成,在目前以工具理性为根基的人类生存语境下,所能预见的只是科学技术使社会在“量”上的累计,而非社会总体变革与人类精神“质”的进步。
由此可见,“信仰”的内在批判性价值与“运动”外在现实性价值都具有其独立意义。乌托邦精神的重建无论是将其仅仅降落在个人沉思与实践的“信仰”领域,还是仅仅客体化在现实社会动态的“运动”当中,在目前的历史阶段都有其片面性,因此,在康德与马克思之间寻求乌托邦精神的重建,就是在“信仰”与“运动”间寻求张力,将这两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实现有效的整合,在“信仰”中点滴地创造“运动”的历史契机,在“运动”中加强“信仰”的力量。
[收稿日期]2009-08-12
标签:乌托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反社会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康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