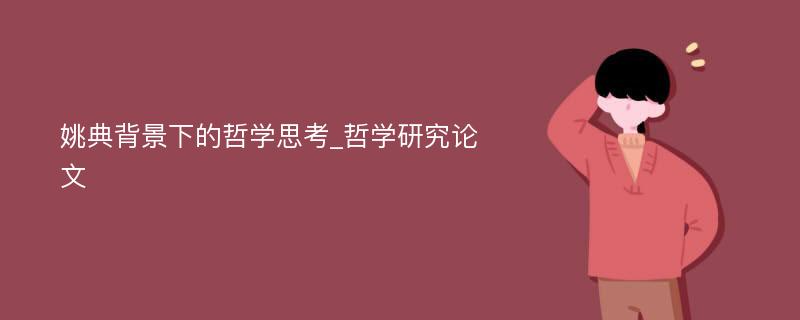
对《尧典》背景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背景论文,尧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尧典》虽然以史料价值而闻名于世,但它的形成与古典哲学的萌动、产生与发展过程是同步的。从《尧典》的传闻阶段开始,就闪烁着人类童年认识的火花;到了有文字记载时,便凝聚成具有一定时空意识的观念范畴;再到零散的口传和简片相归成类,编纂成文时,已囊括整个人文、自然的普遍规律,成为一篇带浓重主观色彩的“教科书”。
关键词 《尧典》 五行 儒墨显学 历史“教科书”
《尧典》作为《尚书》的首篇,在我国古代史上的地位十分明显。两千多年来,学者们不仅承认《尧典》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并且相信《尧典》所记录的都是史实。然而,在《尧典》的著作年代上争论不休,造成对《尧典》的历史背景模糊不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对我国古史的研究价值,以及《尧典》对我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所做的贡献。为此,我们借助现有的原始资料和部分研究成果,通过分析、比较、综合的逻辑方法,力求对《尧典》的历史背景进行重新审视与观察,尽量使这篇富有争议的史料,予以历史的、哲学的再认识。
一、从《尧典》的简编,看夏、商时代哲学思想的产生
中国的成文历史,靠现有的材料推断,只能上溯到殷代(商朝)。殷以前有关夏朝历史还限于传说之中,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掘出夏朝文字。所谓夏朝的记载都是以间接的表述形式传于后世的。其中较早的应为《尚书》中的《夏书》了。尽管《夏书》被认为是后人的追记或假托,它必然是有些史影在里边。可能出于这一认识,清代诸多学者主张《尧典》是夏史作的。清代的顾炎武、赵翼、刘逢禄、章炳麟等人也都持这种看法。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由原始部落制向奴隶的殷代过渡的夏朝,客观上是应该存在的。作为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转向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字的发明,虽说还相当粗陋(以符号形式出现),但它毕竟是后来文字的起点,也是文明社会中一切传说、记载的唯一标志。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很可能《尧典》的简编记录在夏朝是以某种简便易记的形式存在,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未能保存下来而已。至少这种推测也晚不过商朝。
《尧典》在夏、商时期,经历了氏族社会的瓦解到奴隶制社会的兴起和繁盛阶段。由于阶级的形成,在权力的传接上,废除“禅让”制,主张“世袭”制;财产由公有方式转变为私有方式;从游动的纯牧业生产发展到有相当规模的农业生产。特别是商朝,它的国家机构已经形成,有官吏、有刑法、有牢狱、有军队,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治富思想;同时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也较夏朝发达得多。当一个初具规模的阶级社会出现时,人们的原始自然宗教意识开始动摇,一种掺杂着主观成分的人为宗教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变应运而生。在奴隶制的社会里,奴隶主为了专制的需要,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上帝的儿子,把自己的种种作为视为“天命”。《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受)天命”。《诗经·商颂》云:“帝立子生商。”《尚书·康诰》也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与)厥邦厥民。”等等记载,足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天命”观,已不是单一的信奉自然,而是反映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多神教向一神教过渡的宗教世界观。
在古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遭受“浩浩滔天”的洪水灾害。《尧典》中记载,尧面以“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的情景,与四方诸侯商议由谁去治理洪水呢?大家一致推举鲧。结果鲧治水九年,因用堵塞的方法,违反了“五行”的性能,毫无成绩,“殛鲧于羽州”而死。后来派禹去治理,“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尚书·洪范》),改用疏导的方法,获得成功。“五行”一语来自《尚书·洪范》,但在《尧典》中已经有所隐伏。这就是我们祖先通过平治水土的生产斗争,最早对自然现象、性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初步观察、总结而产生了唯物主义思想的胚胎。在征服自然的幻想升华为解释自然的科学过渡环节中,蕴育出一颗包含着逻辑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在内的哲学思想的萌芽。
《尧典》中规定的“天”、“地”、“人”、“物”等概念,尽管它的内涵与外延有些尚不确定,可经过观察与实践,再经过思维的判断,由“术”而演化为“道”了。其中“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部分,所阐述的四季变化,已经对“道”(基本规律)进行了合理地揭示,正标志着哲学思想的开始。在伦理道德方面,尧要求舜负责推行德教,倡导“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在维护国家机器上,《尧典》中规定了“奖善惩恶”的具体措施。从家庭的教化到国家的规范,都充分表现出哲学开始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掌握世界。某种意义讲,哲学已成为“生活的响导,宇宙的探索者,邪恶的驱逐者!……”[①a]
二、从《尧典》编纂,看周、春秋战国时代哲学思想的发展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历史时期,从社会制度的更替角度,我们把周朝拟为封建制度开始时期(西周)和封建制度完善时期(东周)。西周初期和中期,虽说不乏奴隶社会的“宗法”观念,但其统治者用“天意”代替“天命”,并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来维护周礼,主张“德治”,与殷朝那种暴力统治相比,是一种进步思想。西周末期,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核心的哲学宇宙观得以相应的发展。到了列国兼并时期的东周(含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我国封建社会已跨入第一个历史新纪元,地主阶级以革命者的姿态,跃到具有特殊时空意义的政治舞台。于是,他们从思想到观念都显得异常活跃与新鲜,尤其在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迎来了文化上空前繁荣的春天,诸子蜂起,学派林立,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史学、哲学的发展。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动荡局势,历史的演义性也就比较大,结果造成后人对《尧典》的撰写年代和编纂情况理解不一。
认为《尧典》是周初人所作,除表现形式上(文字相近)接近周初的作品之外,就是内容和哲学思想与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相通。原始八卦在殷周之际,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对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和人类本身的男女生殖现象所得的观念进行概括。八卦中的对立范畴在《尧典》所叙的事实中基本得以体现。如“钦若昊天”,“望于山川”是“天地”之象;“烈风雷雨弗迷”是“雷风”之象;“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谓“水土”之象。还有“考妣”、“夙夜”、“寒”、“暑”等等。把“阴阳”的对立视为宇宙间的基本对立,这符合周初“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五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五种物质形态——“水、火、木、金、土”。《尚书·大传》传说:武王代纣,兵到殷郊,士兵们欢唱:“孜孜无息!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这种对“五行”的朴素歌颂,虽在《尧典》中没有明见,可当舜在尧去世三年后的正月初一,来到文祖庙,和四方诸侯之长共商国事,分封二十二人之职时,其中首命伯禹担任司空,并说:“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又命弃担任后稷,“播时百谷”。还命益为山泽之官,掌管“上下草木鸟兽”。这足以看出,从前以累世斗争的沉重代价,换取了对“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的朴素认识,将对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坚持《尧典》为春秋战国时编纂的作品,就其哲学思想的发展来讲,首先表现在“天道”观这一哲学范畴的确立与发展上。《尧典》第一部分的第二段介绍当时的历法情况。“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表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按照一年春、夏、秋、冬的四时变化,要求人们作好播种、耕作、收获、储藏等事宜。据《春秋》记载,春、夏、秋、冬的四季概念来自春秋时代。所以,这段对“天道”观的具体描述,跟春秋时秦国的医和、晋国的史墨、郑国的子产、越国的范蠡等人,把“天道”视为自然本身的变化规律,而不是上帝的垂示,并解释为“三辰”(日、月、星)在太空中的运行,“四时”(春、夏、秋、冬)的交替,以及“天之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和“地之五行”(水、火、木、金、土)的相互作用思想是一致的。由此可见,用“天道”揭示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来推动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从哲学的角度看,虽没有建立完整的体系,但用朴素的哲学方式来理解世界的本源问题,仍是十分可贵。
其次,反映出儒墨显学“人道”观的基本思想。《尧典》更多是记载尧、舜二帝在一生社会活动中人伦道德方面的情况。无论是选贤任能,还是待人接物,都体现一个“诚”字。当挑选治国人才时,有人举荐尧的儿子丹朱,尧曰:“吁!讼,可乎?”在与四方诸侯之长商讨由谁继位时,尧说,应考察贵戚中的贤人,或隐伏在下面能干的人。大家告诉尧,在民间有一个处境困难的人,叫虞舜。后来为了考验虞舜,尧将两个女儿做他的妻子,并让他处理政务。经三年考验,尧让位给舜。舜继位后,接纳百官时,也跟尧一样诚心诚意的与四方诸侯之长商议,吸取他们的意见。这种以“诚”相待的处事哲学,含有“仁”、“爱”等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因素。因此说,与春秋时代第一个建立哲学思想体系的孔丘以“仁”为核心的儒道遥相吻合。孔丘说的“仁者爱人”,第一,要求在统治者内部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里仁》、《颜渊》),进一步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第二,提出以“仁”为标准的“举贤才”的从政原则。第三,提出了“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的原则。《尧典》中尧、舜二帝以“诚”相待的道德观,还与战国时代以“人道”理论为核心的墨子“兼爱”原则互为包容。墨子认为“兼相爱”就是“仁”,“交相利”就是“义”。他主张从农工肆人中选拔贤人,并用“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思想反对世袭继承制(《墨子·尚贤》上)。那么,“诚”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孔丘的孙子子思认为:“遵道而行”要有“择善而固执之”的主观精神——诚。“诚”作为一般概念,具有真诚、无妄、纯正、专一等含义。但,“诚”这种主观精神状态,在子思的哲学思想范畴中,又成为贯通天人的绝对精神,即“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二十章)
在春秋战国时代,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是为“人道”通往认知所架起的桥梁。《尧典》中的“诗言志”思想与此有相通之处。孔孟的“仁”学是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可细细地品味一下,应有哲学的属性。“仁”能否由主观意识来决定,“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即个人的主观意识可以达到“仁”的自觉。这种主观意识论与诗歌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特点,强调由主观达到客观的效果是很相似的。
鉴于以上的对比分析,说《尧典》是孔子或成于子思等儒家的托古造作,是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的。
再次,《尧典》中蕴含着孔孟之道的“知行”观因素。“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纯属“中庸”思想,与孔丘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相同。孔丘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第六章)这里提出“两端”,即事物都有其对立的矛盾。但孔丘称赞舜处理事物的态度,就是采取折中的办法。此思想在《论语》、《荀子》和《中庸》里比比皆是。如《论语》的“子温而栗,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君子惠而不费,劳无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荀子》的“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不苟》)《中庸》的“君子之德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词意相同。此种用“而”转,或用“而不”、“而弗”、“而无”两字转其文义的句法,在战国初年以来比较盛行。从文法结构上看,《尧典》的整编年代可在《论语》出现之后;从思想内容上看,《尧典》述音乐教育的性能时强调的“直温”、“宽柔”、“刚简”都是渊于孔丘以来的儒家思想,以前没有提这种性能的。《论语》有人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在战国时代编写的;荀子约死于公元前230年;《中庸》是子思所作。由此推断《尧典》是战国中、末期作品,或由子思所编,还因为子思发展了孔丘的“中庸”思想。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中庸》第一章)把“中庸”的概念上升到哲学范畴,认为“中”与“和”乃是宇宙中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遵循这一法则,让事物平衡、和谐的发展,就可以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繁荣兴旺。钱玄同说《尧典》中的观点与《孟子》、《大学》同。这可能与孟子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相关。《孟子》曾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后来《大学》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完成了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今《尧典》首段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里的“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就是修身;“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就是齐家;“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就是治国;“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就是平天下。次序井然地表现着儒家的政治哲学程序。
《尧典》所以能较充分而集中地反映儒墨显学中的天道观、人道观和知行观,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息息相关。不论是假托也好,还是编写也好,其自觉或不自觉地交杂些颇有代表性的哲学观点,是顺理成章的事实。在阶级对峙、矛盾复杂尖锐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史料的辑选或搜集不注入编者的主观色彩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出于价值观的需要,任何超出时代而不打上阶级烙印的编者,是很难摆脱那残酷的现实社会而存在。
综上所述,我们把《尧典》的撰写年代及历史背景如帷幕一样,一下子拉了近二十个世纪,真可谓长矣!
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们普遍承认,历史学既是社会进化论的验证,又是社会进化论的最初形式。”[①b]《尧典》从原始氏族部落时的神话式的传闻,经过漫长的奴隶制社会的夏、商两代追记性的简编,到封建制社会的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托古造作,最后演义成历史的“教科书”。它既反映各个历史时代的科学、文化成果,又不同程度地保留最初的史料形式。这是历史的多棱镜在不同时空领域里边,反射出不同时期历史遗存的特有功能。那种只从单一的视角或平面似地观察《尧典》的历史背景,势必要陷入主观臆测的囹圄,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分析考究式的研讨局面,结果肢节了史料,影响了史实存在的价值。有人问历史是什么?卡尔的答复是:“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历史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的相互印证的辩证思维形式,也是现在与过去进行参照对比,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尧典》以事实存在的方式光照人间几千年,说明它是“关于结果或现象的知识”,所以能获得这种知识,“是根据我们首先具有的对于结果或现象的原因或产生的知识,加以真实地推理”。就是说,有关《尧典》的历史背景认知,通过机械的方法,预测的方法,都将无济于事,只有从哲学理性进行绵密地思考,才会闪现出智慧的火花,才能使真理与我们的距离缩短。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把《尧典》这篇名著摆进哲学的殿堂,犹如一个婴儿经过母亲十月怀胎,到呱呱落地,必须具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它是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萌动、发芽、生长成熟这一历史过程是同步的。否则,它就不是《尧典》,自然也就不具备其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注释:
①a 西塞罗:《辩论集》,见《西方思想宝库》第1319页。
①b 勃朗宁:《帕拉塞尔萨斯》,见《西方思想宝库》第1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