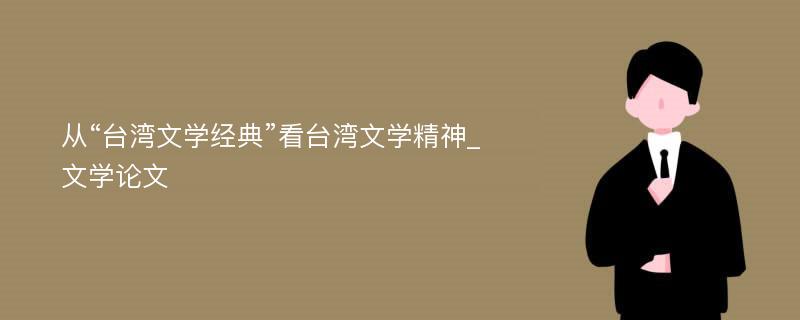
从“台湾文学经典”看台湾文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台湾论文,看台论文,精神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春季,台湾多个团体参与评选的“台湾文学经典30部”揭晓,为我们审视台湾文学精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这次“台湾文学经典”的评选是由王德威等7 名专家学者组成评选小组,提出150本参考书单,寄发给91 位讲授现代文学的教授进行通信投票(回收有效票67张),依此得票高低,选出54本参加决选。7 名原先的提名委员决选出27本之后,评选委员再推荐得票较高的部分作品集角逐最后3本书,由票选结果的前3名当选。钟肇政、林海音、朱西宁、李乔、张大春等人的作品以些微票数落选。
我在《20世纪视野中的文学典律构建》一文中谈及文本的典律化本来就属于一种选取性、排他性的文学评论运作,由于包括文学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歧见和审美参照系的差异,任何一种文学典律的构建都很难被各方都认同,任何一套文学经典也难免遭受当代其他次群体或不同时代文化人的非议责难。以票选的“民间方式”来产生经典,自然只是参与投票的诠释群体(包括投票者所能代表、影响的读者群)认可的经典,而且票数的些微差别不应成为经典的界限。筛选、评价经典都是出于对文学的理解、尊重。因此,本文在通过“台湾文学经典”来探讨台湾文学精神时,也将涉及到那些进入决选名单而以些微票数落选的重要作品。同时,我也充分注意到台湾笔会等6 个团体就“台湾文学经典”发表的声明。文学经典的确认是一个文学系统多个层面参与运作的动态累积过程。这次“台湾文学经典”的产生只是这一动态累积过程中值得重视的重要一环。本文初步的探讨就是基于上述认识展开的,所论述的台湾文学精神也应视作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
台湾文学经典30部中,创作时间最早的当推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此书完稿于抗战结束前,而梁实秋《雅舍小品》第一集全部完稿在战事结束后了)。台湾文学经典以本土作家的长篇创作为起点是颇有意味的。《亚细亚的孤儿》诞生于日据后期台湾进步作家的秘密写作状态,吴浊流闭户秉烛,书稿秘藏于炭篓之中,完稿一批即被秘密转到乡下。这部小说原名《胡志明》(何不“志”于复“明”之意),1956年重版时改名《亚细亚的孤儿》,都无疑表明了作品的中国意识。这种中国意识既包含政治、国家层面上的归属意识、认同意识,又包容文化层面上的寻根意识、认同意识。吴浊流述及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过一段极有意味的话:“由于汉文被禁,所以只好借用日文来表现,例如拙著《亚细亚的孤儿》也是用日文写成。‘啊,胡太明终于发疯了。果真是个有志的人,谁又能不发疯呢’(此句话出现在《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关键之处,决非等闲之笔——笔者)这是中文式的表现,语言虽是日本的,其表现形式则是中文的。开门见山,即先提出结论。说明在后。李白的诗有谓:‘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也是结论为先,说明在后。”(注:吴浊流:《睽违三年,重游日本》,载《台湾文艺》第47期。)熟悉日语交际的人都知道,日语表达的习惯、策略都是说明在前,结论在后,甚至不直言结论。吴浊流在中文被禁的绝境中将中文的表现形式深嵌入日语中,这种拼死固守民族文化的历史悲壮,足以让人深信,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意识”是不会也不能消亡的。
当然,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意识”早已不囿于地域、党派、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了,它更多地表现为作家们用自己的创作,超越台湾“孤岛”的隔绝,而努力定位于中国现当代的历史脉络中,回归于中华文化的传统长河中。这使我想起写下《城南旧事》、《烛芯》、《晓云》等书的林海音。她原籍台湾苗栗,幼居北平时,就体味到“没有根而生存,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常常是“许多个夜晚,我们就打开地图,看看那一块小小地方的故乡”。而她回到台湾后,“却又时时怀念北平的一切”,甚至“不敢想什么时候才能见那熟悉的城墙、琉璃瓦、泥泞的小胡同……”在苦思而不得见中,她不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城南旧事》,还写下了《我的京味儿回忆录》。林海音这种心悬两地的乡思是属于20世纪的中国的,大幅度的多地迁徙使作家有了多个故乡,也许人们真的不必孜孜以求于何者为故乡,不变的是作家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的恒久追寻。台湾文学中一向有本省籍作家和外省籍作家之分,然而,台湾文学的经典性显然不是产生于这种区分之中,而会产生在林海音那样的创作心态中:北京、台湾都不是地理名词,也不是政治图腾,而是能让人始终梦牵魂绕的精神家园。
入选的台湾文学经典中,跟吴浊流遥相呼应的该是简媜,因为她是入选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且在钟情传统上有独异表现。简媜在描绘台北时曾有入骨的剖析:“台北打破四季,模糊国界,兼具最草根的古典与最前卫的现代,勇于嬗变,拙于处理变化所带来的灾难,终于出现了独树一帜的台北逻辑。”(注:简媜:《忧郁女猎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简媜散文给人印象极深的一点是她的文学充满创造的胆略,但她又善于平衡于各种变化之间,其中她对中华文化的古典性和台湾文化的草根性两者的感悟和融合尤使人难忘。而简媜的散文就是以此作为基点,构筑起了她极具现代性而又不迷失于现代性的散文世界。简媜的散文自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看,但她创作所呈现的中华传统性和台湾草根性的一致,则是会给人以许多前瞻性启示的。
总之,“台湾文学经典”所揭示的台湾文学精神是充溢着中国文化精神的。这种精神并不因为环境、世代的阻隔而消亡,而它表达层面、表达方式跟同时期中国文学的差异,则恰好说明了台湾文学在生生息息中表达中国文化精神的强韧。
一种文学的精神孕成于该文学生存体系的形成历史中,考察台湾文学生存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台湾文学开掘本土文化资源的努力尤为明显,这种努力使本土文化资源从一度“边缘”的地位移到了台湾文学的中心,并形成了亲民忧世的文学传统。黄春明的《锣》、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入选“经典”,李乔的《寒夜三部曲》、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提名“经典”,正是从赖和开始的,一代代作家开掘本土文化资源的结果。而黄春明当年为了写作,不惜辞职以清贫相伴创作,足见其对本土文化资源的热情关注。他们开掘本土文化资源的创作实践,增强了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联系着关怀底层、关注小人物等文学传统。除此,其他因素是难以长久容身其中的。
对于台湾文学而言,台湾社会的特殊性恐怕主要在于其历史的殖民性和现实的移民性。这使得台湾文学一直追求着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包容性。
白先勇的《台北人》在此次“经典评选”中以第一高票当选,他在出席“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时说, 《台北人》的创作年代是1965 至1971年,那时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他受了很大冲击。当时他觉得,整个中国文明似乎要完全毁灭了,因此《台北人》虽然写的是台北,却也可说是他对整个历史、文化的哀悼和反思。(注:参见台湾《联合报》1999年3月15日“文化”版。 )白先勇的“文明毁灭感”实际上是对时代转折、历史转型的敏感,正是这种敏感使他在“台北人”身上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悲凉。展开来看,梁实秋对于人性的敏感,张爱玲对于普通人生的敏感,跟白先勇也有相通之处。也许正是殖民地的历史,使台湾作家敏感于时代的转捩,也敏感于文学上发出自主性极强的声音。从吴浊流到陈映真、七等生、李昂,台湾文学一直显示出很强的叛逆性,这种叛逆性有侧重指向政治层面的,如陈映真的《将军族》;有侧重指向伦理层面的,如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也有侧重指向人性层面的,如李昂的《杀夫》。每次叛逆都是一次文学的超越,而这构成了台湾文学宏大历史叙事空间。从整体上看,台湾文学无疑具有凝重、丰厚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正来自于台湾文学的抗争精神。从日据时期对“皇民文学”的抗争到50年代对“反共八股”的反拨,台湾文学正是在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疏离、反叛中走向了成熟。而近40年的台湾文学,更以直面人生、逼视人性构筑了自身的历史感。
30部台湾文学经典有约三分之二产生于六七十年代,时值中国大陆文学元气大损,这使人们不禁去探究:在20世纪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是否有过一个“台湾文学中心时期”?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这一时期。考察20世纪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是存在着文学中心迁移而后形成文学多中心格局的情况的。五四时期的北平,30年代的上海,都曾聚集起最优秀的作家,以其创作、出版机制提供最优秀的作品,并以其辐射机制,影响了其他地区,包括台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学,无可置疑地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如果用同样的标准看待台湾文学,那么应该承认,六七十年代确实构成了“台湾文学中心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不仅提供了一批富有创新锐意的上乘文学作品,而且对包括东南亚、欧美澳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为日后跟中国大陆文学构成互动关系作好了充分准备。承认“台湾文学中心时期”的存在,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去梳理清20世纪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而对于台湾文学自身而言,它经历了呼应五四新文学、形成本土化创作格局等阶段,而进入了“台湾文学中心时期”,也意味着它的成熟。而这种成熟的到来,很大程度上孕成于台湾文学开放兼容、有容乃大的精神襟怀。
虽然在台湾文学史上,现代主义文学、乡土文学等都曾各领风骚,但仔细辩析,两者当道并行,各为中心,却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内在格局。尤其是近20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互相制衡,“让文学回归文学本身”日益成为作家们的共识,各种文学的“异数”都有可能被容纳,而作家间的歧见也尽量回到文学自身来化解。同时,在华文主流社会中,台湾是个相当特异的“移民社会”,移民社会特有的文化多元性保证了台湾文坛兼容并包空间的存在和拓展,先锋和通俗、传统和现代、乡土和世界……都有可能在经典性上获得栖身之地。赖声川的剧作“成功结合了精致艺术和大众文化”,而王文兴《家变》那样极具实验性、前卫性与争议性的作品也在经典榜上有名,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王幼华在他的长篇小说《广泽地》中曾蕴有喻意地写到了“容百水而成淤”的“沼泽型文化”。从某个角度看,台湾文学就呈现出“沼泽型”的兼容并蓄,它虽然不似海洋那样浩大,但也有着自身的丰富深邃。正如“湿地”已成为生态环境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台湾文学这种“纳百水而成淤”的“水土融合”形态(明显区别于“海洋型文化”和“大陆型文化”)也是文学体系,尤其是中华民族文学中极其重要的一环。这种形态得以形成,最重要的缘由恐怕在于台湾文学看重文学自身。20世纪华文文学遭受过种种外部压力,台湾文学可以说是抵御外部压力最为自觉,失落文学自身最少的。入选“台湾文学经典”的29位作家,或寻求社会使命感和文学创新意识的沟通,或超拔于世俗世界,探索人类生存本体,他们都具有很强的文学主体意识,却将拓宽、深化社会的文学审美品位视为根本。文学是最为宽容的,把文学始终当作文学,就永远不会失落博大开放的精神胸怀。以诗为例,作为最纯的文学样式,这次“台湾文学经典”新诗类选入了痖弦、郑愁予、余光中、杨牧、周梦蝶、洛夫、商禽7人的诗集,或古典,或现代,或传统,或西化, 但都极端个人化。7位诗人不少出身军人,但政治等因素在他们面前纷纷溃散, 不能不归于他们对文字魔力的痴迷。台湾文学也一直遭受种种干扰,时至今日,政治上的“统、独之争”也时而给文学投下阴影。但台湾文学不改文学初衷,以台湾岛的“土”接纳着艺术的百川之水,才有了台湾文学的丰富和深邃。
台湾文学中,无论哪一种文体,其在应变创新中的多元取向都是明显的;例如,所有文体中,中国的散文传统最为丰厚,现代散文的突破也最为艰难。然而,台湾散文却辈有创新,代有佳作。这次入选“经典”的散文有7种,包括了台湾四代散文家“起、承、转、合”的努力。 第一代是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开了散文纵谈人性、人生的风气,家常闲话,幽默亲切。第二代是琦君的《烟愁》,承接五四现代散文的流风余绪,创作更显人性深度,且以在台湾文坛的起步营造出新的散文世界。第三代是王鼎钧的《开放的人生》、杨牧的《搜索者》、陈之藩的《剑河倒影》、陈冠学的《田园之秋》(余光中的散文也应列其中),他们大都接受了台湾文化环境中的现代艺术洗礼,在散文观念上有大的突破。《搜索者》所呈现的浪漫和理性,《剑河倒影》对科学和文学的整合,似乎都改写着以往的典律。而王鼎钧散文将人生视作一部大书写得峰回路转,使他后来的创作超越五四“为人生”的传统而另成一脉。第四代就是简媜的《女儿红》(林清玄等的散文也可列于其中),他们拥有中华传统和台湾经验,文笔无拘,于传统和现代间有更大的变通和综合。四代相传中时有革新之势。当中国大陆散文由杨朔、刘白羽、秦牧模式三足鼎立30余年中,台湾散文却众彩纷呈,在中国散文史上留下了显赫的一页。散文的实绩最足以说明,创新求变是台湾文学极可宝贵的精神。
“台湾文学精神”是个大话题,30部“台湾文学经典”使我们再次思考台湾文学精神的内涵,包括它对中国文学精神的丰富和调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