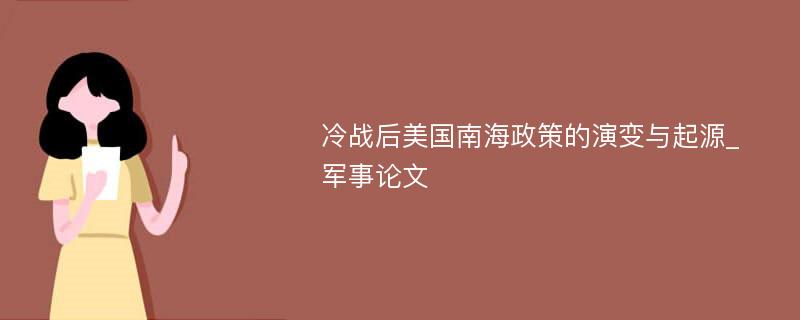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海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根源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4)06-0023-22 一 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上普遍认为在东北亚地区和台湾海峡可能发生冲突并导致常规战争。但近年来,许多人认为另一个冲突正在东南亚的南海显现。在他们看来,南海可能成为一些小国与中国之间政治、经济和军事争端的根源。不仅这一地区的国家,其他与这一地区有贸易往来或对勘探和开发石油、天然气有兴趣的国家,都对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有极大的关切。 东南亚地区已经出现了各国军事装备的明显增长。为了对未来南海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充分准备,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东南亚国家的武装力量获得了第四代战斗机、潜艇、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护卫舰、两栖攻击艇、反舰巡航导弹以及命令—控制—通信—计算—情报—监视和侦察(C[4]lSR)系统。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进口的武器在2000-2010年期间分别增加了84%和722%。越南为购买6艘俄罗斯潜艇开支了20亿美元,为购买俄罗斯喷气式战斗机开支了10亿美元。马来西亚不久前开放了在婆罗洲的潜艇基地。菲律宾2011年支出了1.18亿美元购买一艘巡逻舰和6架直升机,旨在为壳牌菲律宾公司的天然气合资开发提供安全环境。泰国对海洋也有相当大的兴趣。为了保护其沿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它从美国和英国购买了护卫舰,从中国购买了海岸巡逻艇,并同德国谈判购买其翻新的潜艇。东南亚对南海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彼此之间也存在对抗,例如,1999年马来西亚空军在中国也申明拥有主权的榆亚暗礁驱逐了菲律宾空军的飞机;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和印尼军舰在西里伯斯海因西巴丹和利吉丹群岛发生了冲突,2008-2009年因安巴拉特群岛发生冲突。这两个国家都增加了在沙巴附近水域的部署。① 美国的南海政策对于南海局势和东南亚国际关系来说举足轻重,随着南海主权争端的加剧,美国的南海政策在国际上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即使是在美国,研究者们对美国的南海政策一般也只是泛泛而谈,强调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持有一贯立场。如果再向他们深究根据是什么,却鲜有人回答得上来。为了能够更好地在南海问题上同美国进行博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有必要准确地解读美国的南海政策和意图以及美国的南海政策是否发生过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将对此做出分析。 二 持中立立场(1990-1994年) 冷战结束初期,1990-1994年期间,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不对各方领土要求的合法性做出判断,只强调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纠纷,同时关注南海的航行自由。 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时期,南海岛屿争端就被认为是潜在的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不过,在整个20世纪70-80年代,对于美国来说,它从未成为一个安全问题。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之间达成《上海公报》,表明中美为了各自的利益建立起了共同应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战略伙伴关系。1973年6月4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个法案,停止对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拨款。紧接着在同年7月,越南共和国政府宣布它与一些石油公司达成了在主要位于南海西部边缘地区进行石油开发的8个合同,其中包括同壳牌、埃克森、美孚和加拿大石油公司的合同。1973年9月,越南共和国将南沙群岛的一部分划归为一个行政单位,越南共和国政府至少在南沙群岛的五个岛屿上驻有军队。1974年1月17-20日,中国夺回了西沙群岛。美国对中国行动的反应是保持沉默,而且美国海军的作用仅限于帮助越南共和国撤出这些岛屿。②美国国务院表示,南海冲突应在“有主权要求的国家之间自行解决”。1980年,美国国防部在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几乎没有提及南海,只是在谈到苏联在金兰湾和岘港的利益以及南海将如何使“美国第七舰队在协防日本联络线的任务复杂化”时才谈到南海。③ 虽然越南在1978-1982年试图从中国手中夺取这些岛屿,但中国一直保持着对西沙群岛的有效控制。1975年4月11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夺取了在越南共和国军队控制下的六个南沙岛屿。此后,直到1992年,南海岛屿的主权争端主要发生在中越之间。 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阶段,尽管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眼中的“中国人权问题”使中美关系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依然是相当冷淡的。美国在1991年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又在波黑、索马里、科索沃采取了军事行动,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南海上。 从1992年起,与南海有关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1992年2月,中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重申对南海所有岛屿的主权。越南在东南亚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1991年10月23日,在巴黎和会上达成了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定,它标志着延续了13年的柬埔寨战乱从此结束。1992年7月,越南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从而不再被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视为敌对国家。1995年7月,越南成为东盟成员国。 也是在1992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公司——克里斯通能源公司(Crestone Energy Corporation)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个名为“万安北-21”石油开发合同,合同规定双方将在南沙群岛西南部万安滩附近的“万安北-21”合同区进行石油开发。该合同于1992年5月22日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并于1992年6月1日开始被执行。该合同是中国在南沙群岛海域的第一个石油合同。④引人注目的是,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出席了合同的签字仪式。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解释说,克里斯通是一家私人公司,美国在其同中国的合同问题上不持立场,美国使馆官员出席签字仪式不应被解释为美国支持中国对南海领土主权的要求。鉴于在南海存在着相互竞争的领土主权要求,美国的立场是,有关国家应当用和平方法自己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强烈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南海的领土争端,同时关注在南海的航行自由。⑤ 事实上,在1995年之前,南海问题很少成为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和国会听证会的主题。从另一个事实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在1990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东亚的报告中,基本上没有提及南海问题。在1992年的报告中,南沙群岛只被简短地提到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稳定的九个潜在问题之一,但并没有被视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在1992年3月的一次美国同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日本的对话中,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表示,美国对南沙群岛不负有特殊责任,中国在2月25日宣布其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不过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立场。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也说,虽然美国反对用武力支持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但美国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时所能做的是有限的,而且他并不认为南沙群岛将会成为下一个爆发点。⑥根据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h)的说法,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仍然是不对领土要求的合法性做出判断,只是要求维持航行自由和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纠纷。⑦ 三 关注程度加深(1995-2009年) 第二个阶段是1995-2009年。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渐加深。不过,美国仍然认为它所关注的航行自由并没有受到阻碍,因此它没有改变在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的立场,只是要求各方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 有评论认为,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在东南亚的安全目标和美国支持这些目标的行动显示:“美国并没有选择对南海领土争端做仲裁,而是选择做一名观察者”。⑧不过,美国对南海的关注度在1995年中国同菲律宾关于南海美济礁的争端中明显加深。在此之前,东盟作为一个集体首次在南海问题上表达官方立场是在1992年。在当年7月于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六国外长会议上,菲律宾利用东道主的身份号召尽快解决南海的领土争端,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关于南海的行为准则。会后,东盟六国——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签署了《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东盟宣言》。1995年3月18日,东盟再次采取统一行动,发表了一个声明,号召所有有关方遵守《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东盟宣言》。1996年,东盟外交部长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号召把“南海行为准则”作为地区长期稳定的基础。1998年12月在河内召开的第六次东盟峰会上,菲律宾被授予起草“南海行为准则”的任务。 1995年2月,菲律宾指责中国在美济礁上修建建筑物,中菲之间的冲突由此而起。同年2月到7月,在历次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南海问题被多次提及。⑧美国此时关注的焦点仍然是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领土争端,不使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受到破坏。美国最初对美济礁事件的反应是发表温和的声明,表示对航行自由的担忧,希望和平解决领土争端。1995年4月19日,美国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表示:美国对所有六个对南海岛屿有主权要求的国家都有接触,并有定期会谈。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也对中国外长钱其琛直接表明了美国的立场,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⑩ 1995年5月10日,当中菲之间在美济礁问题上处于紧张状态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里斯丁·谢利(Christine Shelly)宣读了一份关于南海问题的正式声明,这是一份重要声明,它包含了现在被人们所熟知的美国的基本原则:第一,美国反对使用武力。第二,美国在维持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始终不变的利益。第三,维持航行自由和符合国际法的海上行动自由是美国的根本利益。第四,美国对相互竞争的领土要求的法律优劣不持立场。 这篇声明表示,美国担心在南海的单边行动和反应模式增加了这一地区的紧张状态,美国强烈反对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来解决相互竞争的领土主权要求,并敦促所有有领土主权要求的国家自我约束,避免采取使局势不稳定的行动。该声明提出:“美国在维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有始终不变的利益。美国号召有领土主权要求的国家加强外交努力,考虑所有当事方的利益,以解决有关问题并加强地区和平与繁荣。美国愿意以有领土主权要求的国家认为有帮助的任何方式给予支持……美国重申它欢迎1992年东盟关于南海的声明。维护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所有船只和飞机在南海不受阻碍地航行和飞行,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对有关南海各种岛屿、礁石、环礁和码头的相互竞争的领土主权要求在法律上的优劣不持立场。但是,美国对不符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对南海海洋领土主权的要求和对海上活动的限制表示严重关切。”(11) 谢利强调,美国在和平处理争端方面有很大的利益,在航行自由方面有根本利益。南海的紧张局势在过去的两周内有所减弱,但过去几个月里,在南海的一系列单边行动及其引起的反应,如开火和扣押渔船事件,导致了日益增加的危险,包括武装冲突的危险。谢利拒绝说明是哪个国家威胁了航行自由,而是表示,“这份声明是针对所有有领土主权要求的国家的”。她还表示,如果说这份声明中有什么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是一份“更为强烈的声明”,“更为强烈地表达了我们的担忧”。(12) 在中国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于1995年5月16日发表讲话指出:“5月13日,在菲律宾军方的策划和组织下,菲方两艘军舰和一艘运载菲律宾和外国记者的游船编队驶往南沙群岛美济礁进行所谓的‘采访’活动。此前,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曾多次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取消这次挑衅性行动。5月13日凌晨,菲律宾海军一艘配有两架军用直升机的4000吨级登陆舰和一艘配备7门大炮的护卫舰所组成的编队,掩护一艘轮船,企图闯入美济礁潟湖区,轮船上载有国际媒体的记者。正在美济礁值勤的南海渔政总队34号船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后,对该船进行了拦截和喊话阻止,在双方对峙了8个多小时之后,菲律宾的轮船退却。”(13) 美济礁事件之后,美国国务院官员被多次问到假如中菲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美国同菲律宾的安保条约是否会延伸到南沙地区,而每一次,国务院的官员都用不做此假设来回避。例如1995年5月17日,副国务卿伯恩斯声明:“美国不是争端的一部分,因此我不想对此做预测,也不预测这一冲突会扩大。”(14)同年7月25日,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表示:“我不认为任何人猜测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明智的”。(15) 1995年2-5月,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内部对美国的南海政策有大量辩论,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政策过于被动,基本上是对中国的行动做出反应。而且美国在过去的十年中都没有认真地重新考虑过其南海政策,美国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政策却发生了变化:1991年9月16日,菲律宾参议院投票决定美菲军事基地协定不再续约。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军在1992年撤离了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把该地区的军事力量转移到了关岛、冲绳和横须贺等军事基地。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美国应更多地鼓励在东盟和中国之间制定行为准则,以便在发生严重冲突时,能够依此来进行规范,并建议对中国做出态度鲜明的谴责。然而,当时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没有接受这种观点,他认为,美国同中国之间有太多的利益交错,美国在许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如果国务院发表一个谴责中国的声明,一定会给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从而损害美国的利益。于是国务院的表态只是申明了一些原则,如尊重国际法、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等。(16) 鉴于国务院的态度,美国军方中有人指出,“1996年克林顿政府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承诺美国不担当领导,而是跟随”。他们认为,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四方会谈中、在代顿和平协议中的作用,是美国领导地位和维持和平行动的例证。然而,“在南海争端中,美国一直是在观察、倾听,偶尔对担忧和问题做评论”,其消极行动削弱了美国的朋友和盟友对美国承担和平与稳定责任的信心。他们说:“对南海争端保持沉默损害了美国的其他目标,尤其是美国想要成为可靠的安全伙伴。亚洲领导人把美国的行动看做是对他们的人民和政府视为重要的事情的漠不关心或不感兴趣。亚洲国家中的武器竞争、新安全安排、公共和私人申明都反映出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对美国承担地区稳定与安全责任的信心下降了”。(17) 可以说,美国此时最大的关切仍然是南海领土争端问题的和平解决,只要不对航行自由构成威胁,美国就不认为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重大问题。 1998年,菲律宾挑起了第二次美济礁事件。这一次,美国众议员达纳·罗尔巴克尔(Dana Tyrone Rohrabacher)要求国务院为其对美济礁的考察提供便利。美国国务院曾以安全和其做法没有先例为由,劝阻他不要成行,但是罗尔巴克尔坚持自己的想法,并向国务院正式提出要求。为此,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向菲律宾政府转达了他的要求,在菲律宾政府的安排下,1998年12月罗尔巴克尔搭乘菲律宾空军C-130飞机巡视了美济礁,并在之后展示了他拍摄到的中国军舰和中国在美济礁修建永久性设施的照片。他发表言论说:“当我们飞过上空时,看到中国人正在拼命建造这些防御工事。我们看到焊光闪烁,看到恐惧与不祥之兆。中国人把军舰派到这里,为的是夺取一个邻国的领土”。(18)这一举动被国际上看做是美国国会支持菲律宾立场的象征性事件。 然而,美国国防部1998年11月发布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完全没有提及南海问题。虽然菲律宾政府做了极大的努力,但它并未能使美国承诺在领土争端中站在它一边,菲律宾对中国继续占领美济礁的抗议也没有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19)1999年2月11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仍然表示,虽然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上进行建设是潜在的单边挑衅行为,但这种做法“远没有阻碍航行自由”,并且表示,“我们注意到有领土主权要求的国家过去在南海问题上的声明,包括1997年12月中国和东盟的联合声明,它们已经表示愿意通过和平方式并根据普遍承认的国际法来解决领土争端,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敦促中国和其他有领土主权要求的国家运用所有适当的外交渠道来解决争端”。(20) 1999年2月12日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坦利·罗斯(Stanley Roth)作证说,中国在南海的军力“并不是主要的安全威胁”。美国更愿意同东盟一起努力通过印尼领导的有关南海问题的研讨会或东盟地区论坛来解决南海问题。(21)鉴于美国的表态,菲律宾国防部长安吉洛·雷耶斯(Angelo Reyes)将军公开声明,尽管菲律宾和美国之间有共同防务条约,但菲律宾不能依赖美国来进行防卫。(22)1999年3月11日,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鲁宾(James Rubin)声明,美国的利益是在南海维持和平与稳定以及航行自由。(23)2000年1月7日,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斯同样强调,虽然在南沙群岛进行的军事设施建设是美国所担忧的,但它还没有构成对航行自由的阻碍和威胁,因为所有各方都表示它们不试图阻止国际航行自由。(24)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加强。2000年5月24-25日在吉隆坡举行的第15次东盟与美国的对话中,美国官员指出,南海仍然是一个潜在的冲突之地。尽管美国欢迎有关各方努力用和平手段解决分歧,但它也敦促采用其他步骤来促进南海的稳定。2000年7月,美国参加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的官员建议在讨论的问题中包括南海问题,并且建议,除了中国同东盟的对话之外,还应考虑采用其他有用的多边渠道。在这次论坛上,中国外长唐家璇首次表示了中国对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关注,提出亚洲地区有增无减的联合军事演习“逆流而动”,“抵消着本地区建立信任的努力,不利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25)中国也向美国、菲律宾和其他国家提出了不要在敏感地区(即在南沙群岛周边或邻近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要求,认为这些联合军事演习使南海地区的气氛更为紧张,成为这一地区安全局势的新的干扰因素。 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但该事件同时也对亚太地区产生了其他一些重要影响:美国加强了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开始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并加强了同印度的军事关系;此外,恐怖主义袭击扩大了日本和印度在南海的战略存在。这些新的发展将对未来整个南海局势产生影响。 美国同其盟国菲律宾、泰国以及其他友好国家如新加坡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同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美国人得到了它一直想要在东南亚得到的东西,他们现在有了与愿意保持海洋通道开放的国家的双边关系。”(26)在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菲律宾立即对美国提供了充分的和无条件的支持,允许美国使用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2001年11月,菲律宾总统为纪念《美菲共同防御条约》50周年而访问了美国,在访问期间,小布什总统强调确保两国维持面向21世纪的牢固防御伙伴关系的紧迫性,两国领导人也同意通过增加训练、演习和其他联合行动来加强同盟关系。自九一一事件以来至2003年,美国向菲律宾派出了650人的军队,包括特种部队,帮助菲律宾加强其武装力量来同恐怖主义做斗争,并考虑以某种形式恢复在菲律宾的基地。 九一一事件也为美国和越南提供了改善彼此安全关系的机会。2001年12月10日,美国和越南的双边贸易协定生效。越南谴责恐怖主义袭击,并支持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联盟。此外,越南接受了美国提出的要求,愿意帮助控制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金融交易,允许某些因天气原因而改变航线的美国飞机飞越其领土。2002年2月,在河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太平洋司令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表示,他曾同越南高级官员讨论过“越南更多地参与地区军事行动的可能性”。(27) 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也都对美国的反恐战争给予了支持。总的来说,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安全对话机制和组织都把它们的关注焦点转向了反对恐怖主义和相关的合作措施。(28) 此时,美国对中国的地区政策还有许多正面评价。例如2005年9月15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高级顾问詹姆斯·基斯(James R.Keith)在对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证词中,对中国更加透明和更加全面地参与地区政策表示了赞赏。他提到2004年中国建议把2003年10月中国加入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变为“南海行为准则”,并建议在军事官员之间进行合作,还提到中国不久前与越南和菲律宾达成了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进行联合勘探的协议。他认为,中国的目标是更为彻底地融入地区体制,并运用其日益增长的权力来影响地区对话和互动的发展。这是理想的和积极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将对地区稳定和地区军事关系透明度的提高做出贡献。美国不寻求把中国,也不希望把自己排除在整个亚太地区稳步发展的对话和一体化之外。(29) 然而,从2009年开始,南海问题开始成为美国全球事务和亚太事务的关注重点之一。关于南海政策的美国重要官员的讲话、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国会的听证会急剧增多。而对南海问题关注的天平也开始从南海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向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倾斜。这从2009年7月15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斯科特·马西尔(Scot Marciel)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中可以解读出来。(30) 在马西尔的证词中,他继续强调美国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不选边,即对南海岛屿、礁石和环礁等的陆地主权归属,或产生于这些陆地的海洋地区(如领海)归属不选边。但是,美国对“领海”或对任何非陆地的海洋区域的主权要求存在着担忧。因为在它看来,这些海洋主权要求不符合国际法。此外,美国“无瑕”号海洋监测船在航行中所遇到的中国渔船的“干扰”,体现了中国对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内其他国家船只行动的法律权利的理解,而且美国认为中国用了“不安全”的方式(干扰航行的方式)来申明自己的海上权利。 马西尔强调说,许多国家对南海有领土主权要求,这些要求引起了一个对于国际社会来说重要的问题,即有关海上航行和海洋资源准入的问题。中国对南海主权的要求,包括南海领土边界以及无论是对整个南海海域的领海要求还是仅仅对南海陆地的领土主权要求,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在过去,这一模糊性对美国的利益几乎没有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在意领土主权要求本身,只要争议各方能够和平解决争端。但是现在,美国感到这一模糊性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了美国的利益:一是影响了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在美国看来,虽然中国一再强调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并没有受到阻碍,但是美国的“无瑕”号海洋监测船在执行“符合国际法的日常行动”时,在南海的国际水域多次受到中国渔船的“骚扰”,使双方的船只都处于危险之中,干扰了航行自由,“中国没有表现出对其他国家船只安全的尊重”。(31)美国就此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并敦促通过建立对话机制来解决分歧。美国注意到自2009年5月中旬以来没有再发生类似事件。二是从2007年起,中国有关方面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停止同越南在南海的勘探合作,否则它们将在同中国的贸易中面临不利后果。美国表示反对中国的做法,特别是因为有些勘探活动并不在中国有主权要求的区域内,并且向中国直接提出了美国的担忧,认为国家之间的主权争端不应通过向并非争端方的私人公司施加压力来解决。 马西尔指出,在战略层面上,中国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在维护自己的海洋权利上日益增长的强势,而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同意甚至不能理解中国对海洋法的解释”。这些担忧促使美国做出明确的政策反应。不过马西尔认为,仍然存在着用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关于美国船只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问题,在2009年6月召开的中美两国防务磋商对话(The Defense Consultative Talks)中,美国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提出了这一问题,中国一方同意根据1988年签订的《海上军事磋商协议》(The 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在2009年7月份举行一个特别会议来讨论该问题,并寻求解决分歧。关于美国公司受到压力的问题,弗卢努瓦注意到中国已经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方法来解决关于其一些陆地边界的争端。例如,2008年中国同越南达成了一个陆地边界划界协议。他还指出,中国一般对东南亚国家采取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此外,中国在亚丁湾打击海盗的部署一直是对处理国际共同关注问题的积极贡献。弗卢努瓦承认,美国同中国之间有广泛的联系,包括在一些对于两国有关键战略重要性的问题上。中美能够重视并通过对话来负责任地解决这些分歧。(32) 四 实际上的“选边站”(2010年至今) 2010年至今是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第三个时期,它显示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美国对在南海航行自由的担忧加剧了,二是美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实际上做了选边。这主要表现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没有同中国事先沟通的情况下在越南河内做出了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提出对中国在南海行为的正式指责,而不论中国的行动是否是被动的;强调解决主权问题必须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当事国不能单方面改变领土现状;敦促国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就是说,美国不再是持中立立场的观察者,而实际上变为了一名干预者。 从2010年至今,随着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南海领土问题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关注的重点,在南海问题上发言的官员的级别也提高到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等内阁重要官员。甚至有人认为,在2010年之后的两年中,围绕南海冲突的外交主导了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33) 2010年中国海军在南海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分别是在4月初、7月上旬和7月下旬。第一次和第二次演习动用了来自北海、东海和南海舰队的海军战舰,第三次演习是同类演习中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中国海军南海演习之后,第43届东盟外长会议于2010年7月19—20日在河内举行。会上东盟外长宣布,东盟认为“南海行为准则”是“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基准文件”,并指示其高级官员重启“中国与东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工作组会议(The ASEAN-China Joint working Group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C)”。在2010年7月23日举行的第17次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之前,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向美国表达了它们对中国对西沙和南沙群岛“强势的”主权要求的担忧。美国随后私下通知了一些东盟地区论坛国家,国务卿希拉里将在会上发表一个美国关注南海问题的讲话,并要求这些国家在她发言后给予支持。在东盟地区论坛的外长会议上,27个成员中的11个,包括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和韩国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讲话做出了响应,同美国一起提出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四个东盟国家没有表态,它们是: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 希拉里·克林顿的讲话提出:国际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虽然美国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不选边,但美国认为这些要求必须符合国际法;领土争端应当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她说:“像所有的国家一样,美国在航行自由问题上、在对亚洲海洋公域的准入、在南海地区尊重国际法等方面有国家利益……美国支持所有有领土要求的国家在外交上进行协作,不通过压力来解决各种领土争端。我们反对任何有领土要求的国家诉诸武力。虽然美国在相互竞争的对南海岛屿的领土争端中不选边,我们认为有领土要求的国家应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追求其领土要求和与此相应的海洋和空间权利。在南海,对海洋和空间的合法权利要求必须符合国际法,应当仅仅产生于对岛礁的合法要求。美国支持2002年中国与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34)希拉里还在会后对媒体的讲话中,把解决南海争端说成是“地区稳定的关键”。 虽然美国官方至今不承认其南海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是东盟国家普遍把希拉里的讲话当做是美国南海政策的转折点:从“观察”转变为“干预”。人们普遍认为,希拉里的讲话是“催化的一刻”,不仅标志着美国政策的改变,而且标志着中美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争端的开始。美国的做法实际上鼓励和纵容了对中国南海岛屿有领土要求的部分东盟国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从此,在美国“战略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的南海问题开始成为中美之间的主要争执问题之一。 希拉里的“干预”行为令中国外交部极度震惊,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在外长会议上当场提出了谴责。中国的反应之激烈大大超出东盟国家的意料,这对之后发生的事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10年9月下旬,第二次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纽约举行,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在其所起草的联合声明中加入了反对有主权要求的国家“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在南海强行实现有争议的领土要求”,但在联合声明的最后文本中,“使用武力”和“南海”两个词被删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些东盟国家认为现在不是同中国进行对抗的时候。一位东盟资深官员说,“现在似乎不是招惹中国重拳还击的时候”。另一位东盟外交官表示,“我们不想造成一个印象,我们想要按照美国人所说的所有的话去做。删除‘南海’一词挽回了中国和美国的面子。”(35)这些事态表明,东盟国家不想表现出同中国的直接对抗,或危及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它们更希望美国起平衡作用,支持它们的立场。(36) 在这次会议的前三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担心美国和东盟可能在会后提出一个声明,并表示中国反对任何与南海问题无关的国家介入争端,因为这只能使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外交压力产生了所期待的效果,在第二次美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没有讨论南海问题。(37) 实际上,在希拉里河内讲话之前的半年中,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在讨论美国的南海政策。根据美国方面的辩解,有两个情况促使奥巴马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南海问题:一个是2010年3月中国外交部官员在一次会议上向美国人表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另一个是越南等国家迫切要求美国出面制止中国在南海的强势行为。(38)但事实上,来自中国方面的信息是,中国资深官员并没有做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样的表达,连一位出席此次会议的美国资深官员也在私下里说,希拉里对美国记者肯定地说某中国资深官员说了这番话,“确实是她记错了”。(39) 从那时以来,美国不断申明南海领土问题的解决必须依据国际法,暗示中国的领土要求不符合国际法,并且鼓励和支持菲律宾把南海问题提交到国际法庭,要求所有对南海有领土要求的国家不能单方面改变领土现状。 2011年6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Mark C.Toner)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的两天内所发生的事件引发了重要的海洋问题,包括国际航行自由、不对经济发展和商业设置障碍以及尊重国际法等问题。美国并不支持越南的某些做法,因为“我们认为任何使当前紧张状态升级的行动都是没有帮助的”。(40)同年7月21日,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东京接受访谈时也强调,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有利益,但美国的主要利益是诸如航行自由等问题。(41) 2011年6月14日,当南海局势趋于紧张时,托纳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支持中国同东盟一起制定“南海行为准则”。2011年6月30日,希拉里在同菲律宾外交部部长会见后表示,美国承担对菲律宾的防务承诺,美国正在同菲律宾政府讨论菲律宾需要什么,什么是它的优先考虑等问题。美国将根据菲律宾政府对其海洋防务支持的要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菲律宾。(42)据美国国务院官员的介绍,美国同菲律宾在军事领域里的合作包括情报分享、通过支持菲律宾的国家海岸监视系统来提高其防务能力。 到2011年,南海成了中美关系中存在最激烈争执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5月,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启动了有关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对美国的经济、国家安全和主权产生何种影响的听证会,美国军方领导人、企业高管、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法律顾问以及智库代表都投入了争论之中。2012年5月9日,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国会作证时明确要求国会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表示,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美国在实践中也一直遵循这一公约,但如果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遵循,而自己却还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么美国的要求就缺乏说服力。2012年5月23日,希拉里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也强烈呼吁国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她说:“我们的航行权利和挑战其他国家的能力应建立在最牢固和最有说服力的法律基础之上,包括在诸如南海这样的关键地区。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加入国,将使我们在援引公约规则方面具有更大的信誉和更大的执行能力。”(43)在行政部门的推动下,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进行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审议程序。 2012年下半年,美国不断对南海日益紧张的局势表示担忧,包括中国与菲律宾相互攻击的语言升级、双方在资源开发方面采取的行动以及围绕着黄岩岛发生的冲突。美国的一个新举动是,国务院媒体关系办公室代理发言人维多利亚·纽兰德(Victoria Nuland)于2012年8月2日发表正式声明,公开批评中国政府建立三沙市的决定,并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海地区派驻新的驻军。(44)在美国资深官员的公开讲话中,对越南和菲律宾是否在南海采取挑起事端的行动基本上只字不提,而且完全不考虑中国的做法在许多情况下是反应式的。这种做法即使在一位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看来,也表明美国已经跨越了不选边的界限。(45) 2012年9月20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国会就亚洲海洋领土纠纷和主权问题作证时,对美国的南海政策和“再平衡”政策做出了详细的说明。他再次强调,为了促进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美国已经根据其长期政策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原则和利益,即维持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无阻碍的合法商业以及在南海的航行自由。美国对相互竞争的关于南海岛礁的主权要求不持立场,继续鼓励各方通过外交的和协作的方法来处理争端,包括使用中间人或其他国际法律机制。为了减少误解和误判的危险,美国继续敦促所有有关各方澄清并追求符合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领土和海洋主权要求。(46) 2013年5月,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约瑟夫·云(Joseph Yun)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关南海问题的会议上做主题发言,谈到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奉行的五项原则:(1)美国对相互竞争的领土主权要求不持立场。(2)这些领土要求必须建立在国际法的基础之上,必须与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一致。(3)对南海海洋和领空的主权要求必须来自岛礁,必须证明这些要求是合理的。(4)虽然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美国在如何处理争端和解决争端上有巨大的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南海是一个具有巨大商业意义的全球公域,有占全球大约50%吨位的海运通过南海。因此美国的利益是,商业必须受到保护,在全球公域里应有航行自由。二是在南海的合法资源开发。美国在南海地区有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公司,它们的合法活动应不受领土主权归属的限制。(5)应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领土争端。一种手段是外交谈判,另一种是通过第三方的国际仲裁,如国际海洋法法庭。不允许单方面改变领土控制现状。此外,美国支持东盟与中国之间就建立“南海行为准则”进行对话。 约瑟夫·云承认,南海的争端在国际上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海洋争端不仅发生在南海,还发生在东海的钓鱼岛,在日韩之间也存在独岛(竹岛)争端,美国同加拿大之间也有岛屿争端。但是,与其他海洋争端相比,南海的争端有所不同,它对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都有巨大影响,包括渔业、石油和天然气以及航运。这就使得和平解决南海问题与许多国家都利益相关。(47) 最近的一次美国政府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官方立场的重要表态是2014年2月5日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l)在众议院有关东亚海洋争端的听证会上的证词。在表述美国政府对中国南海政策的立场时,拉塞尔使用了更具有指向性的、措辞更为强硬的语言,认为中国在南海基于“九段线”的领土要求缺乏明确性,“造成了这一地区的不安全性或不稳定性”。他指出,“我们在与任何领土要求有关的行为上采取强硬立场:首先,我们坚决反对使用恐吓、压制或武力来宣称领土权利。其次,我们采取一个强硬的立场——领海要求必须建立在国际法之上。这意味着,所有领海要求必须产生于对岛礁的主权,或者必须符合国际海洋法。这样,虽然我们不偏向有领土要求的任何一方,我们确定地认为,不是产生于对岛礁的领土要求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为了支持这些原则,为了与美国长期坚持的航行自由计划(The U.S.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相一致,美国继续反对妨碍对属于所有国家的海洋权利、自由和合法使用海洋的主权要求。”“我们已经反复申明航行自由反映在国际法中,而不是大国对其他国家的恩惠。”(48) 拉塞尔的证词意味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下述变化:其一,美国在对领土主权的要求上做了选边:中国的领土要求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因此不具有合法性;对其他国家的领土要求是否符合国际法未做表态。其二,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要求妨碍了美国长期奉行的原则——国际航行自由。美国此时对中国南海行为的指责是:继续限制菲律宾进入黄岩岛;对菲律宾在仁爱礁的长期存在施加压力;对接近其他国家陆地和远离中国有领土要求的岛屿的地区封锁供水;宣布在南海有争议的地区设立行政区甚至军事区;将钻井平台移至与越南有争议的水域内。许多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就美国应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形成了共识。 五 美国南海政策改变的动因 如果仔细观察上述美国政策的演变过程就会发现,当美国认为自己的航行自由没有受到威胁时,它对领土归属问题并不关心,只要有领土要求的各方能够用和平方式来解决领土纠纷。而当其感到中国的“九段线”的模糊性可能使南海成为中国的领海,或至少中国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内能够限制美国舰只的活动,美国就开始担心它将在南海失去“航行自由”,特别是当美国正在把其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并把其海军兵力更加集中地部署于亚太地区之时。 许多中国和美国的分析者把南海问题仅仅归结为“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一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国际航行自由是美国生命攸关的利益。因此当南海主权问题同在南海的国际航行自由问题叠加在一起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第三方因素”,而成为一个直接关系到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因而美国对其他在南海地区有领土要求的国家之利益的关切,也相应地转化为美国用于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策略。一位外国评论者的看法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认为2009年3月美国“无瑕”号探测船事件使美国切身感到需要维护其航行自由。同时,2009年5月一些国家相继提出了自己在南海的主权要求,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担忧同美国对航行自由的担忧产生了重合,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于是成为它们的一个共同关注的焦点。(49)2010年越南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它在使南海争端国际化方面的自身利益也促使其努力把美国推向这个方向。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南海政策的基本原则自冷战结束以来并没有发生变化,从一开始它就坚持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它现在所申明的其他原则。但是,美国对争端的关注和介入程度发生了变化。在2010年以前,美国一直避免介入或选边,甚至是在菲律宾的不断呼吁之下仍不为所动。那么是什么促使美国的政策发生如此的变化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南海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日益增长。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在其2011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南中国海将是未来冲突之地,21世纪的战场将是在海上。他的根据是,欧洲是一个大陆,东亚是一个海洋。20世纪和21世纪至关重要的差别是,20世纪的最大争夺发生在欧洲陆地上,尤其是在德国东西部边境外的广阔平原地带,这一地带在军队行进的铁蹄下不堪一击。但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地球上的人口和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在这里,主要人口中心之间的空间绝大部分是海洋。南海尤其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它把东南亚国家同西太平洋连接在一起,成为全球海运的咽喉要道。(50)虽然奥巴马总统等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在做出关于南海政策的决策时,并不是按照卡普兰的思路来考量,但是卡普兰道出了南海在全球经济中心发生转移情况下特殊的地缘战略重要性,而且这一分析从一个视角支持了美国的海洋战略。 美国官员确实从海上运输的角度承认南海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位于南海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第二繁忙的国际海上通道,仅次于霍尔木兹海峡。每年有一半以上的世界超级油轮通过马六甲海峡、巽他岛和龙目岛,大多数驶往东亚国家,所运载的主要是原料和能源。通过南海运输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比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多3倍,比通过巴拿马运河运输的多1.5倍,韩国2/3、日本和台湾地区约60%的天然气运输是通过南海地区的。(51) 第二,海上航行自由对于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来说具有极端的重要性。2007年10月,美国海军提出了一个新的海洋战略——《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该战略认识到,存在着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经济体系,它依赖于在海上公域之间的行动自由,90%的世界商业活动主要通过海上或海洋上空的运输。美国必须通过把海上兵力集中在某些地区和进行前沿部署来防止和威慑冲突及战争。美国将把可信的战斗力量部署在西太平洋、波斯湾和印度洋,以保护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使美国的朋友和盟友确信美国将继续对地区安全承担责任,保障海上联络和商业航行的畅通。(52) 美国海军在2010年又提出一份报告:《2010年海军行动概念:执行海上战略》(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trategy),这份报告不仅用于指导海军组织、部署和利用当前的和所设计的能力在短期内执行《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而且将用于指导美国海军参与联合行动概念(Joint Operations Concepts)的发展过程,对它进行检验和评估,以长期支持联合能力的发展。该报告称:“海军力量非常适合于影响21世纪的安全挑战,并对其做出反应。”(53)在这份文件中包括一个“海上基地”的概念,即“部署、集合、命令、投放、重组和重新部署来自海上的联合力量,而不依赖于作战区域内的陆上基地”。(54)该文件指出,对海上基地的挑战可能来自沿海国家,它们基于对自己的环境、保护区、移民、卫生、安全、习惯法或海上治安的担忧,颁布对航行自由的限制。一旦得到指示,美国海军将根据国际法,挑战任何超越海洋国家合法权威的限制。(55)这里的要点显然是美国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 一个可以对此做出解释的观点是,设在弗吉尼亚的海洋法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Oceans Laws and Policy)主任约翰·穆尔(John N.Moore)2010年12月在题为“全球化与海洋法”的国际会议上的开场白中,集中谈到了军舰在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的绝对必要性。美国海军军法署署长詹姆斯·霍克(James W.Houck)在这次会议上批评一些国家提出过分的海洋要求,特别是把专属经济区当做领海,想要在这一区域内禁止军事活动、演习和行动,理由是出于安全或环境的考虑。他表示,美国将继续挑战这些过分要求。(56)美国监测船在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遭遇引起了美国的警觉,被它看做是一个美国未来可能遇到海洋准入问题或其海洋活动受到限制的先兆,因此美国要预先防范。 然而,一些美国的分析者也指出,美国对“航行自由”的担心是夸大其词,是在法律外衣下保护自己在亚洲的海洋地位和影响,至少是保护其执行侦查行动的能力。事实上,中国并没有为美国的航行自由设置障碍,因为中国也同样依赖于在南海和其他海域的关键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之外,马来西亚、印尼和印度等国家也同中国持同样的立场,其中印度像中国一样也反对美国的海上监测活动,不过它没有采取干预行动。其他一些国家也表示反对美国扩大对“航行自由”的解释。(57) 第三,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2010年美国做出了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决定。2012年1月,奥巴马总统发布了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国防战略指南。在2011年国会通过的《预算控制法案》规定要对国防开支做出大幅度削减的情况下,这份报告仍然提出有必要对美国的全球关注点进行“再平衡”,把重心转向亚太地区。这是美国第一次就加强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做出明确表态。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随即表示,国防部制订了一个五年规划和执行新的“再平衡”战略的具体蓝图。根据这些计划,到2020年,美国海军将把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部署的兵力比例,从现在的50%∶50%提高到60%∶40%,将包括六艘航空母舰,大多数巡洋舰、驱逐舰、海岸战斗舰以及潜艇。2010年前后,美国已经改变了其亚太防务部署,使兵力更加接近于亚太海洋运输线。同时,美国对其太平洋舰队的水面舰只进行了升级,在关岛部署了洛杉矶级潜艇,并把一些舰只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还计划把一些战舰永久性地停靠在新加坡。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使得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对于美国来说变得尤为重要。 第四,在亚太地区加强同传统盟国的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是巩固其与亚洲传统盟国的关系,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同时,美国谋求积极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新的伙伴关系,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58)在这些国家中,菲律宾和越南是同中国在南海有领土争端的国家。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偏袒菲律宾和越南,是同其实行“再平衡”战略相一致的。对于美国来说,在南海问题上同东盟国家站在一起,可以得到它们对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地位的肯定,也可以带给东南亚国家一个信息,即希拉里在夏威夷所宣称的“美国回来了”。此外,奥巴马政府介入南海争端的举动也是其确保美国参与充满活力的地区经济努力的一部分。 第五,平衡中国在东亚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日益增长,对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的分析,美国尤其担心中国军力日益增强并以更强势的方式提出对有争议的海洋领土的要求,将对航行自由和美国在这一地区投放兵力的能力造成限制。(59) 六 结论 综上所述,美国的南海政策在冷战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完全持中立立场,到1995年中菲美济礁冲突之后对南海领土争端的关注度加深,再到2010年7月以希拉里·克林顿的河内讲话为标志,转向了在南海问题上实际上的“选边站”。美国日益显露出对其在南海航行自由的担忧,主要是针对美国海军在全球投放兵力的能力可能受到的限制。鉴于海上航行自由对于美国执行其全球战略的至关重要性和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趋势,我们可以预料,未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不会软化,而且会越来越坚决地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国际法依据,包括对领海的要求必须建立在对岛礁主权要求的基础之上、在南海的领土要求必须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美国在南海政策上对中国更加强硬和介入程度的加深不仅会影响南海局势,也会深刻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中国需要对此做审慎的政策选择和充分的应对准备。 截稿:2014年5月 注释: ①Sheldon W.Simon,"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View from Washington," Asian Survey,Vol.52,No.6,2012,pp.998-999. ②Ang Cheng Guan,"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Revisited,"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4,No.2,2000,p.203. ③Ang Cheng Guan,"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Revisited," p.207. ④1994年4月,克里斯通公司根据合同条款,租赁中国勘探船只“实验2号”,进入“万安北-21”合同区实施首次海上勘探作业。在这艘中国勘探船于1994年4月13日到达合同区的当天,越南便出动5艘武装船只对其进行游弋监视。次日下午,两艘越南武装船只靠近中国勘探船,先是锚泊于500米处监视,然后在“实验2号”中国勘探船周围盘桓,实行抵近威胁和骚扰,最近距离仅为30米。此类举动一直持续至深夜。4月15目上午,越南武装船只再次出动,重复前一天的抵近威胁和骚扰活动,直至深夜。为避免事态恶化,防止冲突升级,中国勘探船始终保持克制,在尚未展开作业的情况下于4月16日清晨起锚,撤离作业区返航。参见http://www.nansha.org.cn/study/8.html,登录时间:2014年4月20日。 ⑤Federal News Service,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June 18,1992,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 2014年1月5日。 ⑥"Work with China on Spratly Row,U.S.Urges ASEAN," Straits Times,March 28,1992,p.19,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920328-1.2.29.7,aspx,登录时间:2014年4月30日。 ⑦Susumu Awanohara,"Washington's Priorities:US Emphasiz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Vol.155,No.32,1992,p.18. ⑧Dale C.Eikmeier,"Air Defense,Leadership Vacuum:U.S.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chool of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United State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Fort Leavenworth,AY 7-98,December 7,1998,p.3. ⑨例如1995年2月13日、4月19日、4月20日、5月10日、5月12日、5月17日、6月27日、7月25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南海问题都成为关注的焦点。 ⑩Federal News Service,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April 19,1995,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5日。 (11)Federal News Service,State Department Regular Briefing,May 10,1995,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5日。 (12)Federal News Service,State Department Regular Briefing,May 10,1995,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5日。 (13)《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菲军方组织南沙“采访”是对中国主权严重侵犯我国政府向菲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载《人民日报》,1995年5月17日。 (14)Federal News Service,State Department Regular Briefing,May 17,1995,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5。 (15)Federal News Service,Prepared Statement of Ambassador Winston Lord,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and Asia and Pacific Affairs Subcommittee,on U.S.Security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and Pacific,July 27,1995,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5。 (16)根据一位这一时期在温斯顿·洛德领导下工作的美国前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官员对笔者的陈述。 (17)Dale C.Eikmeier,"Air Defense,Leadership Vacuum:U.S.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20,p.37,p.44. (18)《第二次美济礁事件:菲拉拢美议员对华放狠话》,http://v.ifeng.com/mil/arms/201306/a3645d6e-71a7-43e3-8dfd-b1cba212d979.shtml,登录时间:2014年3月18日。 (19)Ang Cheng Guan,"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Revisited," p.209. (20)Federal News Service,State Department Regular Briefing,February 11,1999,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5。 (21)Lee Siew Hua,"U.S.Reject Talks of Massive Spratly Building-up," Straits Times,April 12,1999,p.28,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990412-1.2.39.2.aspx,登录时间:2014年4月25。 (22)"Manila Cannot Rely on US,Says Military Chief," Straits Times,December 6,1999,p.36,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991206-1.2.44.2.aspx,登录时间:2014年4月25。 (23)Federal News Service,State Department Regular Briefing,March 11,1999,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5。 (24)Federal News Service,Stanley O.Roth,Assistanc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Department,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Press Center Briefing,1999 Review,Year 2000 Preview,January 7,2000,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5。 (25)转引自宋予南:《美国在亚太地区联合军事演习成为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载《中国国防报》,2000年8月25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2/18/20000825/202264.html,登录时间:2014年5月5日。 (26)Yann-Huei Song,"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New Millennium:Before and after 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l.34,Issue 3/4,2003,p.256. (27)"Adm.Blair Discusses Vietnam's Anti-Terrorist Support," US Department State,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Februay 4,2002,http://www.vietventures.com/Vietnam/terrorism.asp,登录时间:2014年1月6日。 (28)Yann-Huei Song,"The Overall Situ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New Millennium:Before and afterthe September 11 Terrorist Attacks," p.261. (29)James R.Keith,"U.S.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aiwan," Statement to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September 15,2005,http://2001-2009.state.gov/p/eap/rls/rm/2005/53266.htm,登录时间:2014年1月16日。 (30)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earing,"Maritime 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East Asia," testimony by Scot Marciel,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East Asian and ASEAN Affairs,July 15,2009,Federal Information and News Dispatch,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6日。 (31)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描述,2009年3月5日,一艘中国护卫舰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的情况下接近美国“无瑕”号海洋侦测船,并在距船首约91公尺处穿越。不到两小时之后,一艘中国Y-12侦察机以183米高度、30到90米的距离11度掠过“无瑕”号上空。然后护卫舰再次从“无瑕”号前方通过,这次距离约为366-457米,既未礼让,也不表明意图。3月7日,一艘中国海军情报搜集船用船上无线电向“无瑕”号舰发出警告,指责它非法作业,并要求它离开该海域,否则就“承担后果”。此后,美国国防部于同年3月9日声明称,3月8日五艘中国船只,包括一艘中国海军情报搜集船、一艘海洋渔业局的巡逻艇、一艘国家海洋行政巡逻艇以及两艘挂有中国国旗的小型拖网渔船,跟踪并危险地接近美国海军船只,“明显蓄意骚扰正在公海进行日常作业的美国海洋监测船”。美国国防部官员表不,中国船只用逼近“无瑕”号(最近时仅有25英尺,即8米);直接停在“无瑕”号前方,迫使其紧急制动;在“无瑕”号航向前方投放木头等方式,追使其最后撤离。此事件发生在距海南岛约75英里(120公里)的地方,即中国专属经济区内,而且靠近中国三亚的榆林海军基地。美国国务院就此向中方提出了抗议。对此,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美舰行为违反了国际海洋公约及中国相关法规,中方已提出严正交涉。“无暇”号海洋侦测船是用来侦听水下潜艇音响的专用船只。2009年5月13日,美国国防部报告提出,它已经派遣军舰在“无瑕”号继续执行监测任务时为其护航。 (32)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earing,"Maritime 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East Asia," testimony by Scot Marciel,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East Asian and ASEAN Affairs,July 15,2009,Federal Information and News Dispatch,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6日。 (33)Sheldon W.Simon,"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View from Washington," p.1002. (34)Speech of Hiliary Rodham Clinton,Vietnam,July 23,2010,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登录时间:2014年2月3日。 (35)Carlyle A.Thayer,"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n Affairs,Vol.2011,Issue 1,2011,p.21. (36)Renato Cruz De Castro,"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Pivot to Asia:From a Diplomatic to a Strategic Constrainment of an Emergent China?"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Vol.25,No.3,2013,p.337. (37)Carlyle A.Thayer,"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21. (38)根据笔者对多位美国智库人士的访谈。 (39)根据笔者2012年9月对一名前奥巴马政府资深官员的访谈记录。 (40)Federal News Service,Mark C.Toner,Deputy Spokesperson Daily Press Briefing,Department of State,June 10,2011,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6日。 (41)Federal News Service,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Interview with Kurt M.Campbell,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Interviewer:Kyoko Yamaguchi,Yomiuri Shimbun,Bali,July 21,2011,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6日。 (42)U.S Department of State,"Remarks with Philippines Foreign Secretary Albert del Rosario after Their Meeting," June 30,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12/218835.htm,登录时间:2014年1月19日。 (43)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s Written Testimony on Accession to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nd Ratification of the 1994 Agreement Amending Part XI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May 23,2012.http://www.virginia.edu/colp/pdf/Clinton-LOS-testimony-2012.pdf,登录时间:2013年5月20日。 (44)States News Service,Office of Press Relations,Patrick Ventrell,Acting Deputy Spokesperson,"South China Sea" August 3,2012,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6日。 (45)根据笔者同这位美国专家的交谈。 (46)U.S.Department of State,"Maritime Territory.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Asia," September 20,2012,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2/09/197982.htm,登录时间:2013年1月15日。 (47)Federal News Service,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Keynote Address by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oseph Yun at the Third Annual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South China Sea Conference,Washington,D.C.,June 5,2013,http://www.nexis.com,登录时间:2014年1月6日。 (48)"Assistant Secretary Russell's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on Maritime Disputes in East Asia," February.5,2014,http://www.cfr.org/territorial-disputes/assistant-secretary-russels-congressional-testimony-maritime-disputes-eastasia/p32343/,登录时间:2014年2月6日。 (49)Alice D.Ba,"Staking Claims and Making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How Troubled Are the Water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2,No.3,2011,pp.269-291. (50)Robert D.Kaplan,"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Future of Conflict,The 21st Century's Defining Battleground Is Going to Be on Water," Foreign Policy,August 15,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8/15/the_south_china_sea_is_the_future_of_conflict,登录时间:2014年1月10日。 (51)Joshua P.Rowan,"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ASEAN,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sian Survey,Vol.45,No.3,2005,p.415. (52)U.S.Navy,"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October 17,2007,p.5,pp.8-9,http://www.navy.mil/maritime/maritimestrategy.pdf,登录时间:2014年4月30日。 (53)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trategy," Joint publication of the US Marine Corps,the US Navy and the US Coast Guard,2010,p.95,p.28,http://www.navy.mil/maritime/noc/NOC2010,pdf.登录时间:2014年4月30日。 (54)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trategy," p.99. (55)Department of the Navy,"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trategy," p.22. (56)Erik Franckx,"American and Chinese Views on Navigational Rights of Warship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0,No.1,2011,pp.191-192. (57)Alice D.Ba,"Staking Claims and Making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How Troubled Are the Waters?" p.283. (58)关于对美国“战略再平衡”的详细分析,参见周琪、齐皓:《奥巴马连任的原因及其第二任期面临的挑战》,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第7-29页。 (59)Mark E.Many N.et al.,"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 March 28,2012,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448.pdf,登录时间:2014年2月9日。标签:军事论文; 南沙群岛论文; 南海事件论文; 南海争端论文; 南海战争论文; 南海局势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国务卿论文; 菲律宾南海论文; 中国南海论文; 南海军事论文; 美国领土论文; 航行自由论文; 菲律宾总统论文; 南海美国论文; 东盟外长会议论文; 美国国务院论文; 岛屿论文; 美济礁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