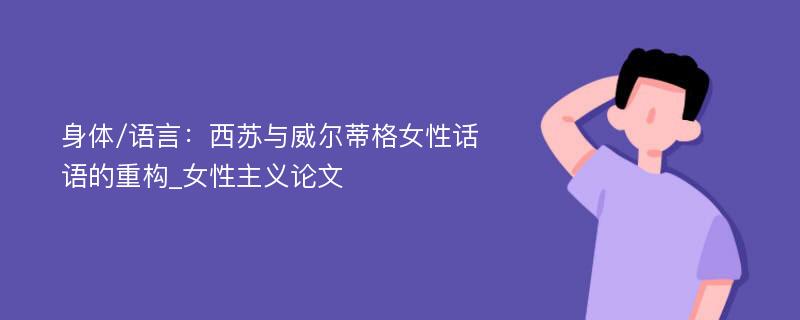
身体/语言:西苏与威蒂格的女性话语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身体论文,语言论文,女性论文,威蒂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3-0077-07
“女性话语”是指女性基于对话语权的觉醒,用语言来言说自我,言说自己对男人和女人的感受、对这个世界的体验以及对历史和现实、人类的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在男权文化世代延续的侵凌下,女性如何表述自身,如何突破传统限制,保持女性的想象自由,把女性对生活的特殊体验写进历史,是现当代女性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早在20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夫就曾感叹于文学传统中女性视角的缺失,认为妇女应该摒弃依靠他人代言的幻想,自己动手书写自己的形象。她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妇女写作的初步设想——“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伍尔夫:404)伍尔夫的观念具有的先驱意义在于,她第一次将女性视角的缺失与语言联系起来,暗示我们所知道的语言妨碍了女性表达,指出要容纳女性的思想,须先从语言层面进行变革。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美女性主义批评家进一步揭露以往文学史缺乏女性观点,没有真实表现妇女的生命状态,同时积极探索妇女写作抵抗现实遮蔽的可能性和策略。法国女性主义在理论建设上一马当先,把“女性”作为一种话语类型加以建构,用以抵抗传统话语的男女等级制和二元对立思想。本文尝试分析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苏和威蒂格分别在其著述中表达的“女性书写”和“女同性恋书写”的思想,探讨两种女性话语重建模式所蕴含的颠覆力量,并且通过对比揭示其局限性。
一
说起法国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家,人们的目光一般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和西苏(Hélène Cixous)。她们三人之所以能代表法国女性主义,与她们利用后结构主义的武器挑战男权文化传统,推动女性主义理论建设的突出成就密不可分。(李银河:59,63,71)女性话语是女性意识的反映,对于重建女性话语而言,拉康有关语言的精神分析和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三位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根据拉康关于象征界(the Symbolic)的中心能指是阳具的表述,指出我们使用的语言在结构上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phallocentric,即阳具崇拜的)。而德里达对优待言说而贬抑书写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批判,最终促成了第三个术语的出现,即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意思是西方的文化传统既具有男权中心的特点,又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根基。这种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化制造出各种对立的概念:男/女、阴/阳、秩序/混乱、主动/被动、在场/缺场、言说/书写、光明/黑暗、理智/情感等等,从语言和文化上建构起对阳性和男权的崇尚。
按照拉康的精神分析范式,儿童必须与母亲的身体(现实界)分离,方可进入语言王国(象征界)。顺着这个逻辑,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母亲的身体,广而推之女性的身体,进而包括女人的性,都是现有语言无法表现的,或者说在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象征界无法被言说和书写。结果对于妇女来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按照男人想象和表现妇女的方式表达自己(即她们可以开口,但要像男人那样说话),要么就选择“沉默”,成为看不着、听不见的性别。
当女性的自我表达在语言的桎梏中似乎山穷水尽之时,从语言内部寻找突破,建构一种“女性的”写作,其颠覆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早期的妇女文学评论家已经注意到,妇女的文学创作在主题、体裁、形象和风格上,都存在一些有别于男性作家的特征。克里斯蒂瓦发现女性的语言具有节奏感强和多种表意手段一体化的特点(“rhythmic and unifying”),她对语言结构中的符号要素(the semiotics)的论述,为后来构想女性语言、颠覆象征界的男性权威开启了一扇门。继克里斯蒂瓦之后,西苏发出了建构女性语言的理论强音,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她首次使用了“女性书写”概念。
二
“女性书写”是西苏解构了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后,为建立女性身体与语言的新联系而提出的策略。由于拉康关于象征界的表述将男性置于靠近菲勒斯中心能指的主体地位,女人处在象征界的边缘,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于是认为,女人更接近想象界(the Imaginary),距离固化和稳定的意义更远,与形象和幻想的距离更近;她们的语言较之于男性的语言,也是流动、无中心和开放式的。西苏说女人是流动的,在象征界的位置不及男人固定时,她是在两个层面谈论女人,既指字面意义上作为个体存在的女人,又指作为隐喻能指的“女人”。她呼吁“女人必须写自己”,“女人必须写女人”,不但意味着女人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写出自己的生活体验,而且还意味着作为能指的“女人”必须用新的方式与另一个能指“我”建立联系,在象征界之内书写女性的自我和主体。
这种新的方式,对于西苏而言,就是“写身体”(writing the body),她在堪称“女性书写”宣言的《美杜莎》一文中敦促女性作家:“写你自己,必须让人听见你的身体!”(Cixous:245-64)这里,西苏在女性书写与女人的性之间,假设了一种必然的联系。在多个文本中,她似乎都在强化这样一种印象,即,通过一种全新的书写,女性身体的特质和女性欲望分散和多形态的性质将改变旧的生活秩序。
要理解西苏的观点,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弗洛伊德对女人的性征说了什么。按照弗洛伊德的论述,女童必须经过从阴蒂到阴道的快感、从女性身体到男性身体的性吸引、从主动到被动的性体验等诸多转变,才能顺利过渡到“正常”的成年期。而在拉康对弗洛伊德的改写中,进入“成年期”就是成为一个语言主体(a linguistic subject)。在西苏看来,这一切只构成一种性,即被动的、阴道插入的、异性恋的、以生殖为目的的性,然而这种性其实不是女人自身的体验,而是出自男人的性,是男人想象中的女人的性,因此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系中不存在真正的女人的性;以建立女性视角、实现自我表达为主旨的女性书写因而必须(重新)主张以女性为中心的性,女人开始写作之前,要弄明白自己的快感究竟在何处。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曾经用一个隐喻等式,将象征写作特权的笔等同于象征界的中心能指阳具。对于女性语言及写作与女人的性之间的联系,西苏和伊丽格瑞的看法与吉尔伯特的比喻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她们认为,就像女人的快感是分散的、多形态的,指向不同的方向,她的语言也是散射的、流淌的,不纯粹依赖稳定固化的意义体系①——这个体系中起稳定固化作用的,恰恰是中心能指、单一快感的所在:阳具。
西苏本人的文章其实就是她提倡的新型书写的样板。她的文风以“无意识流”为特点,通篇流动着冗长的语句,关于子宫和乳汁的隐喻,以及俯拾皆是的涉及几种语言和语气的双关语。对于西苏而言,这种书写既是对女性身体的赞美,又是该身体欲望和冲动的产物。
由于女性书写基于女性特质,与女性身体相关,是新的语言主体地位建构的结果,西苏认为只有女人才能进行女性书写。这一概念具有强大的解构潜力,它是一种断裂(rupture),一个变化的场所,它对一个体系的总体性予以拆解,让人看清这个体系的结构,不再把它奉为“真理”或必然的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女性书写是一种进行内部解构的语言,它将抹去言语与文本、秩序与混乱、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界线,让使用它的人更贴近现实界(the Real),回归母亲的身体,回归与母亲非分离的状态;这应该就是西苏用“白色墨水”的隐喻,即用乳汁写作所要表达的意思。
虽然“女性书写”的概念蕴含着强大的解构力量,但是它表现出的明显的本质主义倾向受到很多其他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批评。(Jones:247-63)反本质主义的意见主要从社会建构论出发,抨击将女人的性当作女性固有的“自然”特征,以区别于与之相对立的男人的性。最近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大都强调,性认同绝不是在孤立或单纯的生理条件下形成的。建构论的观点认为,儿童的性别身份认同,取决于他/她在家庭生活环境中遇到的男人、女人和相应而树立的如何做男孩或女孩的观念。女童和她长大后变成女人的性征,终归不是来自孩提时她身体孤立的性感受力,其性感受力要受到她在性别化的世界中成长的一系列经历的诠释,这个过程正是孩童把得自后天的各种意义赋予其身体的过程。因此,从精神分析学中拿来身体冲动和力比多等概念,却闭口不谈儿童自我认知体系后天发生的事情,势必脱离男权中心社会维护其权力的根本靶心:性别化的家庭——是它首先在儿童的意识上烙下了性别化存在的印记。而建立在性差异基础上的“女性书写”概念,一方面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文化逻辑的男权思想,另一方面却颠倒对立两端原先被赋予的价值,使自身也陷入了男权文化逻辑,结果十分不利于深入了解妇女地位的历史成因,忽视了妇女推动深刻社会变革的重大作用。还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任何强调女性特质的概念都抹杀了不同年龄、国别、种族和阶级背景的妇女之间的生活差异,因而也掩盖了妇女遭受压迫的实质和复杂性。
“女性书写”理论有助于批判男权文化传统和语言结构,但是身体能成为新型话语的源泉吗?精神分析理论和社会生活经验似乎都暗示,从身体到语言的飞跃,对女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一个女人对快感的体验,是与自己身体之间的私密联系,而写作常常是为他人的。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谁写作、为谁写作、谁把女性的文本送到读者手中、一个女性读者想读到另一个女性的哪种经历,那么女性书写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女作家身体冲动和欲望流动的问题了。
三
妇女所受的压迫,从本质上讲,不是基于男女的生理差异,而是属于社会范畴,故而是一种可以改变的状况。正是在这一点上,威蒂格(Monique Wittig)表现出与西苏的思想分歧。威蒂格是活跃于与西苏同一时期的法国女性主义作家,但是女性语言和书写在西方文论界的盛名曾一时遮蔽了她的思想光芒,20世纪80和90年代以来,随着女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研究的异军突起,威蒂格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威蒂格同样关注如何通过拆解语言达到拆解男权制度的目的,也认为必须书写女性经验,将女性经验纳入主体意识,进而进入象征界的话语。然而不同的是,威蒂格的最终目的是消除“女人”这个概念。换言之,如果西苏拆解男权制度的策略是探索基于男女差异并彰显女性特质的某种独特的女性语言,那么威蒂格的矛头则直接指向压迫妇女的历史和物质基础。她坚持认为生理差别在历史决定的男权文化话语之外没有意义:“……两类个体之间任何根本的差异(包括性差异),任何构成对立概念的差异,都是属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范畴的差异。”(Wittig:115)当女性主体与语言的关系表现为书写时,书写必须正视男权文化的种种架构,包括将人类分别定义成“男人”和“女人”两大社会阶层的架构。因此对威蒂格来说,写作是政治行动,旨在为不是以性差异为基础的新型文化创建表达方式。她以一系列写作实践来表达有关话语重建的思想,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界一般冠之以“女同性恋书写”(lesbian writing)。
在威蒂格的女性书写理论里,lesbian一词是政治和社会阶级的指称,而不是性别身份或性偏好。女同性恋人群是指那些拒斥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对立和等级关系的人,她们尤其反对“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当威蒂格用“女同性恋”取代“女人”时,同样被抛弃的还有“母亲”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代表了长久以来被男性权力机器宰制和剥削的女性生殖力。尽管威蒂格的lesbian不具有性别和性偏好的内涵,但她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诗意的公正,因为迄今为止,作为话语主体的“人”在西方思想史上总是写成man(男人),所以威蒂格要用女性作为具有激进意义的未来话语的主体。
20世纪60和70年代,威蒂格发表了四部代表其“女同性恋书写”的文学作品:《愈伤草》(L'Opoponax,1964)、《女战士》(Les Guérillères,1969)、《女同性恋身体》(Le corps lesbian,1973)和与泽格(Sande Zeig)合著的《女同性恋词典的素材》(Brouillon pour un dictionnaire des amantes,1976)。在这些彻底抛弃女人刻板形象的虚构语境中,男人或是边缘存在,或是女人发动全面战争的对象,或是全然不在场。威蒂格的全女性世界使性别差异和性别范畴成为不相干的问题,从而临时构建起一种语境,让妇女成长为话语言说/命名的主体。
威蒂格的话语重建实践首先体现在她对传统文学体裁的反叛。通观四部作品,不难看出她不满足于退守女性作家常见的创作体裁——很多“女性书写”文本依托的小说、回忆录、自传等;相反,威蒂格宁愿挪用那些传统上为男性作家偏爱的文学体裁,颠倒其塑造和反映男性语言及现实的力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此,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一类主要文学体裁的改写和重新界定。《愈伤草》开启了女童挑战并超越性别社会化的潜能,成为新型的女性“成长小说”;《女战士》嘲讽传统史诗讴歌男人组成大军为上帝、君王、国家征战,而把女人留在家中远离战场的定式;而在这部作品中,恰恰是妇女组成军队去歼灭激发史诗体裁的父权制。《女同性恋身体》对《圣经》的雅歌和西方神话进行了改写和矫正;而《女同性恋词典的素材》则尝试创造一部词典,重新定义我们使用的词语。在威蒂格的笔下,成长小说、英雄史诗、圣经、词典这些男权话语的强大工具都被颠覆,从而利于另一种话语的诞生。
为了进一步拆解传统男性话语的性别限制,威蒂格大胆尝试代词和名词的新用法。例如《愈伤草》大量使用中性人称代词on(有些类似于英语中的one,即泛指的“人”、“某人”,有时可以作“你”解)。在小说的特定语境下,on有时指代的是主人公——全名叫凯瑟琳,勒格朗的小女孩,用法相当于“我”;有时它指代全体小孩,用法相当于“他们”;有时指代凯瑟琳·勒格朗和瓦拉莉·博热的二人组合,相当于“我们”。On消除了其他人称代词具有的严格的性、数意义,创造出一个准乌托邦的自由地带,让这些小姑娘能够在性别差异的社会化限制之外成长。贯穿《女战士》全文的是阴性复数代词elles(“她们”),指代书中的女性主人公集体,以此强调女人这一概念指涉的是一个历史上的社会阶级,而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本质。而“女人”一词在整个法语文本中几乎完全消失,从而达到削弱这个名词的传统用法和与之共生的角色和行为预设。在拼写法语“女战士”一词时,威蒂格故意违抗传统拼写法guérrières,杜撰新词guérillères,生成新的概念。她改写原词,在其中加入双写的ll,强调双写字母在elles中的出现,点出这些女战士们不同一般,有着反体制的无政府主义的战斗策略。在《女同性恋身体》中,对“你”(tu)讲话的“我”(je)被写成了j/e,所有第一人称单数物主形容词中间都插入一道斜线:m/on,m/a,m/es,凸现欲成为话语主体的女性自我内在的(精神)分裂性。最后,在《女同性恋词典的素材》中,关于“女人”的这些见解汇集起来,形成对“女人”和“母亲”等词语/概念的重新定义。在威蒂格和她的合著者泽格想象的时空中,旧语言的遗迹已随父权时代的终结而被抛诸脑后,女性同胞都变成了女勇士(amazones)和女恋人(amantes)。
1978年,威蒂格在纽约现代语言协会年会上宣读论文《异性恋头脑》,②指出异性恋思想对性范畴和性别差异的决定性影响。她认为“女人”是男权思想制度创造的超级神话,时至今日一直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和反对同性恋的恶毒话语中延续着。这些话语的基础就是所谓的“异性恋”头脑和这样一些关键词/概念:“女人”、“男人”、“差异”以及“历史”、“文化”、“真实”等等。这些词语/概念力图创建一般法则,使之在一切社会和所有时期普遍适用。“异性恋”头脑无法想象在任何方面存在着非绝对异性恋的社会或文化,因此把异性恋当作强制性的要求:你必然是异性恋,否则你不能存在。于是,威蒂格提出了一个解决语言和语言权力问题的临时办法,既然语言是创造并延续“女人”神话的东西,就有必要对语言、对“女人”、“男人”等概念进行政治改造。
在威蒂格创建的全女性语境和文本中,女性已经打破了男权社会和文化禁止她们相爱和自爱的戒律。《愈伤草》中凯瑟琳·勒格朗和小伙伴瓦拉莉·博热在教会学校极力抵制性别社会化,她们通过读诗滋养彼此的爱慕。《女战士》里受压迫的妇女有了阶级觉悟,并且针对男女之间实实在在的社会差异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对象也包括维持男女差异的那些话语,例如,小说虽没提及但却无处不在的弗洛伊德、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文本所构建的话语。对“女性书写”不可或缺的女性身体崇拜在这里遭到拒斥,在威蒂格看来,身体从来不是写作行为的隐喻,“女同性恋书写”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消除男权文化强加于女性身体的沉重的隐喻和意象之累,恢复女性身体的完整。因此,威蒂格的文本把身体的每一部分及其产物都表现为同样的赏心悦目,这种迥异于以前文学作品的新话语直接挑战读者习以为常的男性话语对女性身体的割裂,反对男性话语将它划分成性感撩人的部分和令人不快的部分。威蒂格拒斥关于身体的所有象征和比喻,藉此颠覆把女人作为性欲对象而禁锢于他者地位的语言。
四
“写身体”是法国女性主义发出的最急迫和最有争议的号召。它在欧美引发的论争决定了建构女性主义未来设想的两种见解,这两种见解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身体与语言的关系,使我们得以了解法国女性主义颠覆现存秩序、改变未来潜力和它们承袭过去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和局限。
西苏与威蒂格的书写思想体现了两种见解在文化层面上书写女性经验的个人需求和抵制“女性本质”的政治需要之间的张力。她们的出发点不乏相同之处:两人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压迫,主张追求更合理的社会秩序;两人也同时将这种对新秩序的追求寄寓于深刻的语言和书写变革,而变革的语言和书写又始于对身体的反思。然而,正是在表述身体、语言与未来的关系时,两位女性主义作家表现出重大分歧。
西苏的“女性写作”以性差异驱动语言变革,把对语言的关注落在精神分析学提供的俄狄浦斯话语之内。西苏赞美的未来可以藉女性书写最终表达女性特有的无意识欲望,通过有别于传统(男性)逻辑、语言和文化形式的另一种选择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然而在威蒂格看来,未来的前景恰恰在于彻底推翻西苏探索和颂扬的那些基本差异。西苏把女性书写与某种女性特有的生理/心理冲动联系起来,通过普遍的生物性假定来界定女性主体性,其中的本质主义倾向昭然若揭。当书写的欲望被等同于女性力比多,尤其是母性冲动时,我们仿佛听到弗洛伊德关于缺失的话语在回响:由于阳具缺失,小女孩希望生下父亲的孩子,并最终靠接受以阳具为中心能指的语言系统来为其存在赋予意义。这样的回响当然会让“女性书写”的颠覆性大打折扣。
威蒂格的女战士既前瞻新世界,又追思“压迫前时代”。她设想“堕落前的”状态意味着这个状态并不是真正的历史时刻,而是把压迫视为“非自然的”社会建构的概念。应该指出,设想现存腐朽制度之前必然存在着原初的(尽管也是虚构的)平等公正的时刻,这无疑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失去的天真”的哲学玄想。虽然威蒂格极力抵制本质主义的生理决定论,但是她也难免要从父权传统中借用同样理想主义的和同样可疑的一些思路。尽管如此,威蒂格对未来的设想也有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因为她强调把性差异问题纳入阶级斗争范畴,视之为政治上社会集团之间的压迫问题。对威蒂格而言,反对压迫的惟一出路是彻底重组得到承认的标准语言、文学形式和关于身体“本质”的观念。如果说威蒂格秉承黑格尔精神的地方表现出某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那么她将压迫视为非自然的建构物,则体现了积极的行动姿态,为运动、变化和进步的可能性开启了门户,不管最终的进步距离我们多么遥远。
注释:
①参见Luce Irigagray,"Ce Sexe qui n'en est pas un"和Hélène Cixous,"Le Rire de la Méduse",both translated in New French Feminisms,pp.103-05,259-60.
②这篇文章已经以《正常的心灵》为标题由李银河全文翻译成中文,收入她的译文集《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笔者把标题The Straight Mind译作《异性恋头脑》,以利此处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