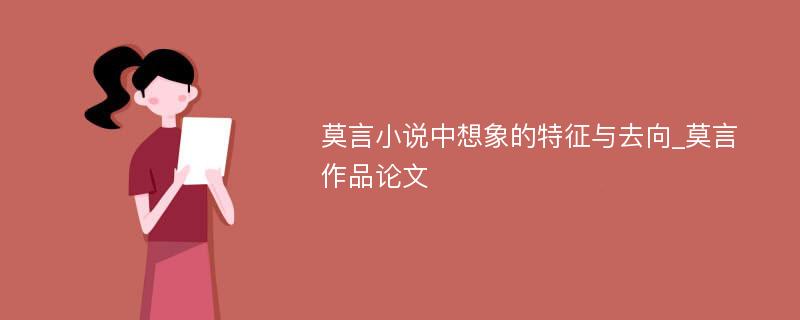
莫言小说想象力的特征与行踪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踪论文,想象力论文,特征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由异域发现中国,经由先锋发现民间
将近十年前,我在与朋友以莫言为例讨论“文学中的民间精神”时说:“从民间的角度解读莫言不是唯一的角度,却可能是最切中要害的一个角度。”②十年来,莫言的创作迭有发展,这一判断却并没有过时。不过今天回顾莫言的整个创作,我们发现,民间因素在莫言作品中的敞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程,中间的关键,是借径于当时引介的异域现代主义文学及与之相关的当时中国的探索文学思潮的刺激,发现莫言自己独特的来历与独有的世界。
莫言创作标志性的改变发生在1985年。此前他的尝试性写作,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之处(譬如民间性因素的尝试性萌发),但总体上尚不脱当时文坛的基本格调。1985年,莫言的创作发生彻底转变,先是发表实验性的文本《透明的红萝卜》,继而在《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老枪》、《草鞋窨子》等作品中,一个活生生的民间世界初步跃出水面。1986年,他在《人民文学》第8期发表著名的《红高粱》,兹后接续写出后来汇为《红高粱家族》的系列小说,莫言迅速成为一个具有独特面貌的作家,并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贡献出一系列的重要作品,成熟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1985年当然是一个广为人知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影响延续至今。从历史上看,“先锋文学”潮流,相关于西方现代文学对中国当AI写作作的影响和启发,这一影响与启发的作用是巨大的。考虑到中国文学在当时借之获得的语言实验、叙事革命以及相关的对既定世界图景的突破,说是革命性的也不为过。“寻根文学”思潮,当时虽冠以“文化寻根”的名号,实际上在当时除阿城对传统文化的核心智慧有所体会之外,更多的作家关注的其实是经由底层民间经验而来的本土民俗性因素的发掘。莫言并未自外于这两条在当时充满活力的文学路线,他的创作中这两种因素互相交织,但也各有偏重,形成两个系列。《透明的红萝卜》、《红蝗》及由之发展出的《食草家族》,更加接近探索性的先锋文学思路。《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老枪》、《草鞋窨子》等作品,则更为偏重于本土民间经验的呈现与表达。当时乃至事后,都有评论家把莫言当时的写作放到“先锋文学”与“寻根文学”的框架中进行探讨,但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两个框架对于莫言来说都太小,远不足以容纳其作品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从今天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的文学潮流对莫言最大的影响,是促使他有了独特的觉醒、解放与发现。换句话说,文学影响与时代潮流的刺激,导致的不是使他模仿与发现别人,而是发现自己——自己的来历与自己独有的世界。在这之后,莫言之为莫言的独到与不可替代之处,才真正站立了起来。它提供的能量,支撑莫言的写作持续至今,仍未见有衰歇之势。而对自己的独特之处,莫言其实有非常清楚的自觉。以外来影响而言,莫言从未否认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他的巨大影响,但他没有简单地摹仿这些作家。他曾经这样说过:“我比很多中国作家高明的是,我并不刻意地去摹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世界的看法。”譬如福克纳,他欣赏的是“他那种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③这与马尔克斯当年从卡夫卡那里受到的启发简直如出一辙。马尔克斯也是在十七岁时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发现小说“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我认为他是采用我外祖母的那种方法用德语来讲述故事的。”④兹后拉丁美洲的经验、记忆和感觉、想象方式源源不断地涌到马尔克斯笔下,成就了一代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大师。事实上,从影响的角度看,从先辈作家那里获得启发乃至解放的作用,要远比直接的摹仿高明几个层次。回头来看莫言,如果说他受到这些作家的影响的话,他其实是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种启发、一种胆量,从而自由地解放自己的感觉、体验、想象乃至语言和叙述,而尤为重要的,则是让他重新发现了自己所从来、自己也一直生活于其间的活生生的民间世界。可以说,世界文学的启发给莫言的写作打开了一道闸门,使得民间的生活经验与生命气息在他笔下源源不断地流动起来。
文学影响与时代潮流的刺激,导致的不是使他模仿与发现别人,而是发现自己——自己的来历与自己独有的世界
文学史上曾经有很多作家有过类似的发现自己的经验,譬如沈从文,也是在早期杂乱无章的摸索之后,发现故乡才是自己永远抒写不完并进一步思考、成长的基地,此后的写作方呈现出独特的面目。⑤若与前辈作家的类似经验相比,莫言一辈作家的独特之处,是这一发现经由了域外现代主义文学(在当时中国成为先锋作家最主要的借鉴对象)的刺激。这一借径有利有弊,好的一方面是带来了语言、感觉、叙述、观念及世界图景的全方位解放,坏的一面是刻意借鉴而来的尖锐、怪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形式,无论如何还是有种种束缚作用。坏的方面后面再谈,先谈前一方面。对莫言来说,这一觉醒、解放与发现的最大作用,乃是经由这一刺激,让他发现了自己生存的、被此前种种叙述遮蔽着的中国,经由貌似高蹈的先锋文学的形式革命,发现了自己所从来、自己也一直置身其间的民间世界。如果说在感觉与叙述方面,莫言与一代青年写作者共享了这一解放作用,他笔下那个不受任何现成框架羁绊的鲜活的民间世界,在当时却是独此一家。任何熟读《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老枪》,尤其是《草鞋窨子》、《飞艇》、《苍蝇·门牙》、《红高粱》等小说的读者可能都不会忘记最初看到这些小说时的激动。这里面没有了前一个时期中国小说写民间世界时的迂腐、冬烘与矫情,更没有此前被种种条条框框束缚着的紧身衣,一切都是那么舒展、随意、放肆、有声有色,伴随着感觉、叙述与观念的解放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民间实感世界的解放。时至今日,莫言在这一方面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其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大致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文学中的“民间”问题就成为文坛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莫言也常常被当作其中的一个典型来讨论。⑥如果不纠缠于过多琐细的争辩,更值得追问的问题其实可能在于:民间到底为文学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看来很清楚,首先就是不可替代的“实感经验”。中国新文学自萌发以来,域外观念、文化、文学的刺激始终超过对本身经验的忠实。这种刺激即使到现在,也是我们文学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动力。但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种新的创造的新文学,一开始并没有与民间生活、民间大地建立有效的联系。与生活世界中断联系,这种缺失是致命的,观念的移植很容易,背后的实感却很难从别人那里借取——而这种实感,才是文学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来源。
与生活世界中断联系,这种缺失是致命的,观念的移植很容易,背后的实感却很难从别人那里借取——而这种实感,才是文学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来源
我比较相信鲁迅说过的话: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学。⑦在这个意义上,我很看重像沈从文和莫言这样的来自民间的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的新的质素。这种新的质素,首先就是来自民间生活的“实感”经验。我曾比较沈从文的《萧萧》和五四时期蹇先艾著名的短篇《水葬》,《水葬》里单一的启蒙主题,处处显示出理念的痕迹,可是在《萧萧》里,各种感觉是混合在一起的,显示出丰富的旋律和变调。有没有这种丰富的旋律和变调,可以说是一部作品是不是浸润着生活实感的很重要的标志。实际上,来自民间生活的实感经验,使我们的文学不再是单纯的个人感觉、思想、情感和想象的表达,而是获得了一种来自生活世界的深度和厚度。这种与民间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与单纯表达个人理念和情感的作品相比,其中自有轻重之分,厚薄之别。表面上看,沈从文与莫言的区别很大:同样是写乡村,沈从文捕捉的是乡土中国人情风俗的美,其中有他自己的切身体验,也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莫言构筑的高密东北乡,也是一个想象空间,却更能体现藏污纳垢、有容乃大、贫穷艰难却生机勃勃的民间本相。然而话说回来,他们的区别可能并没有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这么大,不论他们的作品表面风格的区别如何明显,我们都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来自民间大地的“实感”——这与他们同为来自底层民间的作家是分不开的。所以,沈从文钩沉的民间的人情风俗的美,他所建造的理想世界,主要的旋律之外始终有其他的音调——乡野的、悲苦的、忧伤的变调与和弦;而不论莫言如何着力表现乡村的艰难荒蛮、藏污纳垢,野腔野调之中始终能够让人感受到来自大地的生命的流淌与呼喊。来自民间的切身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的作品有丰富的变调与和弦,这在没有民间生活实感的作家那里是极为缺乏的。他们的成败得失,可能都会对以后的中国作家吸收民间生活世界的营养提供可贵的经验与教训。
文学与民间接通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接地气”问题),除了接续“实感经验”的源头活水之外,也会获得来自民间的丰厚的文化资源的支撑,譬如说民间的信仰、想象、记忆和生活方式,可以说积淀了非常重要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莫言接续了中国的这一“小传统”,其“野语村言”也便得到了来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源源不断的供给与营养。不过在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不妨先检视一下莫言小说中表现出的想象力的两个特征。一般来说,想象力可能会被更多地当做作家个人的特质,然而检视莫言想象力的两个典型方面,我们会发现,这两个特征其实与他的文学所从来的两个来源——民间世界与文学写作资源——有着隐蔽却非常密切的联系。
二、“欢乐”与“阴郁”,“嬉戏”与“怪诞”
阅读莫言小说,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色调,一种是明亮的、欢乐的,一种是阴郁的、怪诞的。似乎作为小说家的莫言,内心里面有一个“顽童”,也有一个“愤怒的青年”(或“感时忧国”的书生),由此也自然让他的想象力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顽童式的想象力,把严肃的、重大的事情,变为一场游戏与狂欢,消解了其中的严重性,而化为生命力的张扬;一是阴郁、荒诞的想象力,其色调之凄厉,想象之怪诞,表达之极端,经常挑战着人的承受力的极限——对不义的愤怒,经常让他的写作夸张变形,有着非常极端的想象(经常是对“恶”的极端想象),于是在他的小说中便经常出现类似于来自地狱边缘的非人间的风景——莫言有时甚至会表现出沉溺于这种风景的倾向。莫言想象力的这两种倾向,在他的写作获得自我解放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此后则迭有发展。第一种倾向,我想以较早的《草鞋窨子》(1985)、《飞艇》(1986)和后来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1998)及近些年写作的《生死疲劳》(2006)作为代表。第二种倾向,我想以《十三步》(1988)、《酒国》(1993)、《四十一炮》(2003)和莫言最新的长篇《蛙》(2010)作为代表。
来自民间的切身的生活经验,使得他们的作品有丰富的变调与和弦,这在没有民间生活实感的作家那里是极为缺乏的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尽管此前已有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开始摆脱此前的意识形态束缚来呈现民间生活,莫言的《草鞋窨子》和《飞艇》等小说的出现,却自有其不可代替的意义。汪曾祺延续了沈从文的写作路线(也对之做了一定程度的纯化),表现民间生活的同时也寄托着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带有一定程度的文人色彩;莫言的这两部作品,则更能体现民间的本色,尤其其中包含着某种兴高采烈的意味,显示出普通民间粗糙简陋甚或艰难的生活中,本身便包含着生命力的恣肆张扬。这两部小说都接近于速写,《草鞋窨子》更容易被误解为谈狐说鬼的小品,实则其中连通了一个一直被遮蔽着的民间生活和想象的世界,夸大一点,甚至可以说,它复活了一种传统,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应太低。小说的结构很简单,辍学的少年我在五叔、六叔的草鞋窨子里学习编草鞋,其中会来一些村中闲汉像于大身、小轱辘子来闲聊,中间穿插着小贩薛不善进来卖香烟零食,而以小轱辘子冒充薛不善去调戏他的害雀盲眼的女人被后者刺伤返回草鞋窨子结束。结构非常松散,完全是一个乡村闲谈的生活场景,不过细察的话,则不难看出其中实不乏巧妙,恰恰是这样的结构才能够充分且自然地容纳三五乡人谈狐说鬼的“乡村怪谈”——而后者无疑是这篇小说的重心。这些“怪谈”,有些是传说,有些据说是亲历,而不论是传说或亲历,都是“齐东野语”,不可究诘,一般人也不会究诘,随便谈谈,高兴高兴也就算了。不过仔细分辨,这些“野语村言”,其中也有不同的色调,有的偏于嬉戏,有些偏于恐怖,前者像小轱辘子说的“话皮子挂号”的故事、于大身自称的卖虾酱时碰到的泼辣女人“大白鹅”的故事,后者像五叔说的阴宅闹鬼的故事、于大身说的扫帚成精的故事。然而不论恐怖还是戏谈(更多是恐怖与嬉戏融合起来),在小说中写来都带着某种神采飞扬,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沟通了某一不登大雅之堂的隐秘世界,有一种触及日常生活边界的未知与禁忌的好奇与兴奋——就此而言,“草鞋窨子”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象征。这是一个日常意识之下的集体无意识的世界,也是一个被正统(尤其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排除与压抑在地下的民间想象世界,“齐东野语”的闲谈让这一世界呈现出来,让读者赫然发现,原来写作可以这么无需承载过多的外加意义,也可以这么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却也自然而然地有着释放、疏解与逃离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这倒是中国“小说”古来的传统,⑧但这一点先按下不表,且来关注一下这篇小说中某种欢悦与兴奋的语调。小说中的“怪谈”,一开始就是极为精彩的小轱辘子讲的“话皮子”的故事——这个精彩的故事为后面一系列精彩的“野语”开了个好头——一种像黄鼠狼一样会说人话的精灵,月夜站在墙头让人“挂号”(做鉴定的意思——人说:你会走了,它就真的会走了)。其实是有些怪异恐怖的,然而故事的气氛随后发生了陡转,张老三一砖头把那堵墙给打倒了,话皮子喊一声娘落荒而逃,更精彩的在后头:
“后来每逢傍晚,那个‘话皮子’就带着一群‘话皮子’在断墙那儿喊:‘哎哟地,哎哟天,从西来了张老三;哎哟爹,哎哟娘,一砖打倒一堵墙……’袁家五叔说,他小时候好像唱过这个歌。”
话皮子的故事当然不可究诘,不过民间话语就有这种力量,可以把恐怖的想象化为欢乐的笑声,让本来沉重郁结的压力得到纾解。《草鞋窨子》中的故事,不少就有类似的结构,像于大身遭遇“大白鹅”的故事,像小轱辘子讲的高密南乡的老婆子让闺女逃脱蜘蛛精的荼毒的故事,从正统的观点当然略显粗鄙,然而这里难道就没有某种特定的精神治疗的作用,没有某种民间自发产生的智慧?
然而不论恐怖还是戏谈,在小说中写来都带着某种神采飞扬,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沟通了某一不登大雅之堂的隐秘世界
这种笑声延续在《飞艇》、《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生死疲劳》等一系列小说之中,成为莫言作品特有的一种声调。从通常的眼光看,《飞艇》写的其实是一件严重的事故(飞艇爆炸坠落),小说中的人们生活也一点都不好(背景是“文革”年代,村人们要出外讨饭),然而贯串在作品中的笑声,把严重的事故与艰难的生活都化为了生命力飞扬的欢悦,像一群讨饭的孩子喊着要操“冷的娘”、“热的爹”,像他们看到飞艇坠落时的即兴创作,像方家七老妈不自觉地把忆苦化为了表演与戏说……这个小说中的某些细节,换个语境,其实会让人反感的(像对方家七老妈被飞艇碎片击死的婴儿的描述),然而在文本特有的生命力飞扬的叙述脉络中,它们都在某种欢快的语调中消解了沉重与压抑,生发出某种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的氛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若从故事的骨干来看,乃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也颇有些苦涩、同时有些触犯禁忌(如朱老师为爱人治病偷种大烟)的故事,然而在莫言讲来,同样兴兴头头、妙趣横生。小说的写法也颇不合常规,交代背景和人物的“小引”和“大引”,几乎占了小说的一半篇幅,而“正文”的绝大部分,也是炫技式的对比赛的描写,真正可以称为情节的“正文”最后不到二页的篇幅,结尾抖开的包袱则凭空为阅读增加了悬念与遐想——在整个小说中,莫言几乎表现出一种民间说书艺人的才能(比照扬州评话艺人说书,单单一个下楼就能讲几个小时),关注的不仅是故事,更是细节与氛围,从一个简单的故事中引出了整个世界,制造出一种特殊的兴兴头头的气氛。《生死疲劳》也一样,仅有最后的部分由于莫言对新时代的迷惘而显示出阴郁、绝望的色调。小说的绝大部分由于叙述者轮回转世成驴、牛、猪、狗等动物的故事非常精彩,化解了严重与严肃,也有着某种戏谑与狂欢的氛围。不用说,小说的主线是非常严肃的,其中孤独面对整个时代的农民形象,更是有着某种悲剧英雄的特点。曾有评论者说,小说中太为精彩的动物故事喧宾夺主,掩盖了全书写六十年乡村编年史的严肃性。我曾经也同意这种意见,现在回头来想,放在莫言小说游戏与狂欢的脉络中来考察,这一现象其实也不难理解,莫言是不自觉地又受到这种精神的吸引,把严肃、沉重化为了叙述与想象中生命力的舞蹈狂欢,把随时可能伴随严肃而来的石化的危险,化为了复活的欣悦……若按照巴赫金的说法,狂欢节的精神本身有着世界观乃至宇宙观的意义,莫言的这一类作品,岂非感通了这一精神?——虽说中国并不存在西方历史上的那种狂欢节,但民间并不缺少类似的节庆感受。这类小说的不合常规(譬如轻故事,轻主要线索,重细节,重氛围),岂非恰好呈现出了一整个民间世界的气氛及其生命感受?
莫言几乎表现出一种民间说书艺人的才能,关注的不仅是故事,更是细节与氛围,从一个简单的故事中引出了整个世界,制造出一种特殊的兴兴头头的气氛
不过如果就此仅仅把莫言看作一个“狂欢化”的作家,我们却要遭遇莫言的另一类作品中阴郁、怪诞的想象的挑战。这里面,最为典型的可能要推《十三步》与《酒国》中的极端想象。我一直觉得,《十三步》是莫言的一部被忽略了的杰作,今天重新读来,虽已不似当年初读时那么震撼,然而其阴森怪异的世界,仍是一次极端的阅读体验:像物理教师方富贵晕倒后被当作死人推进火葬场然后又从停尸房逃离的情节,像殡仪馆的整容师李玉婵为尸体整容及把死人脂肪带去动物园饲养猛兽的情节,像复活的方富贵与同事张红球改换面容的情节,像李玉婵与王副市长及猛兽管理员之间畸形的情感纠缠,像张红球最后进入动物园笼中以粉笔为食滔滔不绝叙述整个故事的情节……整部小说弥漫着一种腐烂、恶臭的气味,其基本的氛围则是阴森、狞厉的,包容着巨大的黑暗与愤怒,预示着恐怖和不祥。与此相对的,则是小说在叙述艺术层面的丰富成功,几乎是莫言在技术上最为复杂有机的小说,叙述人称转换的复杂圆熟更是与小说中想象的怪诞极端相辅相成,共同营造出迷离恍惚的阅读效果……如果说要代表莫言想象力阴森、怪诞、狞厉的一面,可能并不是广为人知的《红高粱》中剥人皮的场景,也不是《檀香刑》中对施行酷刑的细致描绘,而是《十三步》中整体上变形的怪诞、恐怖的世界——在莫言的创作中,能够与此匹敌的,可能唯有《酒国》中想象的“食婴”故事。莫言在前些年的一次谈话中,承认《酒国》中的这一想象,受到鲁迅小说中的“吃人”意象的启发,⑨当然我们也马上会联想到鲁迅的“人肉筵席”的著名论述。这当然指出了莫言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感时忧国”、批判现实的精神的联系,然而如果看小说中恣意挥洒的阴暗想象,你也很难说,莫言无形中为这种阴森狞厉的想象所吸引——对于特定创作个体特定的时空来说,这种想象未必不会在无意中显示出恶魔般的吸引力。《酒国》的结构虽不似《十三步》那么复杂有机,却也颇具匠心。现实中侦查员丁钩儿侦破食婴案是一条线索,酒博士李一斗寄给“作家莫言”的小说习作中叙述的“食婴”故事和带领婴儿们反抗的小妖精出没的场景等则是另一条线索。两条线索以丁钩儿走出烈士陵园在幻觉中步入粪池淹死和“作家莫言”进入酒国与李光斗和一干地方官员酒会的场景结束,现实与虚构在结尾合龙,小说中的故事真耶、幻耶,一时也恍惚迷离,难以分辨。不过从阅读效果来看,至少可以说,小说中的极端想象,不仅在象征层面唤起读者的理性反思,也在感性层面引起读者肉体上的厌恶感,若说引起读者的感性反应本是艺术的一种功能,莫言可以说把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莫言对阴森、恐怖、怪诞的意象和场景的偏好似乎是一贯的,此前的《红高粱》中“剥人皮”场景已发其端绪,此后的《檀香刑》中对酷刑的描述、《四十一炮》中对“注水肉”(甚至注福尔马林液)的描写继其端绪,新近的例子也许是《蛙》中姑姑夜归遭遇蛙群(被她强制流产的婴儿们的化身)包围的阴森场景,在在都显示出他对这一类想象有一种隐秘的兴趣。这类想象如此阴森极端,其描述的详尽、恣肆更显然不符合艺术上中和节制的古典标准,从美学上如何对此进行界定和判断,此种想象背后的动力为何?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若说引起读者的感性反应本是艺术的一种功能,莫言可以说把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评论界讨论莫言后一类创作,一般马上会联系到中国学界耳熟能详的巴赫金的“怪诞现实主义”,我对此却始终持有某种保留态度。莫言的这些作品的确可以称为“怪诞”的作品,也确实有着现实批判的锋芒,却缺少巴赫金所谓的“怪诞现实主义”既“毁灭、否定”,同时也“肯定、再生”的意义,它们更偏向于整体的荒诞和否定,更适合用沃尔夫冈·凯泽尔的“怪诞”理论来描述。关于“怪诞”的性质,凯泽尔是这样说的:“怪诞是异化的世界。”“……潜藏和埋伏在我们的世界里的黑暗势力使世界异化,给人们带来绝望和恐怖。尽管如此,真正的艺术描绘暗中产生了解放的效果。黑幕揭开了,凶恶的魔鬼暴露了,不可理解的势力受到了挑战。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对怪诞的最后解释:一种唤出并克服世界的凶险方面的尝试。”⑩可以看出,不需过多的解释,这个论述便可以充分解释莫言想象力的第二个方面。不过,问题并未就此结束,我们仍需要对这种怪诞的性质、来源和位置加以界定。我同意巴赫金对于凯泽尔怪诞研究的评论,凯泽尔的研究实际上只适用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怪诞风格,严格说只是现代主义的怪诞风格”(因为他“是通过现代主义怪诞风格的三棱镜来观察浪漫主义风格的”),而与此前的怪诞风格格格不入。古典时期的怪诞需要另外研究,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怪诞风格,巴赫金则颇为敏锐地指出,有着“与民间诙谐文化和狂欢节世界感受完整世界的不可分离的真正本性”,(11)由此所产生的作为“怪诞现实主义”的标志性特征的“降格”和“贬低化”等,“不仅具有毁灭、否定的意义,而且也具有肯定的、再生的意义:它是双重性的,它同时既否定又肯定。这不单纯是抛下,使之不存在,绝对消灭,不,这是打入生产下部,就是那个孕育和诞生新生命的下部,万物都由此繁茂生长……”(12)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把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怪诞风格看作“怪诞现实主义”退化,浪漫主义的怪诞风格已然遁入个人主观感受和想象领域,却仍保留了对此前怪诞风格的民间和节庆来源的记忆。现代主义的怪诞风格则将怪诞完全形式化,固然借此获得了尖锐与刺激之力,却抹去了其本所负载的民间节庆感受的意义,因而不免落入了凯泽尔所描述的以“阴暗、恐怖和可怕的音调”为基调的“令人震惊”的“陌生”的“怪诞世界”——“这种音调与怪诞风格在浪漫主义之前的整个发展绝对是格格不入的”。(13)
关于莫言小说想象力的这两个方面的特征,一直是萦绕在笔者心头的问题,此前对其朦朦胧胧的感觉,现在借助巴赫金和凯泽尔的理论,终于能够比较清楚地进行描述和解说。(14)一直以来,我以为这两种风格之间乃是并列或平行的关系,现在参照巴赫金的有关研究,可以赫然发现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承续和演化关系,其间隐秘的联系,远比我们可能意识到的紧密。从历史上看,前者牵涉到与民间大地的生命感受浑而未分的关系,后者则相关于个体独立意识和艺术独立意识的产生(浪漫主义之后的东西),问题现在变得很清楚,就是如何从后者的演变所导致的窒碍、狭窄、幽暗与封闭中解放出来,还返到与民间大地的生命感受更为充分的交流和更深层次的感通上去。巴赫金对广场上欢笑的人民大众的节日感受(巴赫金将之上升到世界观、宇宙观的层次)的描述对此不乏启发作用:它“是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危机、转折关头相联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因素永远是节庆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15)也因此,它具有一体两面的性格,充满了游戏精神和解放冲动,加冕脱冕、戏仿亵渎、插科打诨、不拘一格,而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它们与突破种种桎梏压抑的生命的发展的总体性冲动联系在一起,因而永不会向隅孤立,也永无止息,永未完成,封闭、悲观绝不会成为它的基调:“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一般说来,赤裸裸的否定是与民间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16)
事实上,借助巴赫金与凯泽尔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莫言的后一类小说,在整体上正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的怪诞风格,虽然其中也延续着五四新文学批判现实的精神以及来自民间集体无意识的想象传统(譬如《十三步》中的怪谈与《酒国》中出没着的“小妖精”形象),但前者的尖锐、刺激、怪异、刻意引起人的震惊感的形式诉求,却无疑对来源于民间的生命活力,形成了严重的窒碍。若进一步扩展来看莫言的写作资源,其最基本的生命感受和文化资源,无疑是来自民间大地的实感经验和文化传统,莫言对此有极为深入的感通,并以此贯通了古来中国“小说”的传统。但其直接承续和从属的文学写作传统,却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和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集中吸收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而实际上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很早就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学精神与“怪诞”风格,所以这两种文学写作传统在强烈的质疑、否定精神和尖锐、极端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又可以重合起来——莫言的后一类小说,集中借鉴、吸收和契合的,也正是这一方面。而这一方面,事实上也是从“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中就萌发出来的中国先锋文学精神的两面——对环境的强烈的分裂、不适感,由之产生的质疑、否定意识和刻意在话语、形式方面的颠倒、翻转。从这几种文学资源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不是形式上的创新不需要,也不是批判与质疑现实的精神应该放弃,而是如何让来自民间大地的那种元气充沛的生命活力,不至受到太过尖锐、极端乃至局促的文学形式和批判精神的束缚的问题。如何由此创造一种更为具有弹性、灵活、包容的更有生命力的形式,这显然是摆在莫言乃至更为广泛的中国当代作家面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三、隐秘的线索与不尽的长流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讨论莫言创作中的民间资源问题。这一储存着民族集体无意识(包括民间信仰、想象、记忆、生活方式)的宝库,可以说是作家创作的无尽宝藏。莫言对此已有颇多的体会,并显然也有不少吸收。以民间想象为例,实际上,民间想象成分,在莫言一开始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时就有浓厚的体现。在《透明的红萝卜》、《草鞋窨子》这样的作品中,民间的想象与传说,直接构成了作品的内容,很像《聊斋志异》。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如《铁孩》中的孩子因为饥饿化作“铁精”以铁为食,《翱翔》中的人化为“飞鸟”,《红蝗》中的奇异家族,《十三步》中的死而复生,《酒国》中的以婴儿做菜等,作为作品的基本构思,不排除作家受中外文学中的想象和意象的影响,更不是要否定作家的个人特点和个人才能(莫言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但很明显是与民间想象的传统沟通的,乃至直接是从民间传说中撷取的。
古代中国的正统文学,一直不太强调想象的传统,这不是说中国人的想象力贫乏,只是由于强烈的理性传统,各种怪怪奇奇的传说和想象,只好流落到志怪、笔记、演义、戏曲等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属于边缘性的文体中去,或者就一直仅在民间口头流传。莫言的某些作品,譬如《草鞋窨子》、《飞艇》等,看起来就像是对民间传说或民间记忆的记录,从强调个人独创性的现代文学观念来看,似乎它们不大合乎正统,而跳到这种观念和传统产生之前去看,它们岂非正是中国小说乃至世界小说最初的传统?张新颖在近些年的讨论和发言中,曾经以《聊斋志异》为例,指出这些被我们后来认为是“小说经典”的作品,其实最初也并不强调虚构性和创造性,而只是一种“闲聊”的记录。(17)“闲聊”的内容,当然不外“街谈巷议”与“奇闻异事”。事实上,中西小说的起源莫不如此,参照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谓“小说家流,乃出于稗官”,记录的乃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而此后“志怪”之作,也并非意在创作,而在“志怪”、“传奇”。西方语言中表示小说的词汇,如“Romance”这个词,“即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种最后表示‘小说’的词——源于中世纪的副词romanice;romanice的意思就是用民间语言、而不是用学者的拉丁语来写作或讲话。”(18)而英语中表示小说的“Novel”一词,则有“新的,新颖的,新奇的”的意思;分别无形中与中国小说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和“志怪”、“志异”、“传奇”的意思暗合(19)。若再向上追溯到远古文化中的说唱艺人,正可说是人类远古以来一脉相承的文教传统——在诸多民族,这一传统都产生了史诗,在西方由于希腊罗马对epic的尊崇上升为经典,兹后以俗语常言、志异记奇的novel和romance,则以散文的形式发展接续这一传统,而逐步进入文化中心区域(其记奇、记新、记怪的传统仍有保留)。中国则由于高度发达的“史官文化”由此分流出诸多思想学术的精彩“大说”,“街谈巷议”、“野语村言”、“怪力乱神”只好流入“小说”的领域。近代以来则因为大规模吸收西方文化,新知识界借之表达思想、制造神话(“大说”),宣泄感情(“小说”),附庸逐步蔚为大国,若追究其来源,则仍不可忘记由此返回“小传统”的隐秘线索,(20)并上溯远古文化的文教传统(今天仍有许多元素散落在民间),以沟通民族乃至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无尽宝藏。
对中国小说连通的此一传统,莫言显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感应,他充分地表现出一个“说故事的人”的才能,(21)俨然这一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的一个天才的后继者。说是天才,并不过分,莫言在这方面确实具有特殊的天分与才能,他的世界,繁华、热闹、充满戏剧性,不管是乐观张扬,还是阴郁荒凉,写来都眉飞色舞、兴兴头头,生来便是这一行的“缪斯”或“祖师爷”赏饭的人。随便什么事情,在别人写来可能枯燥乏味,思致枯窘,在莫言笔下,便另有一番神采,别有一番兴味。像《十三步》的触因,不过是因为当时教师待遇低下,《天堂蒜苔之歌》,也不过是由于1980年代他家乡一桩群体性事件的触发,《蛙》则处理几十年间计划生育问题引起的两难,都貌似不过是“问题小说”的材料,若仅看关于写作动因的陈说,不免让人丧气,他的写作却渲染出另一番汪洋恣肆、异想天开的境界(仅仅看《十三步》的怪异世界,难道你还能看出素材简陋贫薄的迹象)。剪纸为马、撒豆为兵,莫言真是具有小说家“无中生有”的特殊才能,连最不成功的《红树林》,其中不少段落,也常常是才华平平的写作者望尘莫及的。不过也许想象的才华太过洋溢,让莫言的小说里,处处是戏剧、处处是意象,热闹繁华,没有空隙,大气磅礴,而少清流。他的写作动力是充沛的情,这种情不仅仅是个人的,更与他所从来的民间大地息息相通。这种“情”带动他(有时是牵制着他),汩汩滔滔,泥沙俱下,却难得安静,更未能触及至深的寂静,所以莫言的小说里听不到寂寞的声音,听不到沉思的声音,更听不到清澈的心灵最深处的声音。沟通“小传统”之外,却也还有“大传统”的问题,“小传统”可以让我们触及民族乃至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象”,个人禀赋可以让我们充分感通流淌在民间的充沛的“情”,而如何解析和安排这些“象”,疏导与化解这些“情”,则除了沟通“大传统”中的智慧之外,别无他径。最好的小说,相通于民族整体的憧憬和想象(22),并可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的顶峰对话。
他的世界,繁华、热闹、充满戏剧性,不管是乐观张扬,还是阴郁荒凉,写来都眉飞色舞、兴兴头头,生来便是这一行的“缪斯”或“祖师爷”赏饭的人
尽管其间不无差异,在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家中,莫言的气质最为接近的,可能仍然是拉伯雷。虽然是通过巴赫金的慧眼,我们才对拉伯雷身上集否定与创造、破坏与重生的狂欢精神有清晰的认识,然而,任何曾经接触到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即使仅仅是粗粗的浏览翻阅)的读者,都不难感受到他身上那种难以言传的独特气质。从其来源来看,拉伯雷一方面连通了以“狂欢节”为代表的民间的节庆感受(中世纪的官方世界之外的“第二世界”,官方世界观之外的另一种更为生机勃勃的世界观),另一方面预流当时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复兴和新生的充满朝气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心目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景象。尽管这一景象拉到现实之中仍在历史上造成无数流弊,却已足以让他感通那万古常新、永无穷尽的生命长流不断破坏、却也不断创造和更新的一体二面的精神,爆发出巨人般的粗野但却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笑声。
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家和他们所自来的传统,经常给予后来者无穷的启发。
注释:
①对于莫言这样体量巨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中的标志性作家,要在一篇文章中论说清楚其创作的整体风貌,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在本文并不措意于此,而仅仅处理其中牵涉到的几个问题:首先是莫言对于民间实感经验的发现与感通问题,其次则是作为小说家的莫言的想象力的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三则尝试在较为宏观的背景下解释其想象力的来踪去向,并且尝试指出其可能存在的限度以及可能的出路。这表面上是几个互不相干的问题,实则随着论述的展开,我们会发现其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而类似的情况也不仅仅限于莫言一人,实际可能牵涉到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中非常普遍的一些问题。
②参阅笔者与王光东的对话:《文学的民间精神——以莫言为例》,节稿初刊2000年12月14日《大连日报》“星海副刊”。全文收入《百年文学十二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莫言小说精短系列”《苍蝇·门牙》代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④[哥伦比亚]加·加西亚·马尔克斯、普利尼奥·阿·门多萨著,林一安译《番石榴飘香》,39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⑤参阅笔者与张新颖的对话:《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初刊《长城》2005年第5期,后作为张新颖著《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的“前言”。
⑥这一问题最初由陈思和先生提出,参看其论文《民间的沉浮》、《民间的还原》及一系列评论莫言的文章。兹后围绕这一问题有诸多讨论和争辩。
⑦鲁迅在许多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譬如在《革命文学》一文中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收入《而已集》,见《鲁迅全集》第三卷)。
⑧此点受到张新颖观点的启发,特此申明。
⑨参莫言、孙郁对话《说不尽的鲁迅》,收入《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2月版。
⑩[德]沃尔夫冈·凯泽尔著,曾忠禄、钟翔荔译《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引文分见第222页,第225—226页,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对凯泽尔著作的阅读,受到王德威先生的指点,特此致谢。
(11)(12)(13)(15)(16)[俄]M.M.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译本收入《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引文见该书55页,第26页,第56页,第10-11页,第13页。
(14)在《文学的民间精神——以莫言为例》这篇对话中,笔者就曾指出:“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生命力喷发的狂欢化的因素,也能够发现很强烈的民间的痛苦和愤怒。也许只有将这两方面联系起来,才算得上真正的和民间精神沟通,也才能触及真正崇高的生命境界?”十年前的这种粗浅感受,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界说为莫言想象力的两个方面的特征。
(17)参张新颖在与笔者的对话《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从〈妇女闲聊录〉反思文学性》中的有关意见,该对话刊《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在2010年于复旦大学召开的“莫言作品研讨会”上,张新颖结合莫言的作品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重述。
(18)[美]杰拉德·吉列斯比著,胡家峦、冯国忠译《欧洲小说的演化》,第5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19)中西“小说”词源本义的贯通暗合,此点受张文江老师讲课内容的启发。
(20)“小传统”与“大传统”的区分,始于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他“在对墨西哥乡村地区研究时,开创性地使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并于1956年出版了《农民社会与文化》,首次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对概念,用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散布在村落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引自郑萍:《村落视野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田野札记》,《读书》2005年第7期)在海外,李亦园与余英时先生较早借用这一对概念,用于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分析,分别大致相当于对中国文化中的“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区分。在当代文学研究界,陈思和先生提出“民间”概念时,余英时《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一文对“小传统”的论述是相关启发性因素之一。关于此一“名词旅行”的有关考辨见李丹《一个关键词的前世今生——“民间”理论的旅行与变异》,《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不过“民间”理论的提出,仍有其他触机,提出者由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获得的“实感经验”,犹不可忽。
(21)据云在现今东北的萨满教这一活态的原始宗教仪式中,仍然有一个“说故事的人”的角色,可以看出现已充分发达和专业化的“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的原始文化起源。
(22)参张文江:《〈西游记〉讲记》,收入《古典学术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标签:莫言作品论文; 酒国论文; 十三步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红高粱论文; 读书论文; 生死疲劳论文; 巴赫金论文; 想象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