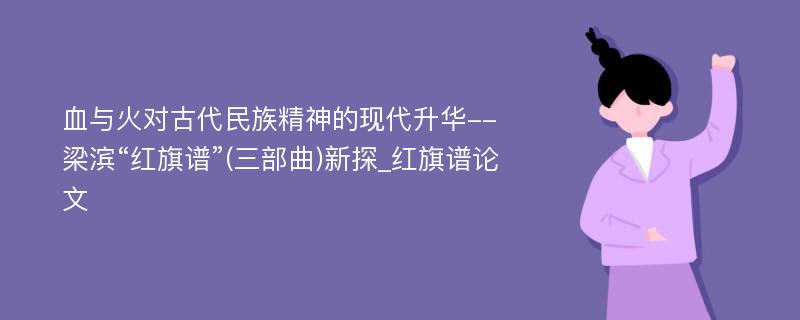
古老民族精神在血与火中的现代升华——梁斌《红旗谱》(三部曲)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民族精神论文,古老论文,梁斌论文,三部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片古老的土地,养育了一个最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民族,创造了她的极其古老的文化;那古老的文化中明明白白映现着这个民族的历史的古老,而那古老的历史中又实实在在记录着这个民族所经历的太多的坎坷与磨难。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如此古老,也正是由于她能够不断地克服和战胜这些历史的坎坷与灾难,从而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存,勇猛地跋涉。因而,也正是由于这种过于沉重的生存,也就自古形成了这个民族的过于强硬的精神,然而也正是靠了这种强硬的精神,也才支撑了这个民族的世世代代的生存与跋涉。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似乎都可以作证:
夜深了,远远传来滹沱河里呜呜咽咽的水流声,那是渗彻人心的、几千年来永恒不变的、被压迫人们的心声!那是几千年来,永恒不变的、反抗的力量!
这是梁斌在其长篇巨著《红旗谱》的第三部——《烽烟图》中接近尾声时的一段极其简短的描述和议论。我认为,这也正是对于全书主题的最深层的揭示。我同时也觉得需要特别指出,对于《红旗谱》的研读,也只有读到此处,才能真正感受和领悟到作者在这部宏篇巨制中所要传达和表现的真实意味和基本精神。
时至今日,为了便于更加整体和进一步深入地分析与把握《红旗谱》、《播火记》以及《烽烟图》这规模宏大的三部曲的更为深层的艺术内涵,我认为有必要先解除一个多年来的偏见,即认为这部本为一体却被作者分为三部且各有书名的作品,只有第一部亦即《红旗谱》才是最好的,而其它两部在艺术上远远不及《红旗谱》,甚至认为主人公朱老忠的性格也“停止了发展,没有显著变化”等。[①]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看似已成定论的偏见,导致了至今很少有人将这三部作品加以认真细致地整体研读,也至今无人对其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较为科学的微观分析。致使所有的文学史著差不多都只谈一部《红旗谱》,却对另外两部只加以三言两语的“缺陷”指责或者干脆加以回避。一部本来完整统一的作品也就被文学史家们人为地肢解,许多读者也就因此而受到误导。实际上,对《红旗谱》的阅读绝不能轻易放弃后两部而将其从整体上割裂出来,尤其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更不能忽略后两部在其艺术整体上的意义和价值。三部作品是内在统一的,是有着深层而严谨的有机联系的。一旦加以割裂之后,就会严重影响对其整体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把《播火记》和《烽烟图》看作《红旗谱》的“续作”,[②]因而,也认为与其它“三部曲”之作同样有着“一部精品现象”,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红旗谱》的三部曲,是从一开始就统一构思的。而且据作者在《烽烟图》的《后记》中回忆:“《红旗谱》全书,一九四二年开始构思。”直到1953年才开始正式动笔,也就是说整整酝酿了十几年。而且,正式写作之后,是先写出了《烽烟图》的初稿(1953—1954),然后1995年至1956年又连续完成《红旗谱》和《播火记》,到1981年,才由于种种原因,又修改完成了《烽烟图》。可见,这三部作品的写作很难从出版顺序上判定其写作的先后。严格地说,它们在作者头脑中的生成是共时的。因而,这也就注定了三部作品在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上的一致性与不可分割性。此外,认为朱老忠的性格没有大的发展和变化,也是后两部的败笔和不足,甚至认为是最要害的一点,我认为也不足为据,相反,恰恰应该说是作者根据现实主义原则,尊重历史真实的结果。因为作为一个刚刚摆脱封建性的政治统治和压迫的农村革命者来说,其思想发展的跨度不可能会太大。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我们更应该要求他的立体丰满,而不应该是人为的拔高和太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作者本人在对朱老忠性格的把握上是十分清醒的,他在《烽烟图·后记》中这样谈道:“《红旗谱》全书,原来想写五部。第四部写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繁荣和‘五·一’大扫荡,第五部写游击根据地的恢复,直到北京解放。当时,我还没有掌握写长书的经验。在我修改这部原稿的过程中,感觉到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已完成。再往下写,生活是熟悉的,但人物和性格成长不能再有所变化,只有写故事,写过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因此改变计划,《红旗谱》全书,到《烽烟图》为止。再写抗日战争时,另起炉灶,另写新的人物。”可见,朱老忠的性格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这是完全符合其思想实际的。
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红旗谱》三部曲的整体性,首先是从其作为一部“史诗”的意义和价值来看。把《红旗谱》看作是“农村革命运动的壮丽的史诗”,这早已为众多的文学史家所认同。然而,作为一部“农村革命运动的史诗”,如果仅有一部《红旗谱》显然是远远不能名副其实的,能够称得上“史诗”的作品也当然必须具有“史”的宏阔和“诗”的浓烈。从这样的意义上看,仅把一部《红旗谱》作为“史诗”,也就显然既缺乏“史”的跨度,也在“诗”意方面略嫌不足。从“史”的层面看,《红旗谱》的主要斗争事件是“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不仅涵盖的历史年代很短,即使把“朱老巩闹柳树林”事件也算在内,历史跨度也不算很长。尤其是,这样的两个中心事件,并没有真正显示出农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力量,而且在实质上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其次从“诗”的意味上看,《红旗谱》也的确创造了较浓烈的诗的氛围,但是,还毕竟显得不是那么厚重。如果再进一步加上《播火记》和《烽烟图》,不仅历史跨度大大增加,一直延伸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全书历史已包容了近半个世纪中三代农民的革命斗争,而且,“高蠡暴动”以及“发动抗战”这些重大事件,也才真正表现出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潜力和伟力。就“诗”意而言,“高蠡暴动”中的血与火的惨烈,七·七事变后日寇轰炸保定的残酷,抗日军民面对强敌的英勇,都实际上大大强化了《红旗谱》中的整体诗意,这是从宏观的总体的崇高和悲壮一方面而言。就个别的细节来看,后两部中也往往充满生活的诗意和斗争的诗情,请看《烽烟图》中的这样一段:
小囤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冯老锡说:“当家的!要是我的胳膊上碾过大车去,你放我抗日去!”
冯老锡不待思索,哈哈笑着说:“好!放你小子抗日去,下半年的活钱,算你白花了!”
小囤一听,心上一下子高兴起来说:“好啊!”他扔地站起身来,紧了紧“腰里挺”。两手卡着腰,晃了一下膀子,绷着嘴唇走到大车跟前,先打了一套“小太祖”,运了运气,两只胳膊互相碰了一下,攥紧了拳头,说:“来吧!”他单腿跪在大车底下,睁圆了两只眼瞳向前看着,屏气宁神,把右胳膊放在车轮底下,伸出左手打了个手式,好象说:“来吧!”这时,小囤的身子骨儿如同春天地皮下的嫩芽,灌满了浆液,以茁壮的姿态,足够的精力,破土而出。他年轻的、滋润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当他真个要耍那俊把戏的时候,雅红曾想跑过去拉他一把。两脚刚刚要迈过去,游击队员们兴兴搭搭地把车一推,咕咚地响了一声,车轮轧过了小囤的胳膊。雅红心上扑通一跳,脸色象纸一样黄下来。
这里通过一个非常具有农村生活气息的场景描写,即充分表现了广大农民(包括中小地主)奔向抗战前线的热情,又反映了农民体魄的强劲以及青春的活力,当然也渗透着一种精神的强力;同时,也绘出了一对男女青年朦胧的爱心,几层意味交织成一种浓浓的诗意。这在《播火记》和《烽烟图》中是随处可见的。因而,作为“史诗”之作,三部作品前后一贯,不可分割。
作为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运动史诗,《红旗谱》最为突出的成就是首次正面描写了农民革命战争的大型场面。这种群众性的而且也是纯粹民族式的枪战场面,可以说是整个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和情节在一些古典小说中早已有过相似的描写,而这种农民的个人的反抗在其它现代小说中也不乏见。但是,像“高蠡暴动”那样的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场面,在文学史上,至今也是罕见的。即使像《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等作品也写了农民革命战争,但也大都是参加了革命军队,或至少也经过了一定的训练,打起仗来也就显得多少有些章法,而《红旗谱》中的农民战争却是最地道的农民方式。作者没有对其进行任何主观的加工和拔高,更没有故意写得无往不胜、无坚不摧,从而也才真正反映出了农民革命斗争的道路的艰难。如第一次战斗即攻打冯家大院的场面就非常能够表现这种农民战争特色,战斗一打响,毫无战争经验且未受过任何训练的农民红军整个乱了阵脚,紧接着有这样一段:
朱大贵扛着机关枪,跟在朱老忠后头,一时无法制止这样庞大的人群。高跃老头走过来说:“这样不行呀!”冯大狗也生气跺脚,说:“这么打仗不行呀!碰上国民党兵,一下子就被消灭了!”朱老忠咂咂嘴,说:“你说的哪里话,群众游击战争嘛,新起的队伍,当然不能和正规队伍一样!”人群冲到了锁井村边,一出庄稼地,不提防哗啦地一排子枪打过来,象是无数飞蝗落在庄稼叶子上,劈啪乱响。人群又呜地兜回来。他们今天第一次打仗,又是惊喜,又是骇怕。听到第一声枪响,很觉稀罕。枪声不够清脆,但是很响,震得人心上突突跳着。不一会工夫,有火硝的气味顺着风飘过来……
这样的描写,简直把农民初上战场的心理写得微妙微肖。此后,还有各大队汇合之后向强大的白军包围圈突围的描写,那就更是见出这一刚刚组建起来的游击部队的幼稚和散乱,大多数人连抢栓还不会拉。所以暴动只能失败。这就是我们的农民革命战争初起的状况,但是,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战争也终于锻炼了广大农民,即使战争再艰苦,也阻挡不住农民革命的烈火,《红旗谱》中就记录下了那最壮丽的一页。
其次,我认为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红旗谱》三部曲的整体性,还在于其深层内涵的整一性。无论如何,把《红旗谱》看作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画卷,都还是属于比较表层的认识和把握。从更深一个层面来看,《红旗谱》全书不仅为我们提供和形象地描绘了农民革命斗争的壮阔的历史画面;而且,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她全面完整地、多侧面地展现了我们民族的那种自古以来所铸炼成的自强不息、英勇无畏的强硬精神。这种精神支撑了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的跋涉,也同样支撑了现代中国的革命斗争和解放运动。当然,现代中国的革命斗争不仅靠着民族精神的支撑,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取得胜利的坚实的基础。《红旗谱》对于这种民族精神的表现是全方位多侧面的,同样不能忽略其后两部的价值和意义。
作品对于民族精神的张扬首先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朱老忠这个人物的身上,这也是历来的评论家们所共同认可的。早在《红旗谱》刚刚出版不久,著名评论家冯牧、黄昭彦就曾在《新时代生活的画卷——略谈十年来长篇小说的丰收》一文中指出:“朱老忠这一典型,不仅是一个普通贫雇农的典型,更主要的他是一个兼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他的旧时代起义农民的那种英雄品格;他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有点像鲁智深;他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有点像李逵;他的勇猛向上、正直无私的气慨,有点像武松;他底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的能耐,又有点像李秀成。他可以够得上鲁迅先生所称为‘历史的脊梁’般的英雄人物。”[③]这里从朱老忠身上看到了古代许多英雄豪杰的影子,的确是很有见地的。朱老忠的性格中的确凝聚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中的许多方面的优秀品格。朱老忠可以看作是我们民族传统精神最为集中的一个典型和化身。这也的确是作者最为用力的一个人物。作者曾这样谈道:“我爱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于是竭力想表现他们,想要创造高大的农民形象,所以一见到开朗、乐观、身体矫健、两眼炯炯闪光的老人,立刻感到自己的理想可以体现在他的身上,这位老人应该成为我小说中的主人公”。[④]作为全书主要人物的朱老忠,正是作者长期从现实生活中孕育出来的。朱老忠的性格在《红旗谱》第一部中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但是,他的真正圆整丰满,还在于第二、三部中才算最后完成。尤其是在第二部里“高蠡暴动”中担任红军大队长,那出生入死、冲锋陷阵的英勇无畏,以及失败后,在第三部中所表现出来的绝不向敌人低头,又终于投入抗战的气魄,都是最能体现这个人物的民族气节的。
从全方位多层面表现民族精神这一角度来看,朱老忠虽然可以成为全书中的主干,但他又不可能担负各种类型的民族精神内涵。就主要的方面和类型来说,与朱老忠相颉颃、相伯仲的一个人物是严志和。作为对于中国传统农民的性格与心理的刻画来看,严志和身上则更多一些纯粹农民的意味。作者曾说:“我是把他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来写的。”[⑤]与朱老忠相比,他的身上的确也更多了一些传统农民的成份,他勤劳朴实,善良本份,乐于助人,但他心胸比较狭窄,有些胆小怕事。他打官司输了一条牛,便不声不响地回到锁井镇,想守住自己那块“宝地”,“低着脑袋过日子”。而严酷的现实却并不能让他就此安宁。老妈妈惊愤而死,“宝地”丢失,运涛、江涛先后相继被捕,这些沉重的打击使他苦闷、迟疑,心里“象铅块一样,又凉又硬”,甚至想投河自杀。[⑥]这里都体现了农民性格中较软弱的一面。但总的来说,严志和在“温顺”的性格之中仍然潜埋着巨大的反抗的基质。作品中对严志和农民性格表现最浓烈最精彩也最让人动情的地方是丢失“宝地”后去与之告别的一段:
“宝地”上收割过早黍子,翻耕了土地,等候种麦,墒垄上长出一卜卜的药葫芦苗,开着粉色的小花儿。两只脚一走上去,就陷进一个很深的脚印。严志和一登上肥厚的土地,脚下象是有弹性的,发散出泥土的香味。走着走着,眼里又流下泪来,一个趔趄步跪在地下。他匍匐下去,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咀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江涛在黑暗中看见他是在干什么,立刻叫起来:“爹,爹!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严志和嘴里嚼着泥土,唔哝地说:“孩子!吃点吧!吃点吧!明天就不是咱们的土地了!从今以后,再也闻不到它的香味了!”
农民与土地的这种血肉相联、命运相关的密切关系和难以割舍的深情,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正是通过严志和这种与土地的无比强烈的感情和极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才最透彻地揭示了广大农民最深层的意识和最高的心理向往。
在《红旗谱》的众多农民形象中,差不多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一种个性,也都能够体现出民族精神的一个质点,可以分别从不同层面作为朱老忠、严志和的精神的补充与丰富。全书正是以朱老忠为精神中轴,环绕和聚集了最广大的农民精神之群。如百折不挠的朱老明,宁死不屈的朱老星,火烈刚强的朱大贵,天真纯洁的二贵、春兰,善良柔顺的涛他娘,泼辣仗义的贵他娘,甚至连老套子、老驴子等人物也都各具风采(书中老驴头杀猪一段令人叫绝)……他们共同织造成了我们民族传统的多姿多彩的精神图景。
然而,除此之外,我认为还应该特别加以指出的是,本着对于民族精神的全面展示,也不能轻视其中的张嘉庆、李霜泗父女、严知孝父女以及第三部中的马老将军等。其中,张嘉庆的形象具有双重性。他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干部,而又带着非常浓厚的中国传统风范。他的“张飞”的绰号,就已经很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主导个性成份。严知孝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清高、孤傲,又坦诚正直,在豺狼当道,社会污浊的世界,想尽量远离政治,又不失报国之心。本质上还是怀抱着一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士古风。在民族存亡、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仍然敢于拔剑而起,不辱斯文。其女严萍是他性格的一种延伸,更是一种升华。严萍最后成为党的一名优秀战士和领导干部,内心中仍然流动和承继着父辈的遗风。李霜泗这个形象比较复杂,但也确很真实,在当时的中国也不乏见。他在第二部中出场参加暴动,又在第三部中英勇就义,不仅给全书增加了许多慷慨悲壮的诗意,而且也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精神内蕴。李霜泗出身于土匪,但他本质不黑。他的落草同当时的许多同类一样,实在是被逼无奈,拉起竿子之后又坚守“杀富济贫”的原则,从不骚扰百姓,而且到处行侠仗义。这样的人物一旦找到正确方向,定会发挥巨大的正面作用。其女芝儿也是他的性格的延伸,芝儿最后的下落不明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想象的余地。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古梁山众好汉中的许多传统品质。
在第三部才正面出场的马老将军一下子占了不小的篇幅,这在全书的总体氛围中无疑形成了一次较大的缓冲,如同一首雄壮激越的乐曲中插入一段舒缓流畅的抒情音调。马老将军的性格属于我们民族精神中的又一种类型。他看上去生活得很闲散,过着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每日拾缀自己的一片小小的田园。但是,他的内心却一直涌动着一团炽热的烈火。在表面的情绪高度平静中,丝毫没有泯灭抗敌报国之心,实际上是一种外柔内刚。作为一个充满正义情怀的老军人,他对世事人情洞若观火,他最不满的是官场的腐败尤其是国民党内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在整个革命斗争和抗日活动中尽可能地发挥着一些带有关键性的作用,如释放江涛、组织后援会等。马老将军在他的看似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生活中并未走向心灵的消沉,他一方面养炼着自己的体魄,也强化着自己的正直的精神,同时思考着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命运。书中通过他的养蜂,表述他的一种较朴素的社会理想,他面对繁忙有序的蜜蜂对严萍说道:“我最喜欢蜜蜂,它们的生活,比目前的人世社会安排得还合理……”他羡慕的是蜜蜂的勤劳和秩序,是他们的社会分工与平等。当然也就表露了对于当时社会的强烈不满。
《红旗谱》全书就是从以上的各个层面和方位上,全面展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人民的意志,并以朱老忠为主干,最终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从而整体显示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强硬。作品以雄浑的气魄告诉人们,只要有这种民族精神在,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顽强地生存下去,就会战胜一切邪恶的力量和强大的外敌。这也正是我们民族能够得以自强不息的根本。
在《红旗谱》的重大主题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层,那就是,《红旗谱》所表现的时代,毕竟已不再是梁山好汉的时代,也不再是李自成的时代、洪秀全的时代,朱老忠们的反抗也就不再是完全出于自发,而是终于找到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沉积在广大人民之中的顽强刚硬的民族精神一旦有了充分科学的现代思想的组织和指导,才终于开辟出了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红旗谱》就是把这种正确的领导形象化为鲜艳的红旗,从此照亮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心。在《红旗谱》的第二、三部中,“红旗”的意义和作用才真正展开和充分发挥出来。从“高蠡暴动”开始的精心缝制红旗,到暴动失败后庄严地埋藏红旗;后来在重新建立党的组织之后又以红旗作为证据,并再次打起红旗进一步发动抗战。红旗这一象征和艺术内涵到此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党的领导人贾湘浓、江涛等都向革命群众反复宣传红旗的意义,而书中的贾湘农、运涛、江涛也都是红旗式的人物,是他们直接体现着党对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尽管他们也出现过一些不同程度的失误,但,他们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在斗争中不断成熟起来的革命精神,却在广大农民心中树立起了一面永恒飘扬的红旗。在“高蠡暴动”开始时,朱老忠向人们讲述了红旗的意义:“看!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党旗,我们就凭着这面红旗指挥千军万马,向日本鬼子进攻,杀尽那些汉奸卖国贼们,打退日本鬼子”,“这面红旗要出在你们妇女之手,看看你们光荣不光荣?你们要好好把你们的革命的心思,和抗日的要求缝在这红旗上,要一针针一线线缝得结结实实,每个针脚都缝上你们的心血和希望。”朱老忠这些农民革命者对于党的领导也许始终没有达到多么高的理论上的认识,一直到抗战以后,江涛还这样评价朱老忠:“江涛只觉得这位革命的老爸爸是可爱的,只是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把这个久经锻炼的老战士限制住了。”但是,他们对于红旗的信念却是永远坚定不移的。朱老忠还曾这样表示:“我们要听从党的领导。党在我们心里就是一面红旗,这红旗向东指,我们就向东冲。这红旗向西指,我们就向西冲,我们听从上级的指挥。”从理论上说,对于农民意识的改造和教育显然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尤其是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农民成员来说,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中便脱尽农民的局限。许多客观条件确实牢牢地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如《烽烟图》中有一段写江涛组织县委会成员学习《党的建设》、《游击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等理论著作,朱老忠和严萍也列席参加,其中就有对朱老忠的这么一段描写:“朱老忠拿起一本小书,他眯细了眼睛,在灯下反复看着。离远一点,再离近一点,模糊一片,说什么也看不清楚。他抓着脑瓜皮,急得浑身发痒。他想:‘这样重要的文件,咱要有个眼,多好!’他转过身递给严萍说:‘你有眼,你看。’”这虽然表面是写他的人老眼花,但同时也表明了这位农民革命者对于理论学习上的距离。但是,他们对党的坚定信念,却融化在了血液之中,书中还有一处写朱老明在听到江涛出狱的消息之后,激动地“一时头晕,瘫软在神桌底下,立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一面血染的大旗,飘在他的眼前,贾老师带着暴动的队伍迎面走来……”作品中还有几处写农民群众在幻觉或梦境中出现红旗的描写,都极其深刻和形象地说明了农民对于党的领导的渴望和坚信。继承了传统民族精神的广大农民,又有了对党的坚定信念,革命的成功已经有了最基本的保障。这是《红旗谱》中蕴涵的一个深刻的主题。
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一个更有创造性的特点是其开笔定调和一句抓住人心。这是许多读者阅读《红旗谱》时都共同感觉到的,却是历来的研究者们所大多忽略了的。《红旗谱》的开头一句:“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这样的开头在语言上看似平平淡淡,实际上却具有无限的魅力,它一下子在读者心中响起了一声惊雷,而且随即设置了较大的悬念,激起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和追根究底的欲望,从而也就一步步将读者带入一个雄浑的艺术境界。这样的开头在整部《红旗谱》的艺术建构中粗看上去也许显得微不足道,但这其中却实在有着非常奥妙的心理学方面的道理。是值得从接受美学角度加以细细分析的。在《红旗谱》刚刚出版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书中财政局长的原型曹承宗曾这样说道:“刚刚拿到这本书的那天晚上,我睡在被窝里,把书打开,才看了第一句——‘平地一声雷……’,就把我的思想一下子吸引住了。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学上的原因,我当时欢喜的看不下去,脑子里总在想着:这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这里面有些什么东西……。”[⑧]这实在是一个普通读者早就给研究者提出的一个学术问题,的确也是应该从理论上加以深入地解释的。
至于《红旗谱》在艺术上的某些粗糙之处,也确实是存在着的,但却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指出的只表现在后两部中。严格地说,后两部在语言操作及节奏掌握上甚至显得比第一部都更加成熟和老练。我认为,这本书在整体上的缺陷在于受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经常强行向政治概念靠拢,唯恐其中革命和抗战的主题不够鲜明。时时由作者直接去讲述或者强加给人物一些政治术语,读起来显得很生硬。尤其是再版时的修改之处,更是带有更多的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的痕迹。
《红旗谱》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难得的佳作。对于其艺术价值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愿作一个新的起点。
1997年2月16日于河北大学
注释:
①②参见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③二十年高等院校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梁斌专辑》。
④《漫谈〈红旗谱〉的创作》,《春朝集》第28页29页。
⑤同④第37页。
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红旗谱》中江涛入狱后,有一段对严志和探监的描写。这段描写在初版时是写严志和感到非常绝望,于是想投河自杀,其中有一大段思想斗争。但后来再版时却把这一段改成坚决与敌人作斗争的心理活动。这样的修改实际上不如原稿更符合严志和的性格。
⑦梁斌:《播火记·后记》。
⑧《老战士话当年》,《文艺报》,195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