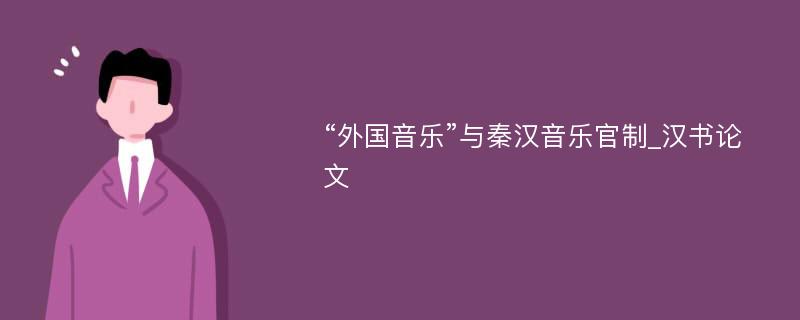
“外乐”与秦汉乐官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官论文,秦汉论文,制度论文,外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关于乐府制度的探讨中,人们往往追溯至秦代。关于秦汉乐官制度,通常有如下认识:奉常所属太乐和少府所属乐府是秦汉时期的两个重要司乐机构①。太乐掌宗庙祭祀乐舞,乐府掌供皇帝享用的世俗乐舞②。近年来,学者对秦汉乐官系统的构成有进一步探讨,但由于对新材料的使用不够,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新的重要结论③。 有关秦代乐官系统的探索中,人们曾注意到秦代封泥中“外乐”一品④。关于“外乐”,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外乐”为秦乐种类。有学者认为:“秦之音乐有宫寝、宗庙、祠祀之乐,又有宫廷、宴飨、韶武之乐,前者或为‘内乐’,后者或即‘外乐’。又秦有奉常属之‘大乐令丞’,又有少府属之‘乐府’,前者或司‘内乐’,后者或司‘外乐’。”⑤ 第二,“外乐”为秦代司乐官署之一。刘庆柱说:“‘外乐’系秦之官署,为‘乐府’或‘太乐’之属官。”⑥万尧绪推测“‘外乐’可能为奉常的下属机构且极有可能是‘太乐’的前身,秦时设置并拥有后来属于‘太乐’的职能,汉初沿袭秦制而称‘外乐’,汉初之后才更名为‘太乐’。”⑦ 第三,“外乐”为秦代乐官之名。许继起说:“‘外乐’职官可能是‘外乐丞’的省称,为太乐令之属官,非乐府令属官。”“外乐”所司为外祀之乐事⑧。 以上各家主要只依据“外乐”封泥进行讨论,而真正能够据以解读“外乐”性质的是《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中的相关内容。《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一种重要司法文书,系议罪案例的汇编。其中,“四月丙辰黥城旦讲乞鞫”条同时出现了“外乐”与“乐人”名目⑨。该条所述案件的主要案情如下: 四月丙辰,黥城旦讲气(乞)鞫,曰:故乐人,不与士五(伍)毛谋盗牛,雍以讲为与毛谋,论黥讲为城旦。覆视其故狱:元年十二月癸亥,亭庆以书言雍廷,曰:毛买(卖)牛一,质,疑盗,谒论。毛曰:盗士五(伍)牛,毋它人与谋。曰:不亡牛。毛改曰:……与乐人讲盗士五(伍)和牛……讲曰:践更咸阳,以十一月行,不与毛盗牛……其鞫曰:讲与毛谋盗牛,审。二月癸亥,丞昭、史敢、铫、赐论,黥讲为城旦。 今讲曰:践十一月更外乐,月不尽一日下总咸阳,不见毛……毛曰:十一月不尽可三日,与讲盗牛,识捕而复纵之,它如狱。讲曰:十月不尽八日为走马魁都庸(傭),与偕之咸阳,入十一月一日来,即践更,它如前……史铫谓毛:毛盗牛时,讲在咸阳,安道与毛盗牛?……鞫之:讲不与毛谋盗牛,吏笞谅(掠)毛,毛不能支疾痛而诬指讲,昭、铫、敢、赐论失之,皆审。⑩ 这是一件冤案。案件当事人名“讲”。他被判刑且已施刑,成了刑徒。秦王政元年四月十一日,“讲”提出案件重审的申诉,他的请求被接受。经过重审,冤案得以昭雪。《奏谳书》说: 二年十月癸酉朔戊寅,廷尉兼谓汧啬夫:……覆之,讲不盗牛……其除讲以为隐官,令自常(尚),畀其于於。妻子已卖者,县官为赎。(11)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下面对该文书中使用的法律术语及其他专门用语略作说明:“黥”,肉刑的一种,刺额并以墨填之。“城旦”,刑徒名,男称城旦,女称舂(12)。“乞鞫”指请求重加审判(13)。“讲”、“毛”、“处”、“和”均为涉案人员的名字。“隐官”,秦代法律术语。秦法律规定,因受肉刑而身体残伤的人,如能免罪,要安置在不易为人所见的处所工作,称为“隐官”(14)。上述案件中,当事人“讲”的身份为“乐人”,与案情发展有关的秦代司乐官署为“外乐”。 “外乐”一名,不见于《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15),《奏谳书》中“外乐”与“乐人”并出,使我们得以对秦代乐官系统的构成和运行方式进行新的思考。 如前所述,《奏谳书》“四月丙辰黥城旦讲乞鞫”条所载案件中“讲”的身份为“乐人”。案件涉及“讲”与“外乐”的关系。“讲”自述:“践更咸阳,以十一月行,不与毛盗牛……践十一月更外乐,月不尽一日下总咸阳,不见毛。”(16)针对“毛”所说“十一月不尽可三日,与讲盗牛”之说,“讲”又自辩:“十月不尽八日为走马魁都庸,与偕入咸阳,入十一月一日来,即践更。”(17)“践更咸阳”是说当事人“讲”到咸阳去服徭役。“践十一月更外乐”,说明他十一月正在“外乐”践更,不在案发地,自然没有“盗牛”的作案时间。 “践更”是秦汉徭役制度术语,意为当役者亲自服更卒之役(18)。《汉书·吴王濞传》云:“卒践更,辄予平贾。”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自行为卒,谓之践更。”(19)由《奏谳书》可见,“践更”更为完整、更为准确的表述方式为“践”某月之“更”。“践更”一词后面可以加上地名表示服役的地点或处所。上引文中“践更咸阳,以十一月行”,指乐人“讲”在案发当年十一月到咸阳服更役。“讲”说他自己“践十一月更外乐”,则表明其具体服役处所为“外乐”。由此可知,“外乐”必为秦代司乐官署的一种。 下面结合《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其他内容,进一步讨论秦汉时期“外乐”的设置情况及其职司。除《奏谳书》,“外乐”一名又见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二年律令》含二十七种律和一种令。据简文整理者推断,《二年律令》系吕后二年实施的法律。简文包括了汉律的主要部分,内容涉及西汉社会、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诸方面情况(20),其中《秩律》是对职官品级的规定。现依据本文需要,节选《秩律》所载西汉早期职官设置和秩级的部分内容如下: 御史大夫、廷尉……少府令、备塞都尉……奉常,秩各二千石。 未央厩,外乐,池阳,长陵,濮阳,秩各八百石,有丞、尉者半之。 太卜,太史,太祝,宦者,中谒者……居室,西织,东织,长信私官,内者,长信永巷,永巷詹事丞,詹事将行,长秋谒者令,右厩,灵州,乐府,寺、车府……秩各六百石。(21)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乐为奉常属官,乐府为少府属官。上述引文表明,奉常与少府令为同一级别,皆秩二千石。太史、太卜、太祝等(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奉常属官)与乐府、中谒者、西织、东织等(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少府属官)同秩(22),皆六百石。“外乐”为八百石,秩级较乐府略高。按:六百石是秦汉官吏秩级的一个重要界限,六百石以上为“显大夫”。《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23)《史记·叔孙通传》载,“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叔孙通制朝仪“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24)。《汉书·景帝纪》云:“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颜师古注引张晏曰:“长,大也。六百石,位大夫。”(25)六百石为“显大夫”,八百石自然属较高级别的职官(26)。 《奏谳书》“四月丙辰黥城旦讲乞鞫”条所记事件发生在秦王政元年和二年,结合前述秦封泥,可知“外乐”在秦代已有设置。从前引《秩律》关于“外乐”的记载来看,在西汉初年的乐官系统中,“外乐”建置仍然存在。《张家山汉墓竹简》的整理者对“外乐”的职能作了简略说明,认为:“外乐”可能是奉常属官,主管乐人(27)。“外乐”是否奉常属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其职掌则确实与“乐人”相关。 “乐人”一名见于传世文献。《史记·滑稽列传》云:“优孟,故楚之乐人也……优旃者,秦倡侏儒也。”(28)“孟”与“旃”同为“优”,然而司马迁分别称其为“乐人”和“倡”,可见“乐人”与“倡”所指不同。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推测,“倡”系就其从业而言,“乐人”则为其社会身份。 秦人在社会生活尤其是狱讼等事务中,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内容包括是否为士伍、刑徒、有无爵位等。《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有鞫”条说: 敢告某县主:男子某有鞫,辞曰:“士五(伍),居某里。”可定名事里,所坐论云可(何),可(何)罪赦,或覆问毋(无)有,遣识者以律封守,当腾,腾皆为报,敢告主。(29) 上述引文中,“名事里”即指当事人的姓名、身份、籍贯等事项。作为司法文书,《奏谳书》需准确记录当事人的身份,故“四月丙辰黥城旦讲乞鞫”条中,有对涉案人员的身份即“乐人”、“士伍”等表述。 “士五(伍)”,是秦汉时期男子身份的一种,指无爵的成年男子或被削爵者。《汉旧仪》云:“无爵为士伍。”(30)《史记·淮南王传》:“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31)秦汉制度,对有爵者可称其爵(32),无爵者则称其“士伍”。 “乐人”名目在《奏谳书》这样的法律文书中出现,说明其必为当时官方认可的社会身份的一种。出土秦代法律文献中记录有其他身份种类,可与之相比较。《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 可(何)谓“集人”?古主取薪者殹(也)。 可(何)谓“署人”、“更人”?耤(藉)牢有六署,囚道一署遂,所道遂者命曰“署人”,其它皆为“更人”;或曰守囚即“更人”殹(也),原者“署人”殹(也)。(33) 上引文献不但记录了“集人”、“署人”、“更人”等称谓,还记载了持有这些身份的人为官方服务的具体内容。“乐人”这一称谓的法律内涵与此相似,考校名实,当是为国家提供乐事服务者的正式社会身份。 在我们对“外乐”性质作出判断之前,学界考察秦汉乐官系统时,主要注目于太乐和乐府。“外乐”在秦汉司乐官署中的地位以及乐人践更外乐的制度在秦汉乐官系统中的作用如何?下面勾稽文献,试作阐述。 秦代及西汉早期,“外乐”的设置及乐人践更“外乐”制度的实施,在秦汉乐官系统的运行中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存续和消亡与秦汉乐官系统的构成及内部分工,包括乐府职能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关于乐府的设置及职能,学界曾有长期的讨论。1976年在秦始皇陵附近发掘的乐府钟证明秦代已有乐府的设置(34)。秦“乐府钟官”、“乐府丞印”(35)封泥等材料的公布,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秦代乐府的属员与职能提供了资料(36)。2004年7月,在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大型土圹墓中出土了一件石磬,上面刻有“北宫乐府”四字。该墓的时代为战国晚期或略晚(37)。学者据此指出,乐府的建立当在这一时期(38)。乐府出现之初,其主要职能是监造及贮藏乐器(39),至汉武帝“乃立乐府”,乐府的规模逐渐扩大,职能也有所转变(40)。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从人员构成的角度对秦代乐官系统进行新的解说,认为除“太乐、乐府而外,秦内廷乐也相当多……在内廷乐宫中,有倡、优、俳、宫女、侍者诸称”(41)。这一阐述,较以往的研究更为细致,但由于未充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故未能对秦代乐事从业者与相关官方机构之间的关系作出适当判断。如前所述,乐人践更“外乐”的制度是秦代乐官系统运行中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一点,目前尚未得到注意。 在秦汉礼乐制度的运行中,与《奏谳书》中乐人“讲”“践十一月更外乐”相类似的践更行为亦见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史律》。《史律》载:“祝年盈六十者,十二更,践更大祝。”(42)“祝”为专职司礼人员之一。大(太)祝系奉常属官,太祝令“凡国祭祀,掌读祝,及迎送神”(43)。《汉官》:“百五十人祝人,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六十人。”(44)“祝”践更大(太)祝,服役于祭祀;乐人践更“外乐”,执事应差,为宫廷用乐服务。乐人践更“外乐”与祝践更“大祝”,皆属于秦汉礼乐机构运行过程的组成部分,可以相互印证和补充。 《奏谳书》记载乐人“讲”所涉案件由郡县审理,说明乐人日常由地方自行管理,与《汉书·礼乐志》所载乐府治下常备属员不同(45)。秦汉乐人践更“外乐”,是有特定服役场所的轮值性徭役(46)。随着乐人到“外乐”践更,具有地方特色的乐器、乐曲等也就有机会进入宫廷,从而丰富了宫廷用乐。这一点,可以从《汉书·礼乐志》的相关内容得到佐证。《汉书·礼乐志》记载了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所奏报的乐府属员构成情况,其中包括江南鼓员、巴俞鼓员、临淮鼓员、兹邡鼓员、楚鼓员、秦倡象人等来自各地的乐人(47)。地方乐人大量进入乐府,可能是西汉前期以后乐人践更“外乐”制度消失的原因之一。 由上可见,“外乐”所辖乐人是秦代及西汉早期司乐官署常备属员的重要补充。在乐人践更“外乐”这一制度下,秦汉司乐官署的常备属员与“外乐”所辖乐人共同执事,在不增加财政开支的情况下,为宫廷用乐提供了保障。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乐府规模的扩大和属员的增加,逐渐不再需要依靠乐人践更“外乐”来维持宫廷的礼乐运行,“外乐”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裁撤的。 关于秦汉乐人身份的探讨,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秦汉乐官系统的构成及其运行模式,对于“乐户”的渊源也有重要意义。乐户是名隶乐籍的社会群体,乐人的户籍往往单列,以另册记之(48)。项阳依据《魏书·刑罚志》等文献资料,将乐籍制度的起源追溯至北魏时期,现已成为学界共识(49)。而综合考察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推断秦汉时期已存在乐籍制度。 乐籍制度是古代户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户籍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户籍分类。秦汉时期,已出现按社会成员的不同身份进行编户的制度。学者指出,文献所见秦汉户籍分类中的“市籍”,是将商人这一特殊群体单列另册(50)。前文已述,秦汉时期“乐人”一名并非泛称,而是人们社会身份的一种。这一点与编入“市籍”的商人相似,“乐人”亦当编入“乐籍”。从这一角度来看,《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所载“乐人”与后世“乐户”的身份约略相当。乐人世世相袭。《汉书·礼乐志》云:“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颜师古注引服虔曰:“制氏,鲁人也,善乐事也。”(51)我们曾指出:“‘汉兴’是汉代人习用的历史、政治术语,特指高祖立国、汉朝兴起到文帝这段时期。”(52)制氏“世世在大乐官”,说明其家族技艺自先秦时期已相传袭(53)。乐人技艺的这种世代传承当是以乐籍制度为保障的。 综上所述,《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所见乐人践更“外乐”的记载对于秦汉乐府制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它促使我们对秦汉乐官系统的构成及演变进行新的审视,对于中国历代乐制包括乐籍制度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①奉常,汉初改称“太常”。《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6页。) ②参见杨生枝《乐府诗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永鑫《汉乐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扬州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 ③(41)黎国韬:《先秦至两宋乐官制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100页,第98页。 ④周晓陆、路东之、庞睿:《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载《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⑤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这一观点亦为其他学者接受。如傅嘉仪说:“秦时音乐较为纷杂,有宫廷、宴席之乐,也有宗庙、祠祀之乐,或以‘内乐’、‘外乐’分之。”(傅嘉仪:《新出秦代封泥印集》,西泠印社2002年版,第8页。) ⑥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载《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 ⑦万尧绪:《“乐府”新证》,载《黄钟》2013年第3期。 ⑧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第22页。 ⑨(11)(12)(13)(16)(17)(20)(27)(4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1页,第102页,第8页,第102页,第100页,第101页,第7页,第73页,第82页。 ⑩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100—10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有关该案件的详细情况,参见李学勤《〈奏谳书〉解说(下)》,载《文物》1995年第3期。 (2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69—7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4)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3、205页。 (15)《汉书·艺文志》“外乐”二字含义与此不同,其文曰:“房中者,情性之极,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汉书》,第1778页)按:这里的“外乐”与下文“内情”相对,似非职官名目。 (18)除“践更”外,还有“雇更”的形式。雇更是指不欲践更,而出钱雇人代更,其钱曰“雇更钱”(参见张金光《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载《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9)(25)(47)(51)《汉书》,第1905页,第149页,第1073—1074页,第1043页。 (22)《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庐、考工室、左弋、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又中书谒者、黄门……官令丞……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汉书》,第726—732页。) (23)(29)(3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33页,第247—248页,第233—236页。 (24)(31)(28)《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23页,第3094页,第3200—3202页。 (26)成帝时除八百石,故八百石在传世文献所载秦汉官吏秩级中出现较少。《汉书·成帝纪》:“夏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颜师古引李奇曰:“除八百石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汉书》,第312页。) (30)卫弘:《汉旧仪》,《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5页。 (32)如“上造甲盗一羊”(《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3页),“五大夫礼出亡奔魏”、“五大夫贲攻韩”(《史记》,第212—213页)。 (34)袁仲一:《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35)参见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卷一,转引自陈直《汉书新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9页;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载《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36)有学者仍然认同乐府官署由汉武帝建立。如王运熙认为:《史记》、《汉书》武帝前的乐府、乐府令名称,只是太乐、太乐令的泛称。至于少府中的乐府官署,在西汉则仍由汉武帝建立(参见王运熙《关于汉武帝立乐府》,载《镇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37)参见张天恩、侯宁彬、丁岩《陕西长安发现战国秦陵园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25日;张天恩《新出秦文字“北宫乐府”考论》,《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317页。 (38)参见陈四海《乐府:始于战国》,载《音乐研究》2010年第1期。另外,黎国韬《乐府起源新考》(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没有使用“北宫乐府”石磬这件出土文物,但结合其他传世文献亦作出了“乐府极有可能起源于战国”的结论。 (39)参见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40)参见《乐府诗史》,第4—5页;赵敏俐《中国诗歌通史·汉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43)《后汉书·百官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72页。 (44)孙星衍辑《汉官》,《汉官六种》,第2页。 (45)乐人践更“外乐”理应具有应节性。非践更期间,乐人所面对的主要是社会艺术消费。有关这一问题,参见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第四章“汉代歌诗艺术生产的基本特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8—103页。后世地方乐人的活动方式与此相似。有关这一问题,参见郭威《乐籍体系的创承与传播机制》,载《音乐研究》2011年第5期。 (46)在唐代施行的乐人轮值制度中,由各地征召乐人到宫廷中轮流应差执事。关于这一问题,参见项阳《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14页。对比可知,秦汉乐人践更“外乐”的制度,可能对后世的乐人轮值制产生过影响。 (48)项阳:《山西乐户研究》,第2页。 (49)参见《山西乐户研究》,第4页。王立《中国古代乐户研究》(载《语文学刊》2011年第7期)提出:“至迟在东汉时期即有乐户存在,然其确切起始年代待考。”黎国韬《早期乐户若干问题考》(载《戏剧艺术》2014年第3期)认为:“乐户制度的正式出现是在北魏迁邺以后的东魏时期,而不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北魏,但北魏的杂户制度对其出现则有一定影响。” (50)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24—828页。 (52)姚小鸥:《“汉兴”“大收篇籍”考》,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3)先秦时期已有世代以司乐为职的情况。《左传·成公九年》对此有所记载,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4页。又《通典》:“昔唐虞讫三代,舞用国子,欲其早习于道也;乐用瞽师,谓其专一也。汉魏以来,皆以国之贱隶为之,唯雅舞尚选用良家子。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18页)由此可知,在唐代人的观念中,至迟在汉魏时,乐户已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