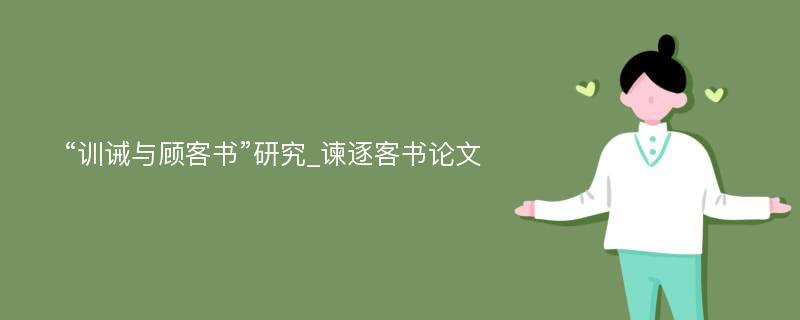
《谏逐客书》杂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88(2009)02-0085-05
李斯被许多中国古代文学史称作“秦代的唯一文学家”,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那篇流传千古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在各种文学史中都有论述,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它同郑国渠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已经成为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的基本常识。①然而常识并不一定就完全等同于事实,其背后可能掩藏着许多意想不到的材料。分析研究这些材料,有助于对这篇作品的认识,进一步逼近“历史的真实”。
关于《谏逐客书》的写作背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解题”最具代表性:
据《史记·李斯列传》略谓:李斯拜为秦客卿。适值韩人郑国来作间谍,被秦发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乃上此书,历叙客的有功于秦,力陈逐客之失。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据《秦始皇本纪》,逐客事在始皇十年,即公元前二三七年。[1](P1)
这段“解题”详尽说明了《谏逐客书》的写作缘起:时间是秦始皇十年(前237年),事件是韩国人郑国来作间谍被发现,秦国宗室强烈要求驱逐这些“外来户”。事实上,这一解释似乎有着可靠的文献证据。《谏逐客书》从产生开始,第一次完整被记录于书面文献,就是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后来又被《文选》所收录。因此,根据《史记·李斯列传》来说明其写作背景,应该是真实可靠的。然而一旦深究,就会发现这仅仅是一种表象。
首先发现问题的是清代学者孙志祖,他的观点见于清代学者梁章钜的《文选旁证》。在《文选》中,李斯的这篇文章被命名为《上书秦始皇》,唐人李善对作者“李斯”有一段详细的注释,正是压缩了《史记·李斯列传》的原文,其基本事实没有任何出入。这段注释不但成为现代所有《谏逐客书》“解题”的核心,而且进一步巩固了《史记·李斯列传》所确立的这篇文章同郑国间秦的密切联系。孙志祖正是从这里发现了问题,梁章钜在《文选旁证》卷三十二引用孙志祖的说法:
此引《李斯传》以逐客事为因郑国,与《始皇本纪》不同。孙氏志祖曰:逐客之议,因嫪毐,不因郑国。郑国事在始皇初年。《大事记》云:是时不韦专国,亦客也。孰敢言逐客乎?《本纪》载于不韦免相后,得之矣。[2](P879)
原来认为有根有据的基本结论受到了质疑:写作的原因是针对郑国的间秦,还是针对嫪毐的乱国,甚或其他?写作的时间是始皇十年,还是始皇初年?这些都需要从原始的文献中加以认真的考证。
《史记·李斯列传》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收录《谏逐客书》的文献,也是确立这篇文章同郑国间秦有直接联系的最早文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书言曰……[3](P2541)
这段文字将《谏逐客书》的写作同郑国间秦联系起来,而郑国间秦的最终成果就是形成了古代闻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如果说《谏逐客书》同郑国渠的联系是真实的,那么考定郑国渠的建成情况就必然对了解《谏逐客书》的背景有很大帮助。然而,由于文献的错综复杂,要真正理清修建郑国渠前后的相关情况,还需要一番细致入微的梳理考证。
修建郑国渠这一历史事件,在《史记》一书中共有三处提及。一处是上面引到的《李斯列传》,一处是《河渠书》,还有一处是《六国年表》。比起《李斯列传》,《史记·河渠书》对修建郑国渠的前因后果表述得更加清晰: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用注填閼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3](P1408)
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引汉人如淳注:“欲罢劳之,息秦伐韩之计。”[3](P1408)郑国渠的修建原来是韩人的一个计策,其目的是想要阻止秦国继续向东扩张,这就是有名的“疲秦计”。然而这种目的也可能仅仅是韩人的最初设想,计策最终能否实现,或者说郑国渠的最终开工和完成,当然只有秦国当政者才有权决定。可以设想,在郑国提出这一建议的时候,即使秦国的当政者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疲秦计”的实质,但有一点他们有清晰认识:这项水利工程对秦国农业的发展极为有益。想要进一步东扩、逐步消灭诸侯,秦国迫切需要一个稳固的大后方以及富裕的军需供给。也正是有了这个前提,在秦人发现了韩国“疲秦计”的实质后,并没有中止郑国渠的修建,这肯定是权衡了“疲秦”的消耗和这项水利工程的作用。因此,“中作而觉”后②,秦人仍然坚持完成了这项工程。郑国所说的“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实秦人未尝不知,而且他当时说了什么也并不重要。挽救他生命的并不是他的辩解,而是这项水利工程本来也符合秦人的想法。
历史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延续的,时、空、人、事是历史学者们最为关心的基本问题。《史记·河渠书》中虽然对修建郑国渠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有详尽叙述,但却没有揭明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这就为后来的许多争论留下了伏笔。《辞海》对“郑国渠”是这样解释的:
古代关中平原的人工灌溉渠道。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采纳韩国水利家郑国建议开凿。[4](P210)
《辞海》的“历史地理”部分是一般学者研究古代历史地理的基本参考文献,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因此,在许多人的理解中,郑国渠的修建时间就是秦始皇十年,即公元前237年。③这一说法是如何得出的呢?原来,《史记·李斯列传》中“斯乃上书曰”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加注:“在始皇十年。”[3](P2541)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套推论:李斯的《谏逐客书》作于秦始皇十年,而这篇文章又是因为修建郑国渠的事情而做的,那么修建郑国渠的时间也应该是秦始皇十年。然而推论毕竟不能代替历史真实。《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也记载了郑国渠的修建,史料基本来源于《史记·河渠书》和《李斯列传》,仅有个别字句的出入,但时间却定在了秦始皇元年,即公元前246年。司马光的说法有根据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就在《史记》中。《史记·六国年表》明确记载:
始皇帝元年,击取晋阳,作郑国渠。[3](P751)
这一行文字很值得注意。首先是“作郑国渠”,如果说没有关于郑国情况的知识储备,一般人读到此处,都会认为这是秦国自己组织的一次水利工程。对比《河渠书》中关于郑国渠修建的详细情况,似乎更进一步印证了前面的假设,即郑国渠从开始修建到最终完成,始终都是秦国统治者的主动行为。他们分析当时的形势,将计就计,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也为自己的统一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面对着两种说法,一是郑国渠作于始皇十年,一是郑国渠作于始皇元年,单纯从文献学的角度说,更有理由相信《六国年表》,因为作于始皇十年的观点毕竟史无明文,是后人的推论,而且这一推论存在着对文献的误解,本身就有问题。
也许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六国年表》将郑国渠的修建确定在秦始皇元年就一定可靠吗?司马迁的《六国年表·序》: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3](P686)
司马迁作《六国年表》的主要文献依据是《秦纪》,但由于这部书记载简略,似乎也只能作为编辑年表的基本线索,还必须有其他的材料来进一步充实。至于司马迁编年表时还曾经参考了哪些文献,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完全考实了。从文献流传的情况看,《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入的先秦史籍还有许多,如《世本》等,应该是会被司马迁采用的。另外,据今人考证,《史记》中还采用了秦以前战国各诸侯的历史记载。④从《六国年表》材料的来源看,应该相信它的可靠性。
确定秦始皇元年为郑国渠开始修建的时间,这也符合当时诸侯各国之间的形势发展。《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5](P2)这是以王权的名义确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这一年是公元前403年,《资治通鉴》的纪年即从此开始。从此以后,群雄并起,各据一方。在分裂的群雄中,韩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备受秦国的关注。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掉了郑,迁都到新郑,韩国的疆域包括今山西的东南部和河南的中部,刚好介于魏国、秦国和楚国之间,韩国在外交上的任何转向都会影响当时的天下形势。秦国要消灭诸侯,一种主要的策略是将他们分裂开来,各个击破。于是,消灭韩国,切断魏、楚之间的联系就成为首要的战略任务。只要检索一下《史记·秦本纪》、《韩世家》等,就会找到大量这类的战争。远的不说,仅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在位的三年间,就发动了两次这样的战争。一次是蒙骜攻取成皋、荥阳,设置了三川郡,一次是秦国攻占了上党。⑤可以推想,韩国屡次受到秦的侵略,应该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原因。
当时和韩国地理位置相近,命运相同的还有早已失去天子权威的东周。东周所占据的地盘相当于今天河南洛阳以西和陕西、山西接壤的地方,也是秦进一步扩张的主要障碍。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二年:
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3](P218)
据史载,周显王二年(公元前368年)东周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都王城,《战国策》中称作“西周”,一都巩,称“东周”。[6](P1)说“初亡”是因为此时都王城的所谓“西周”灭亡了,还有都巩的所谓“东周”在。到了秦庄襄王元年:
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3](P219)
《史记集解》注:“《地理志》河南梁县有阳人聚。”[3](P220)看来,这是一块面积有限的地方,表面上“不绝其祀”,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出师消灭东周,主要的由头是“与诸侯谋秦”,影响了秦国扩大领土的战略部署。而到了秦始皇元年:
当是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3](P223)
秦始皇彻底将东周消灭了。如果说他的父辈们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还不愿明目张胆地消灭东周,而给他们一块弹丸之地让其苟延残喘。到了秦始皇时候,已经有“六世之余烈”,实现统一天下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二周灭亡了,在《史记·六国年表》中从此没有了周的位置。而这一切的发生,韩国人当然完全了解。东周在当时虽然已经早没有了天子的实质,但它头上毕竟还有一顶虚假的王冠。秦国连这些也不顾忌,使“九鼎入秦”,其野心之大可想而知。而要进一步扩张来实现这样的野心,韩国必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正是在这时候,韩国人想出了看似巧妙的“疲秦计”,想要用这样的办法来阻止秦国的东扩。更应注意的是,这一年,秦王政刚刚即位,年龄只有十三岁,改换了新皇帝的秦国内部肯定会有一些宗族派别的斗争。选择这样一个时机来实施“疲秦计”,韩国人显然煞费苦心。从以上分析看,将郑国渠的修建时间定在秦始皇元年,应该合乎史实。
上文花费大量篇幅来考证郑国渠修建的时间,其目的是想为《谏逐客书》的写作确立一个准确的背景。郑国渠修建于秦始皇元年,而一般都认为《谏逐客书》是因为郑国渠的修建而写的,那么是不是说《谏逐客书》是应该作于始皇元年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始皇十年?换言之,《谏逐客书》作于始皇十年的说法可靠吗?依据现有的史料,《谏逐客书》作于始皇十年的说法是可信的。《史记·李斯列传》中有“斯乃上书曰”等文字,张守节《史记正义》即注明“在始皇十年”。张守节的注释不是空穴来风,《史记·秦始皇本纪》为他的说法提供了必要的注脚:
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3](P227)
这一文献有几点很值得注意:一是确定了《谏逐客书》的写作时间是秦始皇十年。二是并没有说明逐客是因为修建郑国渠的“疲秦计”被发现。对比《李斯列传》的叙述,透露出了许多深层的问题。为了更加清晰,再将《李斯列传》的原文抄录下来: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书言曰……[3](P2541)
前面引到的《史记·河渠书》说“中作而觉”,然后有郑国的一段陈述,最后秦王又让他重新回到修建的指挥现场,并没有提到宗室大臣的议论。另外,我们考证了郑国渠是秦始皇元年开始修建的,考虑到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成。一般认为,郑国渠到始皇十年才完全竣工,共用了十年的时间。⑥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依据《李斯列传》,“已而觉”之后,宗室就提出了“请一切逐客”的强烈要求,从而就产生了《谏逐客书》。那么,“已而觉”即“中作而觉”,应该是郑国渠开始修建后不久发生的事情,时间肯定没有到工程完成的始皇十年。这样,《谏逐客书》作于始皇十年的结论就靠不住了,这就和《秦始皇本纪》的记叙发生了矛盾。同时,也应该留意《秦始皇本纪》在叙述中并没有提到郑国渠的事情。从史实上说,即使秦宗室在发现韩国人的阴谋后提出了“一切逐客”的要求,李斯也是刚刚学成,初到秦国,地位仅仅是吕不韦门下的一个食客,未必有资格上书秦王。⑦另外,即使李斯当时已经有上书秦王的资格,如果逐客的要求仅仅是因为郑国渠的事情,以李斯敏锐的政治嗅觉,一定会发现秦王不会采纳这些人的意见,也不必要大动干戈去上书。⑧从逻辑上来推论,只能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李斯列传》所建立的《谏逐客书》和发现韩人“疲秦计”之间的联系是不存在的,《谏逐客书》不是因为修建郑国渠的事情而写的。汉魏以后的许多重要文献,如《水经注》等,都曾涉及郑国渠,但并没有在论述中提及《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不是因为修建郑国渠的事情而写的,那么这篇文章产生的真实背景又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在现存的有关文献中去寻找答案。《谏逐客书》是因秦始皇的逐客令而发的,可惜这篇逐客令已经在文献流传中佚失了,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多参考的是《史记》中的相关材料。《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这里有几点是很值得深究:一是这段文字出现的上下文,二是秦始皇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逐客。为了说明以上问题,解开这些疑团,摘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如下:
九年,彗星见,或竟天。……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3](P227-230)
原来,在秦始皇九年,长信侯嫪毐作乱,假借秦王的命令发动了一次政变。秦王发觉后,当机立断,发兵平息了政变。虽然嫪毐本人在战斗中不知死活,但他的党羽有的被杀,有的被抓,因为牵连这件事情,其门下有四千多家后来被迁徙到四川。显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促使秦王下逐客令的一个直接原因。但这还仅仅是表象。试想,如果逐客令单纯是为了消灭嫪毐的残余,似乎此时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尽得毐等”表明当时参与政变的人几乎全部被抓获了,再加上后来发配四川的一部分,大概嫪毐的部下已经全部落网了。可见,逐客令是应该另有所指的。其实,通过考察就可以发现,这道逐客令的矛头直接指向相国吕不韦。
吕不韦是秦代的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本来是濮阳的商人,但有着超乎寻常的政治嗅觉,精于算计,想用投机的办法遗泽后世。⑨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还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利用金钱帮助子楚树立声望,并亲自到秦国游说,使子楚成为安国君爱姬华阳夫人的养子,具备了将来继承秦国王位的基本条件。后来,子楚回到秦国,并顺利继承了王位,这就是庄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在位仅三年就去世,秦王政成为了秦国的国君。此时的吕不韦地位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他被秦王尊称为“仲父”,地位相当于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值得注意的是,吕不韦在取得了极高的地位之后,他又在明里和暗地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3](P2510)
这是吕不韦明里做的工作。表面上是壮大了秦国的国威,实际上也是在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吕不韦掌权后,还网罗天下贤才,主持编辑了《吕氏春秋》。除此之外,吕不韦还在暗中干了许多勾当:
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3](P2509-2510)
始皇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3](P2511)
从以上《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看,吕不韦在秦王政即位前后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已经为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吕不韦原本不是秦国人,却招门客三千,“家僮万人”,再加上他所引荐的嫪毐也是“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这样的局面,不但会引起秦国宗室的不满,也成为已经成年的秦王政真正掌握政权的绊脚石,秦王政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吕不韦的失败应该是迟早的事情。⑩可能是因为秦王政当时的年龄还小,再加上太后的干预,没有能力和适当的时机处理这件事情。秦王政九年,嫪毐的政变成为一根导火索,恰好为秦王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他迅速平定了政变,并把自己的养母太后华阳夫人迁出咸阳,同时免去了吕不韦的职位,将他放归河南。同时,还下令搜索吕不韦的大量党羽,并把他们逐出秦国。这也就是《秦始皇本纪》中“大索,逐客”的真实用意,也是李斯上书的具体背景。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参考《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吕不韦死后的一些情况:
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3](P231)
只要是吕不韦的门客,凡是秦国以外的人,一律驱逐。更为有趣的是,平定嫪毐政变的主要将领昌平君,根据记载也是楚国的公子,却能在此关键时刻被委以重任,显然深受器重。而且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也没有被排挤。(11)这一反一正的两个事件充分说明,秦始皇并不是要真正驱逐所有的客卿,逐客令有着具体的指向。根据《史记》和《资治通鉴》等文献的记载,秦王后来废止了逐客令。但上面的历史事实证明:李斯的建议并没有完全被听取,这也反衬出始皇及秦宗室对吕不韦的怨恨之深,更凸现了逐客令发布的具体针对性。透过以上历史事实,再来分析《谏逐客书》,也许会有一些新的看法。这篇千古传诵的名文,实际上产生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其写作的动机可能原来仅仅不过就是李斯在为自己开脱罪责,寻找进一步上升的契机。当然,这篇作品所阐明的关于人才使用的道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有几点还需要说明一下。上文考证《谏逐客书》实际上和郑国渠的修建并没有多少关系,那么又应该如何看待《史记·李斯列传》中的记载呢?其实,史籍中相关记载发生矛盾,这是史书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从《史记·李斯列传》、《秦始皇本纪》以及《吕不韦列传》的对比来看,司马迁在撰写有关秦国历史的时候可能使用了不同的文献材料。比如关于吕不韦的有关活动牵涉到秦始皇的出身问题,这些材料不大可能在诸如《秦纪》等秦国历史文献中出现。而《李斯列传》在逐客令发布的问题上显得比较模糊,存在记载的断点,也许正是司马迁采用了诸如《秦纪》等材料的结果。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而已。好在前文的考证大概还能够成立,这样逐客令以及《谏逐客书》的相关问题也就比较清楚了。
同时,前文引到的清人孙志祖的观点,认为《谏逐客书》是因为嫪毐的事情引起的,虽然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可能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实质。关于逐客和吕不韦的关系,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了。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者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说:“可见逐客令是和不韦有关的。”[7](P142)但他关于郑国渠和《谏逐客书》关系的一些梳理仍有可商榷之处。(12)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拉杂考证也许对理解这篇文章以及秦国历史的相关问题有所帮助。
总结一下本文的观点:
第一、郑国渠的修建是秦始皇元年的事情,它同《谏逐客书》的写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二、《谏逐客书》作于秦始皇十年,是为了回应秦王的逐客令,而逐客令的矛头直接指向吕不韦。
[审稿 袁书会]
注释:
①当前流行的各种文学史,凡提及《谏逐客书》的写作背景时均持此观点。另外,一些古文鉴赏类书籍也是这样解释的。
②“中作而觉”亦见于《汉书·沟洫志》,唐颜师古注:“中作,谓用功中道,事未竟也。觉,露也,韩之谋露也。”
③现在一般关于秦国历史的著作仍坚持郑国渠的修建在始皇十年,例如林剑鸣《秦史稿》“秦国的最后胜利”一节,认为郑国事被发现在嫪毐乱后,显然是以郑国渠的修建在始皇十年为基础的。
④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中有《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一文,从《史记·六国年表》入手来讨论了《史记》的文献来源。
⑤攻占成皋、荥阳,设置三川郡的主要将领是蒙骜,时间是庄襄王元年,又见《史记·蒙恬列传》。攻占上党的是王龁。
⑥例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曾讨论过郑国渠,解说词就坚持修建这条渠道共用时十年,其具体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史记》中有关郑国渠的材料分析,这一说法应该有可靠的文献依据。
⑦李斯到秦的时间就在始皇元年前不久,《史记·李斯列传》说“至秦,会庄襄王卒”即可说明此点。
⑧李斯政治觉察力是很高的,这可以从他辞别老师荀卿时所发表的言论证明。另外,李斯后来在秦大一统建设中的作用也体现了这一点,可参考《史记·李斯列传》中有关部分。郑国渠对秦国农业有利,有助于统一大业的完成,秦王不会反对修建郑国渠,这一点李斯应该能认识到。
⑨吕不韦援助子楚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这一点除《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叙述后,《战国策·秦策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章”描述更详细。
⑩林剑鸣《秦史稿》中有“吕不韦同秦王政的矛盾”一小节,即持此论,可参看。
(11)《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贞《索隐》:“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又根据《秦始皇本纪》记载:昌平君被徙是在秦始皇二十年。
(12)张氏仍然坚持郑国渠的修建在秦始皇十年,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论证过了。
标签:谏逐客书论文; 秦始皇论文; 吕不韦论文; 史记论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秦国历代国君论文; 李斯列传论文; 六国年表论文; 长信侯论文; 郑国论文; 郑国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