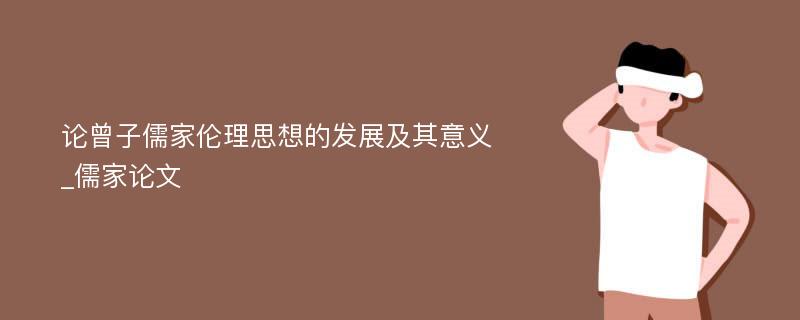
试论曾子对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伦理论文,试论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在儒家伦理学说的发展中,曾子做出了巨大贡献。曾子对于儒家传统的“仁”“礼”学说进行了重新思考,旨在使孔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普及于社会各阶层,让尽量多的人能够理解和实行。他将孔子博大精深的仁学体系简单化、具体化;而对于“礼”,一方面固守维护等级名分的礼,但又使它呈现出内化的倾向,变为主观的道德情操。曾子关于道德修养的理论也独具特色。
关键词 儒学 伦理学说 忠恕 道德修养 孔子 曾子
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学派中,就孔子的及门弟子而言,宣扬和阐发孔子思想者,以曾子最为有力,贡献也最大。曾子曾经被孔子讥为生性鲁钝,似乎没有多大灵气,然而我们考察曾子的言论和著述以后,则知曾子发奋好学,精研孔子学说,特别是对于儒家伦理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以自己的深邃思考和具体阐述,将儒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可以说,曾子是孔子以后,孟子、荀子以前在伦理学方面的重要儒学大师。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曾子伦理思想的特色,来说明他对儒家伦理学说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这对于缕析先秦儒学变迁的历史轨迹,应当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笔者不揣谫陋,试提出一些粗浅看法,敬请专家指教。
一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面貌变化很快,曾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孔子所提出的伦理学说进行了认真的诠释和演绎,在相当程度上巩固了儒学伦理学说的阵地。“仁”的思想可以说是孔子伦理学说的核心。按照一般的理解,“仁”是孔子对于周代贵族的道德情操“德”的抽象化结果,而他关于“礼”的学说则渊源于周代贵族的各种礼制,是维护宗法制度、区别等级名分的外在规范。就重视程度而言,应当说孔子对于“仁”的学说倾注了更多的关心,作了更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和孔子大异其趣的是,曾子对于“仁”、“礼”这两项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的重视程度,从表面上看却远远逊于孔子。《大戴礼记》所载曾子10篇,是曾子思想最集中的汇总,其中提到“仁”、“礼”者并不多。这并不是说曾子对于孔子的“仁”、“礼”学说真的不重视,而是他对于“仁”、“礼”进行了重新思考,不停滞于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而是将这两项孔学理论的核心具体化、现实化,使之更易于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让尽量多的人能够理解和实行。这对于使儒家学说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为了便于探讨,我们先来考察曾子对于孔子“仁”学的发展。
在孔子的伦理道德学说中,“仁”是德的最高境界。它强调的核心内容是自身与他人交往关系的准则。孔子强调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把这一点作为立身行事的基点;在“爱人”的基础上,孔子追求“忠恕”之道,即“立人”、“达人”,其中包含着尽心尽力为他人着想的高尚情操;孔子所说的“仁”,又是复杂的道德意识,《论语·阳货》篇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按照孔子自己的解释,这“五者”,是“恭、宽、信、敏、惠”。《论语·子路》篇载孔子语谓“刚、毅、木、讷近仁”。可见,孔子赋予“仁”以极高远的理想色彩。 孔子极少用“仁”来称许别人〔1〕,自己也不以“仁”自居。
对于孔子所阐述的具有无比高远境界的“仁”,曾子对它做了新的阐释。曾子将博大精深的“仁”学体系进行分解,抽取其主要的内容进行单独论述,将原来包罗万象的“仁”简化为一项项具体内容。概括说来,对于“仁”所包含的“爱人”这一意蕴,曾子以“孝”来涵盖;对于“立人”、“达人”之道,曾子将其作为单纯的待人原则,即“忠恕”之道;对于“仁”所包含的其他道德意识,曾子则是将其统括为“仁”。当然这种概括并不能将孔子的“仁”学体系包揽无遗,但我们以为,这三项内容恰恰是孔子仁学体系中的精髓,曾子将其抽取出来,单独立目,使其变得明确而具体,正显示了曾子对于孔子仁学体系的深邃思考。下面我们先对后两项内容进行探讨,而关于“孝”的问题则在后面详细阐述。
《论语·里仁》篇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见曾子对于贯穿孔子学说的总线索早已心领神会。在曾子本人的理论中,他更是对于忠恕之道进行发挥。曾子说:“是故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也。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他还说:“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疾其过而不补也,饰其美而不伐也,伐则不益,补则不改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曾子认为君子之善应当和他人同步而行,对于别人的美善和才能,绝不据为己有。君子提倡美善之事,但并不强迫别人去做;他人有了过错要让他自己改正;别人有了美善之事,不要过多地夸奖,以免使其骄傲自满。按照曾子所讲的“忠恕”之道,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绝不幸灾乐祸,“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完全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这种与人为善的态度还表现在君子对别人总是满怀希望,衷心愿意别人取得更大的成绩,用曾子的话来说便是君子“见其一,冀其二,见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于人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是相当著名的论断,其中居于首位者便是“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充分体现出待人的诚挚之心。曾子时时强调与人交往过程中对于别人的充分理解和宽容,设身处地为别人提供帮助,这实际上就是“忠”、“恕”之道的具体体现,可是曾子并不许之以“仁”的桂冠。曾子在实际上是将爱人、立人、达人这些范畴从“仁”的总体系中抽取出来,在阐述时尽量将其具体化,使之成为独立的待人接物原则。和孔子所提倡的几乎是无所不包的道德总体概念——“仁”比较起来,要明确得多,具体得多,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也就是更容易在实践中贯彻。
在曾子的理论中,以“仁”相称许的多属道德意识,表现为一种精神和气节,类似于后来孟子所倡导的“大义”。曾子说:“君子无悒悒于贫,无勿勿于贱,无惮惮于不闻,布衣不完,疏食不饱,蓬户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无悒悒,不知我吾无悒悒。”(《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表现出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曾子提倡“尊仁安义”(《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执仁与义而明行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他认为“冻饿而守仁,则君子之义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曾子所说的“仁”、“义”均指君子的气概。曾子将仁、义连用,这对于孟子的影响很大,经过孟子的进一步发挥,它就成了后来儒家最为重要的两项道德观念。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曾子把在孔子那里极富理想色彩,几乎与尘世富贵和私利无涉的“仁”,与现实中的功利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仁”以现实的内涵。“仁”不再是难以企及的境界,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简直变成了可以由人们触摸到的东西。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说他们“求仁而得仁”(《论语·述而》),并不因为当初相互推让国君的位置而懊悔。对于在孔子那里罕见的以“仁”相称的两位贤人,曾子却说他们“死于沟浍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一方面说明“仁”与成名有所关联,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惋惜的心情。曾子还论述了“仁”与“富贵”的关系。他说:
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则得而有之;人徒之众,则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将说富贵,必勉于仁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
在曾子的观念里,“仁”与“富贵”是统一的,在求仁的同时,就可以得到富贵。在对于两者的价值取向方面,曾子的看法与孔子有一定区别。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孔子的目标在于求“仁”, “富贵”是为“仁”服务的;而在曾子看来,君子虽然“勉于仁”,但那却是求取富贵的手段,或者说是必经的道路。曾子认为,“仁为富”、“仁为贵”,仁与富贵密不可分,富有天下土地、贵有天下之众的舜,自然也就达到了“仁”的境界。曾子虽然也在肯定伯夷、叔齐那样的精神,但对于“富贵”的舜却更为青睐。曾子在实际上是将经世致用哲学掺进了具有无比高远境界的“仁”的观念之中。
总之,为孔子推崇备至的“仁”的精神,到了曾子的理论中虽然其地位并没有下降,但是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曾子对于“仁”的改造,主要表现为使其具体化、现实化,可易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实践。据《论语·子张》篇记载,曾子曾经批评子张将“仁”理解得太玄乎太高远,说:“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可见他并不主张将“仁”弄到高不可攀的地步。经过曾子重新阐释后的“仁”,具有可操作的性质,对于“仁”学的普及和影响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
二
曾子对于孔子“礼”学的发展,与他对于“仁”学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取向。概括而言,可以说曾子一方面固守维护等级名分的礼,另一方面曾子所阐释的“礼”却呈现出内化的倾向,变为主观的道德情操。
春秋时期,虽然在周天子和一些诸侯那里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况,但是在广大的贵族阶层中,“礼”却呈现着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人们对于礼的兴趣有增无减。据《论语》记载,孔子所大力倡导的“礼”,虽然也强调以“仁”为其核心,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但其所注重的仍是区别等级名分,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主张“使民以时”、“齐之以礼”,作为臣下的要“事君以礼”,作为君主的要“以礼让为国”。关于个人行为中的“礼”,孔子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孔子的言行中可以看他对于礼的形式还是十分讲究的。《论语·乡党》篇载,孔子主张朝见诸侯国君主的时候,“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登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朝见国君时要十分恭谨,好像在君主面前没有容身之地一样,站立的时候,不站在门的中间,走的时候,不踩门坎,在国君面前说话要做出底气不足的样子。《论语·八佾》篇载,子贡要将告朔时所用的羊去而不用,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些都表明孔子对于礼的仪节的重视。
曾子虽然也认为“礼”对于维护等级制度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避免“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强立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之类的行为出现,但是他更重看的是人们“行礼”时内心的道德修养。他说:“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在这里,曾子把原先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为主的“礼”改变成为人们相互关系中的道德准则,对于尊贵者的尊重,对于年老者的孝敬,对于幼小者的慈爱,对于年少者的友善,对于贫贱者的恩惠,这些内容本身所强调的并不是对于别人的统治、对于别人的管理,而是对于别人的理解、帮助和关心。据《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篇记载,在谈到孝敬之礼的时候,曾子说:
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微谏不倦,听从而不怠,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谓孝矣。尽力无礼,则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则不入也。是故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饮食移味,居处温愉,著心于此,济其志也。
曾子认为孝敬父母必须有一定礼数,但这礼数必须由忠爱之心支配,必须“著心于此”,才能够成就其行礼之志。曾子强调的是发自内心的恭敬感情,如果没有这种情感支配而只是在表面上尽力于孝,那就是小人之礼,便可能引起混乱。曾子这里所说的“心”,就是道德修养。
在儒家伦理学说中,曾子虽然强调“礼”要严于律己,进行内心反省,但并非提倡人们都成为谦谦君子,而是强调要从内心的自律和对人的友善之情出发,不仅对自己进行反省,而且也对别人反省,从而达到“致善”的目的。《礼记·檀弓上》篇载有关于曾子批评子夏的一事: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久矣。”
曾子认为子夏居西河的时候西河人民把他当成孔子;居亲丧没有特殊表现以显示自己的哀痛;儿子死了哭坏了自己的眼睛,这三者都是子夏的过错,所以子夏哭喊自己无辜的时候,曾子便严辞指明其错误之处。曾子的批评切中要害,对于自己朋友的过错绝不敷衍姑息。曾子提倡“直行而取礼,比说而取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从他批评子夏的事情上看,可以说他是言行一致的。在他看来,“礼”并不是要人们变成唯唯诺诺的人,而是要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曾子以恪守孝道著称,其孝道的内容之一就是强调对于父母的过错应当进谏,这实际上是对于父母的言行进行反省。曾子说:“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对于父母不“中道”的言行,子女应当劝谏,若父母没有接受,子女便承担父母的过错,按照父母的意志行事。同时,又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努力感化父母。由此可见,曾子的“礼”包含着在反省自身与反省他人的过程中来提高内心修养的因素。
将外在形式上的礼转化为内在的情操,可以说是曾子伦理学说中关于“礼”的论述的基本点。曾子所阐释的这种在“著于心”基础之上的“礼”,适用于一切社会等级的人,这在实际上就使得原来主要施行于贵族阶层中的“礼”靠近了普通的社会民众。“礼”的内涵在这个方面的变化到了孟子的时代更为显著,成为孟子所倡导的“礼”的最重要的内容。有人问孟子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走上仕途为官,孟子回答说:“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孟子·告子下》)这里是说要注重别人的礼敬之心。据《孟子·离娄上》篇记载,孟子还说过“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强调要从内心反省的角度来分析人际之间的礼的问题,将礼变成内心对人的恭敬态度。
就周代而言,礼的发展变化轨迹可以这样来概括:首先,作为贵族统治的工具,礼实际上是西周时代贵族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其次,到了春秋时期,礼的主要作用表现于维护社会的等级名分,繁琐的仪节和不同的礼器成为人们社会地位的一项标识。春秋后期,当礼趋于颓势的时候,孔子曾经大声疾呼要“克己复礼”,以维护传统的礼制。再次,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传统的礼逐渐向人们相互关系及自我修养中的道德情操发展,变为待人恭敬、谦虚的礼貌之“礼”。相比之下,礼在原先所起到的统治作用和等级地位标志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开始退居于次要位置。礼在春秋战国之际所开始的这个转变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久远,其意义不可小觑,而这个转变的发轫者正是曾子。
三
在对于儒家伦理学说的发展上,曾子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大体来说是通过对于“仁”、“礼”等理论的深入诠释,便儒家的伦理学说更适合社会的需要,更贴近社会生活,更易于为广大的社会阶层所接受。他对于作为伦理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孝道的阐释,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曾子所阐述的作为伦理观念的“孝”,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它是孔子仁学体系中“爱人”观念在曾子理论中进一步具体化的体现。事实上,曾子的孝正是以爱亲、爱人为基础,去强调发自内心的真诚之爱。但它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曾子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了新的诠释和探讨。
首先,在曾子那里,孝已不再是为贵族阶层所遵循的规范,而是他为广大社会阶层——甚至可以说是为社会上所有的人进行的人生设计。曾子把孝分为“大孝”、“中孝”和“小孝”,谓“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这个划分的目的显然在于说明有适合社会各个阶层需要的孝道存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顺利地进入孝的境界,即曾子所谓“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大戴礼记·曾子本孝》)无论是作为贵族的“君子”“士”,抑或是作为普通民众的“庶人”都可以使用孝的规范律己。在曾子看来,孝是理想境界中甜美的道德之果,进入这美好境界的任何人随时都可能将它摘取。
其次,曾子强调“孝”是内心的自觉行为,它摆脱了社会等级之类条条框框的束缚,所有的人都可以进行这方面的修养。曾子说:“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强调了以内心活动为主的忠与敬。这在实际上为普通民众道德情操的升华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并且十分简易的路径。
再次,曾子继承了孔子关于孝与“为政”关系的理论,并且注入一更多的功利色彩,使它更近于现实社会。曾子说:“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依照这种逻辑,可以说,传统伦理观念中注目于家庭内部关系的“孝”实际上变成了从政的演习。曾子将政治原则注入了温情脉脉的血缘亲情的孝道之中。曾子孝道理论在这个方面的合理发展,便是以孝治天下。曾子认为天子施恩泽于普天之下,受到人们的拥戴,接受许多贡纳,即所谓“博施备物”,这样便会更丰盛地祭祀祖先,这就可以称为“大孝”。孟子承袭了曾子关于“大孝”的理论,称舜具有“大孝”的品德。并且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对孝道作了更为深入的发挥。对于个人利益而言,曾子将孝与个人功利相联系,认为孝可以扬名。他说:“行无求数有名,事无求数有成,身言之,后人扬之,身行之,后人秉之,君子终身守此惮惮。”(《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要能够使“身言之,后人扬之”,实行孝道是相当重要的内容。
从以上几处方面可以看出,曾子赋予孝以相当广泛的内涵,其根本点在于肯定孝是人类内心所固有的美好情怀,所以他才一再强调“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又说“君子立孝,其忠之用”,(《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将发正内心的由衷的情感作为孝的本源。曾子认为恪守孝道的过程,只是将这种情感在实际言行中抒发体现出来。从这一点上看,曾子在实际上肯定了人心向善的本性,只是还没有用性善的观念表达而已。但是,曾子并不否定人性中固有着“恶”的一面。曾子说:
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为能也,色勿为不可能也;色也勿为可
能也,心思勿为不可能也。太上乐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强。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君子对于那些“不善”的、丑恶的事情,自己不去干是能够做得到的,但若不去看它却未必能做得到;进一步说,即使不去看它,但是心里面不去想它,则是不可能的。曾子认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人心以向善为乐,其次是不去看它,最末等的做法便是自己强制压抑心中的不良念头。那些“恶”的念头,曾子认为它存在于大部分人的心中,所以说“太上不生恶,其次而能夙绝之也,其下复而能改也”(《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属于“太上”层次的人可以达到保持心中纯正的最高境界,绝无丝毫恶念,但那毕竟是少数。总之,曾子对于性善、性恶论,将伦理思想的阐释推进到了崭新阶段,如果究其源流的话,可以说这种理论都与曾子相关的论述有着隐然可见的关联。曾子对于人性的思考虽然尚处于朦胧阶段,尽管还没有系统的理论总结,但他那富于开启性论断的提出,却为后来的儒学大师留下了无穷思辨的余地。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伦理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德修养问题,始终为曾子所关注。曾子关于道德修养的理论十分丰富而且全面,专家多有所论,这里不再重复,只是要补充和强调的一点是,在学、行、思等道德修养的主要途径里面,曾子特别注重思,并且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还说君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这里讲了反躬自省的方法和具体内容,然而这还只是关于道德修养的比较肤浅的层面。曾子从提倡认真的反躬自省开始,将道德修养推进到净化心灵的深入层次,并且由此出发再深入到以“义”为尺度净化心灵的更为深入的层次。这对于儒家关于道德修养的理论是一个重大发展。
孟子的时候,有个名叫北宫黝的人,他可以做到在每一件事情和任何一个人的面前都无所畏惧,另一个名叫孟施舍的人与北宫黝不同,他只培养自己的无惧之心。在评论北宫黝和孟施舍两人的道德修养方法的问题时,孟子说:“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所谓的“缩”,前人释为“义”,相当精当。清代学者谓:“《释文》云:‘缩,直也。’《广雅·释诂》云:‘直,义也。’缩之为义,犹缩之为直,盖缩之训为从,从故直。从亦顺也,顺故义;义者,宜也。”(焦循:《孟子正义》卷6)曾子借阐述孔子的微言大义, 说明要真正具备“大勇”,必须“守约”。“守约”的具体内容便是当别人伤害或厌恶自己的时候,便要在灵魂深处以义为原则进行自省,如果断定自己确有不义之心,那么对于伤害或厌恶自己的人,即使他只是披褐宽博的一介草民,自己也不可居高临下使之惴惴不安;如果自省在而断定自己正确,那么即使敌人有千万之众,自己也会勇往直前,毫不畏惧。孟施舍强调的是培养无惧之心,而在曾子那里,仅有无惧之心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灵魂深处认真自省,所以孟子认为曾子的修养要比孟施舍深入一个层次。曾子在这个层次上的说明,关键在于“自反而缩”和“自反而不缩”,将心灵放在“缩”——即义的位置之上来考虑问题。只有如此,才能通过内心自省来判断善恶,才能够审视自己言行的是与非。曾子所谓的“缩”并非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有明确说法的。曾子谓:“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他将孔门的仁义学说深入于人的灵魂深处,从而使儒学伦理学说关于道德修养的探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曾子发展儒家伦理学说的努力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扩充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学说的范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曾子的再诠释和发展之后,使得原来距离社会现实比较高远的儒家伦理学说贴近了社会,靠近了普通贵族和民众,使得哲理化的伦理学说更为具体,从而获得了比较强的实践性。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如果没有曾子对于儒家伦理学说的重新阐释,儒家思想是否能够获得后来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是令人怀疑的事情。发展了儒学伦理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比较深入的命题,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这些大概就是曾子最大的贡献之所在。
收稿日期:1996—04 17
注释:
〔1〕《论语·公冶长》篇载,楚国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子张问这算不算是仁,孔子只称为“忠”,不称为“仁”。齐国的陈文子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人物,孔子只称他为“清”,说他只是清白,还谈不上“仁”。鲁国的孟武伯曾经问子路、冉求、公西赤等是否达到了“仁”的境界,孔子回答的时候虽然肯定了这些弟子的优点,但却不称其为“仁”。孔子最欣赏的弟子颜渊,孔子只称许他“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也还没有达到“仁”的完美境界。孔子所说“我未见好仁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可谓是其关于“仁”的实践问题的一个概括,孔子实际上认为社会上一般的人很难达到“仁”的境界。
〔2〕《论语·述而》。孔子常将“仁”与成名联系起来,如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将“成名”作为传播“仁”的一种手段,然而,孔子却从不将“仁”与富贵之事相联系。
标签:儒家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曾子论文; 君子论文; 大戴礼记论文; 孟子论文; 道德修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