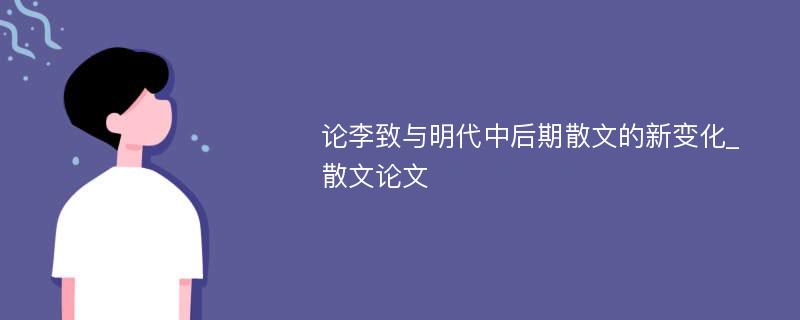
论李贽与明中后期散文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期论文,散文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中后叶的一百多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是热热闹闹的一百多年。经济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阶级上市民阶层壮大,社会心理上市民思想日居重要地位,思想史上王阳明“心学”的革新运动,李贽等狂禅派的勃兴,使这一时期成为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转向的枢纽,并为近代的思想解放作了铺垫。郑和的下西洋,利玛窦的传教中国,则又显示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展开。文学界亦不甘落后,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重情求真尚俗与宗经宗圣宗道的对立,小说戏曲新文学样式的发展,都成为我国文学史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其中,中国最古老的文体之一——散文,就在这一热闹的中晚明期产生了某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变,为这一古老文体向现代散文的演进创造了条件。
一
明人弥尔岐在其《蒿庵闲话》卷一中曾说:“明初,学者崇尚程朱……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始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有明一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起承转变。明代的散文新变——“文章日丽”,首先是由“议论日新”而导引的。这种“议论日新”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及其先导王阳明。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理学体系窒息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心灵的扩展。面对这一现实,王阳明首在思想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思想界吹来了一股清新而自然的惠风。针对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他认为良知并非存在于外界,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即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这样,良知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天理”的绝对地位,显示了个人的主体意识的萌生和地位的提高。同时,他还认为良知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只给自家良知”,每人各适其适,各得其得即可,不必也不需依傍圣贤。这就使良知具有了人人平等的价值,打破了道学的陈旧格套,内含着自由解放的精神。王阳明还抛弃了朱熹“知行分离”的作法,而主张“知行合一”。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答顾东桥》)这种主张使他打破了世儒无所不知而实一无所知的虚诞习气,而教人各据自己的才性而行,这使良知非常的切实可行,包含着实用的精神。王阳明还倡导“狂者胸次”、“五经皆史”,也都是当时“议论日新”的组成内容,成为明代中后期思想启蒙的嚆矢。
在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下,产生出了“非名教所能羁络”的泰州学派,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激烈冲击。特别是以李贽为中心掀起了一场似儒非儒似禅非禅的狂禅运动,他们以“狂”自诩,以“异端”自居,借用佛学,阐发一系列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主张,把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思潮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李贽否定圣人的权威地位,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指儒家的经典不过是“史官过为褒崇之词”、“臣子极为赞美之语”(《焚书》卷三《童心说》);斥道学家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两面人(《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俟》);他反对儒家的“践迹”、“执一”,响亮提出,对于过去的迹“不必践,不可践,不当践”(《藏书》卷三十二《乐克传论》);他反对封建束缚,要求发展人们的“自然之性”,提出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理论,并以此提出了要“物各付物”、“因材并育”的主张(《明灯道古录》卷上);他反对封建等级制,提出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天子庶人壹是无别”的观点(《解老》),认为女子与男子在才智上没有差别,并对“妇女见短”一类的轻视妇女的封建观念进行了批判(《焚书》卷二《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他倡言事功,明白而干脆地承认个人欲望的合理性,要求“各遂其千万人之欲”(《明灯道古录》卷上)等等。这些惊人的立论,翻千古成案,集中到一个中心,即反对传统束缚,要求尊重人的个性,鲜明地体现了明代中后期思想解放思潮的重要特征,即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价值的被发现,被重视。
李贽的文艺思想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李贽文艺观的核心是“童心说”。“童心”即童子之心,是赤诚而纯挚的,是禀赋天地而来的最初之心,它不杂丝毫的尘滓,与琐屑的俗世相比,童心是一种在高处的灵魂。李贽正是深悟了这种童子之心的可贵,故而以此为喻,提出了他著名的“童心说”。他认为真正的文学是从“童心”而发,而且是写“童心”的文学。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在李贽看来,这种出自“童心”的“至文”的第一要义,就是“真”。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真心说》)把文学创作中的“真”强调到这样突出的地步,这是李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表现。还应指出,李贽的“真”又是和“愤”相联系在一起的。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他说:“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焚书》卷三)在《杂说》中他又对这种发自真心的“情”作了如下描述:“其胸中有如许可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焚书》卷三)一切都是发自真心实感,而不作任何的矫饰,这才是天下的“至文”。李贽还指出这种真心之文是与那种出于假心的假文鲜明对立的。他对那种“言语不由衷,为政无根柢,著文辞不达”的假心之文曾进行过多次毫不留情的批判。由此可见,“童心说”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绝假纯真、斥伪存真,这个真就是要表现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社会生活。
与这一真心相应的,李贽主张文学的最高审美应是以自然之为美。他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天性,因而它是最真实的。人而为人,穿衣吃饭,数钱睡觉,逃不了的七情六欲,躲不掉的爱恨嗔痴,这是自然,这就是人伦物理,因而文学应真实地表现这些内容,发乎本心,才是文学的至美境界。在《读律肤说》中李贽说:
盖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性情,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性情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焚书》卷三)
可见,这种自然,不雕饰,不刻意,是天成,而非人作,是“化工”,而非“画工”。这种非理性的直觉意识恰与当时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性相颉顽,发出了文学的“以情反理”的呼声。
既然“真心”、“自然之美”是评价文学的标准,李贽认为只要“童心常存”则“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由此出发,他指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六朝文降而为近体,变而为传奇,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水浒》,文学总是这样一脉相承地发展,怎么可以“时势先后论”?李贽的这一思想,强调了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学,文学总是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每一文学样式只要是“发自童心”就都会自有特色与价值,这就不仅以其革新思想抛弃了窒息明代文坛的复古主义的拟古不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明代中晚期的文学繁荣指明了道路。
总之,“童心”一出,明代文艺启蒙思潮即以此为滥觞,蔚为大观。“童心说”所阐述的文艺观在当时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价值。这一思潮对散文这一特定的文学体裁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亦或审美上都使其受到深刻影响,为其带来了新的扩展与变化。
二
明代中后期的“异论”一起,影响到散文领域的议论也随之日新。但这一议论走到真正意义的“新”,却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明初文坛台阁体固守平庸守正的理论,使散文创作平易啴缓,思想和表达都力求淡化作者的主观感情和主体意识。于是,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新的议论来涤清文坛。但从茶陵派至前后七子至唐宋派走的却是一条复古路线,这一路线不仅没有使散文获得新生,反而又使之蹩进了另一条死胡同。试看他们的言论:
后世文趋时对偶而文不古,诗物声律而诗不古。文不古而有宫体焉,文益病矣;诗不古而有昆休焉,诗益病矣。复古之作,是有望于大家。(李东阳:《余冬序录》)
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李梦阳传》)
攀龙……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
(余)自六经而下,于文则知有左氏、司马迁,于骚则知有屈宋,赋则知有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盖日夜置心焉。(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
通观前后七子的这些代表言论,均是以复古为声气,他们妄图以摹古的方式来再现古文正道,即讲求辞采、高雅的格调和道统的内容。但是,他们最终却是落入狭小的窠臼,于无法再现昔日辉煌的困惑中走向式微了。
在困惑中,散文只有再向真正的新议论发展,才能寻觅到一条新变的出路。随着李贽的“异论”而起,应运而生的即公安派的“性灵说”。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曾直接师事李贽,面向李贽问学,在文学思想上深受李贽的影响。故而可以说,“性灵说”是在“童心说”的指导下发展而来的。
“性灵说”明确而系统地阐明了三袁的散文理论。他们主张为文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序小修诗》)。即著文一定要是真情流露,发自肺腑。正因为如此,才能达到“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袁宗道:《论文·下》),即各人须言真情,言己心,才能创作出不同于他人的文章,袁宏道在《序小修诗》中还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这表明“性灵”理论的真谛就在重情求真尚俗,这和李贽的文艺思想完全一致。“性灵”理论主张情真的同时,亦主张趣。他们反对传统古文宏阔高雅平正的格调,而是讲求文章的独得之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这种趣,是一种自然流露,具有主体的独特个性,亦是使人可触可感的。正是因为三袁主张真情、真趣,所以他们强烈反对那种“死前人语下”的盲目模拟因袭之文,认为“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倡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也”(袁宏道:《雪涛阁集序》)。时代在发展,文学亦同样必须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袁宏道:《序小修诗》)
由以上可以看出,三袁的“性灵说”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古文文以载道的文道关系,使“文”从“道”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树立了鲜明的创新旗帜,新的内容——人之性灵;新的文体——不拘格套;新的风格——自然之趣。继“性灵”理论之后,汤显祖的“至情说”,冯梦龙的“情教观”,直至晚明张岱的小品文理论,这一系列散文理论显示了古文理论的变化。在这些理论中,散文不再有拘束,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可以刻画人物,可以描绘风景……举凡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有真情自然之趣,即是可喜之文。这一新变使古文不必再循规蹈矩在正统文论及其创作模式之中,而与近代散文的创作相接轨。
三
“议论日新,文章日丽”,理论的新变亦带来了散文创作的新变。
中晚明散文创作的一个重大新变是大量小品文的涌现。“小品”原为佛家语,晋代高僧鸠摩罗什等翻译佛经,详本称“大品”,简本称“小品”(见《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后来,“小品”则指散文中的一种文体。这一文体到中晚明大为发展,其主要特点为内容上独抒性灵,无所拘束,形式上随意着笔,短小活泼,体裁上不拘一格,丰富多样,总之与传统散文的“高文大册”相对,显示出新鲜活泼、清新自然的特色。中晚明小品文蔚为大观,形成了一个上自徐渭、李贽,中经公安、竞陵,下至陈继儒、王思任、刘侗、张岱、祁彪佳的创作群落,成为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小品风格的散文虽不是明代所独有,但它的大量涌现,带有新的时代意义。首先,小品文在内容上将传统古文不屑的题材引入其中,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特色。如李贽的一些作品,在内容上突破了文以载道、宗经宗圣的传统,发起了对千百年来束缚人民的封建枷锁——纲常伦理、仁义礼教、孔孟圣道的猛烈攻击,对假道学、封建卫道士进行了剥皮剔骨、淋漓尽致地揭露,表现了对平等、自由以及个性解放的追求,表达了新的时代内容和启蒙思想家的不群与卓识。同时,与这一崭新的战斗性的散文内容相适应的,是其散文的杂文特色。这类文章嬉笑怒骂,如匕首与投枪狠狠刺向了封建传统、假道学和世俗之弊。如《赞刘谐》:
有一道学,高屐大履,长袖阔带,纲常之冠,人伦之衣,拾纸墨一二,窃唇吻之三四,自谓真仲尼之徒焉。时遇刘谐。刘谐者,聪明士,见而哂曰:“是未知我仲尼兄也。”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默然自止。
通过简练的笔墨,夸张的手法,将“拾纸墨”、“窃唇吻”却以“真仲尼之徒”自诩的假道学形象,与聪明士刘谐的反唇相击而自信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孰真孰假,孰为真真,孰为假真,在这鲜明的富于寓言色彩的生动形象中彰显无遗,而且深刻地体现出李贽反对迷信偶像反对盲从他人的思想。用漫画与特写手法,将深奥的哲理化为感人的生动形象,是李贽散文特别是杂文的一个显著艺术特征。这一特征在他的书答、议论、随感、序跋、传记、赠序等多种文体中都有所体现。如《又与焦弱侯》中那种“饿狗思想隔夜屎”的山人黄某形象(《焚书》卷二),《与焦弱侯》中以巨鱼而喻豪杰的描绘(《焚书》卷一),《圣教小引》中对那种“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前犬吠形、众犬吠声”的讽刺(《续焚书卷二》),《寒灯小话》第二段对“狗皮包倒人骨头”也不足以骂透假道学的嘲愤(《焚书》卷四)等,都立论惊挺而深刻,构思奇巧而自然,语言泼辣而风趣,使文章具有极强的透彻性与艺术感染力。
李贽的杂文式散文还具有严整而缜密的逻辑性。这类文章既有正面立论,又有反面驳论,更有正反结合之法,使议论犀利而精到。
我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绝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与曾继泉》,《焚书》卷二)
所云山农打滚事,则浅学未曾闻之;若果有之,则山农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何与诸人事,而又以为禅机也?夫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倖一时之宠。无人不然,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而独山农一打滚便为笑柄也!侗老恐人效之,便日日滚将去。予谓山农亦一时打滚,向后绝不闻有道山农滚者,则虽山农亦不能终身滚,而况他人乎?即他人亦未有闻学山农滚者,而何必愁人之学山农滚也?此皆平日杞忧太重之故,吾独憾山农不能终身滚滚也。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不知山农果有此乎,不知山农果能终身滚滚乎!吾恐亦未能到此耳。若果能到此,便是吾师,吾岂敢以他人笔故,而遂疑此老耶!(《答周柳塘》,《焚书》增补一)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其曰“圣则吾不能”,是居谦也。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
儒先億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矇聋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不曰“徒诵其言”,而曰:“已知其人”;不曰:“强不知以为知”,而曰“知之为知之”。至今日,虽有目,无所用矣。
余何人也,敢谓有目?亦从众耳。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续焚书》卷四)
《与曾继泉》正面立论,得出“我”陡然去发的决心和以异端自视的坚定。此虽一纸短笺,却气势磅礴,堂堂正正,真真表现出卓吾老子的异端形象。同时,虽“信”犹论,显示着李贽散文的一大特色,他的很多信笺,或长或短,都包含着深切的哲理,具有着辩驳议论的特色。又如《答周柳塘》是借回信周思久(字柳塘)而对耿定向的回答。耿定向曾说,李贽的离经叛道言行,如同颜钧(字山农)讲学会堂上就地打滚一样,是一种参禅悟道的方式。李贽在这里则对“山农打滚”的绝假纯真的意趣,与那种为追求名利而在权势者面前奴颜婢膝之徒的打滚丑志作了鲜明对比,文章层层深入,反复辩驳,在逻辑推理中予以形象描绘,既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又具有雄辩的说服力。《题孔子像于艺佛院》简直就是在逻辑推论中完成了对盲从世俗陋习的批判。在《与友人论文》中李贽曾说:“凡人作文章皆从外边攻打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余也。”(《焚书》卷一)李贽在这里强调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驳论手法,是他散文特别是杂文写作中的惯用手法,这一方法的运用,不仅大大增强了其论辩的尖锐与力度,同时也增加了强烈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就语言方面来说李贽的散文特别是杂文语言极富变化,有的尖刻冷峻,有的幽默含蓄,有的正面论述,有的反唇相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加之比喻、联想、夸张、借代、描绘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历史家特有的史实典故的引证,思想家哲理思辩的具象化、情趣化,使之作品确实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可以说,李贽的散文特别是杂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性质,思想的尖刻性、批判性,手法的丰富性、多样性,说理的形象性、情趣性,以及语言体式上的变化性、灵活性,都已呈现出了近现代散文特别是杂文的某些基本特征,成为传统散文向近现代散文转型的先驱。
如若说中晚明散文新变的先驱是李贽,那么,其中坚就是公安三袁了。如若说在这种新变中李贽以其杂文式的散文开辟了一个新境界,那么,公安三袁则在游记、尺牍、传序等多方面促进了这一新变的发展,其中尤以山水游记成就最为突出。袁宗道游记虽数量不多,但其中所体现出的不拘格套,随意挥写,以清新语言表达独特的主观感受,已表现出公安派性灵理论的真髓。袁宏道游记近90篇,极富独创性,达到了中国山水游记创作的顶峰。袁中道《珂雪斋集》游记类文十八卷,丰富而系统,使中晚明的散文新变更加显示出实绩。公安三袁以察情山水的豁达胸襟来与社会对抗,故而其山水游记具有深刻的意义。
首先,他们的山水游记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晚明文学新思潮所体现的追求生活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倾向。袁宏道说:“与其死于床笫,孰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布》)袁中道亦曾言:“回思向时与尘务相弊铩,以丘山之苦,易毫发之乐者,真如狂如醉,追悔莫及。始知予于山水间,亦有至性焉。”(《玉泉拾遗记》)可见,山水有“至性”,他们最理想的自适场所就是山水,全身心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是寻求生命价值的最佳选择,因为他们都是生性自由之人,即如李贽所说的“平生不愿属人管”。袁宏道《答王则之检讨》中说:“京中之苦在拜客,家中之苦在无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闭口不得,家中之苦在开口不得。”正是深谙个中之苦,故而三袁更是在山水之中寻求个性张扬的契机与自由自在的心境。
其次,他们的山水游记突破了旧游记的格套,主要以表性情为旨。袁宗道山水游记已打破了山水游记附着议论,借题发挥,或隐寓哲理和微言大义的传统写法,而是全凭兴趣和印象,记其可记,略去其余。在袁宏道笔下更是将表情与描写相结合,着重传达山水之乐与山水之趣。如“虎丘如冶女艳妆,掩映簾箔;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上方》),“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孤山》)。形象的比趣,将山水写得情味盎然。同时,在这种山水乐趣中还表现出了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表现出对世俗的追求与快乐。如《上方》篇中所描写醉酒而归的豪放:“乙未秒杪,曾与小修、江进之看月,藏钩肆谑,令小青奴罚盏,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胜始归,归而东方白矣。”这份纵情恣肆,既是属于山水的,又是属于作者的。
总之,山水游记至三袁手中,才真正显出游记本身的独特魅力,而不再附着于思辩似的议论。后世有人论及三袁的山水游记时,认为他们沉湎于山光水色之间,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其实三袁借山水以自遣是有的,但更主要的则是借助山水的自然真趣来表达对社会现实虚伪黑暗的对抗。恰如周作人《〈燕知草〉跋》所言:“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也指出:“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所谓不平、讽刺、攻击、破坏,当然首先是指李贽那一类杂感式的文章,同时也包含有公安三袁的山水游记之作。因为这类作品也是作者对现实不满的产物,只不过采用了以退为进的方式罢了。在三袁的影响下,后来的竞陵派、王思任、刘侗和徐霞客等也都在山水游记上取得了不同成就,尤其是徐霞客更是将实地考察的准确细致与游记的形象、抒情紧密结合,使其游记独具特色。
论述明中晚期散文的新变,不能不说到张岱。张岱是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他进一步扩大了小品散文的题材,进一步拓展了小品散文的表现手法,特别是进一步发展了小品散文的审美风格,把明中晚期散文的新变向前推进一步。
张贷小品文的内容极为广泛,诸如人物传记、民俗民情、观戏品茶、集市贸易、士女冶游,以至买卖妇女等,无所不有。加之公安三袁以来的山水游记的扩展,真是奇情状采,刻画了一幅幅社会画卷,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方式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散发着个性自由和反禁欲主义的启蒙思想的光辉,体现出明显的叛逆性质,以及反传统理学、追求思想解放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他的大量人物小品,摆脱了传统古文从政事、品德、礼教的角度来品评人物的特点,而着重表现以人自身为主题的人的智慧、聪明、才能和技艺,写出了人物独具的神质。《柳敬亭说书》中那位外貌奇丑而技艺极美的说书艺人柳敬亭;《濮仲谦雕刻》中那位“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而技艺巧夺天工的竹雕艺人濮仲谦;《五异人传》中那位一生落魄而偶得意外之财的“癖于钱”的瑞阳;《鲁云谷传》中那位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事事精办”、多才多艺的医生鲁之谷……。不管是大智还是小慧,不管其出身是尊贵还是卑贱,在张岱笔下,都活灵活现,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对于地位低微的下层群众的歌颂,反映了对社会普通人的尊重,对普通人价值的肯定。这一切都表现出晚明时期对人的价值的重视。
张岱的小品文还进一步发展了散文的审美功能,达到一种新的美学境界。如对说书艺人柳敬亭的描写,用柳的“黎黑、满面疤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的奇丑外表,与“口角波俏,眼目流利”、“声如巨钟”的说书技艺之美互为比衬,这种美丑映衬、美丑辩证的审美方式,反映了晚明时期对人格美力量的一种新认识,是中晚明时期社会资本主义启蒙中人的价值的发现在审美情趣上的一种反映,闪耀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这一审美思想与情趣在对自然美的描绘上也有所体现,如其描绘西湖之美,常人多喜爱其春夏之美、花朝之美、晴明之美,而张岱独喜爱秋冬、月夕、雨雪之美,因为这时的美是一种更具特色和个性的美。重视把握自然美的个性特色,是晚明个性张扬的时代特征在散文领域的反映。
中晚明时期散文的新变在以上论述的几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但是,既然成为文学发展中的一种新的潮流,也就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的创作思想,在作家群体中有所反映。实际也是这样,中晚明时期的很多作家的散文创作,都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在不同程度、从不同方面显示了这一新变的特征。例如,在明中叶秦汉、唐宋复古派如火如荼的斗争之际,文微明、祝允明、唐寅等书画家的散文创作,就已经显示出不依傍门户、独立自主、注重真情的特色。他们都颇具才气,性格中带有狂狷之气,且多受挫科场,仕宦不显。故而他们为文潇洒狂逸,有才子名士之气。如文徵明之文,不拘泥定式,笔法纯正而不刻板,其主风雅数十年,在他周围形成了“吴中才士派”。祝允明之文不拘体格法度,立意谋篇往往有出奇制胜之妙。唐寅之文喜文彩,风格峻爽遒劲,最富才子气。再如徐渭、汤显祖等戏曲家之文也溶入了这一新变的潮流。徐渭思想怪狂,异端色彩浓厚,与其杂剧“嬉笑之骂怒于裂毗,长歌之哀甚于痛哭”的风格相一致,其文抒情深切,主观色彩浓重。如《张母八十序》、《陈山人墓表》等文,或抓住某种特点或突出典型细节叙事写人,都饱含着作者惺惺惜惺惺的主观感情,在其怪诞乖张的背后,隐藏着诚志笃实之心。汤显祖主要创作在传奇。在戏曲上作为吴江派的对立面他提出“至情论”。为文也同样反对形式主义,提倡独创和情意趣。他在《答吕姜山》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其为文词采华丽,多骈俪之语,这同样是受到了南曲戏词绮丽之影响,是晚明张岱奇情状采的小品之先声。
阳羡口中,吐奇不尽;邯郸枕里,变幻无穷。总观中晚明小品文,虽形式短小却表达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和隽美的情趣,在散文创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并形成了一股主潮流,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在中国古老的散文中成为一种新变。
四
从以上论述可以窥见,在李贽“童心说”文艺观的指引下,从“性灵说”直到张岱的小品文理论,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散文理论体系。与此相呼应,在散文创作上也发生了新变,特别是小品文的创作鲜明诠释着新散文理论的精髓与要旨。由于这种变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首开近代人文主义文学的风气,故而说中晚明时期实质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新变期。虽然这些新变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在清代继成气候,但它如一股潜流暗蕴在社会机体的内部,待鸦片战争后,近代的很多学者文人在对中晚明启蒙思想认同的同时,对其文学新思想也给以充分的肯定。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股革新的文学思潮便如势不可遏的热泉,勃发而光大。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阿英、刘大杰等作家学者对中晚明的文学革新思潮都给以高度评价,甚至把公安三袁等视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在创作上,鲁迅杂文的嬉笑怒骂与李贽杂文宛若同出一辙,郁达夫的山水游记中时时可见袁中郎小品艺术的处处屐痕,周作人的美文与张岱之文具有着共同的趣味……尤其是“五四”散文的“为人生”和向人的内心探索的主基调,更是与中晚明散文解放思潮声气相通。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曾说:“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在指明中晚明时期散文新变与中国新散文的渊源关系上是非常确切的。由“五四”开始,散文在沿着这一渊源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创造,最终促使了现代意义的散文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