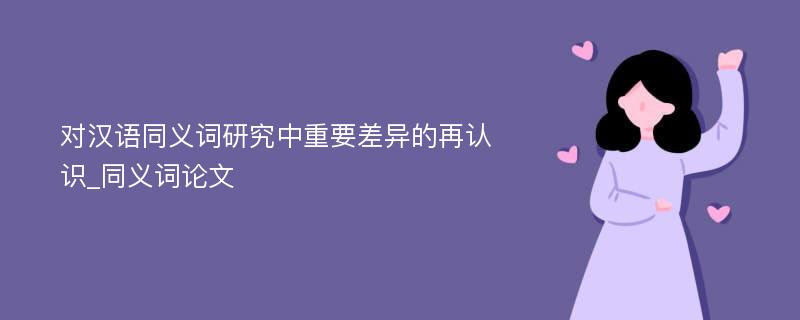
对汉语同义词研究重要分歧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汉语论文,同义词论文,分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存在的问题
从对五十年来的同义词研究概述(注:参见池昌海《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载《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8年第7期。)来看,半个世纪以来, 研究者们竭力寻找分析同义词的科学的方法、理论,使得在各个方面新说层出,体现出研究者们的辛勤与成果。但毋庸讳言,我们也发现同义词研究分歧迭出,其实质,笔者认为,在方法论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理论表述上的多元、摇摆
这是指在同义词的确定标准等理论上彼此摇摆,自身理论缺乏内在的系统性和外在的排他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同一理论系统的内在随意性,如陆善采在《实用汉语语义学》中认为:“读音不同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词,叫做同义词”,在举若干词例证明后,却紧接着从另外一个侧面得出了结论:“同义词所表示的是同一概念之内的各种细微差别。也就是说,表示同一概念之内的各种细微差别的词,才是同义词。”(注:陆善采:《实用汉语语义学》,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我们知道,“同义词”属词汇学范畴,而具有同一关系的“概念”则属逻辑学范畴,从词汇学角度立论,却得出了逻辑学的结论,其间的转移至少缺乏适当的过渡。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对某个对象采用多维的方法从两个或多个侧面来展示其性质,但就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同义词”与具有同一关系的“概念”之间有一致性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同义词并不都表达同一关系的概念,而同一关系的概念也并不都是用同义词来表示的(注:辛菊:《同义词和同一关系的概念》,载《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
另一种情形是,看上去似乎坚守了理论的统一,但实际上又将并行的其他说法糅进来,使之看上去周全些,但正是这一举动显示出对自己原有说法的不确定和犹豫。这种情形最突出地体现在刘叔新先生的相关论著中。关于同义词的确定标准,刘叔新首先强调他的“对象同一”说,甚至认为“所指对象的同一,是词与词成为同义词的决定因素”(注: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载《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而他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以下简作《描写》)中又将逻辑范畴与“义同、义近说”拉进来,从而在他的叙述中将三个方面糅合在了一起:“不同的词语只要各自的意义(当然是一个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就互为同义词语。它们在意义上通常互有差异……即意义内涵上互有差异……”(注: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11月版,第 280页。)这里显然强调了同义词的逻辑角度的规定。此后,他又将上述意思表述为:“相应的词语指同样的事物对象,互为同义词语”(《描写》280页 ),这突出了“对象同一说”。而在同一著作的另一个地方则提出了“义同义近说”:“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其主要理性义素或主要理性意义万分必定相同,也必须相同;意味方面,某个主要的理性义素或理性意义成分的是否强调,以及表达色彩方面等,则可以不同……”(《描写》282 页)我们且不讨论“对象的外延一致”的词语是否“就互为同义词语”,这一点,辛菊的文章已作出了较详尽的介绍。既然“指称(亦称所指、概括等)对象的同一”是“决定因素”,按照一般的理解,就应该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该说法的最早提出者孙常叙先生就是这样看的:“判别同义词,唯一的依据就是它们是不是根据同一对象?”(注:孙常叙:《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0页。)那么, 根据这一标准应该是可以规定同义词的主要属性的,词义角度的属性以及逻辑范畴的特性与它并不同处一个平面,至多置于补充或附加的地位。而事实上,据《描写》的行文来看,三个方面是很难分出伯仲的。三个不同的角度提出的三种主要标准,应该说是不能轻易地糅合在一起的。糅合的结果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如刘在《描写》中认为,“威望”与“声威”有共同的反映内容,也各有强调重点,它们同义,因为它们“有同样的意义外延”。而“改进”与“改良”也有共同的“反映内容”,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侧重,但却“不可能有相同的外延”,故不同义。从对这两组词语的深入分析来看,这一结论及其认定理由并不充分(详见本部分第二节)。
(二)认定手段上的主观、随意
迄今为止,共提出三种认定同义词的方法:替换法、义素分析法、同形结合法(注:参见池昌海《五十年汉语同义词研究焦点概述》,载《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 1998年第7期。),但没有一种被公认为是科学而有效的,在这三种方法中,“义素分析法”首先是该屏弃的,它在其发源地——西方至少在70年代以前就不断受到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批评,至70年代中期后已不再作为一种有效的语义分析方法而使用(注:徐烈炯:《语义学》,语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119页。),因此,作为一种主要的词义(主要针对类义、同义现象)分析法显然是不合适的了。即使在国内,在方法论意义上也被认为有太多的主观性、经验性而难于操作,如连每每在分析同义词时都很强调该方法的刘叔新自己也指出了它的致命弱点:“它不可能给检验提供客观的、形式的标志。”(注: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载《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因而该方法实际上仅限于举例分析。“替换法”是从应用层面提出的判断方法,简单而直观,其操作的有效程度也极易决断;同时,它也有相应的心理依据的支持,从而使它成为鉴别同义词最容易想到的手段。只是其性质和使用的条件尚需明确。对此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是刘叔新(注: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载《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而“同形结合法”,据其提出者刘叔新的解释是“以逻辑及加词形式为基础的”(《描写》284页), 其基本原理是:“如果甲+丙和乙+丙指同样事物,那么就可以确定甲和乙有同样的对象,互为同义词。”(同上)该方法可公式化如下:若甲+丙=乙+丙=丁(同样的事物),那么,甲与乙同义。试看刘著中的两例:
A.保护主权 维护主权:指同样的行为
“保护”“维护”:指同一种对象;互为同义词
B.博得掌声 赢得掌声:指同一种效果
“博得”“赢得”:指同一种对象;互为同义词
当然,“有时,甲词语和乙词语分别加上了丙词语,但不易分辨是否指同样的事物”,则可以启用辅助措施,即“那就须换以别的词语,至能作出判断为止;或者在加上同一个词语的基础上再多加上其他的。”举例如下:
C a
b c
繁荣: a1繁荣的城市 b1繁荣的商场 c1镇江是否繁荣的城市?
繁华: a2繁华的城市 b2繁华的商场 c2镇江是否繁华的城市?
刘氏的结论是:“a式不易看出a1和a2是否指同样的事物;换为b式就比较清楚……因此b1和b2指的不是一回事。”再加了c 式后又发现:“c1会得到毫无疑义的肯定的回答(?),而c2则会得到否定的回答或至少使人想作肯定回答时要再三踌躇。”因此,“‘繁荣’和‘繁华’各指不同的对象,是互为近义词而非同义词。”A、B例类可称为基本式,C例类可称为补充式。
我们觉得,刘氏的说法在以下两方面是难以解决的:首先,“丙”的选择条件是什么?是凭偶然性感觉吗?像A例, 如果“丙”选择“学生”、“农田”等词语,虽然“同形”却无法“结合”了。其次,“丙”的选择有无数量及规则上的制约?如C 例的操作就暴露了这一问题:既然a、b两组(注:c组在语法及应用上都不通)都有效,为什么选b而不选a?如果“丙”再被设定为“景象”等词语, 那又如何从“意义的外延”上来区别呢?若再看刘著中的其他词例,我们就会对其所谓“同样的对象”或“相同的意义外延”等提法产生疑问。如上节提到的“威望”与“声威”例,如果与“他有崇高的____”联结,我们就无法得出它们有“相同的意义外延”了。又如《描写》第297 页列为同义词的“凶猛”与“凶悍”等等,也存在同样问题。最后,如果将“同形结合法”与“替换法”比较一下,我们发现,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替换法”其本质可简述如下:设给定语言单位为“甲+丙”,其意义为“丁”,如果“乙+丙”的意义也等于或基本等于“丁”(即甲+丙=乙+丙=丁),那么,“甲”与“乙”为同义词。看上去两者不同处有二:一是“丁”的所指不同,前者指“同样的事物(对象)”,后者指“基本(主要)意义”。但根据刘著所述,“(事物)对象的本质特点和重要的一般特点,反映到词语的意义中来,是词语意义的主要理性义素或主要理性意义成分……”上举刘著词例也表明,所谓“同样的事物对象”也就是词语的指称内容。可见,“事物对象”与“词语(理性)意义”是从不同侧面对同义属性而运用的同义概念,因此,此“丁”与彼“丁”所指应该相同。二是叙述的角度不同,前者是选择一个词语(丙)与待检测两词(甲、乙)进行组配,通过比较查看两词的意义相同度,后者则是对有甲、乙组配成单位中的甲(用丙等)进行替换,通过比较查看两词的意义相同度。从实质上看,两者都是通过词与词搭配的方法来检测词语同义关系的。由此可见,“同形结合法”与“替换法”间是貌离神合的关系(注:詹人凤在《现代汉语语义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8页)中也有类似看法:“这种方法我们认为与替换说在实质上是相同的。”)。
(三)术语、概念上的游离、朦胧
同义词研究中另一个较明显的现象就是有的研究者使用术语、概念时缺少明晰而准确的界定。这种情形可以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容易使其立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表述上的精确性。如刘叔新在《描写》中“同一种(样)事物(对象)”、“同样的对象”等概念,表述本身的多样就已违反了科学表达的同一律,更为严重的是概念自身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根据字面意义及其陈述似指词义指称的客观对象,即奥格登、理查兹语义三角中“referent”(注:C.K.Ogden & 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Ark paperbacks,1985,p.11.), 如作者在对“保护”与“维护”二词运用“同形结合法”与“主权”组配时,认为它们都“指同样的行为”,结论是“指同一种对象”(第284页)。这里,“同样的行为”当为词语所指的客观对象,在作者看来也即“同一种对象”。而在解释“同形结合法”时又将“同样的对象”与“同一种事物”两个概念画上了等号:“两个词语单位若指同样的对象,那么各与同一个对象的词语相联结, 得出的两个联结体必然也指同一种事物。 ”(284 页)但作者在此前讨论确定标准时又将“事物对象”与词义等同起来(280页)。另外一种结果是它也容易给他人造成误解, 产生不必要的争论。如关于同义词的分类,传统的或多数研究者都分为等义词与近义词两类,其中“近义词”这一概念就颇有争议。有的将近义词界定为“(意义)并不完全相等,有种种细微的差别,应用上也不能任意替换”的词(注: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有的界定为“指称的事物、现象相近相似, 指称的意义大同小异,从而在用法上或色彩上也往往存在差别的一些词的组系”等(注: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从他们的陈述来看, 所谓“近义词”首先是属于同义词家族的部分成员,只是相对于“等义词”而言,是指词语间词义并不完全相等,而是在主要意义相同的前提下,在应用特征、附属色彩等方面有差异的次类词;其次,“近义词”不包括那些没有共同的主要意义作基础,仅仅相互间有类属关联的词语,如“美丽”与“中看”,虽然“美丽”一定包含“中看”成分,两者相互关联,但两词所含成分的“差异”远大于关联因素,而且实际表达中,语用价值也绝不相同、相似。
然而,尽管对“近义词”界定彼此间表述稍异,但大多研究者忽视了上述强调的诸方面。这便给所谓“争议”带来了可能,虽然这一“争议”仅仅是名词之争。如不同意将“近义词”划归“同义词”的研究者,主要理由是前者不“指同一对象”,而后者“指同一对象”;在意义上,前者是“概念属性中有某些相近相似或者相同的非本质的共同特点”(孙常叙,1956年,237页)、主要理性意义成分不一致(刘叔新, 1995年,287页)、 “近义词只指那种所指不一而又有相近的意义关系的词群”(注:周荐:《近义词说略》,载《天津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而后者则相反。
从上述论述来看,他们所指的“近义词”与上面多数或传统的研究者所用的“近义词”存在着质的不同(如周荐即说:“同义词间的意义和近义词间的意义关系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出处同上),本不应产生争执,但一些论者却将两者牵扯了起来:“是否指同一的事物对象,成为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区别标志和划分准绳”(注: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载《语言研究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不应将同义词语、同义关系等也称为近义词语、近义关系,而必须视同义与近义为两种判断有别、不容相混的范畴。”(《描写》, 286页)之所以说这一争论仅仅是名词之争,理由如下:一是如上所述,从理论上讲,孙、刘、周等所言的“近义词”与多数或传统研究者所言的“近义词”,本质上不同,两者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是从实践看,两种说法在具体分析时出现交叉现象,即被刘等批评的不该归为同义词的“近义词”用例,在刘著中却被处理为同义词,只是不再叫“近义词”,而称“一般同义组”。下面以《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刘叔新主编,简作《词典》)与《现代汉语词汇概要》(武占神、王勤著,简作《概要》)为例,略举几个作一比较:
词例 干预-干涉
功劳-功勋
鼓动-煽动
希望-期望盗窃-偷
《词典》同主147页 同义161页 同义164页 同义495页 同义458页
《概要》近义129页 近义128页 近义129页 近义130页 近义111页
从该表可知,两方在对实际词语的划归上有共同性,区别在于所给予的名称;三是反对者自己也同意同义词中有些词之间是近义关系,所以不能称为“近义词”是因为该概念已被用作称没有同义关系而意义相近的词。如刘在《描写》中说:“彼此有同义关系的词语,绝大多数由于只存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从某种逻辑推理(?)来说,就未必不是近义。但是既然那些彼此意义相近而没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已称为近义词语(?),为了在词汇学中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词语关系,就不必把同义现象也看作近义现象……”(286 页)这段话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首先,作者也认同那些“有同义关系的词语,绝大多数由于只存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它们之间实质上有“近义”关系;其次,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被多数或传统的研究者称为“近义词”的绝非是“那些彼此意义相近而没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将此类词称为“近义词”的也仅有孙常叙、刘叔新、周荐等屈指可数的几位,这一点,连周荐自己也承认,不过是在说明反对方的正确时用作反衬的:“正是在这主张近义是同义词语的根本性质的观点占压倒多数的背景下,有学者(据其下文应指刘叔新——引者注)独树一帜,指出了把近义看作同义单位的本质特征并进而把近义混同于同义的做法的危害性。”(注:周荐:《汉语词汇研究史纲》,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足见,坚持“近义词”不是“同义词”的说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中都没有充足的理由,纯属名词之争(这可能也是迄今国内大中学校汉语教材中绝大多数仍坚持将“近义词”作为同义词成员的真正原因)。所谓“独树一帜”(按:这一评价本身与周的行文也有矛盾之处——在该书第98页又指出刘的观点系来自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并对此加以深化,可见持相反意见并非一人,而且远早于刘,因此“一帜”固有,而“独树”却不实)的真实价值也可能应重新评估。
(四)古今汉语同义词研究投入不均
综观近几十年的研究,相对来说,现代汉语同义词研究投入的力量远多于古汉语的,尤其是理论方面。后一方面的研究在《汉语词汇史纲》中少有反映,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的。近期有代表性的如高守纲的《古汉语词义通论》(语文出版社,1994年)一般地讨论了同义词的定义等。冯蒸的《说文同义词研究》(首都师大版,1995年)对《说文》中可能的同义词进行了归类;马景仑的《段注训诂研究》(江苏教育版,1997年)中列专章总结了段注中同义辨析的方法及成果。而王凤阳的《古辞辨》(吉林文史版,1993年)、黄金贵的《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版,1995年)则主要以类义词、同义词为对象辨析了古代一些语词间的同异;洪成玉、张桂珍的《古汉语同义词辨析》(浙江教育版,1987年),王政白的《古汉语同义词辨》(黄山书社,1992年)则集中考辨了一些同义词的异同。但皆系纵向综论类型,这对科学总结某一共时状态的词汇结构系统以及认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都缺少针对性,而弥补这一缺陷的、系统地对某一断代文献作较全面的研究尚处空白状态。
二、本文的认识及尝试
首先,必须申明的是,确定同义词的认定标准、划定范围等工作,其目的在于方便我们欲开展的工作,即认识同义现象,辨析具有同义关系的词语间的差异,最终为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等服务(古汉语同义词研究与此相比则另有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周祖谟先生的看法:“我们研究同义词的积极意义在于如何从许多意义相似的同义词辨别出它们彼此不同之点,以便在应用时能够选用恰当的词,正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至于不同的词是否属于同义词范围之例,似乎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注: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页。)当然,“不是很重要”并不是不重要,在具体研究中,为保持研究范围的相对确定及研究系统的相对完整,对同义词确立相对稳定的界定范围应该是必要的。
我们认为要较妥当地找到同义词的标准、范围及做好辨析,基础的工作是正确地解释同义词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产生的客观基础、主观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探求这种现象可能存在的逻辑差异状态,最后据此归纳上述所提及的标准和方法。
(一)同义词产生的客观基础与主观需求
1.客观基础。不管“同义词”该如何定义,作为词语中的异形同义的现象是一个自有语言以来便存在的事实。那么,这一事实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呢?首先,客观对象本身的界限相对模糊性产生同义词。如“广阔”与“辽阔”便是此类情形,两词都有“既宽且阔”义,但有时侧重于“广大”,有时侧重于“辽远”;又如“优良、优秀、优异”等;古汉语中的“旦、朝、晨、夙”等词也属此类。其次,历史文化的变异导致同义词的产生。人类社会的等级价值观念促成了相应同义词的出现这一现象,便是很好的例子,如同是表“失去生命”意义,在秦汉及先秦时期用“死、崩、薨、终、卒”等不同形式来表示,而同为“在外过夜”意义,现代则有“住宿、下榻”诸形式。第三,地域差异也会产生同义表达。同一语言系统内,不同地区对某一事物、行为或状态等常会采用不同形式的表达。如秦汉时期,同为“猪”义,“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狶”(见《方言·卷八》);在现代,同为“厨房”义,吴语区说“灶头间”,福州说“灶前”等。第四,词义演变导致同义词。原来不同义的词经过一定年代的意义演变而具有同义关系,如“穷”与“贫”本不同义,前者指仕途不济或无业,但既因“穷”,则当与“贫”相关,如孔颖达疏《左传·昭公十四年》“分贫振穷”时说:“大体贫穷相类,细言穷困于贫。贫者家少财货,穷者全无生业。”因此,“穷”后来分离出“贫”义,从而与“贫”构成同义关系。又如“囹圄、狱、牢”等,也属此类情形。
2.主观需求。同义词的生成既有上述的客观基础,同时也有主观上的需要:第一,显示描述对象的细微差异。如“皮、肤”在秦汉时期就有适用对象上的不同,故《史记》中“肤”仅用于述人,“皮”则主要用于述兽畜;而《淮南子·说山训》中的“宁一月饥,无一旬饿”,就体现出“饥”在程度上较“饿”浅;而“趋、走、奔”则能表现古代的礼仪规约(参《说文解字段注·奔》)。第二,表现作者的主观态度。如对同一个人“死”的记述,《史记》与《汉书》多选择不同的词,如司马迁记汉时大臣时多用“卒”,而班固则多用“薨”,如丞相申屠嘉、陈平及樊哙、灌婴等概莫能外。我们知道,按儒礼,“卒”指士之死,而“薨”指大夫之死,两书用词的不同表现了作者的态度与情感。第三,取得表达上的特殊效果。同义词除了可以满足内容上的要求外,还可以实现表达形式上的特殊效果,如为前后对称、语音节奏以及语体风格协调等提供选择手段。
(二)同义词差异的三维表现
以上从两个方面讨论了同义词产生的可能基础,下面我们将宏观地对具有同义关系的词语所可能出现的差异进行简要构拟。笔者认为,其差异可以从三个方面(即三个维度)来看:首先,词语指称对象本身的差异。如古汉语中“商、贾”被视作同义词,历来有“坐”贾“行”商之辨。此辨实则为指称对象之辨。又如“功劳”与“功勋”则源于两者指称对象的范围大小不同,等等。另外,指称对象本身的文化伦理差异也会表现以词语聚合的形式,如“帝、皇、后、王、皇帝”构成同义词群,但它们所具有的历史内涵是有相对时代限制的。其次,语言符号意义的差异是同义词之间不同的主要方面。词义特征便为基本表现,如程度、情感色彩、称述视角等等,其他如语法能力等都可构成同义词的差异。最后,语用(修辞)能力的差异,包括词语的应用能力和修辞价值。应用能力虽不是词语本身的属性,但在同一意义的词族中应用能力的差异也是它们特性的外在反映,因此也当视作词间差异的构成因素。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就整个同义词来说的,在具体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同义词的差异除了一些共同参数如适用对象、情感色彩、语体风格外,还有一些是为特殊词类所具有的,如名词可有事物质地的不同,如古汉语里“扇”与“阖”都有“门窗”义——《说文·门部》:“阖,门扉也。”《说文·户部》:“扇,扉也”。段注则进一步引郑元注解析出它们在质地上的差异:“《月令》:‘乃脩阖扇。’注云:‘用木曰阖,用竹苇曰扇。’安析言如此,常言则不拘。”而动词则可有行为施事的差异,如“住宿”与“下榻”,则因行为施事地位等不同而作不同的选择,等等。而这一特点在现有的研究中多被忽略了。
(三)确定标准
在经过上述讨论之后,我们来看看在研究过程中如何给所研究的对象下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义,框定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通过上面的讨论可知,同义现象从产生的角度上说,源于不同的词语的指称内容相同、相近,无论其具体途径差异如何;从实际价值角度上说,在于实际表义上的丰富性与表达风格上的多样性。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同义”提出如下的界定和说明:若干个词语间,如在同一意义层面上有一个相同、相近的义位内容(对于单义词来说也可理解为词义核心),则诸词语具有同义关系。关于该定义及同义关系构成,要说明以下几点:
1.“同义”是就词的某一个义位而言的,并非针对整个词及其意义。
2.所谓“同一意义层面”,指构成同义关系的词义在逻辑层面上应属同一层次,不得越级串联,如“马”——“白马”虽有共同义位或词义核心,但具种属关系,不同义。
3.具有同义关系的词语的最终判定是规范作品(包括口头与书面)的实践用例,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因为确定研究对象的依据是对象本身的存在状态,旨在研究的科学、方便,而不能方枘圆凿,要求实际材料为自己的理论作出牺牲。
4.定义中“近义”指在同义(指理性意义)前提下词语间在附属表达色彩上有差别的情况,相对于“等义”而言,如“鼓动”与“煽动”、“迎接”与“迎迓”等,而不包括仅仅出于某种形式的关联所产生的相近,如“富丽”与“美丽”,有人认为是同义词,但它们仅仅是因含有共同的语素“丽”而造成的误解。为避免在理论及实际操作中可能带来的混乱,本文拟在给同义词分类时将有同有异的称“基本同义词”,将完全同义的称为“特殊同义词”。
5.关于词性与同义关系。从理论上说,研究同义词,“意义”无疑应该是首要的依据,词性属于句法范畴,不必把两者放在一个层面上考虑。承认这一点,并不是回避词性问题。这主要是由词性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词性决定于词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及它的组合能力所反映出的抽象的语法属性,它实现的是语言单位之间的结构功能,而不记载和表现人对客观对象的正确或歪曲的认识结果,因此,我们不能从某个词的词性得到其具体词义。但我们又须进一步地看到两者间的关联,那就是,从逻辑上说,同类词性的词的意义在反映客观对象及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的特征上,是具有词义指称的共同类属性的。如名词类的词记录的是人对客观对象、主观世界等事物、概念的命名;而形容词类的词的意义是对事物、行为的属性、状态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从某个词的词性中得到其相对词义指称的共同类属性。词语间同义,当然首先得有词义指称的共同类属性这一前提,这就势必推导出“同义词语应该有相同的词性”的结论。根据这一结论,我们觉得“刚毅”与“毅力”、“勇敢”与“勇气”(注: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是不能成为同义词语的。 但语言终归属人文现象,偶然性当然不可忽视,加上各人认识角度及程度的不同——如个别词的定性[“永久”、“永远”,刘叔新(《词典》)定为副词,林祥楣则认为前者为形容词,后者为副词(注:林祥楣:《现代词语》,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兼类词的认定等,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个别的、例外的存在是正常的。否则,即使避而不谈,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突然”与“忽然”等词语,即使按“同形结合”法也不好说就不是同义词:“他突然倒下了”与“他忽然倒下了”,“突然刮起了风”与“忽然刮起了风”等两对“词语单位”间在“所指的事物对象”、“意义的外延”、“主要理性义素或理性意义成分”上有什么区别?然而在刘叔新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里是找不到这类词例的。
(四)辨别方法
在给同义关系作了界定以后,我们能采用什么方法或步骤来辨别同义词呢?笔者觉得“类比”与“归纳”两种方法的结合是比较可行的。“类比”指将待确定及待辨别的若干词语意义尤其是内含这些词语的语句意义进行综合比较,较全面地得出各个词语意义、语法及语用等方面的特点;“归纳”指在此基础上总结若干区别特征。具体步骤是:假设有待确定或辨别的“同义词”:A、B、C、D,第一步是找出含有上述词语的所有(这在理论上可行,在实际上只能是尽可能)典型用例。第二步是运用替换(注:关于“替换”法,需作若干说明。首先,这一方法不是最终的判定手段,因为有些词例在附属表达色彩或习惯用法上的特点而导致它们在实际运用中并不能自如替换,如“煽动”与“鼓动”两词,在句子“他们____不明真相的群众到省政府门前闹事”中,其中空处一般用“煽动”,而在句子“经他一____,不少人都去学习气功了”中,其中空处则多用“鼓动”;其次,这一方法的使用有前提限定,即在理论上替换前后的两个语言单位的实质或基本意义( essential meaning)应相同或相近。如上举两词,在实际运用中不能随便替换,但在理论上,替换前后在“用语言、文字等激发人们的情绪,使他们行动起来(做)”这一本质意义上有共同性,但在附属表达的情感色彩上不同,从而将两者确定为(基本)同义词;第三,因为上述两点,我们认为,“替换法”只能看作同义词认定的辅助方法,因而,“可替换性”也就不能被视作同义词的基本属性之一。)的方式初步确定这些词的同义资格。与此同时,在对每个词语在典型例句中的特征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得出的词义特征称聚合特征),我们还要对不同词语的例句在可替换或不可替换的情形中找寻其存在的同和异(得出的特征称组合特征)。第三,对前面得出的词义聚合特征和词义组合特征进行细致地归纳,按一定秩序梳理出该组同义词语间的差异。
最后,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对“鼓动”、“煽动”两词的词义同异举例作一简析。其中同点有三:
1.共同义位——皆可指用语言、文字等激发人们的情绪,使他们行动起来(做)。
2.语用能力——皆只用于转述(指记述或陈述他人行为,与“自述”相对)。
3.附属色彩——皆可用于口语或书面语。
异点有五:
“鼓动” “煽动”
1.施事动机善良(鼓动他去学英语)险恶(煽动他们闹事)
2.行为状态个体或群体性行为 群体行为
3.附属色彩中性 贬义
4.语法特点后面常带主谓结构成兼语式 可直接带动词宾语(
煽动罢工)
5.运用语境普通 特殊(多见于政治性
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