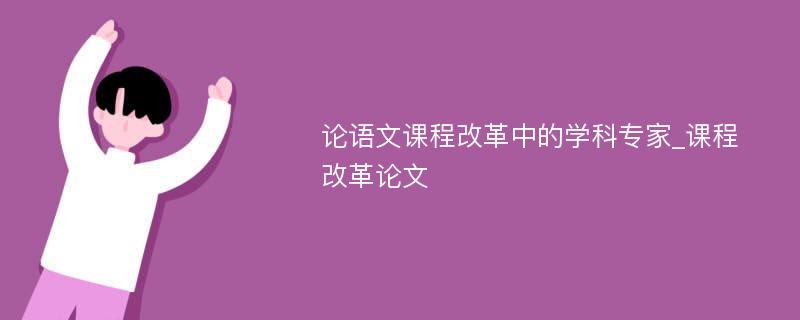
论语文课程改革中的学科专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课程改革论文,学科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1世纪初的语文课程改革中,原先从事语言学、文学等学科研究的专家(以下简称学科专家)纷纷参与语文课程标准的制订和修订、主编语文教科书、发表大量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著。他们发声最多、影响最大,可以说是他们主导了这次语文课程改革,给语文教育改革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目前对这些介入语文课程改革的学科专家的评价存在天壤之别。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学科专家介入语文课程改革的价值、态度、行为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学科专家的准入条件。 一、语文课程改革是否需要学科专家? 泰勒认为,学校教育目标确定的三个来源包括对学习者本身的研究、对校外当代生活的研究和学科专家对目标的建议。[1]前两者主要依靠专门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专家的研究。学科专家的意见虽然十分重要,但作用有限。说重要是因为教育学研究者对语文课程的本体即语言学、文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逻辑结构、学习方式、未来发展等方面的理解并不深入和全面,对这些知识中哪些最有价值、十分重要也不清楚,而学科专家恰恰相反。说作用有限的原因之一是学科专家不太能正确、全面地认识受教育者的需要。一方面,学科专家往往不清楚学生作为社会公民的一般需要。以教育目标的确定为例,泰勒认为许多人批评教育主管部门利用学科专家来制订教育目标的理由是“学科专家提出的目标太专门化和专业化,或在其他方面对大多数在校学生不适宜”[2],学科专家错误地把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视为未来的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数学等领域的专家,像要求大学生那样规定学程。他们应该把学生视为未来的普通公民,同时思考“你这门学科对那些不会成为这个领域专家的年轻人的教育有什么贡献?你这门学科对外行或一般公民有什么贡献”[3],然后再制订相应的教育目标。另一方面,学科专家往往不清楚学生支撑未来发展的全面需要。学科专家一般从自身学科发展的角度,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强调所研究的学科的重要性。例如,从事古汉语研究的专家认为语文主要应提高学生的文言文读写能力,从事现代汉语研究的专家认为语文主要应提高学生的现代汉语读写能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认为学生应能背诵大量的古典诗文,而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认为学生应广泛阅读现代名著。在不同教育目的观的指引下,他们在制订课程标准、确定课程内容、编写教科书时,一般偏重自己熟悉的学科领域而降低其他学科的地位,减少其他学科的内容。学科专家作用有限的原因之二是他们不太懂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尤其对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的知识不太了解,经常发表一些有悖历史常识的言论。如有人称20世纪30年代叶圣陶反对以知识点讲授为主要内容的教学而主张进行文本细读。其实,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夏丏尊与叶圣陶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就是20世纪30年代“知识+选文”型教科书最典型的代表。又如,有人称本轮课程改革开设选修课程是创举,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许多中学开设过选修课,20世纪后期的课程标准也不时有相关的规定。一些专家在对待语文课程(教材)与教学问题时,多凭经验而不是学理,凭直觉而不是分析。尤其在对待有关教材编写、教学实施的问题上,他们基本上是靠自己所理解的“教育哲学”加上自己在中小学时的求学经验和在大学任教的经验,缺乏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依据。如此次课程改革中,一些学科专家一概否定知识教学,排斥必要的训练,主张语文教育的目的是“立人”或培养“语感”,认为语文教学内容主要是审美,强调教无定法、重道轻技等。这些主张貌似合理,实则违背了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 总之,语文课程改革需要学科专家的参与,但是学科专家的作用是有限的。无论是学科专家本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是普通语文教师,对此都应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认为学科专家就是“真正的专家”,甚至是“专家里的专家”,应该对学科专家的作用进行必要的认定。 二、介入语文课程改革的是哪些学科专家? 从介入语文课程改革的态度来看,学科专家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蔑视型。从行为上看又可分为排斥和拯救两种。排斥型学科专家认为教育学根本就不是学科,公开宣称教育学不是什么学问,不屑从事这一学科研究。拯救型学科专家承认教育的重要性,却以救世主的身份进行语文教育的言说。拯救型学科专家又可细分为两小类。一类是自称“门外汉”实则以“内行”的身份进入。这类人嘴上说自己是“门外看语文”,心里却想着“门外的人往往比门内的人看得更清楚”[4]。这些学者大多受胡适谈中学国文教授问题的影响,但是他们忘记了两点:一是胡适发表此说的时间是学科研究起步期,那时因为专业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都很缺乏,胡适等人与专门研究中学国文教育的人之间很难用专业与非专业来区分,和现在论者所处的学术环境迥然不同。二是胡适明确指出自己只是提出一些新鲜意见,仅做参考资料而已,和现在论者的心态也迥然不同。另一类专家认为,既然研究语文教育的没有学问,那么自己虽是外行也比内行更有学问,比内行更内行,于是要冲锋陷阵、攻城略地。当然,有人也指出还有一种情况:一些学科专家在本学科已经做不出更大的贡献又受名利驱使,于是转移阵地到语文学科从事“学术抢滩”工作。 二是敬畏型。从行为上看又可分为避让和介入两种。敬畏型专家认识到教育学是一门学科且相当重要,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必须是专业的教育学者,认为自己只是对文学、语言学等学科有所研究,与教育学还存在一定的隔膜,在教育学者面前,自己是真正的外行。避让和介入的专家代表分别是陈平原先生和王富仁先生。陈平原先生曾经被邀请参加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但是在参加几次会议之后他果断地退出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之所以主动退出,是因为“中学语文教学是一个专业,不是‘客串’一下就可以搞好的,我们必须尊重这个专业”[5],“为中小学生编教材,这是一件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能只是‘玩票’,随便进来插一脚”[6]。王富仁先生虽然从事了大量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如参与了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主编了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培养了语文教育专业的博士生,出版了《语文教学与文学》等著作,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清醒的、谦逊的介入者。潘新和先生在写《语文:审视与前瞻(走进名家)》前,准备将早先从事语言学研究而后来参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研制和语文教育研究的一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但是这位学者觉得自己并不值得研究。 三、语文课程改革需要何种学科专家? 如果以态度和行为两方面作为判断语文教育研究所需要的学科专家的标准,那么语文课程改革需要的是对教育学(尤其是语文教育学)心存敬畏、认真学习并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去研究语文教育的学科专家。 先说敬畏的态度。鲁迅在《名人与名言》中对这种随意跨界摇身一变成为其他学科“专家”的行为进行过讽刺。他说:“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7]在此次课程改革过程中,一些原来从事文学、语言学研究的专家,摇身一变成为语文教育专家,不知己“悖”,四处发声,信口开河。他们应该认识到在语文教育学面前,自己真正是“小学生”。学科专家之所以纷纷主编语文教科书,不仅有利益驱动的因素,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就是选几篇文章,加一点注释,设计几个习题,再写一些解读文字而已。他们不知道教科书的编辑是一项十分专业的工作,需要专业人员来完成。1939年,署名“端”的作者指出,编写国定教科书应十分审慎,“教科书为数百万儿童的恩物,影响至深且巨,决不能粗制滥造,自应审筹熟虑,斟酌至当”,“担任编辑者须为有学识而且有教学经验的人。因为教学是一种专门的技术,与理论截然不同,譬如对于理科有精深的研究而无教学经验的学者,所编成的教科书,一定不切实际。因此,我们希望教部能审慎选择专门人才,以担任编辑的工作”。[8]1942年,又有人指出:“编辑教材的人,应有专门的修养,才能称职。第一,他有编辑教材的经验与技术;第二,他应了解现代教育的原理与趋势;第三,他应了解儿童学习心理;第四,他应了解中国教育的需要;第五,他应有实际的教学经验。这五项都十分重要,缺了任何一项,不能成功一个优良的编辑。”[9]可见,编写教材的人员,首先应该是对教育学素有研究的学者(虽然不必是一流的教育专家),其次才是在某一学科领域有突出成就的学者。因此,学科专家应该像陈平原、王富仁先生那样,真正把自己当成“门外汉”,对这一学科心存敬畏,热心投入、真心研究,与语文教育研究者、语文教师虚心探讨,谦逊地认为自己的见解是一孔之见、自己所说仅是一家之言,别人尽可姑妄听之,而不能把自己当成“全国语文教师的教师”,发号施令。 再说研究的行为。学科专家对语文教育进行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固守自己的学科立场,思考自己的学科与语文教育的关系,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去研究语文教育。术业有专攻,从自己的学科出发来谈其他学科,才能显示出内行的功力,才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有所贡献。例如,杨文虎先生主编的《文艺学与语文教育》、蒋成瑀先生著的《语文课读解学》、王建华先生著的《语用学与语文教学》等,均是这种研究取向的典范之作,为语文教育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有学者用社会学理论分析语文教科书中的人物形象,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统计百年语文教科书中一些词语的数量变化进而分析其内涵的演变等,这些研究也十分有价值。另一种方式是放弃自己的学科立场,重新学习教育学,从教育学的角度去研究语文教育。这种方式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因为教育学是一门“易学难进”(入门容易但精深很难)的学科,需要阅读大量的教育学原著并从事(观察)中小学语文教学实践。不经历潘新和先生所说的“述学”、王富仁先生所说的“补教育学”和到中小学去听课甚至兼课的过程,那么对语文教育的见解往往只能流于肤浅和褊狭。这些年来,成功转型的学科专家可谓凤毛麟角。 目前,介入语文教育的学科专家动辄以20世纪前期胡适、黎锦熙等人积极投身中学国文教育建设来证明自己言行的合理性,但是他们只知道介入,不了解胡适、黎锦熙等学科专家对待国文的态度和行为。胡适1920年发表了《中学国文的教授》等论文,1923年草拟了《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对中学国文课程(教材)和教学进行了全面规划。即便是渊博、睿智的胡适也承认自己确立课程目的时“没什么标准,全凭理想立言”[10]。这与今天一些文学、语言学专家以“语文教育专家”自居,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真理的态度和胸襟截然不同。又如,1920年教育部宣布“国文”改为“国语”之后,社会各界纷纷埋怨甚至指责教育部行事鲁莽,认为在国语是什么、怎么教等基本问题还没弄清楚的情况下就力推改革显得很不负责任。面对这些责难,参与推动这项改革的黎锦熙并没有凭借自己早年从事过中学语文教科书编写、当时在教育部担任教科书审查员期间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和钱玄同等人开展语言文字改革研究的成果与责难者展开无休止的论战,而是积极投身国语教育的研究之中。他从1920年开始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为师范生开设《国语国文教学法》和《国文教材研究》课程,经常和附中的教师讨论国语教育,到全国各地考察国语教育,并相继出版了《新著国语文法》《新著国语教学法》和《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等著作,指导编者怎么编语文教材,指导语文教师教什么、怎么教。 总之,学科专家在语文课程改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语文课程改革需要对语文教育心存敬畏、努力学习并能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去研究语文教育的学科专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