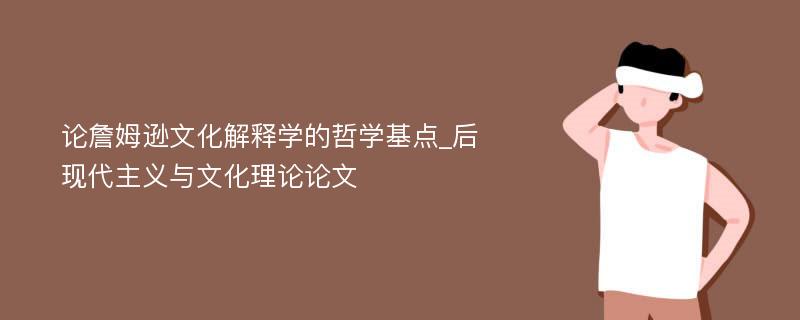
论杰姆逊文化阐释学的哲学基本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点论文,哲学论文,文化论文,论杰姆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杰姆逊的理论性格
弗·杰姆逊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由于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与对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被公认为当今具有深远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权威。在70—90年代间,他写出了一系列著作,如《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诊断学》(1982)、《后期马克思主义:阿多尔诺或辩证法的持久性》(1990)、《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等。这些论著被译成不同文字,为杰姆逊赢得了世界声誉和地位。杰姆逊以研究、讲授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的阐释为己任,到过欧洲各地讲学,并自1985年来北京大学授课后多次来中国。早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中,他就已经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应该随着时代而被赋予不同的特点。杰姆逊的研究视野开阔,他以敏捷的思维、灵活新鲜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执着信念融入当代,在“后现代”语境下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一度被视为“陈腐教义”之古典传统。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有资格自称要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在多元格局中的“优先地位一辩”,尽管他的理论不无纰漏、甚至重大原则的错误。
以下我们从几个方面,对他的建构性文化阐释学的哲学基本点和特性加以概括。
(一)唯物主义反映论与经济(基础)决定论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来自“主体论”、“价值论”与心理主义的挑战与认识论相关。而当代唯物主义哲学所接受的挑战,也正是对认识论的批判与否定,这方面遭受攻击最甚者莫过于反映论。然而反映的观点可以说贯注于杰姆逊的所有论述之中,虽然他没有专门谈反映问题。在这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悬置法”,即加诸括号、存而不论,似乎是一种方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的哲学认识论根基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反映论在《政治无意识》中也可视为“存而不论”的东西。因为一方面如他所说,“历史不是本文”,我们绝不真正在作为一种‘物自体’的鲜活性中,直接面对一个本文”,而只可能达到的是“本文”化的“历史”。在这里,不可及但却是实在的客体的历史对“本文”化的“历史”,是作为“不在场(缺席)的原因(absent cause)”,它的出场也只有通过本文化,方能为我们所认识、所研究。“缺席的原因”虽不在现场,但却是最根本的决定论的原因。在这里所说的“不在场的原因”也就是胡塞尔的括弧中的“原因”。不过杰姆逊没有提及胡塞尔,而是从阿尔都塞对“机械的因果律(mechanical causality)”与“表现的因果律(expressive causality)”的批判中转述的从斯宾诺莎那里来的,即把“上帝”替换为历史的第一位决定论原因之客观社会存在,表达作为历史第一客体的自在与第二客体的本文化的存在,以及现时的第一客体的政治无意识与第二客体之阅读和写作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他的“政治无意识”实质上是经济无意识,政治无非是“本文”化了的经济,因为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的情况中,“最终决定的要求”是经济,经济是政治本文中作为“不在场的原因”之“上帝”,而政治又是文化的和文学的本文中的“上帝”,它们之间是一环套一环的中介关系(大括号套小括号的连环)。以此见所谓“无意识”是对“本文”原因的无意识——因其不出场而对其无意识。所谓“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述”也就是在决定论之中、而又不知身在其中的叙述。在这里一切非决定论和多元决定论的出现都归结为一个唯一的决定论。
早在1972年研究俄-法结构主义批评的《语言的囚牢》一书中,杰姆逊就认为结构主义的“二项对立”原则作为语言结构同现实的“有机结构”是“同构”的,带有精神特性的语言和形式的东西与现实东西的“同构”性实质上就是现实矛盾的反映。在《评论之评论》一文中,他更为直接明确地认为“一种确定的文学形式的存在总是反映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可能的经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 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445—466页)。80年代以来,他在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状况的分析中,把后现代主义既作为一种风格,更作为资本主义第三发展阶段的“文化逻辑”。这种逻辑对于历史就是总体性的反映关系。从反映论这个出发点必然导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著名的大段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 —83页),再加上剩余价值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综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9页)。因此,他对文化的批评阐释既立足于经济决定论,又强调意识形态各层面在功能上的“半自律(相对独立)性”,并将其归结为阶级的意识,而文明的历史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一切阐释最终都是政治的”(《政治无意识》,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0页)。在《语言的囚牢》一书中,他批评结构主义把上层建筑与现实隔离开来,而导致一种“唯心主义”。阐释的“去神秘化”作用归根到底是意识形态分析,即显示出“意识形态真面目(ideological unmasking)”。他指出, “神秘化”的根源在于现象与本质分裂,而意识形态的本质根源于现实的阶级关系。他把这种分析的原则与方法贯穿于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本文阐释中,在宏观上把它们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历史分期加以对应,并以后者为决定论的依据。
(二)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与《语言的囚牢》中, 杰姆逊已经反复声称自己的批评是一种“辩证法批评”,认为“没有对矛盾的认识(也就是没有辩证法的思想)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并系统地表述了辩证的批判观,指出“辩证的判断使我们能实现内部与外部、内在的与外在的、实存与历史的一种暂时的结合,但这是一种通过对我们自己进行客观历史的判断而付出了代价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38页)。杰姆逊的辩证思维方式的灵活性为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带来一种独特的理论格局,即打破一般的学科的与文化的分类——批判笛卡尔式的传统,把文化现象,甚至经济政治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压缩成为一个整体性——资本主义与文化逻辑。他认为:“最简单的、表面的东西也就是最高级的东西,……对文化或任何事物的理解只有通过交叉考察,或学科间互相涉指、渗透才能获得完整全面。”(《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7页)
这种辩证法也贯穿于对历史与本文关系的论述中,贯穿于关于阐释之“总体”与“中介”范畴,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处理道德、美学、认识与历史的一系列对策中。正如他在《政治无意识》一书前言第一句话中所说:“总是历史化!——这个口号——这个绝对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切辩证法思想的‘超历史’的专断……”。辩证逻辑的“超历史”的专断在总体化的历史专断之中。正是辩证法使他免于机械的反映论与经济决定论,而展开为一种宏大的历史观。
(三)历史主义。在1979年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中,杰姆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在这里“绝对”可以理解为“辩证法的‘超历史’的专断”,这种历史观不是对过去的苦思冥想,而是一个“现在的客观境遇与一个过去的客观境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价值理论的个人发现”不只是出于他的思想体系,也是“历史环境促成的”。在这个历史环境中,“资本的发展首次允许这一概念——劳动价值理论——的产生,以此可以让人们事后重新发现前资本主义的千年人类历史中的真理性”(《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5页)。尽管杰姆逊在这里犯了一个知识上的错误(“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发现,而是马克思之前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等提出的),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产生的历史决定性条件阐释上是正确的。在杰姆逊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不仅是现在与过去的关系,还有过去、现在同未来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结构主义者,主要是阿尔都塞等,以其“共时态”观念把这种历史主义批判为“本原”模式和“目的论”。在“目的论”的问题上,杰姆逊认为应该分清资产阶级“进步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点,“在清除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点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将被逐渐地消除掉”。但是,他认为“以‘历史的终结’为名义来说服人们为‘未来’而牺牲自己的现在”便是“目的论”的表现,并同“救世主、‘人文主义’或斯大林主义对‘未来’所编造出的欺骗性意象”“混合在一起,牵就于笼统地认为这一切都“从根本上是宗教(和专制主义)思维模式的病症”(同上书,第24页),未免简单而含混不清。“目的论”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类似“为‘未来’牺牲自己的现在”的思想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确实有:“‘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 —126 页)这种未来观念当然既不是“目的论”,也不是“乌托邦(贬义)”。
在杰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不同于“本原”之模式在于其作为“主导符码(master code)”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并不像人们有时所想象的那样,“是经济学或者是狭义的生产论,也不是局部事态或事件的阶级斗争的主导符码”,其本身“制定出一种完整的共时结构”。这是贯穿于“历时态”之中的“共时结构”,实质上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结构,如杰姆逊指出,“《资本论》不是本原建构,而是共时模式”。就是说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包含着人类历史过去生产方式的一切基本要素,而无需直接去追索最古老的生产方式的本原。生产方式是作为历史“非本文”性之最客观而确定的事实,于其现在时态以共时性得以表露出来。这个结构的宏大与深层,可以把种种异己的阐释方式,如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包容其中。就是说“原欲”、存在的本体论等的最终阐释必须回到“生产方式”上来,或是作为“缺席的原因”,正如历史不直接呈现而总是通过本文的形式显露那样,也是由于其宏大与深层性。这样,杰姆逊通过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便导向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文学的阐释学。
历史的终极目的与对权力的看法有关。杰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范畴不是最终目的,“当代社会理论(从韦伯到富科)对权力范畴的兴趣经常是策略的,而且有系统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疑难问题进行移位”。(《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33页)这显然是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而言。但他似乎没有就这个问题专门展开论述。这是一个本世纪末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需要解决的又是最棘手的理论问题。如果把国家的最后消亡作为所谓“终极关怀”,马克思关于“权力(国家政权)”的理想在“巴黎公社”的政权模式上就已现实化,具体为其“公仆”与“民主”制度。当然,这必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加以巩固。然而,由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在实践中常常倒错——由于目的的遥远而模糊甚至改变了手段的性质,接近目的之手段蜕变为愈益远离目的的东西,导致在现代史上,除了公社的七十天“伟大的创举”,马克思的权力理想就从未成为现实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中包含着作为非宗教形态的“终极关怀”之国家作为权力之消亡的理论,其“非宗教性”即在其通过对非理想之现实权力的批判达到的最终的“现世性”。现实权力形态的逐步理想化,作为权力国家最终消亡之实现同对非理想之现实权力的批判,必然地走在同一条路上——马克思主义终止对现实非理想权力批判功能之时,就是权力实现理想化而自身消失之日。
杰姆逊在论后现代主义时,涉及到了在学术理论领域中作为权力文化给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后果。他说:“对某种日益加强的整体系统或逻辑的看法越是有力……读者就会感到越是无力。因此,通过一种封闭可怕的机器,理论家所赢得的也正是他所失去的,因为他的著作的批评能力会由此丧失,而否定和反抗的冲力……处于这种情况也会被认为是徒劳和微不足道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6页)显然,“一种封闭可怕的机器”,即理论对权力的依附与借助,或可称为权力文化结构,理论家因此可能赢得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虽因体制而有所不同,但这种“赢得”毕竟不是依靠理论自身的力量(理论家承不承认理论本身有这种力量),所以这也正是他所失去的——理论的“批判能力、否定和反抗的力量”——对于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否定、反抗“反对人自身的社会现状”——商品拜物教、异化、腐败、特权和官僚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生命与活力之所在。所以在现有非理想的权力庇护下的权力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总体上是败坏的。正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力量的信心,杰姆逊认为前苏联东欧解体不是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它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
二、源于卢卡奇的理论误区
杰姆逊思想理论中我们认为是错误与矛盾的地方,表现在他一方面表示“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商品价值理论及物化的概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他在那里展开论述的不是“物化”概念,而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并据此申明他不喜欢“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称号,他自己的理论立场是“新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他在自然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又声称自己是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8、81 页)他重复着卢卡奇早期的错误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唯物主义,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我说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辩证唯物主义企图把辩证法同时运用于解释历史的自然,而这是和斯大林、恩格斯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说法,这本书也就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反社林论》区分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整套完整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 将辩证法看成了自然界‘永恒’的规律”(同上书, 第243页)。杰姆逊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关于历史的, 和形而上学、存在、自然等没有关系,辩证法只是在历史发展中起作用,在自然界中则不能说有辩证法。”(同上书,第93—94页)
杰姆逊所说的这个意思不是他自己的创见,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较为普遍的历史误区。他受卢卡奇早期思想与萨特晚期思想的影响,似乎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卢卡奇的“伟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建立了马克思曾‘失掉’了的哲学体系”(同上)。这确实不是个枝节问题,而是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即能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问题。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真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们所说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一致的话,他们绝不可能长期合作直到最终。
在马克思的晚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发了关于自然界对立统一规律——即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发表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特别是写作了后来被前苏联出版者定名的《自然辩证法》。在以上三部著作里,恩格斯系统全面地论述了自然辩证法的问题。马克思没有相应的论著,这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把他们区分开来的把柄。但问题是不是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呢?首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版序言》中特别加以说明:在该书付印以前,曾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过,并指出“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 既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恩格斯已深怀偏见,可能以为他本人的声明不足为据,那么我们再从马克思本人来看。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自然辩证法问题,但他在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就把“对立统一”看成是一个万应的原则”,既是“万应的原则”,当然既包括自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同时他以充分的肯定阐发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他写道: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 of 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 “两极相通”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
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又写道:“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同上书,第75页)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正是自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高级阶段。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看到以上所引的文字, 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偏执者,就不会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辩证法原则上的这种一致性。
以上这个问题搞得不好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性质改变了,即变成唯心主义了。也就是从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的本体论,变成形形色色人本主义的本体论,即精神的东西(名谓实践本体实质是精神本体)第一性的本体论上去。因为不承认自然辩证法,必然导致否认人类同样要受自然规律支配,进而否定社会的总体性规律是不以主体的认识与意志转移的“外部规律”,而走上主体“自律论”,即人的本质不是由人以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而是由“人自身”的理性、欲望、心理的情感的东西,即杰姆逊所批判的“利必多”东西规定的;走到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是不能规定”上面去。而这种主观唯心的人本主义正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种种反意识形态,非社会、非历史、非政治批评的根源。这也正是杰姆逊所批判的“在局部上是正确的”种种“多元”理论。
杰姆逊的矛盾也正在于此,我相信对此他并不自觉。因为正是在同一本讲稿中,他表现出自身的这种矛盾,如他在前面说自然界与社会没有共同的规律,而在论述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的“二项对立”原则时,他写道,有X和Y两组矛盾,从共同的矛盾结构上有其“相似性”,“因为宇宙就是这样的,这成了普遍现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15页),这实际上说出了矛盾规律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
三、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功能和使命
建立在一般哲学认识论之上的阐释学从古典的——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现代的——海德格、伽达默尔的发展变化可概括为三点:(一)历史性与现时性,(二)客体与主体,(三)理性与非理性。我们将从这几个层次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解决中,窥见阐释学在当代的发展是怎样必然地引向马克思主义的。
“古典的”阐释学,以个体化生命在精神上的统一性来解决上述关系,这种“统一性”也就是贯通古今的主体生命通过个体体验对客体化的历史本文的认知与思维能力。他们深信人文性历史本文就是不同时代主体“自我”的外在化,或客体化,因此现时的“自我”与通过本文所搜寻的昔日的“自我”是同一个“自我”。海德格以“此在(Dasien)”在存在论上的“先前”结构,并通过“领会(Verstehen)”的“筹划”活动中所包含的“能在”,即存在现实性中包含的可能性——与存在在时间上的未来相通。海德格给旧阐释学注入的是真理论、历史主义,及相关的突出于现时的主体性和更为明确的本体论——语言本体论。(见《20世纪西方美学主流》,第231—243页)在他看来,历史不是意味着“过去”的东西,也不是从现时来看“过去”业已发生的事,而是应该从存在的“整体性”,从生存的源自“将来”的本真的历史事件,回到“过去”的重演。
然而,海德格的这种真理论与历史主义是基于其独特的“基本本体论”之上的。由此出发,他把历史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致力于“使此在异化于其本真的历史性”的历史学,也包括“今天变成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实际上,这种历史主义与他常说的对“在的遗忘”相关联。另外,在他看来是源远流长的历史主义是“从‘在’的历史的角度去加以思考的辩证法”。(《根据的原则》,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2辑,三联书店1982年,第26 页)这就是说他基于把“存在”与“世界”区别开来的基本本体论原则,把“在的历史”与一般的“世界历史”加以区分。因此他的阐释学中贯穿着的真理论与历史主义带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气息。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把艺术作为对“真理的认识”,并召唤当代理性(《论理性的力量》,1968年)。与海德格不同的是他把历史作为“真理的源泉”。这个历史是世界史而不是“在的真理”的本体论源泉。他把理性重新恢复到人在精神方面本质规定性的地位,指出,正是理性特质才使人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显出了“人之为人”的特征。(《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 第431 页)真理就是在理性支配与驱动下主体对自身与对象本质意义的追求。这种本质意义是历史地呈现在理解着的、现实地存在着的主体的面前,所以,伽达默尔认为“历史就是一种与理论上的理性完全不同的真理的源泉”(同上书,第43页)。“理论上的理性”就是思维推理的逻辑能力,就是解释的主体依据。把历史作为“真理的源泉”与“理论上的理性”加以区别,这正是把“历史的”东西置于“逻辑的”东西之前,正是对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颠倒。伽达默尔在这一根本的哲学出发点上已接近了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
伽达默尔提出“效果史”与“视界融合”来解决“历史与现时”、“客体与主体”间的紧张关系。正如杰姆逊所说:“历史不是一份本文,……作为一个不出场的原因,除了在本文的形式中,对我们却是不可及的,我们要与之接近达到真实本身只有通过先有的本文化(的历史),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述。”(《政治无意识》,第35页)在客体性曾经自在的历史、本文与解读之间总有一个主体理解的误差,这个误差也正如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与玻尔的量子力学互补原理所认为的那样,自然客体世界亦如人类社会的客体世界那样,认识的、观察或测量的主体对客体的理解性描述,无论借助多么精密的仪器显示的数据,总存在着由于仪器本身量子动量对客体量子动量扰动造成的误差,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个误差的觉察程度与允许限度。比如,在牛顿经典力学的宏观与宇观层次上,可以把量子互补原理的误差略而不计(当然牛顿当时对此并不自觉),而认为我们对客体运动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但承认这种误差不等于否定客体自在的理由。虽然阐释学被限于人文科学,但这种主客体关系是完全同样的。这正是本世纪自然科学发展对人文科学的重大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争论尚在继续,并未定论,所以在哲学上曾被引入主观主义的主体论也不足为奇。
伽达默尔从早期的新康德主义立场,通过新阐释学的道路向马克思主义接近,这正如他自觉认识到的、在1974年为《哲学历史辞典)的阐释学辞条中所写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振奋人心的意识形态批评与阐释学对社会科学中存在的朴素客观主义的批判相一致”。这种“一致性”正是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历史必然性。在1982年《作为实践哲学的阐释学》一文中,这位哲学老人又指出:“在理解经济与社会生活现象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之一便是,戳穿那种乞灵于科学之客观性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自我解释”。(《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88—98页)
在这里,对“资产阶级文化的自我解释”之“科学的客观性”的否定就指向一种真正的主体性,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世界观系列,在阐释学上的第二义的决定性。这完全可以与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概念对应起来。
本世纪末到21世纪,已走向资本的“多国化”之西方发达国家,“高消费”之商品拜物教现象依然存在,而前苏联与东欧体系也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目标,第三世界也在发展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及其伴随着的负面现象,仍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世界性潮流。市场经济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解放生产力振兴经济的历史进步趋向,但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商品拜物教是人的异化(非人化)的根源。我国当前腐败集中表现为“权钱交易”的特点,表明“权力”本身也已“商品化”、“资本化”,成为可与“通货”互换、产生剩余价值的东西。由于“权”之商品化,随之,“批件”、“书号”、“新闻”、“文凭”、“奖状”,直到肉体灵魂……无一不可买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以人的全面解放及相应的生产力的更高发展为标准的,而在这种批判的同时又对资本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现实化”的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高度成就加以肯定。美学对商品市场经济发展(无论它在世界的哪一地区)所不可避免的商品拜物教与人的异化(人自身的商品化),不可能完全等同权力文化对改革作为历史的要求那样进行赞扬与歌颂,揭露与批判是其功能的主要的与基本的姿态,而这种姿态有时表面上看来似乎有背于历史潮流,如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然而从历史与道德东西最后的一致性之宏观来看,恰恰与经济生产的东西形成平行四边形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正如我说过的,“‘金钱万能’推动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向全盛发展,‘金钱万恶’把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引向美学顶峰”(《逃避崇高,也躲闪卑污——痞文学与新写实小说的美学错位》,《文学报》1994年,4月15日), 这已由整个美学文学艺术的历史证明。
马克思主义除了自身有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批判现实异化的使命之外,相应地,在其阐释学方面对文学艺术的批评与指导作用也应顺应这一功能的要求。然而问题复杂的是,当代世界与资本主义早、中期,即上一世纪末至本世纪中期,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文学艺术创作形式的实践与美学、文艺学理论与批评上带来的问题就是现代主义与所谓后现代主义。这一问题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未曾接触过的,因而也就必然地挑战性地提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面前。杰姆逊指出:“阐释在这里被视为一种基本的转喻行为,它是在本文重写中根据一种特定的主导符码构成的。”(《政治无意识》, 第10页)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意义也主要是就此而言。其叙事“转喻”的意义也正如《政治无意识》一书的副标题所示,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本世纪在理论批评上的,从语言形式主义诗学开始,到结构主义,符号象征主义之非历史的形式主义运动,是对文学艺术创作在形式上不断的变异性要求的顺应,同样需要更高的解码阐释。
杰姆逊把第三世界的叙事文学称为“政治寓言”。就对解码的要求而言,西方现代主义的形式变异性同样带有政治寓言的特点,只不过第三世界的创作往往是在专制独裁政权下躲藏的寓言,而西方现代主义则是逃避古典的人道主义传统的隐匿。发掘隐义,转换符码,反溯始原,则是唯马克思主义(历史的)阐释,方能在根本上完成的使命与功能。这一使命与功能又是同在新历史条件下对异化的继续批判联系着的。这整个理解—阐释的过程也就是对于现代—后现代主义本文“去神秘化”的解码行为,即从本文的现实关系的层面上破译本文对现实批判的密码意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超越现代主义阐释方法,作为一种从“最终点”之“绝对视野”的根本优越性之所在。这一性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对一切有识之士应有更大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又不是可以使之在新时代形成权力文化的思想统治的力量,而是理论的“彻底性”所具备的“说服力”。这也正是我在1989年说过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不是多元的拼凑,但它的当代发展将通过外部的‘多元’对话来推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第26 页)这也如杰姆逊所说,不会把其他多种方法扔进“历史的烟灰缸”里面去;“不是多元的拼凑”决定着其“彻底性”,而是“通过‘多元’对话来推动”表现其“说服力”。
标签: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决定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