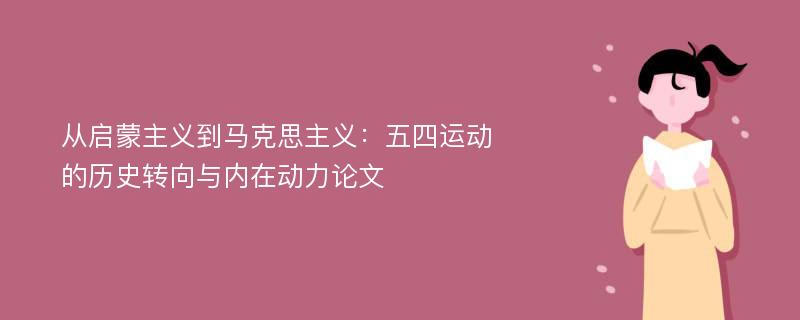
从启蒙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历史转向与内在动力*
□ 包大为
内容提要 新文化运动以降,启蒙主义政治解放的构想主导着知识阶层的理论方向。不论是德先生、赛先生,还是移风易俗、重塑人民和改造语言的努力,都是五四启蒙者投身救亡图存的理论凭借。但是,当半殖民半封建的内外危机打破了启蒙式的政治解放的想象,知识分子便开始自觉地反思局限于意识形态变革的启蒙。同时,当十月革命展现了另一条依靠庶民而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便开始成为了五四运动新的历史特征。尽管在一开始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转向由于缺乏组织和理论译介,仍然掺杂着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泛左翼的内容,但随着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逐步获得了能动性,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接过了启蒙主义未竟的救亡图存的使命。
关键词 启蒙主义 马克思主义 五四 革命
五四运动是一场不断被命名的事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五四运动由于其历史特质的内在断裂,不断地被研究者赋予新的名称,文化抑或政治、民族抑或国家、自由主义抑或布尔什维克主义,交织在这场衔接古今、融合内外的宏大事件之中。在当下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性质的诸多“定论”中,启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易在史料中得以自洽。毕竟就前者而言,新文化运动以来“德赛”二先生以及由法语标示封面的《新青年》杂志,已经不可争辩地将五四运动与1789年大革命联系了起来。而就后者而言,1917年俄国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冲击,以及李大钊和陈独秀等知识界领袖率先师法俄国,则预示着五四运动必将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诚然,五四运动的不同参与群体及其主张原本就不是统一的,时人对启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更是千差万别。但是,救亡图存和创制新社会的历史情势,最终将大部分五四时期的知识群体(学者和学生)推向了庶民,而庶民本身又将在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中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并最终走向一个扬弃古代乃至现代的激进政治实践。
一、重叠的历史: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意图
毋庸置疑,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的意图和特质。这不仅是后世学者的一个看法,更是当时学者们的一种共识。但是,在18世纪末达到思想高峰,并在此后引发欧美政治经济变革的启蒙时代(Le siècle des Lumières),却并非依赖运动式的科学和民主,而是理性主义长期培壅日渐发达的市民社会的结果。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鲁迅所描述的麻木而一盘散沙的状态,人民普遍囿于“人的依赖关系”,在对地主、行会和军阀等传统权威的依附中求得生存的条件。启蒙时代被哲人触发的,潜居于欧美市民社会的文化生命力(理性和科学)和政治诉求(民主和自由),在中国却并不能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土壤中自发生成。人民既无法能动地期冀启蒙的社会愿景,也很难抛却“人的依赖关系”所给予的现实利益——而去追随知识分子所呼吁的启蒙口号。①
因此,从新文化运动伊始,当知识群体发现“德赛”二先生在广大民众中的孤独,就立刻将改造民众作为首要的启蒙主义目标。正如邹蕴真在五四之后总结,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征,文艺复兴注重“新宇宙”,而启蒙运动注重“新人”。②而李泽厚则将新文化运动的最初意图辨识为“国民性的改造”③,即通过文化自我意识而实现对旧传统的摧毁,从而使得民众获得思想的改造和民主的启蒙。“作新民”这一任务在清末就已是文化反思的一个主题,并非民国学人的首创。但是这一启蒙主张却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中才具备了“彻底性和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④因此,作为文化批判和“作新民”实践之顶峰的五四运动,尽管缺乏18世纪启蒙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其主流理论和社会风尚还是体现出了与欧美启蒙主义的历史重叠。
第一,呼唤基于理性的主体性。虽说启蒙的理性主义起点可以追溯到笛卡尔主义,但是理性在启蒙政治中的运用,却是由伏尔泰、卢梭和康德等大革命前后的学者所推动的。卢梭认为只有理性才能赋予我们合法的幸福观念,并根据这一观念去判断价值和行为。⑤同样,深受卢梭影响的康德⑥,更为直接地认为启蒙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脱离“受限于自身的未成年状态(Unmündigkeit)”。⑦这种状态尤其指向了处于“人的依赖关系”的前现代的生存方式,即人们由于政治自由(bürgerlicher Freiheit)的长期匮乏,习惯于被他人的理性和权威所左右,进而失去了自主使用理性的能力。这种理性主义的启蒙政治伦理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广泛译介和运用。例如通过对倭伊铿(Rudolph Euken)哲学的介绍,将启蒙主义的时代特征展现为“把人作为出发点”和“以人的理性来解释宇宙”。⑧又例如陈独秀将抹杀个体理性和主体性视为儒家传统的最大弊端,这种弊端所导致的“依违调和”是发现真理的最大障碍,因而呼吁民众“勿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试揩尔目,用尔脑。”⑨
第二,以理性和科学批判宗教与迷信。西方的工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早在清末就已向国人展现了征服自然的震撼力量,以至于作为最新科技的电力成为了一些中国学人用以构建世界本体的一种想象。到了五四时期,随着进化论、历史主义和启蒙理性的广泛传播,包括儒教在内的一切宗教与迷信都成为了进步的对立面。譬如在李达对郭泰(Her-mann Gorter)著作的译介中,极为强调唯物主义无神论对宗教的批判,对待宗教的不同态度甚至直接事关阶级立场:“唯物史观对于宗教的态度决不是可以和绅士阀的无神论相混同的。无神论者直接敌视宗教,以为宗教是保守阶级的思想,是进步主义根本上的障碍物。他们把宗教当作单是无智无学的结果,因此要把科学的启蒙运动来破坏愚民的迷信。”⑩又例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指出,正是科学和人权使得近代欧洲走出“蒙昧之世”并“优越他族”,而中国的“浅化之民”却“有想象而无科学”,受制于作为“想象时代之产物”的“宗教美文”,因此必须“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⑪这些主张的历史原型,不言而喻是伏尔泰、拉美特利直至达尔文的欧洲反宗教的理性主义哲学,甚至在五四之后出现了通过运用启蒙政治哲学逐条批驳宗教教义的文章。⑫
第三,以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统治。到了启蒙晚期,民主概念是对18世纪以来一系列权利、政体和法治理论的集中表达。尽管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和康德对权利的政治条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民主政体及其法治却是实践这些权利观念的共同指向。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将“科学与人权并重”⑬视为国人摆脱矇昧的关键,而人权的代言人则是“德先生”。到了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进一步将拥护德先生的任务拓展至“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而“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⑭陈独秀对民主政治的宽泛讨论,似有将政治服务于文化和文学批判的意图,这当然可以溯源至启蒙政治创制新民、移风易俗的激进传统,但也与新文学为主调的前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关。而到了五四运动之后,关于民主政治的专业性分析愈发多了起来。高元在《新潮》撰文详细分析了民主政治的内涵和要求,指出“民主政治是要人人发表自由意志来讨论政治的,他们对于政治善恶的批评,要由理性的判断,不要作习惯的盲从。”人们必须将“专制政治的Popular Consent”和“民主政治的 Popular Consent”区别开,因为前者依赖专制政治的舆论,将习惯言说成善恶的标准,后者则是Free Consent。⑮这不仅是对新文化运动和启蒙早期的民主政治泛论的具体化,更是将学科化的民主政治理论引入启蒙主义的文化革新。因为统一表征为习俗和习惯的旧文化、旧政治、旧宗教乃至旧语言,是遏制着民众走向理性和权利自觉的无形障碍。
出租车还在门前,水仙芝上了车,随蒋海峰一起前往墓园。把花献上,蒋海峰神色凝重,叩了三个响头,声音颤抖:“伯父,海峰和仙芝来看您啦,我们准备给您出版诗集,现在您可以安心了!”
一般有两种匹配方法:在线更新和离线编程。大众品牌授权经销商(4S店)多采用在线下载软件进行更新、编程来解决这一问题,未获授权的可借助ODIS-E工程师软件进行离线编程,无需在线,即可完成本操作。
因而在此意义上,李泽厚所说的新文化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始于文化而终于政治的轨迹不无道理。清末以来,从器物革新到制度改良,再到制度革命的救亡图存的不懈努力,尽管一败再败,却从未让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全然绝望。到了已然民国的新文化五四时期,通过对启蒙主义之理论来源和实践历程的深刻理解,卢梭式的“倒果为因”⑯的理想制度建构成为了这一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奴隶”、“矇昧”、“麻木”、“沉沦”、“盲从”和“虚伪”等旧民特质并非全然是旧制度造成的,而是旧制度得以残存的真正原因。因此要实现救亡,就必须先将毒害人民的旧习俗和旧文化进行革除。 《新青年》、《解放与改造》、《新潮》、《新社会》、《新时代》和《少年中国》等等这一时期的刊物,虽内容上多有争鸣辩论,但是其名称和意图却都是为了创制新的中国人民,以期通过文化上革新的中国人民来支撑起自由解放的理想制度。事实证明,这种基于启蒙主义“政治—教育”辩证逻辑的激进思潮,的确“为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 ⑰
二、张力和阻碍:未竟的启蒙
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运动,及其文学变革和思想改造,最终消没于爱国救亡为主线的政治实践。如果说在1921年尚有沈雁冰和郑振铎等知识分子将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平民主义的文学研究会,那么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抛却了柏格森、克鲁泡特金、卢梭和杜威的理论,走向了扶助工农的革命浪潮。这一转变在北伐前后走向了第一次巅峰,并且在此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完全扬弃了新文化五四前期的启蒙主义文学政治。因此,就结果而言,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是未竟的。在郑振铎发表于1919年底的总结性文章《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已经可以窥见这一未竟的结局。一战结束之后,新文化运动使得“德摩克拉西的思潮”席卷中国,以至于麻木不仁的社会里“居然透出解放、改造的声浪来;睡气沉沉的中国人,也显出一些活动的象,进取的精神来”。而五四运动之后,“文化运动的力量”更有“日盛一日之势”。但是,这种启蒙主义的民主思潮和文化运动最终还是遭遇三个问题。一是“我们的运动,仍旧是阶级的”——“平民绝对没有受到这种报纸上的文化运动的益处…他们虽稍听见一些‘救国!救国!’的演说…但这与新思潮的输入,又有什么关系?…什么德摩克拉西的思潮,什么解放改造的学说…都是知识阶级的专利品罢了。”二是启蒙主义的文化运动没有现实基础——“中国不识字的人怎样多,识字的人,又大半数是顽固的守旧党,言论的效力,能有多少?所以现在大家的社会改造运动,都注全力于言论界…多数还是埋头于口头,纸上,肤浅,直觉的著作。”三是“运动的范围,过于广漠”——一些启蒙者“好务虚名,急功近利”,罔顾自身实力的限度、目标的远近、启蒙效果好坏和运动成败,只为“搏得一个虚名”。⑱
但是,撇开郑振铎所列举的文化启蒙之未竟的方面,即使是五四时期最为真诚 (并非为了虚名)的启蒙主义者,其理解和意图也并不尽然与其主张的启蒙主义口号相一致。且不谈五四启蒙者缺乏欧美启蒙主义特定的历史土壤:原生的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伦理,借助古希腊哲学的文艺复兴以及穿上古罗马服装的启蒙政治。⑲即使是直接“拿来主义”的启蒙口号也始终与启蒙主义本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其中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个人/集体、求新/除旧两个方面。
㉙[法]卢梭:《政治经济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页。
首先,最为根本的是爱国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张力。个人主义是近现代西方社会风尚的基本特征,但是其起源则是启蒙政治哲学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现代性的判断。例如霍布斯以人人冲突的自然状态作为起点,这使得从冲突到合作的进化成为一个类似“无中生有”的难题。⑳因此,个体理性和福利既是启蒙主义原初的解放对象,更是国家、民族和制度等集合性概念的基础。斯宾诺莎将不受他人支配的个人意志称为自由人㉑,卢梭和康德用以建构启蒙政治的前提是公民个体的理性在权利和义务体系中的自觉运用,黑格尔更是将自我意识指认为启蒙的“正当权利”㉒,更毋宁说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启蒙主义者用以论证市场机制的经济人假设。但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却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即在被殖民侵略强行推入现代历史的背景下,启蒙和解放中国人民的个体理性,首先需要通过集体的抗争来解除外侮的枷锁,而这种集体的抗争又必须要求个体作出超越私人福利的牺牲。谭鸣谦在五四前夕呼吁知识分子必须为“平民正义而战”,其首要目的是集体性的,即“联合自由之民族,造成一正义之大同世界。”㉓王光祈则感叹中国人民的“个人主义”(自私)过于发达,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究竟有几人真正牺牲?每到紧要关头便虑及个人的利害问题有几人真正是澈底的爱国?不过是凑热闹罢了!”使得发达国家兴盛的牺牲个人的“爱国运动”需要“一种团体生活国家主义”——“缩小个人自由从事国家生活造成一个最强固的团体。”㉔而傅斯年对待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的定义更为谨慎,认为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主要在于通过直接行动来“唤起公众责任心”,因为“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㉕因此,李泽厚所认为的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目标,并非是文化的改造和传统的扔弃,而是为了国家、民族,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这仍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和近代中国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与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和平等的启蒙主义有着本质区别。㉖
其次,激进求新的五四启蒙与欧陆启蒙主义的传统遗存的张力。启蒙主义并非是对前启蒙的文化遗产的彻底离弃。“谓之启蒙时代其最显著之特征在反抗旧说及自古相传之制度”也许只是五四时人对启蒙主义的想象。㉗五四时期的启蒙者继承了20世纪初西方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启蒙主义的反思。因此,尽管其彻底性超过了18世纪启蒙者,但是在面临与18世纪启蒙者类似的历史目标——终结封建而又迷信的前现代历史,又不得不借用法国大革命的流行观念和口号。这就使得五四启蒙者的目标远远超出了启蒙时代乃至同时期西方社会的理论需求。
一如对民主政治的激进诉求超出了启蒙的审慎限度。德先生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中承担着开启民智、重建国家和救亡图存的重任,民主政治的真理性在五四理论坐标中的中坚地位已绝非国故派所能撼动,甚至将当世最为先进的主张命名为“政治的德谟克拉西”、“经济的德谟克拉西”、“文化的德谟克拉西”和“社会的德谟克拉西”。㉘在启蒙时代,民主政治不仅有其限度,更需要外在条件的支持而不蜕变为恶政。例如迄今为止都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在卢梭看来是“一个由一群徒逞口辩的知识阶层人士统治的暴虐的贵族制国家。”㉙当五四启蒙者抛却了古典政治人物及其经验,卢梭及其大革命的追随者却通过宣扬古罗马贤人政治来反对“任性”的现实政治。㉚
二如对宗教的无神论态度超出启蒙的实践理性。赛先生既是理性主义在五四的代言者,又是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批判者。因而新兴的唯物史观和进化论裹挟着启蒙时代无神论在五四时期掀起了打击面甚广的对彼岸世界的批判。周太玄认为宗教宰制的精神世界在启蒙时代的终结,使得“欧洲长梦渐渐复醒”,进而使得“人类真正的感情排山倒海而来,文学与艺术得其救助方霍然有脱出宗教之勇气。”㉛人们甚至直接将“一种机械的世界观”和“物质的人生观”指认为法国启蒙哲学的精神。这种精神与一切宗教想象相对立,“将人看作自然界的一个现象。”㉜但是宗教事实上并未被所有的启蒙主义者禁绝。且不说卢梭肯定了加尔文教对建构公民宗教中的意义,康德将灵魂不朽视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公设”——使得至善和人的道德的无穷前进称为可能㉝,黑格尔也保留了宗教对启蒙的辩驳的权利。
在传统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常用的教学方式就是“填鸭式”,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使学生感觉语文学习是枯燥乏味的,还导致他们对语文学习失去兴趣。基于此,教师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可将多媒体技术巧妙地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多媒体有着自身独特的优点,它可以将语文课本中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教师应合理的应用多媒体技术,以此激发小学生的语文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
由上图可以发现,相关系数和输出SINR形成零陷的频率增量Δf周期为3 kHz,与理论计算值一致。改变干扰位置为(9°,65 km),使得干扰角度与目标角度不同,但仍在主瓣内。仿真图如图5、图6所示。
三、“庶民的胜利”:作为继续启蒙的马克思主义
选取Accuracy、P-R、F1、ROC、AUC、KS作为评价指标,对基于LCS、TF-IDF、CNN、LSTM的语义相似度模型进行实验对比分析。
第一,凌驾于民智的启蒙已然无法在赤贫且闭塞的中国社会推行。启蒙时代,理性被视为点燃现代文明的火把,而能够拿着这一火把,带领着人民走出“洞穴”的人,只能是自觉运用和发展理性的知识分子。这并不是一种出于智性的“自吹自擂”,而是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占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远离知识和文化的残酷现实的反映。正如艾德蒙·伯克及其他保守主义启蒙文人对民众的不信任,并非出自纯然的道德优越感,而是落后生产方式下,大多数人民“整日忙于生计,不可能有闲暇从事训练智力的活动”。因此“伯克们”认定“理头匠、蜡烛匠等类人被允许个别或集体上台统治,国家就会遭受压迫。”㊳这种知识分子/人民的二元结构在启蒙主义的五四运动中得到了继承。陈独秀在1916年仍然认为“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引导,而不可为代庖。”㊴但是,由于被“三座大山”压迫,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民不仅遭受着启蒙时期法国、英国和德国人民数倍的内外剥削,更在孤立和分裂的封建社会结构中无法将思想启蒙转化为值得抛却个人利益的革命行动。
第二,十月革命所激化的左翼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让五四启蒙者看到了结合民众走向解放的可能。虽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体是成立的,但事实上马克思的理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得到传播。而这两场间隔将近两年、位居亚欧大陆两端的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显然也不是粗略和独断的“拿过来”、“送过来”的概括所能体现的。李泽厚的观点大致是正确的,即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1918年对白卫军和多国干涉军的胜利)使得原以伦理觉悟为“最后觉悟”的文化斗士,开始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组织群众进行革命的政治斗争,推翻旧制度,以取得“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唯有如此其它一切才可迎刃而解。㊵与此同时,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列宁主义平行的其他左翼理论,也在五四运动中愈发兴盛,形成了一股平民主义/政治经济变革的新思潮,取代了曾经聚焦于知识阶层/文化领域的启蒙主义运动。
第三,失败的内政外交和残酷的经济剥削,迫使五四启蒙者寻求一种更为“彻底”的理论武器。启蒙时代的思想变革和法国大革命的核心要义是人的政治解放,将个体摆脱封建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桎梏,获得抽象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这种政治解放在五四时期的中国遭遇到了即使是启蒙先贤也很难设想的历史性阻碍。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为五四启蒙者“预备”了脱去国王外衣却远比国王暴虐、专制和任性的军阀们,以及在背后支持这种军事专制的国际帝国主义、国内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所乐见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困难大体分为两类观点。一是1919年底的陈独秀,对于该问题的看法仍具有浓厚的启蒙主义特征,他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想冲出这三害(军人、官僚、政客)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的“许多明白有良心的人”。而这种明显聚焦于政治解放的观点,又与其“唤醒老百姓”和“实行民治”的启蒙理性结合了起来,最终折衷为既想要“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又“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的幻想。㊶二是李大钊,将造成中国黑暗时局的力量总结为“乡愿和大盗”㊷,前者也许可以通过新文化运动而被击倒,但是后者则必须以更为有力的革命手段予以消灭,而十月革命给出了当时最为成功的典范。
这三方面原因并非就此终结了启蒙主义在五四运动的使命。相反,正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主义的成果,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人民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救亡图存的实践中将两种主义统一了起来。瞿秋白之所以在五四之后认为“革新的时机已经到了”,是因为五四的启蒙主义运动使得“新思潮骤然澎涨起来”,而问题只是在于如何将这种新文化运动推广到“极偏僻的地方去”,“使全国国民觉悟”。㊸周炳琳则指出五四运动之后紧接着发生的是“除旧布新的觉悟”——“理性的根据一到手,勇气陡然增涨”,“抵抗强权和开辟新机”成为了五四以后北京学生的生活。㊹罗家伦等五四运动的意见领袖则进一步认识了反抗实践的重要性,因为“世上没有理性不与威权为敌,也没有威权不要压制理性”,而“没有物质的势力”的理性之所以能够成功,“惟一妙谛就是”牺牲——“为真理而牺牲,为主张而牺牲是绝对值得的。”㊺所有这些求新、求革命、求反抗乃至求牺牲的精神状态,已然超出了原先囿于照搬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启蒙运动的限度,为当时最新、最革命和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开辟了理论需求和理论空间。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1921年之前,五四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的理论、方法和目标并不是统一的。在五四运动前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大量左翼激进思潮都成为了解救人民和民族的理论武器,以至于“与民声发刊差不多都是讲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好处的。”㊻事实上,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著作尚未获得较为完整的译介,实践尚不能依靠完备科学的组织,原本由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所支撑的问题不得不同时接受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参与。这些参与者在五四时期的表现形态,体现出与未竟的启蒙任务在方法和意图上的紧密衔接。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成为“继续”启蒙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五四时期,行至“彻底”的德先生就不再是陈独秀极力避免的美国式的二元的“民治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崇拜个人之自由”,将矛头指向政府,因为“政府者,威权总汇之处也”,而权威又是“一人或少数人,行使无限之威权,以屈伏他人。”㊼另一方面则提倡人民之间的“互助主义”,认为“互助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有秩序的、积极的、建设的……”,能够“把极悲苦的旧社会推翻、另造一种既快乐的新社会出来……”。㊽这种互助主义又与深入农民,实践赫尔岑等俄国民粹主义的思潮结合了起来,影响了包括青年毛泽东和少年中国学社成员在内的大量进步青年。㊾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兴盛,诚然与显得愈发无力的启蒙主义,以及欧洲的理论环境有关。㊿但是从欧美舶来的新文学和新戏剧所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质,极大地推动了该思潮的流行,并且将泛左翼的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治特征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学特征融合了起来。例如在中国舞台上演的第一个西洋剧本,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中,就含有如此的对话:“华伦姑娘,你要晓得,我生来是个赞成无政府主义的人(I am a born anarchist)。我最恨的是威权。威权两个字把亲子间的天性关系——甚至于母女间的亦然——都戕贼尽了。”51相比之下,更多表现为阶级斗争和革命政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会遭受一些保守倾向的文人的拒斥,例如张东荪认为:“欧战完了,忽然大家都讲起社会主义来了,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么?所以从这一点看去可以说现在讲社会主义的人都是学时髦出锋头,我所以不敢附和就是为此。”52而无政府主义的新文化形式更易被人们接受。
最后,1917年前后国内外革命形势所带来的剧烈社会变化,实际上使得一些无法跟上时代步伐的五四启蒙者徘徊于传统和启蒙的陈旧范畴,因而不得不感叹:“新的太新旧的太旧。”53但是,随着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以来就不断组织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Bolshevism这种“全世界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也不再是五四启蒙者所陌生的“太新的”理论了,五四运动中工人乃至农民广泛参与的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自觉斗争,也使得曾经幻想着通过思想文化改造实现和平富强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十月革命的确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54,东方世界无法阻挡的来自庶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迫在眉睫。也许,许地山在五四运动爆发一年后所呼吁的“五四”向“五一”的转变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五四历史转向的实质,以及在这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启蒙主义之间的关系。全球性的政治危机和革命风潮使得一部分五四学者看到了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五四运动的局限性,即“五一是世界的运动,而五四只是邦国的”,同时“五一是反对经济的强权,五四是反对政治的强权”。55因此,马克思主义最终接过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主义所承担的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既成为了中国人民——而不仅仅是知识阶层创造新社会的理论依靠,更成为中国人民加入世界历史发展之探索者行列的伟大契机。
注释:
①这种对启蒙主义口号的消极性尤其体现在农民阶级,除了民粹主义者,大多数知识群体都感慨农民的消极性所造成的历史阻碍。事实上,直至北伐,农民才真正获得大多数革命者的重视,而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将农民纳入革命的主体。而延安时期,农民的文化和艺术的主体地位才得到知识阶层广泛的认可。在此之前,尤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农民对知识分子所提出的启蒙主义口号是冷漠的。尽管五四之后出现了涉及农民生活的平民文学,以及鲁迅、郁达夫和李大钊对农民启蒙的呼吁,但这仍然是外在于农村来描述农民的精神现象。这种表面上容纳农民的启蒙主义的平民文学,实际上“意指着市民而不是工农大众,所谓平民文学,其实是市民文学。”参见向林冰:《新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潘梓年同志的发言》,《新华日报》1940年7月4日。
②邹蕴真:《现代西洋哲学之概观》,《新时代》1923年4月10日第1卷第1号。
③④⑰㉖㊵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年版,第11、8、15、12、28页。
《成长的烦恼》该阅读材料分析讲解期间,教师需要让学生通过阅读与学习,认识自我并正确面对成长中的烦恼。课前播放《小小少年》,让学生围绕主题尝试着表达自己对其的独特认识,经过仿写与指导训练,能够将学生的情感激发。
⑤卢梭认为我们生来具备感觉的能力,并由此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感觉所导致的趋利避苦的行为必须符合理性赋予我们的幸福观念。参见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9页。
⑥康德哲学中“理性=成年”、“非理性=未成年”的等式,必然受到他所热衷阅读的《爱弥儿》的影响。在该书中,卢梭已经给出了类似的“等式”:“当我说感性的理解或孩子的理解时……当我说理性的理解或成人的理解时。”参见卢梭:《爱弥儿》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2页。
⑦Immanuel Kant:Werke in zwölf Bänden.Band 11,Frankfurt am Main 1977.Erstdruck in: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Dezember 1784,S.481~490.
作为定论和事实,五四运动最终从布尔乔亚式的启蒙主义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转变的历史细节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已有巨量的研究,在此就不赘述了。作为衔接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事件,这种转变暗含着两种历史功能:一是在未竟的启蒙主义理想中,五四学人自发总结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化批判和思想改造的正反经验;二是在多元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示范下,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为了救亡图存和拯救人民的最终方案。但是,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何种样态?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在中国的终结?如果不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主义又是何种关系?这些问题尽管曾经被人们提起——却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值得我们再一次进行澄清、界定和反思。事实上,当我们回望五四时期人们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意图和内容,不难发现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并非是决然对立的。这两种“主义”最为直观、统一地表现为被巴黎和会激发的救亡图存的激进探索。启蒙主义的“德赛”二先生继承自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前期被认为是开启民智和重建共和国的必由之路。但是如下三个原因使得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民众的二元运动结构最终自行趋向瓦解:
⑧宰平:《倭伊铿谈话记》,《解放与改造》第4卷第5号。
⑨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1916年12月1日第2卷第4号。
⑩郭泰(Her-mann Gorter):《唯物史的宗教观》,李达译,《少年中国》1921年5月15日第2卷第11号。
⑪⑬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年1卷1号。
⑫例如兼生发表于 《解放与改造》1919年第1卷第6号的《克鲁泡特金的道德观》,借助典型的启蒙政治哲学,即善恶的标准起源于趋利避苦的自然法,指出宗教利用了这种自然法则而对人民进行欺骗。其言辞在激进之余,又细心地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批驳,例如根据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节,作者指出:“这些昆虫龈鼠和野人之类没有读过康德的书,没有看过教会牧师或是摩西的训诫,然而他们却有同一的善恶观念。你回想一会你就可以知道,蚁子龈鼠和那耶教徒或是无神论的道德家所谓善的,就是那些有利于保全他们族类的,所谓恶的就是那些有害于种族的”。
⑭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1月15日第6卷第1号。
⑮高元:《民主政治与伦常主义》,《新潮》1919年12月1日第2卷第2号。
㊷《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5页。
(1) 提高碳纤维生产能力和水平。目前,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投入商用的CFRP大都来自国外。国内应加大相关产业的投资力度、更新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能力,使相关产品质量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⑲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了这一现象。由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古典时代的传统和符号“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人们通过革命来创造历史的时候,总是会借用“亡灵”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 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
⑳赵汀阳:《深化启蒙: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㉑[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第222页。
⑱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1919年11月21日第3号。
㉒[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9页
㉓㉘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而观》,《新潮》1919年5月1日第1卷第5号。
㉔王光祈:《团体生活》,《少年中国》1919年12月15日第1卷第6号。
㉕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新青年》1919年11月1日第6卷第6号。
㉗刘伯明:《非宗教运动平议》,《学衡》1922年1月第6号。
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在实践层面的无果而终,以及在理论层面与原生理论的巨大张力,有着深刻而又辩证的历史原因,并非李泽厚所指认的趋向爱国运动而非个体解放的历史传统。㉞直观而言,五四启蒙者所面对的时局与18世纪启蒙哲人有共通之处,却又更为凶险。共通之处在于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与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一样黑暗:“政治上的专横,宗教上的腐败,种种罪恶充塞一时…多数民众负着一个地狱似的国家。”㉟更为凶险之处在于胡适所描述的亡国灭种的时局:“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术语,成了一般爱国志士的口头禅。”㊱但是辩证之处在于,爱国主义的集体行动,由于与私人理性和福利的冲突而在中国遭受非议,事实上在启蒙主义的母国也有过同样的境遇。作为爱国救亡运动的巴黎公社,标示出被限定于个人主义的启蒙理性的局限性。布朗基的呼吁:“在这祖国、家园和个人的命运朝不保夕的时刻,人们不能过于挑剔…战斗…为了所有人的呼吸与生命,为了作为人的最高表现,为了祖国”㊲——不仅打动了久受启蒙理智浸淫的法国底层民众,更成为五四时期极具影响力的词句。
主题出版着眼于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但是在出版过程中,又要根据不同主题的特点分步骤、有节奏地完成议程设置,追求主题出版的“长尾效应”,避免昙花一现。因此,主题图书的议程设置应由宏观层面总体设计,各出版单位协调分工,各展所长。
㉚卢梭对加图的推崇,他认为加图是公民中的佼佼者,他心系祖国,为了保卫国家、自由和法律并反对世界的征服者而奋斗了一生。参见卢梭:《科西嘉制宪意见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1~22页。
㉛周太玄:《宗教与中国之将来》,《少年中国》1921年8月1日第3卷第1号。
教师的心理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责任和义务要求全社会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在当今世界上,经济的实力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而劳动者的素质又取决于教育水平[5]。未来的世界竞争实际是教育水平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教育要靠教师去成就,人才要靠教师去培养,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全社会都要重视的问题。
㉜㉟筑山醉翁:《社会主义简明史》,《解放与改造》1920年1月1日第2卷第1号。
㉝[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4页。
㉞李泽厚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怀国事民瘼的观念意识和伦理精神,肇始于汉代的大学生运动,延续至清末的甲午公车上书和辛丑后留日学生的投身革命。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㊱胡适:《四十自述》,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99页。
㊲[法]布朗基:《祖国在危急中》,顾良、冯文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39页。
Gas是以太坊系统中执行交易所需要的计算工作量单位。所有的交易不论是转账交易,还是执行智能合约,都要消耗Gas。Gas的价格由交易的发起人和矿工的工作量决定,交易打包进区块中需要矿工们进行哈希运算,矿工们付出了劳动,因此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如果交易发起人设置的Gas价格过低,矿工们基本不会将交易打包进区块里;如果交易设定较高的Gas,该交易将会得到较高的优先级。
㊳[英]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2页。
㊴陈独秀:《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2月15日第1卷第6号。
㊶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7卷1号。
⑯卢梭认为,习俗和舆论是无形的宪法,是法律和政治制度得以成功的前提。因此要将理想政治制度成为现实,只是将设计好的制度落实到权力机构是完全不够的,而是“要倒果为因,就需要使本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会精神转而超越在制度之上,使人民在法律出现之前就成为他们在有了法律之后才能成为的那种样子”。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7~48页。
㊸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新社会》1919年11月21日第3号。
㊹周炳琳:《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少年世界》1920年1月1号第1卷第1号。
㊺罗家伦:《近代西洋思想自由的进化》,《新潮》1919年12月1日第2卷第2号。
㊻《查禁“妨害治安”的机会出版之经过》,《每周评论》1919年1月1日第24号。
㊼南陔:《无政府主义之由来及无政府党各家之传略与学说》,《解放与改造》1919年11月15日第1卷第6号。
㊽若愚:《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4月20日第18号。
2.1 患者基线资料 导管组患者31例,其中男性11例,女性20例,平均年龄59.65(25~91)岁;原发病:原发性肾小球肾炎16例,多囊肾3例,糖尿病肾病9例,高血压性肾病2例,狼疮性肾炎1例。内瘘组患者195例,其中男性91例,女性104例,平均年龄52.65(22~86)岁;原发病:原发性肾小球肾炎126例,多囊肾7例,糖尿病肾病25例,高血压性肾病17例,狼疮性肾炎2例,其他18例。
㊾我们中国的少年要改造“少年中国”,只有与农民打成一气,因为农民是劳动界的大多数,握着一般缙绅先生的生命……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不愿在都市上鬼混的都可以加入此项团体,系指我们会员中有一部分人在都市上奋斗的,我们的新生活,就是他们的大本营,随时可以回来……若愚:《讨论小组织问题·致夏汝诚先生书》,《少年中国》1919年8月15日第1卷第2号。
㊿“克罗巴金(Kropodkin)的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现在却为各国政府所利用。这是过渡时代的现象呵。”蔡元培:《大战与哲学》,《新潮》1919年9月20日第1卷第1号。
51 [爱尔兰]萧伯纳:《华伦夫人之职业·第一幕》,潘家洵译,《新潮》1919年10月30日第2卷第1号。
在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面积的临时施工场地、土石堆放场、预制加工厂和施工便道等。据统计,新公路临时占用土地一般占总面积的30%左右。公路建设过程中,临时占地区域原有地貌的破坏,易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
52 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1919年12月1日第1卷第7号。
53 钱玄同:《通信·写白话与用国音》,《新青年》1919年11月1日第6卷第6号。
54 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5号。
其中,a为调域上线频率,b为调域下线频率,x为测量点频率,得出来的T值就是x点的五度值(chao)参考标度。
55 许地山:《“五一”与“五四”》,《新社会》1920年5月1日第19号。
作者包大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启蒙到解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多元实践研究”(18FZX035)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余 越
标签:启蒙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五四论文; 革命论文;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