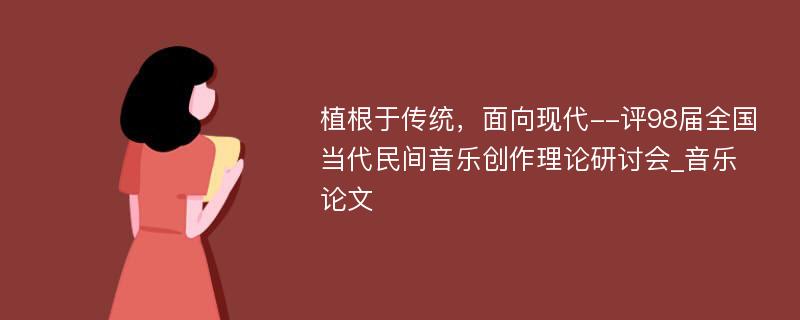
根植传统 面向现代——“98全国当代民乐创作理论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民乐论文,研讨会论文,当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唯有创作的繁荣,才是发展民族器乐艺术的根本之路。——这已是广大音乐工作者早已达成的共识。在世纪之交,回顾我国民族器乐艺术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成功与失败同在,欣慰与忧虑并存。如何进一步提高创作水平,写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作曲家个性的作品,这是摆在众多作曲家和广大民族器乐工作者面前迫在眉捷的问题。为此,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山东省音协、青岛市音协和《人民音乐》编辑部于10月27日至29日在青岛联合主办了“98全国当代民乐创作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三十余位作曲家、指挥家、理论家和演奏家济济一堂,共商民族器乐创作之大计。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放送了自己近年的代表作,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民乐创作必须根植于民族民间传统
学习民族民间传统,并非只是摆在从事西洋管弦乐创作的作曲家面前的任务,实践证明,在审美价值取向和具体写作技法方面,从事民乐创作的作曲家,仍然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中西关系、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传统的问题。民族器乐艺术只有深深扎根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才能生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黎英海指出,过去争论最多的问题是中西关系、古今关系,焦点是如何对待民族音乐传统问题。过去虽然也一直提倡继承发扬传统,而对保证优秀传统却有所忽视,过分强调了“改进”、“出新”、“借鉴”,致使传统有所消弱,甚至被抛弃。尤其严重的是在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中民族传统音乐至今还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受到极大摧残,民族自尊心受到挫伤,妄自菲薄。今天要振兴民族文化,首先就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把自立点重新回到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在世纪之交,我们面临着重新认识传统的问题。在民族器乐创作中,过多的"ABA"三段体,滥用模进手法,生硬的和声配置,单调的多声织体等,都反映出我们对传统重视不够。借鉴不是代替,模仿不是创造。民族器乐创作更应根植于传统。金湘指出,西方人看不起我们,这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看不起自己,思想中还是“欧洲文化中心”论。例如有的指挥家以不会指挥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为耻,却对不会指挥中国作品不以为然。顾冠仁认为,在创作中如果不去研究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不研究我们蕴藏丰富而有特色的民族民间音乐遗产,不熟悉它的调式、旋律、表现手法及乐器的演奏特点、技巧及其风格,那我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没有生命力。所以,我们应该把继承传统放在首位,把学习、研究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作为作曲家重要的基本功。于庆新认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伴随着音乐事业发展全过程的一个永恒课题。近年来,对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存在持基本否定的意见已日渐减少,这次研讨会上也几乎听不见这种尖锐的反对意见。可以说,这一基本形式已得到了广大音乐工作者和听众的认可。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对大乐队持否定的意见虽然有失偏颇,但其主张中具有根植于民族民间传统、反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合理内核,在当今出现一窝蜂地拥向同一乐队模式的时刻,这一意见的合理内核发人深省,他们对某些创作技法和观念、乐队编制、乐器改革所提出的批评不容忽视。半个世纪以来,民族民间传统中丰富多样的地方乐种普遍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在全国绝大多数专业团体的创作表演中,在艺术院校的教学中,这些传统乐种几乎无立足之地。应该使我们艺术院校的学生从小就熟悉并热爱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当然,我们在克服民族自卑心理的同时,也要防止“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在消除“欧洲文化中心”论影响的同时也要避免“东方文化中心”甚至“大汉族文化*
心”论。我们应该具有立足传统、多元互补的宽容心态。长期从事民族音乐工作的同仁们对此也要有所警觉。
(二)民族乐队组合形式的规范化与多样化
20世纪以来,我国民族乐队的组合形式一直处于多样、游移的探索阶段。实践证明,尽早将多种组合形式规范化,是繁荣民乐创作的重要环节。
刘再生指出,有人在归纳本世纪民族乐队组合形式时提出了“彭修文模式”、“新潮音乐模式”和“新古典主义(民族室内乐)模式”三种典型模式。应当指出,这些模式都是现代民族器乐创作在不同时期具有时代变异特征的产物,其形式并不属于交替更迭的性质。有的模式可能长期存在下去,有的或许“昙花一现”,时代呼唤着规范化的定型模式。即便是大型民族管弦乐合奏的“彭修文模式”,也存在着多元倾向。民乐创作应该在模式问题上求得共识,创作形式的多样化和选择若干定型模式并不互相排斥。刘再生认为,迄今为止的民族器乐模式可分为传统模式、民间模式和现代模式三大类型。传统模式多数已成为历史,但模式演变的成因及其规律却仍有启迪意义。每种新兴乐器的出现必然导致器乐模式的变革。现代模式则是本世纪西方音乐文化传入中国后在外力作用和内向选择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大、中、小型各种形式。严格地说,现代模式尚处于多样化的探索阶段,其成熟与完善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作曲家多样化的创作实践。我们要创造出一个既体现不拘一格的音乐创作多元化,又提倡民乐模式规范化的文化氛围。
鲁日融作了《重视民族室内乐、重奏作品的创作与演奏推广》的专题发言,他回顾了近几十年来我国民族室内乐、重奏艺术发展的历程。他认为,中国民族室内乐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作曲家、演奏家们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多彩多姿的组合形式,积累了一批优秀的曲目。十分可喜的是80年代以来,一批优秀的专业作曲家们积极投身到这一领域中,他们大胆吸收西方现代技法并与我国民族传统相结合,创作了一批优秀室内乐作品。他们大大扩展了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术和表现力,为当代民乐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室内乐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表现空间。于仲德、胡天泉、朱晓谷等代表指出,现在大中型作品较多,中小型作品太少。作曲家应多尝试写作各种组合的中小型作品。
张殿英在题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团需要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的专题发言中提出了包括吹管组、拉弦组、弹拨组和打击乐组在内的70余人乐队编制的构想。张式业以自己在前卫民族乐团多年的创作、指挥实践,作了题为《现代民族乐队的创建与实践》的发言。他认为,现代民族乐队的概念应包括:编制上具有立体化多声部结构;乐器性能上具有准确性,并具有适应多调性、高技巧的功能;在训练上要求达到谐和性、平衡性并能适应多风格、高层次作品要求的具有交响性的乐队,他认为,我国现代民族乐队的编制结构和常规乐器可能趋于统一和规范化,但各自的编制规模和使用的特色乐器仍将百花齐放。现代民族乐队必须具备几个相对平衡的基本组群,即常规乐器组。应该使用哪些乐器为常规乐器?各常规乐器组是否要按照高、中、低纵向结构来编成?张式业主张,多种音色对比的横向协调,与高、中、低宽音域纵向跨越的立体化结构,是现代民族乐队编制规范化的重要原则。对争议较多的弹拨乐器组的设置,他认为,我国的弹拨乐组是一个多色彩、多功能的乐器组,把它看成是一个单音色乐器组是不恰当的。弹拨乐器组是体现我国民族乐队特色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技法和表现力,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多彩性,切不可把它当作第二弓弦组来使用。
(三)民乐创作的交响性民族性探索与创新
我们目前的民族管弦乐队,基本上是从民间吹打乐队和丝竹乐队的传统基础上并借鉴西洋管弦乐队的经验发展起来的。西洋管弦乐队经历了近四百年的历史才发展到如此完备的规模,并积累了千百部经典之作。而我们目前的民族管弦乐团才仅有几十年的历史,其稚嫩与不完善当在情理之中。乐队的完善与作曲家的创作是相互制约和促进的。民族乐队要不要交响化?如何使民族乐队具有交响性思维,从而表现具有时代性、英雄性或哲理性的题材?
金湘认为,沸腾火热的现实生活,奔腾前进的历史步伐,艺术家的冲动激情,哲学家的冷静思考……,反映到作曲家的头脑里,汇成了作曲家心中涌动的交响性乐思。当作曲家的目光选中了民族乐队作为这种乐思的载体时,民族乐队交响化就是势在必行了!那种认为民族乐队不能交响化的观点,不仅是认识上的偏差,而主要是存在心理障碍——“欧洲文化中心”论在作祟!民族乐队怎样交响化?实际上这是一个具体实践的问题,这里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对于处在发展过程中初期阶段的民族乐队,既要看到其局限性,更要看到其独特的个性。能否扬长避短,这是衡量一个作曲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郑冰认为,交响性民乐作品的出现,是我们民族管弦乐的重大进步。民族管弦乐队的长处和短处都是由民族乐器的个性决定的。我们作曲家的任务就是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所长,比如其随意性和独特的音色特性,同时回避这些个性造成的不协和效果。
王甫建指出,有些大型作品缺乏应有的力度,总想通过乐器来解决力度问题,仅仅增大了乐队的音量,但奏出的音响却是散的,作曲家是否要考虑一下这里面是否存在一个写法的问题。王甫建还着重谈了“音色”在民乐作品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音色在西洋管弦乐队中只是个配器问题,但在民乐队中却是个决定性因素。古琴的音色是无法替代的,二胡的音色在《二泉映月》中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音色的质地感是音乐形象的主要因素,往往是其他乐器所无法替代的。二胡拉《梁祝》就不如拉《新婚别》,把钢琴协奏曲《黄河》改为扬琴,就更为可笑。有的和声配置,在谱表上是合理的,因没有考虑到音色的特性,其音响效果就未必合理。有人常常把民族管乐当铜管用,其结果是悲壮感有余而雄壮感不足。在写作时要讲点“音色配器”,即利用民族乐器音色的个性、分离性,这与西洋配器中的“融合性”恰恰是相对的。
刘文金根据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作了题为《重视传统基因、元素》的专题发言。他说,我们对传统音乐的基因、元素要给予充分的重视,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民间音乐“引用式”的阶段。对传统音乐中的“基因”、“元素”要做深入的开掘,例如,音型结构即音的运动状态,常规或非常规的演奏方法,各种不同的装饰音等等,都是民族民间音乐所谓“韵味”中的重要因素。另外,戏曲音乐中丰富多样且极富表现力的打击乐节奏型,更是有待我们开发的文化宝藏。
如何对待现代技法即新潮音乐?是近十多年来的热门话题,这次研讨会仍不例外。
冯光钰在《回眸20世纪中国现代民乐创作》的专题发言中认为,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我国现代民乐创作正面临着民族音乐文化传统的逐渐流失。这种流失,反映在现代音乐作品中首先是远离生活;这种流失也反映在创作思维的倾斜,生搬硬套西方现代派音乐的模式;这种流失还表现在有的民乐作品对旋律的忽视,八九十年代的民乐作品中,有的却只是一些音响和音色的对比和不协和音的堆砌。
朱晓谷则认为,新潮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乐创作,尤其是各种音色的搭配,许多中青年作曲家敢于创新,有些作品已逐渐为听众所接受。不能盲目地认为都是噪音的堆砌,当然也不能盲目地认为这是唯一的模式,传统与现代要互相补充。金湘认为,有的人可以在传统的大树下细品慢嚼,但不能对敢于突破传统、勇于创新的人稍稍有点出格就大加指责、扣帽子。演奏技法的突破常常是作曲家先行。只有观念突破才能有技法的突破。唐建平认为,创作观念上不能保守,对荒唐的东西不必过多鞭笞。音乐创作要多元发展,对传统要予以保护,对发展也要予以保护。王甫建指出,从事新潮音乐的作曲家们,他们通过不断的探索,也在不断调整自己,可以说,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点”。于庆新认为,对艺术上勇于探索的人要采取鼓励至少是宽容的态度,不能轻易以“自由化”论之。最近,不少作曲家又开始创作调性音乐,有些批评者自以为“三年早知道”,似乎这些作曲家是“浪子回头”,重新回归。应该看到,他们并非简单地回到原位,而是螺旋式地上升,毕竟在音色、音响的开掘等方面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技法。最为可贵的是,他们敢于冲破几十年“左”的思想禁锢,追求创作的个性化,这种作曲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其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杨青指出,作曲家们为更好地表现当今社会的情感与脉动,在民族乐器的演奏技艺及细致音色处理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用新的思维来处理传统技法,大量非常规演奏方法的出现,极限音区的使用,乐器音域的拓宽,各种非常规定弦方式的实施,新的记谱符号的出现等等,这一切都极大地开拓了民族乐器的表现力,同时又对演奏家们提出了挑战。
朴东生会长代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李岚清副总理于今年7月在中国音乐学院发表了《为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民族音乐做贡献》的重要讲话,《人民音乐》已于98年第9期全文发表。这是党中央对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创作是民族管弦乐发展的关键。在世纪之交举行如此规模的创作研讨会,必将为21世纪我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取得更辉煌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和思维基础。山东省音协主席于仲德、青岛市音协副主席孙厚存在发言中呼吁社会各界都应关心、支持民族音乐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研讨会上,许多代表还呼吁,要打破中国民族音乐与交响乐创作格格不入的局面,广大作曲家都应来关心并积极参与民族器乐的创作。
研讨会上,许多代表宣读了论文或发表了讲话,如刘锡津的《民族器乐创作的燃眉之急》,房晓敏的《世纪之交民乐创作的思变》、张鸿伟的《重视青少年题材的民乐创作》、刘寒力的《创作随笔》、景建树的《创作札记》、权吉浩的《民乐创作中现代技法的探索》等等。
与会代表认为,这次研讨会与近年来历次召开的民乐创作研讨会相比,是一次高水准、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达到甚至超过了会议的预期效果。其成功的原因,除山东省音协和青岛市音协的大力支持外,每位代表必备的高质量的论文,以及高水准作曲家和专业院校优秀青年教师的加盟,是两条重要的原因,值得同类学术会议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