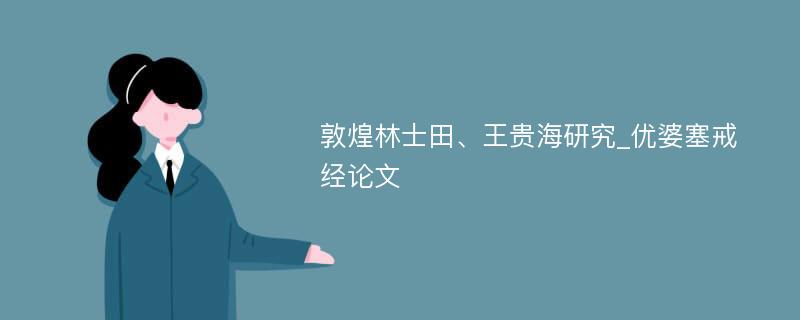
敦煌写本《优婆塞戒经》版本研究林世田汪桂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写本论文,版本论文,优婆塞戒经论文,林世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在参加全国古籍保护情况调查时,于山西博物院发现3件未见于著录的敦煌写本。其中一件隶意较浓,当属六朝写本。我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隔着玻璃拍摄了照片,经过认真比对,发现内容为《优婆塞戒经·尸波罗蜜品第二十三》。以此为起因,我们将现存敦煌写本中的《优婆塞戒经》汇集一处,排比考索,薄有所得,不揣谫陋,略申管见,就正于方家。
一、敦煌写本《优婆塞戒经》及其版本
《优婆塞戒经》,北凉昙无谶译。因系以《中阿含经》卷三十三之《善生经》为基础推衍、发展而成,故又称《善生经》。该经是一部佛陀为在家修菩萨行者所说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修行证果的重要典籍。经中教导学人要以无量善业因缘,发起菩提心和大悲心修习六波罗密,成就福德、智慧二种庄严,以养成具足大悲心的菩萨性。在此基础上,围绕受持优婆塞戒这一中心,开示受戒、修善、净戒、息恶等方法,并具体教导学人广修六度万行,成熟众生,自他兼利,共成佛道。该经不仅是在家信徒的修行指南,也是出家僧人的行为规范,修习者甚众。
《优婆塞戒经》在敦煌地区亦曾广泛流行,我们根据已出版的图录和目录在敦煌文献中发现有36件写本:S.315、S.2201、S.3967、S.4162、S.4570、S.4579、S.5332、S.5354、5.6600、P.2276、P.5581b、BD07348(鸟48)、BD04157(水57)、BD03369(雨69)、甘肃图书馆014、天津艺术博物馆018、敦煌研究院100、北京大学图书馆D083、上海图书馆105—9、敦煌研究院221、敦煌研究院162、敦煌研究院208、敦煌研究院228、敦煌研究院262、敦煌研究院027、敦煌研究院028、上海图书馆091、甘肃省博物馆005、台北“中央图书馆”088、敦煌研究院004、傅斯年图书馆05、S.8099、S.8293、BD10777、BD11023、山西博物院藏本。其中只有傅斯年图书馆05、S.8099、S.8293、BD10777、BD11023和山西博物院藏本等6件写本,尚未公布图版。傅斯年图书馆05则仅见于郑阿财《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卷子题记》的著录①。据郑阿财介绍,傅斯年图书馆05的卷尾有两则题记:
“比丘志念所写,顶载(戴)供养〈经〉,愿与一切人受持流布,共升道场,三会之初,俱在上首。”
“都司马姚英妻李法姜造写戒经,顶载(戴)供养,愿共一切众生读诵受持,世世所生,常与佛会,弥勒出生,愿在初首。”
该题记表明,《优婆塞戒经》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与弥勒下生信仰有关。中国对弥勒经典的翻译始自西晋,盛于南北朝时。西晋大安二年(303)竺法护译《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姚秦弘始四年(402)鸠摩罗什译《弥勒大成佛经》、《弥勒下生成佛经》,南朝刘宋时沮渠京声译《弥勒上生经》,北魏永平元年至天平二年(508-535)菩提流支译《弥勒菩萨所问经》。随着弥勒经典的翻译,弥勒信仰在南北朝时开始逐渐盛行。弥勒信仰分为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下生信仰认为弥勒将来下生时,于龙华树下,三会说法,救渡众生,而自己亦能生此世界,于龙华树下听受说法而成佛,因此有龙华三会之说。下生信仰流行社会各阶层,刘宋明帝曾撰《龙华誓愿文》,周颙作《京师诸邑造弥勒三会记》,齐竟陵文宣王作《龙华会记》。
南北朝时,因弥勒信仰的流行,《优婆塞戒经》也得到广泛传播。根据楹雅珍写经题记(详见下文所引),我们知道抄写《优婆塞戒经》有超荐亡灵的功德,而且与抄写《灌顶经》、《善恶因果经》、《太子成道经》、《五百问事经》、《千五百佛名经》、《观无量寿经》,造观世音像、卌九尺续命神幡等结合在一起。这也对该经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优婆塞戒经》的内容分集会、发菩提心、悲、解脱、三种菩提、修三十二相业、发愿、名义菩萨、义菩萨心坚固、自利利他、自他庄严、二庄严、摄取、受戒、净戒、息恶、供养三宝、六波罗蜜、杂、净三归、八戒斋、五戒、尸波罗蜜、业、羼提波罗蜜、毘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等二十八品,其中“杂品第十九”、“业品第二十四”之后有“杂品第十九之馀”、“业品第二十四之馀”。历史上因为对二十八品的分卷不同,形成卷数不同的各种版本。关于《优婆塞戒经》的版本,《历代三宝记》卷第九记载有十卷、七卷、六卷三种版本。另《佛光大辞典》还提到有五卷本。现在传世《大藏经》本为七卷本。敦煌本《优婆塞戒经》发现之后,使人们认识到曾经还有一个十一卷本流传。《敦煌学大辞典》所收方广锠先生撰该辞条即以十一卷本为依据,他说:“敦煌本系十一卷本,分卷与入藏本不同。但内容一致,可供校勘。”②该辞条撰写较早,当时许多资料尚未公布。随着敦煌藏经洞资料的出版公布,不断有新的《优婆塞戒经》写本进入人们的视野。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敦煌本《优婆塞戒经》远不止十一卷本一种,典籍记载的十卷本、六卷本(或五卷本),以及仍然传世七卷本,这三种版本在敦煌写本中同样都存在,也就是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优婆塞戒经》至少应该有四种版本:
第一种是与传世《大藏经》本相同的七卷本。如S.5332尾题“优婆塞戒经卷第七”,卷中品题有:“优婆塞戒羼提波罗蜜品第廿五”、“优婆塞戒毗梨耶波罗蜜品第廿六”、“优婆塞戒禅波罗蜜品第廿七”、“优婆塞戒般若波罗蜜品第廿八”,正与七卷本的卷数及分卷方式相合,可证其应为七卷本。台北“中央图书馆”088、敦煌研究院004亦为七卷本。
第二种是十一卷本。如BD04157(水 57)尾题“优婆塞戒经卷第十一”,卷中有品题“优婆塞戒般若波罗蜜品第廿八”;法国国立图书馆P.2276,尾题“优婆塞戒经卷第十一”,残存内容亦为“般若波罗蜜品第廿八”。第廿八品为该经最后一品,说明此种写本属于十一卷本。
第三种是十卷本。如S.3967尾题“优婆塞戒经卷第十”,卷中的品题有:“优婆塞戒经羼提波罗蜜品第廿七”、“优婆塞戒经毗梨耶波罗蜜品第廿八”、“优婆塞戒经禅波罗蜜品第廿九”、“优婆塞戒经般若波罗蜜品第三十”,说明十卷本有三十品,最后一品与七卷本之第廿八品相同,都是《般若波罗蜜品》。可见,此写本将原来的二十八品析分为三十品。因为敦煌遗书中没有完整的十卷本保存下来,难以确定十卷本所析分出来的两品的品名,我们推测可能是将“杂品第十九”、“业品第廿四”之后的“杂品第十九之馀”、“业品第廿四之馀”皆单独立作一品。
第四种是傅斯年图书馆05。据郑阿财《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卷子题记》著录,该写本为晋人写卷,内容是《优婆塞戒经供养三宝品第十七》,尾题作“优婆塞戒经卷第二”③。而《供养三宝品第十七》在七卷本中为卷三结尾的内容,那么它的分卷应该少于七卷。至于其为六卷本抑或《佛光大辞典》中所说的五卷本,因资料不足,目前尚难断定。
二、楹雅珍写《优婆塞戒经》的版本问题
颇为珍贵的是,敦煌写本《优婆塞戒经》中有一组有仁寿四年(604)楹雅珍④写经题记,为我们研究十一卷本与七卷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图书馆D083(卷第二)、大英图书馆S.4162(卷第三)与S.4570(卷第六)、甘肃省博物馆005(卷第十)、法国国立图书馆P.2276(卷第十一)。从纸张和抄写字体风格上看,这些写经应该是属于同一种抄本。我们知道,一部正规的敦煌写经,通常有较为完整的首题、尾题和题记。尾题即卷尾的题目,尾题与经文末行之间通常留一空行。尾题之后的位置常用来写题记,如果没有空地,也要加纸写完。题记一般包括年代、抄写者和供养人的姓名、发愿文,许多题记比较简单,甚至只有一个人名。题记与尾题之间也留有一行空白⑤。楹雅珍写经文字精整,隶味较浓,一望便知是正规写经。照理来说,其尾题与题记在格式上应当较为规范统一,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下面先将这几个写本的首题、尾题、题记以及品题的情况逐一介绍一下:
(1)北京大学图书馆D083
有首题,曰“优婆塞戒发愿品第七卷第二”。卷中有品题:“优婆塞戒名义菩萨品第八”、“优婆塞戒义菩萨心坚固品第九”。没有尾题。题记在加纸上抄写,题记后面有“卷第二”三字,字迹与题记和经文不同,显系后来所添补。题记的文字曰:
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为亡父写《灌顶经》一部、《优婆塞经》一部、《善恶因果经》一部、《太子成道经》一部、《五百问事》一部、《千五百佛名》一部、《观无量寿》一部,造观世音像一躯,造卌九尺幡一口。所造功德,为法界众生,一时成佛。
(2)大英图书馆S.4162
卷首残损,首题缺失。卷中有品题:“优婆塞戒自利他利(利他)品第十”、“优婆塞戒自他庄严品第十一”、“优婆塞戒二庄严品第十二”。尾题和题记均与经文抄在同一张纸上,尾题与经文之间有一行空栏,题记抄写在尾题正下方,从尾题与经文之间的空白行开始。尾题曰“优婆塞戒经卷第三”。题记三行,曰:
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为亡父写《优婆塞经》一部、《灌顶》一部、《善恶因果》一部、《太子成道》一部、《五百问事》一部,造观世[音]像一躯,造卌九尺幡。为法界众生,一时成佛。
(3)大英图书馆S.4570
首残尾全,品题没有保存下来,残存内容为“业品第廿四之一”。有尾题,曰“优婆塞戒卷第六”,与经文抄写在一张纸上。题记三行,抄写于加纸上,曰:
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为亡父[写]《灌顶》一部、《五百问事》一部、《千五百佛名》,造观世音像一躯,造卌九尺幡一口。为法界众生,一时成佛。
(4)甘肃省博物馆005
首残尾全,首题、品题缺失,残存内容为“业品第廿四之馀”。尾题和题记均书写在加纸上。尾题曰“优婆塞经卷第十”,题记六行,抄写在尾题正下方,曰:
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因向京⑥,为亡父写《灌顶经》一部、《优婆塞经》一部、《善恶因果经》一部、《太子成道经》一部、《五百问事经》一部、《千五百佛名经》一部、《观无量寿经》一部,造观世音像一躯,造卌九尺续命神幡一口。所造功德,为法界众生,一时成佛。
(5)法国国立图书馆P.2276
首残尾全,首题、品题缺失,残存内容为“般若波罗蜜品第廿八”。尾题与经文抄写在同一张纸上,曰“优婆塞戒经卷第十一”。题记五行,抄写在加纸上,曰:
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为亡父写《灌顶经》一部、《优婆塞》一部、《善恶因果》一部、《太子成道》一部、《五百问事经》一部、《千五百佛名经》、《观无量寿经》一部,造观世音像一躯,造卌九尺神幡一口。所造功德,为法界众生,一时成佛。
法国国立图书馆P.2276号表明,这五件楹雅珍写《优婆塞戒经》应属于十一卷本。根据各写卷的情况分析,这些写卷中有的原来前后衔接。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D083号属于《优婆塞戒经》卷二,包括有优婆塞戒发愿品第七、优婆塞戒名义菩萨品第八、优婆塞戒义菩萨心坚固品第九。而大英图书馆S.4162号属于《优婆塞戒经》卷三,包括有优婆塞戒自利利他品第十、优婆塞戒自他庄严品第十一、优婆塞戒二庄严品第十二,无论在品次还是卷次上都恰好可以与北京大学图书馆D083号的内容相衔接。又,甘肃省博物馆005号属于《优婆塞戒经》卷十的最后部分,残存部分为业品第二十四之馀。法国国立图书馆P.2276号属于《优婆塞戒经》卷十一的最后部分,残存内容为般若波罗蜜品第二十八。按照十一卷本对二十八品的划分,第十一卷的内容为羼提波罗蜜品第二十五、毗梨耶波罗蜜品第二十六、禅波罗蜜品第二十七、般若波罗蜜品第二十八,P.2276如果保存完整的话,应该正是与甘肃省博物馆005号相衔接。
值得注意的是,楹雅珍写《优婆塞戒经》,在多处尾题、题记上显示出草率和不规范的特点。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D083号的经文与题记之间竟然没有尾题,只是在题记后面以另外一种笔迹添补了“卷第二”三字。大英图书馆S.4162号尾题之后已没有空地,其题记本应加纸抄写,却没有按照常规去做,仅将题记内容压缩,抄写在尾题正下方。甘肃省博物馆005号的尾题“优婆塞经卷第十”和题记均在加纸上抄写,题记亦未按照常规在尾题左下侧抄写,而是抄写在尾题正下方。
另外,从图录上看,大英图书馆S.4162号尾题“优婆塞戒经卷第三”中的“三”字原本应作“二”,最末的一笔横划是后来添加上去的,添改痕迹非常明显。法国国立图书馆P.2276号尾题“优婆塞戒经卷第十一”中的“十一”原应是“十”或“七”,末笔的“一”划显然也是后来添改的。对于这种存在明显改动的迹象,学界一般认为可能属于毫无意义的涂改,比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即著录S.4162为“优婆塞戒经卷第二”,大概在该书的编者看来,“二”下的“一”划没有意义。笔者最初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可能是当时勘经者留下的痕迹之类,但后来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这些增改的笔画不是随意所为,而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该经尾题、题记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与楹雅珍写经的形成方式有关。从现有的迹象推断,楹雅珍写《优婆塞戒经》未必是为楹雅珍抄写经文者(名曰向京⑦)亲手所抄,而是他利用旧有写经,经过改装而成。
楹雅珍写经对原写卷所作的改装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一、改变原来的分卷,对写经的分卷作了进一步的析分。原来的写经并非十一卷本,而是七卷本,经过进一步的析分,原来的写经遂成为十一卷本。从现在见到的这五件楹雅珍写经来看,北京大学图书馆D083完整无缺,首题曰卷第二,但在内容上仅相当于传世七卷本之卷二的前半部分。大英图书馆S.4162卷首略有残损,首题缺失,尾题曰卷第三,内容相当于传世七卷本之卷二的后半部分。这显然是把原七卷本的卷第二拆分为两卷。
大英图书馆S.4570首残尾全,尾题曰“优婆塞戒卷第六”,内容也相当于七卷本的卷第六。
甘肃省博物馆005首残尾全,尾题曰“优婆塞经卷第十”,内容仅为七卷本之卷第七的前半部分(即“业品第二十四之馀”)。法国国立图书馆P.2276首残尾全,首题、品题缺失,残存部分为“般若波罗蜜品第廿八”。尾题曰“优婆塞戒经卷第十一”,内容应为七卷本之卷七的后半部分。这显然是把原七卷本的卷七拆分为两卷。
由此可见,十一卷本从七卷本新析分出来的四卷中,有两卷的来源是清楚的。另外两卷是从哪些卷中析分出来的,目前还不清楚。
二、改变原来的卷次,添补部分首题和尾题,撤换掉原来的写经题记,重写题记。经过析分,原来的写卷卷数增加,旧的卷次必然要作相应的变化,例如原来的卷二析分出一卷,新析分出的一卷即为卷三。这样,其后的各卷无论是否析分,首题和尾题中的卷次都要改变,就出现了我们所见到的大英图书馆S.4162号、法国国立图书馆P.2276号尾题中卷次的添改现象。
经过析分之后的有关各卷,还需要相应增加首题和尾题,因为这种析分是将原来的写卷在某一品与下一品之间分割开,分割之处的后一新立之卷就需要添改首题,而前一卷就要补加尾题,因系分割,尾题无处书写,这就出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D083号和甘肃省博物馆005号所反映的情况。北京大学图书馆D083号(卷第二)内容仅相当于传世七卷本之卷第二的上半部,大约重新分卷时将七卷本的卷第二分为两卷,上半部为卷第二,下半部为卷第三。北京大学图书馆D083号为新的卷第二,卷尾需要加纸以补写尾题和题记,因为疏忽,先写了题记而漏掉了尾题,为了弥补,就只是在题记后面写下“卷第二”,只标明卷次。“卷第二”的笔迹与S.4162、P.2276改动的笔迹非常接近,应该是同一人所为。甘肃省博物馆005号相当于七卷本的卷第七的前半部分,也是因为从中间分卷,原来并没有尾题和题记,分卷后,将需要补加的尾题和题记书写在加纸上。
令人困惑的是,大英图书馆S.4570尾题曰“优婆塞戒卷第六”,残存内容为“业品第廿四之一”;甘肃省博物馆005尾题曰“优婆塞经卷第十”,残存内容为“业品第廿四之馀”。这两个写卷虽然都已经残缺,仅存卷尾,但从内容上看,他们应该是前后衔接的两卷,何以所标的卷次一曰卷第六,一曰卷第十,前后相差竟有四卷之多?
前面说过,甘肃省博物馆005号与法国国立图书馆P.2276号分别属于十一卷本《优婆塞戒经》的卷十和卷十一,二者可以缀合。可见,甘肃省博物馆005尾题作“优婆塞经卷第十”没有错。有问题的显然应该是S.4570的尾题“优婆塞戒卷第六”。众所周知,十一卷本与七卷本尽管都是二十八品,但其分卷截然不同。但S.4570的现存文字与传世七卷本的卷第六不仅在内容上相同,都属于“业品第廿四之一”,而且二者的卷次也一致,这是完全不应该出现的。按照目前所知楹雅珍抄写十一卷本的分卷情况看,传世七卷本的卷七前半部分相当于十一卷本的卷十,由此我们就可以推知七卷本卷六结尾部分肯定应该属于十一卷本的卷九。可见,S.4570号写经的尾题“优婆塞戒卷第六”的“六”本应当在当时改为“九”。可能由于一时疏忽,此处未加改动,从而造成楹雅珍写经既有十一卷本又有七卷本的假象。不过,正因为这一疏忽,使我们可以确认,此十一卷本是从七卷本直接改装而来,P.2276写卷尾题“优婆塞戒经卷第十一”中的“十一”原应是“七”。
以修补旧的写经来做功德,在中国古代非常盛行,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道真补经就颇为有名。道真是五代宋初敦煌三界寺的一位管理佛经的僧人,他在典藏佛经时,发现许多年代久远的写经都损坏或缺失了。他考虑到,这首先是对法宝的不敬;其次,敦煌地处偏远,法宝匮乏,需要大量佛经来丰富敦煌百姓的精神生活,于是就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修补佛经的活动⑧。修补旧的佛经与改装旧的佛经尽管都是属于旧本新用,然而两者还是有些微的差别。与楹雅珍写经性质更为接近的是隋炀帝利用南方经典造宝台经藏的活动。据《隋炀帝宝台经藏愿文》,隋炀帝平陈之日,“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鬘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未及期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司,依名次录,并延道场义府,覃思证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类。庄严修葺,其旧惟新。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悉连卷后。”⑨由此观之,隋代皇室修造经藏,尚且利用平定南朝时所收集的佛典,然后整理排比,得“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庄严修葺,其旧惟新”,并书愿文,连缀于卷后,民间百姓抄经作功德,利用收集来的旧卷,重新装潢,并书愿文于后,也就比较自然了。
以上讨论了题记中明确署有楹雅珍名字的《优婆塞戒经》的有关问题,由此出发,可以使上海图书馆091号写卷的一些问题得到清楚解释。上海图书馆091首残尾全,卷尾有木轴。卷尾仅有一个乌丝栏行格的馀幅,而没有尾题,题记也接抄在经文之后,这在正规的写经中十分罕见。该题记的内容,《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叙录》录为:“善生灌顶千佛无量寿像一躯,卌九尺幡一口,为法[界]众生一时成佛。”起初单独解读这则题记时,让人有如坠五里迷雾之中,现在结合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写经题记,再看该题记,其含义就豁然开朗了。原来,该题记应该做如下句读:“《善生》、《灌顶》、《千佛》、《无量寿》,像一躯,卌九尺幡一口,为法[界]众生,一时成佛。”《善生》亦即《优婆塞戒经》的别称。该题记内容与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写《优婆塞戒经》题记相同,只不过更加简略而已。大约因为卷尾馀幅小,抄写者又因某种原因没有加纸,所以只能简写。如果没有同组题记对照,很难作准确句读并复原其本意。此卷的写经字体和题记字体均与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写经相同,说明上海图书馆091写本应该也是仁寿四年四月八日楹雅珍写《优婆塞戒经》残卷。该残卷内容为杂品第十九,相当于传世七卷本卷四的后半部分,七卷本卷四的经文在抄完后,原来大约如同P.2276一样留有一行的余幅,然后书写“优婆塞经卷第四”的尾题。(该尾题很有可能是在重新分卷之前或之后加装卷轴时,被卷在里面,造成尾题缺失。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因为卷尾仅存一行的余幅,题记也就简单地接抄在经文之后,与楹雅珍写经其他各卷题记格式又有所不同。
楹雅珍写经,字体风格一致,隶味较浓,应该是同时代抄写的。这些写经既然是利用旧抄本改装,那么其最初抄写经文的年代应早于题记所显示的仁寿四年。上海图书馆091题记中未署年月,启功先生鉴定为六朝写经,并在包首上题签:“六朝写经卷元白启功题耑”。《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叙录》编者采用了启功先生的鉴定结论,亦作六朝写本。而《甘肃藏敦煌文献》和《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的编者均将残卷的时代定作隋代,这显然是受仁寿四年题记的误导所致。敦煌写本的断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从文本内容、纸张、书法、避讳、题记、形制等诸方面综合考察,如果仅从题记来做判断,难免失之偏颇,未足凭信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优婆塞戒经》在南北朝时因弥勒信仰的盛行以及该经具有超荐亡灵的功用而广泛传播。在36件敦煌写本中至少有七卷本、十一卷本、十卷本、六卷本(或五卷本)四种版本系统。楹雅珍写经原本是六朝时期抄写的一个七卷本,到隋代仁寿四年被经生向京改装成十一卷本。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十一卷本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经生向京利用一个旧的七卷本改装为十一卷本时,其卷次的析分是否依照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十一卷本,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不过,从常理推断,这一可能性是很大的。无论怎样,楹雅珍写经作为一个将七卷本《优婆塞戒经》改装为十一卷本的例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优婆塞戒经》七卷本与十一卷本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研究该经不同版本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条件。
注释:
①《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第360-361页。
②《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710页。
③《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第360-361页。
④“楹雅珍”,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S.4162、P.2276著录为“楹维珍”,S.4570著录为“杨维珍”;《敦煌学大辞典》该条目录为“楹惟珍”;段文杰主编《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叙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录为“楹维珍”。
⑤有关敦煌写经的形制,可参看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3-344页。
⑥段文杰主编《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叙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误将“因”释作“目”。
⑦甘肃省博物馆005号题记有“楹雅珍因向京为亡父写《灌顶经》一部”之语,此处的向京应是代楹雅珍抄写经文的经生。
⑧林世田、张平、赵大莹:《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古代修复浅析》,《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3期。
⑨《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2册,第257页b-c。此条材料由史睿博士提供,谨致谢意。
⑩有关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断代,可参见陈国灿:《略论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的史学断代问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
标签:优婆塞戒经论文; 般若波罗蜜论文; 博物馆论文; 观无量寿经论文; 文化论文; 图书馆论文; 甘肃省博物馆论文; 敦煌博物馆论文; 经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