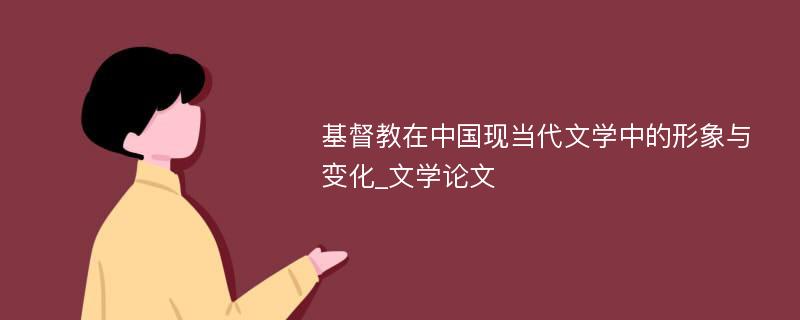
基督教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形象及其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中国论文,现当代论文,形象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854(2007)01-0032-06
基督教自从传入中国以来,不言而喻,便与中国文学发生了联系。这不仅因为基督教的宗教典籍本身同时便是一种文学典籍,而且由于既已介入中国文学之语境,在精神、思想、言述方式等方面对后者发生影响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从《大秦景教流行碑》便可看出。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在任何时期的关系都是可研究的。但众所周知,至少就大陆而言,人们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现当代文学①上。虽然基督教至今仍非中国文学的主流话语,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信众的迅速增长,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思想对基督教的主动“承纳”(刘小枫语),基督教已然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声音之一,在形塑中国文学未来走向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然,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话语融入中国文学,难免要经过曲折漫长的历程。所谓“漫长”,是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学全面而日渐深入的互动已有百年;所谓“曲折”则是说,基督教在中国文学首先遇到的是各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ism)的改造、扭曲与抵抗,但与此同时上帝中心主义(theocentricism)进路亦日渐拓展,基督教文学方兴未艾,预示出中国文学的某种方向。
一、人类中心主义进路:从诗艺开始的多重变奏
基督教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开始于《圣经》语汇及其文体的引入。古汉语《圣经》译本1823年面世,1919年白话“国语和合本”出版,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滥觞,西方文学被作家与诗人大量“拿来”,《圣经》语言遂同与《圣经》有千丝万缕牵缠的西方文学一起进入中国文学。“上帝”、“天使”、“伊甸园”、“魔鬼”、“撒旦”、“亚当”、“夏娃”、“安琪儿”、“诱惑”、“堕落”、“原罪”、“救赎”、“十字架”、“复活”、“末日审判”、“永生”等词汇,以及摹仿《圣经》文体的“祈祷体”(如冰心《圣诗》、《春水》、《繁星》;周作人《对于小孩的祈祷》;梁宗岱《晚祷》;陆志人《向晚》;王以人《读〈祈祷〉后的祈祷》,闻一多《祈祷》;穆旦《祈神二章》;王独清《圣母像前》;石评梅《我愿你》)“赞美体”、“书信体”(冰心小说《悟》、《疯人日记》、散文《寄小读者》;石评梅《祷告——婉婉的日记》、《再读兰生弟的日记》;王统照《15年后》、王以人《孤雁》)、“雅歌体”(朱白清:《雅歌》)等文体,在中国文学中大量涌现。
中国文学借鉴圣经语言的另一种方式是袭用福音书的叙事结构。如鲁迅著名的小说《药》:革命者夏瑜因其族叔夏三爷的出卖(以二十五两赏银)而被杀,其母清明节上坟,坟上的乌鸦显灵般“箭也似地飞去了”,坟上“一圈红白的花”在夏母眼中也像是神的显灵。显然,这和福音书里耶稣被门徒犹大(同夏三爷一样,他们都是被卖者身边亲近的人)以30两银子出卖被杀、死后妇女去探坟、耶稣复活的故事如出一辙。其散文诗《复仇(二)》更直接取自耶稣之死。茅盾则以耶稣被钉直接写了《耶稣之死》。[1]诗人徐志摩、艾青也写了同样题材的作品(前者:《卡尔佛里》;后者:《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和《马槽为一个拿撒勒人的诞生而作》)。应强调,对福音书叙事结构的这种模仿是《圣经》语言渗入了中国文学的更深层处的标志。因为文学语言实分为文本(text)、文体(style)、文类(genre)三个层面,文类居最深层,是其它两层的根本基础。[2]依海德格尔(Heidegger),“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怎么说便怎么在,对《圣经》语言的借鉴为基督教切入中国文学开辟了路经。
然而,中国文学对圣经语言的借鉴却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或曰“去神圣化”(dymystify)的,即那些语汇在《圣经》中本来所具之神圣内容被全然还原(或“篡改”)为纯世俗的东西。如在鲁迅《药》里,上帝之子被换成了人之子;救主耶稣基督被换成了寻常的“革命者”;耶稣为将世人从悖神之罪中救赎出来的献祭变成了革命者将人从世俗王朝的专制中解放出来的斗争;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奇迹被变成了老妇人昏花眼中似是而非的“显灵”。茅盾的《耶稣之死》什么都写了,但唯独不写他的神迹奇事和复活。鲁迅《复仇(二)》里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向父神求赦免戏弄他的众人(《加拉太书》第23章34节),而是对“看客”们始而“玩味”,继而“悲怜”,最后则愤然在心里对之“复仇”,并得意于自己的“胜利”。这与福音书里耶稣在十字架上对自己作为神之子的清醒意识,以及他在自己作为“完全的人”与“完全的神”那双重身份之间的挣扎——他死之前的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可福音》第15章34-37节)——显然大相径庭的。
中国作家《圣经》语词借鉴中这种“去神圣”是十分普遍的。如在根本不信上帝,说“宇宙是个大骗局”,“我的心应该信仰什么呢?宇宙没有一件永久不变的东西。我只好求助于空寂”[3]的石评梅那里,“上帝”一词的使用频率却很高。其《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云:“欢乐的泉枯了/含笑的花枯了/生命中的花,已被摧残了/是上帝的玄虚?是人类的错误?”[3](P.328)“上帝”在这儿只是种修辞手法,用以表达其痛苦、困惑的情绪,并未被看成真的存在着的至高者。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现在。例如,当今年轻诗人肖铁的《逆光中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一诗。而文学家们所以能这样,原因端在于他们眼中《圣经》只有文学价值,基督教信仰的东西是人为的,并不真实。如周作人说《雅歌》“全是文学上的,因为它本是恋爱歌集,那些宗教的解释,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了。”[4]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以理性目光批判地检省传统,提倡独立、自由、平等,张扬个性、个人权利与价值,乃当时之文学潮流。18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本由对基督教的批判而来,如今基督教既已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话题,其遭受人类中心主义式解读自然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首先不是被看成一种宗教,而是被看作一种文化;《圣经》也首先不是被看作上帝之默示、不可随意更改的圣书,而是被看作可任意剪裁的人的著作。
先看鲁迅笔下的撒旦。在《圣经》中,撒旦是与上帝为敌、引诱人犯罪的元凶,是罪恶的渊薮。但鲁迅却极力赞美撒旦,称其“惠及人世者,撒旦其首矣”,“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撒旦开启了人的智慧,否则伊甸园中的人类将仍如笼中的鸟儿般无知无识。另一方面,撒旦又敢于反抗上帝之强权,是位“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5]的英雄。
再看“忏悔”的问题。忏悔是基督教一核心性信理,鲁迅深受影响,对自己、尤其对中国文化有自觉的反省。但基督教的忏悔是对上帝的,是人向神的忏悔,德或罪的判准由上帝所定;鲁迅的忏悔则是对人的,是对中国之“文化原罪”的忏悔,德罪的判准由人给出(理性、个性、自由等),如其小说《狂人日记》即省察中国传统道德之“吃人”性质。对于鲁迅从不存在向上帝忏悔的问题。关于“宽恕”亦然。他明说不宽恕敌人,不学耶稣,他要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复仇(二)》中十字架上的耶稣便如此。在鲁迅看来,只有属人的才是可认同的。其兄弟周作人亦然:“《圣经》没有什么了不得,这原是当然的,除了几篇传道书与雅歌是文学作品外,别的都是关于以色列人的宗教的,文明人看了难得有什么好的印象。”[6]
道德化是中国文学对基督教去神圣化的另一种方式。所谓道德化即否定基督教的道德要求的超验根源,将之从与上帝创世、道成肉身、死与复活、因信称义等教理教义割裂开来,使之成为全然世俗的德性。
这里较有代表性的可先说到许地山。他加入过闽南伦敦会,1917年入燕京大学,先后获文学和神学学士学位,1922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宗教史,曾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参加过规模盛大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并作演讲。然而,他却认为“基督教由希腊借来的‘原质观念’的神学思想是走不通的。他以为耶稣本身的上帝名示之证据,非因其原质,乃因其德性,由其降生后的现实生活,而推动生以前生以后的本性和状态,由已经实现的人格,而证明未实现的,目不可见的神格。故许先生眼光中的历史基督,不必由‘童生’、‘奇事’、‘复活’、‘预言应验’等说而发生信仰,乃在其高超的品格和一切道德的能力所表现的神格,更使人兴起无限的景仰崇拜,信服皈依。”[7]也就是说,在许地山,耶稣本非神,惟因其人格伟大高尚才是神;信他不因其有复活,乃因其人格,与《圣经》所说基督信仰由耶稣基督而来的经文迥异。
例如许地山的小说《春桃》、《东野先生》。《春桃》主人公春桃善良,有爱心而又独立自主,敢担当,以捡破烂带领两个男人维持生计,并与他们同居。她没受洗,但有如此德性,小说说每天捡破烂回家后的梳洗便是“行她每日的洗礼”了。《东野先生》中的东野梦鹿不是基督徒,不懂基督教教义,但对周遭的人却有爱心,牺牲奉献。许地山的《落花生》更为著名,他以“瑟缩地生存”于土里,“在世界里”但“世界却不认识他”、“怀疑他”的“落花生”作喻,暗示有好的品德即为好的基督徒了。将基督教道德化的作家及学者甚多,甚至像反对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也盛赞“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感情”,称“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8]应指出,对于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中国人,将基督教道德化的倾向根深蒂固、强韧有力,这在今天大陆“三自”教会“神学建设”中十分明显。在这种观点看来,信不信耶稣基督无关紧要,紧要的是道德行为。如清末民初大儒辜鸿铭云:“宗教的生命所在是君子之道。反之,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宗教所规定的各种道德法则都只是宗教的外在形式。”[9]但不言而喻,没有了上帝信仰,基督教也就不是基督教了。
倘说以上两种进路对基督教毕竟还有所肯定的话,那么,由民族主义而来的回应就只有否定了。
这里先谈谈萧乾。萧乾认为“洋牧师们归根结底是跟在洋枪洋炮后头进来的”[10],基督教不过是“用无形的刀子从东方人的灵魂里把民族情感挖个干净。”[11]其小说《皈依》即这一观点的集中表现:妹妹妞妞加入了救世军,从此很少回家孝敬母亲;兄长“景龙” (“景”仰“龙”的意思,而“龙”者,中华民族的象征也)认为救世军“是帝国主义。他们一手用枪,一手使用迷魂药”,把中国人的灵魂勾去了,洋牧师“那两只毛茸茸的手,像是掐着民族喉咙的一切暴力”,最终将妹妹从教堂拉回了家。小说《昙》则写同母亲一起在洋牧师家做工的启昌最终将“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罢课游行的旗子扛回了家,民族尊严取得了胜利。
在反对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进路中还有一重要现象:民族主义同政治上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流。如戏剧家田汉在《午饭之前》一出戏里,要工人投身反对资本家的“年关斗争”,因“帝国主义把我们的血吸的快干了,那班走狗还劝我们爱敌人”。剧中另一位人物,原来信耶稣的大姐在“血的现实面前”也终于觉悟,发出了“上帝!不,你这恶魔,滚到地狱里去吧!我要复仇!”的喊声。诗人臧克家在长诗(150余行)《罪恶的黑手》中以修建教堂为题材,将基督教描绘成阶级压迫的帮凶,号召工人起来反抗,将教堂变成自己的“食堂或卧室”。这种情形一直存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久。如当代著名作家、曾做过文化部长的王蒙自述其小说《青春万岁》时说:“解放以后,我们学习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带着强烈的无神论倾向和一种对宗教的相当严峻的批判,我的小说《青春万岁》里就把我参加打击一贯道,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来残害我们的同胞,把天主教作为侵略的工具的经验写进去了。这在历史上也有过。鸦片和天主教几乎同时推到中国来。……《青春万岁》里可以说有相当浓厚的反宗教情绪。”[12]
二、上帝中心: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漫长努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回应基督教的另一条进路是上帝中心主义的,即认同三位一体的上帝为独一真神,认同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为“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第14章6节),以此为基础重建中国文学的意义殿堂,赋予中国文学以新的、并且富于生命活力的精神方向。
这里首先应提到的是基督徒作家冰心。她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我加基督=?》说耶稣基督乃“世界的光”,人当“信从这光”,“成为光明之子”。因“光是普照大千世界的,只在乎谁跟从他,谁愿做光明之子”,“愿笼盖在真光之下?谁愿渗在基督的爱里?谁愿借着光明的反映,发扬他特具的天才,贡献人类以伟大的效果?请铭刻这个方程在你脑中,时时要推求这方程的答案,就是:我基督=?”[13]冰心给出的答案就是爱:“真理就是一个字:‘爱’。耶稣基督是宇宙间爱的结晶,所以他自己便是爱,便是真理。”[14]这便是她著名的“爱的哲学”,即领受基督之爱,并活出基督之爱,她完全是“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15]
也许可以说,冰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督教方向的奠基人。笔者以为,冰心的文学堪称基督教文学,其本人也堪称基督教作家。理由:她是以文学方式来表现基督教信仰,传扬福音信息的,虽然并不专意传扬某一教会或教派的教理教义,但以文学传讲福音显然乃其创作的宗旨。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小说家徐雉许多作品也堪称基督教文学。[16]端木蕻良的《复活》[17]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在众多以耶稣之死为题材的小说中,端氏的《复活》独树一帜地力求表现出基督信仰的真实性,虽然他对《圣经》有些偏离。以冰心为代表的这一批活跃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作家堪称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先行者——当然,这样定义“基督教文学”妥否自可讨论,其内涵当是十分丰富的。
然而,冰心的创作却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她不乏纯正的爱的信仰的告白,但对信仰生活的复杂性,对在具体的生存处境中活出信仰真义的困难和挣扎,即在既保全信仰的纯正性,又同时成全人性世界的丰富性上缺乏较深入的思索与探究。因为人虽然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创世记》第1章26-27节),但毕竟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的神”,而只是个“完全的人”。这样,人要想既活出“完全的神”耶稣基督的样式,又同时保全自身“完全的人”的丰富性,无疑是困难的,要经历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的挣扎跋涉。况且,上帝的救赎、创造是历史性的,这自然会带来人的得救的历史性、处境性,会使人在对爱的践行上其实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也就是说,人可能自以为是“爱”了,但是否真的合乎爱的要求,最终的判准却不在人而在上帝。否则,“最后审判”便用不着了。因此,只单向度或单纯地强调爱,强调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中间其实隐藏着刈除人性之丰富性的危险,它可能会导致人性的贫乏与干瘪。使人不再是“完全的人”,而这自然是不合《圣经》的教导的。依《圣经》,人是要完完全全被带到上帝面前来的。而既完完全全,单向度的爱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即使是爱,此一爱也无疑是以人的人性与神性的错综复杂的紧张、冲突为基础的,是此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相反相成或“对立统一”,其中会充满灵魂的困惑、冒险和痛苦。那种爱不会只是喜乐宁静、温情脉脉的。而这一切对于冰心却较陌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子堪称中国基督教文学继冰心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当然,海子(1964-1989)不是基督徒,思想亦颇驳杂,他的自杀(1989年3月26日山海关卧轨)更与基督教教义相悖。虽然他对基督教比对其它宗教有更多的认同,但显然不能与冰心以及现在仍然十分活跃的基督徒作家北村相比。另一方面,就自觉表现基督教情怀而言,海子更远不及冰心。使海子配得中国基督教文学第二个里程碑之誉的,是他以自己独有的在世性情(刘小枫语)和情感遭际,以自己坚信无疑的心灵认知以及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生命意志以基督自命,以一个“完全的人”而活成为一个“完全的神”——那是他的志向或自命,他当然不是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的神”,也许可谓希腊式的那种“半神”——像上帝有三个位格而又三位一体那样,诗歌、生命、信仰追求——或曰诗性、人性、神性是海子的三个位格、三位一体,这三位一体整体上体现为其以基督自命:
让我再回到昨天/诗神降临的夜晚/雨雪下在大海上/从天而降,1982/我年刚十八,胸怀憧憬/背着一个受伤的陌生人/去寻找天堂,去寻找生命/却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夜晚/1988年11月21日诗神降临//这个陌生的人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父兄,停在我们的血肉中/这个陌生人是个老人/奄奄一息,双目失明/几乎没有任何体温/他身上空无一人/我只能用血喂养/他这把神奇的老骨头/世界的鲜血变成马和琴。[18]
当然,自比基督或以自己取代基督(其写于1984年的《阿尔的太阳》云:“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要画就画橄榄收获/画强暴的一团火/代替天上的老爷子。”[18](P.5))从基督教传统看,这无疑是异教的,是骄傲自大之大罪。但当他真诚地认为“我们的世界”、“父兄”已“奄奄一息,双目失明”,“老人”般“几乎没有任何体温”而需要他“用血喂养”,并且他真的以血“喂养”“他”的时候,当他感到今天的基督教也苍白衰老而需要以凡·高般的“强暴的一团火”去“代替”的时候,读者从他的诗中感受到的不是他同基督教传统信仰的错位,而是他那种基督式的以身殉道的震动——当然,你也可以说其是以身殉诗,是“诗歌烈士”,[19]但这与说他以身殉道并无差别,因其诗即其道、即其身的。在海子之前,在“新时期文学”(1976-1986)中,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20]竹林《地狱与天堂》[21]也都写到人因信基督遭受磨难,但影响远不及海子,关键便在于海子不是单向度地传扬福音信息,而是呈示出了个体生命与基督信仰相互纠结、牵缠的复杂性。应当说,海子预演了一个基督徒个体信仰的诗歌时代。
相比之下,目前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基督徒作家北村则显得有些逊色。他1992年“归入主耶稣基督”,[22]自觉以小说传扬福音信仰。北村不同于此前认同或同情基督教的小说家的地方在于,他是针对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生存问题来给出相应的福音信息的,构思方式上颇似于蒂里希(Paul Tillich)的“关联神学”。比如:《施洗的河》说人被罪恶充满,沉沦极深,惟基督可使人洁净得救——这显然是对当代中国严重的道德堕落而言的;《玛卓的爱情》、《伤逝》、《水土不服》等说美、艺术不能使人享有荷尔德林(Friedrich H·Iderlin)所谓“诗意地栖居”,惟上帝方能给人抚慰和安宁——这显然针对当代中国的审美主义泛滥而说的;《张生的婚姻》说哲学不能救人,能救者惟有《圣经》——这显然是针对当代中国人的知识崇拜的;《消逝的人类》说金钱、地位、名誉、书法及游乐皆不能使人生有意义——这显然是针对当代中国普遍的物质享乐主义的。北村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拥有影响,原因便在于他对中国人目前所临到的精神、心理问题给出了不同寻常的即基督教的答案,在于基督教的答案能给人以不同寻常的启迪。在这个意义上,北村匡正了海子,将对基督教信仰的文字表达拉回到了基督教传统所认可的领域。
但北村的问题同冰心是一样的:他仍未能触及如何在人性的丰富性中展现基督教的神圣认同问题。我们看到,他主要是站在信仰立场,从“外面”评判现实,而未能从“内部”,即从人灵魂深处发掘人同上帝之间、人的此世遭际同上帝的天国召唤之间的张力中揭示福音信息的丰富内容,或易言之,未能在人作为“完全的人”与作为“完全的神”的耶稣基督之要求的紧张中把握和发掘人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基督教文学还远未很成熟,虽然她已走过了百年漫长历程,离产生T·S·艾略特(Eliot)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那样的诗人、小说家怕也还有不短的距离。
然而,对此正不可悲观。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毕竟才只有百年。并且,尤为重要的是,发生在冰心等身上的中国文学对基督教是“主动承纳”(刘小枫语)的,是“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作家对中西古今各种思潮、学说、精神、信仰进行自觉比较判别的结果,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在中国人文精神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有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中苦苦探索的结果。况且,从精神发展演化的内在规律[23]来看,目前以儒释道、启蒙、现代派及后现代派多元共存的中国文学,在逻辑上实已“终结”,已走至生命的尽头,目前的中国文学实已是“终结的中国文学”,[24]即终过程之中或终结时期的中国文学,怕惟有基督教方能为之注入一些活力吧。我们深信基督教乃中国文学的某种方向,中国基督教文学将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别开一片洞天。
收稿日期:2006-10-22
注释:
①本文所谓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时间性的分期概念,“现代”和“当代”的区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
标签:文学论文; 基督教论文; 圣经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当代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耶稣论文; 青春万岁论文; 天主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