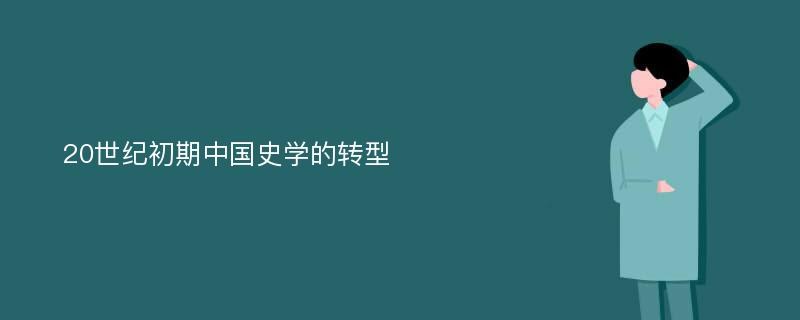
刘俐娜[1]2003年在《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文中认为本文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考察了20世纪最初30年间,中国史学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经历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上篇1~3章概述了中国近代史学转型艰难曲折的历程。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史学,而以封建专制政治文化为中心形成的传统的史学研究范式不能满足这一需要,遭遇到不更新就难以发展的困境。时代在呼唤新史学的同时,也为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戊戌救亡启蒙思潮催动了“史学革命”潮流。新史学观念因适应政治变革需要得到发展,新式历史教科书改变了史书的面貌。辛亥革命后复古思潮虽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新史学的发展势头,但也提供了反思传统与现代的机会。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经历了困境中觅路、改革中求新的史学借助更为开放的中西交流环境、政治和学术的相对自由,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史学范式阶段。新文化运动造就的新一代学者借鉴西方观念与挖掘传统资源,积极探索现代史学的理论方法,并尝试将其付诸实践,基本形成一套新的史学研究范式。 传统向现代研究范式的转换关系到史学研究中历史观念、研究对象、内容,研究方法和史着体例等诸方面的更新和改革。下篇4~7章从史学理论体系的内在发展理路上对此作了详细考察。首先,是借鉴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学说,通过厘清历史概念、引进新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建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科;其次,通过对传统史学研究目的和功能、对象和内容以及研究任务诸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建立起“重今”的、为普通民众服务的、关注与民众生活相关内容的,在记述的基础上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再次,通过引进西方新的研究方法和改造完善传统的史学方法,树立运用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治史的新观念,建立起新的史学方法论体系;最后,运用新的史学观念更新旧的史料观念,以表述新的史学思想和内容为目的变革旧的史学表述方式和史书体例,实践新的史书体例,丰富史学表述体裁。
郭艳飞[2]2013年在《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研究方法概述》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史学处于新的历史转型时期,为了适应新环境必须改变传统的史学模式。此时的史学不仅注重理论创新,更加注重理论实践即史学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由此产生了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史学方法。其中,以梁启超"跨学科"治史方法和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实验方法影响最为深远。
程鹏宇[3]2013年在《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史观》文中提出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近代以来影响力最大的史学流派,对中国历史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在新中国建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五四时期、社会史论战时期和通史研究时期叁个阶段。在这叁个阶段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史观不断发展丰富,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遗产。首先,19世纪末,孙中山等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李大钊、胡汉民开始尝试用唯物史观的新观点来研究中国的历史,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解释中国思想史的问题。其次,1927年以后,中国爆发了社会史论战。郭沫若、吕振羽、陶希圣分别提出了西周奴隶社会说、一元的中国原始社会史观、战国秦汉奴隶社会说和魏晋封建社会说等观点。最后,193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通史研究时期。周谷城在“历史完形论”下扩大了其中国通史的视野,提出了纵横斗争说,无奴论到有奴论的观点,两段式封建说。吕振羽对秋泽修二的中国史观进行批判后提出了发展的中国史观、平等的中国民族史观、殷商奴隶社会论、两段式封建社会史观、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作用、辩证的中国传统文化观。范文澜重视世界历史的共同性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论、农民起义及其历史的作用、辩证的儒学观、国家统一与历史的发展的关系等观点。翦伯赞主张整体的历史观,提出符合一般历史的中国古史观、殷商奴隶社会论、叁段式封建社会论、汉民族的形成观以及重视各个民族的历史作用的民族史观,并且注重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史观。侯外庐提出历史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辩证统一的历史观,并且在其基础上建设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思想史的研究以社会史的研究为基础的史学理论,在中国社会史上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社会观和封建化的过程与法典化的标志的封建社会观,在思想史上提出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相统一的中国思想史观。对于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史观,我们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反思其价值,为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
谷学峰[4]2011年在《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国史学领域曾发生过一场规模宏大的所谓“史学革命”运动,这场“史学革命”给中国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还直接左右了其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史学的发展走向。本文通过对这场“史学革命”的考察分析,旨在准确把握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征,探求史学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助力。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建立,中国史学也面临着转型,即由现代多元史学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也就是说新中国要建立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大背景下,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1958年“大跃进”时期,史学领域出现了“史学革命”运动。“史学革命”,是对以批判资产阶级史学、建立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史体系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的总称,其内容涵盖史学界的“厚今薄古”大讨论,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及史学家的批判,“打破王朝体系”,“构建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人民史体系”,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写史、编教材活动,史学的“大跃进”等等。这场“史学革命”运动以“厚今薄古”大讨论为其开端,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达到高潮,由于“史学革命”本身所主张观点的不合理性,随着“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结束而渐趋衰弱。“史学革命”中的一些荒唐做法,引起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的反对与批评,不过,“史学革命”的影响却难以彻底清除。随着1966年前后阶级斗争形势的高涨,“史学革命”的提法被套用,以吴晗、翦伯赞为首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几乎都遭到了政治批判,甚至有些历史学家为此付出了生命。从本质上来说,“史学革命”不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革命。1958年的“史学革命”并没有展现学术正常发展进步的一面。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而是对其进行的公式化、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理解运用,并且还否定了此前史学工作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当时提出的“人民史体系”的史学编纂体系,是阶级斗争观点在史学研究中极端运用的体现,不能够反映整个中国历史的实际面貌。“史学革命”是社会变动与史学工作者思想认识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1958年“史学革命”实质上是当时各种政治运动在史学领域的综合反映。当时的国家开展的每一项政治运动可以说都直接冲击、影响着史学领域的工作。史学工作者思想认识的变化也推动着“史学革命”的开展,他们按各自的理解把阶级斗争观点运用到当时的史学研究之中,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可见,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动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反映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与当时史学家的治学心态,也反映了史学变动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诠释密切相关。“史学革命”的要害在于把阶级斗争观点全面引入到史学领域,把政治标准作为区分资产阶级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标准。“史学革命”中,在“左”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下,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逐渐上升到历史观的层面,并且脱离了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甚至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显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理解。“史学革命”给中国史学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史学的政治化倾向,从而使史学丧失了学术自身,走向了“文革”中的“影射史学”之绝境。“史学革命”提出了史学的批判、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但没有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史学革命”对史学遗产强调批判,缺乏继承,严重削弱或中断了一些优良的治史传统。民国史学有两大传统:一是注重史料;一是注重借鉴西方史学。建国后,这两大治史传统皆被严重削弱或中断,至少不再被视为治史的重要方面。“史学革命”展开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错误批判,削弱了中国史学的研究力量,使一批学有专长且正值学术盛年的学者无法专注甚至一度中断了史学研究。这些都警示我们要做好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史学革命”提出了史学革新的问题,这一点容易被人所忽视。当时,“史学革命”中有人提出“打破王朝体系、建立人民史体系”的观点,这体现了当时史学面对现实政治需要作出的一种主动适应。虽然,这一观点因其不合理性遭到了批判。但是,它却带给我们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随时代发展而不断革新的问题意识。“史学革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来讲,虽然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如,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就在此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可以说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史学革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那就是要正确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正确处理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要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通过对“史学革命”的考察,我们看到了建国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一面,但是这并不是抹杀和无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更不能把中国史学出现的问题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取消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十一届叁中全会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自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新迸发了生机与活力,但也不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有些问题还需我们重新审视,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在结合中国史学传统与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各种文明及不同学科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丰富自身,发展自身,强化在中国学术领域中的主流地位,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刘俐娜[5]2004年在《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转型与史学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初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 ,也是中国史学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时期。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激发了新史学 ,并推动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变革式的发展。
蒋海升[6]2006年在《“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渗透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史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为中介进行的。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享有盛名的“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析而产生的分歧,体现了“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越来越频繁地接受“西方话语”冲击的中国史学研究不无裨益。 所谓“五朵金花”,是指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史学界围绕着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大规模讨论和争鸣。回顾“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兴衰过程,考察其与西方话语的广泛联系,有助于推进对20世纪学术史、特别是当代50年学术史的研究,对当前的学术研究亦能提供一些借鉴。“五朵金花”在这里是被看作学术史研究的一个个案,而非在“历史理论”意义上要求回答、解决的几个命题:如果说当年“五朵金花”所讨论的问题是“思辨”性质的问题的话,那么这里则是在“史”的意义上的问题探讨。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参与五个命题的讨论,而是在知识论意义上去探寻这五个问题提出的过程,去分析它们身上体现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 “五朵金花”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依托分析中国历史而产生的一组命题。而马克思主义最初只是众多进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潮的普通一种。在西潮汹涌的背景下,绵延2000余年的中国正史体系被打破了,并被一步步拖入西方话语系统,新史学思潮蔚然兴起。外来观念、术语改变了中国人对历史的描述,最终控制了对中国历史的表达。20世纪前半期“西方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交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话语系统的形成,并最终取得了史学界的核心地位。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批判运动,为“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土壤。“五朵金花”在这种语境下应时而生、应势而起,并受既定理论预设的限制。特定社会环境下的“革命”诉求成为“五朵金花”
魏衍华[7]2007年在《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成就与特征》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是现当代学术界中较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本文试通过对一百年来所编纂中国通史的编纂概况、社会背景及学术条件、理念特征和编纂学特点等方面所取得成就的分析与研究,考察其在20世纪由传统类型的中国通史向近代转型的过程,并揭示中国通史编纂的规律性特征。其目的在于展现其史学的原貌,并为未来编纂新的中国通史提供有益借鉴。全文由前言、正文四章和结束语叁部分组成。前言部分主要说明本课题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本文研究的范围以及当前学术界对该课题研究的现状。正文部分,第一章主要从清末民初、叁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文革十年和20世纪最后20年等前后相继的五个阶段尽可能地展现中国通史编纂所取得的成就;第二章主要是将20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作为一个整体从制度的变迁和观念的转变、民族的危机和历史的反思、中国文化碰撞的文化以及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等几个方面,考察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因素和学术自身的内在理路。第叁章主要从历史观念、价值观念以及中国通史职能的变化等方面探索和研究,进而对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理念特征进行有重点的剖析,以展现不同于传统通史的一些特点;第四章试图从中国通史编纂的体裁综合化、历史语言的变化、史料的态度以及历史分期等几个与中国通史编纂学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来透视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学上的主要特点。结束语部分概括性地说明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所取得的成就,并对本文研究所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孟德楷[8]2014年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研究说明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叁,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捍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董姝懿[9]2016年在《严复与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文中研究指明严复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启蒙家、翻译家。他一生心系祖国,以救国为己任,翻译介绍了以《天演论》为代表的许多西方着名思想着作。他为中国启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启蒙思想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还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尤其在史学方面,他促进了20世纪初中国史学历史观的根本性转变、推动了20世纪初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与此同时,也促进了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家的产生和转型。严复不仅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描绘了蓝图,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朱煜洁[10]2015年在《外国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时期,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西学也随之进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外国史学作为西学东渐中重要的一部分,其在中国亦产生了的深远影响。在传播过程中,外国史学逐渐与中国当时最大的实际——救亡图存产生联系,成为爱国知识分子们论证观点,针砭时弊,宣传思想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外国史学还为中国传统史学提供了新的参照,促进了中国的史学近代化。而作为外国史学宣传的重要载体的近代期刊,如同一面镜鉴,如实地反映出外国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程。通过对期刊上外国史学内容的研究,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外国史学传播内容的侧重点,进而可以总结出不同时期的外国史学传播特征。本文主要由五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从社会、思想、文化叁方面论述晚清外国史学传入的背景,并对晚清期刊的产生及发展情况进行叙述分析;第二章则从时间和传播群体两方面出发,系统阐述了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传播群体以及由此带来的传播内容上的变化,并对各个时期的传播特点和传播影响进行了简要的总结;第叁章对晚清期刊上外国史学理论内容进行整理,并分析其对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产生的影响;第四章则介绍了晚清期刊上关于政治人物史的传播情况,通过深入分析彼得大帝传播的案例以点带面地来分析期刊上外国政治人物的主要传播内容和特点,同时总结出维新派期刊所想表达的政治诉求及维新派期刊的兴衰;第五章则对晚清期刊上外国亡国史内容进行整理概述,并以埃及亡国史宣传内容为案例,以分析当时外国亡国史期刊宣传情况以及对中国的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转型[D]. 刘俐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研究方法概述[J]. 郭艳飞.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3
[3]. 建国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史观[D]. 程鹏宇. 西北大学. 2013
[4]. 1958年“史学革命”研究[D]. 谷学峰. 山东大学. 2011
[5].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转型与史学的发展[J]. 刘俐娜. 教学与研究. 2004
[6]. “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D]. 蒋海升. 山东大学. 2006
[7]. 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成就与特征[D]. 魏衍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07
[8].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
[9]. 严复与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D]. 董姝懿.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10]. 外国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D]. 朱煜洁. 苏州大学. 2015
标签:史学理论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通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