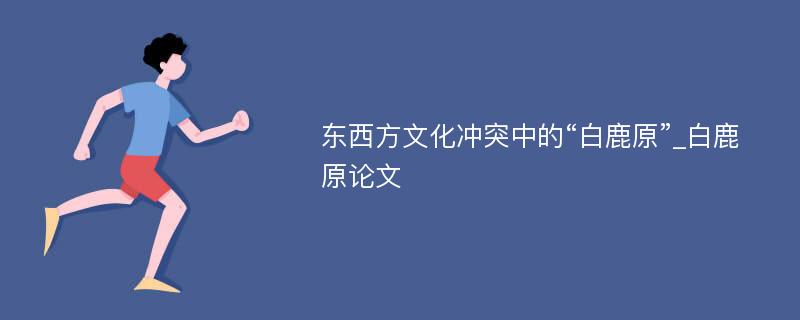
东、西文化冲突中的《白鹿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文论文,冲突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白鹿原》以小说形式重新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
小说“时间面”——自民国初年到1949——的开端并不是这个历史的源头。辛亥“反正”消息传到原上时,白嘉轩正在为女儿灵灵举办相当隆重的“满月”。她是他三个儿子后面的第四个孩子,仙草坐的第八次月子。而仙草又是白嘉轩的第七房女人。白嘉轩用做“教材”的白家“故经”又将白家的历史上推了六代。鹿子霖所遵从的专意供子女读书的家训将鹿家的历史也上推了四代。白鹿两姓合祭的祠堂把白鹿村的历史上溯到侯家(或胡家)村,而白鹿神话又将白鹿原的历史上溯到“很古很古的时候”。
这是一幅“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活图画。
它以家族为本位。
小说着意描写的两个家族并非固定不变地属于某一阶级。
白嘉轩上推大约六代的祖宗里,继任的家主在三年孝期变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败家子,把土地牲畜房屋踢荡净尽,沦为乞丐。而经历这个拔锅倒灶痛苦过程的老二,半是打短工、半是乞讨地度过童年,长大后靠打土坯维生。他每天把打土坯挣下的铜子麻钱塞到有进口没出口的木匣里,三年后用所积铜元麻钱买回一亩一分二厘水地。到他死时,家产发展到哥哥败家前的景况。鹿子霖的老太爷过烂了光景讨吃要喝流逛到西安,在一家饭铺先是挑水拉风箱,后来竟学成了一手烹饪绝技,被誉为“天下第一勺”,发了财,买下土地。
白家的长工鹿三家也有二亩旱地。
这是一个阶级界限极不分明的社会。
《白鹿原》以小说形式为梁漱溟理论上的中国历史社会结构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画卷。梁漱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状况是“独立生产者之大量存在”,“此即自耕农、自有生产工具之手艺工人、家庭工业等等”,[1]“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2]由此,梁漱溟论述道:“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3]因而“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4]梁漱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是“职业分途”的社会。[5]
《白鹿原》同时也在解构。它描绘农耕文明的社会生活图景时,不做阶级分析,政治思维荡然无存。这里有的只是“家道殷富”,“首富”,“财东人”,“大财东”,“乡性恶劣的财东绅士”,“仁义的主人”,“正经庄稼人”……它不以阶级地位而依道德的高下来写人。因此富人和穷人中都有仁义与劣顽。白嘉轩甚而相信“各家坟里家里也就是那几个蔫鬼鬼子上来下去轮回转着哩。”[6]
小说还写到白嘉轩六代先祖的老二打坯挣钱攒钱时,遇上雨天在仅可容身的灶房里读书,鹿子霖的“勺勺客”老太爷谢世时竟然留下鼓励后人读书及第的遗嘱。白嘉轩读过5年书后,回家亲躬农业劳动。他恪守“耕读传家”治家传统,兴办学堂,及时送子女上学,接受儒学教育,并且严格规定子女获得一定程度的文化之后辍学务农。他资助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相信“穷汉生状元,富家多纨袴”。小说描写普遍存在的“耕读传家”、“半耕半读”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7]加上科举考试等选官制度,能够从民间吸收人才参与政治,“统治被统治之间得以流通”,[8]因此,“阶级问题乃亦比较轻松,而竟自趋于融解。由此而风度泱泱数千年一直是阶级意识不强”。[9]
《白鹿原》中的“农耕文明”是儒学治下的文明。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文化是儒学的原始起点。这得到儒家经典的有力证明:“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白嘉轩作为一家之长,以“孝悌”为修身、齐家之本;作为一族之长,遵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规范。
白鹿传说作为家族神话,“人们一代一代津津有味地重复咀嚼”,“一旦在人刚能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它强化家族成员对家族共同体的认同,增强家族的凝聚力,成为家族的精神支柱。而小说所描写的一个接一个的礼俗,诸如耕织、家政、祭祖、婚礼、拜祖宗、拜亲人、满月、认干亲、伐神取水、治丧、迁坟等等,则是外化了的家族神圣传统与秩序。罗素认为,“任何地方的原始宗教都是部族的,而非个人的。……祭礼往往能鼓动伟大的集体的热情,个人在其中消失了自己的孤立感而觉得自己与全部族合为一体。”[11]
梁漱溟认为:“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12]“以家庭恩谊推准于其它各方面,如经济生活上之东伙关系、教学生活上之师生关系、政治生活上之官民关系,一律家庭化之——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伦理。”[13]他称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14]白家与长工鹿三家三辈人交好,亲如一家,是“东伙关系”的典范,“伦理本位社会”的美好图画,而白嘉轩在朱先生的支持下,倡导、建立乡约村规,镌刻在白鹿村祠堂大墙上,则是以伦理组织社会的写照。“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这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15]的旧日中国的缩影。
朱先生局处白鹿书院,心系世事民情。体现了中国士阶层自古以来的“经世致用”意识,“治国平天下”人格。
朱先生遵循孔子私人讲学“有教无类”原则,“到我书院来寻我的人,我一律视为君子,概不分党政派系”,把白鹿书院办成“一方清净之地”,[16]表现了中田士阶层以及儒学的社会独立性和超然地位。如梁漱溟所说,士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17]“士人无恒产,不代表经济势力”,[18]其使命是“力促阶级之融解”[19]。这有儒家经典的有力依据:“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不党”(《论语·述而》);“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朱先生身体力行不与民争业。“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是朱先生的名言之一。《蓝袍先生》就已将此写为徐家的祖宗遗训。这种生活哲学同乡土中国大量存在的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以及不绝于中国历史的“均田”、“限田”运动相互契合。诵读圣贤书籍,求解“修平”之道,已成为朱先生的“生命的需要”。他亲自动手推倒白鹿书院大殿内不知什么朝代什么人塑下的四座神像,声言“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20]“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都不信神”,[21]维护儒学的理性精神和非宗教性质。
《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国历史、文化最为完整、最为坚实的重构。它在社会、文化构成上找到了中国历史社会稳稳运行三千年的原因。三千年的历史不再是“吃人”的,儒学不再是统治阶级“杀人”的“软刀子”。朱先生翻阅历代县志,虽然各种版本的县志出入颇多,但关于滋水县乡民的评价却是一贯的八个字:水深土厚,民风淳朴。[22]《白鹿原》和《战争与和平》一样,表现出对各自民族古老的太平盛世和先祖的愉快的缅怀。而列夫·托尔斯泰十分向往中国的“农耕文明”。托尔斯泰逝世(1910)以前,中国农业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比得过中国人那样善于耕种土地并靠土地养活自己。一俄亩土地能养活一个俄国人,两个德人,而这同一面积的土地却能养活十个中国人。”[23]他认为中国这个“最富有,最古老,最幸福,最爱好和平的民族在生活中遵循着某些原则,”[24]中国“比基督教世界所处的充满仇恨、刺激和永不停止的斗争的情形要好上千百倍。”[25]
因此,革命在白鹿原没有土壤。
作为国民革命的先声——武昌举事“反正”的消息是正值白灵满月传到白鹿原的。
随着“反正”而来的所谓“新文化”同“农耕文明”格格不入。白狼传说给白鹿神话的故乡带来的并非吉祥——“城里的反正只引起了慌恐,原上的白狼却造成最直接的威胁……那是一只纯白如雪的狼,两只眼睛闪出绿幽幽的光。”[26]
两种文化的冲突在《白鹿原》中无处不在:
农历三月,桃红柳绿,阳光明媚,突然从南方传来了一股寒流,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了。[27]
黑娃和他的农会骨干们整天忙着组织训练农协武装。梭镖矛子和大刀绾上了红绸,看起来挺威风的,三百多人的武装队伍,在白鹿镇游行了一回儿就散伙了,因为小麦黄了要收要碾了。等得小麦收打完毕进入三伏,庄稼院桃树上的毛桃发白了又变红了,革命的形势却愈见险恶。[28]
今年收成不错,老天爷许是看到黑娃们搅起的动乱而有意赐惠庄稼人连下了两场好雨,麦子豌豆在农协狂妄的喧嚣中蓬蓬冒起来孕穗结荚。[29]
他站起来摇摇手臂似乎还不要紧,就绕过一个个横竖摆列着的尸体朝东南方逃去,脚下是绵茸茸的被攘践倒地的麦子的青秆绿穗儿,辨不清大哥的士兵和自己战友们的尸体,反正都像夏收时割倒捆束的麦个子摆在田野里。他走着跑着直到看不见尸体直到站立着的麦子档阻脚步时才又放缓下来,从黑夜终于走到黎明。齐腰高的麦田小路上走来一位拉牛扛犁的老汉,在甜润润的晨风里唱着乱弹,兴致很好噪门也很好。黑娃跳到老汉当面老汉一句乱弹卡在肚里扔了肩上的犁杖软软地瘫倒了,紫红色的大犍牛扬起尾巴跑进麦田里去了。黑娃这才看到自己被血浆红了的衣裤。[30]
小说表现这种冲突时,无形中形成了两个系列的意象:小麦、桃花、犁杖、乱弹;寒流、梭镖、血浆、尸体。前者宁静,后者喧嚣;前者正常,后者反常;前者通向生命,后者通向死亡。
黑娃十弟兄到他们所在的十个村子发动革命,在白鹿镇小学校举办为期十天的“农习班”;白嘉轩去看望在城里念书的宝贝女儿灵灵,而灵灵在按上级紧急命令“挖万人坑,抬埋死人”,还当着“运尸组”组长……《白鹿原》所描写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实质是“本位”的冲突,亦即所谓的“新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背离,对于“根”的背离,因而表现为无根基,经常被斥为“死皮赖狗”、“烧包儿”。小说入微地描写了黑娃的造反、沦为土匪与他从白鹿镇小学退学、未接受儒学启蒙教育之间隐秘而实在的因果关系。如白嘉轩所说,“黑娃当了土匪,我开头料想不到,其实这是自自然然的事。”而白灵这位“新女性”左方眼睛里由朱先生相面相出的“黑洞”以及她所表现的狂热——甚至狂妄,是不是从她在白鹿村学堂戏弄徐先生时就已开始形成?
因而黑娃造反后是以“协会”取缔祠堂,以他的办公桌换掉祭桌,将自己置于白鹿家族列宗列祖的地位。他手中的铁锤首先砸碎的是“仁义白鹿村”石碑和“乡约”;白灵革命的对象是“中国”,她在朱先生面前断言“整个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大黑洞,咱们全都在这黑洞里头”。[31]
《白鹿原》中巨大的、根本的冲突是“阶级本位文化”同“伦理本位文化”的冲突。研究认为:“阶级意识形成意味着家族意识的削弱”,[32]“历来大乱之所由兴”乃为“其礼俗失效”。[33]
梁漱溟经过多年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阶级对立,正是集团间的产物,不发生于伦理社会。”[34]他认为,西洋社会是“阶级对立”社会,“一个人生在阶级社会里,其一生命运几乎就已决定了……他们若想开拓自己的前途,只有推翻这种秩序,只有大革命。”[35]因此,“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的生活。”[36]中国社会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有阶级融解而无阶级对立,“不能产生西洋式的政党或革命党”,[37]中国历史自秦汉以后“不见有革命”。[38]中国1911年开始的革命,梁漱溟将其看作“自外引发的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而不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爆发的阶级斗争”。[39]他还于1930年指出:“中国近三十年一切改革或革命大抵出于所谓‘先觉之士’主观上的要求,而很少是出于这社会里面事实上客观的要求。”他将此看作“贻误”。[40]他坚信:“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无能外之者”。[41]这同托尔斯泰主义相吻合。托尔斯泰锲而不舍地探索“俄国道路”,其目的就是以此抵御西欧制度,力图避免在俄国发生革命民主主义者所主张的欧洲革命式的流血革命。他还于1905年向中国自上世纪末开始的“维新变法”运动进言:“改革就意味着成长,发展,完善,是不能不表示同情的。但是改革只是模仿,把一些形式(在欧洲和美洲的有知之士看来,都还完全站不住脚),输进中国,那是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改革必须从一个民族的本质中生长出来,而且应该是一些新的、同其他民族完全不相像的形式。”[42]
《白鹿原》描写了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掀起了的风暴的外来性质。受此风暴影响裹挟的人言语间“不断冒出一些新名词”。[43]生力军“新青年”多是“洋学生”,[44]被白鹿原人认作“洋种”。[45]他们接受的是“西学”。[46]他们满嘴的革命理论——土生土长的黑娃听了将它说成是“趸来”的。[47]他们过上了集团斗争生活。白鹿村的几个“新青年”即便是同胞兄弟也处于敌对营垒。白孝文对白灵说:“现在亲老子也顾不上了,甭说一个村的乡党。两党争天下,你死我活地闹……”[48]
《白鹿原》表现了人在历史激流中的无奈处境,个体选择经常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所驱动。鹿兆海和白灵起初竟以掷铜元这样的近似乎游戏的轻松方式决定各自所属。尔后,随着情势变化,集团矛盾公开,导致分裂。二人的集团归属发生易位的同时,也就开始了相互攻讦。天真烂漫的激情让位于严肃严酷的集团斗争。斗争不表现为善与恶的斗争,不取决于个人品质的优劣——甚至他们身上不乏天生的丽质,只是因为他们从属于不同集团,效忠于所属集团的斗争方略而失去了独立性。他们的悲剧与《静静的顿河》主人公一样在于“历史的迷误”。[49]“鏊子”说象征性地揭示了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本质,集团斗争必然陷于内战的非程序化的历史更迭中,陷于兄弟相煎,陷于梁漱溟所说的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之循环”。[50]白鹿村人称其为“乱世”,[51]朱先生也称其为“乱世”。[52]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借用了梁启超的下述论点:“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时代”。[53]《白鹿原》描写了集团主义强烈导致民族意识削弱的现实,描写了“打胜了,又撤了”的可悲现实。鹿兆海曾被白鹿村民以抗日杀敌民族英雄隆重祭奠,然而现实对他开了一个可悲的玩笑,其实他是“撤了”以后死的——死在内战里。若干年后,鹿兆海高大的墓碑竟为屎尿所覆盖——历史对他,对集团斗争做了无情的评说。《白鹿原》继老舍的《猫城记》对“内哄”做了深沉而近于绝望的描写。事隔50多年,日本友田锡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当时,日本乘中国混乱之际,试图向大陆扩张。”[54]
白鹿原的最大悲剧在于白灵。
她是白鹿原有数甚少的体附白鹿精灵的人。“无论这个女子怎么不像个女子,徐先生却惊奇地发现她十分灵聪,几乎是过目不忘,一遍成诵,尤其是那毛笔字写得极好。”“既有欧的骨架,又有柳的柔韧……白嘉轩看着品着,不由地心里一悸,忽然想到了慢坡地里父亲坟头下发现的那只形似白鹿的东西。”特别是她那双眼睛,“习文可以治国安邦,习武则可能统帅千军万马”,“整个白鹿原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种眼睛的女子了”。她在低潮里义无反顾地踏上奔赴延安的前程,神奇般地躲过一路的搜捕,可却躲不过“内伐”。这位纯真的女革命家被以“革命”的名义活埋了。这是白鹿的迷失。
《白鹿原》审视了中国从民初到本世纪中叶这段“民族的秘史”,[55]由民族生活史、生命史组成的悲怆国史。阿诺尔德·汤因比说中国“1911年到1949年是动乱时期”。[56]《白鹿原》审视这段云谲波诡的历史时表现梁漱溟般的忧患意识。梁漱溟说从民国成立到1949,“其统一的时日,怕前后还凑不足三年,你看可怜不可怜!所以认真讲,简直就未曾统一过!”[57]
但是,“要乱的人巴不得大乱,不乱的人还是不乱。”[58]
《白鹿原》不是“时期小说”,它不满足于表现“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的社会”,不将自己“束缚于某一时代”。[59]《白鹿原》有一个恒久的中国。
黑娃等十兄弟回到他们所在的十个村子发动群众,有两个回家以后就“趴下不动”了。其中一个的父亲竟要替儿子还上在城里“农讲所”受训三个月“吃人家饭”的饭钱。黑娃在白鹿村仅发动起两个人——他的女人田小娥和开配种场的白兴儿,致使黑娃气恼地说:“我在原上能刮起风搅雪,可是在白鹿村连一根鸡毛也搧不起来。”
集团斗争理论在白鹿原为固有的文化所消解。鹿兆鹏运用刚刚听来的理论把白鹿村称之为“封建堡垒”,显得无依据,无根基,表现出此理论的外来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把俄国革命运动描写为非俄国所固有、人为地从西欧搬来的东西,描写同俄国人民格格不入。《白痴》中的梅什金把革命者称做“失去了根的特殊阶级”。
梁漱溟曾经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每值大乱,往往有超然于混乱之上者。[60]《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朱先生就是超然于集团斗争之上者——这是由他们身上的儒家人格决定的。
白嘉轩充分预感到愈逼愈近的混乱,同时也愈来愈坚定地做好了应对的策略:处乱不乱。支持他的是“实实在在的庄稼人”[61]意识,四合院主人的“独立人格”。[62]他不染指集团政治,拒绝让他出任“乡约”的请求。他最反感满口新名词的“烧包儿的言谈举止”。他在“风搅雪”中给儿子办婚事,认定集团斗争跟他“屁不相干。”[63]
作为族长,白嘉轩在朱先生、徐先生帮助下,乱世中恪守“治本之道”,“教民以礼义,以正世风”。实践《乡约》,治赌反毒;修复被黑娃造反弟兄砸碎的《乡约》碑文,补缀人心;超然物外地把“兄弟相煎”的戏楼称作“烙锅盔的鏊子”,体现了儒家非阶级、非破坏、重协调、重建设的特质,“新儒家”在民族危难之际表现的参与意识。梁漱溟在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濒于灭亡时,致力于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并且尖锐指出:“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64]
白嘉轩在农民运动中曾被戴高帽游行,而当农会骨干后来惨遭报复时,他不计前嫌,跪下来为他们求情;黑娃一伙曾打折过他腰,他却以德报怨,竭力营救黑娃。民国初年,他曾发动大规模的鸡毛传贴抗义运动,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并且徐先生他俩认为这不算“犯上作乱”,不算“不忠不孝”,认为“对明君要尊,对昏君要反;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65]表现了儒家的开明、开放精神。
儒家超然、开放精神中的最高意识是民族主义。朱先生在中国整个即将沦陷之际,怨愤以至蔑视中国的军人,无法理解如此泱泱大国如此庞大的军队怎么就打不过一个“弹丸之地的倭寇”。[66]他颂扬中条山“砥柱人间是此峰”,颂扬开赴中条抵抗日寇的中国军人为“白鹿精魂”。他冷下脸向鹿兆海索要一样“念物”——“亲手打死的倭寇一撮毛发”。[67]他亲自上原迎接灵车,为晚辈鹿兆海守灵——“民族英魂是不论辈份的”。白嘉轩拄着拐杖主持葬礼所含不同寻常的意义,及其动用族款族粮办丧事的动议深得众望,还有白鹿原绝无仅有的隆重葬礼本身,都表明民族主义的魂灵游荡在古原的大地和天空。而朱先生等八位关中大儒要弃笔从戎、亲赴抗日战场的民族正气,更加鲜明地表现了民族主义对于集团斗争的超越。朱先生才是真正的“白鹿精魂”。他身上所体现的儒家精神和民族主义才是真正的“白鹿精魂”。
《白鹿原》继《四世同堂》给民族主义以最高褒扬。
抗战中的朱先生,像是国难当头,一面投身抗日前线,一面多方奔走以求共同抗战实现民族命运转机的梁漱溟的身影。
朱先生整体形象,也像是“新儒家”的领袖人物梁漱溟。
而《白鹿原》小说,就文化意义上讲,可以称之为“新儒家小说”。
《白鹿原》不是对于中华民族某一阶段历史的摹写——何况这段历史并不是“英雄时代”——而是民族精神的重构。陈忠实确信中国当代各种文学流派“其主旨无一不是为了写出这个民族的灵魂”。[68]陈忠实运用了和梁漱溟的“历史——文化”相同的方法,写历史中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历史存在,文化存在,亦即陈忠实所重视的“文化心理结构”。[69]《白鹿原》的重要人物,都代表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是“历史的迷误”下面的深层构造,对行为和命运具有强大支配力。作家将其置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去解析,便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心理冲突。
《白鹿原》属于托尔斯泰潜心创作的“心理历史小说”[70]即“现代史诗”。
《伊利亚特》的主线阿喀琉斯的愤怒——息怒,表现了盲诗人荷马对民族前途的忧戚与拯救;托尔斯泰是塑造俄罗斯灵魂的作家,他的史诗小说中贵族和人民之间联系的纽带就在于俄罗斯灵魂。《战争与和平》表现依靠这个纽带俄国得以度过了1812年那场民族危机,《安娜·卡列尼娜》则表现通过改革,重新依靠这个纽带度过俄罗斯民族所面临的新的危机;《白鹿原》揭示历史的本质,重构民族精神,寻求民族救赎——复兴的途径。白嘉轩总是岸然地走在白鹿村道上。朱先生超然地穿越历史。小说尾声,白孝义将白鹿、白狼两个意象联系到一起,自然而又坚定地选择了前者。
他随着队伍开到河南打了一仗,既幸免于死而且未伤一根毫毛,打掉的只是他对战争的恐惧和稀奇,心里顿时派生出对战争根深蒂固的厌恶。他看见那么多死人,己方的和敌方的尸首交错叠压在一起,使他联想到麦收时原上田地里的麦捆子。他与生俱来的那一股拗劲儿从心底冲荡起来;这都是图个啥为个啥嘛?刚刚长成小伙子还没出过大力,“嗄嘣”一声倒下就把伙食账结了!我不想算别人的伙食帐,也甭让旁人把我的伙食帐算了。我不想变成麦捆子,也不想把别人变成麦捆子,我还是回去种庄稼喂性畜吆牛车踩踏轧花机子好些。他趁一个黑夜逃跑了,逃奔了近两个月才回到家乡。
《白鹿原》表现了生命的无尽,华夏民族精神的源远流长。
《白鹿原》的时间是天文时间。历史的循环,生命的运动——诞生、死亡、诞生——是它的节律。1911不是这个历史的源头,1949也不是终结。就象小说开头不断地向上溯源一样,结尾又不时地向下延伸:白孝文在解放前夕摇身一变,投机革命,成了解放后滋水县第一任县长,随后便以“革命”的名义处决了顺应历史起义的同族兄弟鹿兆谦;土改运动白嘉轩幸亏三年前听了朱先生指点辞掉长工送掉些土地免于被划为地主,青年作家鹿鸣50年代中期在白鹿村搞农业合作化时结识了白嘉轩,后者成为前者轰动文坛的长篇小说《春风化雨》中反对集体化道路的顽固落后势力的人物原型,1966年红卫兵打落、烧掉字迹斑驳漆皮脱落的“白鹿书院”匾牌;批林批孔运动中红卫兵掘墓鞭尸,却搜出了朱先生刻在一块砖头两面的“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和刻在砖头夹层的“折腾到何日为止”的箴言,80年代中期,鹿鸣终于弄清白灵的死亡过程,并且“在他年过五十的今天,才弄清楚,白灵是他的亲生母亲”,其时白嘉轩已经过世……这里有人世的沧桑,人生的不尽,也有历史的连续感。秉笔直书,将中国20世纪历史连起来写,显示后来的事情与先前的之间的必然联系。六七十年代红卫兵捣毁白鹿书院和20年代黑娃弟兄们捣毁白鹿村堂两事不是出于同一因子吗!这就是作家对于民族“大命运”的思考。作家写道:“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化大革命’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71]
在这些必然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必然。
《白鹿原》的问世显示了这个更大的必然。
儒学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黑格尔哲学理论中的所谓“正、反、合”过程。《白鹿原》中朱先生查阅的滋水县历代县志所记载的儒学治下的太平盛世是“正”;不言而喻,“反正”就是“反”,它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虚无为特质持续四分之三世纪之久;作家鹿鸣对“历史悲剧的根源”所做的“反省”,[72]以及几乎与此同时出现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都属于“合”的过程。《白鹿原》则是这一过程的里程碑。
《白鹿原》等上述文学作品的问世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复壮”的组成部分。
陈铨于1943年写道: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互相争斗,使全国四分五裂,给敌人长期侵略的机会,而是内部如何团结一致,对外求解放。他将文学的这一使命寄托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发扬民族固有精神的“民族文学”[73]随后,《四世同堂》问世,将“民族文学”推上一个高峰。然而,这一高峰后来又长期地为阶级本位文学所淹没,直到《白鹿原》等作品问世,才又使其在更高意义上崛起。
“学衡”派重要成员梅光迪于1920年1月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写道:“于此革新声浪之中,人方以为晨光始启,而已独抱隐忧,以为漫漫长夜之将至。”[74]——这里预言的“漫漫长夜”为后来出现的持续近四分之三世纪的个人本位、阶级本位文学所验证,它实际是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反”,《白鹿原》等作品问世则是“晨光始启”,亦即“合”。
黑娃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拜倒在朱先生门下,皈依儒家,坐在白鹿书院诵读《论语》;朱先生死前算定要被人揭墓,所以一个红卫兵愤怒中捞起那块砖头往地上一摔,砖头竟没折断却分成两层,里面刻着那句箴言——这些奇异而神秘的细节隐喻着那个更大的必然。以红卫兵运动为终结的集团斗争毕竟是过眼烟云,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则是“不废长江万古流”。
《白鹿原》等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托尔斯泰1905年向中国所作的“进言”已被理解并开始实现。这应验了罗曼·罗兰1928年对此所作的预言:“现在中国虽闹着政争与革命,但这不过是历史的永久性中兔起鹘落的一片断;托尔斯泰的主张和中国数千年来圣哲的教训既是一致的,那么怎见得中国人民不会一步步接近托尔斯泰的思想呢?”[75]这个理解的方式很像白鹿村人一度经历过的:
白鹿两姓的族人拥进祠堂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断裂的碑石,都大声慨叹起来,慨叹中表现出一场梦醒后的大彻大悟……[76]
注释:
[1]《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第155页。
[2]同上,第156页。
[3]同上,第151页。
[4]同上,第155页。
[5]同上,第139、156页。
[6]《白鹿原》,第356页。
[7]《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53页。
[8]《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83页。
[9]《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75页。
[10]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1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页。
[12]《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81页。
[13]《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74-175页。
[14]《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80页。
[15]《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98页。
[16]《白鹿原》,第398页。
[17]《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75页。
[18]《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79页。
[19]《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75页。
[20]《白鹿原》,第23页。
[21]《白鹿原》,第24页。
[22]《白鹿原》,第225页。
[23]《中国的贤哲》,《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1页。
[24]1884年7月9日《日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31页。
[25]《致张庆桐信》,《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26页。
[26]《白鹿原》,第83页。
[27]《白鹿原》,第227页。
[28]《白鹿原》,第228页。
[29]《白鹿原》,第271页。
[30]《白鹿原》,第277页。
[31]《白鹿原》,第406页。
[32]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2页。
[33]《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17页。
[34]《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89页。
[35]《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91页。
[36]《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8页。
[37]《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46页。
[38]《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19页。
[39]《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40页。
[40]《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2页。
[41]《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6页。
[42]《致张庆桐信》,《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26页。
[43]《白鹿原》,第118页。
[44]《白鹿原》,第403页。
[45]《白鹿原》,第199页。
[46]《白鹿原》,第406页。
[47]《白鹿原》,第173页。
[48]《白鹿原》,第410页。
[49]《萧洛霍夫研究》“前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50]《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19页。
[51]《白鹿原》,第219页。
[52]《白鹿原》,第472页。
[53]见《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220页。
[54]《对华战略最好和最坏的结局》,日本《中央公论》,1995年12月号。
[55]见《白鹿原》卷首题词。
[56]《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8页。
[57]《中国建国之路》,《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323页。
[58]《白鹿原》,第203页。
[59]埃德温·缪尔:《小说结构》,《小说美学经典三种》,上海文艺出版社,第404页。
[60]见《中国文化要义》第11章,第2节。
[61]《白鹿原》,第208页。
[62]《白鹿原》,第203页。
[63]《白鹿原》,第202页。
[64]见《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453页。
[65]《白鹿原》,第100页。
[66]《白鹿原》,第549页。
[67]《白鹿原》,第552页。
[68]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69]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70]托尔斯泰1865年3月19日《日记》。
[71]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漫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
[72]《白鹿原》,第547页。
[73]《民族文学》第1卷第1期(1943年7月)。
[74]《自觉与盲从》,《民心周报》第1卷第7号。
[75]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与东方》,《东方杂志》第25卷19号(1928年)。
[76]《白鹿原》,第237页。
标签:白鹿原论文; 梁漱溟论文; 白嘉轩论文; 儒家论文; 陈忠实白鹿原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鹿兆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