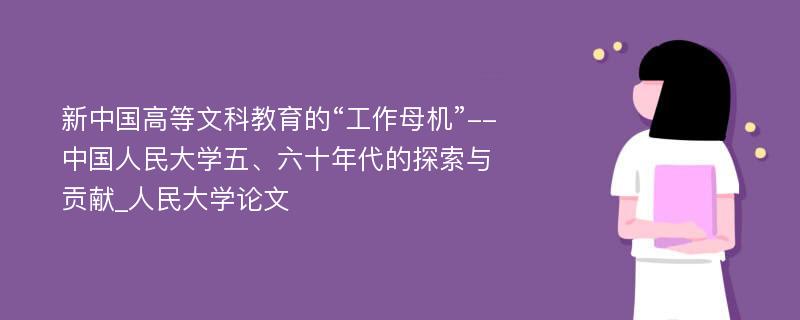
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探索与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作母机论文,中国人民大学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新中国论文,五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国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各行各业急需各种机械设备。在时代使命感的驱动下,生产建设一线的工作及科研人员以满腔热忱投入到“工作母机”的研制当中。而“工作母机”这一概念也逐渐从工业领域延伸到国家建设的其他领域,如教育领域。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就曾在总结学校工作时将苏联专家比作“工作母机”,他指出:“为了合理而有效地发挥专家力量,我们一开始就不是把他们当成普通的教授给学生讲课,而是把他们当成‘工作的母机’给教员、研究生讲课。”[1]而“工作母机”这一说法,也常常被用于形容学校在学科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
1950年10月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刘少奇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所没有过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立其他的大学”[2](P102)。因此,中国人民大学早在命名组建之初,就责无旁贷地扮演了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工作母机”的角色。学校创建之后,坚持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在专业设置、师资培养、教材编写、制度建设以及办学理念等方面,顺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教学科研机制,成为全国其他文科高等院校学习的模板,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著贡献。
一、“学科母机”——专业设置及学科建设对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产生示范作用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从当时的高等教育资源情况看,“旧式教育下的学校所占比例很大,国民党控制下的很多高校带有明显的党化教育痕迹”[3](P10)。据统计,“1949年,全国有大专学校205所,其中私立学校81所。”[4](P17)在这些学校中,“仅教会大学就有21所,其中接受美国津贴的就占17所”[5](P256)。这样一种高等教育机构组成情况,在意识形态、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不能适应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对此,1950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
在这一指示下,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高等财经、政法教育体制,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建校初期,根据政务院的决定,学校设置了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工厂管理系、法律系和外交系,其中有6个属于经济领域,后又增设国民经济计划、农业经济等专业。此外还开设专修班,包括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借贷、贸易、合作社、工厂管理、统计、外交、教育、法律等。[6](P95)随后,学校又开设了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专业,并且很快开办了与以上专业相应的研究生教育。
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的这些专业,都是为培养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急需人才而设置的,并且许多都为全国首设。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率先设立了法律、贸易、工业经济、档案、党史等15个本科系或专业,同时还首次设置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贸易经济、民法、刑法等35个研究生专业[7]。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的前身——1950年建校时设立的财政系下属的会计专业,虽然规模不大,却成为当时高等学校的样板专业,并在新中国会计工作和会计教育的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8](P523-526)。1956年,由何干之教授、胡华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奠基并创立了中共党史系[9]。另外,中国人民大学首创了档案学系,并使其散布到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中国人民大学也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如著名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缪朗山教授开设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课,就为当时全国高校首设[10](P67-68)。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中也十分重视意识形态教育,例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四门政治理论必修课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核心[11],这也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必修课的范例,对我国高等院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各个系科之下,中国人民大学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41个教研室。作为学校的基本教学组织单位,教研室的功能主要包括:组织教研室工作人员的教学工作并保证教学质量、制订讲授大纲、编写教材、组织科学研究工作,以及与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协作、培养研究生等[12]。财政、统计、贸易经济、工业经济、国民经济计划、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刑法、民法[13]等教研室,都是与实际联系较为紧密、社会需求十分迫切的专业领域。这些教研室的组建,一方面能够为国家相关领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其他院校的相关学科承担起师资培养、成果交流的作用。在1954年召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的杨秀峰明确指出:“教研室应当作为开展教学工作的基本单位”[14](P46)。随后,教研室这一形式逐渐为我国其他高等院校广泛借鉴,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教学组织机构。可以说,教研室的出现,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促进了我国高等院校的文科专业建设和科系发展。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些系科,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整个中国高等院校文科学科建设的最初模型,其中许多专业和系科现在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优势专业和系科。
在帮助其他院校进行院系组建和学科建设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也是不遗余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正规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在创办初期就曾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学院等第一批政法院校培养师资,提供教材和教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也以培养师资、派人支援等方式,为其他高校设立相关教学研究机构提供支持。另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在全国高校近30个哲学系中,有26个系的系主任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他们基本上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15]。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母机”。
二、“师资母机”——为全国其他高校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文科教学及研究骨干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文科高等教育“工作母机”的另外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师资培养。建校初期,中国人民大学承担了“为全国高等院校培训社会科学领域教师、研究者的任务”[16](P161)。1954年,高等教育部进行了一次院系调整,将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进一步明确为:“培养财经、政法及俄文干部和高等学校师资”,“改造和提高高等学校现有的财经、政法师资”,以及“培养马列主义师资及研究生”。[17](P126)此次调整后,全国各地建立的财经学院和政法学院在业务上需要“接受人民大学的指导”,任职的教员也要“接受人民大学的重新培训”。[18](P114)直到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基本任务依然包括培养高校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师资和科研人才以及其他建设干部。
以统计学系为例,从建校初期到被迫停办,中国人民大学先后“为政府统计系统和经济管理部门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并承担了向全国各综合大学和财经院校输送统计师资的任务”[19](P556)。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师资培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更可谓是独挑大梁。学校开办四年,即有一、二、三年制的政治理论和其他专业研究生共计1 158人毕业,其中有767人先后在全国210所高校担任马列主义理论和各相关专业的主讲教师以及教研室的正、副主任[20]。到1956年,全国几乎每所高校都有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政治理论教师[21]。
当年,全国许多高校的教师曾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课,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如哲学界的贺麟、张岱年,法学界的吴恩隆、龚祥瑞等。组织教师集中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课也是许多大学及其院系的一种做法,如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当时就经常组织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课。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涵盖财经专业的各个方面,在全国独此一家,因此,全国其他院校如现在的中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以及上海的一些学校,都曾派人来学习。[22](P169)资料显示,中医大学、河南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商业专门学校等,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就曾派大批干部来学习,并采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改造自己的学校[23](P164)。可以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在校生培训、教师旁听及教师进修等方式,中国人民大学为全国其他高等院校的师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
对此,吴玉章校长曾经指出,“在全国高等学校改造的工作中,中国人民大学曾经给了有益的帮助”,首先就是“帮助解决高等学校的教师”,“三年来从本校毕业的研究生有九百人,其中校外的五百四十八名,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四十二个高等学校工作,在教学上一般地都受到学生的欢迎以及领导的重视”;同时学校还“抽调了教员和其他教学干部到其他高等学校工作,直接帮助建立教学组织,进行教学工作”;此外,学校应京津地区部分高校及工业部门的邀请,派政治理论教员和业务教员去讲课,对各单位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工作有很大帮助。[24]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是最早开办研究生教育,培养师资和高层次人才的高校。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之初,就设立了35个研究生专业,后来又设立了马列主义研究班,这些都卓有成效地培养了大量高校师资。特别是马列主义研究班,开办七年,就培养了2 500多名研究生,许多人后来成为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骨干及政治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战线上的中坚力量。如郑必坚、滕文生、孙尚清、蒋学模、吴树青、黄楠森、萧灼基、何建章、朱佳木、朱作霖、胡福明等。从招生规模上看,1951年,全国高校共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500名,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的研究生数量就达到了200名,占招生总名额的近50%[25](P425)。到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研究生占全国高校培养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这些毕业生成为全国高校的重要师资来源。
三、“教材母机”——引进和编写了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最早的一批教材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以后,承担了翻译苏联的社会科学教科书,并为相关领域制订教学计划、写教材、写讲义的任务,“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教材为全国各高等院校使用”[26](P161)。学校翻译或编写的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到建校五周年时已经印刷了765万册,其中大多是被各个高校拿去参考或者使用。另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或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多达101种[27](P89-92)。这些教材或译自苏联成果,或由学校教师编写,涉及面广,涵盖政治理论、财经、政法等诸多专业领域,被各大高校所广泛采用,并在他们编写自己的教材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不但陆续接待了全国各地高等学校来校参观者,向他们赠送各种材料,利用文字较系统地向全国介绍了学习苏联的经验,而且还有计划地向有关机关和学校供给业务教材参考材料,以及较普遍地供给了政治理论教材和参考材料。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三年中供给各地业务教材、政治理论教材及参考材料100余种,合计166万册[28]。
在当时的教材建设方面,苏联专家功不可没。首先,专家们的讲座被翻译成中文后,各个教研室的成员据此编写中文教科书,撰写苏联专家的讲座概要,并且通过复制,将其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全国的教材。同时,苏联专家也就各个主题面向教研室成员发表演说、报告,这些主题有的是关于苏联教师研究的特定领域的学术知识,有的是关于如何开展大学的工作,例如,如何管理大学的院系或科室,如何安排考试,如何撰写论文等。中国人民大学将这两种类型的材料,即有关专业的以及有关“如何”开展工作的材料印刷出来,供本校以及国内其他高校使用。
1951年8月,为了适应兄弟院校、厂矿企业和机关单位对学校教材的迫切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在出版处领导下成立了教材出纳组,对外凭证(持单位介绍信)供应学校内部铅印教材,使得学校教材的发行范围扩大到全国各地[29](P435-436)。此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专门设立了教材供应组,其职能主要是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供应到全国各地。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召开后,在高等教育部学习人大经验的号召下,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及各高校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表现出巨大的需求。为此,中国人民大学率先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一直到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办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共正式出版了400多种新书,发行量达到800万册,许多教材和书籍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影响十分深远。
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这些教材和讲义的陆续出版,对我国的一大批学者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代学人都受惠于此。当年,部分教材和讲义出版以后,随即成为该学术领域的奠基之作,被全国其他高校及科研机构广泛采用。例如,尚钺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纲要》是新中国第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著作;何干之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通用教材;王嘉谟主编的《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函授讲义》后来被全国财经院校广泛采用;阎金锷、陈共合著的《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成为我国第一本联系中国实际的经济活动分析教材[30](P132-133);胡华编写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作为第一本中国革命史类教材,被指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并成为同类教材的母本[31](P166);新中国第一本《工业会计》、《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出自中国人民大学。此外,为了配合全国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热潮以及实际教学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组织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专题言论摘录”以及《马克思论报刊》、《毛泽东论哲学》、《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共产主义》等系列书籍[32]。中国人民大学编写和出版的这些教材和书籍,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意义。
四、“制度母机”——率先探索建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的一系列基本制度
制度是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顺利开展的基本保证,是学校各项工作有章可循的基本依托。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一系列苏联模式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教学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在中国人民大学施行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中共中央和高等教育部的高度肯定,成为全国其他高等院校争相学习的范本和模板。
在这些新型的教学制度当中,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强调组织性和计划性,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在苏联专家身上感受最深的一个品质。在所有的专业领域里,苏联专家都强调制定详细的计划,并且严格明确每一个人在完成计划过程中所负有的责任,同时制定出各项工作的考评标准。与这些计划相伴随的,是“单一负责制”,这种责任分配体系强调每一项具体工作都有一个明确的领导者和负责人。例如,在每个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是核心的负责人,他通过召开会议、旁听教师讲课及撰写报告的方式,监督其所在教研室教学工作的开展[33]。可以说,强调组织性和计划性,落实“单一负责制”,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初期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有序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而这一制度经由中央肯定,也为其他高校所效仿,并且随着学习苏联经验的推进,逐渐延伸到我国各行各业的工作中。如今,对于计划的制订以及对于效果的评估,依然是我国诸多高校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和基本保证。
在具体的教学模式上,中国人民大学也在全国率先建立起诸如习明纳尔(семинар)、口试、四级计分制、生产实习等教学制度。习明纳尔即“课堂讨论”,是从苏联借鉴来的一种教学模式,十分强调计划性和组织性,特别适用于理论学习。这种课堂讨论的学习模式在当时经由中国人民大学采用并推广,逐渐成为我国其他高校,特别是文科高等院校推崇的一种教学手段,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为我国各学科的人才培养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考试和评分制度方面,中国人民大学采用的是苏联模式的口试和“四级计分制”。由于启用了“优秀”、“良好”、“中等”、“劣”[34](现称之为优、良、中、差)这四个等级对学生的口试情况进行评分,教师不再需要将分数精确到“百分制”的个位,而只需对学生的整体学习水平进行评判。在当时的情况下,口试和“四级计分制”被认为是更能准确地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考试和评分方式。因此在1954年年初,高等教育部颁布条例,将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尝试采用的口试方法以及“四级计分制”在全国各高等院校强制推行①。
相比于以上两项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生课外实践方面所采取的生产实习制度,对我国其他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而深远。这既是将书本学习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一制度不仅对中国人民大学的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其他高校的学生课外实践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范例。直到今天,生产实习依然是学生专业学习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途径,并且为国内高校所普遍采用。
此外,在科学研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也率先建立了一套系统化、规范化的制度。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每个教研室都要起草科研计划,在学校每年召开的由全体研究人员参加的“科学讨论会”上总结该研究计划的完成情况,也以此来展示中国人民大学作为高等院校排头兵的角色。各系及各教研室在举行一些庆典活动的时候,也会召开科学讨论会,同时提交一批相关主题的论文,如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斯大林宪法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日。可以说,在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工作启动得很早,和教学是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而这些关于科学研究的制度,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如今,许多高校仍然保留着当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来的科研体系。
五、“理念母机”——办学理念及学术思想对其他高校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除了在学科、师资、教材和制度的建设方面发挥“工作母机”的作用之外,在办学理念以及国家建设理念方面也源源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智慧。首先,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理念对当时其他高校的影响十分深远,如“实事求是”、“治学报国”、“服务社会”等理念。吴玉章校长提出的“以马恩列斯的学说与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并把他们培养成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专家”,以及“联系理论与实际,使生产经验与科学相结合”等诸多办学理念,更是为全国其他多所高校所认同,并被运用到自身的办学实践当中。
同时,中国人民大学还积极将自己的理念输出到国家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学校通过业务挂钩、社会调查、生产实习等方式,组织教师同业务部门、厂矿企业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由此掌握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定科研方向,产生一批理论联系实际的论文,再通过这些论文将先进的科学理念传达到一线的生产部门。
此外,国家也委托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许多决策的前期调研。1960年,在黄松龄副校长的协调和组织下,经济、计划、统计等系的系主任数十人,前往国家计划委员会参与调查研究,承担部分工作任务。由此,中国人民大学被正式列入参加每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的名单,也成为参加该会议的唯一高校,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198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除外)[35](P184)。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还经常应邀到中央有关部门作报告,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和胡乔木同志就经常向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咨询一些问题。直到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依然承担着国家许多重大决策的前期调研任务,一些教授也常常被邀请到中南海去给国家领导人讲课。
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法律、哲学、经济等领域拥有一批建树丰厚的学者,他们经常通过各种方式,将自身研究领域最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新知传递到中央。例如,法律系的许崇德和高铭暄老师先后参加了国家宪法和刑法的起草工作。1958年,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和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被派去进行有关人民公社的调查,毛主席在他们临行前嘱咐说要带两本书去,其中一本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且说即使没有时间也至少要把中国人民大学编的这本书看一看,可见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大学这方面作用的认同和肯定[36](P163)。1963年,哲学系肖前老师因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这一号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一文,毛主席和周总理阅读后表示了高度的赞赏[37](P197)。
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教学与研究》杂志,作为服务于全国高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和科研的专门刊物。该刊先后发表了《为什么学习以及如何学习〈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谈《共产党宣言》等理论文章,成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的重要理论阵地,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57年4月,毛泽东同志阅读了人大教师王方名和黄顺基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很感兴趣,随后约见了包括王方名、黄顺基在内的部分在京逻辑学专家到中南海讨论形式逻辑问题,金岳霖、冯友兰、贺麟、费孝通等学术大家都参与了讨论[38](P15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大学在各种理念和学术思想的倡导和普及方面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中国人民大学不仅教师的文章和建议被中央采纳,一些学生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关注和肯定。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的学生李希凡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蓝翎合作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一文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毛主席据此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不要迷信权威,要大胆地批判。自此,全国上下开始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派观点的批判[39](P131)。此外,1959年毛主席还发表过一篇《关于发展养猪业的一封信》,文章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刘芳圃的作品《魁星庄养猪经验》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全国人民学习报道中的经验[40](P173)。一名在校学生写的文章能够得到国家主席的批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工作成果及其文风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运用。
总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在努力建设新型正规大学的过程中,大胆探索,借鉴创新,形成了一套适应新中国国情的文科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教材编写、制度设计、理念培育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工作母机”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伴随着中央政府“对旧大学进行改造”的契机,“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41](P152),为新中国文科高等教育体系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注释:
①由于这一考试方法和计分制度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太适合理工科的学习考核,因此到了1956年9月,高等教育部再次指出,在笔试方法被重新采用的情况下,允许人们使用过去更为熟悉的“百分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