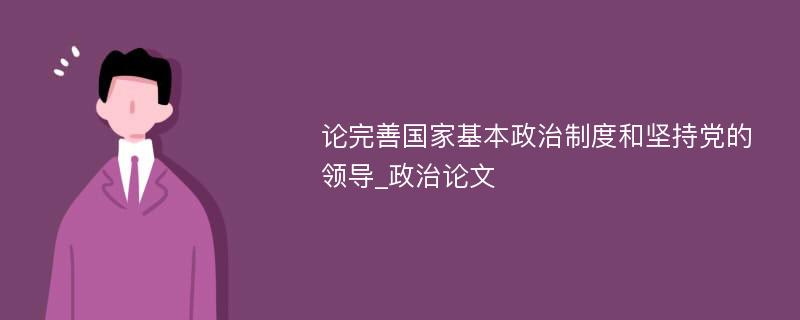
论完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与坚持党的领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制度论文,领导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往今来,任何国家为了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都要采用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亦即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民主共和制政体在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经过长期探索所作出的审慎抉择。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中国各族人民在定期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并由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其他国家机关,以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制度。从建国伊始至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创制(1954年9月正式确立)到巩固发展,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 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政治制度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实践也已经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健全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保证。
一
加强和完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不仅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而且符合现代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列宁说过,“政治活动有自己的逻辑。”这一逻辑在现时代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政党政治成为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的基轴。政党是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政党政治是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当今时代是一个政党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一般而言,现代国家都有着一个议会、政府与政党的关系问题,尽管这种关系的具体演绎方式错综复杂,但总的来说,议会或政府是以政党为轴心来展开运作的。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政党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在各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虽然近来有些西方学者称,西方国家的政党时代已告结束,继之而来的是“利益集团的时代”,然而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主导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仍是政党。在组织竞选、掌握政权、制定政策、控制社团等方面,政党仍是左右各国政坛的主体力量。在常规态势下,当代西方政党政治既在高度发展又井然有序,从而强有力地保障了西方政治体系的运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不仅是我国基本国情的内在要求,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现代国家政治权力运作一般规律的内在要求。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起发达国家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为艰巨和紧迫的发展任务。世界进入现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公共权威的确立及其有效运作往往需要依助强大的执政党力量来实现。因此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每个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不可避免的政治课题。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把一个强大的政党看成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实现政治安定、保持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一个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同有强大的政党的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注: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96~397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政党数量、政党力量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亨氏认为,一党制可强可弱,但多党制却毫无例外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稳定的多党制。在发展中国家,一党制要比多党制稳定得多。”“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的。在现代化中国家,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注: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08~410页)亨氏的逻辑是,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需要政治安定,政治安定需要国家公共权威来保障,国家公共权威又根植于强大的政党——强大政党以强有力的组织力量确保了权力运作的权威。尽管我们对于亨氏众多见解可以作进一步的评析,但是他的上述见解是通过深入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而得出的,是有现实基础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就非常注重政党对国家权力的保障与支持作用。他认为,“党作为阶级的先锋队、教育和组织者,其作用有特殊意义。”(注:《列宁全集》第1卷第317页)列宁特别看重执政党所具有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他指出,“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之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注:《列宁全集》第7卷第360页)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内在规律乃至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内在规律是一致的,近代以降,不少国家的历史与实践已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离不开现代国家权力运作的内在规律。在这样一个大国,任何社会权威的确立及其运作,没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的支撑与保障是不可想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现代国家权力运行的必然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自然地承担起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重任,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这一政制呈现了维系中国社会公共权威并适应现代国家权力运作内在规律的显著特点。
二
加强和完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也是人民民主国体这一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在国家类型(国体)与政治形式(政体)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类型对政治形式具有决定作用,国家类型对政治形式的决定作用首先体现为对政治形式性质的决定作用。国家政治组织形式与国体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般说来,国体是政权组织形式的基本决定因素,同时,国体又通过一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予以反映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的性质与任务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只能选择民主共和制。恩格斯曾说,“如果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制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 页)共和制是国家政权机关和国家元首定期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一种政治制度。“由于社会经济形态、政治关系、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国家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同一类政体在不同国度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民主共和政体在美国表现为总统制,在法国为半总统制,在德国为议会制,在瑞士则为委员制等。民主共和制政体在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亦即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注: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的讲话》,《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44页,法律出版社1994年9 月版)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人大制度的基石。只有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才能根据人民的委托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宪法的规定,表明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及其在整个国家机构建构中的地位。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一根本性质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区别于西方国家代议制的一般特征: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中国的国体性质,决定了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保证。因此,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注:《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36页)具有坚实的人民性。
国家权力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现代政治学认为,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国家权力具有统治性和管理性的双重性能。国家权力的统治性即权力主体通过实施一系列政治统治行为,保持自己对社会或政治群体中其他力量和成员的制约地位,它是政治权力存在的保证,集中体现着政治权力的利益本质;国家权力的管理性质则是权力主体通过对于保持统治所必须的社会职能的领导、组织和贯彻实施,实现对于社会或政治群体的管理,它是政治权力运作得以保持和持续的基础。党的领导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权力的统治性质,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政治权力的主体归属,防止政治体制与人民的分离,避免“公仆”与“主人”关系的倒置,杜绝国家对社会的异化。从本质上说,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职能和作用在于,支持和保证人民作为真正的国家权力主体去当家作主,行使国家公共权力。
反过来说,不同的国家政体规定着政党在不同的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同的作用、作用方式和程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执政党,党就通过领导人民,把为人民谋幸福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国家意志。这是我国人民民主的国体所要求、所决定的。
三
坚持和完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也是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运作方式的内在需要。从社会发展历史看,国家机构的设置原则一般有三类形态:集权形态、分权制衡形态和议行合一形态。集权制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国家机构设置的通常形态;分权制衡是现代西方国家一般的设置形态;议行合一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政权组织形态。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政权组织经验时,提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精髓在于,人民控制代议机关,代议机关控制全部国家权力,从而保证全部国家权力都置于全体人民的控制之下。着眼于机制的科学运作,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应“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09页)在后来无产阶级国家政治实践中,议行合一在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议行合一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第一,人民对于国家事务拥有最高权力,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实施这种权力;第二,人民对于各种国家职能机构具有统辖权。一方面,人民可以委任各种机构和官员执行政治职能,他们应向人民负责;另一方面,人民对这些官员和机构有监督权和撤换权。在国家机构方面,这种组织原则具体体现为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有一定任期的立法机关,兼执国家立法、行政双重最高权力。
实行议行合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建构的基本原则,也是一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国家领导体制和新型运作方式。其一,议行合一在国家机关间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与行政的统一”。在这一制度下,全国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全国的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一切权力。它直接行使最高立法权和最高决定权,同时组织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等机关,分别赋予它们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并对这些权力的运作实施监督。这种建构蕴涵着“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从权力体系运作上说,这种集立法与执法于一体的权力体制,由于其所具的整体性,其有效展开和有效运行,有赖于一个中流砥柱,斡旋折冲的政治核心。其二,议行合一在机制运行上表现为“功能与效率的统一”。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注:《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36~37页)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避免不同国家机构之间容易出现的议行脱节、相互抵销、影响效率的弊端,具有三权分立原则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然而这种“优点”的发挥,亦有赖于另一“政治优势”的发挥,亦即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与统一协调。
中国是一个有着绵延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中国历史传统之深厚、民主法治建设与社会综合性发展的任务之艰巨、之艰难,乃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无可比拟。要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实现现代化,要把数量如此之巨的群体组织起来,形成万众一心的政治局面,没有一种强大的政治凝聚力量、社会整合力量是不行的。缺乏党这样一个“政权的核心”(注:列宁语,转引自《斯大林文选》上卷,第418 页)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政治中轴作用,必然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再完善的政治体系也难以发挥其应有效益。而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效率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特殊意义。因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注:《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38页)成为国家权力体系可资运用的宝贵政治资源,也体现了适应中国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
从人大内在结构上看,人大代表作为人民权力的受托者,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各行各业、各个民族都有其代表(这与西方议会的构成不一样),这种广泛性代表了利益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忠实代表,使上述广泛性得到了体现与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和国家机关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党和国家机关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根本任务都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党对人大工作领导的内在统一性。
四
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国家类型,中国特殊的国情与特殊的发展任务,决定了党对国家事务保持领导这样一种核心地位,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的必然性。当然,这里说的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自然是指科学的、法治的、程序化的、适应人大工作内在规律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在规律的领导。决不能一讲党的领导,就出现那种对人大工作过多干预,党政职能不分甚至越俎代庖的现象。我们知道,“党是政权的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而且不能是一个东西。”(注:列宁语,转引自《斯大林文选》上卷,第418页。)从性质上说, 党是“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59 页)不是社会的公共权威,而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是社会的管理系统。因此,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领导(包括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而不是对国家权力的具体运作。所谓政治领导,指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其中包括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尊重与遵守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决议、接受人大的宪法监督等(注:参见浦兴祖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第19页,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5年9月版))。党要通过适当的途径,以正确的路线、方针、 政策去组织和支持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机关为人民行使好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独立地行使职权,善于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邓小平同志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77 页)“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注:《中国共产党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不仅有一个加强的问题,更有一个改善的问题。在实现领导的内容与任务、方式与渠道、结构与功能等方面,都要法治化和科学化。
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完善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保证,“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注:《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43页)
标签: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人民代表大会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