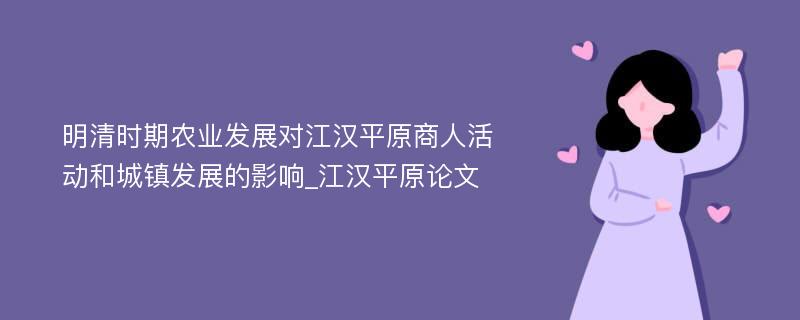
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汉平原论文,市镇论文,明清论文,商人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就江汉平原明清时期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作了较系统的考察。指出该地明清时期在农业全面开发之后,有大量米粮、棉布和少量棉花输出,于是吸引了以徽商(贩米)和晋陕商(贩棉布)为主的外省商人和以武汉附近地区商人为主的省内商人积极参与江汉平原与境外的商品交易活动。这种商业活动不仅有利于加速江汉平原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也促进了该地农村市镇的繁荣,具体表现在市镇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和种类多样化方面,并出现一些小型专业市镇。然而该地的一切商业活动均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的输出和境内外物质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的功能显得过于单一,反馈于农村则不利于该地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的樊篱,因而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
江汉平原是湖北境内一块肥沃富饶的冲积盆地,它自东租西包括今黄梅、武穴、蕲春、浠水、黄冈、鄂州、新洲、黄陂、武汉、嘉鱼、孝感、汉川、广水*、洪湖*、仙桃*、天门*、潜江*、监利*、石首*、公 安、江陵、沙市、松滋、枝江、当阳*等县市。 江汉平原不仅是湖北省的经济重心所在,也是驰名全国的经济区,该地区县级市(带星号者)的密集分布就表明了其经济地位的重要,同时也说明其发展潜力巨大。然而江汉平原历史上的开发却只是明清以来500多年的事, 相对于其它发达经济区而言,起步较晚。江汉平原的农村商业活动和市镇发展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并臻于繁荣。本文拟就当时农业开发、商品发展与该地区市镇发展的相互影响与作用一粗略的探讨,以期能对今天湖北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明清江汉平原农业开发概述
江汉平原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其经济的发展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楚庄王问鼎中原倚靠的正是以江汉平原为腹地的楚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当时江汉平原的经济实力与吴越所属地太湖地区可谓不相伯仲,因此能够几度称霸。但好景不长,楚亡以后,该地即一蹶不振,而太湖地区则日渐发达,宋元时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最重要的粮食产区。进入明清以后,太湖地区的粮食生产逐渐被丝、麻、棉生产所取代,由粮食出产区变为输入区,以此为契机,江汉平原的农业逐渐走上了以输出米粮为主要特征的全面开发之路。
明清两朝持续未缀的移民是江汉平原农业开发的生力军,这些移民包括①战乱造成的难民;②灾荒导致的饥民;③和平时期由人口密度高、粮食紧张地区(如江浙一带)流向人口密度低、容易觅食的江汉平原地区的自由移民。这些人构成了移民的主体。较次要的移民还包括:④政府有组织的移民;⑤经营工商业而定居者;⑥为宦荆州而落籍者;⑦削籍后的明代藩王世系及分散各地的清代八旗占领军后裔。这些移民人数虽然不多,但显示出该地移民成份的复杂性。其它类型的移民还有短期的流民佣工等。
以上成份各异的移民其地区来源也十分广泛,其中最突出的是江西移民约占移民半数以上,其它地区的移民则多业自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等地。各地移民进入江汉平原的动机也不尽相同,“东南之人以觅利至,西北之人以避地至”〔1〕。很显然,“觅利”的“东南之人”对江汉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类移民中的手工业者为江汉平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商业工作者则活跃了江汉平原的商品经济。从广泛出现于江汉平原各地方志中的占谷(福建)、江西早、苏州晚等水稻品种看,如果真如稻名所示,这些品种确系各地移民传入,则这些移民所引进的新的作物品种,对提高当地粮食产量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大量移民的不断迁入及移民与土著的人口自然增殖使得明清江汉平原的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大致趋势是明代增长较慢而清代较快,由明代的180万左右猛增至清后期的1865万左右,增加了十多倍, 从而使得江汉平原的人口总量在湖北全省乃至全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2〕。
移民群趋江汉平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该地存在大量可以垦辟的湖荒,加之明清统治者对垦辟湖荒又给予免税或低税的优惠条件,于是“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闲田隙土,易于购致,稍稍垦辟,岁月寝久因攘为业。又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二十里而租不数斛,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以自固,家富力强则又增修之”〔3〕。开垦湖荒所成之田即垸田,垸田是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特有的土地利用方式,该两地区农业经济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垸田的开发。江汉平原大规模筑堤围垸系肇始于明初且几与境外民大批移入同步,“明兴,江汉既平,民稍垦田修堤”〔4〕。这与明初重视兴修水利的政策有关, 明太祖曾多次诏令“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5〕。 永乐三年又规定“凡开官田,夏税麦二升,秋呈米三斗”〔6〕。以轻税刺激人们开垦湖田。 明政府还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如“正统间知府钱昕筑黄潭堤数十里”、“新开堤明成化时修,正统间布政使周季鸾重筑”、“知府吴彦章重修李家埠堤”〔7〕等,这些堤统称万城堤,即今荆江大堤的前身,为整个江汉平原的屏障,其存毁直接关系垸田的兴废。如果说众多湖荒是吸引大量移民开发垸田的主要原因,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则又为垸田的持续垦辟提供了条件,循环往复,以至逐步形成本地区农业生产中垸田经济的历史特色。
正因为垸田是围垦湖荒而成,其种植水稻的目的就很明显了。江汉平原水稻生产的发展与垸田的大量垦辟密切相关。明清江汉平原的水稻生产除表现在由于围垸造田使种植面积扩大外,还表现在种植制度的改进、品种的增加和产量提高、稻米大量输出等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产量提高主要表现在总产增加而不是单产提高。在明清两朝,江汉平原的水稻单产一直徘徊在2石即268斤左右,只是偶尔略呈上升趋势,但总产则由明成化时的17亿斤上升至清雍正时的37亿斤,继而上升至同治、光绪时期42亿斤的高峰。据推测,在人口压力尚不紧张的雍正朝整个江汉平原可供流通的稻谷高达23亿斤之多,构成“湖广熟,天下足”谚语得以广为流传的丰厚的物质基础〔8〕。江汉平原因此得以与洞庭湖平原一道取代太湖地区而成为清代全国最重要的米粮输出地区。
在米粮不断输出而使江汉平原名重天下的同时其经济作物的种植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棉、麻、烟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尤其是棉花的广泛种植与家庭棉纺织业的突出发展,致使棉布有大量输出,使江汉平原的农业呈现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共同发展、并行不悖的格局,这在全国各大农业区中是少有的现象。不过,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棉纺织业都是个体性质的家庭手工业,这种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但由于从业人户面广量大,集中起来仍能提供大量的棉布。因而从总体上看出产着数量相当可观的棉布,只是由于分散、孤立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而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异常低下的水平。
江汉平原粮棉兼重特点的形成笔者认为系取决于当地丰富的水、热、土资源和位于南北气候交汇地带的独特气候条件,并与该地区耕地总面积中水田、旱地各占60%和40%的比例有关。这种作物格局至今仍无多大变化,在江汉平原境内,较高的平原与较低的湖沼洼地沿长江、汉水两岸成带状相间排列,平原为重要棉产地、洼地为水稻主产区〔9〕。
二、农业开发刺激了省内外商人的活动
上文已简要指出,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导致该地有大量米粮、棉麻及其制成品的输出,这种输出除部分由官府以行政手段(如调拔漕粮)进行外,更多的是通过商人为中介而进入流通领域来完成,在迁入江汉平原的大量移民中就有不少是商人,商人的活动一方面使各地的剩余农产品纳入流通领域以完成商品化过程,另一方面也运进当地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有利于将当地市场纳入全国市场网络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一)省外商人
1.贩运米粮的商人
稻谷作为江汉平原的头号输出品对商人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江汉地区的稻谷交易中,商业资本表现得相当活跃。江汉平原境内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渠中大小运粮船只往来“不舍昼夜”〔10〕,商品稻谷输出主要流往江浙地区。江浙由于人口增加、粮食作物种植让位于经济作物等原因已成为缺粮区,在明末即已“半仰食江楚庐安之粟”〔11〕,清康熙时更是“全赖湖广米粟”〔12〕。从事两地间贩运米粮的商人以徽商势力最大,也最活跃,而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正集中在楚地、吴越间,“吾徽之人不讳贾,以故豪长者多游于吴越荆襄间”。徽商倚仗其雄厚的经济势力几乎垄断了吴楚之间的粮食贸易,他们贩粮的多寡往往直接影响湖广粮价的涨落〔13〕。可以这么说,徽商的运营致富正是以江汉平原等地粮食生产的发展为前提的。
2.经营棉、麻及其制品的商人
在江汉平原的棉、麻及其制成品中以棉布外销量最大,也最著名。江汉平原棉布外销大致有几个市场走向,即平原北部所产的棉布趋销北部中国,平原南部所产棉布趋销南部中国,平原东部所产棉布则南北均销。北部地区如云梦,“西商于云立店号数十处,本地贸易市店,亦藉以有无相通”,是以城中凡“宽闲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14〕,孝感“棉布有长三十三尺,宽一尺五寸者,为大布,细薄如; 三十尺以下,皆曰椿布,西贾所收也”〔15〕。这所谓“西贾”既包括山西商人,也包括陕西商人,晋陕商人是江汉平原棉布输出的主要中间商。另外也有川滇等处的商人,如南部地区的江陵“乡民农隙以织为业者十居八九,其布有京庄、门庄之别,故川客贾布、沙津抱贸者,群相踵接”〔16〕。而监利“所产吉贝大布,西走蜀黔,南走百粤,厥利甚饶”〔17〕。东部地区如汉阳“扣布……盈千累万,买至汉口,加染造,以应秦晋滇黔远贾之贸”〔18〕。汉川亦然,其所产大布、小布“近而襄樊、楚南,远而秦晋黔滇,咸来争市焉”〔19〕。
尽管江汉平原的织布业较发达,棉花主要以棉纺织品形式输出,但由于该地的棉花质量好,原棉也直接进入流通领域,以供应那些织布业较发达而缺少原棉的地区。如四川德阳“邑产木棉不敷服用,商贩厂花,向惟楚省”〔20〕。湖南邵阳因当地棉花质量不好而多贩自他处,“来自湖北最多”〔21〕。上述各例中的棉花可能是自用后多余的产品,但有些地方却已很明显具有专业性商品化棉花生产的性质,如汉川县“百谷之余,产棉恒广,富商大贾携金钱而贩运者,踵相接也,租赋待于斯,家哺给于斯”〔22〕。类似的例子还有如枝江县,“邑产棉,洲地尤佳,年丰亩地以百斤计,贾人多于董市口买花入川,呼为楚棉”〔23〕。
晚清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凋敝,织布业亦日渐衰落,江汉平原所产原棉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更多,然而这时的经营者已不再是“赁屋而居”、“沙津抱贸”的国内贾客,而是带有掠夺经营性质的外国商人,19—20世纪之交,湖北输出棉花从几百担到几十万担不等,其产地为汉阳、黄陂、孝感、沔阳、里河口、武昌、蔡甸、汉川、宜昌等地〔24〕,基本上集中在江汉平原。
(二)省内商人
省内(包括江汉平原境内)商人的势力虽不如外省商帮那么强大,经营规模和营销区域范围也无法和外省商人相比,但在区域经济活动中他们也是一股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商业力量。这些商人多数也以江汉平原的剩余农产品为重要经营内容。他们或则在本省内活动,如咸宁人“多事贸迁……若汉口、沙市、襄樊悉谋生理,家累巨万,未可一二数”〔25〕。或则在本省及周边诸省之间进行贸易,如黄州商人“购棉花于新洲歧亭、宋埠,舟运至川,载土药售宜昌、沙市、岳州,获利不资。贸汉口、歧宋及河南之光州、新集、仙花及本邑各市数亦伙,约一二万人”〔26〕。江汉平原境内商人如江夏县之“金口镇米船到岸,向不投行,即在河下摆棹,听民零籴,最为利便”〔27〕。显然这些商人的势力尚不够强大,强大者来自“外籍”,因该县“当省会冲,租税所入,不足以备一年之储〔28〕,仰给者皆湖南、沔、汉所输运……至其廛肆牙侩,鱼米市魁……率多外籍”〔29〕。这里的外籍既指湖南等省外商人,也包括沔阳、汉口等地的省内商人。该地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对商人颇具吸引力,不过更多的地方是以其产品特色吸引商人,如监利县“棉有白紫二种,绒深厚而温暖,产者不一处,惟监利最擅名,贩买者由近及远,难定所止”〔30〕。由近及远表明其中也包含有本地商人,如乾隆时沙市的10个商人会馆中就有两个系本地人开设(一为黄州会馆,一为武汉会馆,另外8个会馆是:晋陕1、福建1、徽州1、江南1、 江西2、金陵1、吴兴1)〔31〕。 这种现象又表明江汉平原的商人有溯江而上经商的倾向,如地处鄂西的长乐县商贾即“多属广东、江西及汉阳外来之人,行货下至沙市上至宜昌而止”〔32〕。宜昌的情况也差不多,“郡城商市半皆客民,有川帮、建帮、江西帮以及黄州、武昌各帮”〔33〕。黄州及武汉附近至今仍是江汉平原经商意识最为浓厚的地方。
三、农业开发促进农村市镇发展
江汉平原的市镇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伴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兴起并至于繁荣。明清大批境外移民进入江汉平原对该地农村市镇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移民进入江汉平原时,原有平原区但凡条件较好的地方已被土著占居,外来移民只好开垦湖荒另辟新地,他们为了便于统一生产和防止外来势力侵入,往往聚族而居,形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移民垦殖区,当人丁逐渐兴旺之后,结构比较简单、功能也较为单一的“市集”也就应运而生。这类市镇在江汉平原不在少数,如带有滩、珰、垸、口、嘴等字样的市镇名在江汉平原极为普遍,几占市镇总数的一半以上〔34〕,它们显然如名所示系围垦湖荒淤地之后逐渐形成,尽管还不能断定这些市镇全系外来移民拓殖(土著也会垦荒部分),但大部分属于他们所建当无疑问。其次,外来商人移民定居原有市镇之后不仅增加了所定居市镇的人口数量,而且他们的商业经营活动无疑对定居市镇经济的不断繁荣起了促进作用。
综合各地历朝方志记载可以发现,明清时期江汉地区的农村市镇发展具有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和种类多样化等诸多特点。
(一)数量增加
江汉平原的农村市镇起始较早,如江陵县的沙市“其盛在唐时已然”〔35〕,明清时期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了不少“贾客鳞集”(石首黄金堤市)〔36〕、“商民辐辏”(监利朱家河市)〔37〕的繁华集镇。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市镇的发展同整个农村经济一样亦曾一度衰败,清康熙中期以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村市镇才又有所恢复和发展。如黄梅县的36镇“明盛时地阔人稠、烟火相望、鸡犬相闻”,到清顺治年间则仅留存下来十余镇〔38〕。又如云梦县的利塘镇,明时“邑北要冲近河,商业人文并盛……今(康熙时)茅舍数间”〔39〕;而黄冈县明时的市镇中到清初则有不少是“昔有今废者”,至康熙中期以后又出现“昔无今有者”〔40〕。这种昔有今无、昔无今有的情况普遍存在于江汉平原各地,从江陵、监利、公安、石首等县方志中都可以看到关于市镇“昔无今有”的记载,市镇增加的趋势十分明显(表1),到清中期,江汉平原的市镇数目已经颇为可观了(表2)。
表1.清代江汉平原市镇数目变化举例
朝代 江陵 监利 公安 石首
同治 52*
23 3629
光绪 5142 3460
资料来源:据各县同朝方志,其中*系乾隆朝数字。
表2.汪代江汉平原市镇数
地名 数目朝代 地名 数目 朝代
天门 34 道光 枝江 33光绪
江陵 51 光绪 松滋 46光绪
沔阳 132 光绪 公安 34光绪
黄陂 14 乾隆 石首 66光绪
监利 42 光绪 潜江 43光绪
资料来源:据各县同朝方志。
(二)规模扩大
人口增加和商业活动的频繁势必导致市镇规模的扩大。江汉平原农村市镇的发展一般呈现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日中之市,交易有无,阜通货贿”〔41〕的以物易物式简单市场,依时聚散;然后发展为“商贾云集,一市而开数典迩来”〔42〕的固定集市;这种集市依其地理条件及周围地区经济发展便会逐渐形成“列肆则百货充牣,津头则万舫鳞集”〔43〕的商业城市。完成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然而江汉平原农业经济的勃兴却创造了市镇发展的奇迹,汉口镇在清代商业都市中异军突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作为清代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镇,在明代前期还只是一块与汉阳相连、鲜有居民的荒地,不过供水陆客商晾晒货物而已。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汉阳与汉口分开,居民渐多并开始小范围的贸易活动,到嘉庆年间其人口已有近13万了,此后人口日增,其地位也日渐重要〔44〕。汉口人口的增加并非自然增殖,而是倚靠商业人口的加入,“大半皆西南东北之人,弃其庐墓,捐其伯叔甥舅,以此逐什一之利也”〔45〕。汉口的交易业务中以“食盐、米、木材、棉花、布、药材六行最大”〔46〕。其中的米、棉花和布三项是当地主产品,也是该地区最主要的输出品。当然并非所有通过汉口交易的米、棉、布都是江汉平原所产,但江汉平原的产品在其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则无疑问〔47〕,江汉平原农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汉口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三)种类多样
市镇作为农产品的集散中心、加工场地和消费市场,其发展程度与周围地区的农业经济水平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不仅表现在市镇的经济规模上,也表现在市镇的种类方面。无论是不定期的易货贸易场所、固定集市,还是规模较大的商业城市,都是整个农村市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水稻生产、棉花种植及织布业的发展,江汉平原出现了一些各具特色的专业化市镇,如石首市之米市,即是以交易米粮为主要内容的专业集市,“米市在县西与长街相连,……水陆交通,商贾往来,人烟辐辏”〔48〕。云梦县也有米市,它在“县城东门外濠上,阛阓比栉,贸易米粮之所, 为往来大路”〔49〕。类似的专业市镇还有监利的陶郑巷(布市)〔50〕、枝江的董市口(棉花市)〔51〕等。这些专业市镇属于某一物品的固定交易场所,有的专业市镇属于某一特定物品的固定交易场所,有的专业市镇则以加工地的某一主要出产品为特色,成为农产品专业加工市镇,如监利的朱家河“居民多业织布”、常家湾“居民多织绢布”〔52〕。可惜这种专业市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无法与江南地区的类似市镇相比拟。有些专业市镇虽然并不以米、棉、布等为交易、加工内容,但其经营仍与农民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它表现出了农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这些专业市镇如江陵的筲箕洼市(交易竹木薪炭)〔53〕、沔阳的沙湖(鱼市)〔54〕、天门的岳口(药材市)〔55〕和广济的田镇(盐市)等。这些专业化市镇既是江汉平原农村经济商品化、专业化的产物,也是市镇内部生产、交换活动高度发展的结果。
四、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地区经济特征
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国性商品交流的日趋活跃,不同地区的商业活动具有不同的特色,这种特色在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方面也有所反映。如商人中有以汇兑银钱主要特色的山西票号商人,有以长途贩运为主要经营内容的徽商等;市镇发展中如江南地区不断涌现的专业市镇,靠丝织业的兴旺维持其繁荣。
江汉平原并没有产生如票商、徽商之类的著名商帮(不过票商,徽商参与了江汉平原的经济活动),也没有形成如江南地区震泽、盛泽之类的著名专业市镇,但该地特有的经济背景和地理环境决定了商人活动(包括本省、外省商人)和市镇发展有其自身的区域特色,在商人活动方面主要表现为易货贸易的形式,以输出初级农产品为主,这一特点又决定了市镇发展所带有的明显的运转贸易特征。
(一)易货贸易,以输出初级农产品为主
易货贸易是封建社会商品流通的普遍形式,并非江汉平原所特有,这里所以强调指出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指在所交易的货物中至少有一方,有时是双方的交易物均系江汉平原出产,产品又主要是初级农产品如米谷、棉花等,棉布也是江汉平原的大宗输出产品,但其生产多数情况下只是农闲时的副产品,专门以织布为业者不多。
交易中至少有一方的货物为江汉平原所产的商业活动主要表现在境内外的物资流通上,本地区的米谷、棉花、麻类等农产品多以初级产品形式输出。如前所述,徽商几乎垄断了江汉平原的米粮输出(当然不排除其他商帮的小额输出),而徽商同时又是著名的盐商,他们在船运淮盐至楚之后再载米粮顺江而下,以盐易米是徽商的重要营运内容之一,米谷又是江汉平原的头宗输出品,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徽商在江汉平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徽商所贩之盐主要以高价销往两湖地区,两湖地区输出稻谷所得几乎全部耗于高额盐价之中〔54〕,这就不能不影响江汉平原农业的扩大再生产,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其它初级农产品如棉、麻等类在小规模输出时尚不足以全面影响到农家经济,但当外商侵入、输出规模扩大,农户商品生产的比重加大,由于受到外商的盘剥,农民最终所获无几,这更无助于农业生产的进步。由此可见,历史上江汉平原初级农产品的输出对该地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极为不利。
交易中双方货物均为江汉平原产品的商业活动主要表现在境内物资交流方面,如米、棉、布的相向流通,集中产米地区和集中产棉地区相互调剂输出棉花、布匹和米粮,这种交流有利于各集中产区向更专业化的生产方向发展,促进农产品商品化。
(二)转运贸易
商业活动的易货贸易特点决定了商业活动的中心——市镇的转运贸易性质。转运贸易最明显地表现在属于区域经济中心的大市镇尤其是商业都市里,因为影响该地经济发展的大规模交易活动尤其是对境外的物资交流主要是通过这些大市镇进行,江汉平原的这类大市镇主要有两个,即地当荆江要隘的荆州——沙市(沙市原为荆州外埠)和位于江汉交汇处的汉口。沙市、汉口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的基础之上。
汉口的勃兴已在前文叙及,它所交易的货物从食盐、粮食、茶、棉布、食油等生活必需品到棉花、木材、药材、纸张等手工业原料及其制成品,种类繁多,来源广泛,而其主要交易又集中在食盐、米、木材、棉花、布、药材等六个行业方面。其中食盐、木材、药材是来自江汉平原境外的物资,米、棉花、布则主要为江汉平原本地所产,米、棉花来自农村,布也主要来自兼营副业的广大农户,不象江南地区多来自专业的机织户,也就是说,汉口商业贸易的发展依赖的是这些货物的转运贸易而不是象江南的许多市镇那样依靠较发达的专业化加工业。
国外经济势力入侵内地之后,汉口的转运贸易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从海外进口的洋货大部分由上海通过汉口转销中南、西南内地,中南、西南内地的初级产品又通过汉口被掠走〔55〕。沙市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它继汉口之后沦为开放口岸,成为国外经济势力在江汉谷地攫取初级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另一据点,以致沙市最发达的工业行业就是服务于转运贸易的运输业及其辅助产业(如棉花打包业)〔56〕。
汉口、沙市的中转贸易特点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江汉平原夹长江、汉水而立,东西北三面缘山,只有朝南临江可以作为向外交流的便利孔道,而正是借江、汉之利决定了该地水运的方便:循江而下可通皖赣吴越,逆江而上可达巴蜀云贵,南越洞庭入沅湘通两广,北沿汉水达汉中通西北。这样就自然形成转运内地货物出境、转运海外货物入境的贸易特点,该特点也无例外地表现在江汉平原较小的市镇中,江汉平原至少有半数以上的市镇位于水路要津以通货贿〔57〕。
江汉平原市镇发展的这种特点对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副作用,因为转运贸易的特点决定了这些市镇充其量不过是农产品的集散中心(包括某些较小的专业市镇如米市、花市亦然),而不具备或极少具备农产品的加工功能,这种情况反馈于农村其结果势必只能促进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却无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无助于农民突破单一种植业的樊篱,因而江汉平原始终以农业区见长,甚至解放后国家对该地区的投资也仍以发展农业为宗旨。〔58〕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已如上述,从中不难看出该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倚赖于农业的全面开发,水稻、棉花及其制成品的巨额增长不仅满足了当地人民的日常需要而且可以大量输出,于是吸引了以徽商、晋陕商为主的外地商人,同时也刺激了本地商人加入到境内外物资的营运行列之中,他们的活动不仅加速了江汉平原农产品的商品化过程,也把江汉平原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全国大市场之中,同时自然而然地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场的发展。正由于江汉平原市镇的发展建立在境内外商人营运米粮、棉花(布)的基础之上,兼以地处内陆与沿海货物中转的中心地理位置,因此江汉平原市镇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依靠转运贸易,该特点对促进市镇经济的继续繁荣极有好处,却不利于带动本地区农村经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这或许正是江汉平原当今形势下发展农村市镇所必须注意的关键所在。
注释:
〔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方舆汇编》卷1114。
〔2〕有关明清江汉平原人口增长的论述详见拙作《明清江汉平原的移民迁入与阶段性人口增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1期。
〔3〕嘉靖《沔阳志》卷8,《河防》。
〔4〕嘉靖《沔阳志》卷8,《河防》。
〔5〕《明史·河渠志》。
〔6〕《明会要·田赋》。
〔7〕光绪《荆州万城堤志》卷8,《堤防》。
〔8〕见拙作《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详析》,《中国农史》, 1991年第2期。
〔9〕见拙作《粮棉兼重、 各业发展一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第3期。
〔10〕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1〕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0。
〔12〕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23。
〔13〕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4〕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风俗》。
〔15〕光绪《孝感县志·土物志》。
〔16〕乾隆《江陵县志·物产》。其中“抱贸”取《诗经》“抱布贸丝”之意。
〔17〕同治《监利县志·物产》。
〔18〕嘉庆《汉阳县志·物产》。
〔19〕同治《汉川县志·物产》。
〔20〕同治《德阳县志·物产》。
〔21〕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商务志》。
〔22〕同治《汉川县志·物产》。
〔23〕同治《枝江县志·物产》。
〔24〕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21页。
〔25〕光绪《咸宁县志》卷1,《风俗》。
〔26〕光绪《黄安县乡土志》。
〔27〕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8〕同治《江夏县志·风俗》。
〔29〕同治《江夏县志·风俗》。
〔30〕同治《监利县志·物产》。
〔31〕乾隆《江陵县志》卷9,《建置六·级镇》。
〔32〕同治《长乐县志》卷12,《风俗志》。
〔33〕乾隆《宜昌府志》卷11,《风俗》。
〔34〕参见拙作《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35〕光绪《荆州府志》卷4,《地理志·乡镇》。
〔36〕同治《石首县志》卷2,《营建志》。
〔37〕同治《监利县志》卷1,《古迹》。
〔38〕顺治《黄梅县志》卷2,《市镇》。
〔39〕康熙《云梦县志》卷1,《市镇》。
〔40〕光绪《黄冈县志》卷3,《乡镇》。 上三例均转引自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41〕同治《石首县志》卷2,《营建志》。
〔42〕同治《公安县志》卷2,《营建志》。
〔43〕光绪《荆州府志》卷4,《地理志四·乡镇》。
〔44〕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45〕吕寅东:《夏口县志》卷13,《商务志》。
〔46〕晏斯盛:《请设商社疏》,《清经世文编》卷40。
〔47〕参见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论述》,《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
〔48〕乾隆《石首县志》卷1,《市集》。
〔49〕道光《云梦县志》卷1,《市镇》。
〔50〕光绪《荆州府志》卷4,《地理·乡镇》。
〔51〕同治《枝江县志·物产》。
〔52〕同治《监利县志》卷1,《古迹》。
〔53〕乾隆《江陵县志》卷9,《建置六·乡镇》。
〔54〕光绪《沔阳州志》卷3,《建置》。
〔55〕道光《天门县志·物产》。
〔56〕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57〕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第70—71页,中华书局,1989。
〔58〕徐凯希:《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第4期。
〔59〕见拙作《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
〔60〕徐林茂:《发展小城镇带动大农村》,《湖北日报》, 1988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