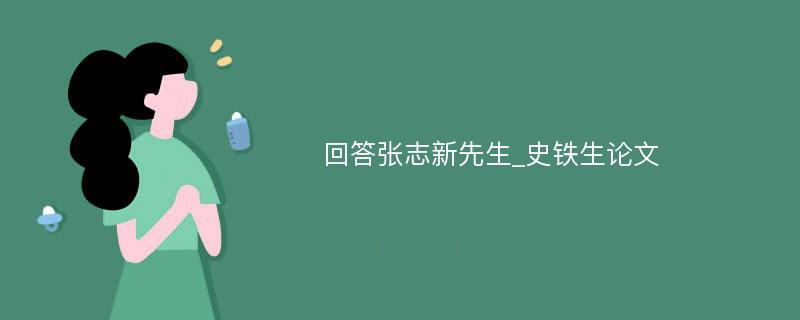
答张直心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答张直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我主编的《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以下简称《心态史》)出版后,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既有樊骏、古远清、童庆炳等先生从鼓励后学的角度给予肯定,也有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张直心先生,已就该书发表了三篇专文,第一篇见于2000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题目是《倾斜的天平》;第二篇见于2000年第四期《学术界》,题目为《评〈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第三篇即发表于《文艺争鸣》2001年第五期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张直心先生表示:由于《心态史》的“优长已有一些识者指出”,故而他的几篇文章是专门针砭不足的。这是很可取的,相信无论对于读者还是对于我们作者,都是大有裨益的。稍觉遗憾的是,张先生的这三篇文章,内容大致相同,特别是第三文与第二文,除了题目及个别字句的改动之外,几乎是同一篇文章的重发。读了这几篇文章,深感张先生是抓住了《心态史》的某些重要不足的,当然,有些问题也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念及本书已有包括张先生在内的学者们发表的十多篇不同看法的文章,已足可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徒添文坛的躁乱,也就没打算再就此写什么文章了。
首先,我同意张先生关于该书“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批评。张先生的意思是:《心态史》既然是国家课题,自然就应该做出国家级的水平。国家级的标准虽然不太好说,但按我个人的想法,至少应做到自己满意,而就该书的现状来看,是连我自己也很不满意的。第一,虽然尽力从作家心态的多面性、复杂性、变异性以及政治、功利、宗派之类心态入手,探讨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经验,但在理论方面,仍有很大欠缺。究其原因,除了张先生所说的我们的“无力”之外,也还与另外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有关:一是限于客观条件,有些问题毕竟还是有所顾忌的;二是其中涉及许多在世的作家,心理分析的非实证性是很容易招致这样那样的麻烦的。事实上,有几家出版社,当初就是因上述担心,而拒绝接受这部书稿的。所以,我有时想:目前也许还不是完成这样一部著作的时候。正是鉴于该课题存在的风险,我当初对作者们的要求是:首先保证资料的客观性、丰富性,这样,即使缺乏理论深度,至少还可以因其资料性而有一定价值,还可以为他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点儿基础。第二,我虽在绪论中谈到作家的心态构成与主体的生理条件、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按照逻辑脉绪,其“心态史”亦应兼及三方面展开,而我们亦远远没有做到。虽在论及某一作家(如胡风、林语堂、谢冰心等)尽可能地有所顾及,但主要还是按社会文化心理的线索展开的。因为在实际写作过程中才发现,作家生理及自然环境两个方面,似乎本来就无“史”可言。叫人怀疑,“心态史”这一“元命题”本身,似乎就隐含着难以切近写作目标的无奈。故而从实际内容看,这部著作称之为《20世纪中国作家社会心态史》或许更为贴切,由此也许更可以看出本书的“盛名难副”了。还可以提及的一点是:我曾经收到一位学者的来信,批评我们忽视了对少数民族作家心态的分析,这自然亦可以说明《心态史》的“盛名难副”了。
我们之所以有勇气完成这一课题,亦如《后记》及《绪论》中提到的:中国已有大批现当代文学史、文艺思潮史问世,但尚少从史的角度,专注于作家特别是作家心灵历程的探讨,这至少是可以进一步尝试的,是有利于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开拓的。另一个想法是:“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这一命题,自觉还是有一定新意的,以此命题的著作,毕竟也还没有出现过。由此入手,可以弥补文学史研究的某些不足。比如中国的“文革”时期,由于正常的文学创作几近停止,通常的文学史似乎是没多少话好说的,故而大多较为简略,而在本书中,则恰是作为重点进行充分论述的。这样一部书稿,虽然还存在很多缺点,但我想,既然文学作品史、文艺思潮史可以有多种,这样的作家心态史,也是可以另出几种的。我们完成这部尝试之作的另一目的也正是在于:希望能够增强人们对于这一研究思路的兴趣,并期待着真正高水平的“作家心态史”的问世。
另有一些问题,愿提出来与张先生商讨。
一、张先生批评《心态史》“盛名难副”的第二重意思是:“作者惯于材料平面的罗列排比、不无简单化的分门别类,却拙于分析,更无力纵深地‘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且概念抵牾,涵义不清,思想内哄,空泛偏颇,有着庸俗社会学的眼光等等。如上所述,在理论分析方面,《心态史》确有很大欠缺,但如张先生这样几乎是全盘否定式的批评,似也有失学术公正。张先生的具体批评意见是:《心态史》对作家心态类型的归类失当,导致“复杂多元的作家心态”因其“机械解析,剪不断,理更乱”。不知张先生想过没有,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除非你避开分类,只要分类,就必然会导致研究对象被“解析”的问题,因为每个事物都是复杂的、都是存在多面性的,何况是更为复杂且多变的作家心态呢。张先生这儿的批评,实际上涉及到至少从康德开始就为西方许多哲学家大为伤脑筋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否有效?康德当年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至少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行,所以才寄希望于未来,才把他那本浅释《纯粹理性批判》的著作定名为《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而当今的情况是:历史虽又前进了两个多世纪,不仅仍未出现科学的形而上学,前景之渺茫甚至已使许多思想家为之绝望,所以才有了“解构主义”之类哲学思潮的产生。而概括归纳问题的方法,正是基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其局限也就是注定的了。但在人类尚未找到更为高级更为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情况下,归纳分类的方法,在许多方面的研究中恐怕还是无法废除的。比如尽管苏东坡、辛弃疾的词中虽已不乏《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清平乐·茅檐低小》之类浅唱低吟之作,即便在《念奴娇·大江东去》、《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之类激昂之作中,也不无悲伤低沉意绪,但至今似乎还没人怀疑苏、辛在主导倾向上是“豪放派”的定论。《心态史》中将作家心态概括为“政治型”、“人文型”、“超然型”及“自责式”、“感恩式”之类“文革心态”类型,如同《心态史》行文中曾特别强调的,也只是依据作家的主导心理动机及创作活动的外在表现相对而言的。对此,我想张先生是应该理解的。张先生在批评文章中建议将“人文型心态”改为“自由主义”,因为前者“涵括面太大”,后者才更为贴切,而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涵括面不是更大吗?比如鲁迅可谓中国作家中最崇尚自由人格、最富有自由精神的作家之一,胡适也通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志摩自己即标举自由主义,那么,是否可以将鲁迅、胡适、徐志摩等人归之为同一心态类型呢?而且,就算可以,那么,“自由主义”,不仍是一种分类意义的概括吗?用之于具体作家,不也存在着“复杂多元的作家心态被机械解析”“剪不断,理还乱”的弊端吗?
张先生所批评的“盛名难副”,还有一重意思是:这本来是一本水平不高的著作,其封底竟赫然印着“国内第一部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入手,分析描述20世纪中国作家的心态类型”的专著。出版社如此设计,固然不无“广告”用意,但就本书选题与整体框架而言,说是“第一部”,好像也无可非议。此外,张先生也应该明白,这儿的“第一”,并不等于“最好”,只是说明时间的先后,当然也就不具“学术史定位”的意义了。至于张先生据此而推导出我们缺乏对前人成就的了解,而似乎是在试图抢夺“作家心态研究”的“拓荒者”这把交椅,那可就更是误解了。我在绪论中已明确谈到:“目前,有不少研究者已开始了对作家心态的关注,且已出现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成果。”并特别举例赞扬了李辉对巴金、周扬、冯雪峰等人的心态剖析,以及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等。另如张先生提到的吴俊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王晓明的《漩涡与激流》、孙郁的《百年苦梦》、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等,还有张先生没有提到的凌宇的《沈从文传》、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等,虽然未能一一列出,实际上都是曾经被我指定为撰写者的必读参考书的。《心态史》的水平差,自是能力问题;但说我们缺乏对国内已有同类成果的了解,涉及的就是学术态度问题了,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了。
二、张先生批评《心态史》“貌做‘宽容’、却试图藉此掩护绝不宽容的‘左’的观念之机心”(《倾斜的天平》)。我不否认本书存在着对某些作家心理判断失当的缺憾,但以此定论,恐也不符合《心态史》的实际。张先生在他的几篇文章中,特别表示不满于我们对浩然的《艳阳天》的肯定,以及对浩然在“文革”中表现的宽容。我至今仍认为,浩然的《艳阳天》虽然存在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一部有相当艺术成就的作品,说他是在“积极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也并不为过。香港《亚州周刊》组织海峡两岸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14位学者、作家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艳阳天》名列第43位,大概也不是毫无道理。至于“文革”期间浩然与老舍之死的牵连,张直心先生分析有三种可能:浩然有可能是老舍的保护者;也有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甚至有可能对老舍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浩然当时的身份,他对老舍之死客观上是应负一定责任的,我们相信他自己关于保护过老舍的说法,只是就他当时的主观意愿而言的,这与张直心先生的分析似乎也并不矛盾。另如他对杨沫的保护,则是有杨沫本人当时的日记为证的。此外,与“文革”中同样得势的其他某些文人相比,浩然毕竟是没有多少可实证的劣迹的。按张先生的逻辑,我们把“文革”中的浩然说成是“恶魔”,说成是“四人帮”的走卒,就不“左”了,就正确了?
张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证明《心态史》“左”的另一些例子,有的则纯是由于他对有关章节的阅读不够仔细所致。比如批评我们赞扬了“文革”后复出的丁玲、刘绍棠“着力于歌颂党、歌颂人民”的心态。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先是客观地描述了这几位作家复出之后的言论,既而指出了其对创作的负面影响。不知张先生注意没注意到《心态史》第568页上的这样一些文字:“文革”后复出的某些作家“不曾有过当年的鲁迅、当代的巴金那样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自我省察意识,亦缺乏欧洲人那样一种对自己的文化、社会、个体状况的复杂性、暧昧性、局限性的敏锐把握。饱经人生磨难的丁玲、公木、刘绍棠等人,就很少这样一种个体性、精神性的反思,他们的作品中虽然不乏历史的凝重,但缺乏卢梭、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一种震撼人心的灵魂拷问。”话虽说得比较平和,但对丁玲等人的心态是不是出于对“左”的机心而一味予以赞扬,不是很清楚吗?
更为有意思的是:与张先生观点截然相反的是,在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人不满于对周作人的分析,认为这是在“为汉奸翻案”,这不是“左”,大概要算是可怕的“右”了。在这样的政治性批评面前,又叫人如何是好呢?这也进一步说明,一部内容复杂的《心态史》的写作,的确是面临着极大风险的。
此外,张先生十分不满于《心态史》中存在着“上纲上线”式的“政治批判”,具体所指是:在评析萧红、沈从文时用了政治的或阶级斗争的视角,强调应进行“学理探讨”。据我理解,“学理探讨”的要则是:实事求是地讲道理,而不是随意的谩骂,或是用心不良的讥讽,更不是无中生有地乱扣帽子。《心态史》中的个别用语,也许存在不当;某些见解,也还不够出新,但自信还不是仅以“政治批判”而代替学理探讨的。比如对于萧红、沈从文,甚至胡适、徐志摩、梁实秋这样的作家,都是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肯定的。而且,诸如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生活的本来构成,恐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很难彻底回避的。如有涉及,便被视为“政治批判”,恐也难以服人。张先生强调“学理探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目前的学术研究中(自然也包括我们的《心态史》在内),在讲究“学理”方面,还是存在很大欠缺的,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进一步反思,这或许也该包括张先生本人在内。比如,张先生的批评文字中,不乏充满“火药味”的用语,讥讽的笔调,以及“左”的政治帽子之类,这本身恐怕也是不够“学理”的吧?
三、张先生批评《心态史》中某些资料的使用失当,既有有道理的一面,也有值得申明之处。如“对邵洵美称其负责接待萧伯纳并出席了那次宴会这一说法未加辨析的引用,疏忽了当事人的证言必须经过验证。事实上这一史料显然有误已有倪墨炎等识者指出。”张先生的文意,除说明这则史料不可信之外,同时似乎也在暗指我们的写作态度成问题,居然连学术界早已澄清的史料也了无所知,仍在不负责任地胡乱引用,这后一层意思就缺乏说服力了。这则史料源自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狱里狱外》,当时考虑到贾植芳先生既是熟知那个时代的老人,也是一位负责任的令人敬重的学者,既然贾先生未加质疑,所以也就放心地使用了。至于倪墨炎先生关于这一史料的考证文章《邵洵美请过鲁迅萧伯纳吃饭吗》发表于1999年2月24日《中华读书报》,而《心态史》已于1998年11月出版,在写作过程中,显然是不可能看到倪先生的考证的。我想,张先生关于这类问题的批评,也还是应该实事求是些才好。另如废名,张先生以其存在“热狂心态”为由批评我们赞誉了他建国后的真诚、潇洒及新时代再度唤起了创作热情等。众所周知,废名的个性确有怪异之处,但是否因此就可以把建国后曾出任过吉林大学中文系主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也有过一些有价值的著述的废名简单地判定为“一个颇具病态心理学意味的个案”,予以全盘否定呢?在目前深得好评的洪子诚先生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也这样肯定过50年代中期的废名:由于受到“百花齐放”浪潮的感染,废名曾经“有过宏大的小说创作规划,准备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写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经历的道路,另一部以个人的经历,‘反映江西、湖北从大革命开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解放后土改、农业合作化为止社会面貌的变化’”(参见该书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这不也正可以说明废名确曾有过“欣逢盛世”之感吗?这难道也都可以被视为是“病态心理”的表现吗?
四、张先生在《学术界》发表的文章中,批评《心态史》“632、633页论及史铁生残疾心态时部分抄袭了”《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42页的吴俊先生《当代西绪福斯神话》一文。“部分抄袭”,且有确凿的两个面码,这自然是不容置疑的了,这样大面积的抄袭,也足见《心态史》问题之严重了。读了张先生的文章,我当时十分震惊,遂立即找来《文学评论》仔细查对,情况如下:《心态史》这两页中论及史铁生的篇幅大约有600字左右,内容是:作者首先直接摘引了史铁生本人在《我与地坛》一文中关于“发自生命本质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一段话,据此引申出其作品中贯穿的着一种宗教意味的“壮烈理想”的结论,然后结合作者的生理病残,进行了具体论述,继而又征引了杨晓敏先生的相关论述及史铁生的有关作品作为参证。其主体内容,明显可见是作者在参阅其它相关资料基础上进行的梳理与概括,与吴俊先生的论述并不完全相同。只是在引证史铁生的短篇小说《命若琴弦》的内容时使用的:那位老瞎子,“在生命即将终了时,仍将那张无字的白纸——一个虚幻的希望——当作生命的真实的希望传授给年轻的小瞎子”一语与吴俊先生对这篇小说内容的描述近似。如果张先生所批评的“部分抄袭”指的就是这句话,那么,不论事情的原委如何,我都愿意向吴俊先生及读者致歉。因为毕竟有吴俊先生相近的文意概括在先,不排除执笔者有所借鉴的可能,而作为主编,未能在审改时发现,责任完全在我。
张先生在《文艺争鸣》发表的文章中,再次批评《心态史》抄袭了《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42页吴俊先生文章中的内容,只是不知自觉证据不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次未提《心态史》632、633页,而是另指绪论中的“主体生理机制与作家心态”一节。文中说得尚算委婉,认为该节在谈及史铁生残疾心态时,“也有一段”与吴俊先生文章的“类似论述,想是不约而同,否则理应注明出处”,而在文末则径直注明“抄袭”。同一本书,有两处同时抄袭了《文学评论》的同一页,问题似乎就更严重了。为了弄清是非,兹将张先生所说的《心态史》那一节中关于史铁生的所有文字照录如下:
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坛上,史铁生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深邃意味,特别是在他的《命若琴弦》、《山顶上的传说》、《原罪》、《我之舞》之类作品中,充满了一种对于人生苦难与不幸的冷静思索,以及对命运的探问与理解,这显然也是与作家本人的残疾有关的。在散文《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写道:在病疾的郁闷岁月里,每当他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独处北京地坛公园的一角,望着远处笑闹嬉乐的少男少女时,心里便想到:“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有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命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在一个健康的正常人那儿,怕是很难产生这样一种对于世界本原构成与人生苦难的超然体悟的,也是很难写出史铁生笔下那样一些充满人生哲思意味的作品的。
这段文字是由我本人执笔的,又经仔细查对,我实在找不出张先生所说的“抄袭”了或者叫“类似”、或者叫“不约而同”于吴俊先生文章的哪“一段”话。其实,上述这段文字,只不过是用来说明作家生理机制与创作心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资料,除了转述或直接引用了史铁生《我与地坛》的大段原文外,并没有更多的理论分析。吴俊先生的那篇文章发表于1989年,而此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尚未问世(《我与地坛》初写于1989年5月,改定于1990年1月,初刊于《上海文学》1991年第5期),故而我所转述或直接引述的《我与地坛》的文字,与吴俊先生的文章不可能有什么牵扯。其余寥寥几句中简略谈及的史铁生小说中追问命运的意蕴与其生理残疾之间的关系,大概是对史铁生及其作品稍有了解的人,特别是读过《我与地坛》及另一些相关散文的人,很容易就能想到的。我自信也还不至于低下到连这样简单的意思也想不出、写不出的程度,还要靠抄袭别人才行。抄袭,这无疑是学术界最为令人痛恨的丑恶现象,用之于批评他人,也往往是颇具毁灭性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是非争端的。正因如此,我想,在判定别人“抄袭”的时候,还是应慎重些、实事求是些才好。
尽管张直心先生的批评文章中存在上述一些值得商讨的问题,最后,我还是要再次感谢张先生,他的批评,毕竟有值得我们正确对待,认真反思的地方。同时,这样一部涉及到大量资料,在前人已有大量成果基础上进行的尝试之作,肯定也还存在其它诸多疏漏与不足,亦望读者给予进一步批评指正。
标签:史铁生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艳阳天论文; 作家论文; 我与地坛论文; 吴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