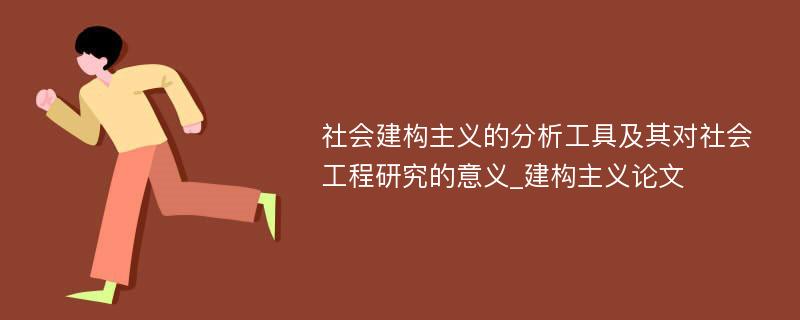
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及其对社会工程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其对论文,意义论文,建构主义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572(2006)03—0012—08
对于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国内外学者做了各种概括和总结。Wiebe E.Bijker和John Law在1992出版的《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一书中认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三种,“对技术的社会研究至少有三种不同、有时是交叉的和富有结果的方式:第一,有一种系统理论的观点,是Hughes在1983年在研究技术历史的过程中开发出来的。”[1](P12) “第二,角色——网络的理论。这是Callon在1980年第一次开发出来的。这种理论在于用一种中性的语言来描述那些称之为‘异质的工程师’的行为。这个思想认为,异质工程师所建构的这个技术网络包含技术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等各种因素。……但如何界定机械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这种研究的问题。”[1](P12—13) “最后,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研究。这种研究企图利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技术案例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科学社会学已经认为,知识是社会的建构而不是自然之镜(或多或少有所缺陷)的反映。……因此科学知识——包括技术和技术实践——是在社会建构和商谈过程中构建的,这个过程通常被看成是由参与者的社会利益所驱动的。”[1](P13)
一、技术的社会建构(社会形成)对社会工程研究的意义
Wiebe E ·Bijker 和John Law 在1992 年出版的《Shaping Technology /Building Society: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The MIT Press)》中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有力的分析工具。他说,“最后,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研究。这种研究企图利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技术案例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科学社会学已经认为,知识是社会的建构而不是自然之镜(或多或少有所缺陷)的反映。……因此科学知识——包括技术和技术实践——是在社会建构和商谈过程中构建的,这个过程通常被看成是由参与者的社会利益所驱动的。”[1](P13)
Philip Brey进一步指出, 在技术研究中最具有鲜明特色的分析工具就是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strong social constructivism)。这种研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密切相关,包括SCOT研究,以及像H.M.Collins和Steve Woolgar等学者的研究。这种研究绝对地信奉对称性原则,因此避免任何在分析中论及技术的真实性质,完全用社会行为解释技术的变革。特别是用不同角色或社会群体的解释、协商和决议来解释技术变革。技术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建构,一个被固定了的技术只能被社会因素(包括其他的被社会地建构了的实体)所解释,技术本身无所谓“性质”、“力量”、“功能”。[2]
我国学者也同意对称性原则作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但却认为对称性原则本身就是社会建构主义。[3]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建构主义方法,主要受用建构主义方法研究科学知识的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影响。SSK广泛地使用了历史的和科学社会学的方法,认为所有的知识和论断都要被看作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反映自然的结果,它不是惟一地由自然现象是什么而给予科学家的知识,而总是有不止一种解释。像SSK一样,SST将技术纳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中,要寻找事例来说明技术可以以不止一种方式来设计,在各种不同技术可能性中存在着选择:他们还要解释某一种设计或人工制造物的成功很难说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成型(pattern)或形成(shape)于特定的选择环境。技术和技术实践是在社会建构和谈判中被建造起来的,这经常被看作是由各种参与者的社会利益驱动的过程,特别关心冲突的利益群体是如何达到问题的解决的。
平奇和比杰克还通过自行车发展的历史对此进行了有名的案例分析:自行车最初的轮子很大,它有利于提高速度,作为理想的运动工具;但由于骑在这样的车上人的重心会很高,所以就变得极不安全,作为大众普遍使用交通工具就受到了限制。这样,在自行车作为运动工具和交通工具之间就出现了矛盾。经过19年之久的改进发展,自行车最后变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基本的模型,双轮变小,安全性提高,主要行使交通工具的职能。而这个过程就是用户造就的,从而再现了非决定的、多方向性的、在塑造技术的群体之间和之中不断地协商和再协商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哪些问题与人工制造物及其意义相关,由社会群体所决定。一个问题甚至被确定为问题,仅当存在着这么一个群体,它将其发起为一个问题。所以,在SST看来, 是社会群体将意义赋予技术,认为社会环境塑造人工制品的技术特征。其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技术的人工制品是向社会分析开放的,换句话说,社会因素进入了这一解释之中。这种方法被看作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社会学,或者用SCOT即“技术的社会建构”来表达。
Wiebe E.Bijker和John Law在1992年出版的《Shaping Technology /Building Society 》中从技术社会学的角度描述了社会因素对技术进行社会建构的意义:“我们的技术反映我们的社会。技术再生产并包含着专业的、技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的相互渗透的复杂性。……‘纯的’技术是没有意义的。技术总是包含着各种因素的折衷。无论技艺被何时设计或建构出来,政治、经济、资源强度的理论、关于美与丑的观念、专业倾向、嗜好和技能、设计工具、可用的原材料、关于自然环境的活动的理论,——所有这些都被融入其中。……本书的基本主题就是,不论成功的技术还是失败的技术,它们总是被一系列不同的要素所建构的。我们想说的就是,技术是被建构的。它们是被一系列异质要素所建构的。”[1](P4)
高强度荧光灯就是一个多家公司协商成功的案例。Wiebe E.Bijker 和John Law在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通过对荧光灯形成过程的社会学分析指出,“我认为,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荧光灯是由各种各样的相关的社会群体连续不断地改造和重新设计的。”[1](P75) 在荧光灯的发明和使用过程中,Mazda公司、电业公司、零件制造商、顾客、政府等在其产生的过程中都各自发挥作用。其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就是Mazda公司和电业公司的决定性作用。 二者虽然各自的目的不一样:前者是售灯,而后者是售电,但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通过展示不同的相关社会群体是如何向其添加不同的影响来说明这个道理,不同的相关社会群体组成了三种在1938—1942年期间不同的制成品,即:“彩色荧光灯”、“高效荧光灯”和“高强度荧光灯”。前两者在Mazda 公司和电业公司之间的“争论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种制成品是作为这场争论的终结而出现的。最早出现的是彩色荧光灯,这种‘彩色荧光灯’对于作为相关社会群体的电业公司和Mazda公司并无两样。这一点不足为奇, 因为电业公司关于荧光灯的知识是相对有限的,而且几乎都是以Mazda公司向其所提供的知识作为基础的。但是在Mazda公司推出高效荧光灯之后的早期,电业公司真正有了危机感,担心这种高效荧光灯的出现会减少自己对于电力的销售额。因此,一场在两种荧光灯之间的争议开始了。电业公司极力宣传高效的荧光灯是不存在的,以此误导公众,而Mazda 公司极力推崇其高效荧光灯。最终,为了共同的利益,二者之间举行了一次谈判,结果,两种荧光灯都被禁用,而高强度荧光灯作为折中的结果出现。
此外,还有一种称之为社会形成(social shaping)研究(如Wackenzie &wajman,1985a;1985b;Wackenzie,1990)。社会形成研究在社会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之间保持既定的均衡,它也充分承认社会因素在技术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并不否定非社会因素在技术形成中的作用,尽管这些非社会因素在形成技术的性质过程中也依存于一定的社会氛围。因为技术是社会形成的,技术的这些性质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功能,而且技术的这些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能被归因于社会的偏好或政治学,并被整合(built into)或体现(edbodied by)在这些技术之中。[2]
我国学者也认为,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技术史学家托马斯·胡斯,用“系统”的术语来对待技术,力图描述大型技术系统是如何生长的。胡斯的观点是,成功的企业家是那些善于用系统的观点看问题的人,不仅要考虑其创新的技术特征,而且要思考创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内涵和环境,因此这种方法注重于对不同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物质的人工制品、制度和他们的环境,然后提供技术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方面的整合性,并使宏观的和微观的分析联系起来。胡斯也用爱迪生的发明活动中的社会关联性作为案例分析:爱迪生的发明问题同时是经济的(在价格上电如何能与气竞争)、政治的(如何说服政客们同意发展供电系统)、技术的(通过缩短导线、减少电流和增加电压来使传输电力的成本最小化)、也是科学的(怎样发现高阻抗的白热灯丝),爱迪生成功地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由此也表明他作为一个系统建造者的成功,并且也说明了胡斯所提出的“网是无缝的”——社会与技术和经济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3]
二、角色——网络理论及其对社会工程研究的意义
“Wiebe E.Bijker 和John Law 在1992 年出版的《Shaping Technology /Building Society: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The MIT Press)》中认为,角色—网络的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是社会建构主义有影响的分析工具之一。“这是Callon在1980年第一次开发出来的。这种理论在于用一种中性的语言来描述那些称之为‘异质的工程师’的行为。这个思想认为,异质工程师所建构的这个技术网络包含技术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等各种因素。乍看起来,角色网络理论与Hughes的系统理论很相象。但与Hughes的系统理论不同的是,Callon和他的合作者强调构成角色网络理论的要素(包括企业家)在构成网络的同时,也在这个网络中被建构和被生成。这就意味着,Callon及其合作者避免对社会的、经济的或技术的要素的背景做假设:这些背景本身也在建构网络的过程中被建构,这也是Law和Callon贡献给这个论文集的观点。它也意味着他们对于人、企业或机器等自然出现的范畴不做一般性的假设。……但如何界定机械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这种研究的问题。”[1](P12—13)
对于角色—网络的理论,Wiebe E.Bijker 等人有一个经典的概括:“我们的技术反映我们的社会。技术再生产并包含着专业的、技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的相互渗透的复杂性。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责技术,我们也不是提出某种技术的导向。我们并不想说,‘如果技术是纯粹的技术,那该有多好。’相反,我们将要说的是,全部技术都是构成我们社会的各种复杂要素所建构的并反映着这些要素;运行得好的技术与那些失败的技术并没有什么不同。‘纯的’技术是没有意义的。技术总是包含着各种因素的折中。无论技艺被何时设计或建构出来,政治、经济、资源强度的理论、关于美与丑的观念、专业倾向、嗜好和技能、设计工具、可用的原材料、关于自然环境的活动的理论,——所有这些都被熔入其中。……本书的基本主题就是,不论成功的技术还是失败的技术,它们总是被一系列不同的要素所建构的。我们想说的就是,技术是被建构的。它们被一系列异质要素所建构的(technologies,we are saying,areshaping.they are shaped by a range of heterogeneous factors)。也可以这样说,技术也可以是别样的(they mightbeen otherwise)。”[1](P4)
这是国内外学者得到高度共识的说法。Philip Brey认为, 这种分析工具有时被简单地称之为建构主义(没有‘社会的’这个形容词),是第三种有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认为技术的和科学的对象看成角色—网络的建构的结果。
Philip Brey在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一文中指出,第三种方法是参与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迈克尔·卡隆(Michel Callon)用一个高度抽象的词“参与者”(actors)来把科学技术和其他范畴的东西归入一类。参与者是多样性的统一体,他们构成了一个网络,创造出一个协同的参与者世界,即各种要素在结合为网络的同时也塑造了网络。这意味着他们不同意有技术的因素和社会的经济的背景之区分,或者说要打破人的参与者与自然现象的区别,他们都被看作是参与者网络的要素,因此力图要建造一个活跃的语义学词汇来平行地谈论人和机器,不应该将有生命的同无生命的、个人的同组织的区分开来。参与者将塑造和支持技术的目标。卡隆相信,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部的和内部的(即社会的/技术的)二元区分。
这种角色—网络是由人类的行为者和自然及技术现象所构成的。角色—网络理论家利用归纳出来的对称原理,技术实体是由社会的、自然的或技术的等异质要素所构成的,这些要素都参与了技术的定型过程,这些要素在技术的定型过程中都发挥相同解释力的作用(Callon,1987;Latour,1987;Callon & Latour,1992)。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因其偏好社会因素,如社会群体和解释过程等而受到批评,在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活动的解释中,自然的或技术的因素,以及自然力和技术设计都被排除在解释之中。角色—网络理论把技术设计和自然力也看成是网络中的角色(或称“actants”),技术的或科学对象正是凭借这种网络而被定型。 通过对角色网络的分析,任何实体都被看成是一个先验的建构,但实体本身并不是社会地建构,因为技术的定型并不只是社会因素的结果。[2]
我国学者也很重视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社会建构主义分析工具的重要意义。[3,5,6] 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的含义有三:一是微观网络, 指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实验者、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环境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行动者(实验者)与其他因素相互关联,构成了实验语境,也就是一个行动者—网络。这个行动者—网络系统不断构造自然,不断生产新的科学知识;二是宏观网络,指实验室与其之外的社会的关联,形成社会语境。在宏观网络中,行动者不仅是科学家,也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这些行动者共同编织成自然—社会之网络,三是微观网络和宏观网络是双向互动的。实验室通过建构进而塑造社会,即把科学知识社会化;社会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支撑和资助实验室。他们认为,科学论的研究不应停留在对已经形成的“科学文本”的哲学考察,而应对正在建构中的“科学实践”即实验室活动进行考察。他们由对科学的哲学建构走向了社会建构,由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自然、实验室走向了自然、实验室、社会的语境化建构。总之,网络方法强调了如下几点:(1)牵涉到解决技术问题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2)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其作用的方式是复杂的;(3)解决技术问题的方式是在冲突中形成的。
在对法国巴斯德微生物学实验室扩展与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之间共变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拉图尔展示了“行动者网络”是如何被成功地建立的过程。在对巴斯德的案例中,拉图尔探讨的是一种“社会背景”与科学的“内容”尚未分化的场域。巴斯德在1881年之前几年间,利用他的微生物实验室成功地介入了炭疽病的研究,并拯救了法国的牛、羊和农民。巴斯德首先把引起牲畜大量死亡的疾病定义为一种细菌传染病,并从农场带回细菌病原体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通过控制温度成功地培养出了炭疽疫苗。这时,人和炭疽杆菌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转移,巴斯德的实验室成为更有力的一方。他的实验室成了那些要驱除炭疽病灾难的潜在盟友的必经点(obligatory point of passage)。 “如果你们想解决你们的炭疽病问题,你们必须首先通过我的实验室”,因为,“炭疽病现在就在高等师范学院”。同时,为了招募更多的盟员,使他的炭疽疫苗得到农民的承认,即扩张他的“网络”,因此,他必须和农民的代表协商把农场转变成实验室。1881年5 月他和这次“农场实验”的组织者达成妥协,把农场的足够多的特征改变成类似于实验室的条件,以便在原先已取得的力量平衡的状态下进行这次公开的实验。他们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在巴斯德的“网络”里,炭疽杆菌、农民、兽医、内科医生,都是“行动者”,这些“行动者”联合在一起,共同建构了炭疽疫苗这样的技术。由此可见,科学的“与境”(context)和“内容”(content)不再被明确地区分开来,知识和技术随一个行动网络而出现、扩展和加强;社会结构也不再是构造科学家行动的原因,而是先前存在的各种社会网络(包括非科学网络)及其在一个论争场中的冲突关联的结果。拉图尔所使用的“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非人(nonhuman)的存在和力量:“我使用‘actor’,‘agent’,或‘actant’并不对他们可能是谁和他们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们可以是任何东西——个人的(‘彼特’)或集体的(‘民众’),比喻的(拟人或拟兽)或非比喻的(‘灾难’)。”[6]
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车案例”(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一文中提供了另一个著名案例。[7] 1973年,EDF(Electricite de F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 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 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 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有的学者指出,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 卡龙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 “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龙看来, “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 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三、修辞学方法及其对社会工程研究的意义
在Sheila Jasnoff、Gerald E.Markle、James C.Petersen和Trevor Pinch等人合著的Handboo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age publications1995)一书中,有几处提到修辞学方法论及其相关内容。例如,第15章中的“话语、修辞学与反思性”,第19章中的“科学争论”等。
修辞学方法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国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凯(M.Malkay)的研究方法。它是在科学哲学的反实证主义、现象主义等哲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顿传统方法论的地方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据传统社会学的方法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考察与分析。马凯在对科学知识作社会文化的解释时,提出了“科学社会修辞学”这个新术语,其含义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家行为并不能用统一的规范来说明,而只能以科学家各自的利益和目标来说明。也就是说,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的行为并不是依据科学语言来说明的,而是依据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社会语言或文化资源来说明的;科学规范不是用默顿所说的科学体制来保证的,而是用科学的文化资源来说明的。在他看来,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客观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学知识是经科学家磋商(negotiation)建立起来的。磋商就是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之间运用共同的文化资源提供的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ulary)进行的协商和交流。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并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马凯的社会修辞学就是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科学家的行为规范要在其社会语境中得到说明。科学知识的意义以及它产生的过程都要用社会修辞学来说明。这种社会修辞学方法说到底就是一种社会语境分析方法。”[5]
Paul Ernest在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就曾经指出,“从流行的观点看,采纳商谈作为基本旗帜的思想领域正在增加,社会科学尤其如此。例如,young(1987)追随Goffman,Berger,Luckmann以及其他人, 提出了一种把商谈作为基础的现象学理论。另一个例子就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本体论的核心……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像Gergen和Harrè一样,人类的基本现实,就是商谈(Shotter1991a,13)。[8](P162)
其实,自古希腊时期,以书写对话的形式进行商谈就在哲学和认识论中被使用了。苏格拉底的一个最著名的哲学贡献就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寻求真理。’对话被许多重要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使用,包括柏拉图、Boethius、Alcuin、Bruno 、Galileo、Fontenelle、Berkeley、Leibniz、Hume、Nietzshe、Renyi、Heytion、Lakatos等人。他们的目的是想表明并比较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观点及其讨论;权衡观点和它的批判,通过讨论走向清楚并有说服力的概念。[8](P163)
科学修辞学的核心范畴是协商或对话,协商或对话既是真理的本质,也是寻求真理的方法。“真理不是在个人头脑里被发现的,而是诞生在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在他们的对话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8](P164)
卡林·诺尔—塞蒂纳在她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比较典型地使用了修辞学的方法。她指出,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建构性的,是由决定(decision)和商谈(negotiation)构成的链条。大致说来, 这种科学知识的建构包括前后相继的两个过程:实验室中知识的建构和科学论文的建构。诺尔—塞蒂纳认为,实验室知识的建构即研究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科学事实是由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渗透着决定。实验室中知识的建构具有很强的与境偶然性,具有当地的特质。科学家进行的实验室选择(包括对决定标准的选择与转换)随研究境况的不同而变化。
诺尔—塞蒂纳认为,利益融合与利益分裂支配着资源关系,通过资源关系维持了可变的超科学领域,形成了某种以权力游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之网。实验室中知识的生产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之网中(而不是像库恩所说的以科学共同体形式)进行的。科学知识建构的另一方面是科学论文从初稿到终稿的复杂建构过程。发表的论文即作为终稿的论文掩饰了文学意图,掩饰了作者与其他人之间进行的商谈,掩饰了权力的干预。在对初稿的多次修改和终稿的确定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利益的融合与分裂。
英国的TSR.2型战斗机则是协商没有成功的案例。TSR.2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英
国皇家空军寄予厚望的战斗机。50年代初期,苏联海军舰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充,以求挑战美国和北约的海上优势,尤其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级新型巡洋舰更是对西方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此,英国皇家海军决定采购一种舰载低空攻击机,它可以从低空以高速突破苏联海上作战集群的防御,随后投掷核弹将其摧毁。1959年,一个研究技术与设计问题的团队成立。根据分工不同,这个团队又分为两个小的团队,一个是Weybridge团队,主管费用和武器等问题;另一个是Warton团队,主管其中的动力机制,但与TSR.2工程有关的网状系统不止包括这些群体中的成员,而且两个小团体之间也存在分歧。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各自要求的不同以及相关能力的缺乏。低空飞行要求飞机采用小机翼、高翼载,以减少阵风和紊流造成的颠簸;但是舰上起降一般又要求采用大机翼、低翼载,以缩短起飞滑跑距离,降低着陆速度。这样,冲突便出现了,团体之间存在冲突,团体内部也存在冲突。不过,最终采用折中的办法达成一致。但不久,设计者很快便发现了设计出来的轰炸机过于笨重。为了进一步推动航空事业的发展,研制出更好的飞行器,政府部门、军事机构、航空部门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部门打算重新设计这一项目。1964年秋,TSR.2被设计成一种中型的飞行器,但费用却远远超过了预算,参与这一工程的人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歧也不再局限于财政部门、皇家空军、国防部门以及飞机制造业之间了。事实上,一些机构正试图改变他们的想法。争论逐渐变得公开化起来,保守党支持TSR.2项目的建设,而工党极力反对这种做法,原因在于它的成本费用和利用情况。最终,这一项目在经历了无休无止的争吵之后,于1965年被取消。
四、简单的结语
社会工程研究是一个有着伟大前程的学术探索领域。只要进行不间断的探索以及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我们相信,社会工程研究一定会取得成功。
收稿日期:2006—04—01
标签:建构主义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角色理论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成功要素论文; 社会学论文; 科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