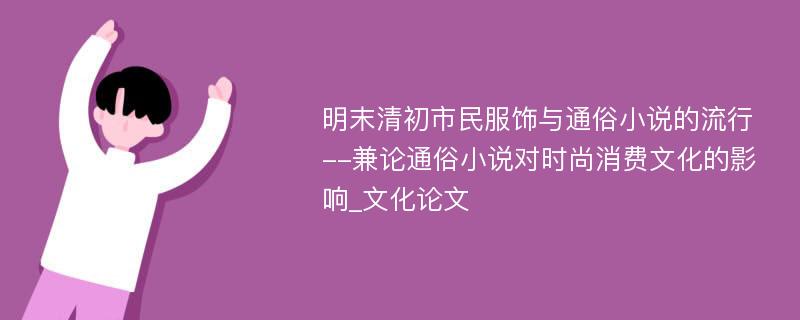
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与通俗小说——兼论通俗小说对时尚消费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俗论文,时尚论文,明清论文,说对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5-0199-07 上世纪80年代末,受西方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理论的影响,海内外明清史学界开始从消费而非生产的角度,重新审视晚明清初不同于以往的文化特征。近十年来,又兴起了一股明清奢侈风气的研究风潮,[1]且借助新文化史的历史视角微观转向,对晚明清初消费文化的研究和审视,也朝着关注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的微观纵深拓展,研究论题包罗甚广,诸如“城市生活与消费”、“日常生活的物质消费(衣、食、住、行等)、“流行风尚的形成”、“浪漫思想与消费欲望”、“商人的消费文化”、“妇女与消费文化”等等。 史学界对明清奢侈消费文化的微观纵深研究,也为古代小说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他山之石”。事实上,明清时尚消费文化与通俗文学之间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正是消费文化的兴盛和市民社会的壮大,才催生了晚明清初通俗小说的空前繁荣与发展,消费社会的市场逻辑贯穿在通俗小说生产、出版到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深刻地影响着通俗小说的文学观念、结构形态与叙述方式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作为文化消费品的通俗小说,往往也借着大众阅读与传播的渠道,影响市民的价值观念并进而影响其消费行为,当消费成为大众趋同的行为选择时,便形成了某种时尚的风潮。 本文选取从“市民服饰时尚”的角度切入晚明清初消费文化与通俗小说这一研究论题,是基于以下思考:其一,从消费的层面看,服饰既属于一种生活必需品,也属于一种地位性消费品或奢侈品,它存在于社会脉络中,属于一种文化消费;其二,通俗小说中的服饰描写内容,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辅助工具,也是制度、观念、价值、阶层等的文化符号信息的外在投射,“服装是一个显现社会意指的承载者,它是一种社会以及文化等级的承载者——这些都体现在物的诸多细节之中:形式、质料、色彩、耐用性、空间的安置——简言之,物构建了符码……符码中隐藏了严谨的社会逻辑,虽然它从来不说出来,但却可以依据每种社会地位的特殊逻辑来重建和操控。”[2] 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通俗小说中市民阶层服饰时尚消费的呈现;二是通俗小说中市民服饰时尚的阶段性特点;三是通俗小说如何参与和影响市民服饰时尚的变化。 一、市民服饰时尚消费在通俗小说中的呈现 关于晚明清初是否存在服饰时尚消费,一度曾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过去西方史家在论及中国近世服饰时,透过当时在华传教士的观察资料,往往低估了中国服饰上的变革,如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劳代尔(1902-1985)的研究提到中国15到18世纪因为处于稳定的状态下,所以几百年来无太大的变化,也没有流行时尚,[3]这一观点在西方学界占据主流,却遭到来自王鸿泰、巫仁恕、林丽月等台湾史家的质疑,他们通过对笔记、方志等史料的发掘和梳理后指出,至少在明弘治、嘉靖时期,由于服饰礼制的松弛,崇奢观念的兴起,“在物质上各种商品的流通,成为个人生活表现的丰富资源,以致形成不断变化的‘流行文化’”。[4] 若将眼光投向通俗小说的文本视野,这一问题更是迎刃而解。因为晚明清初通俗小说,特别是以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等,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不少市民服饰时尚的细节与动态描写,只不过这些内容除了被史家作为新型史料运用外,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笔者通过对《金瓶梅》、“三言”“二拍”、《型世言》、《醒世姻缘传》等通俗小说的解读后发现,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社会氛围,为市民阶层利用服饰时尚消费重塑身份和地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而最热衷于服饰时尚消费的人群,是市民阶层中的士人、商人和女性等三类群体。 1.士人服饰时尚 晚明士人是一个积极创造时尚的群体,尤其热衷于在儒服上花样翻新。儒服又称“方巾衫”,简称“衣巾”,是有明一代儒士(或称秀才、诸生)的专属身份服饰。但晚明社会由于制度管控乏力,儒服的身份标识渐趋弱化,市民阶层皆以穿儒服扮“斯文”为尚,以至于出现“满城文运转,遍地是方巾”[5]的现象。如《醒世恒言》第3卷“卖油郎独占花魁”,小商人秦重为见倾心爱慕的花魁娘子,听从妓院老鸨九妈的建议,“到典铺买了一件见成半新不旧的绸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闲走,演习斯文模样。”[6]《醒世姻缘传》第67回“艾前川打脱主顾,陈少潭举荐良医”中的觅汉常功,“不知哪里得来一件幅子大袖的衣裳,便穿了紫花布面月白绫吊边的羔皮道袍,戴上花二十四个钱在集上买的一顶黑色羊毛毡帽,穿上老婆亲手自做的一双明青布面沙绿丝线锁的云头鞋,学着斯文人的做派逢人便拱手行礼。”[7]甚至女性也以穿儒服为尚,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学出众的佳人们大多有过穿儒服女扮男装的冒险经历。 为了与庸流俗侩区分开来,儒士们不得不周而复始地创新时尚。谢铎(1435-1510)曾写诗描绘“方巾”的变化多端:“阔狭高低逐旋移,本来尺度尽参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样何能更入时。”[8]《醒世姻缘传》第26回“作孽众生填恶贯,轻狂物类凿良心”借一位老乡绅之口写道:“那些后生们戴出那跷蹊古怪的巾帽,不知是甚么式样,甚么名色。十八九岁一个孩子,戴了一顶翠蓝绉纱嵌金线的云长巾,穿了一领鹅黄纱道袍,大红缎猪嘴鞋,有时穿一领高丽纸面红杭绸里子的道袍,那道袍的身倒只打到膝盖上,那两只大袖倒拖到脚面。”[9] 在奇装异服的背后,是儒士们在身份遭到侵犯后的浮躁和焦虑心理,由于“面临着来自平民社会的激烈竞争,逼使他们更积极地、刻意地创造新的流行服饰时尚,以重塑并维持自己的身份和文化霸权地位”。[10] 2.商人服饰时尚 相较于儒士的积极创新,商人是一个善于模仿的群体,商人本是明代服饰制度中备受歧视的身份群体,早期的地位甚至不如农民,只等同于仆伇和娼优。①但明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处境得到极大改善。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商人有机会通过消费改变屈辱身份,《金瓶梅》主人翁西门庆便通过消费实现了身份的逆转。西门庆在完成财富原始积累后,便开始购买权贵身份体验,体现在服饰上,便是这样一个蜕变过程:刚开始是附庸风雅的“绿罗金扇”,其后是官员的“官服冠带”,最后竟然有幸穿上了何太监赠与他的“飞鱼蟒衣”。蟒衣是居于明代服饰制度顶端的服饰,地位仅次于龙袍,商人穿上蟒衣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制度森严的明中前期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晚明的消费社会,蟒衣作为一种优质服饰资源进入民间市场,为富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们提供了绝佳的消费机会。[11] 西门庆把权贵阶层服饰作为目标和追求,是因为作为一名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商人,他有着强烈的、摆脱低贱身份的心理诉求,但伴随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不少读书人的加入,这一队伍的文化内涵也大大提升。相比浓墨重彩的官服和蟒衣,之后的商人更青睐斯文一脉的儒服,《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贩卖米豆的徽州人陈商,“头上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骢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12]《喻世明言》卷2“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一位从南昌来的“卖布的客人”,“头上戴一顶新孝头巾,身穿旧白布道袍。”[13]《初刻拍案惊奇》卷2“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一位叫吴朝奉的商山大财主,“头戴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竹简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线道袍儿,脚上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绫僧鞋儿。”[14]此时期的商人,明显少了西门庆的浮华之气而多了几分儒雅风度。 3.女性服饰时尚 女性成为晚明时尚舞台引人瞩目的群体,是因为“对于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使自己变得有点突出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15]日趋开放的社会风气将女性从家庭的狭小空间解放出来,借着庙会、节日等冶游机会,晚明女性也四处抛头露面展示形象。如《型世言》第4回“寸心远格神明,片肝顿舒祖母”描写女性聚集寺庙闲聊时尚的情形“更有没要紧的,且讲甚么首饰带来好看,衣服如今怎么制度才好,甚么颜色及时。”[16]小说《照世杯》卷3“走安南玉马换猩绒”也写道:“就如我们吴越的妇女,终日游山玩水,入寺拜僧,倚门立户,看戏赴社,把一个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万人瞧,他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谈笑过路的美丑,再不晓得爱惜自家头脸。”[17] 在晚明清初女性中先后流行过大红大绿,清雅素淡和品牌服饰等时尚。热衷于大红大绿服饰的,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女性,因为大红大绿是制度为权贵女性设定的服饰,其中蕴涵的阶层与身份符号信息,对地位卑贱的平民女性颇具吸引力。《型世言》第3回“悍妇计去嬬故,孝子生还老母”书生周于伦收购城里的衣服贩卖到乡里去,他敏锐捕捉到“乡间最喜大红大绿”的时尚信息,于是“把浅色的染木红,官绿,染来就是簇新,就得价钱。”[18]《金瓶梅》中的女性,地位高贵者如兰氏、林氏、吴月娘等,卑贱者如潘金莲、李瓶儿、春梅、桂姐、爱香儿等,几乎人人都着一身大红服饰,只不过贫穷的穿布、有钱的衣锦而已。小说中大红服饰也数次成为西门庆妻、妾、婢女间地位竞争的导火索。[19]甚至大红颜色的布料也更为昂贵,《醒世姻缘传》第65回“狄生遭打又赔钱,张子报仇兼射利”里的绸店铺伙计李旺对前去买顾绣衫裙的书生狄希陈说道:“这顾家的洒线是如今的时兴,每套比寻常的洒线衣服贵着二两多银哩。要是大红的,就是十两来出头的银子哩。”[20] 相较于大红大绿在平民女性中的流行,晚明才学女性则追求一种清雅素淡的妆扮。《国朝杭郡诗辑》记载当时蕉园诗社的活动:“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21]冯又令、钱云仪等才女简淡到极致的“练裙椎髻”,令邻船的盛妆游女自惭形秽,也将才学女性的身份优势凸显无遗。 随着服饰时尚的发展,在明清之际,印有生产商标记的品牌服饰也大肆风行。《醒世姻缘传》第63回“智姐假手报冤仇,如卞托鹰惩悍泼”中出现了“顾家洒线”、“仇家洒线”等服饰品牌,小说写道:“且说南京有一个姓顾的人家,挑绣的那洒线颜色极是鲜明,针黹甚是细密,比别人家卖的东西着实起眼。”[22]“顾家洒线”很可能就是晚明清初流行的“顾绣”,“顾绣”是明末松江顾名世家族女性织绣的时尚藏品,后也被装饰在服饰上面。[23]以顾绣制作的漂亮衫裙,成为薛素姐、珍哥、智姐等女性的时尚新宠。《醒世姻缘传》第63回“智姐假手报冤仇,如卞托鹰惩悍泼”,监生狄希陈的老婆薛素姐元宵节去莲花庵进香,碰到邻居智姐穿了一身鲜明出色的顾绣裙衫,“甚是羡慕”,回来便着狄希陈去买,狄希陈没有及时买到,性情泼悍的薛素姐将其好一顿暴打。[24] 有关晚明清初市民的服饰时尚消费,中国台湾学者巫仁恕、林丽月,英国学者柯律格等均有研究成果面世。②但细察既有论述,由于受限于笔记、方志等的零散记载,研究多是对某一时尚现象、某一人群或地域的个案考察,尚未具全盘或贯通的眼光,这一点恰可以借助通俗小说加以弥补。通俗小说对士人、商人和女性等市民群体的时尚消费展示得较为细致,且相较于笔记、方志等正统史料,通俗小说结合个体生命经验的书写,更能曲尽幽微地折射出时尚现象背后的欲望与冲动,它所呈现的史实,往往更具整体性与连贯性。笔者也在对通俗小说的解读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观点,即晚明清初的时尚发展,并非缺少变化的过程,而是大致经历了阶层模仿、文化模仿与品牌模仿的三个不同阶段。 二、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发展的三个阶段 古代中国最早对“时尚”下定义的是明人祩宏,他在《竹窗二笔》说:“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25]一个“随”字,便将时尚中“跟随与模仿”之意表达得十分明确。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对“时尚是模仿”的观点作了更为细致透辟的阐释: 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模仿可以被视作一种心理遗传,以及群体生命向个体生命的过渡。……模仿给予个体不会孤独地处于他或他自己行为中的保证。[26] 既然时尚是群体对个体的模仿,那么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则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阶层模仿 简言之,阶层模仿即是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模仿。阶层模仿一般发生在等级秩序分明的社会,而这种模仿行为之所以得以实现,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制度在社会等级秩序安排中唯我独尊的地位,给了财富和消费一定的话语权,即所谓的“不以分制,而以财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在传统社会,社会结构的演变与重构是依靠阶级的分化与对立来完成的,而消费社会的区隔则是通过消费活动、生活方式及生活品位的差异得以实现的。[27]对于那些被压制在制度底层,从未享受过身份特权的群体而言,因了财富的许可,他们能够借助模仿高等级阶层的着装,轻易地拥有过去无法奢望和企及的身份体验。 晚明社会阶层模仿的代表群体是商人和女性。商人群体在明初“重农抑商”的政策下一直被打压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没有所属阶层的身份服饰,只有在模仿其他阶层中找寻身份认同和归宿,避免置身无根飘荡的孤独和恐慌之中。明中后期商人群体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崛起,也使得他们有资本去实现身份的逆转。商人群体以外,地位较低下阶层,如农民、手工业者、贩夫走卒,底层女性等,也时常卷入阶层模仿的行为。 充分反映阶层模仿特点的通俗小说首推《金瓶梅》。《金瓶梅》成书年代约在嘉靖、隆庆年间,这是一个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并对铁板一块的制度发起冲击的时代。③巫仁恕认为,大约在嘉靖年间(1522-1566)约当16世纪以后,旧有的尊卑、长幼、良贱、上下、主佃、主仆、绅民等社会关系的颠倒现象,冲击了明初均有等差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在此背景下平民服饰的变革发生,甚至已形成一种流行风尚。[28]《金瓶梅》细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市民服饰风貌,小说中的人物,不分贫富贵贱都把奢侈华丽作为服饰着装的终极追求,商人西门庆沿着儒服、官服、蟒衣的路线向制度顶峰攀缘,他的妻妾们则将身份与地位的竞争付诸于对大红服饰的攫取和占有。 2.文化模仿 这一阶段是伴随印刷经济的繁荣而来临的,明中后期印刷经济的迅猛发展,对社会心理的改造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指出,“对于早期现代化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性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从最初的书写经验开始,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已经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29]美国学者高彦颐根据以往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断言,“16世纪的中国,白银的涌入和接踵而至的商品化,宣告了一个大规模出版时代的到来。”“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词能够形容嘉靖时期(1532-1566)中国出版业出现的转折。……对书籍的供求都急剧飘升,而价格则大幅下跌,促成前所未有且持续一个(16)世纪之久的出版社会。……作为这一出版繁荣的结果,以前不能接触到印刷纸页的人们,或以前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借阅和抄写书籍的人们,都能毫不费力地从公开市场中买到书籍,并建立一个私人收藏。这些人,包括学生生员、在乡试中举的、农村小地主、小业主和士绅家庭女性,都加入了传统的精英行列,而构成了一个新的读者大众群。”[30] 印刷经济的空前繁荣,对晚明市民风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印刷时代表现出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的特征,[31]使得远距离的事件更容易侵入到日常意识之中,产生于精英阶层的新思想、新观念能够迅速渗透到社会大众,对整个社会的伦理与价值进行重构;二是印刷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读者大众群的形成,而在这一个以阅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市民群体中,占据文化资源优势的文人与地域,获取了话语权,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生活和新观念的代言人。“文人学士成为一种力量,赢得了某种权势,因为他们在机械印刷时代占据了主动。”[32] 如果要对晚明文化模仿划定一个起始时期,大约应在万历1592至1620年左右,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公案小说,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等新的流派,从讲史演义分化出来的,以当代史实为内容的时事小说已开始出现。[33]拟话本小说集《古今小说》也在1621年首次印刷出版。伴随印刷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和地位,市民阶层逐渐放弃“权贵”而将“文化”作为身份标签,文化人或文化地域成为时尚的引领者。比如文化发达地区的苏州便引领起了“苏样”的时尚,[34]文化名人冯梦龙、陈继儒等也成为万人追捧的“时尚偶像”。④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型世言》、《醉醒石》等,便突出反映了文化模仿阶段的时尚风貌。 3.品牌模仿 这一阶段可以说是文化模仿的精品化与个性化时代,文人士大夫精致化、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品牌商品,与阶层模仿和文化模仿不同的是,打上商家烙印的品牌商品具有更鲜明的主体性特征,更注重彰显与众不同的品位与格调,品牌中凝聚的价值与观念更为清晰和明确。 在阶层模仿与文化模仿中,消费者主要是通过消费来获得身份认同,而在品牌模仿阶段,消费就不仅仅是消费者本身的身份认同行为,更是生产者积极主动参与社会阶层重构与划分的行为。服饰品牌的生产者掌握了文化阐释的话语权力,他们创造出品牌并赋予卓越性与稀缺性,使之在既存的商品序列中占据合法而有利的地位。晚明清初的品牌制造者是掌握权力和文化话语权的精英士大夫,他们致力于日常生活的精致化与艺术化,使之成为品位与身份的象征,台湾学者王鸿泰称其为“赏玩文化”或“文人文化”。它是建立在对“长物”(花木、水石、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蔬果、香茗等)的赏玩基础上的富有仪式化的生活方式,文人藉由这套文化来自我确认,或互相标榜,彼此认同,像这样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套雅文化就成为一种具有特定族群意识的文化符号,它成了可以用来指称标识特定士人类型的“文人文化”。[35]然后精英文人再借助印刷媒体资源向市民社会推广其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 品牌模仿阶段的兴盛时期,大约是在文人精致艺术化生活风行的明末清初,描写品牌模仿阶段特征的是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醒世姻缘传》中的女性对品牌服饰“顾绣衫裙”的喜爱,显示出这一阶段女性不同于以往的独特时尚追求。 市民服饰时尚发展的三个阶段,为解读小说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语境,从追逐时尚的行为与方式切入,有助于探知人物隐秘的情感与心理。以女性服饰时尚为例,《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和《醒世姻缘传》分别描绘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女性时尚。《金瓶梅》中的女性,有着强烈的阶层模仿意识,她们所生存的环境,是等级与阶层壁垒分明的环境,置身这样的环境,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向更高阶层攀援和奋进,以改变自身屈辱低贱的身份处境。而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才女们,则摒弃浓妆艳服穿上素服淡妆,以彰显其高雅脱俗的气质和品味。《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看重的是更能凸显独特性与个性的“品牌”,她所模仿的时尚对象,是社会地位甚至远不如她的商人妻子智姐,从中所透射出来的,是薛素姐们反叛妇德规诫的不驯服态度。 当然,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发展的三个阶段,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时尚模仿因个体身份、地位、阶层、财富、文化程度等不同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且不乏多种时尚模仿特征集于一人之身的情况,比如《醒世姻缘传》中的戏子珍哥“穿着大红通袖衫儿,白绫顾绣连裙,满头珠翠。”[36]其中,“大红通袖衫儿”是阶层模仿的服饰,“顾绣连裙”是品牌模仿的服饰,珍哥借一身华服向世人传递出的信息是,她是一位身份高贵和兼具时尚文化品味的女性,珍哥这一人物形象已经与《金瓶梅》中的女性有着迥然相异的内涵和意蕴,而这样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背后的时代所赋予她们的。 三、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与市民时尚的文化模仿 通俗小说呈现了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走势,那么,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流行读物和文化消费品,通俗小说有没有对市民时尚施加独特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旅美学者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2006)中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究,他从文化消费与传播的角度,明确提出晚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对社会尚“奇”风气和书法艺术有深刻影响,这一新鲜立论也给了本文以启示和灵感。 笔者认为,通俗小说发挥时尚影响力的时代,正是文化模仿的时代。晚明印刷经济助推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刺激了城市及其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欲望,文学从传统的文人自娱走向大众消费,而在所有文化读物中,通俗小说对印刷传播的依赖尤其严重。明代后期,印刷经济的发展大大降低了通俗小说的印刷成本,使之成为市民社会消费得起的文化产品。陈大康认为,“通俗小说的发展在停滞近二百年后的重新起步是在嘉靖年间,作品数量开始明显增多是在万历朝,两朝时间跨度相当,但后者的作品总数却是前者的十倍。明显差距的产生有着多种因素,而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万历朝正是明代的印刷业得到长足发展的时间。”[37] 从口耳相传的说书过渡到个人化的阅读,通俗小说文化消费方式的转变,对读者心理的影响是十分深刻。麦克卢汉指出,机器印刷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思维和感知,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印刷物的心理和社会影响之一,是将其易于分裂而整齐划一的性质加以延伸,进而使不同的地区逐渐实现同质化。[38] 通俗小说使社会同质化的方式,便是类型化的生产和创作。晚明清初先后出现了拟话本小说、英雄演义小说、历史传奇小说、时事小说、世情小说、神魔小说等多种类型化小说,培养起了一个忠实的“读者大众群”,基本成员便是高彦颐所说的“学生生员、乡试中举的、农村小地主、小业主和士绅家庭女性”。不同的类型小说各有其主流消费人群,而拥有知识与文化资源的作者,分享了对读者大众群的话语权力,使得他们可以通过文字的组合和重新编码,对其进行隐秘的、持续不断的心理、思想乃至行为模式的渗透和影响。 以拟话本小说为例,拟话本小说是晚明率先兴起的小说类型,扛大旗者为苏州文人冯梦龙(1574-1646)。冯梦龙青年时代弃仕途投身于通俗文学的编创事业,在书商推动下编辑出版了《古今小说》,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39]“因贾人之请”,表明这本小说集与商人的亲密关系。在印刷出版文化发达的苏州,商人与文人常常如影随形,“如蝇之聚膻”。⑤对拟话本小说而言,商人既是出版发行的推动者,也是主流的阅读消费群体,正如陈大康所言:“嘉靖、万历时期购买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群是由那些既相当有钱,同时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组成,若从阶层的角度划分,那么这最初的主要读者群应该是商人。”[40] 拟话本小说的风行,客观上确立了冯梦龙的“文化偶像”和“物带人物”地位,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商人读者群中均具典范效应。据说当时社会流行的赌博游戏“叶子戏”便与冯梦龙的推广分不开,邓之诚《骨董琐记》“龙子犹马吊谱”条记云:“犹龙(冯梦龙)好叶子戏,一时从之风靡。”[41]冯梦龙从事编创活动的主要地点在苏州,苏州同时也是“苏样”时尚的发源地,林丽月认为,“‘苏样’服饰蔚为风尚,得力于苏州丰厚的文化资源与繁荣的商经济,而时人对苏州文人雅士的崇拜,更使苏州成为创造品味的最佳都会。”[42]“苏样”时尚的重要元素包括高冠、白道袍及浅履等,彰显的是闲散淡远的文人意趣和风度。冯梦龙自称“冯子名梦龙,字犹龙,东吴之畸人也”,[43]著名文人钱谦益说他是“晋人风度汉循良”[44],“畸人”和“晋人风度”都是对蔑视礼教、洒脱不拘之人的称谓,与“苏样”时尚的内涵一脉相承。尽管“苏样”时尚源起何时何人殊不可考,但借助在商人群体的“文化偶像”地位,冯梦龙的“名人效应”无疑扩大了这一时尚的社会影响。事实上生活中“苏样”时尚的跟风者也以商人居多,如前文提到在“三言”“二拍”中,穿高冠、白道袍及浅履的“苏样”商人也是对这一现象的侧面反映。 冯梦龙通过“文化偶像”的行为对商人读者的时尚进行引领。另一类型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则籍由审美价值观念的输送对女性时尚施加影响。 繁衍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可谓是落泊文人用文字编织的成人童话,满足了闺阁女性飞驰于脑海中的爱情想象。晚明清初女性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小说读者群体,“热衷于阅读言情小说的中下层阶级妇女,将这些小说中的某些因素当作‘现实’,当作有助于她们认识世界的信息的源泉加以接受,与此同时,她们聚焦于小说中有助于她们作为妇女具有的自尊和满足滋养情感的需要的某些内容。”[45]男性文人为女性读者塑造出痴情才子的同时,也用千篇一律的书写,塑造了一类才貌双全、品位不俗、爱情美满的才女形象,与平民女性热爱大红大绿不同,才女们喜爱清雅素服,“恶绝脂粉,只是淡扫蛾眉,天然佳丽。”[46] 清初通俗小说作家李渔对于女性服饰审美有过如下论述:“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绮罗文绣之服,被垢蒙尘,反不若布服之鲜美,所谓贵洁不贵精也。红紫深艳之色,违时失尚,反不若浅淡之合宜,所谓贵雅不贵丽也。”[47]署名“鸳湖烟水散人”的小说作家也在《女才子书》序中说“刺绣纺织,女红也;然不读书、不谙吟咏,则无温雅之致……必也丰神流动,韵致飘扬,备此数者而后谓之美人”。[48] “贵雅不贵丽”与“温雅之致”的“雅”,正是文化教养在外貌气质上的投射,在男性小说家眼里,艳妆意味着才学的匮乏和灵魂的苍白,素服则代表才学的丰盈与灵魂的饱满。世俗的艳妆女子是令人生厌的,内外兼修的才女才是男性文人的理想伴侣,因为当“文字环境把他们搁浅在个体孤立的沙滩上”[49]时,只有文化才能沟通彼此的精神与心灵,在冰冷世界里相互慰藉和温暖。 消费社会并没有离开男权文化的背景,男性中心的文化暗中支配着消费文化中的女性并通过印刷媒体不断强化和巩固,男性借助消费社会的文化工业张扬“才女气质”来构造一种文化陷阱,女性读者通过阅读和消费的过程,潜移默化地接受男性输出的审美价值观,并将其外化在着装上面,以此与世俗女子区别开来,成为一个以“文化”为标识的女性群体。 诚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指出的,影响消费模式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知识与艺术阶层定义下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50]晚明清初文人阶层占据了文化资本,因此拥有了定义时尚的话语权力,并借助通俗文学的宣传阵地,使其观念和价值成为万众趋同的消费行为指南,时尚亦由此诞生,这亦是晚明清初通俗小说对时尚消费文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 晚明文人冯梦龙曾言,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51]这是冯梦龙及其同行文人投身小说编创事业的话语策略与良好愿景。事实上,在消费文化与市民社会语境中应运而生的通俗小说,注定了娱乐与消遣才是其首要功能和存在道理,担当“六经国史之辅”的功用尚在其次。作为一种广泛流行的通俗读物,通俗小说在消费社会的广告和宣传功能,对市民消费行为与价值观念的引领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功能与作用究竟如何发挥却不易考察,本文借着“市民服饰时尚”的切入点探究通俗小说对消费文化的渗透与影响,算是一次大胆的探索与创新,但囿于相关资料的匮乏,不成熟之处也在所难免,这也为笔者指明了继续深化和拓展的方向。 注释: ①徐学聚《国朝典汇》记:“(洪武十四年,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穿绸、纱。……正德元年,禁商贩、吏典、仆役、娼优、下贱皆不许服用貂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卷110,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741-743页) ②林丽月:《大雅将还:从“苏样”服饰看晚明的消费文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映》,《新史学》(台北)10卷3期,1999年9月,后该文基本内容收入其著《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 ③《金瓶梅》的成书年代素存争议,学界有“嘉靖说”“隆庆说”和“万历说”等观点。 ④(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记云:“童生用方包巾,自陈继儒出,用两飘带束顶。”1928年奉贤褚氏重刊铅印本。 ⑤明人周晖《二续金陵琐事》中记:“凤洲公詹东图在瓦宫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羶’,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羶。’凤洲笑而不答。”标签: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小说论文; 时尚消费论文; 中国服饰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时尚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女性服饰论文; 文学论文; 醒世姻缘传论文; 古今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冯梦龙论文; 型世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