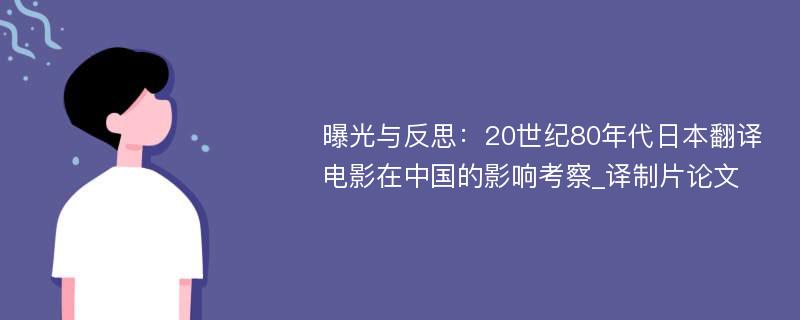
敞亮与反思:日本译制片在中国1980年代的影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制片论文,敞亮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译制片在1980年代的中国产生过较大影响,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却对这段文化交流形成了遮蔽,使得日本译制片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其影响也一直未得到官方和学界的应有正视。与此同时,民间还有一种反向的、近乎夸张的说辞,认为日本译制片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者”,并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影响”。出于正本清源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本文拟对日本译制片1980年代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进行还原、敞亮和反思。 一、对个体认知、态度和行动的重构 按照学界的通行看法,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对民众的影响可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外部信息作用于民众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民众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作用于民众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属于态度和心理层面上的效果;这些变化通过民众的言行表现出来,即形成行动层面上的效果。从认知到态度到行动,是一个效果的累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①日本译制片对1980年代民众的影响亦如是。 首先是认知层面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影片呈现的现代化景观对民众关于现代化认知的触动。对于当时刚从“文革”蒙蔽中走出的大多数国人来说,“城市”、“现代化”仅是些抽象语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也只是生活理想,但这些在日本译制片中都“实现”了。如《追捕》(君よ、愤怒の河を渉れ,1976)中有繁华的商业中心区新宿,《生死恋》(爱と死,1971)中有风驰电掣的新干线列车,《人证》(人間の証明,1977)中有华曼妙丽的时装表演。虽然它们不能给国人带来实在的现场体验,却能以虚拟的方式满足他们的心理欲望,并丰富其对于现代化的认知。二是改变了民众对日本和日本人的固有偏见。在此之前,关于日本,民众从国家宣传机器中得到的常常是“水深火热”、“苦情无边”、“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负面说辞;关于日本人,也大抵停留在《地道战》、《地雷战》描绘的身材五短三粗、色厉内荏、行为猥琐的模样。但1980年代日本译制片中出现的外表英俊时尚的日本人,如高仓健(おだごういち)、山口百惠(やまぐちももえ)、栗原小卷(くりはら こまき),则颠覆了这些偏见。三是影片中的民族化景观实现了对民众文化地理知识的补充。对于被封闭了几十年的国人来说,他们不仅不知晓日本的现代化为何样貌,就是日本的“土样”也不了解。影片全面逼真地对这些予以呈现。《望乡》(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1974)交代了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和服”,《柳生一族的阴谋》(柳生一族の陰謀,1978)展示了穿上和服后碎步疾驱的行走方式,《伊豆的舞女》(伊豆の踊子,1974)突出了木屐文化,《泥之河》(泥の河,1981)表现了神祀文化,《绝唱》(絶唱,1975)展示了婚冥文化,《兆治酒馆》(居酒屋兆治,1983)展示了酒馆文化等等,这些民族文化毫无疑问重构了民众的日本认知。 价值层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方面表现在破与立上:首先是“破”。破除了民众意识中的一些陈旧观念,如“娇生惯养”观念②、阶级斗争观念、血统观念及认为谈情说爱、梳妆打扮可耻的观念。然后是“立”。影片中日本的现代化景观激发了国人强烈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立下了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宏志,也积攒起了积极学习和工作的信念。比如有人说:“当时的日本电影对我触动很大,比如《追捕》、《人证》,从影片中我们得知,原来日本不是政府以前一直宣扬的那样‘寒酸’,他们的男人和女人也长得很好看,经济也发达,当时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到这样的国家去留学、去看看,后来我终于去成了。”还有人说:“我就是从《追捕》中才开始知道了现代化是什么样子,以前只是听说。从《海峡》(海峡,1982)中才知道了现代化建设需要付出怎样的精力和努力,当时沉默又有男人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酷毙’了的高仓健带给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努力的榜样,一定要像他那样,有责任心,最好再留个寸头,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工作。”消极方面体现为两点:一是色情和暴力场景对民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价值观的扭曲性冲击。“《蒲田进行曲》(蒲田行進曲,1983)确实是一部很逗的影片,但在这部影片中有些不雅镜头,我记得很清楚,有女主人公被脱光了强行做爱的场景,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不良反应,很多小青年专门到影院看这个。”③一些涉及坑蒙拐骗的影片对青年的价值观和心理成长也有不小震荡,受此影响,1983年云南省电影公司专门发出通知,禁止再映《诱拐报道》(誘拐報道,1982)、《蒲田进行曲》等影片。④二是影片过分渲染日本的现代化和强调自由的文化氛围造成了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哈日”情结的生成,这为1990年代末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反哺”埋下了伏笔。 在内在的认知和价值观均有所改变的联动下,民众的外在行为也发生了累积渐进性的改变,突出表现在三个“事件”上。一是1980年代初期喇叭裤的流行,二是1980年代中期“幸子头”的流行,三是1980年代中后期“寻找男子汉”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相较开放特区、招商引资等宏大国事而言,这三件事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形同蝼蚁”,可略而不提,但它们却对民众产生了从内到外的巨大冲击。我们以喇叭裤的流行来看其影响。诚而言之,穿喇叭裤算不上什么“事件”,但“敢穿喇叭裤”这件事情本身在当时已是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重大变化,因为要在1980年代初期特殊的政治语境中穿上前面开口、低腰短裆、紧裹臀部、像扫帚一样的具有“资产阶级情调”的喇叭裤不是件易事,它需要战胜来自自我、他人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心理性和行为性阻力,所以在当时,敢穿喇叭裤就是一种由内到外的“全面”胜利。这种全面胜利给当时的民众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卸去了单调、繁琐、严密包裹个人身体的绿军装、中山装和大腰裤,从而让腿脚等肢体能自由呼吸、随意舒展,进而让人在容饰上实现了与旧时代的表层决裂;其次是深层的观念更新,即对限制只能穿绿军装、中山装和大腰裤时代的行政律令和价值观念的解放,并将绿军装、大腰裤等衣物阻滞和圈笼下的个人从既有的政治文化秩序中唤醒,帮助他们实现从集体革命快感向个体自由快感的“快感大转移”,最终以轻松自由的心态投入到对自我的体认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可以说,“穿”与“不穿”喇叭裤此时已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和“旧人”的分水岭。翻阅那时的画报可以看到,在生活中,喇叭裤确实成了1980年代初期广受欢迎的“标志性”物件,很多一线工人、青年学生,甚至大爷大妈也纷纷穿起了喇叭裤。那么,1980年代初期流行开来的这些喇叭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研究表明,它的流行“和1978年风靡中国的两部日本电影有些关联。一部是《望乡》,另一部是《追捕》。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不仅成了年轻人最早的偶像,影片中矢村警长的墨镜、鬓角、长发和一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更成了当时年轻人眼中的时尚”⑤。 二、对大众文化生成发展的“催化” 作为综合性的大众化艺术形式,日本译制片对1980年代中国的电影、音乐、画报、曲艺、服装设计等等诸多大众文化形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的生成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催化”功能并促使文化格局出现了转型,但这一点常常被研究者忽视。 它对大众文化生成发展的影响首先在国产电影身上体现出来。一是对剧本创作的影响。《追捕》播出后,一系列国产侦破片从中受到启发,纷纷设置了“被追捕”与“反追捕”的叙述套路,而且结局也总是“被追捕者”获胜。《405谋杀案》、《戴手铐的旅客》、《嫌疑犯》、《检察官》、《通缉令》等均因袭了此种创作模式。 二是对艺术形式和摄制技巧的影响。“日本影片《人证》、《追捕》、《砂之器》、《生死恋》、《望乡》、《W的悲剧》、《火红的第五乐章》等影片或多或少呈现出时空形式的复杂性和摄影技巧的多变性,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对我国电影工作者产生的启发。……电影《生活的颤音》用黑白与彩色、现实与演奏现场的交织来阐释主题曲‘一月的哀思’的音乐动机,与《砂之器》的结尾同出一辙。在上影厂导演黄祖模执导的影片《庐山恋》中男女主角的林中相向奔跑镜头,谢添导演的喜剧电影《甜蜜的生活》中男女主角慢动作追逐的镜头都让我们感受到日本电影的印迹。”⑥《小花》的副导演黄健中说,“该影片是有意识借鉴电影新语言的结果,而这些新语言,主要来自《八部半》、《广岛之恋》及《生死恋》。比如,影片在处理周医生回忆被迫送走的亲生女儿小花(红果)及负伤的小花(翠姑)时使用的彩色与黑白的穿插,就借鉴了《生死恋》的拍摄技巧。”⑦ 三是对影片风格的影响。陈旭光指出:“第四代导演温情感伤的风格及人道主义的理想追求、复杂人性性格的表达和塑造,可能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涌入中国银幕的日本电影,如《人证》、《追捕》、《生死恋》、《望乡》等有一定的关系。”⑧事实上,不是“可能”,而是“必然”,因为在那时,真正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有话语权的不是国产影片,也不是美英法等国的影片(它们批量进入中国的时间均在1982年后),而是来自日本的电影,于是,“趁虚而入”的日本译制片就应和着当时的伤痕、反思等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了1980年代初期国产电影的风格。另外,第四代导演的纪实风格也受到日本译制片的影响。众所周知,日本电影以长镜头和生活化的描写见长,《望乡》、《金环蚀》(金環蝕,1975)、《野麦岭》(あゝ野麦峠,1979)等译制片就从“写真实”的角度对日本社会的面貌尤其是丑陋的一面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展示,尤其是《望乡》,不仅故事纪实,而且色彩的运用也颇具生活化色彩,⑨这给国产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启示和范本。在1980年举行的电影创作学习班上,《望乡》成了老师向学员传授拍摄技巧的样本,林洪桐说:“这类影片虽然也有激动人心、甚至触目惊心的情节和事件,然而却看不出戏剧加工的痕迹,这种调查加回忆的纪实性结构在世界电影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广为采用。”“我国近期摄制的影片《小街》、《沙鸥》、《邻居》也都采用了这种类似的纪实结构。”⑩ 日本译制片不仅影响到第四代的温情纪实,而且在国产电影由温情纪实向商业娱乐的风格转型中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学界在探讨这一风格转型的动因时,习惯于把它归结到港台大众文化的侵入、新型传播媒介的引进、改革的促动,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等方面,(11)对日本译制片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视而不见。实际上,日本译制片在这一过程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如上所述,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的影视版图上,日本电影比较特殊,它进入早,数量多,传播广,在打造娱乐化的社会环境和打磨娱乐化的创作人才、受众方面比其他国家的电影占有先机,因而更具渗透性,这就为1980年代中后期国产电影的娱乐化做了环境、受众、创作人才等方面的先期准备。我们知道,当时以第三代、第四代导演为主力的国产电影还在国家社稷的宏大构想上踯躅,但已充分工业化了的日本译制片却在不断上演:无论是《追捕》还是《望乡》,无论是《人证》还是《砂之器》,都将娱乐化、大众化的风格传递给了民众。即使被誉为“诗化电影”的《远山的呼唤》(遥かなる山の呼び声,1980),其大众文化化的色彩也较为浓厚,在这部电影里,悬念、争风吃醋、英雄救美等等模式化因素无不一应俱全,有力地推动着当时娱乐环境的生成。而当民众常常看到的是《追捕》、《生死恋》等影片时,大脑皮层上就会形成一个娱乐化印区,从而使他们变成这类对象的消费者。影片在塑造娱乐受众的同时,还培养了娱乐片的创研人才,《追捕》对国产侦破片的影响就是个证明。 其次是影片中的音乐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同对影片娱乐风格转型的研究一样,学界在谈到新时期以来中国流行音乐的转型时,也没人注意到日本译制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事实上,它也影响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尤其在歌曲类型和唱腔唱法上。通过爬梳材料我们发现,在《阿西,阿西》(チャンス)[《阿西们的街》(アッシイたちの街,1981)插曲]播放之前,中国大陆尚没有出现像样的摇滚乐,(12)正是它的出现“才使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摇滚音乐”(13);1980年代组建的一些摇滚乐队在演出时,还常常把这首歌当作压轴曲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阿西,阿西》称作中国摇滚乐的开蒙老师。再如《草帽歌》(麦わらの歌)[《人证》插曲],当时乐坛的主要唱法是“嘹亮雄阔”的美声唱法和“高强硬响”的进行曲唱法,《草帽歌》以不同于两者的通俗唱腔极大地震撼了普通民众和专业歌手(它被誉为“60后的最爱”,并被牟玄甫、刘欢、崔健翻唱过)。众所周知,这两种唱法经过长期革命化的“淬炼”后,其内里绍接着革命意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群众性,但是,因其高难度性和强专业性,它们又常常将普通观众拒之门外,并以所唱歌曲的革命性内容对他们进行着居高临下的规训。因此当具有幽怨哀婉、如泣如诉的唱腔,并饱蘸着个人情感的《草帽歌》进入时,就以它的特殊唱法,以及情感上的亲和性、技术上的可模仿性(和邓丽君们、李谷一们一道),极大地冲击了当时乐坛的上述两种唱法,并“登堂入室”升格为乐坛的主要唱法之一。但仔细究来,《草帽歌》与邓丽君们的歌曲又有所不同:在唱腔上它浑而不腻,而且还是日本电影中的英文歌曲,因而在形塑中国流行音乐之大众化发展的同时,还给国人的异域想象和现代化憧憬带来强劲的文化刺激,即在开拓中国音乐的国际化上也力不绵薄。由是言之,学界在关注邓丽君们、李谷一们对1980年代流行音乐的贡献时,应该把《草帽歌》也加进来。另外,影片对相声曲艺、广播电视等大众文化形式的发展也有影响。在这方面,杨振华、金炳昶的相声《下象棋》受到的影响最大。这不仅表现在它创作于影片《追捕》播放后不久,而且在该相声中,不论是“说”还是“唱”,有很多直接从《追捕》中“学”来,而且从相声的实际“笑果”来看,也恰恰是他们在演绎嫁接于《追捕》的这些桥段时——一是插曲《杜丘之歌》,二是杜丘在精神病院中的背景音乐,三是杜丘与唐塔在屋顶上的对话——能把观众“逗”乐,因此相声《下象棋》“说学逗唱”的成功其实是借力于《追捕》。 无需一一细述,日本译制片对198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萌生和发展所起作用的端倪已现。当然,198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还处于发轫期,尚未取得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分庭抗礼的资格,但由日本译制片注入到中国文化肌体中的一些因子已在促动着大众文化的发展,并且已触及了文化格局的结构性转型,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最能体现这种影响。客观而言,“精神污染源”中确有一部分不健康因素,但还有一些根本没什么威胁,只不过是一种具有新质地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而已,如在所谓的“黄色”电影中,有一些仅是叙写了三角恋或者人物穿了喇叭裤、留了长发、戴了墨镜。但是,由于这些内容强化和突出了感官刺激,而与当时的主流氛围和精英想象产生了冲突,因而遭到了合力“清除”。不过,“精神污染”的定性和“合力清除”之举恰恰从反面说明这种文化形式已影响到了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生存,尤其是主流文化多年来牢不可破的领袖地位。由此开始,“一分为三”的文化格局渐具雏形并萌发开来:这一切变化,均离不开日本译制片的推动。 三、对社会生产转型的“药引”式联动 日本译制片在1980年代中国的影响还扩散到了更加广阔的社会中,对社会生产的转型发展产生了一些影响。不过,这些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建立在它对个体认知和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之上的,因为正是影片中的事物和景观对个人造成了视觉震撼和心理冲击才引起了他们对日本的好奇和渴望。比如,与影片中“车来车往”生活方式的影响有关,国人对汽车开始“着迷”,“1985年,中国从日本等国进口了大约10万辆小轿车,相当于当年国产轿车数量(约5000辆)的20倍。据说当时曾有位中国汽车制造厂厂长在天安门数经过长安街的轿车,发现在100辆过往的轿车中有90多辆为日本制造。这种情况在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直至1995年中国进口的轿车(119,600辆)中,从日本进口的仍占将近一半,为54,300辆。”(14)这一方面便利了国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引起了他们寻求变革生活方式的强劲心理冲动,以企求与日本人拥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对中国企业的组建、管理和生产方式的革新也是一种无形的促进,因为中日之间的差距不断敦促他们追求先进经验,进行技术革新。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引进日本产品的同时,日本的技术、生产线等“硬件”,以及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和民族精神等“软件”也一同被捆绑引进。受此影响,1980年代中国大陆组建了许多日本独资和合资企业,海棠洗衣机厂就是从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直接引进技术和设备而建成为1980年代的名牌企业的。在这些企业中,颇具特色的日本现代化生产模式即东亚模式被引入进来,这对于推动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转型发展,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生产模式均有相当的示范意义。事实上,中国从1980年代中后期起,实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的“东亚式”市场经济模式。客观而言,这一切与日本译制片没有直接关系,但与它的“药引”作用似乎又摆脱不了必然干系。 四、对影响的反思及其启示意义 由上可见,日本译制片对1980年代的中国产生过全方位的影响是不争之实。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影响?它对我们又有何启示? 一方面,应正视日本译制片产生过的积极影响并对其做出正确估价。既要看到它对个体的认知、态度和行动产生的启蒙作用,还要看到它对社会转型发展起的“药引”作用,更要看到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它对198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生成起的催动作用(这个作用一直被学界忽视);决不能因为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蔑视或无视日本译制片的存在及其影响,也不能由此情绪化地将日本电影简化为AV电影或“怨羡”地称之为变态电影。但是,承认日本译制片的积极影响并不是要无原则地拔高它,将其置放到诸如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者”之位上供奉起来,更不是要借此泯灭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这样的主张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性。我们认为,历史的、艺术的和文化的问题应该用历史的、艺术的和文化的方法去面对、去解决,最好不要让政治因素的介入把艺术问题政治化从而搅坏文化艺术的自律发展局势。 另一方面,在关注日本译制片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更不能忽略对它的消极影响的审视和反思。日本译制片对1980年代中国的消极影响以“哈日”最突出。“哈日”即在思想上疯狂崇拜、迷恋和追随日本文化,让它僭越于本族文化之上,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表现出对它的迷思。这与通常所说的崇洋媚外不同,是在无意识层面宗“日”为“经”、为“祖”,进而实现对日本文化的全面认同。该行径毫无疑问是对民族文化传统明目张胆地丢弃和漠视,而实践证明,民族文化传统是否得到了有效传承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持续发展的基石,如果民族文化任由他族文化侵蚀,并且受众面不断增大,时间不断延长,就是在进行“自我殖民”式的戕杀。“自我殖民”指的是不用他族文化强行介入,民族共同体内的个体心甘情愿地享用、遵从他族文化的召唤,并让其凌驾于本族文化之上的做法。这是一种比“殖民”式的武装侵略和“后殖民”式的文化渗透更为严重的“自我去势”行为。因此,如果说以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K.Bhabha)、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为代表的学者对帝国主义的后殖民行为忧心忡忡,不断呼吁重新发现本土因而还有一种抵抗色彩的话,那么这种“自我殖民”就是在引狼入室,带来的是灭顶之灾。事实上,当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存在力量的不对等,并有实质性的交流行为发生时,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必然存在“殖民”和“被殖民”的倾向,亦即都会面临一个本土的文化心理、文化机制被他者的文化心理、文化机制植入、改造,直至变形的状况,但这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像“哈日”族们那样任由他族文化“肆虐”,那么本土文化也将很快消亡。但强调对1980年代的日本译制片带来的文化殖民及其文化“反哺”等情势进行反思,并不是要由此限制乃至取消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恰恰相反,我们要做的是继续加强、深化交流,而不是因为有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因噎废食;但在交流中要时刻保持批判性,注意避免片面和盲从,根据国情实际有选择地引进,让交流变得更有针对性,提高以国产电影为代表的文化艺术形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总之,无论是“抗日”般的无视还是“哈日”般的仰视,都不是正确对待中国1980年代的日本译制片及其影响的方式,它们均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谬,而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甚巨,“它绝不仅仅限于对历史自身的扭曲,造成历史的失真,导致历史传承的链条断裂。它更大的危害,是对价值的虚无。”(15)在这个问题上,王彬彬关于近代日本文化对中国影响的反思是有借鉴意义的,他说:“近代中国对日本‘文化反哺’的接受,或许多多少少是在吃着狼奶”(16)。“狼奶”之说可谓生动形象又鞭辟入里:一方面它是“奶”,为社会成员提供着身体成长和思想塑造必需的给养;另一方面它是“狼奶”,又具有必然改变“人”的传统文化基因的“有害性”,但不管怎样,“狼奶”自有它的“价值”。日本译制片对1980年代的中国来说就是不折不扣的“狼奶”,因此,小心谨慎又大胆果断地对其进行批判性萃取实为上策。 注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8. ②《狐狸的故事》播出后,有人指出:“北方狐狸这种严厉的教育,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很有些苛刻和残酷。但是,这对我们人类来说,也具有深刻的寓意。家长对待自己的子女,是严格要求,用心教育,锻炼他们的才干,引导他们奋发图强,不断进步呢?还是一味迁就,百般溺爱,让他们躲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一辈子饱食终日,碌碌无为?”邓小秋:《狐狸离别的启示》,《戏剧与电影》,1980年第2期。 ③这些引文是笔者针对1980年代日本译制片的影响做的问卷调查。 ④陈播.中国电影编年记事·发行放映卷(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946. ⑤叶匡政.1978,喇叭裤是一面自由的旗帜[J].环境与生活,2008,(12):65. ⑥刘永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银幕上的日本电影及其对中国电影观念的影响[J].艺术百家,2008,(6):188. ⑦黄健中.电影应该电影化[J].电影艺术,1979,(5):43. ⑧陈旭光.影像当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9. ⑨沈嵩生.电影中的色彩[J].电影文化,1980,(2):169. ⑩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创作室.电影剧作讲座[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163. (11)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12. (12)1980年,中国大陆第一支演绎西方老摇滚的乐队“万李马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成员有万星、李世超、马晓艺和王昕波。1981年,“阿里斯”乐队成立,成员有李力、王勇等人,以演唱日本歌曲为主。1982年,丁武、王迪等组建“蝮虫及乐队”。艾迪和几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成立了“大陆乐队”。但是,虽然已经有了这些乐队,他们的演出极其有限,根本没有传播开来,所以那时的民众对它的认识依然停留在空白阶段。郭发财:《枷锁与奔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3)王沛人.六十年代生人成长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260. (14)王志乐.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105. (15)张江.文学“虚无”历史的本质[N].光明日报,2014~04~04(01). (16)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