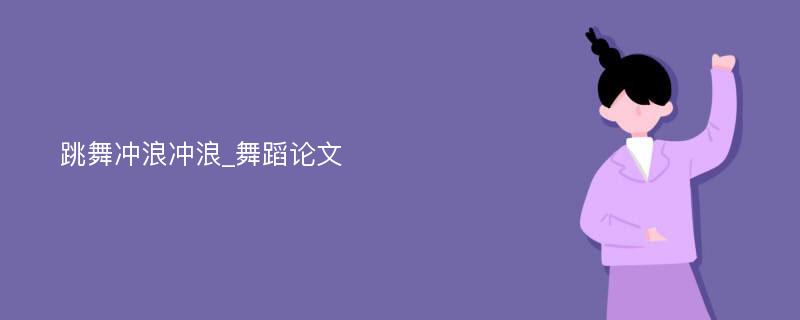
舞蹈大冲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舞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蓝凡 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上海艺术家杂志社主编)
(舒巧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曹诚渊 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艺术总监)
(谢明 上海歌剧舞剧院一级研究人员)
(季玉衡 上海舞蹈学校副校长)
中国舞蹈创作就其文化精神来说,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化蓝凡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聚会,既是沙龙,又不象沙龙。主要是自由地讨论当前中国的一些舞蹈现象。
这几年来,上海舞蹈创作的优势局面急速消退,可是上海以外地区,包括北京,舞蹈的创作却进入或正在进入一个上行发展通道,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强烈的反差,自然激发了批评的反应和理论的思索。不过,引起我本人注意的,倒是近期的有代表性的二次舞蹈展示,即第三届全国舞蹈(单、双、三)比赛和第十六届“上海之春”的舞蹈专场。能够赞喻的,我们已在能够见到的报刊上阅读过了,但它也给我们舞蹈界留下了不少的问号和惊叹号:不是说某些作品的精粗优劣,而是指创作的整体趋势走向,即当今中国的舞蹈创作在其真正的精神面上是日趋褪色还是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这样说,我认为当代中国舞蹈创作就其文化精神来说,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着某种深刻的变化,它包括舞蹈创作思想的重新厘定和廓清,舞蹈创作优势的地域性的重新划分和确定,以及人文精神在舞蹈文化中的重新觉醒。舒巧
当前的舞蹈评奖很值得思考,譬如全国文化大奖中竟然榜上有《月牙五更》。有人说它表现了农民生活的乐趣,可是舞台上表现的是七大嫂八大姨扒男人的裤子,这难道说是表现农民生活的情趣?
搞创作,做人最要紧,人要坦白,有了好的自我,然后方可言现代意识。如果人的品质不好,舞蹈创作决不会成大气候。
说新观念和现代意识,当时我搞《奔月》的时候,视现代意识为洪水猛兽。我不懂现代舞,对我本人来说,你要表现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用自己最喜欢的方法表达出来,忠实于自我,找到自我,这就行了。所以搞创作,做人最要紧,人要坦白,有了好的自我,然后方可言现代意识。如果人的品质不好,舞蹈创作决不会成大气候。譬如现在社会上有人搞创作追求什么“性擦边”,这就决不是什么新观念或现代意识。
说到创作,我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传统影响,国内舞蹈界也是如此。开始是舞蹈语汇和舞蹈语言,后来是民族舞剧与中国舞剧之争,现在是慢慢都改过来了。我国的民间舞观念完全是学苏联那一套,稀里糊涂到现在,可至今还是没有正名。现代舞也是没有正名。大家看现代舞,或者很抽象,或者很深沉,明朗了就认为不是现代舞,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国外现代舞的风格很多。我现在有一点体会,有的现代舞看不懂,并不在于舞蹈本身,而实际上是因它的题材含信息力大,所以我们一时对它难以理解。
从目前舞蹈界的现状中,特别是一部分各种各样的评委来看,存在着看重舞蹈的技巧性,轻视舞蹈的艺术性的倾向。如在这次全国舞蹈比赛中,我对《圆》就比较难以接受,技巧的东西太多。再如《扇妞》,得了创作奖,但难以理喻的是,整个舞蹈变成了扇指挥人,人受制于扇,而不是扇吸引人。当然舞蹈的主题很健康。这里要插一句关于舞蹈评委的问题,各种舞蹈比赛,评委的意见和评分具有导向的意义。评委之间有分歧是正常的,代表了方方面面的意见,但不能就说某些评委的意见是正确的,另外的是不正确的,要允许评委有自由思想,这是一种职业道德。所以舞蹈比赛是考编导,也是考评委。
允许评委有自由思想,这是一种职业道德,所以舞蹈比赛是考编导,也是考评委。
至于说到古典舞,我有不同的观点。我国严格意义上的古典舞是没有的,只是从中国传统戏里往外捞,例如《小刀会》和《宝莲灯》就是这样。因为中国戏曲是唱做念打,所以我国五十年代的所谓古典舞也走这条路子,以打为主,例如《小刀会》一共打了七场,《宝莲灯》是抒情戏,也打了五场。当时认为打才有情感,打才是跳舞。后来又讲没有古典舞。可对我来说,我认为只有古典舞才能搞舞剧。这是因为民间舞只有单一的情绪,如欢乐、悲伤等,就象现在的迪斯科一样。民间舞在民间就是民间迪斯科。我在舞剧创作中就只是将民间舞作为欢乐情绪的手段来使用。
另外,有一个题外之话。现在流行二种说法,叫文化与国际接轨和创一流文化。我认为,与国际接轨,首要条件是必须知道人家怎么样,方可言接轨转。譬如我们歌剧院的歌剧《楚霸王》,是不是按轨接错了?接到国外十七、十八世纪去了。再说接轨也非单线接轨。与一流文化连起来看,应先明确什么叫一流。其实一流文化也就是与国际接轨。所以我建议在理论上应该出版一套丛书,系统地介绍和讨论从古典芭蕾到现代芭蕾,以及当代的现代舞。开头不能太深奥,从这里开头提高舞蹈界的文化素质。曹诚渊
在艺术观上,我认为自己与大部分舞蹈界人士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舞蹈比赛和获奖作品,我认为是滥情、造作和品位低俗。
中国大陆大部分的舞蹈比赛和获奖作品,我认为是滥情、造作和品位低俗。
我想从这次中国舞蹈比赛说起。
在广东省东莞市举行的“中国首届现代舞大赛”已经圆满结束。这次比赛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谁个获奖多少的结果,也不是因此而反映出来的政府对发展现代舞的积极态度,而是评委间对何谓现代舞的论争。这种对现代舞的不同看法和评价标准也触发起参赛者和观众的议论纷纷。大决赛当晚,我添为评委之一,在离开会场途中,被一位专程来自云南的舞蹈教师拉着质问:那来自湖南的《染飘》明明是出民间舞,怎么也会上了现代舞大赛的决赛?
也就是相类似的问题在决赛当晚掀起了观众的疑惑,翌日广州一位文化记者在报章上更大字标题地刊登了一篇颇为尖锐的文章:《现代舞大赛——评委们究竟懂不懂现代舞?》
与此同时,广东省及中国舞蹈家协会中的某几位资深舞蹈家们又挺身而起,向记者们发表意见,盛赞决赛中诸如《染飘》这类节目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是叫人看得赏心悦目的真正中国现代舞。当然,发表以上言论的资深舞蹈家们都是大半身从事民族民间舞蹈的前辈,位高言重,却如此一来惹得专研现代舞理论及实践现代舞教学创作的年青少壮派舞者们更加群情汹涌,他们提出的责难也颇能展示今天中国整体舞蹈发展的一个严重概念问题:“既要民族民间舞蹈借鉴现代手法去加以创新,又要标榜创新的现代舞向民族风格靠拢,则到底民族民间舞和现代舞之间的分野在那里?”
像这样的一个概念问题,在西方、在日本、在台湾,甚至在香港早经解决了:民族民间艺术,当然是愈古老、愈纯粹、愈不受现代文明的“污染”便好;而现代艺术,则自然要创新、突破、愈不受传统规条的“束缚”便愈好。所以在法国,既有崇尚传统高雅品味的古典芭蕾舞剧及歌剧,也有狂放不羁、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的最前卫剧场舞蹈;在日本,保存了四百多年仍然丝毫不变的传统能剧,也和极端新潮而变异莫测的舞蹈艺术并存不悖。只不过,无论是古典芭蕾、前卫舞蹈、能剧、舞踏等,都是经谓分明,各有清楚明晰的艺术目标,绝不会弄得像今天中国的舞蹈圈子中民族传统舞蹈和现代舞蹈的纠缠不清,你转过面来可以是我,我掉过身去又是你的糊涂局面!
在中国首次举办的现代舞大赛中,我发觉有两个颇为严重的中国现代舞发展危机:
其一,今日在中国发展现代舞的少壮派们太急于要建立一个现代舞的正统门户,以和代表传统的古典舞、民间舞及芭蕾舞等分庭抗礼。出于这种门户的心态,少壮派们很容易流于急躁地为自己设立一道界线,在这道界线以内的是现代舞,而界线之外的其他形态的舞蹈,便不能被称之为现代舞。
衡量一出舞蹈作品是否是现代舞,应依据其在特定的环境中有否创新和突破性。
倘若我们承认现代舞应该在意识及形态上对传统有所创新和突破,则我们在衡量一出舞蹈作品是否是现代舞时,便不能不以舞蹈创作者本身所处的历史和地域为比较基础点,才能清楚舞蹈在其特定的环境中有否创新和突破性。譬如玛莎·葛蓝姆早期的作品如《阿博朗茨的春天》、《给世界一封信》、《疆界》等,从动作设计、主题意识方面来看,在今天均显得有陈旧的感觉。但这些舞蹈仍然被奉为现代舞的经典创作,因为对在四十年前美国演艺界仍然是以王子公主爱情故事为题材的时代来说,是深具震撼力和充满革命性的。同样理由,今日广东实验现代舞团或北京舞蹈学院一班年青现代舞者所创作出来的舞蹈,对很多西方舞评人来说或许是停留在被视为过时的表现主义或动作分析折构手法,但这些作品仍将会为在世界舞蹈发展上被记录为划时代的属于中国的现代舞,因为对于今天中国这个仍然是以强调民族色彩并高奏主旋律的舞蹈圈子来说,这些作品正是以其挑战主流并言人所不敢言的精神为中国现代舞开拓了天地,是值得中国现代舞者们所自豪的。
可是,当中国的现代舞者们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目标时,一方面也要小心不要践踏了别人也在作出的同样努力。在我看来,来自湖南的《染飘》也在湖南历史及地域内颇具突破性:它的动作语汇明显地很多提炼自生活的原创成份、它的舞台空间调动灵活多变突破了民间舞的整齐划一性、它的演员全是染漂工厂工人,其“我舞写我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又不是其民间舞专业演员所能体现得出来的。综合整体来看,《染飘》纵有千般万处不足,但被少壮派们因其表现形式的不同而指之为非现代舞,则显得结论太过草率。
发展下去,中国的现代舞者们可能会变得愈来愈自我中心,把现代舞的形式、手法、内涵、概念等锁定在一个自以为是的范畴内,不能接受有别于己的其他意识形态。现代舞应该是开放、包容、充满反思辩证精神的艺术家,所以现代舞的内涵和形式都可紧随时代环境和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变。定要把舞蹈的形式和内涵定于一尊的这种正统承传心态,只能让我们的民族传统舞蹈家们去拥抱,而现代舞者们却适宜开放心灵,以轻松却又审慎的情怀去面对不断的时代变异呢!
现代舞应该是开放、包容、充满反思辩证精神的艺术家,所以现代舞的内涵和形式应紧随时代环境和社会的精神面貌变化
我在中国首届现代舞大赛中感觉到第二个危机是:舞蹈家们太刻意追求现代舞的民族特色了。这种急于要看见“中国式”的现代舞的心态,有时变得过于膨胀而窒碾了审视现代舞美学的专业研究精神。
还是以现代舞大赛中的一些作品为例。《染飘》可以被列为现代舞范畴,被邀请进入复赛,但当和其他进入复赛的作品并列一起,互作比较时,其不足之处便凸显出来:
一、在主题意识方面,它只是重现湖南工厂的生活情景,却没有深入染漂这种民族工业工人生活中进行任何反思,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湖南的工厂工人也肯定曾面对不少冲击,在作品中我们只见到一大群工人嬉嬉闹闹,大概一百年前的湖南染漂工人也会是这样的吧!相对于其他不能入选决赛的节目,如《裙与带子》中对中国戏曲传统内性别定位所进行的深沉思考和深刻表现,《染飘》无疑是显得浅薄及落后得多。
二、在逻辑结构方面,《染飘》呈现的是一段又一段的舞蹈,之间没有选辑性的联系。演员开场时聚在台右后方的一个大道具染缸上,摆出一个颇先声夺人的造型,但当舞蹈开始后,造型散去无迹可寻,结尾时演员聚在台中央摆出个民间舞中常见的叠罗汉,似乎忘记了台右后方那大而又障眼的染缸和曾经出现过的开场造型,使人怀疑编舞者在创作时有否全盘地考虑过舞蹈的整体结构。相对来说,《裙与带子》以一位舞者数度进出及横过舞台的移动过程中,层层加强及展示一位传统舞者对自己性别定位的不安和质疑,在结构上是严谨慎密得多。
三、在动作语汇上,《染飘》确实是丰富多采而具有创意,但在五花八门的动作被抛出来之后,编舞者却并未小心剪裁,去芜存菁,以致整个舞蹈中只见舞者们不停在动,动作的风格却驳杂不纯,也因此叫人想不起有那些设计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再拿《裙与带子》来比较,动作从戏曲中发展出来,既含有传统套路中的温柔婉约风姿,又展示出一种现代品味的内在张力,动作虽然少,但看得出是经过编舞者反覆推敲后过渡出来的菁华意态。
四、在舞台元素的运用方面,《染飘》动用了一个硕大的染缸,半空吊竿又忽上忽下的吊下多幅长染布。元素是多了,却没有怎样运用这些道具和吊竿升降效果,形成了舞台上的堆砌和浪费。《裙与带子》则只是舞者孤身一人,随身一条裙和一条带子,却描绘出一幅意态万千的图画,这才叫做舞台元素的精炼运用。
五、舞者的演出效果方面,《染飘》的演员都是工厂工人,在技巧方面当然很难和其他专业演员相比。他们的演出已经十分投入和认真,但免不了还是频频出现节奏失误、步法错乱、焦点分散、控制不稳种种情形。以这种演出水平状况,《染飘》仍然可以堂而皇之进入大赛的决赛里,便不能怪责观众和其他有份参赛演员大喊不公了。
《染飘》的出现在中国首届现代舞大赛决赛项目里,使广东省某些资深民族舞蹈家目盈泪光,大声赞好,更籍此发表议论:现代舞就应该向民族内格靠拢;也确实使大赛的评委大声向外界宣布:《染飘》才是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舞;也使中国的现代舞大赛出现无可避免的尴尬局面:以《染飘》的编舞及演出水准来说,它绝不可能在任何稍为具有专业水平的舞蹈大赛中打入决赛——在桃李杯、在全国舞蹈大赛等标榜民族特色的赛事里,它可能连复赛也进不去,但在现代舞大赛中,却因为它的民族特色而昂然进入决赛,而其他在编舞技法及演出的艺术水平上要比之更为优胜的作品如《裙与带子》、《光》、《造梦车间》、《小心》、《四肢》等却通通被摒诸门外。“民族特色”成为品评现代舞优劣的最高标准,这宁不使人感到中国现代舞发展的悲哀?
现代舞追求的是现代人类的普遍相通性,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地去探索基本人性,所以现代舞绝对和民族特色没有关系
我认为,现代舞所追求的是现代人类的普遍相通性,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或是北京人、广州人都可以在彼此的现代舞创作中寻找现代人的共同语言及相通感受。现代舞的艺术特色可以具体地呈现在作品的主题意识、结构逻辑、动作语汇、舞台元素及演员表现等最基本的剧场美学内容中,却绝对和民族特色没有关系。现代舞作品倘若有民族特色固然好,没有民族特色也无妨,因为现代舞的目的不是去区分劳动甚么是中国的、西方的、或是北京的、广州的、而是希望全人类能走在一起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地以舞蹈去探索基本人性。至于那丰富而色彩斑澜的民族特色,便应该留待我们中国庞大的民族民间舞蹈家队伍去加以发扬光大。唯愿将我们中国的现代舞大赛中的评委们能够以专业严谨的态度去评价现代舞创作里的美学内容,而不是只为那铺天盖地而来的民族特色而过于激动吧!
谢明
我想先从《醉鼓》说起。
舞蹈是“非文字语言”的艺术。在五六十年代,讲究艺术的思想性,我们常将离开文学语言就很难说清的事件、道理,以至政策硬用舞蹈去表现,结果内容大于形式,甚或成为艺术魅力。这种弊病现在已不多见。但仅仅是动作和技巧的堆积,即使是很巧妙的堆积,如果忽视艺术内涵,提倡形式大于内容,也未必就是舞蹈很好的出路。
《醉鼓》在第三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表演和创作大奖。我在观摹学习时,也喜爱这个节目,但同时也认为这节目在创作思维上,仍有美中不足之处。这节目编排的巧妙在于善用空间,桌上、地面动作交替结合,较好地表现了演员技巧的“亮点”。但缺点是舞蹈包容的艺术信息量不够丰富,艺术思维不够新颖。在《醉鼓》之前,舞台表演艺术(包括舞蹈)已有《醉拳》、《醉剑》、《醉枪》等,其特点是将较丰富的拳法、剑法、枪法融于醉态之中。《醉鼓》是醉态有余,而对击鼓的构思则不足。十几年前曾有《金山战鼓》,击鼓的技巧也不特殊,但其构思却极富情趣。从聚兵布阵,拒敌拚杀,主帅受伤,整兵再战,到全军获胜,有发展,有高潮,起伏跌宕,鲜明有序。台上不直接描绘事件、情节,而情节却在言外。短短一个三人舞,通过击鼓这一构思和形象,使观众似见一场完整的古代战争,联想不尽。是谓舞蹈包含的信息量丰富。表现手法在当时是独创的、新颖的。至于爱国主义,巾帼气慨从艺术形象中自然流露,更为可贵。可见“非文字语言”的舞蹈还是可以讲求艺术内涵,以至思想性(不是教条)的。试比较前两届全国比赛,女演员“旁腿一百八十度朝天蹬”只有寥寥数人能达到,而今天几乎成为“普遍技巧”时,是否会感到技巧发展较大,而艺术思维却相对滞后呢?
今天几乎成为“普通技巧”时,是否会感到技巧发展较大,而艺术思维却相对滞后呢?
我以为判断一个舞蹈的优劣,除了纯技术因素外,主要取决于这个作品:1,传达给观众的信息(社会学的、伦理学的和美学的)丰富还是贫乏;2,意蕴深刻和肤浅;3,表现形式新颖还是陈旧。例如《三国演义》里,有貂蝉以美人计挑起董卓和吕布之间的矛盾,达到诛杀篡权奸臣,作为一个三人舞的素材是可取的。当然,一个小舞蹈不可能传达原小说众多的情节,也无法说清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两个男人之间强烈的妒忌,从情同父子,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是和占有貂蝉的心理行为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心理变化过程,在原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描写,这就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创作天地。舞蹈立意到此,也算在原小说基础增添了新的信息。但是,还可进一步。政治家利用“美人计”来从事政治斗争,从现代眼光来看,就很难值得赞许。一个少女被利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献媚以至献身两个男人,如果她不是职业的色情间谍,而是纯朴的女子,其心境的痛苦可想而知。生活在封建社会的罗贯中,可能不会想到。这又给善于表达感情,揭露潜意识心理的舞蹈以弛聘的天地。京剧大师梅兰芳《宇宙锋》中,就把“疯”和不得不“装疯”的两种情态及其心理刻划得相当深刻。如果我们不加深究,随便套用一个公式化的爱情三人舞,或者把几个诱惑动作和追逐动作组合在一起,就不易引起观众欣赏的兴趣。
当前舞蹈可以“伴歌”、“伴戏”、“伴影视”、“伴旅游”、“伴各种庆典节目”,热闹得很,但作为剧场艺术的创作舞蹈、舞剧却相对沉寂。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可能很多,就舞蹈本身而言:脱离生活,缺乏意蕴,墨字成规;创作上片面鼓吹形式大于内容,教学中忽视创造和智力培养,使舞蹈艺术倾向于工具化、技术化、机械化。这就造成舞蹈宜于“装点门面”、“宣染气氛”,而失掉对人类心灵的关怀。
我们正处在“知识爆炸”、世界文化大交流、大冲突、大变革的时期,在各门艺术中,前卫意识都显得十分重要,舞蹈自不例外。
前卫意识是一种常常与传统的、流行意见相左,一般人一时不易理解,并且遭到一部份墨守成规者反对的意识。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也可能相当长),就显出其生命力,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佳吉列夫和福金进行芭蕾革新,邓肯倡导现代舞,吴晓邦建立他的“新舞蹈”,都是典型的例子。颇令人深思的是,当前一种前卫意识出现时,往往伴随着某些“伪前卫意识”混迹其间。例如故作“超前”、“先锋”的姿态,表现与众不同,作品时而怪诞时而古奥。又例如在创作领域鼓吹没有界定的“游戏意识”,反对“使命感”,把胡编乱造,不负责任,说成是编导的“潇洒”。究竟文艺为人民服务是“游戏意识”呢,还是“使命感”?我并不完全反对艺术中的“游戏意识”,而是说要给以适当的界定。另一令人不解的是,当西方世界已到了“性泛滥”、“性厌倦”,“爱滋病”也都传染到中国大陆,居然还有人把“性意识”当作“前卫意识”。有些双人舞中,但见两个身体越贴越近,越抱越紧,压倒在一起,摩擦在一起,守全丧失了爱情的诗意。顺便说一下,影视给我们的影响也不能低估,裸露的镜头,以敢于谈“作爱”、说脏话而自鸣得意。我们不通过大脑就接受所谓“英雄也有七情六欲”的说法。英雄当然有七情六欲,需知这是与KTV包房里的七情六欲大有区别的。总之,我们应对“伪前卫意识”打假。
舒巧和曹诚渊最近合作创编新的舞剧,他俩是中国舞剧和现代舞的著名编导,现在从各自的领域走到一起,我以为合作的基础是二位编导都具“前卫意识”,并且都有强烈的个性,我希望他们碰撞的火花能照亮沉寂的舞剧舞台。季玉衡
舞蹈从现代向后现代,是一步一步走的,并不是一跃而成。我们搞创作,要的是根据自己体验后认为是好的。同样搞舞剧,通过人物的塑造来达到创作的目的,例如舒巧的《奔月》,以及后来几部舞剧作品,也都是通过自己的体验,正确地把握了剧中的人物,然后才达到目的。如果单纯从样式上决定,什么是现代,什么会是后现代,就会严重阻碍创作思想,束缚住人物的塑造。
在这次全国舞蹈比赛当中的作品《忆》等,通过一个动作,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变化无穷。其中有很多借鉴了现代舞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有规范的改造,突破了原来的古典舞范畴,但是它不叫现代舞。
北京舞蹈学院这几年通过吕艺生院长们的共同努力,提倡现代舞和身韵舞,新的创作不断,培养出了不少年轻的编导,创作的舞蹈一个比一个好,所以我想,只有通过创作现代舞来靠近现代舞。蓝凡
我想谈一谈舞蹈的人类学问题。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当前我们舞蹈界倒底应该关注的是舞蹈的文化面,还是精神面,或者是其它什么?
在人类发明创造的艺术品种当中,舞蹈可以说是最极限地运用人本身来表达人类情感的艺术样式。在其它一些艺术样式中,戏剧需要通过故事的中介,音乐需要人声以外的物质材料的延续(如各类乐器),而舞蹈则是完完全全的“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大序》)的人体表情性艺术,因之而最能强烈地“直露心声”——淋漓尽致地最本原地抒发人类的感情需要的渴求。所以苏珊·朗格说,人类最初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人的力量和意志在人身上的感觉得到的,这些神最初是通过身体活动得到再现的”,“这种活动,就是人们通常叫做‘跳舞’的活动。”正是这种意义上,舞蹈是“人类超越自己动物性存地那一瞬间对世界的观照。”(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
在一定意义上舞蹈是人类从动物脱颖而出的标志之一。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舞蹈竟也成了人类从动物脱颖而出的标志之一。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舞蹈创作却日益背离了舞蹈的这种最本体意义,逃逸了舞蹈人类学的这种基本要求,而只是一味去发展舞蹈艺术的附属性特征:即通过无限止在形式上对舞蹈动作的拷贝和动作技巧的游戏,把舞蹈创作拖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舞蹈创作路向的误区是显而易见的。这里面有创作意识问题,也有各种各样舞蹈比赛的评委导向问题。
大概是从八十年代中叶开始,当舞蹈界提出“从足尖下消失的舞魂”这一命题以来,方方面面就对“一条腿”之类的纯技巧性的舞蹈游戏创作提出了质疑。但是十年过去了,这一问题的症结始终得不到解决。我们不说舞蹈不需要《雀之灵》、《醉鼓》一类的创作,也不是说舞蹈动作编排上的这种流畅没有给我们带来视觉审美上的进步,而只是强调:将玩弄动作技巧作为一种舞蹈创作的主流方向,无疑将把中国的舞蹈创作逼入死胡同中去。我认为这里还存在各项比赛的评委导向误区。因为很明显,舞蹈比赛和舞蹈的技巧比赛(甚或为了教育上的需要)是完完全全的两码事。我们口头上都在讲反对文化上的全盘西化(或者说是崇洋媚外),可偏偏我们的舞蹈比赛却都全要原封不动照搬国外芭蕾比赛的那一套,然而即使是国际芭蕾比赛,它也规定必需有几段舞剧中的片段,并将演员对角色创造的程度作为评判优劣的标准。当然,我们不否认芭蕾比赛中动作评判的科学性,然而,如果将之推向极端,无疑就变成为荒谬。因为它完全将艺术的比赛等同于体育或其它的什么比赛了。而且在世界上,除了芭蕾,还没有第二种艺术品种的比赛其规则是如此类比于体操、滑冰等体育比赛的。中国的这种舞蹈比赛状况,起始于“桃李杯”比赛。作为一种舞蹈院校的比赛,其为了教学上的需要,以技巧为标尺的评分制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将“桃李杯”的比赛原则推而广之到舞蹈比赛的一切领域,就有失偏颇了。毋庸置疑,舞蹈界对舞蹈动作技巧的这种认识和单纯的卖弄技巧已使舞蹈创作走入歧途,现在是应该大声疾呼的时候了:技巧不能取代艺术。
舞蹈艺术丧失抒情言态的品格而成为感官刺激的玩赏对象,舞蹈的主题便也从骨子里“倡伎”化起来。
如果说舞蹈创作中的这种纯技巧游戏是从外形式上走入了路向误区,那么,抽去舞蹈“抒情言志”这一最根本命题的创作,可以说是从根基上在瓦解中国舞蹈的精神。当然诸如什么怪异动作的表演,生搬硬套的创作等这些泡沫现想象是压根儿用不着提的,现在提出应值得引起警惕的倒是舞蹈创作的媚俗化问题。这种媚俗化表现为:一方面将单纯的技巧玩弄取代舞蹈内容的表现,使舞蹈表演完全等同于人体动作技巧展览,另一方面是恶性化地使舞蹈品格沦丧。
自然,舞蹈动作技巧对舞蹈主题内容的剥离,在某种意义上其对舞蹈创作的危害还不是十分严重,因为充其量它无非将舞蹈自身推出艺术的大门而流入体操竞技一类,问题的严重性倒在于另一方面,即在所谓表现民风习俗的招牌下,使舞蹈艺术完全丧失了抒情言志的品格而成为感官刺激的玩赏对象,从而使舞蹈倒退至中国封建社会的“倡伎”舞人一流的卑俗地位中去。舞蹈的主题便也从骨子里“倡伎”化起来。
我并不认为以《月牙五更》为代表的舞蹈创作在倾向上有什么大问题,但作为主流创作现象,确实值得引以震警。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当前中国的创作全都一窝风地不是拟古就是猎奇(所谓民俗展览),而将当代的时代精神远远抽离出题材选择之外。这无非是另一种将舞蹈拉入卑下的创作道路。问题很清楚,地域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中隐含着许多负面情结,譬如对两性关系的不自然处理,以及民生民态中的落后陋习方面等等,对之作为一种研究和展览无可非议,但如作为艺术的创造就大可商榷。不说这种陋习已远离当今的时代,就是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来说,也显得十分无聊。因为它将舞蹈的审美拖落得比“倡优”还更低卑的地步,完全沦落为一种低俗的纯感官刺激和知觉猎奇的对象,这与人类创作舞蹈这门艺术的本位不是完完全全背道而弛?如果再将它作为舞蹈创作的主流,其危害性就更不必言了。
可是话又要说回来,中国舞蹈界的状况并非没有令人值得欣慰的。上海一地是例外,北京和广州等地区现代舞甚或后现代舞的崛起,就可说是当今最能代表中国舞界发展的启明之光。且不说广州实验现代舞蹈团了,北京的现代舞便令人振奋不已。继’94北京国际舞蹈节掀起的现代舞热之后,1994年11月的《新闻》舞蹈剧场,1995年3月的“首届现代舞大专班学生作品展第一号”的举行,都为我们舞蹈的希望画上了最最精彩的一笔。《三寸金莲》、《磨合》、《秋水伊人》、《心慌慌》、《同窗》、《两个身体》、《红扇》、《点线圆》、《无题》、《与你同行》、《心悟》、《符号》、《四季歌》、《嘈杂空间》、《占着……》等等,无不闪烁着舞蹈艺术的真正大智慧。
舞蹈的现代或后现代运动必将给中国当今舞坛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激动和灿烂时代。
毫无疑义,现代舞蹈以至后现代舞蹈——舞蹈的现代及后现代运动,必将给中国当今舞坛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激动和灿烂时代。面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解构运动所带来的深刻悖论状况:在商海的捲裹中价值沦落、理想褪色和精神普通地忧患与焦虑,舞蹈的现代和后现代运动完全可以在这种文化解构中张扬起自身的价值——重新为自己定位,重新注入时代的活力。我早说过,现代舞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精神,中国的舞蹈艺术应该撷取的便是这种精神,在舞蹈的创作上,使主题选择和动作创造都极具张力,即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创造出一个极富发展极蕴内涵的手舞足蹈的活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在中国舞蹈界来一次现代或后现代运动已正是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