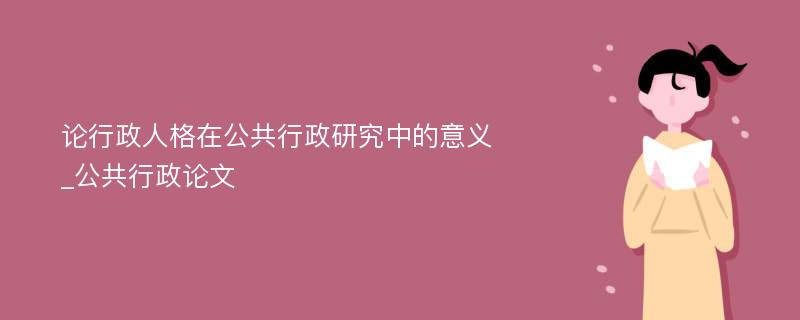
论行政人格之于公共行政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论文,之于论文,人格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1)11-0064-08
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1887)中就提出了以下问题:如何使政府官员和公共行政人员具有一种服务性人格和性格,“用良心作最大的服务”,使为社会服务成为他(她)“最普遍”“最珍视”“最崇高”的“兴趣”,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去例行公事?威尔逊指出,回答这些问题是行政学研究的目的之一,甚至认为,能否回答这些问题将会决定(美国)能否再度掌握世界的航向。①毫无疑问,人类至今仍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人及人格问题仍然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因此讨论行政人格之于公共行政及其理论研究的意义仍是有意义的,在我们看来,行政人格既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主题,又是公共行政及其理论研究的微观基础,还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方法。
一、行政人格: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主题
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所提出的以上几个问题以后,人这一主题一直潜伏于或者说散见于主流行政学的发展潮流中。②就人在政府行政组织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与政府行政的关系而言,威尔逊提出问题之后,公共行政学领域借鉴传统管理学及组织理论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就一直关注行政组织中的人及其行为问题,具有代表性的,如1947年罗伯特·A.达尔《公共行政学:三个问题》中指出,公共行政科学之创立必须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并断言:公共行政科学的发展,意味着在政府管理之服务领域中的一门人的科学的发展。③1955年,德怀特·沃尔多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认为,从某些方面和某种关系上来说,公共行政研究的中心要素是人本身,是通过在公共行政中从事这种行为和过程的人来进行的。④
事实上,除了公共行政学之外,组织理论也对人与组织(包括行政组织)关系及组织中人的人格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如弗罗伊德1922年出版的《组织心理学和自我分析》一书,试图解释个人在组织中进行感情投资的过程、结果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对组织的领导。根据其理论,弗罗伊德认为,个人会为了组织成员的身份而放弃个人的个性和特点,以此形成一种归宿感和认同感。作为组织成员的自我通过对领导进行“渗透”,就像以自己理想对自我进行渗透一样,以达到自己对领导的依附,并因而将领导的自我形象与自己的个人期望混合在一起。他指出,当个人被组织抛弃时,个人就会感到恐慌和焦虑。因此,过分依附于组织和它的领导,从精神学上讲,是一种对于焦虑的防御措施。他同时提出,在组织中希望被平等对待,也是一种防御行为。另外,弗罗伊德对组织成员的个人动机与某些追随者对组织极端的和危险的依赖行为进行了区分。⑤弗罗伊德关于组织的精神分析,开拓了组织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正是在他所建立的有关概念和理论基础上,对行政组织及行政人员的人格分析才成为西方行政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戴蒙德则根据其焦虑理论和组织同一性理论,进行了组织精神分析,他总结了组织成员的三种自我形象:一是“整合的真实的个人形象”;二是“分裂的自我形象”;三是“压抑的自我形象”。⑥这是将心理学应用于组织分析的代表,其他还有大量的运用心理学理论于管理学的文献,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对组织中人性的关注,等等。
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对行政人格的集中讨论是围绕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理论展开的。韦伯根据其整个社会“理性化”理论提出了官僚制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由神秘阶段不断演化到理性复杂阶段的过程,人类的希望正在于理性化。“重要的是制度、法规和正式职务,而不是个性;是公事公办,而不是个人关系;是技术专长,而不是心血来潮,一时聪明。”⑦他注意到了严格的官僚层级制对个体独立人格的排斥,以及非人格化扩张所带来的长期社会问题,并预言人类不可避免地将进入官僚制这座“新的奴役铁笼”,他将逃离这一铁笼的唯一希望寄托于具有非凡气质和能力的克里斯玛型领导者的出现。⑧官僚制理论的提出并首先由韦伯本人对官僚制批评之后,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对官僚制批判的热潮,认为“官僚制的主要受害者是其雇员”,并提出了“官僚人格”的概念,如葛德塞尔提出“‘官僚人格’基本的论点是官僚制度自身的结构产生了其独特的精神或人格”⑨。罗伯特·K.默顿在1940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官僚制的结构及其人格》中指出,官僚的人格类型是非人格化规范的核心,这种非人格化趋势以及从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的支配作用发展而来的绝对化趋势,往往会造成官僚与公众或顾客联系方面的紧张,官僚的官方角色被授予了明确的权力,这常常会产生一种实际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的态度,官僚本人在等级制度中的职位及他与公众相比所处的地位可能会增强这种态势。罗伯特·K·默顿认为,官僚组织至少产生了四个关于官僚人格的基本特质:运用技能的灵活性不足;过度强调规则;谨小慎微、保守;非人格化的、按图索骥的思维方式。⑩进而,默顿呼吁加强对官僚制和人格的相互作用进行经验性研究,并认为这特别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结构的了解,甚至进入“所罗门的圣殿”。(11)安东尼·唐斯进一步阐述了默顿的理论,他将官僚划分为五种类型:权力攀登者,保守者,狂热者,倡导者和政治家。(12)美国著名组织理论家沃伦·本尼斯列举了官僚体系的十大缺点:妨碍个人的成就和个性成熟;鼓励盲目服从和随大流;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不考虑突发事件;陈旧的权力和控制系统;缺乏充分的裁决程序;无法有效地解决上下级、部门之间的矛盾;内部交流、沟通受到压制、阻隔,创新思想被埋没;由于互相不信任和害怕报复而不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无法吸收科技成果与人才;人的个性被扭曲,个个变成阴郁、灰暗、屈从于规章制度的“组织人”。(13)葛德塞尔认为,关于官僚人格最为著名的分析是拉夫·霍梅尔的《官僚经验》一书,该书指出,官僚制度催生了一个非人性化的新物种,或者说新型人格,“从心理层面说,这种新型人格是属于理性主义专家类型的,它没有情感也缺乏意志”,它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的良知被上级的意志所代替,他们行动的自由受到规则与司法的制约。总的后果就是官僚个人的身份被削弱了,个人的潜力没有得到实现。(14)
针对官僚人格问题,有些学者更加明确地从伦理角度进行了充分探讨并提出了解决之道。小威廉姆·H.怀特在《组织人》中论述了组织中基本的个人伦理自主性。他认为,当前我们处于一个组织的时代,人都变成了“组织人”,组织人的实质就是要求其对组织的认同,从而使社会及组织对个人的压制在伦理上得以合法化。因此,怀特反对组织控制组织成员的个人价值观、世界观和行为,主张保持一种组织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坚持个人德性的首要性。(15)威廉姆·斯科特和大卫·K.哈特通过现代组织中的“角色等级”分析,认为“组织控制”已经改变了美国的价值观,必须通过“职业人物”改造现代组织,重建“个人控制”以避免“集权主义”。这与韦伯的观点不谋而合。阿勒多·格雷罗·拉莫斯则主张以一种“解释性的人”替代完全屈从于经济原则的“操作性的人”,即通过社会系统的分析和再设计,实现对“组织的限定”,即限制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度,并以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和系统的方式参与组织活动,从而限定组织对自己职业行为的控制。(16)
官僚制似乎已臭名昭著,以至上世纪70年代末逐步兴起的“后官僚制”学派力图纠正工业社会无人格管理带来的弊端,强调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管理,但支持官僚制的声音也从没有停止过。葛德塞尔的《为官僚制正名》是代表作。他认为,根据他的观察研究,美国公务员“并没有表现出僵化机械、墨守成规、小心翼翼、没有人情味、盛气凌人、令人敬畏、虚伪、高高在上,行事遮遮掩掩的个性特征。恰恰相反,这些特征往往在他们那里得不到体现”。(17)另外还如,梅尔文·科恩、查尔斯·保金和米歇尔·格莱姆斯、丹尼斯·奥根和查尔斯·格林,等等,他们的研究都得出了那些批评官僚制者相反的结论。(18)
国外对行政人格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多途径的研究,尤其是围绕官僚制这一焦点,形成了行政人格研究的繁荣局面。但行政人格研究并未形成专门化的理论体系,更没有成为公共行政研究中的重点。(19)国内对行政人格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20世纪90年代有人开始使用“行政人格”一词,到目前围绕这一概念的研究成果不少,从内容方面来说,国内对行政人格的研究应该说是十分繁荣的;从研究途径看,对行政人格的研究主要也是从心理学与伦理学两方面展开的。
台湾学者张金鉴对行政人员的人格做了分类,提出了“幼稚型”与“成熟型”两种人格类别,进而提出塑造“成熟人格”的设想。(20)台湾另一位学者张润书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行政人员在组织中的行为、工作态度与人格的关系。(21)王沪宁等从“个体人格独立程度”把行政人格分为“顺从型”与“独立型”两种人格类型。(22)张分田通过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主奴综合意识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人格”,“而官僚的政治人格又是主奴综合意识的典型代表”。(23)李善岳研究了行政人员的气质和态度问题,提出行政态度是指导行政人员行政活动的定向器,行政气质是提高行政人员行政效率的基础条件。(24)张丽锦使用艾森克(EPQ)人格问卷和爱德华个人偏好问卷(EPPS),对某地区不同职级行政管理人员人格特质进行了比较研究。(25)崔会玲、刘立惠对当前公务员心理困境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26)赵世明、霍团英、张玲等对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和人格特质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应该在领导干部中开展心理健康干预和辅导,提高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素养。(27)李磊等对公务员心理素质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28)近些年来,人们对行政人员的职业倦怠问题关注得比较多,主要是从行政人员的心理因素方面来进行分析的。(29)
在我国,马文运最早提出“行政人格”这一概念,认为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在执行公务中的行为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在法律上体现为行政主体承担义务享受权力的资格,在伦理学上体现为行政人的道德品质,在心理学上体现为行政人的性格、气质和能力等。(30)在中国语境中,国内学者多从哲学和伦理学角度来探讨行政人格问题,将“人格”理解为人的道德品行,成了“人品”的替代词。
国内对行政人格研究首先注重对党政干部的素质研究上。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贯重视党员和干部队伍建设,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但学术性研究偏少。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九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重要讲话后,各行各业、各级干部、理论界和学术界,都对讲话进行了学习、思考,并对如何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进行了研究,成果颇多。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以德治国”思想后,学术界和理论界更多地重视对党政干部道德人格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李春成博士遵循亚里士多德之德性论传统,提出功能性的“德性行政人”概念,详细分析了行政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探究行政人的道德品质及其价值选择与伦理责任,最后还分析了德性行政人生成的不同路径。(31)王伟教授明确提出了行政人格的概念,并将行政人格定义为包括党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在内的公共管理主体的人格,进而对行政人格的内涵、作用等作了大致论述,将之视为行政伦理价值目标的核心。张康之教授主编的《行政伦理学教程》,专列一章对行政人格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认识和理解行政人格,把行政人格理解为行政人员个体之格与群体之格的统一,作为个体之格,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个体性的体现;作为群体之格,行政人格则体现了公共行政职业的内在规定性,是行政人员社会属性的体现。在同年出版的《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一书中,张康之教授单列一节论述了公共行政中独立人格的生成。2004年11月,张康之教授在《江海学刊》第6期上发表《论行政人格的历史类型》,进一步论述了独立人格的实践价值;2005年9月,在《南京社会科学》第9期上发文《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导向:公务员独立人格的追求》,认为服务型政府只有立足于行政人员独立人格之现实建构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超越。杨艳的博士论文《论行政人格的历史类型》(2006)认为摆脱传统行政改革进入死乱循环的关键在于加强行政人格建设,加强政府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建构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道德制度是形成独立人格的制度保障。谢新水则指出,行政人格转型在行政系统要素变化中具有先在性,是公共性逐渐实现的过程,也是行政人格逐渐健全的过程,并在人格发展的历史视野中,认为行政权力性质的改变、行政文化的发展、治理模式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行政人格两次重大转型(依附型行政人格向工具型行政人格、工具型行政人格向独立型行政人格的历史转变)的关键因素。(32)
综上所述,对行政人格的研究是公共行政学的重要内容,且成果很多。但作为专门理论的研究尚比较薄弱,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表面看起来很繁荣,但多是泛泛而谈,理论深度不够。国外关于行政人格的研究尽管存在多途径、多视角的趋势,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并未形成专门化的理论体系,而且多是集中于官僚制中组织和人的关系研究,明确对人格进行研究的也多是从心理学包括精神分析学、精神病理学角度对私人组织中行政人员的人格研究。而人格是一个总体,我们不能只站在某一学科或某一角度对行政人格进行单向度的静态研究,而应该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制度、体制、文化等方面对行政人员这一特定群体进行动态研究。
行政人格制约着政府行政,政府行政体现了行政人格。因而行政人格研究一直就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二、行政人格:公共行政研究的微观基础
公共行政中,行政人员是“机关构成者”,“视为机关构成者的个人,是独立的人格者;对于国家有权利义务。官吏关系和其他国家使用人与国家的法律关系,皆得由此点说明之”。(33)这是德国行政法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这种观点承认行政人员个体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人格意义,换言之,行政人员基于其角色的个体人格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行政学中,人们普遍将行政人员作为“组织的材料”来对待;(34)尤其在官僚制中,行政人员成为行政的“工具”,“官僚”是为了行政的目的才存在的。也正是因为官僚制将“官僚”视为工具,才显现其非人格化的公正性,从而被视为理性官僚制的一大优点。但这一点正是韦伯所忧虑的一大问题,也一直是被人们批判的焦点之一。对官僚制这一问题的争论,体现了行政人员或“官僚”及其人格在公共行政及其理论研究中的基础作用。如果公共行政将官僚制作为中层的分析单位,(35)那么“官僚”就是官僚制及其理论的微观基础或微观分析单位。
在现实中,行政人员或“官僚”的基础性作用也是明显的和十分重要的。他(她)不仅是“工具”,更是活生生的人,是具有人格的人。无论在民主体制或不民主体制中,直接行使行政活动的行政人员的个体人格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民主不合理的法律规章加上廉洁守法的公务员能构成一个好的高效的官僚体系,而不民主合理的法律规章加上腐化谋私的公务员就会构成一个坏的低效能的官僚体系”,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哪里有‘行政’,哪里就有‘官僚’。但是,哪里有‘官僚’,并不等于哪里就有‘行政’”。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曾感叹说:“我认为我是总统,然而,当到了官僚行政人员那里,我什么事都做不成。”(36)
微观基础是与宏观解释相提并论的。当我们说“某某理论或研究要有微观基础”,往往强调的是,该理论或研究应该从个体层面的人性假设出发,去演绎推导出最后体现在社会宏观层面上的行为结果。(37)换言之,微观基础就是坚持社会现象的宏观解释必须用建立个体层面之上的因果机制来予以支撑。也即社会宏观层面上因果关系的确认,必须指明个体行为者所面临的具体环境与互动机制才有可能。(38)
公共行政学研究也应该有自己的微观基础。虽然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谈到了政府官员的品德与培养及激励问题,但并没有明确指出对官员个体行为进行研究的重要性。默顿在探讨官僚制和人格关系时,则明确提出,“对官僚制和人格的相互作用进行的经验性的研究,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结构”,“在研究社会组织和人格形成的相互依赖性的同时研究宗教、教育、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官僚制,将成为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的一种途径”。(39)而西蒙根据有限理性原则,对走出“行政管理理论的绝路”的探索性研究,就是用“行政人”取代传统的“经济人”,并提出要解决行政管理中个体的非理性问题。(40)他虽然注意到了个体非理性因素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并提出了“行政人”假设这一微观基础的核心,但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之后,对公共行政研究的微观基础作进一步探讨的是达尔。达尔批判了传统行政学的科学主义倾向,提出影响公共行政的三个基本问题或因素:价值、个人个性和社会框架。达尔认为,“公共行政的大多数问题是围绕着人来考虑的,因此,公共行政研究本质上是对处在具体环境中表现出某种行为,以及预计或预测会表现出某种行为的人的研究。公共行政领域能够与心理学、社会学或政治制度区分开的原因在于,它关心的是在政府机构完成的服务领域中的人的行为”,“将人排除在外肯定会使公共行政的研究毫无建树、徒劳无功,并从根本上说是不切实际的”,因而,“较充分地认识到公共行政领域中人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较高的可预测性”,是建立公共行政科学的必备条件。(41)当沃尔多说“公共行政的许多研究是通过在公共行政中从事这种行为和过程的人来进行的”,“在公共行政这个问题上,从某些方面和某种关系上来说,研究的中心要素是人本身”(42)的时候,实际已肯定了人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
这样看来,似乎公共行政研究的微观基础已经确定,但从公共行政研究现状来看,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公共行政研究中关于人性假设至今仍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行政人”当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之后所谓的“公共人”、“社会人”、“政策人”、“线段人”、“比较利益人”等等,都试图去改变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但却都没有超越这一假设,或者说没有更好的替代性的假设。另一方面,即使各种人性假设有一定的道理,也没有建立起在既定假设基础之上的演绎推理过程,或者说没有在既定人性假设基础上,找到公共行政领域中的各种因果关系,从而建立起理论模型和增加公共行政的知识。
我们并不是企图提出一种新的人性假设来替代传统的人性假设,只是以为,将人格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微观基础更具有现实性。对于理论建构来说,“经济人”假设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但行政人员作为人,他(她)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现实。在行政领域,西蒙的“行政人”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但由于其行为及其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对于构建理论用处不大。这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大困惑和障碍。我们对行政人格进行研究,试图吸取目前心理学、伦理学、法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人格或行政人格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微观基础,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现实性原则,也是寻找公共行政研究的微观基础的一种努力。
三、行政人格: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方法
人格是哲学人学理论的主要范畴,也是行政哲学的理论基石,更是我们讨论行政人格问题的逻辑起点。人格问题与人性、人的本质密切相联,中外思想史上对人格的探究极其丰富,歧义纷呈。社会学将人格视为社会或某个团体中的角色特征;心理学上的人格以人的规格、样式为基本内容,关注的是人的“统一的结构性自我”,把人格看作是个人心理品质的总和,是个人稳定的内在特征;伦理学上的人格以人的品行为其内容,关注的是人的“崇高的自我”,将人格主要理解为个人的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法学上的人格研究以人的资格为主要内容,关注的是人的“有存在价值的自我”,指对作为主体(包括法人)的权利、义务的确认;哲学上的人格则以人的主体性资格为其内容,关注的是人的“有自由价值的存在”,强调的是人的主体的自我确证与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质的历史获得。(43)这些不同概念中,心理学的人格概念揭示了人格的心理基础,是人格研究的第一层次;伦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的人格概念揭示了人格的三个主要方面或维度,是人格研究的第二层次;而哲学的人格概念是从人格与文化、社会、世界等关系上进行研究,因此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是人格研究的最高层次。具体而言,在心理人格基础上,社会学中的角色即人格,但人格要求超越角色,这是道德人格或德性人格的要求;法律人格(权利人格、义务人格)只不过是道德人格的“底线人格”;哲学人格是各种人格话语之抽象和简约化。
可见,“人格”的含义、使用是比较宽泛的。这也说明在人格研究中,简单枚举是永远无法穷尽事物的现象的,也无法准确地揭示事物的实质。我们认为,首先应该从哲学上把握人格的含义,它关系到人的最基本的生活意义,关系到个体对自身价值和他人价值的基本看法以及个体特有的性格、气质、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人格一般地说是指社会个体精神和境界的价值定位,更强调人的主体性。人格作为价值,是指人对自身存在的地位、意义、作用,包括权利和责任的认识、评估。因此,虽然“人格”也用来对他人的评判,但在更多情况下,它表现为评判者对自身价值的评估。因此,人们总是把自身人格的修养和对自身人格的尊重看得十分重要。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人格是一个系统结构,是由个人的性格、能力、气质及需要、欲望、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等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总汇和组合,是人的内在精神要素的总和。其中,性格、能力、气质是人格的基础层面,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是人格的价值层面。人格价值层面即价值人格是人格的核心,决定着人格发展的方向,体现人格的尊严。(44)
人格与人的本质是相互联系的。人的本质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是人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根本点。人的本质是对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矛盾及规律的抽象概括,而非就个体的人而言。“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45)人的本质强调的是人区别于“非人”的共同性;人格则突出人的个性。但人格的承载者是人,首先具有人的本质属性。人格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它是人的本质的个体差异性的反映,是人的共性与个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人格与人性也有着本质的联系。人性又称人的本性、秉性。它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行为特征。人性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本质深藏于内,而人性表现于外,它们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人格与人性有内在的统一性。“人性”、“人品”与人格是同等程度的范畴。人的本质的个体差异性,决定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格,表现为人的特殊的具体存在样式。人格与人性基础的共同性,又要求人格与人性认同,寻求与人性的契合。因此,人格只有相对人性才有意义。不在社会中的人,失却了人的本质,也无所谓人格。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46)所以,只有当个人的本质基础得到与人类共同本质一致的发展,人格趋向了与人性的统一,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这一内在联系,要求个体行为的价值标准应该符合人类整体价值标准,表明健康高尚的人格就在于与人性的高度吻合。但应该注意,这种人格向人性的趋向与吻合,虽然涉及社会道德生活和价值问题,但并非以社会要求、道德观念来代替人性和规范约束人格。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和加重“人格面具”即双重人格的现象。
人格通常表现为角色人格,角色是人格的外在表象。社会学角色理论告诉我们,角色是现实特定的社会单元,角色关系就是基本的现实特定关系,角色和角色关系具有鲜明和突出的现实特定性。作为对现实特定关系的反映的人格,显然是在与角色的关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格与角色的关系是内在与外在的关系,二者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人的人格具有整合性、稳定性,而其在社会中担任的角色则是多重的、多向度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丛”。人格形成和发展的理论说明,人格正是由人的角色活动来塑造的,个体通过角色的地位、作用和资格要求体现其特性,展现其做人的资格和实现做人的价值,使其人格在角色化的过程中获得发展,这就是人格的角色化。而另一方面,在角色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格必然对角色活动产生反作用,使角色活动具有了鲜明的个体人格特色,这就是角色的人格化。角色的人格化便是角色人格。
角色是有权利和义务的,它要求角色扮演者维护、行使和实现权利,履行角色义务和承担角色责任。这正是法学意义上的人格规定,是在权利与义务上对人之为人的资格的确认。这一规定并不与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人格规定相排斥,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主张在哲学意义上来规定人格。我们把角色人格规定为:以角色权利为基础,以角色职责为标准,以角色认同为关键,以角色能力和品行为核心的结构体系和存在方式。角色权利和角色职责,是角色的客观规定和角色人格的客观基础,角色认同、角色能力和角色品行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角色认同、角色能力和角色品行是角色人格的主要内容。同时,角色人格中含有某种角色自由,它保证角色扮演者的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角色人格的实质,是角色扮演者对角色要求的适应性。适应的基础是客观存在的角色权利、职责及各方面的要求,适应的前提是扮演者对该角色的认同,适应的条件是具有担任该角色的能力和品行,适应的关键则是角色扮演者的自由创造性。没有认同就谈不上适应;只有具备能力和品行,才可能适应;只有自由,才有主动和真正的适应,才可能有长期和持续的适应。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政府行政的“工具”的行政人员应否具有人格?是否具有人格?按韦伯的官僚制设计,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是不应该渗透入个人人格因素的,这样才能保证行政的公正性。公共行政人员只能是没有精神生活的专家,没有良心的感官机器,是“螺丝钉”。一个真正的公务人员是不能有个人的人格、信念、价值判断的,他(她)必须恪守卡尔·波普所说的“齿轮”精神。当然这种理性官僚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各种批评,韦伯本人也对这种无人格的“人格”感到绝望。在其现实性上,这种理想的官僚制从来没有过,今后也不可能出现。
对此,我们的基本预设是:公共行政人员(群体或个体)因其特殊的职业和角色,具有独特的人格特征。基于此预设,衍生以下具体预设:(1)行政人员的人格是一种角色人格;(2)行政人员不但具有各异的个体人格,而且共享一种普遍人格即组织人格;(3)行政人员的人格影响其行政行为,并因此影响政府形象;(4)行政人员的人格是影响政府文明行政的重要变量。因此,行政人格就是行政人员的人格,即行政人员依据行政职业要求和角色规范,通过行政活动展示自身及组织价值尊严的身心结构的总和,它体现为行政人员良好的能力水平和道德涵养,是丰富的内在行政精神与协调的外在行政行为的有机契合。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及组织价值尊严的载体,承载并体现行政价值。它是行政人员内在的行政精神和外在的行政行为组成的结构体系。
行政人格研究无法回避其暗含的本体论基础,但是如果将人格作为一种方法加以谨慎运用,对于公共行政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将有助于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中更好地理解公共行政,并具有很强的应用意义。
从研究对象来说,由于公共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地位,正如达尔、沃尔多等所论,人格研究必然聚焦于公共行政人员,这是研究能够进行并具有意义的必然保证。但是聚焦并不意味着隔离,人格研究要通过焦点透视整个公共行政生态领域内的各种因素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力,同时也要从这个焦点看到公共行政人员所折射或者衍射的光线,在整个公共行政生态系统中留下的痕迹和变化。因此,人格研究既要聚焦于公共行政人员,却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行政人员,它是一个聚焦同时又发散的过程,一种全面的研究思路,这需要从观念中打破一般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区分的界限。
从知识结构来看,人格研究也试图沟通传统人文哲学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知识体系。在当前的认知领域,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应有的分裂,一种是强调客观和科学的经验主义范式,另一种是思辨和意义探究的诠释范式。实际上这两种思路各有其优缺点,亟待综合。人格研究一方面注重对行政人格界定的内在自我感,另一方面也重视行政人格构成的外在经验事实和结构,获得一个相对全面的认知图式。
从公共行政研究的现有方法来看,除了一些传统方法外,人格方法也不乏见。如西方国家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的名著:《公共行政的精神》(H.George Frederikson)、《行政伦理学》(Teery L.Cooper)、《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Kron,R.M)等,国内如张康之、王伟等一批学者的论著,在研究方法或称为研究范式上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运用了伦理方法,亦即伦理分析的方法,其焦点在行政人员的伦理人格。库珀在其《行政伦理学》中很明确地说明,“本书采用的叙述方法主要是描述法和分析法……本书为我们指出了通向公共行政伦理的可能途径:行政人员个体掌握分析和解决具体伦理困境问题的技术,以及各组织和管理部门的合作以培养负责任的行政行为能力”。(47)还有从心理学人格方法研究公共行政的,如弗罗伊德、戴蒙德等。这些视角为人格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知识,伦理学的、心理学的,抑或是社会学的、法学的等视角和方法,都从某个方面揭示了人格对于公共行政的方法论意义,找到了人格作为重要变量影响政府行政的依据。
但是人格研究注重行政人员个体,是一种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被我国研究者接受和运用尚有一些障碍。一方面由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路径依赖对很多中国研究者的思维构成了强大的束缚,客观上排斥个体主义方法论。(48)另一方面个体主义方法论可能会遭遇政治正确的困境。整体主义的宏观研究,不会牵涉具体的行为者,可以泛泛而谈,不会得罪相关行政参与者;而一旦在研究中明确界定行为者及其偏好目标,就会直接牵涉公共行政中的参与者,形成一种无意的批评,很容易触到“雷区”。(49)但从研究和解决问题的需要来说,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可以和应该尝试的。
作为研究方法,行政人格研究基于以下假定:(1)只有个体才有目标和利益,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只有落实到个体利益,才是现实的利益;(2)行政组织和制度的变迁往往产生于个体行为;(3)大多数行政现象往往可以从个体的气质、信念、能力、品德、资源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加以解释。个体的目标和利益不一定是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感兴趣,还有政治利益、安全利益,(50)甚至还有内在的精神利益。如布劳格指出的,“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作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像宏观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51)。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主张离开个体去谈群体,不否定群体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讲“行政人员”就是认可了一个有着同质化的职业群体。我们只是强调,需要从个体的视野来研究群体。这犹如哈耶克所说:“那些伟大的个人主义作家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实际上是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通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52)。同时,我们反对片面强调个人对组织和制度的作用,我们强调的是个人或个体(行政人员的和民众的)关于他们的利益的观念应成为分析的目标取向,强调公共行政研究与实践将从以市场为中心和以政治为中心的方法中解脱出来,转到以关心个人的基本权利、尊严、经济和社会福利等观察点上来,开阔研究思路和视野。因此,公共行政研究(尤其在中国),关键的不在于是不是纯粹的“经济人”或“行政人”、“公共人”等,关键在于研究中能不能看到“人”(actor)。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视,应该是当代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彭和平等编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②杨艳:《行政人格研究现状及述评》,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③罗伯特·A.达尔:《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载彭和平、竹立家等《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160页。
④德怀特·沃尔多:《什么是公共行政》,载彭和平、竹立家等《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198页。
⑤Freud,Sigmund.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ego.New York:Bantam Books,Inc,1922/1989.
⑥Diamond,Michael & Allcom,Seth.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stress in complex organizations.Administration & Society,1985 Vol.17,No.2(August):217-239.
⑦孙耀君:《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页。
⑧道格拉斯·默里·麦格雷戈:《企业的人的方面》,载彭和平、竹立家等《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218页。
⑨(14)(17)(18)查尔斯·T.葛德塞尔:《为官僚制正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49,152-153,223,153-158页。
⑩Robert Merton.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Social Forces 17(1940):560-568.并参见罗伯特·K.默顿:《官僚制结构和人格》,载彭和平、竹立家等《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1)(15)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5、112页。
(12)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Warren Bennis.Beyond Bureaucracy.New York:McGraw-Hill,1973.
(16)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211页。
(19)杨艳:《行政人格研究现状及述评》,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0)张金鉴:《行政学典范》,(台湾)中国行政学会1997年版。
(21)张润书:《行政学》,(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版。
(22)王沪宁、竺乾威:《行政学导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
(23)张分田:《亦主亦奴——中国古代官僚的社会人格》,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24)李善岳:《行政态度——指导行政活动的定向器》、《行政气质——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条件》,载《江西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1、2期。
(25)张丽锦:《不同职级行政管理人员人格特质的比较研究》,载《宁夏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26)崔会玲、刘立惠:《公务员心理困境产生的原因分析》,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7)参见赵世明《领导干部人群的心理健康及其人格特质分析》,载《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霍团英:《中表年处级干部心理健康及人格特征调查分析》,载《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年第4期;张玲、李燕等:《关于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载《理论与现代化》2002年第4期。
(28)李磊、马华维等:《公务员行政管理心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9)在这方面的研究如刘宏艳的《公务员职业倦怠成因及对策》,载《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朱立言的《我国政府公务员之工作倦怠研究》、张鹏的《公务员职业倦怠成因及干预对策》,载《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4期,孙连荣的《国家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人格因素研究》,载《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1期,等等。
(30)马文运:《社会转型中的行政人格》,载《决策探索》1994年第12期。
(31)李春成:《行政人的德性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2)谢新水:《论行政人格转型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载《学术论坛》2006年第9期。
(33)[日]杉村章三郎:《行政机关的人格性》,载何勤华主编《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34)[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35)参见马骏、叶娟丽《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6)转引自[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7)(38)刘骥:《找到微观基础》,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39)罗伯特·K.默顿:《官僚制结构与人格》,载彭和平等编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40)赫伯特·A.西蒙:《行政管理格言》,载彭和平等编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49页。
(41)罗伯特·A.达尔:《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载彭和平等编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166页。
(42)德怀特·沃尔多:《什么是公共行政学》,载彭和平等编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43)余潇枫:《哲学人格》,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4)详细的阐述见陈建斌《行政人格概念辨析》,载《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3页。
(47)[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48)(49)(50)刘骥:《找到微观基础》,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51)(52)转引自朱宗伟、于建嵘《现代经济分析的原则和工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标签:公共行政论文; 心理学论文; 人性论文; 行政人员论文; 分析心理学论文; 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行政管理学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角色理论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