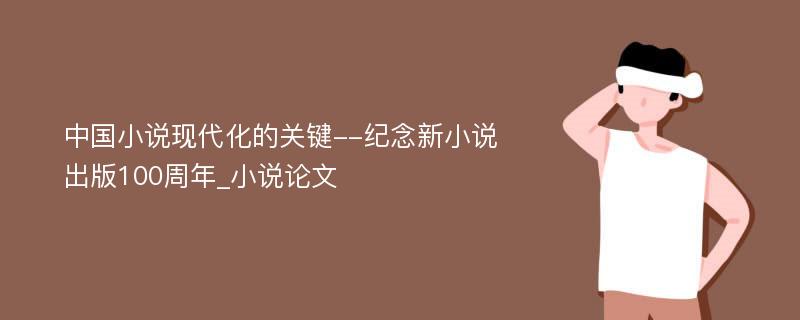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一大关戾——纪念《新小说》创刊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大关论文,中国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4-0080-07 收稿日期:2003-02-15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由梁启超主持的《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正式吹响了“中国小说界革命”的号角,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创作与理论由古典转向了现代,开创了中国小说发展的新纪元。关于创办这一杂志的目的、宗教、内容与特色等,早在同年(光绪二十八年)七月的《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上发表的《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已作了完整而扼要的绍介。梁启超所取“新小说”之名,其“新”字当为使动词,原意就是“使小说新”,进行“小说界革命”,但后来往往也有人将它理解成偏正结构“新的小说”。事实上,《新小说》尽管仅出了24期,但它的确催生了一大批新型的小说与小说杂志,使整个小说界呈现出一派新的面貌。一时间,新型的小说杂志《绣像小说》(1903)、《新新小说》(1904)、《小说世界》(1905)、《月月小说》(1906)、《小说林》(1907)、《中外小说林》(1907)等接踵而至,标着“新小说”牌号的译著大量面世,新式的小说论文也纷至沓来,这正如当时的吴趼人所说:“吾感乎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期所刊)之说出,提倡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1](P232)“新小说”之“新”,还不仅仅在小说译著与编刊的繁荣,而更深层次的是表现在小说内容与形式同时在“新”,在现代化。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实业小说、侦探小说、理想小说、国民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种族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开智小说等等,其所叙的内容一般均为前所未有,其表述的角度与方法也有诸多创新,语言也在有意识地由雅向俗而新变。这是“新小说”之“新”的第二层次的表现。第三层次则表现在社会对于小说的观念普遍更新。小说从文学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同时,也是新民强国的最得力的工具。小说“向所视为鸩毒”,而却迅即成为“最歆动吾新旧社会,而无有文野智愚咸欢迎之者”[1](P292)的时代宠儿。黄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形象地描述了《新小说》后小说的风行和观念的转变:
今之时代文明交通之时代也,抑亦小说交通之时代乎!国民自治,方在预备期间;教育改良,未臻普及地位;科学如罗骨董,真赝杂陈;实业若掖醉人,仆立无定;独此所谓小说者,其兴也勃焉。海内文豪既各变其索缣乞米之方针,运其高髻多脂之方略,或墨驱尻马,贡殊域之瑰闻;或笔代燃犀,影拓都之现状。集葩藻春,并亢乐晓,稿墨犹滋,囊金竞贸。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特起者,小说也。四方辇致,掷作金石声;五都标悬,烁若云霞色者,小说也。竹罄南山,金高北斗;聚珍摄影,钞腕欲脱;操奇计嬴,舞袖益长者,小说也。虿发学僮,娥眉居士,上自建牙张翼之尊严,下迄雕面粥客之琐贱,视沫一卷,而不忍遽置者,小说也:小说之风行于社会者如是。狭钭抛心缔约,辄神游于亚猛、亨利之间;屠沽察睫竞才,常锐身以福尔、马丁为任;摹仿文明形式,花圈雪服,贺自由之结婚;崇拜虚无党员,炸弹快枪,惊暗杀之手段: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又如是。则虽谓吾国今日之文明,为小说之文明可也;则虽谓吾国异日政界、学界、教育界、实业界之文明,即今日小说界之文明,亦无不可也。
黄摩西对此过热的现象有所不满,但这确是反映了当时小说界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新小说》,归功于梁启超,但梁启超与《新小说》确实在这场历史性的变革中为功最高。后来五四一代人在评价包括这场小说革命在内的晚清文学革命时就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1](P501)至30年代,吴文祺在《新文学概要》中论及晚清文学革命与五四后的新文学的关系时也形象地说:“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化以后,逐渐发展,逐渐长征,至五四时期始呱呱堕地。胡适之、陈独秀等不过是接产的医生罢了。”至90年代末,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高度肯定了“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功绩”。总之,《新小说》与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是使中国小说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一大关戾,这是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但是,在如何公允、全面地评价《新小说》与“小说界革命”时,还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一会儿,以政治挂帅、以“革命”挂帅,认为梁启超后期从改良走向保皇,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对抗,因而无视或有意贬低他的历史功绩;一会儿又以“纯艺术”论挂帅,认为梁启超主张“新小说”为“新道德”、“新政治”等服务,过分地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从而削弱或无视了小说的艺术性,从而把整个20世纪小说创作的不足或失败、甚至将“文化大革命”统统与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挂上了钩。因此,在此纪念《新小说》创刊一百周年之际,我想就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功利性与艺术性的问题。本来,办任何杂志都有一定的目的。创办《新小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抢占小说的阵地,利用小说来开发民智,来“新民”,来“改良群治”。《中国之惟一文学报〈新小说〉》开宗明义就说得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要创办这一杂志,就是因为认识到“小说之道感人深矣”,而长期以来学者普遍“反鄙小说为不足道”,于是“好学深思之士君子,吐弃不肯从事,则儇薄无行者从而篡其统”,终致“小说家言遂至毒天下,中国人心之败坏,未始不坐是”。因此,他们要“集业务而从事”新小说的工作,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明确宣布:
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
后于《新小说》正式创刊时,即在第一期上发表的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头,又用了斩钉截铁的语气宣称: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人格,必新小说。
与开头相呼应,在结尾处又作了这样的概括:“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总之,梁启超办《新小说》,第一层目的是要使传统的小说发生新变,而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用新的小说来提高国民素质,改良社会政治风气,具有明确而鲜明的功利性。
我们在评价《新小说》的功利性时,首先应该考察他们所追求的功利是什么?该肯定还是该否定?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亡国亡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戊戌变法失败,改良维新之梦夭折,中国向何处去?梁启超在逃往日本的船上翻译《佳人奇遇》之余,写了一篇《译印政治小说序》,还不忘借用他所认为的“欧洲各国”政治变革的经验,鼓吹译印“政治小说”来直接推动中国的“变革”。但不久,他即深感到群众的不觉悟,“变法”、“新政”就难实现,当务之急是“新民”,是提高国民的素质。“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他借黄克强之口说:“世界上哪能一个国不是靠着国民再造一番,才能强盛吗?”“一国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智、民气三者具备,但民智还容易开发,民气还容易鼓励,独有民德一桩,最难养成。倘着无民德,则智、气两者亦无从发达圆满,就使有智,亦不过借寇兵赍盗粮;就使有气,亦不过一团客气,稍遇挫折便都消灭了。”总之,群治改良的基础,即在于再造“民德”;只有先“新民”,才能“新政治”。他的这一认识,与孙中山等主张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当然不同。辛亥革命后来虽然基本成功了,但不等于说“新民”是不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鲁迅小说《药》中所描写的那种对于革命麻木不仁的群众,即揭示了革命的不足之处,也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所以“革命”与“新民”的大方向应该说是一致的,尽管当时他们为了争夺民众的领导地位而闹得不可开交,但事后看看,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为了改造中国,富国强民,都是值得肯定的。胡适在辛亥革命后一年所写的《藏晖室札记》中曾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这段话就较好地说明了“新民”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梁启超等办《新小说》时追求的功利是值得肯定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即是文学该不该有功利性?自从王国维、周氏兄弟引进所谓“纯文学”的理论之后,不时有人将文学有功利性嗤之以鼻,认为文学当为象牙塔里个人言志缘情的东西。特别是“文革”以后,人们从过分强调文学的功利性、政治性的圈子中跳了出来,纷纷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抒发感情,张扬个性,表现人性,看重远离功利的“纯文学”。在这些人看来,20世纪错就错在不断地强调“载道”,文学的进步被功利与政治绊住了脚。其实,文学都是有某种功利的,自娱自乐,难道不是一种功利吗?王国维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解脱难道不也是追求一种功利吗?说到底,所谓“纯文学”与“功利性”的不同,只是在于追求的功利大小不同而已:是吟诵个人一己之私情,还是抒发一时之群情?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动物,“群”也是人的本性。歌唱群情同样可以抒发真情,同样有其艺术的真价值在。因此不难理解自古以来,杰出的作家都是富有人文精神,都是关心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百姓的疾苦,伟大的作品多数是与广大百姓的脉搏在一起跳动的。当然,我们不应该就此否定那种纯私情的批风抹月、吟山诵水、哥哥妹妹、卿卿我我的东西,它们自有它的价值在,也有不少优秀的作品能永远引起人们的共鸣。但不可否认,它们之中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乌七八糟的靡靡之音。因此,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写私情,还是写群情;是“纯文学”,还是有“功利性”;而是在于写的情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而且,这种情,还得放在当时时代中来加以考察。在《新小说》的时代,广大的百姓是需要什么样的情?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的20世纪,究竟更需要什么样的情?即使在现在,当我们眼看着超级大国在世界上横行霸道,发号施令,不断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着一些贪官污吏花天酒地、一掷万金,而广大贫困地区的儿童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时候,难道就一味强调作家躲在象牙塔里写那些纯之又纯的“纯文学”吗?就一味鼓吹文学围着一个自我转吗?就不要张扬群情、人文关怀吗?事实上,一部世界文学史早就证明,文学是复杂的,其价值同样也是复杂的,我们决不能将它简单化。
再进一步看,梁启超创导的“新小说”并非是不要艺术性,否定艺术性。他之所以强调小说有巨大的社会作用,是“新民”与“改良群治”的重要工具,就是因为他对小说的艺术特征及其感染力自有其独到的理解。早在《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他就指出小说“文体”的特点是:“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有非寻常文家能及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就进一步说明小说除了“浅而易解”之外,还有“乐而多趣”的特点。这是由于小说既能将人生“和盘托出,彻底发露之”,又能“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在这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小说的四种感染力:薰、浸、刺、提,引进了西方的文论术语,将小说划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类。应该说,他在小说艺术方面的探索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前人笼统、零碎、感想式的批评,而是以新的阐述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这种明显带有现代特征的批评方式及其认识也是开一代风气的。更可贵的是,他不但在理论上创导,而且还身体力行,亲自投身于创作实践。《新中国未来记》尽管在艺术上并不成功,弄得“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但其创新开拓的精神还是可嘉的。例如,他有意“全用幻梦倒影之法”,就多少吸取了西方小说的新的表现手法。《新小说》也曾明确主张历史小说用“恢奇俶诡之笔”,探侦小说要做到“奇情怪想,往往出人意表”,传奇小说要注意“词藻结构”,乃至如《东欧女豪杰》就注意“事迹出没有变化,悲壮淋漓,无一不出人意想之外”等等[1](P33),无不说明他们在艺术表现上也是有所考虑的,只是由于他们精力有限,在这方面的确没有下更大的工夫,以致作品的艺术未能达到上乘。这是无庸讳言的事实。但是,假如我们以历史宽容的态度来看问题,应当允许新生的事物有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由粗糙到精细的过程。现代小说整整走了一个世纪,究竟有多少在艺术上经得起大浪淘沙的作品呢?为什么要对刚刚出土的萌芽求备责全呢?我们应该高度肯定它的开创之功,至于艺术上的完美还是让后人来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吧!
二、理论与创作的问题。《新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理论与创作并重。《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在介绍“本报之内容”时对“论说”部分作了如下的说明:
本报论说,专属于小说之范围,大指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如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题尚夥,多不能预定。
这说明,他们之所以要设置“论说”,其目的也就是为了推动“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而其大致规定的内容,也都是紧紧地围绕着这一目的。后来实际上发表的一些理论文字如《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小说丛话》、《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等,都是根据这些论题进行的。其中,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影响尤大。假如说《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是“小说界革命”的宣言的话,那么《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则是“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此文伴随着创刊号《新小说》一出,就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小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首先引起强烈反响的就是一些诸如小说的社会作用、小说的价值、以及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评价等理论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如关于小说的社会作用问题,狄平子、王钟麒、陶佑曾等赞同梁启超的观点,甚至更加强调“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1](P41),认为“几几乎可以改造世界矣”[3],因而“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必先打开小说革新的序慕[1](P34),而曼殊、徐念慈、黄人、黄世仲弟兄等认为“无论何种小说,其思想总不能出当时社会之范围”[1](P58),“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1](P298),“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1](P250),“时势造小说耶,抑小说造时势耶?是二者固未可决言。”[4](P955)。这场讨论尽管及时地纠正了梁启超等人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颠倒小说与社会关系的偏颇观点,但由梁启超、《新小说》引起的这场讨论,毕竟使人们对于小说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功也不可没。而更重要的是,由《新小说》所开创的这一重视“论说”的风气,被同时的小说杂志所普遍接受,它们往往辟有专栏,刊载议论文字,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小说理论批评与小说研究的发展。而这小说理论文字为“新小说”摇旗呐喊,又有力地推进了新小说的创作,其中还有不少文章如寅半生的《小说闲评》、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小说管窥录》、《觉我赘语》,以及无名氏的《读新小说法》等,都是直接总结与指导“新小说”的创作与阅读的,它们与新小说的繁荣,关系就更为密切了。因此可以说,没有“新小说”理论上的活跃,也就不可能有“新小说”创作上的繁荣。
但是,我最近读到一篇论述梁启超小说观念的文章说:
“新小说”等观念开辟了一个“观念”世纪。由于西潮(现代化)的冲击,给20世纪的中国人带来种种新的观念,在文艺上就形成所谓的文学思潮。每当一个新的文学思潮开始,总是以某种“新”观念为标志……仔细研究一番,定然不难看出,提出观念的人一般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创作成就,创造出丰富的艺术成果的大家却都不是以提出观念为能事者。如今……观念的意识形态成份对文学的渗透少了,对一般社会的冲击力也小了,小说像漫游的浪子回家一样寂寞地回归本体了。如果我们不由“观念”来考察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与“观念”保持一定距离,通过那些特别注重小说文体的重塑与现代化中西、雅俗整合的作家作品来考察,那会形成怎样的一种与观念史相区别的小说史呢?[5]
这位作者不喜欢用“观念”来考察文学史,从而也不喜欢提出一个“新小说”的观念,似乎文学史就是创作成果的历史。事实上,文学的历史有创作的历史,也有观念的历史。创作有创作的价值,观念也有观念的价值。观念与创作又从来不是分割的,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新的小说往往与新的观念相联系,“创造出丰富的艺术成果的大家”尽管未必都是“提出观念为能事者”,但不可否认他们一般都在“观念”上自有一套,往往也是个先进者,这样的作家在中外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挑一个中国小说创作最有成就的大家曹雪芹来说吧,他在创作《红楼梦》时,就激烈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历代野史”、“风月笔墨”与“佳人才子”小说“都是一个套子”,提出了“新鲜别致”、“谈情”、“适趣”等观念,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至于那些以理论见长者,尽管其创作并不突出,但他提出的“观念”还是在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比如严羽,提出了“兴趣”、“妙悟”等新观念,就深刻地影响了元明清几代人的创作与理论。梁启超及《新小说》所提出的一些新观念,尽管有许多不成熟的、乃至偏颇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我们决不能因为它的粗糙与偏颇而将它一笔抹煞,乃至进一步将整个观念上、理论上的创新都一笔抹煞。
三、编者与读者的问题。《新小说》作为一种杂志,之所以能开创了一代的风气,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是编者有清晰而崇高的目的,能认真而艰苦的工作,而且也在于它能注意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读者在其周围。本来,梁启超他们的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广大国民,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新小说》也是为了“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1](P31)这样,他们就必须面对广大的“粗人”[1](P114),但实际上,广大的民众既无接受新观念的精神准备,也无接受新小说的物质基础,真正能接受新小说、新观念的还是一批敏感的知识分子,所以《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所寄予希望的就是“新世界的青年”。与此同时,梁启超的办报理论也发生了变化。从《清议报》起已开始刊登广告,《新民丛报》则比较明确地采用了股份制,梁启超所持的股份占三分之一。他既是主笔,又是最大的股东。1907年7月,他在给徐佛苏的信中说:“办报固为开通社会起见,亦必须求经济可以独立支持。”实际上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再到《新小说》,他在办报时已逐渐把启蒙与经营合为一体,他是主笔,又是经营者;读者是启蒙对象,同时也是消费群体。为了满足读者市场的消费需求,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阅读《新小说》,热爱《新小说》,梁启超还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与尝试。其《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标题下原有小字注:“每月一回,十五日发行,洋装百八十叶。”正文中又详细地说明了订购的情况。梁启超这样将杂志定期出版,并与《新民丛报》一样,改用铅印与洋装相结合的技术,这给读者的阅读翻检带来了便利,受到了欢迎。这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梁启超在日本的小说出版活动,虽然时间不长,又因为距离国内读者市场较远,出版的数量也不太大,但却促成了小说与定期、刊物、与铅印洋装技术的结合,确立了近代小说出版的基本规范,并带动了中国小说出版形态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其作用应该得到重视。”[6]除此之外,梁启超又注意处理了以下几个关系:
第一,译与著的关系。梁启超曾将中国古代小说视为“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强调移译外国的政治小说来推动中国的变革,这的确产生过一些不良的影响。一时间,“著作者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1](P298),很多粗制滥造的外国小说因不如“著书之经营久、笔墨繁、成本重”而“呈功易、卷帙简、卖价廉”[1](P298),风行于社会。然而,梁启超在主观上对译、著的比重还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说得很清楚:
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构,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
事实上,《新小说》也是贯彻这一方针的。在当时,不论从启蒙,还是从销售的角度来看,翻译小说,扩大视野,引进新思想、新知识、新事物,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梁启超还是强调“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要以中国文学为本的。所以他提出的译著各半的比例也是合适的。这正如稍后黄世仲在《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一文中所说的:“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扬镳分道,其影响于社会者,殆无轩轾焉。”
第二,雅与俗的关系。关于《新小说》所采用的语言,一开始就定下了这样的原则:“本报文言俗语参用。”梁启超之所以强调采用俗语,不仅仅是因为认识到“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1](P52),它的特点就在于“浅而易解”[1](P41),便于广大国民所接受;而且也由于认识到语言的通俗化是文学现代化的大势所趋。他一再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展开,靡不循此轨道。”[1](P52)“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1](P119)因此,他大力提倡和亲自实践创作通俗小说,推动了清末文学白话化的运动。但当时毕竟是处于一个新旧过渡的时代,多数知识分子还是熟悉雅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对此,徐念慈曾很有感慨地说:“若以臆说断之,似白话小说当超过文言小说之流行,其言语则晓畅,无艰涩之联字,其意义则明白,无幽奥之隐语,宜乎不胫而走矣,而社会之现象,转出于意料外者!”这是因为当时购小说之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旧学界”出身的知识分子。无怪乎林琴南被奉为“今世小说家之泰斗”,崇拜他的人最多[1](P301)。在这样的情势下,显然应当照顾到“文言小说”,以最大多数的争取到读者。
第三,文与画的关系。《新小说》中专辟了“图画”栏,也是争取读者的重要措施。《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对此有如下说明:
专搜罗东西古今英雄美人之影像,按期登载,以资观感。其风景画,则专采名胜、地方趣味浓深者,及历史上有关系者登之。而每篇小说中,亦常插入最精致之绣像绘画。其画皆由著译者意匠结构,托名手写之。
这里的图画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小说正文无关的图像,另一类是小说中的插画。前者画面主要来自国外,二十四期共载画62幅,只有第9号载“北京宫内北海全景”与第13号载“清太后那拉氏”两幅也为一般百姓所难见者外,其他都为他国的图景。这无疑是为了使读者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满足其新鲜感、好奇心,特别在照相并不普及的当时,加之以先进的印刷技术,那些著名文豪、欧西美人和环球名胜,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后者配合小说内容,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这些图像无疑都会提高读者购买与阅读的兴趣,成为一种有力的促销手段。这种文与画相结合的办刊方略,也为后来的文学杂志所继承。
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动机是崇高的,经营是有方的,成绩是巨大的,中国的小说从此向着现代化一路向前。但是,历史发展的道路往往并不是直线进行的。由于梁启超赋予小说的使命过于沉重,过度、过急地追求现实启蒙的功利,甚至将小说“专欲发表区区政见”,这就势必对“新小说”文体的特征不加深究,阻扼了新小说艺术生命的健康成长;再加上社会政治本身一片混沌,中西文化选择、交融又十分艰难,一时使操觚者纷纷感到迷惘;而稿费制的推广,使作家的职业化与小说的商品化并头齐进。来势汹涌的商品化浪潮,很快就将启蒙家们苦心构建起来的美梦冲得支离破碎,借小说以追求猎奇,专揭隐私,渲染艳情,铺天盖地而来,本来是“新民”的良药,很快就成为媚俗的工具。时间不过十多年,当梁启超这位“新小说”的倡导者再来面对市场上的“新小说”时,不能不使他感到大出意外,痛心疾首。他又不得不一次“告小说家”:
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十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簿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黠者濡染于险诐钩距作奸犯科,而摹拟某种侦探小说中之节目。其柔糜者浸淫于目成魂与窬墙钻穴,而自比于某种艳情小说之主人公。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龌龊,其行谊习于邪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循此横流,更阅数年,中国殆不陆沉不止也[6](P68)。
梁启超将“社会风习一落千丈”的罪责统统归咎于“新小说”,正像他当年把“社会腐败之总根源”一古脑儿地算在古小说的帐上一样,未免失之过当。但“新小说”的发展确实为梁启超始料所不及,滑向了一段斜坡,这也不容讳言。“新小说”之所以走了这样一段弯路的责任,恐怕是不应该算在当年倡导“新小说”的梁启超头上的,这主要还是由于后来“著书与市稿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1](P315)所造成的恶果。书生们在一股政治热情的激荡之后,看不清国家进步的希望,找不到个人晋身的捷径,无心于探寻艺术的精微,热衷于追求眼前的利益,“新小说”的光环,就此被铜臭销蚀殆尽。这也是小说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历史教训。直到新文化运动起,又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重新使小说界振作起精神,将小说的现代化又推向了另一个新的境界。今天,当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一步一步地推进小说现代化的时候,回首一个世纪之前,看看《新小说》,看看首倡“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们,一种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们的历史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最后,就借用老杜的一首诗,权作本文的结束吧: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标签:小说论文; 梁启超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一大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