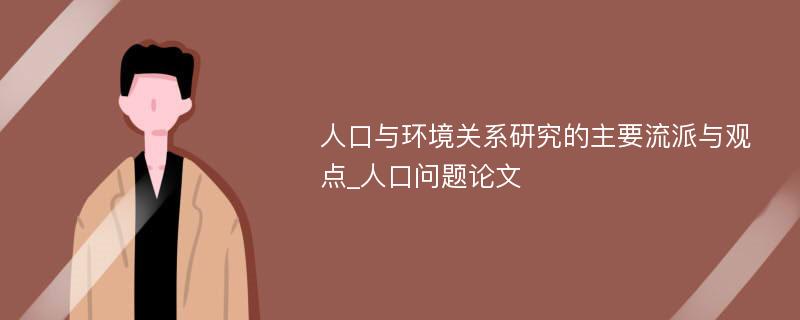
论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的主要思想流派与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人口论文,观点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29X(2003)05-0010-05
一、前言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人们同时目睹了世界上的两大变化趋势:世界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伴随着人口增长而出现的资源迅速消耗与环境恶化。而人们关于人口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与争论,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近50年来,世界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更加严重,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和研究热情。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了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
然而,由于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涉及的内容之广泛,要素之众多,研究者的研究背景和领域之复杂,超过了任何一门学科,因此导致目前人口与环境研究领域中的多种思想流派和观点的不同甚至对立。也由于研究层次的不同,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造成对同一问题的诸多不同结论,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尽管如此,由于如下的几个原因:(1)人口与环境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即都是研究人口与环境的关系,确切说,研究人口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以及环境变化对人口的影响;(2)已经形成一批专门从事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的专家队伍;(3)大量关于人口与环境研究成果的问世。毫无疑问,人口与环境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在此,非常有必要对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思想渊源和理论的形成,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综述,以便对这门学科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本文在阅读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对国外人口与环境研究的思想流派和观点进行简单的归纳、回顾和评述。该综述免不了挂一漏万,不足以真正阐述国外该领域研究的全貌。但可以提供一个目前国际社会对人口与环境领域研究的基本线索,供有关方面参考。
二、人口与环境研究的主要流派与思想渊源
自从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关于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讨论以来,在这个研究领域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流派,有些是针锋相对的论争。这种论争至少已经进行了两个多世纪。从思想渊源和基本观点来看,基本可以分成这样几大流派:
1.从马尔萨斯主义到当代马尔萨斯主义的悲观论派
马尔萨斯主义思想体系最早的代表人物可以追溯到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1697-1771)。早在1761年,他在《人类、自然和上帝保佑的各种前景》这本书中,就写到一个平等的社会将会自我崩溃,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婴儿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照料,从而导致死亡率下降,这样人口的过快增长将会超过地球的承载量。他强调人口的自然增殖能力,认为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将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肥力、气候、瘟疫以及战争、贫困等会限制人口的增长,从而人口得到控制。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在1798年出版了著名的《人口原理》,他沿袭了华莱士的观点,提出了两个级数理论,即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生产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因此食物生产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由于食物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自然界将通过饥饿、疾病、灾荒、战争等制约着人口的增长。后来在该书第二版中,他又增加了人口自我控制,通过晚婚、不婚、节欲等,即所谓道德的约束。由于马尔萨斯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对比观点,被国外人口学界作为人口学的创始人。自从马尔萨斯的观点和论述问世以来,遭到了包括社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学者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从此拉开了人口与环境关系长期论争的序幕。
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与马尔萨斯的基本观点一脉相承。但是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上与马尔萨斯有所不同,即提倡采用避孕节育措施,因此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其最显著的代表人物是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R·卡莱尔(R.Carlile)等。例如普莱斯试图用人口统计数字来证明“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快繁殖”。他与马尔萨斯一样,也把人口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更快的趋势”看作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并认为不抑制人口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出现了一大批当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品和人物。他们的主要观点与新老马尔萨斯基本一致,但是随着世界粮食的生产超过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随着工业革命和农业技术革命,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当代马尔萨斯的研究内容,已经扩展到不可再生资源与环境污染与人口的关系方面,而且所采用的方法也进一步复杂化。例如美国的皮尔逊(F.A.Pearson)(1945)和哈伯(F.A.Harber)的《世界的饥饿》(1948),美国福格特(W.Vogt)的《生存之路》(1956),美国赫茨勒(J.O.Hertzler)的《世界人口危机》(1956),艾利奇(P.R.Rhrlich)的《人口爆炸》(1968)以及英国学者泰勒(G.Taylor)的《世界末日》(1970)等。他们普遍认为,世界人口如果按照原有的速度增长下去,势必造成粮食危机、自然资源枯竭,甚至面临“世界末日”。他们都把人口增长看作是目前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减少人口的增长,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
1972年,丹尼斯·梅多斯和他领导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可以说是当代马尔萨斯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们试图用定量方法证明艾利奇等的观点。他们采用系统动力学计算机模型,模拟了在人口、资源、食物、工业产出和污染条件下的世界经济状况。他们预言,在正常方案下,矿物资源和土地将会在21世纪初出现戏剧性短缺,2025年人口会出现崩溃。其他方案也不能好多少:人口的增长和输出总是超出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地球的同化、承载废物能力,随着人口的增长,可耕地的极限和人均农业产出的下降导致饥荒只是个时间问题。即便食物增长了,工业产出将耗尽能源和矿产,导致毁灭。即便这种状况避免了,工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也会超过地球的同化、吸收能力,在一个世纪内导致崩溃,世界末日不可避免地来到。要想挽救世界,有一个办法,就是将人口稳定在1970年的水平上,大量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单位污染的排放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非工业化、太阳能的使用和所有废弃物的循环使用。20年后,梅多斯在这个书的基础上出版了《超越极限的增长》,增加了技术进步和经济与资源之间负反馈环的限制,然而,有限的资源和指数增长的人口的假定未变,导致了同样的悲观结论。
2.马克思主义者的对立观点
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没有专门论述人口与环境问题,但是在与马尔萨斯主义的长期论争过程中,多次涉及到人口与物质资料(从而土地资源)的关系,所持的观点和立场与马尔萨斯主义针锋相对,因此在此不能不提到这一派的观点。而且,他们对当前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论争,可以追溯到威廉姆·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思想。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威廉姆·葛德文,在1793通过其著作《政治正义论》(I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严厉驳斥了华莱士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永远不可能增长到生存能力以上。他认为地球可以供养许多个世纪的人口,没有必要来为遥远未来的不可知事件而沮丧。相反,他看到了人类社会自私、不平等、犯罪和战争的弱点,认为这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解决社会贫困等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减少人口。
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人口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基本上是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中形成的。他把马尔萨斯观点叫做“对人类的诽谤”。他认为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法则。不存在真正的人口过剩,人口过剩是资本家在机械上投资造成工人失业后形成的相对过剩。恩格斯则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比较系统地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并且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口观点。他在1844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明确指出,马尔萨斯断言人口生来就有一种超过生活资料的倾向,并把他说成是一切贫穷和罪恶的原因,是为私有制辩护。他认为,失业和贫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恶果,并且认为,人口的压力并不是存在于生存手段,而是存在于就业手段。从而批判了人类社会人口增长超过物质资料生产的论点。
3.资源富饶论者的乐观主义观点
与马尔萨斯悲观论者形成较大分歧甚至对立观点的,除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外,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也大量存在。一些西方学者非常(甚至过分)强调人口在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和资源替代等技术上的促进作用,认为在一定的前提下,技术的进步将不会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环境承载容量,所得出的结论与马尔萨斯观点形成非常大的不同甚至对立,对资源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这一派在西方被叫做资源富饶论者(cornucopians)。
这一派比较早的代表性人物应当首推博斯拉普(Boserup)。大约在马尔萨斯观点出现一个世纪以后,博斯拉普在她的《农业增长的条件》一书中,推翻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不是农业的增长决定了人口的增长,相反是人口的增长决定了农业的增长。她多次讨论了在人口密度较大而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是如何改变耕作技术,例如减少休耕期,采用犁具、轮作,灌溉、增加复种指数等以增加粮食产量。如果没有人口的压力,这些旨在提高产量的农业技术就不会采用。所有这些都需要更多的劳力,而在人口较稀少的情况下,人们是不会采用这些需要劳力较多的技术的。博斯拉普也意识到休耕期缩短,坡地上耕种可能导致土地退化,但是她认为修筑梯田、增加肥料和其他技术进步可以防止这种状况出现。由于人口密度增大和人口增多将会引起新的农业技术的采用和农业增产,因此人口的增长不会导致食物短缺。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口与环境的技术论,可以看作是博斯拉普观点在工业革命后的进一步扩展和推广。他们关注的是在一个给定的有限资源和人口增长状况下,经济发展能否维持一个增长的或者稳定的生活水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当人口增长,从而土地资源出现短缺时,土地价格将上升,这样将会促使人们用更丰富的资源去替换土地资源,例如劳力,肥力,灌溉等,或者发展新的技术,例如高产作物品种,增加现有土地的生产力。因此在人口增长情况下,由于上述技术等的采用,土地生产力是上升的,经济发展能够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而不下降。关键的前提是市场必须是完善的,既没有市场的失败,也没有政策的扭曲。否则,人口的增长将会导致土地的退化,并影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学者进一步从技术进步等角度提出了有关资源环境的乐观观点,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赫曼·凯恩(Herman Kahn)、朱立安·西蒙(Julian Simon)等。
凯恩在1976年出版的《下一个200年:美国和世界的方案》书中,反驳了新马尔萨斯的观点。他们不同意人口总是指数式增长,认为人口是按照"S"型逻辑斯蒂克曲线增长,世界人口有望在22世纪能够稳定下来,达到150亿人,到2176年人均收入达到20000美元(1970年不变值)。他提出了推进技术进步,可以推迟资源限制时间的到来,直到它们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为止。由于引入了技术的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或者能够永久地消除一些资源的限制,或者推迟限制直到新的技术能够消除这个限制。另外,食物的限制并不取决于固定的土地,相反,农业技术,高产种子,灌溉技术等最终无土栽培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取消食物的限制。能源最终被清洁能源取代。由于用人口和食物的正反馈取代了增长的极限中的负反馈,因此,他们认为限制人口是不道德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尤其是对穷人是有好处的。
西蒙1981年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一书中,以及后来的《人口增长经济学》一书中,建立了一个人口规模和人类智力之间的反馈关系,这种智力可以引起技术进步从而对短缺产生响应。按照西蒙的观点,人类智力是最终的资源,越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头脑、更大的市场,更大的经济规模,专业化和更容易的交流和最终更大的资源。西蒙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不可再生资源的真正成本将会随着时间按照工资和消费者价格而下降,标志着资源的可获得性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农业土地也一样,当人们对健康的要求呼唤清洁的环境时,污染控制也就到来。短缺仍然会发生,但却是暂时的,人类会发现新的更好的替代和改进的方法的。这样,人口增长不仅导致激励,而且提供方法(头脑),总之,人口越多越好。人口增长不仅容许我们达到最大的利益,而且对子孙后代有好处。西蒙的观点是如此的乐观和极端,以至于他们被称做“富饶论者”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极端对立面。
4.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人口环境关系研究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思想的提出,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也逐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以往研究不同点在于,从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研究人口与环境的关系,目的不在于仅仅说明人口对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而是在于寻求一种在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适宜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因此具有战略研究的意义。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是“既不损害当代人的利益,也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布伦特兰)。在这个概念下,人们不再局限于强调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综合分析人口、环境、资源、经济、社会的关系,将人口与环境的协调放在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下进行,将研究的目标转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所要求什么样的人口条件这样的问题上来。为了研究与可持续发展适应的人口条件,人们作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个是关于资源环境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的扩展。资源环境人口容量研究最初开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比较著名的如198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进行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土地的潜在支持能力》,以及英国爱丁堡大学马尔克姆·斯来斯(M.Slesser)等运用ECCO(Enhancement of Carrying Capacity)对肯尼亚等国家进行的研究。近年来,关于人口承载能力的研究开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结合起来,有人将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容量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标准。例如1987年11月在荷兰举行的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讨班上,斯来斯和金(King)等学者将ECCO技术放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提出人口承载能力的估算能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判断的基础,并进一步认为,如果人口在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之内,发展就是可持续的,否则,就是不可持续的(A.J.Gillbert,1991;Jing,1994)。因此,只要通过适当的方法求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容量,就可以知道是否是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中。
另一个是在适度人口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探讨适度人口条件,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也比较多见。适度人口最初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其创始人为英国的艾德温·坎南(Edwin.Cannan),约翰·斯图亚特(J.S.MILL),卡尔·桑德斯(A.M.Carr-Suanders)等。当代适度人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Sauvey)。基本上是指达到最大经济目标或者经济效益时的人口条件,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以及人口密度等。这一思想近年来逐渐融合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衡量适度人口的目标逐渐从纯粹经济学的指标扩展到社会福利,以及资源环境的指标上,例如美国人口学家麦克尼科尔(G.Mcnicoll)和阿瑟(W.B.Authur)等就是将原来的单纯经济指标修正为人均福利最大化,尤其在福利目标中,将资源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皮彻福特(Pitchfird)则将资源作为定义适度人口的准则之一,认为适度人口是:适当应用资本设备,达到人均消费水平最高,并能维持和提供质量不变的再生资源时的静止人口。实际上,这类研究已经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非常接近,之所以没有直接采用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的标准,主要是因为可持续发展本身的定量衡量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三、结语
我们在此不想对上述这些观点作出简单的谁对谁错这样的评价,因为那样做是肤浅的。实际上这些研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合理的成分,当然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弱点。但是,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出现上述流派和观点上的巨大分歧并不奇怪,主要是由于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观点不同。
1.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不同形成的局限性。
马尔萨斯在200年前并没有预见到技术的进步,他的理论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前。他假定粮食生产力是固定的,人口是指数增长的,因为他没有预见到医学进步导致的死亡率的下降,也没有预见到经济发展导致的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因为他的出发点和假定,人口增长必然隐含着绝对的限制——地球承载人口的能力。
相反,博斯拉普是在农业和工业革命后提出她的理论。她不仅考虑了技术的作用,而且将其作为内生的变量,极大地受到人口增长的驱动。在她的假定下,没有饥荒存在的可能,因为技术进步对人口增长作出响应,资源的限制被消除,马尔萨斯的“承载力”不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在博斯拉普的假定下,马尔萨斯结果出现的唯一可能是,所有的对人口和技术之间响应的通道被堵塞。的确,新古典经济学对问题的阐述,作为博斯拉普的理论在工业上的扩展,就集中在存在扭曲的政策和不完善的市场阻碍了资源短缺信号的响应。对人口-资源短缺的响应的延迟,能够导致马尔萨斯的结果。
2.证据的选择性使用导致了从极端悲观到极端乐观的两种观点。
当代马尔萨斯和极端乐观主义者针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何以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结论?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由于医疗卫生与经济发展导致的死亡率下降和生育率下降,都成为这两种观点的历史事实被记录下来,但是他们的解释却完全不同。当代马尔萨斯论者集中在定量上,资源丰饶论者集中在价格上,前者看到了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污染水平的增长导致的逐渐崩溃,过分强调人口阻碍经济发展,消耗资源的副作用一面,看不到人口的促进作用,以人口的增长来解释社会不良现象以及资源环境中出现的问题,认为人口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走到了一个极端;而后者看到了资源节约的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和资源替代),资源价格的相对下降,改进的生活水平,过多强调了人口增长在促进专业协作、采用新技术等方面的作用,只看到了人口对社会发展和技术的正的促进作用,因而得出与悲观主义者完全相反的观点,甚至极端的观点。证据的选择性使用导致了从极端悲观到极端乐观的两种观点。
3.各种流派的研究出发点和目的的不同,也导致完全相反的结论。
马尔萨斯实际上是从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出发,将一切社会丑恶现象归结到人口的过快增长上,否认社会制度不平等原因,因此得出了人口决定论和所谓人口的“自然法则”。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进行反驳,认为社会不平等以及失业等,完全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并不是人口增长过快造成的,不存在永恒的自然法则,只存在相对于就业手段而言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两种针锋相对的阶级立场,必然带来完全不同的人口与环境观念。
另外,我们通过上述论述,还看到各流派一些共同的变化特点:
首先,虽然各种不同流派研究的内容基本都是围绕着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展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所有观点和争论的问题,在内容上都有所变化和扩展,例如人口增长与食物生产(马尔萨斯)、人口与农业增长(BOSERUP),人口与资源可获得性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西蒙),人口与环境污染(梅多斯),以及人口与土地退化的关系(Blaikie and Moore)。发展经济学家很早就主意到人口增长和相关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新古典经济学则关注着,当面临着有限的资源和快速增长的人口时,是否能够维持一个快速增长或者稳定的生活水平。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人口增长对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作用。除了人口增长对全球资源、全球环境的影响,人们也研究人口增长对地区资源和环境的影响,例如土壤、水、渔业、草地、城市环境等。其次,各流派研究从单层次走向多层次,从简单分析到复杂定量研究。所谓多层次,是指从传统的全球区域、国家区域和地区的宏观层次,进入到社区、家庭与环境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则体现在最初的简单分析和论述,发展到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和观点,乃至复杂的系统动态模型。但是作为一种工具,方法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一种观点,不会影响基本的结论和观点,这一点,我们从马尔萨斯主义的发展看得非常清楚。
[收稿日期]2003-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