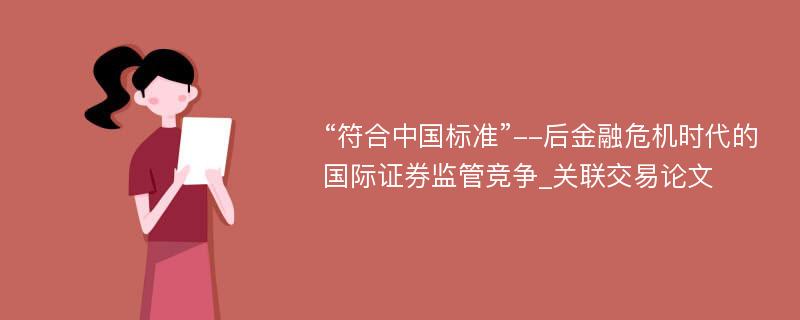
“向中国标准看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证券监管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竞争论文,证券监管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本文希望讨论中国加入国际证券监管竞争是否会降低全球的证券监管门槛,从而降低全球公司治理水平。 从理论层面来讲,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美国州与州的公司法竞争是否带来更好的公司治理的讨论基础上,美国学者罗伯塔·罗玛诺教授(Roberta Romano)提出了国际证券监管竞争(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petition)的概念,侧重讨论国与国之间证券监管竞争如何影响全球证券监管水平。①这种竞争究竟是良性的,全球证券监管标准向“高标准看齐”(racing to the top);还是说,这种竞争是恶性的,各国竞相降低证券监管标准,放低证券发行和公司上市的准入门槛,从而导致全球证券监管向“低标准看齐”(racing to the bottom)?② 从狭义角度来看,证券监管通常涉及公开发行证券是否需要政府批准、信息披露的准确真实完整以及违反前述要求的法律后果。如果从狭义来理解全球证券监管竞争,那么,通常涉及的问题是,外国公司在本国公开发行证券,本国监管机构是否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同本国公司一样对待,还是会适当降低标准,给予外国公司一定的“超国民待遇”。但市场准入和政府审批问题(如外国公司的发行和上市标准)、信息披露要求通常会涉及诸多公司治理领域的问题。比如,一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是否应该有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董事会需要有多少个独立董事?这类要求是不少国家证券法或证券监管规则的内容,但它们同时也是公司治理领域的要求。因此,本文将罗玛诺教授的讨论加以适当扩展,侧重于全球证券竞争如何影响全球证券监管水平,并进而影响全球公司治理水平。“向高标准看齐”、“向低标准看齐”,这里的标准不单指各国证券监管标准,而是从广义上指各国公司治理水平。 从中国角度来看国际证券监管竞争,仅有的少量英文文献只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到美国、香港或其他金融中心上市,中国是其他国家证券监管竞争的被动参与者。③很少有学者关注到,中国可能会是国际证券竞争的主动参与者。实际上,这是正在发生的现象。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的股权证券市场发展迅速,就上市公司市值而言,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④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尤其引人注目。2009年,中国推出了创业板。2011年中国首次公开发行的融资额甚至超过了当年的美国市场。⑤在这个大背景下,2009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积极推进上海世界金融中心的建设。其中的措施之一涉及在上海建立国际板,在适当时候允许外国公司在上交所上市。⑥从近两年监管机构的公开表态来看,中国政府将颁布一整套单独规则,适用于国际板上市的外国公司。⑦因此,中国已经开始加入了罗玛诺教授意义上的“国际证券监管竞争”:通过修订国内证券规则来吸引外国公司到中国上市。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鉴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国证券市场中公司治理出现的诸多问题,比如内幕交易、大股东控制等等问题,中国加入国际证券监管竞争,是否会导致全球公司治理水平向“低标准看齐”?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国际证券监管竞争文献存在固有的“偏见”,用“向高标准看齐”或“向低标准看齐”的简单“两分法”推论国际证券监管竞争的结果,忽视了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忽视了中国公司治理方面发展出来的独特特点。同时,由于公司治理范畴较广,限于篇幅,本文不希望全面讨论中国式国际证券监管竞争给全球公司治理带来的影响,而是选取一个视角,即中国证券法对关联交易的规制,来说明前述“两分法”的缺陷。 具体而言,本文希望说明,中国对关联交易的规制严密、细致,涉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公司治理的多个热点问题,如对大股东的控制、董事和高管的薪酬及利益冲突、“股东权力主义”(shareholder activities)和股东会审批,以及强化公开披露等要求。相比而言,一些发达资本市场,如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在这方面的管制更为宽松,甚至没有任何管制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某些领域的证券监管甚至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密,因此,中国式的国际证券监管竞争,比如针对某些领域降低本国证券监管标准以吸引外国公司到中国来上市,并不必然意味着降低该领域的全球公司治理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选取关联交易规制这一个角度来说明公司治理问题,必然存在一个逻辑完整性的问题。事实上,即便是从狭义上理解公司治理,把公司治理看作是关注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关系、处理代理人成本问题的机制,公司治理所包含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关联交易的规制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领域。⑧其他法律问题,比如并购过程中董事会的权力问题、公司利益相关人的地位问题等等,也是公司治理和全球证券监管竞争的重要领域。同时,对关联交易的某些规制措施,比如会计准则对关联交易的定义和处理办法,可能会被部分学者认为属于会计学的范畴,从而排除在法律人讨论的公司治理之外。因此,本文通过关联交易规制来说明证券监管竞争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只是初步的尝试,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也需要读者审慎对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本文试图论证的是中国式监管竞争并不必然降低全球公司治理水平,因此,只要能够说明在至少一个公司治理领域,中国式监管竞争不会必然降低该领域的全球公司治理水平,那么从逻辑上来讲,即便中国在其他所有公司治理领域的监管竞争带来了这些领域全球公司治理水平的降低,本文的结论仍然是成立的。 二、中国式关联交易规制 在本文看来,中国对关联交易的规制非常严密、细致和全面,涉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公司治理领域的若干热点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至少就关联交易的规制而言,中国的证券监管起点高,中国的公司治理水平并不低。 (一)中国对关联交易的规制 关联交易是中国证券监管的一个重点领域,涉及关联交易界定、关联交易披露、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审批以及关联交易审批时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的回避要求等多个方面内容。 1.关联交易和关联方的界定 什么是关联交易?什么是关联方?中国的《公司法》、⑨中国的会计准则、⑩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招股书披露规则、(11)交易所颁布的上市规则(12)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从字面规定来看,这些规则之间或多或少存在某些不一致之处。但总体而言,根据这些规则的规定,关联交易属于上市公司和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上述规则对关联方做出了进一步界定,包括一系列符合条件的法人和自然人。比如,关联方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股东[既包括控股股东也包括持有一定比例(5%或10%)的股东]、兄弟公司(控股股东或自然人股东控制的其他公司)、董事和高管、董事高管和自然人股东的近亲属、董事高管和自然人股东担任董事和高管的其他上市公司等等。 2.关联交易的披露 关联交易的披露既包括首次公开发行时招股书中的披露,(13)也包括公司上市以后在年报、半年报和重大事项报告中的披露。(14)中国证监会的招股书披露规则、上交所的上市规则和相关报告规则都对关联交易的披露做了非常详细的要求,其中不乏许多有一定中国特色的披露要求。比如,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招股书披露规则要求,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必须在招股书中披露若干信息,如将关联交易分成经常性关联交易和偶发性关联交易,并披露规则要求的交易相关信息;同时,招股书披露规则还做出进一步规定,要求发行人披露公司减少关联交易的具体措施。同样的,交易所对公司上市之后关联交易的公开报告也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要求。比如,上海交易所专门颁布了重大事项报告规则,规定了近二十类交易的报告要求,什么情况下应该报告,采取什么格式报告,报告的信息有哪些。(15)关联交易属于其中一个重要的、需要报告的交易类型。 3.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审批和股东会审批 中国证券监管规则对关联交易审批做出了严格要求。关联交易审批既包括董事会审批,也包括股东会审批。中国证券监管规则没有明确什么样的关联交易一定需要董事会审批,实践中,上市公司通常在章程中做出规定,明确哪些交易应该由董事会审批,哪些交易可以由管理层决定。同时,交易所规则对关联交易的股东大会审批则做出了明确的严格要求。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无论金额大小,都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上市公司从事其他关联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资产净值5%以上的,也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批,并需要在会前聘请第三方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16)当然,对一些不需要股东大会审批的关联交易,交易所规则也做出了相应的豁免性规定。(17) 4.关联交易审批中关联人的回避 作为控制内部代理人(董事和高管)和大股东的措施,中国证券监管规则规定,在董事会审议和批准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在股东会审批和批准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18) (二)关联交易规制涉及的公司治理热点问题 中国对关联交易的规制措施看似繁琐,但它却涉及了公司治理领域的——包括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英文文献中讨论的——若干热点问题。本文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其中涉及哪些热点问题。从这些热点问题可以看出,中国式关联交易管制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公司治理并不总是落后于其他国家。 1.董事和高管的薪酬 董事和高管从上市公司领取薪酬,属于关联方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范畴,同时也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中以及之后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 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高管薪酬问题就成为美国学术界讨论的议题,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的贝布恰克教授(Lucian Bebchuk),讨论的核心是高管薪酬是否过高,是否需要约束机制,比如通过强制性披露来约束高管。(19)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大银行的高管在面临银行倒闭危机的时候,只关心自己的薪酬,不关心银行股东和存款人的利益,这在美国引起广泛诟病。随后在制定《华尔街金融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过程中,美国试图对高管薪酬问题进行管制,其中最为严格的措施是希望将高管薪酬纳入股东大会审批的范畴。但从2010年出台的法律文本第九章第E节(《问责与管理层薪酬》)来看,针对管理层的薪酬问题,也仅仅是允许股东每三年进行一次无约束力的投票。 就中国对董事和高管薪酬的规制而言,在美国金融危机后未能实现的股东会审批高管薪酬动议,中国在危机前就已经做出了明确要求。比如,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董事、高管的薪酬以及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都必须获得股东大会审批。(20)尽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属于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为了获得证监会对首发申请的核准,几乎绝大多数中国上市公司都会遵守指引规定,把相关要求落实到自己的章程中。 2.股东会审批和“股东权力主义” 股东大会有权审批哪些事项,这涉及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分配安排,属于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范畴。在部分发达市场,尤其是美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呼吁给予股东更大决策权从而对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有效控制,进而减少对其他公司治理措施的依赖,比如减少对独立董事、公司并购市场的依赖。 即便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扩大股东权利方面的进展也非常有限。比如,2010年《华尔街金融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第971(a)条授权美国证监会颁布规则,要求公众公司允许股东在股东会上提名董事。现有美国证监会14a-8(i)(8)规则[Rule 14a-8(i)(8)]不允许股东提出新董事人选来对董事选举提出异议,但可以征集其他股东投票支持自己现有的董事。就这个问题而言,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证监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类似工作,希望赋予股东在董事选举中更大的权利。(21)2010年出台的法律当然是发出了更明确的信号,希望扩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但是,就像高管薪酬问题一样,增加股东会审批事项从而扩大股东权利,这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市场几乎很难获得实质性进展。 与此相反,在中国,要求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要事项需要获得股东会审批,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就有了明确的规定。上文提到,根据交易所上市规则,达到一定标准的关联交易都需要得到股东大会的批准。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还规定,上市公司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可以由股东大会决定。如上所述,虽然《章程指引》不属于强制性规定,但几乎所有中国上市公司都会遵守,否则,很难获得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的核准。 要求关联交易、董事高管薪酬获得股东大会审批,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公司治理中一个突出的诉求和安排:扩大股东权利、明确列举应该获得股东大会审批的重要公司事项。因此,中国《公司法》第38条详细列举了11条应该由股东会行使的职权,即应该由股东会批准的事项。而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交易所上市规则这些文件则进一步细化、扩展了股东会决策的事项,包括前述关联交易、董事高管薪酬等事项。 3.董事和高管的诚信和利益冲突 董事和高管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讨论信义义务的文献浩如烟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董事和高管信义义务的质疑和讨论,似乎也仅仅限于上文讨论的薪酬问题,而且对诚信和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办法也不多。 与此相反,在关联交易的规制框架下,对董事和高管诚信和利益冲突问题的中国式管制几乎到了死板和极致的地步。比如,就招股书的披露而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招股书披露规则,公司必须在招股书中披露董事和高管的对外投资情况,对外投资与发行人存在利益冲突的,应该特别说明;(22)又比如,公司必须在招股书中披露董事和高管在其他机构兼职的情况,并说明兼职单位与发行人的关系;(23)再比如,公司必须在招股书中披露董事和高管在前5大供应商和前5大客户中所占的权益。(24) 在首发审核实践中,中国证监会经常要求公司提供前10大、前20大供应商和客户的名称、股权结构甚至财务报表,而不仅仅是规则明文规定的前5大供应商和客户的相关信息。从常理来讲,如果某一个客户仅仅是因为购买公司一定数量的产品,就需要通过公司向证监会提供其所有机密和非机密的公司信息,对这个客户来讲,它很难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在这种近乎苛刻的审核实践背后,蕴藏着监管机构对董事、高管(以及股东)诚信的高度怀疑、对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行为的高度警惕。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对关联交易的规制仍然是董事信义义务这一古老命题的范畴。显然,中国式关联交易管制扩展了对信义义务具体表现类型的关注。 三、向中国标准看齐 (一)中国标准:高还是低 中国式关联交易管制,标准高还是标准低?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世界各国关联交易的管制情况进行详细比较。本文举出几个例子,借以说明中国的管制恐怕属于要求比较严苛的,或者至少并不低于某些发达市场的管制水准。需要指出的是,就方法论而言,本文选择瑞士、法国和美国三个国家,无论从金融中心角度,还是从法系的角度,都不具有完全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的比较对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需要读者审慎看待。但是,从下面对三个国家的介绍来看,在关联交易的管制问题上,这三个国家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瑞士基本上是一个与中国做法完全相反的国家;美国虽然像中国一样对关联交易有管制,但同中国相比它的管制非常宽松;法国在关联交易管制方面与中国有很大的可比性,宽严程度类似,但仍然不如中国细致和严格。此外,由于本文试图说明的是中国在关联交易管制上至少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对这三个国家的分析基本可以得出上述结论。即便读者日后发现,其他某些国家或地区,如德国、英国、日本和我国香港,对关联交易的管制比中国大陆更为严格,这也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和结论。 1.瑞士 瑞士虽然算不上一个资本市场大国,但瑞士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仍然具有一定的世界性地位。就关联交易的规制来讲,值得注意的是,瑞士法并没有“关联交易”这一法律概念!关联交易引起的潜在利益冲突问题,比如董事高管与公司之间的交易,主要通过公司治理的一般性规则处理。 适用于瑞士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准则是《瑞士公司治理最佳行为准则》(Swiss Code of Best Practice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根据该准则第Ⅱ.d.16条,“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尽可能避免与公司利益冲突”。为此,该准则主要是规定了关联人士(主要是关联董事和关联高管)具有向董事会通知的义务,而董事会审议时,关联人员不能参与决定(即需要回避)。(25) 就关联交易的股东会审批而言,根据瑞士法的规定,除保留给股东大会的决议外,(26)不会仅因一项交易存在可能的利益冲突而要求该交易经过股东特别批准。恰恰相反,根据瑞士法的规定,如果决定某项交易是董事会的职权,那么不管该交易是否存在潜在利益冲突,股东大会都无权对其做出决定。实际上,瑞士属于“股东权力主义”倾向较为突出的国家,法律对股东会应该批准的事项做了详细的列举性规定。即便如此,股东会批准某些关联交易也没有被列入证券法管制的范畴。 因此,瑞士对关联交易基本没有特别的管制措施,甚至没有关联交易这一法律概念。它对关联交易的规制主要是通过一般公司治理原则,主要涉及董事和高管的信义义务,强调董事会审批和关联人士的回避。 2.法国 就关联交易的规制而言,法国可能是与中国最为接近的国家。比如,法国商法典对关联方也做出了相对较为明确的界定,既包括董事、高管等自然人,也包括股东。(27)法国也要求关联方必须向董事会通报关联交易的情况,董事会审议时,关联方必须回避。 在股东会审批层面,法国的做法比较特别。董事长必须向审计人员通报所有经董事会批准的关联交易情况,审计人员必须据此向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一份特殊报告,该报告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关联方不得参加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的表决,且在计算法定出席股份数或者多数决要求的股份数时,不应将关联方所持有的股份计算在内。 因此,法国存在一定程度的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的管控机制,也赋予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的批准权,只不过它批准的是审计人员提交的、特别的关联交易报告,而不是对每一笔关联交易进行审批。(28)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对关联交易的管制措施仍然不如中国细致。 3.美国 美国各个州的公司法不完全相同,因此,各州对关联交易的管制也存在差异。就证券监管而言,由于证券监管主要属于联邦政府管理的范畴,实践较为统一,因此,参考美国联邦的证券法和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分析相关问题,较为合适。 就这些联邦层面或者交易所层面的规则来看,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制,几乎全是较为原则性的规定,比如美国证监会颁布的《S-K条例》第404(b)项规定,公司必须制定并披露其审议、批准和认可该等关联方/关联人交易的政策和程序。《纽交所上市公司守则》第314.00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适当审查并持续监督关联交易。至于如何审查、批准关联交易,这些规则都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主要留给公司自己来决定。其中一个渠道类似于瑞士的办法,通过道德性准则要求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比如,根据《纽交所上市公司守则》第303A.10条规定,公司必须制定《道德规范》以解决包括关联交易在内的利益冲突等问题。 因此,美国公司管理关联交易的措施通常也是强调关联人士的主动披露,董事会或者委员会根据利益冲突规则以及公平原则进行审议并批准。在股东会审批层面,几乎都不会规定关联交易需要股东大会审批。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多个扩大股东权力的尝试都进展不大的原因。无论是要求董事高管薪酬由股东会审批,还是要求进一步扩大股东大会能够审批事项的范畴,这些尝试的推进都面临很大的难度。 当然,虽然上面三个国家对关联交易的管制有差别,但相关会计准则、证券披露要求、上市公司报告规则也对关联交易做出了一定要求。因此,即便像瑞士这样法律上不存在关联交易法律概念的国家,遵守国际会计准则准备财务报表时,瑞士公司仍然需要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 不过,总的来讲,在关联交易的管制方面,如果把中国和这三个国家进行比较,大概会发现,中国对关联交易的管制属于比较严格的作法。第一,中国是唯一明确要求某些关联交易需要股东大会审批的国家,既包括一般性关联交易,也包括董事和高管薪酬这样特殊一点的关联交易。第二,中国对董事和高管的诚信、利益冲突极端关注,管制严格。即便根据纽交所《道德规范》来审查潜在利益冲突交易,也几乎没有听说像中国审查得这么严格,把公司的供应商、客户通通梳理一遍,要求董事和高管确认和他们没有关联关系和利益输送关系。第三,中国对关联交易的披露要求严格,假设存在关联交易就没有好事,并要求公司披露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这种做法在以上三个国家都不存在。因此,认为中国的公司治理水平差,参与国际证券竞争必然意味着降低全球的公司治理水平,是没有依据的。这些观点没有看到中国起码在某些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不管其是必然还是偶然的因素导致的。 (二)向哪个标准看齐 即便读者同意中国公司治理在某些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起点更高,但是,如果中国加入了罗玛诺教授意义上的“国际证券监管竞争”,它是否还会维持这些领域的高标准,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为时尚早。由于国际板尚未开通,监管机构如何处理,继续维持高标准还是降低标准,如果降低标准,降到什么程度,这都是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问题。不过,从世界各国可供选择的办法来看,中国降低监管标准的空间有限。 在世界范围,从国际证券监管竞争的角度来看,处理企业跨境证券发行和上市中公司治理和股东权利保护方面的差异,大概有两种模式。 一种做法以美国为代表,除了少数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外,基本尊重跨境上市公司注册地的公司治理做法,不强制性要求跨境上市公司遵守美国公司治理做法,而仅仅要求详细披露公司治理方面的差异。就关联交易的管制而言,前述美国《S-K条例》以及招股书披露准则对关联交易有一些规定,到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这些规定,基本主要涉及对关联交易的披露要求。除此之外,外国公司不需要再遵守任何额外要求。如果外国公司母国的公司治理规则有不同要求,比如,像法国要求年度股东大会要批准审计人员准备的关联交易报告,那么,这些外国公司只需要在有关披露和报告文件中披露这些不同做法即可,外国公司不需要遵守任何美国其他要求。当然,由于美国对关联交易的管制本来就比较松,即便完全遵守美国对关联交易的管制要求,对于许多非美国公司来讲可能也不是一件难事。比如,法国对关联交易的管制就比美国更严格。但从监管态度来看,美国模式几乎是“放任到底”模式,基本不把本国的要求强加给非美国公司。 另一种做法以我国香港为代表,虽然不强制性要求非香港公司完全遵守香港的公司治理要求,但仍然额外规定了一些公司治理和股东保护的测试标准,要求非香港公司必须遵守这些“底线”标准,如果无法完全遵守这些标准,则需要获得交易所的豁免。(29)比如,有一家德国公司的增资存在几种方式,包括股东可以通过一般性授权的方式允许董事会增加一定比例的股本,而不需要每次增资都采用修改公司章程并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方式。而根据香港联交所的公司治理和股东保护测试要求,非香港公司(德国公司)增资时需要修改公司章程并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这是香港公司需要遵守的要求,也是非香港公司需要满足的前述测试之一。但鉴于德国和香港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较大,香港联交所豁免该德国公司遵守前述适用于香港注册公司的要求。(30) 因此,香港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国际证券监管竞争”的折中做法,介于美国式的放任模式和严格要求外地公司遵守本地证券规则做法的严格模式之间。它虽然也放松管制、参与国际证券监管竞争,以吸引外地公司到香港上市,但是,它又不是完全放弃本地监管标准,尤其是一些本地比较严格的标准,比如重要公司事务必须获得股东大会绝大多数(super-majority)批准的要求。 中国大陆的监管者如何选择自己的模式,向美国看齐、全面放宽,还是向我国香港学习,部分放宽,目前仍然不得而知。就本文讨论的关联交易规制而言,是否应该把相关要求适用于来中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如何适用,这都是不确定的问题。因此,即便中国的监管水平起点高,断言中国加入国际证券竞争完全不会导致全球公司治理水平“向低标准看齐”,可能也为时过早。但本文认为,向美国看齐,在公司治理领域采取完全“放任”的做法,可能不会是中国监管者愿意采取的做法。仅就关联交易管制而言,鉴于关联交易管制涉及的诸多重要范畴(董事会审批、股东会审批、信息披露、董事和高管的信义义务等)、监管机构和中介机构对关联交易管制的重视程度,恐怕很难让监管机构下定决心不对外国公司做出任何要求。 如果要做出要求,那就必然涉及做出哪些要求。香港的做法无疑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模式。但即便如此,香港的公司治理测试也没有涵盖关联交易的内容,没有要求非香港公司遵守香港法律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尽管香港监管机构对香港公司关联交易的管制也非常严格。因此,即便采用一个类似于香港做法的“折中模式”,中国的监管机构仍然需要考虑如何折中。如果要求美国公司的董事和高管薪酬也需要股东会审批,鉴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比较失败的尝试,恐怕很难有大的美国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 回到本文讨论的问题,中国加入国际证券监管竞争是否导致全球公司治理水平更差这一命题,本文认为,虽然回答这一命题取决于中国具体如何参与竞争这一问题,但中国不管如何“折中”,它很难完全放弃对关联交易的监管,最后的折中方案,将很有可能仍然需要参考目前对中国公司的监管要求,把中国目前的监管标准作为一个起始线。从这个角度来看,乐观的估计是,不管如何降低已经比较高的监管标准,最后的标准可能仍然不会低于主要资本市场已有的标准,至少从关联交易的管制来看。 四、结束语 中国加入国际证券监管竞争,是否会导致全球公司治理水平的降低,这种担心没有依据。从根本上来讲,这种担心反映了发达市场部分人士的一种偏见。他们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市场,它的监管水平和标准可能也是“发展中的”,标准不高,执行也不严格。本文无意为中国的证券市场和市场监管唱赞歌,毕竟,相当多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对于中国证券市场中的诸多问题都深有感触。但是,即便是发展中的市场,它的监管标准、治理水平并不一定都是低的。至少从中国对关联交易的管制来看,不少要求,比如董事和高管薪酬的股东审批要求,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放松监管要求,加入国际证券监管竞争,虽然仍然需要看如何放松、放松的程度,但断言这就会降低全球公司治理水平,可能会过于武断。 进一步来讲,向“高标准看齐”、“向低标准看齐”这种两分法式的推论,从根本上来讲,忽略了证券监管、公司治理内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实际上,一些批评罗玛诺教授的学者很多年前就指出,罗玛诺教授意义上的“证券监管”(securities regulation)可能是一个含义非常狭窄的术语,一旦把“证券监管”的含义扩大,比如扩大到公司治理这一语义更加含糊的范畴下,那么,“证券监管竞争”的结果可能又会完全不同。(31)因此,将关联交易的监管纳入公司治理讨论的范畴,甚至将许多其他领域的监管纳入证券监管和公司治理的讨论范畴,我们就会发现,不同国家和市场存在不同做法,有时甚至采取几乎截然相反的态度。比如,瑞士和中国在关联交易监管方面采取几乎完全相反的态度。在监管的起点不同、放松监管的手段不同的情况下,很难得出“向高标准看齐”或者“向低标准看齐”的结论。 从未来中国对关联交易规制的发展趋势来看,如果中国推出国际板、加入罗玛诺教授意义上的“证券监管竞争”,为了吸引外国公司到中国上市,一定程度的“降低门槛”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降低门槛”,强制性要求外国公司也采用同中国公司一样的公司治理标准,比如,某些关联交易必须得到股东会审批同意,那么,外国公司即便在其母国也不需要遵守的规则、外国公司母国监管机构也很难推行的规则,如果中国监管机构要强制执行的话,恐怕很少有外国公司能够达到中国目前的要求。因此,在“降低标准”、吸引外国公司的同时,不造成适用于中国公司的标准和适用于外国公司的标准之间差异过大,这可能会是未来中国监管机构积极努力的方向。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是否会由此也降低适用于中国公司的标准,或者不降低适用于中国公司的标准,而仅仅是对外国公司“网开一面”,现在进行预测还为时尚早。不管走势如何,最后的结果可能既不会“向高标准看齐”,也不会“向低标准看齐”,而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标准,本文暂且称之为“中国标准”或者“上海标准”。 注释: ①Roberta Romano,“Empowering Investors:A Market Approach to Securities Regulations”,107 Yale Law Journal(1998),2359. ②其他有关国际证券监管竞争的文献也有不少,有代表性的可参见John Coffee,“Racing Towards the Top:The Impact of Cross-Listings and Stock Market Competition on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102 Columbia Law Review(2002),1757; Edmund Kitch,“Proposals for Reform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An Overview”,41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1),629; Frederick Tung,“Lost in Translation:From U.S.Corporate Charter Competition to Issuer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39 Georgia Law Review(2004-05),525. ③See Erica Fung,“Regulatory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Evidence from China in 2004-05”,3NYU Journal of Law and Business(2006-07),243. ④由于市值处在不停变动的状态,中国和日本上市公司的市值比较接近,两个国家交替处在全球第二水平。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的统计,中国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2012年底的上市公司市值约占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的6.76%,与日本接近,仅次于美国。有关统计数据见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网站(www.world-exchanges.org)。 ⑤参见《普华永道2011年度大中华区首次公开招股透视》,2012年4月,见普华永道网站(http://www.pwccn.com/home/chi/gc_ipo_survey_rpt_apr2012_chi.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06-30)。 ⑥参见2009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要“适时启动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发行人民币股票”。 ⑦参见伍起:《国际板上市交易规则将有别于主板》,载《证券时报》2010年6月23日A2版(http://epaper.stcn.com/paper/zqsb/html/2010-06/23/content_187387.htm,最后访问时间2013-04-26);《上交所正细化国际板相关规则》,载财新网2011年3月10日报道(http://finance.caixin.com/2011-03-10/100234728.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06-30)。 ⑧对公司治理的狭义理解,可以参考Donald C.Clarke,“Law without Order in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30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2010),137,该文第Ⅱ部分作者对公司治理的狭义定义以及相关注释。 ⑨如《公司法》第217条第(四)款对关联关系的定义。 ⑩参见《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号)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的相关部分。 (11)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2006年修订)》(2006年5月18日证监发行字〔2006〕5号)第七节关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披露要求。 (12)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1条及以下规定。 (13)见前注(11)。 (14)关于上市公司年报中关联交易的披露要求,参见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2007年12月17日证监公司字〔2007〕202号)第45条;关于上市公司半年报中关联交易的披露要求,参见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2007年6月29日证监公司字〔2007〕100号)第40条;关于临时报告(重大事项报告)中关联交易的披露要求,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第一号——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2010年修订)的“第二号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告”部分。 (15)见前注(14)。 (16)《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5条和第10.2.6条。 (17)《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6条。 (18)《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2条。 (19)Lucian Bebchuk,Jesse Fried,Pay without Performance: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0)《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40条、41条和76条。 (21)SEC,“Facilitating Shareholder Director Nomination”,Jun.10,2009,available at:http://www.sec.gov/rules/proposed/2009/33-9046.pdf(last access 2013-06-30). (22)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2006年修订)》(2006年5月18日证监发行字[2006]5号),第59条。 (23)见前注(22),中国证监会招股说明书,第61条。 (24)见前注(22),中国证监会招股说明书,第44条第(六)款。 (25)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发生利益冲突,该关联董事会成员或管理人员应当告知董事会主席。董事会主席或副主席应当请求董事会就利益冲突严重性做出决定。关联人员不得参与董事会决定。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或有责任代表与公司存在利益冲突的第三方的人员,在利益冲突的范围内不得参与决策制定。与公司存在永久利益冲突的人员不得成为董事会成员或管理人员。 (26)根据《瑞士债法典》第698条第2款,通过和修改公司章程;选举董事会成员和外部审计机构;通过年度报告和合并财务报表;通过年度财务报表,决定资产负债表所示利润的分配,尤其是股息分配;罢免董事会成员;通过关于法律或公司章程保留给股东大会决定事项的决议。法律为股东大会保留的事项数量众多,例如:拆股;经授权或有条件的增资;发行附特殊权利的股票或参与证书;创制股息权利证书;设立特殊储备金;创设在表决权上享有特别权利的股票;授权查阅公司账簿和信函;启动特别审查;减资;解散公司及相关程序。 (27)根据《法国商法典》,L.225-38以及其下条目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自然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上市公司执行副总裁,或上市公司董事;持有上市公司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在持有上市公司10%以上表决权股东为公司的情形下,控制该公司的股东;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执行副总裁或董事控制的、担任无限责任合伙人的、担任经理的、担任董事的、或以任何形式参与其管理的公司。 (28)就股东大会审批事项而言,普通股东大会(简单多数表决)处理以下事项:选举、更换或罢免董事;任命审计师;批准年度账目;宣布股息或批准以股份派发股息;授权董事会收购、转让或对公司自有股票作其他处理;及批准关联方交易。修改公司章程需要召开董事会特别会议(2/3多数表决),包括:改变公司名称、组织形式或公司目标;增持或减持股本或授权董事会实施;设立新的股权性证券类别或授权董事会实施;发行可转换或可交换证券或授权董事会实施;发行股票期权或授予限制性股票,或授权董事会实施;设立股权性证券的其他任何权利;出售或转让大部分资产;或公司的分立、合并、自愿解散和清算。 (29)参见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与香港联交所2007年3月联合颁布的《有关海外公司香港上市的联合政策声明》(Joint Policy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Listings of Overseas Companies)。 (30)该公司为Schramm Holdings AG。该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公开的招股说明书中有一章,名为“Waivers from strict compliance with the listing rules”,专章披露香港联交所做出的豁免。该公司的招股书见联交所网站(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091215/LTN20091215013.HTM,最后访问时间2013-06-30),点击该章名链接即可阅读该章内容。 (31)John Coffee,supra note[2],1757.标签:关联交易论文; 利益冲突论文; 股东会决议论文; 证券论文; 关联方关系论文; 上市要求论文; 上市公司监管论文; 股票论文; 公司治理论文; 股东大会论文; 董事会论文;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论文; 中国证监会论文; ipo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