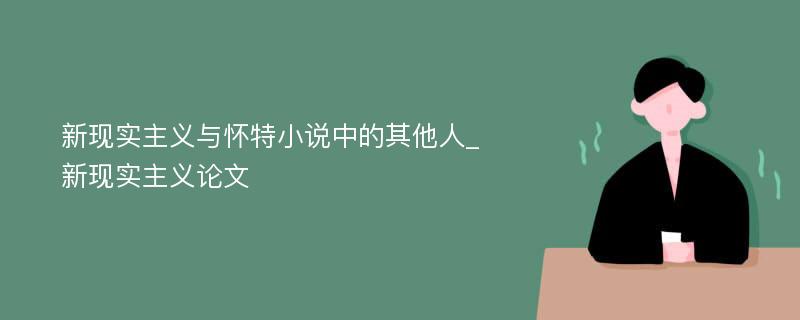
怀特小说的新现实主义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特论文,现实主义论文,及其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英语文学中,澳大利亚文学的后来崛起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其代表人物帕特里克·怀特(1912-1990)自然也受到世人的瞩目。然而,如何看待这位作家,如何评价他的作品,却成了几十年来一直困扰许多专家学者的一个棘手的问题。甚至当瑞典科学院讨论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也曾聚讼纷纭,几起几落。即使当他终于在1973年获此殊荣,其文学地位与成就充分得到肯定之后,有些人仍对此不屑一顾,甚至颇具微词。(注:参见《怀特得奖经过》瑞典驻法大使馆前文化参赞薛鲁·史特雷比瑞著。1980年,台湾中文版。)
一般认为:怀特是一位现代派作家,而且是一位独树一帜的现代派作家。也就是说,他必定具有一般现代派作家所具备的和不具备的某些现代派特征,作到共性与特性的统一。对此,我并无疑意,但不敢恭维的是:一些人只看到他的现代派的一面,只强调其作品的现代主义,反而疏虞,甚至全盘否定另一面——渗透其间的现实主义特色。他们断言:怀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现代派作家,而决非一位地域性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作品表现了二十世纪人们迷惘中的孤独,以及疏远与悲剧性格的扭曲。”(注:参见PearlK·Bell,"A Voice from Down Under",in New leader,January 21,1974,P16-17.)“他的小说证明了另一个世界——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世界的现实”(注:参见Patricia A·Morley,The Mysteryof Unity:Theme and Technique in the Novels of Patrick White,McGill-Queen's Univevsity Press,1972,P1)等等。然而,另有些人则只着眼于并强调其作品的不可或忽的现实主义一面,而对于其显而易见的现代主义特点却闭口不谈。更有甚者,有人直接提出:“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本来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两大文艺流派”,“‘重主观’和‘重客观’两大流派的演变,中国和西方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中国的两大文艺流派(指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笔者注)由对立统一逐渐形成‘两结合’,而西方两大文艺流派(指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笔者注)则互相否定,各走极端”。(注:参见雍容、黄遇奇主编《中外文学流派》雍容:《学习与探索》(代序),第5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究竟算不算文艺流派,这里姑且不谈,单作为两种判然有别的文学思潮,迥然异趣的创作方法,这种所谓的“否定、极端”之说与上述只顾一方,不计其余的绝对提法如出一辙。本文不拟对上述理论作总体评说,但是对怀特及其作品稍加分析,上述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诚然,笔者不赞成所谓的“对话说”,让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平起平坐,就从骨子里潜藏了一种现实主义情结,更不赞同现代主义在对话的旗帜下张扬现实主义的无边性。然而,怀特作品中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同时并存、和平共处,且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应该说,这不是一种盲目的“两结合”,而是一种相斥、相合的融化过程。这里所说的现代主义,当然要涉及到后现代主义的内容,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仅仅是传统或经典现实主义,即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一种革新了的现实主义,或叫新现实主义。(注:“新现实主义”(New Realism或neo-Realism)—语原出自W·P,蒙塔古和R·B佩里所著《新现实主义》(1912)一书;澳大利亚文艺评论家麦克·威尔丁在《后现代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一文中有论述。参见《外国文学》1992年第3期。)我认为新现实主义正是怀特现代主义小说“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其新现实主义有何表现?由来怎样?现分述如下:
二、怀特小说新现实主义种种
(一)社会现实主义
虽然怀特小说有着从外部现实转移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总体倾向,但怀特毕竟是社会人,毕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他深深地扎根于他所生活的那块土地上。在自传《镜中疵斑》中他写道:
“当我离开那可恨的英国学校回到我朝思暮想的澳大利亚时,我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我的周围是一片空白,我需要一个赖以生存的世界。”(注:参见:Patrick White:《Flaws in theGlass》ASelf-Portvait,London,1981,P47.)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个年轻的国家,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届政府对内发展经济,对外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然而,与此同时,那无法医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弊端也暴露无疑。马克思、恩格斯说:“思想、观念、意志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0页。)可见,文艺同其他意识形态形式一样,必然是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的产物。植根于澳大利亚的怀特,势必以澳大利亚作为自己创作的源泉。正因如此,就他发表的十二部长篇小说而言,除1941年发表的《生者和死者》是以伦敦为背景以外,宗旨均以澳大利亚为社会背景,反映澳大利亚人的生活,表达澳大利亚人的心声。怀特小说一个基本主题是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不懈的探索,而这一主题正是通过特殊的环境和时间——二十世纪的澳大利亚表达的。这正是新、老(传统或经典)现实主义的基础。
《姨母的故事》(1948)写一位生长在澳大利亚的中年妇女,后来周游欧美。这位叫西奥多拉的中心人物不像他的早期小说的其他主角那样探索的是人的大彻大悟,而是人本身的属性。
《沃斯》(1957)可谓怀特的一部力作。作者通过该书深入探讨澳大利亚的某些引人入胜的中心议题,包括试图对鲜为人知的澳洲内陆的征服、强权与反叛以及悉尼与未开垦的丛林地的对照等。乌里屈·沃斯是以一位德国科学家、探险家为原型创造的。写澳大利开发时期,一个由沃斯率领的九人组成的探险队深入澳洲腹地探险,直至全军覆没的过程。小说除歌颂人与自然搏斗的坚强意志之外,还再次说明了一个道理:真正能领悟人生真谛的未见得都是专家学者,也可能是一些不谙世故甚至怪诞不经的人们。
《活体解剖者》(1970)和《风暴眼》(1973)是怀特专写悉尼的小说。《活体解剖者》描写的:一是画家赫特利·杜菲尔德。这是部分以怀特深受其影响的抽象派画家德迈斯特为原型创作的;二是一座城市。怀特说:“我要同时为我的城市画像:潮湿的、沸腾的、肤浅的、活跃的、美丽的、丑陋的悉尼,在我有生之年,从一个阳光普照的小村庄,发展成现今这个集旧金山和芝加哥之大成的杂牌暴发户。”(注:参见《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by Ken Goodwin,Macmillan Educa-tion LTD,London,1986,P173.)对城市的这种感情伴以对绘画技艺的迷恋,是怀特苦心孤诣的结果,而绘画原本是他喜欢从事的一种职业。
《风暴眼》写的是年过八旬的亨利太太,躺在病榻上,从昏睡的记忆中回味早年的风流韵事。她的一双儿女为了争夺遗产,从国外匆匆赶回,由对峙到合谋,恨不得早些将母亲折磨死。作者意在表达一种思想:心灵上的折磨,是由于孤独所致,而孤独是金钱至上,人情冷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摆脱不了的阴影。
从上述几部作品的简要介绍中不难看到:怀特小说始终没有脱离澳大利亚,没有脱离澳大利亚人民和澳大利亚现实社会。这也正符合马克思所说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正因如此,来源于社会,又反映社会问题的怀特小说,才有了社会现实主义的基础。(注:参见注释⑧P167.)
(二)心理现实主义
怀特自幼接受的是正统的西方教育。他熟谙欧美文化,深受乔伊斯、沃尔文,以及抽象派画家德迈斯特等现代派艺术大师的影响。主张作品着重反映人的内心矛盾和冲突,以及人对自我认识的思考。(注:参见拙文:)
i《试析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演进》《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4年第6期;
ii《澳大利亚小说走向之管窥》《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96年第2期。)然而,传统文化,特别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杰出作家们对他的影响也不应低估。
怀特的小说,使人不难联想到狄更斯的多彩人物画廊,联想到奥斯丁的温和的讽刺和萨克雷的辛辣的抨击。怀特继承了爱略特的怜悯感和哈代的清醒感。后者所希望的并在他的名著《无名的裘德》中多次使用的“仁爱”(lovingkindness)一词也在怀特的小说《乘战车的人》和《树叶裙》里多次出现。
从理论上讲,怀特似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相信印度苦行主义者甘地的这一信念:“要取消受苦法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进步以受苦多少为衡量标准……苦难愈纯粹,进步就愈大。”(注:参见刘寿康胡文仲合译《探险家沃斯》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7页。)怀特小说经常研究的一个主题是:苦难的含义、对人的拯救,以及为罪恶赎罪的可能。他相信苦难是通向精神进步的必由之路。苦难,对于受苦者和陷入苦恼者,都是有益的。这与陀氏的小说在暴露的同时,又宣扬逆来顺受、从宗教中求解脱的思想,甚至与托尔斯泰的小说在揭露与抨击的背后,也表现皈依宗教、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观点别无二致。所以,有人说:“他的想象不是固有的,而是传统的,是对源远流长的犹太——基督教文化遗产的一种表达……这种想象在我们的文学中已经表达了几个世纪。”(注:参见注释③P7。)
另一方面,从怀特的小说中,如从《沃斯》和《活体解剖者》中,又可看到德国代表进步倾向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影响。但若谈到其中的罗曼蒂克和哥特式小说特征时,人们又不免联想到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和霍桑的《红字》。怀特为乌里屈·沃斯和莫比·迪克创造了一个超真实的,或者说更为现实的浪漫世界。这正象霍桑对此类风格所作的评论那样:“真实和想象是可以相结合的”。(注:引自《红字》“海关段”。)
然而,怀特又与传统的(特别是澳大利亚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文法大相径庭。“他认为澳洲传统文化拘泥于表面的真实,缺乏深度,不足以反映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注:参见注释⑩i。)因此,他的作品决不是“沉闷的新闻体的现实主义的产物”(注:参见注释⑩i。)而是有着“史诗般的气魄和心理上深刻的叙事艺术”(注:参见注释①。)的心理现实主义(注:“心理现实主义”一语出自:Geoge Steiner,'Generalknowledge',New York,May 4,1974,P111.)的杰作。
(三)泛现实主义
心理学家贡布里希说过:“艺术家的倾向是看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注:引自贡布里希:
《艺术与错觉》,第10页。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怀特在艺术实践中,正是如此做的。他在《乘战车的人》(1961)临近结尾处,描绘了土著艺术家杜博所创作的两幅得意之作。在创作《耶稣从十字架放下》那幅画时,“许多地方都被省略了,却又无形地表达出来。”那些“奇形怪状的象形文字”就得留待“那观赏者本人”去破译了;关于《战车》的那幅画,也同样没画完整:“他稍许作弊的地方,遍及那战车本身的形状。恰似他不敢全然确认救世主的躯体一样”。(注:参见Patrick White:《Riders in the Chariot》,Viking Press,New York,1961,P491,P493.)
怀特艺术追求的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以及诸如软弱中的力量、变化中的永恒、死亡中的生命、黑暗中的光明等似是而非的语言现象,通过对省略的联想,引发观赏者——读者动用最深层的自我去体味作品的内蕴。怀特不像十九世纪传统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以牺牲读者的能动探索而偏重于迎合以“舒舒服服不动脑筋的被动接受者,转而变成与作家平等介入文学艺术的主动参与者”。
怀特象福克纳和沃尔夫那样,喜欢使用虚拟语气、条件句和推测结构;象海明威那样,喜欢用第二人称“你”叙述(虽然各自强调的对象不尽相同:如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中的“你”所代替的是普通人,而怀特叙述中的“你”寻求的则是对读者的包容)。这种技巧的作用在于:一则赋予了作品以多层的意义,再则迫使读者对作品的探究。
怀特有时像传统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从某个共同视觉来观察世界,似要达到科学的绝对客观性(如对有些人物传记式的描写),但更多的则是背离传统现实主义的逼真感准则,通过对实在世界的过滤、组合与重构,赋予实在以秩序、形式和意义,从而达到内在的真实。也就是说,怀特更多地是将熟悉的世界陌生化,以期达到现实就是对现实不忠实的描绘的效果。
从作者与读者的上述关系上看,这正是泛现实主义理论家什克洛代斯基的陌生化和现实主义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的用心所在。这是泛现实主义小说的一大特征。
(四)比喻现实主义
比喻的广泛运用是怀特小说的又一特点。这里所说的比喻主要指暗喻的运用,而不是明喻。除在最初的两部小说中,他一般不常使用明喻,而暗喻在他的一些小说中则几乎成了“专利”。暗喻显示出象征和一个文字结构的独立单位之间的关系。激越的暗喻是对假设中的一致的一种陈述。两种事物被认定是一致的,但每一种却保留着自身的形式,这就为他对自然和精神世界融会贯通的驰骋想象提供了一种意义深邃的表述的媒体。譬如《乘战车的人》的四位主人公,可被理解为是对整个人类的四个侧面的具体的体现:博学多才、历经磨难的大学教授,犹太人希梅尔法布体现了智慧;行为诡秘、离群索居的老处女玛丽·黑尔体现了本能;勤劳朴实、乐善好施的劳动妇女鲁思·戈德博尔德体现了感情;聪明过人、纯朴笃厚的土著艺术家阿尔夫·杜博体现了想象。甚至像《树叶裙》中埃伦·罗克斯伯格这样的人物也颇为得体地呈现出平平常常的男人和女人在本世俗的人生旅途中所充当的角色。这种小说可被视为多种比喻心理上的融合,代表着可被接收与合并的独立个体的诸多方面。怀特曾奈张地说过: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是按着他本人的模式创造出来的。(注:参见Carolyn Bliss:《Patrick White'sFicti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1986,P203.)他的小说也可被理解为:是他本人对宇宙探索的比喻的记录。这是比喻现实主义(注:该语参见:注释[20],P204.)的一种体现。
在比喻现实主义的框架内,人物和事件既“意味”着它们本身,又“意味”着另外的内容,而它们的真实性就在此时此刻垂手而得了。也许仅鉴于此,怀特常常告诫读者:希望能领悟他笔下的人物在实际生活中的现实意义——因为他知道自己所执行的是一项文明和人道的使命。正像他在《浪子》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在为着生活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度里,一个知情达理的民族”忘我地工作着。
比喻现实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讽刺的运用。讽刺在怀特所有小说中无所不包,但讽刺的程度各有不同。这就需要读者去细细地品味,仔细地鉴别。譬如《沃斯》,凡读过该书的人,一眼便能悟出:以一名自诩像上帝的人的名字为书名,后面竟省略了任何附加语,这无疑是一种绝好的讽刺。(注:现有中译本书名改为:《探险家沃斯》,见注释[11]。)作者不时提醒读者:沃斯的软弱、偏狭、自私以及不明智的插科打诨等。特别是当他自我感觉像上帝的时候,更是如此。
对于该书中另一个人物——罗拉,作者也照样讽刺不误,只是不那么尖刻罢了。如在渲染她那不可知论和狂妄自大时,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到该书结尾时,当她看起来似乎变成了知识、力量和爱情的源头时,其实质仍不过是一个讨厌、邋遢的女人。她在频频说教之后,嗓音“变得沙哑起来了。她在高声地自问是否带来了咳嗽丸药”。(注:见注释[11],第520页。)这种将罗拉的所谓“精神之美”和她那沙哑的嗓音并置的写法,产生出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从而衬托出对沃斯其人、其事客观评估的错综复杂性。
怀特的讽刺颇似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克雷,是以现实为基础的。鲁迅说:“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注:鲁迅:《论讽刺》,1935.3.)可见,讽刺也是一种写实主义。难怪有人说:“他(怀特)的作品中的淳淳的写实风格,弥漫了对现实生活淋漓尽致的描写。”(注:转引自注释①,米席儿·摩尔论述怀特的文章,原载《贺加洛日报》。)。
此外,隐喻字的使用,增添了其作品的诗情画意,而这又无不以现实为基础。这可与怀特作品中的象征手法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已有拙文涉及,(注:参见拙文《‘乘战车的人’中的意识流》《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第2期。)并将有拙文专论,此不赘述。
(五)其他现实主义
怀特小说经常运用意识流的手段,这时,脉络并非清晰,线条并非单一,跳荡起伏,层层切入,类似于电影“蒙太奇”,如《乘战车的人》中莫迪凯对往事的回忆。(注:参见注释[26]。)这使人联想到电影现实主义。
怀特小说不以情节取胜,重在内心阔展,但为了开掘和阐发现实,有时启用灵活多变的结构形式,通过对角度、层次、方法、时序的变幻,使之具有立体感,如《姨母的故事》开始提供出一个寓言、神话、原型交织一起的构筑框架。这使人想到了结构现实主义。
由于怀特小说突出的现代主义特点之一——异化的结果,其作品有时从古老的神话、民间传说的怪诞部分,提炼出现实成分,再与梦幻杂揉一起,在魔幻中予以表现,使之产生出似真非真、似梦非梦、虚虚实实、真假难辨的艺术效果,如《风暴眼》中伊丽莎白多次梦到自己颇像一只半人半妖的食肉怪物。这不免让人想到魔幻现实主义。
就写作风格而言,如果说上述内容多偏重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话,那么,有些则接近于甚至完全是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谓超现实主义。
综上所述,怀特小说的现实主义,很难用传统现实主义或泛现实主义一言以蔽之,而是一种融化吸收推陈出新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
三、怀特小说新现实主义的由来
要说明这一问题,先得从西方现实主义说起。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西方与东方一样,古已有之,如荷马史诗、莎翁戏剧,甚至雨果小说,其现实主义成分均不可低估;但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或文学运动,一般来说,西方现实主义则发韧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以司汤达的《红与黑》为标志,经过了一个由盛至衰的发展过程,到了十九世纪末,才逐渐为新崛起的思想流脉——现代主义所取代。
澳大利亚和欧美(美国现实主义发展较欧洲晚)由于社会状况不同,其文学发展轨迹也各异。十八世纪末,澳洲沦为英国殖民地,当时出现的澳洲文学多半是对欧美文学的盲目模仿,尚未形成民族特点。
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纪末,澳大利亚人民为摆脱殖民者的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家均以作品为武器,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作品中充满了爱国激情,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和现实意义。
亨利·劳森(1867-1922)不仅是著名的丛林歌手,也是短篇小说的巨匠。他所歌颂的粗犷、豪爽、幽默、乐观的丛林人精神和伙伴情谊在当今的作品中仍有着生命力。劳森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注:参见注释⑩i、ii。)
之后,出现了弗尔菲、理查森、普里杰德等一批现实主义作家。他们所展现的都是富有澳大利亚气息的活灵活现的人物,使人们看到了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
值此,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正当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走向衰落之时,澳洲的现实主义文学异军突起。这时,尽管澳洲也曾出现过像布伦南这样的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但现实主义文学则雄踞文坛的主导地位。
十九世纪末以后的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矛盾,特别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此起彼伏,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二次大战的巨大灾难,使人民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理想破灭、精神苦闷。在叔本华、柏格森、尼采、萨特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形成并发展了具有各种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为特点的现代主义文学,继而出现了一个远比现代主义文学更为复杂的、多元价值取向的混合体——后现代主义。而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往往不再是盛兴于十九世纪的将现实视为完整的、坚实的、可信赖的、以某一共同视觉来看世界的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将现实视为肢离破碎的、变换无常的、令人困惑的、以多棱镜方式,力图从独特的目光中折射出这个世界的不同光彩的泛现实主义。
集独树一帜的现代主义与多元现实主义为一身的怀特及怀特派,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注:参见拙文《书为心画,言为心声——评怀特和他的〈乘战车的人〉》《齐齐哈尔师院学报》96第6期。)至于其新现实主义,决不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决裂。
而是在传统的根基上的前进。世界的状况、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就得去寻找新的形式和方法来把握这个新的世界。
四、结束语
正如前面所述,笔者并不赏识所谓的无边现实主义之说,但通过怀特笔端流淌出的现实主义特色又无法让人闭目塞听。于是,又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上:西方重主观的现代主义和重客观的现实主义究竟能否同时并存?能否作到“两结合”?我想答案也便不言自明了。
其实,所述二者不仅相斥,也可互补。有些作家正是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溶为一体,通过自己“接受的屏幕”的创造性的“投射”,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因而,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作品未必都是清一色现代主义。如现代派大师乔伊斯创造了卓越的现实主义名著《都柏林》;卡夫卡的表现主义小说《城堡》中奥尔加一家的悲剧便是典型的传统现实主义的插曲;而尤内斯库的那荒诞不经的劝剧语言,则借作家介绍布景与道具之机,显出了极其清晰而密致的现实主义笔法。
酌奇而不失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就是说,不仅要求内容与形式、雅正与奇伟有机统一,而且也强调现实因素与理想因素的自然结合。
“水火不容”说可以休矣!
至于怀特的归类问题,我更趋向于将怀特一派称为“怀特派”,将怀特视为怀特派的“开山始祖”的提法——因为他在七十年代兴盛起来的“澳大利亚新文学”运动中,起过开路先锋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