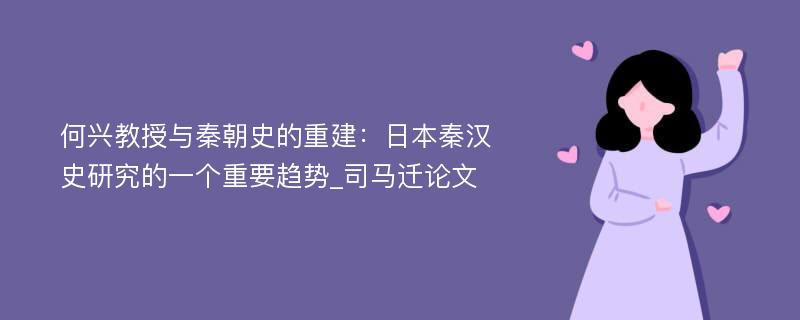
鹤间和幸教授与秦代史的再构成——日本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代论文,秦汉论文,日本论文,一个重要论文,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千年来,秦汉史这块园地经过了多少世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但它并不是一片沃土,所取得的成果和付出的汗水相比,往往少得可怜。这是因为可以依据的资料太少,特别是秦代部分。如果说整个秦汉史若明若暗的话,那么,秦代历史各个部分的轮廓更是模糊不清。多少年来,人们盼望并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将司马迁《史记》的有关记载都当作信史,也仍然难以实现这一宿愿。值得庆幸的是,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系列震惊世人的重要考古发现、特别是记载秦国历史重要内容的简牍的发掘问世,成为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契机。由于秦国历史的发展线索和重要制度逐渐明朗化,于是人们试图将秦国的历史从以往习称的秦汉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单元。马非百的《秦集史》以文献为主,几乎收集作者所能见到的全部有关资料;林剑鸣则综合文献资料、考古发掘以及历来的研究成果,并贯穿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分析,撰写了第一部《秦史稿》。这些重要成果,都是朝上述目标前进的重要的一步。这些年来,随着地域研究热潮的兴起,陕西省研究秦国历史文化的学者又大声疾呼并致力于展开秦文化的研究,有些学者还从理论和历史内涵上对秦文化的学术范畴作了界定和论证。无独有偶, 在东瀛日本, 茨城大学的鹤间和幸教授自80年代以来也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通过文献辨析和实地踏勘,扎扎实实地进行着秦国史再构成的努力。
鹤间和幸原来专攻汉代史,80年代前后曾以汉代豪族问题的研究为学界瞩目。自1986年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年,他发表了《秦帝国的形成和地域——超越始皇帝的虚象》、《古代中华帝国的统一法和地域——秦帝国法的统一与其虚构性》、《汉代的秦王朝史观的变迁》、《司马迁的时代与始皇帝》等等,不下10篇文章,揭示了历史文献与前人研究中关于秦始皇和秦统一的虚构性因素,分析其成因,并对秦国的历史进行再探讨。鹤间和幸的这一系列研究,反映了当前国际秦汉史研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也是近些年来日本秦汉史研究除简牍研究之外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因为对日本以大庭修为首的学者所进行的简牍研究已有论著进行介绍,故本文仅从学说史的角度对鹤间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些评介。
历来关于秦代史的构筑主要依据文献,而文献则以《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有关传、书为主。这些文献资料历来被学者奉为“信史”、“实录”。要对秦代史的构筑进行新的探索,就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主要文献作一番新的检讨和整理。
就某些具体问题而言,前人对《史记》有关秦代历史的记载也作过一些辨疑工作,即以日本学者而言,50年代鎌田重雄、 栗原朋信等人都作过这方面的努力。鎌田在论证秦郡的设置和数目时,对秦始皇统一后采用“水德”说提了疑问。
鎌田重雄在《秦汉政治制度研究》一书的《秦郡考》一文中,专门有一节“秦水德说批判”。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二十六年条中,记述了秦始皇用“水德”。历来对秦国用“水德”之说没有人提出过怀疑,由此解释秦分天下为36郡,正好是6的倍数。钱大昕、 王国维等学者也拘泥于6的数字,将秦郡数说成是36、42、48等。 近人对36郡是6的倍数也很少提出怀疑。鎌田经过细密的考证,得出了如下的结论:(1)关于秦始皇取水德说, 曾任秦柱下史的汉丞相张苍并没有主张秦水德说,反而说秦金德、汉水德,所以秦水德是值得怀疑的;(2)反映秦金德说的史料是汉初主土德说者假托的;(3)秦水德说也是汉主土德说者假托的;(4)汉高祖初年以汉为南方=赤, 秦为西方=白。由此有“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而且还作为秦金德说的依据;(5)张苍根据《管子·幼官图》关于五行的排列, 将金德的下位定为水德,以此主汉水德说。当时考虑汉初尚赤的传说,年始冬十月,仍以“色外黑内赤”。总之,鎌田认为,《史记》关于水德说的记载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秦取水德之说值得怀疑。从汉初的争论推想,秦始皇实际上没有实行水德,秦水德说恐怕是汉初引发的。司马迁也主水德说,《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于统一之年实行水德,但并不意味着始皇帝本人决定实行水德。
栗原朋信在《秦代史研究》一书中,对秦水德说也同样提出了怀疑和否定。与此同时,他还对秦始皇这一名号作了澄清:始皇帝和二世皇帝并不是生前所用的名号,从整体来说,从当时的刻石文来看,当时都是单称“皇帝”,从秦代的史料中没有“始皇帝”的用例。栗原还进一步对《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成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秦本纪》时肯定依据了《(亡)秦纪》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同时也参考了许多其他记录。《秦始皇本纪》也依据了《(亡)秦纪》,但主要是统一天下之前的部分,即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的部分。关于二十六年以后的记载,除了事件、年代依据《秦纪》外,在叙事内容中很明显地混入了汉人所作的文献;又说,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的记载,特别是“水德”说采用以后的部分,除了依据秦王朝遗留的文字记录或以此为基础所撰写的确实记录外,恐怕还混杂了相当部分的出之于非难秦朝的汉人之手的记录。这些混入的记录,即使在《秦本纪》和《秦本纪》的二十六年以前的部分也都存在。
事隔三十年以后,鹤间和幸又提出了秦代史再构成的问题。不可否认,从学术发展史而言,鹤间的研究及其结论与上述研究有承续之处,但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显然大大超过了前贤。鹤间在辨析文献、批判成说的同时,根据其独特的视角,提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不能人为地割裂秦始皇统一前后的历史,在强调秦始皇采摭六国制度的同时,也应该注重秦国自身传统的承续和主导地位。
司马迁撰述《史记》时,将秦国的历史分别记载在《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其后,人们习惯于以秦始皇统一作为界标,将秦国(朝)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和两个部分。这种做法,虽然突出了秦始皇创建统一封建王朝、垂法后世的划时代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导向上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即在强调“创立”、“创建”的同时,割裂了秦始皇统一前后历史的传承性,忽视了秦国原有传统在统一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不自觉地为“罪秦”、“仇秦”的偏见所左右,突出了秦“二世而亡”的悲剧性。
鹤间在探讨秦代史的再构成的时候,首先注意到这种长期因袭成为传统偏见的认识误区。在论及秦统一制度和政策时,他强调历史发展的过程性,注意抉发秦国原有政治文化传统的承袭和演变,突出了秦始皇统一前后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致性。他对始皇陵建造过程的分析,可以说是分析秦国历史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始皇陵的建造,是秦国(朝)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开创了封建王朝陵寝制度的先河,人们还通常将它看成是导致秦王朝灭亡的重大政治事件。而70年代以后,人们从考古发掘中亲眼目睹了始皇陵的宏大气势后,又总是将它看成是秦朝统一威容的象征。对始皇陵建造的或褒或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现有的始皇陵看成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与他的皇帝尊号相称而有计划、有步骤的创作。鹤间却不这样认为。他对秦朝陵寝制度作过专门的研究,并且十分注重实地的踏勘调查。在这一基础上,他写过不少涉及陵寝制度、方位、陵墓区域乃至徙陵政策方面的文章。秦始皇陵自然是其研究的重点之一。他在进行认真的专门研究后指出,秦国的君主原本就有建造大型陵墓的传统,秦公大墓就是一例。始皇陵的建造继承了秦国原有的传统,而同时又增加了新的要素。不承认两者的关系,不弄清两者的关系,就无法理解始皇陵的实态。为此,鹤间对构成陵园的种种要素,联系时代背景,作了一番整理,将始皇陵的建造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国秦王墓的建设(前246—前222年)。这个阶段,始皇帝陵是依照秦王墓的规格建造的,即作为战国时期一个国家君主的陵墓形式而开始建造的,是以昭襄王的陵墓为蓝本而企划的。这个阶段主要是继承传统,还没有看出新的要素。第二阶段是统一、和平时期的建造(前221—前215年)。这一阶段,帝陵坑穴的挖掘工程浩大,但在当时并不是紧急性的工事。在借助军事优势取得天下、并宣言和平的这一时期,并没有产生营造兵马俑式的地下军阵的思想。第三阶段是战时体制下帝陵的建设(前215—前210年)。在战时体制下,始皇帝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年龄,于是他迫切地赶着完成阿房宫和骊山墓这两个生死世界的大工程。徒刑者七十万人都是短时间内集中的。这个时期的土木建筑,如长城、直道、灵渠等都用于军事目的,而帝陵内外城的营造和角楼的设计,使这一地下宫殿最后阶段的建设有着很强的防卫和警备的意味。第四阶段是二世所完成的最终工程(前210年9月—前207年), 二世皇帝想借助完成规模宏大的阿房宫和始皇帝陵来论证自己继承皇帝权力的合法性;而与陈胜、吴广起义反秦这一严峻的军事形势相适应,现存始皇帝陵高大的坟丘,不应该简单看作是皇帝权力的象征,而是为了怕六国势力的反攻和盗掘。
以上介绍鹤间对始皇陵的具体看法,并不是说我们毫无保留地同意作者的意见。目的是为了突出作者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首先,作者对传统因袭的成见持批判的态试,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其次,作者不是静止地、孤立地来观察和论证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将其看作是有着不同背景的历史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始皇帝陵的建设是与政治形势不可分的,其间有着战国、统一、对外战争、二世即位、内乱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因素的影响。由此,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王陵向帝陵的变化,并不是象后世所简单概括的那样,是一次完成的,工事也不是按预想速度进行的,一边遵守传统的做法,一边适应着变化的政治状况,不断附加新的要素,在当时并没有对皇帝陵进行构想,始皇帝陵构造配置的不对称性、分散性就反映了这种情况。适应时代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一系列过程,这就是秦帝国统一事实的实际情况。”
第二,秦统一的虚构性。
鹤间所揭示的秦统一的虚构性,其对象一是史书所记载的内容,二是后人据此所得出的成说乃至偏见。这种虚构性无疑是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多少年来,人们因袭成说,人云亦云,以至指虚为实,弄假成真罢了。具体言之,这种虚构性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统一制度确有其事,但并非完全出之于秦始皇的创制,只不过是秦国原有的制度政策适应于统一的形势和需要而加以变化发展,以至推广于全国;二是纯属子虚乌有,完全出于杜撰,是汉人的秦史观。按照鹤间的理解,就第一种情况而言,秦始皇陵的建造是一个例子,度量衡的划一,法令的由一统也是如此,都是“适应时代变化、不断调整的一系列过程”。即统一事业不是静态的、由秦始皇一次性创制的,而是一个动态的适应和调整过程。人们通常认为,秦始皇统一了法律,或者说统一了全国的法律,这似乎已是一种常识。但鹤间认为,只要认真检讨一下有关的史料,就会对这种因袭的成说产生怀疑,而不断问世的文物资料也冲击着这种成说的不可动摇性。鹤间认为,所谓秦始皇统一天下时统一了法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所谓秦王朝为取代战国时六国的法律而制定统一帝国的新的法律体系的说法更应予以否定。例如,商鞅变法时统一度量衡与秦始皇的统一度量衡原本就是一回事,秦始皇原封不动地承袭了商鞅变法制定的度量衡制度。统一法的记载实际上与统一度量衡的记载混同起来。而将睡虎地秦墓发现的日书与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发现的日书两相比较,也可以得知,秦田律的有关细则是基于楚律制定的,是以旧楚为对象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战国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将本国的法律导入他国的实际情况。睡虎地秦律中的《法律答问》,设定实际案例,解释法律的应用,反映了构成秦律基本内容的商鞅变法时所制定的法,经过百数十年的变化,为了应付统一进程中所出现的新的事态而对原有法律进行的调整,以放大解释和适用的范围。为此,鹤间指出,《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法令由一统”,并不是统一法,而是在统一天下的同时实现法令执行体系的中央集权化,即李斯所说的“今天下已定,法令一出”,不是在秦统一时重新颁定统一的国家大法。总之,“对于历史上最初建立的古代中华帝国的秦朝,也应该注意作为秦统一时代前史的战国秦的时代,以此对统一事业重新进行检讨,统一时施行的度量衡、法律和历法,只不过是将战国秦时已经实施的东西作为划一的政策再度加以确认罢了。”至于对秦始皇统一制度传统成说的虚构部分,鹤间举出了秦帝国道路网统一的例子。他指出,为了责难秦始皇的暴政,必然过分描述他的统一事业,类似象“驰道整备”这类史料,是否真的反映了秦始皇帝时的真相,是大可怀疑的。史书将“筑驰道”放在天下统一的第二年,可以说反映了汉代史书编纂者的意图。当时,即使在关中旧地整理道路网,也并没有在全国进行这项工作。《汉书·贾山传》中所描述的道路整顿的情况,是汉代人看到的样子,并不是秦始皇统一时的真相。究其实,秦始皇的道路统一事业,在战国秦的时代已初具规模。至于各地的道路网,也就是郡县日常负担的道路整备,在战国时代也大致完成。秦兼并占领六国的过程中,将这个方法推行到全国各地,正如将秦王换称皇帝一样,将道(路)称作驰道,虽然有部分的整备,但基本上利用了战国时的道路。
总结以上两方面的看法,鹤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统一事业,应该有这样两方面的分析,其中有秦始皇本人将古代帝王事业作为理想而过高地评价自己事业的一面,也有根据继起的西汉王朝的立场,在论述秦始皇统一事业的一贯性时不实事求是的过头话。”
第三,在进行以上两方面分析的同时,鹤间又提出了秦始皇形象的虚构性,这是很自然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中,秦始皇是歧义最大的一位。褒之者称为“千古一帝”,贬之者斥为“暴君”。鹤间和幸根据对史实的具体分析,认为无论是褒还是贬,两者都包含虚构性的因素。关于秦始皇个人和秦代政治评价的两个极端及其反覆都可以看到时代的影响。为此,鹤间强调在解明始皇帝统一事业的实质时,有必要对基本史料重新作一番清理,在考古文物资料陆续出土的今天,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以上所介绍的,就是鹤间和幸教授关于秦代史再构成的一些基本观点。但是,确认上述虚构性还不能说完成了整个研究工作;何况,我们在上文也指出,鹤间所提出的某些看法,前人也曾作过一些探索和研究。我觉得,鹤间关于秦代史再构成的整体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这种虚构性成因的研究和分析。因为要使读者接受关于秦统一虚构性的观点,就必须对其成因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按照鹤间的理解,要辨析传统成说致误的原因,应该弄清楚这样几点:
1,应该辨析司马迁所采摭史料的地域性
鹤间在最初从事秦汉史研究的时候,就很重视地域研究的方法,譬如在运用这一方法研究汉代豪族问题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既使鹤间的研究避免了空泛的理论架构和一般化的缺陷,又使他所研究的对象和所得出的结论比起一般的日本学者来(特别是近十年间)具有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他在探讨秦代史再构成时使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鹤间认为,作为秦代基本史料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包含两部分史料。一是司马迁所收录的秦始皇时代的史料,如刻石等;二是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亲自游历各地所收集的各种史料,主要是各地传说,即口碑史料。有些学者对《史记》的传说多持不信任的态度,鹤间却没有采取这种简单化的做法。他结合传说流传的历史背景和运用地域分析的观点认为,上述两种史料的性质是不尽相同的,前者即秦代官方的史料显示了秦帝国的正当性,而后者则具有与此不同的特点,许多传说史料反映了反对秦帝国、反对秦帝国权力的人们的感情。秦帝国是征服东方六国后形成的统一帝国,作为被征服地区的老百姓来说,对自己的地域被别人用武力征服自然是怀有强烈仇恨的。即使百年后司马迁从东方地区采录调查的史料,也仍然残留有这种感情。鹤间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单纯依据史料的辨析和理论上的推测。他曾多次到中国,在西南地区,在关中、大江南北,沿着秦始皇巡游和司马迁游学的路线进行过实地踏勘和调查,并且撰写了《秦始皇帝诸传说的形成和史实——泗水捞鼎失败的传说和荆轲刺秦王未遂的传说》、《古代巴蜀治水传说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从蜀开明到秦李冰》等专文。鹤间在这些文章中指出,对秦始皇作为暴君的描述,多以传说为根据,所以传说不能原封不动地作为史实来理解;但强调史实的虚构性,也是不能真实理解秦国历史的。近年来,考古文物的新发现,在指出传说虚构性的同时,也弄清楚了隐藏在传说背后的历史。秦代的长城、直道、陵墓、都城、离宫等遗址,还有将秦代历史传说化的汉代画象石史料,都显示了从新的立场来检讨秦始皇传说的契机。泗水捞鼎和荆轲刺秦王的传说都是强烈反映反秦感情的典型例子。鹤间根据对各地画象石史料的细密调查,提供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即这些传说都在关东即原东方六国地区,而关中(除巴蜀外)则一例都没有。如泗水捞鼎的汉画象刻石有21例,除一例出于四川江安县魏晋石室墓,其它20例都出之于山东、河南。鹤间指出,传说经过反复的口耳相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施加了各种各样的意志,传说故事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同一内容所派生的各种传说,在各地保存着。画象石虽是西汉末和东汉时代制作的,是司马迁以后时代的产物,但画象题材所依据的传说则比画象刻石要早得多。在辨析古代巴蜀治水传说的历史背景时,鹤间也同样运有了这种地域分析方法。他指出,关于巴蜀治水事业有三种传说:一种是禹王的传说,二是开明帝的传说,三是李冰的传说。三个传说的形成和流传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巴蜀一度是秦国的殖民地,罪犯流放此地。秦统一,东方六国的豪族又多被强制迁徙于此。结合这些不同的历史背景,无论是蜀开明帝的治水事业,还是征服巴蜀的战国秦李冰的事业,多有秦汉以降开拓巴蜀的汉人加以传说化的成分,所以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将它作为史料来引用。不仅是对传说,即使是对文献记载,鹤间也持同样的态度,即注意到《史记》有关记载的两重性。如他在分析秦楚争霸和中国统一的问题时指出,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的史料既有秦方面的史料,也有反秦方面的史料。前者反映了征服者秦国一面,而后者则来自批判秦朝政治、坚持反秦立场的长老的传说。我们在阅读和采纳司马迁记述的有关实际战况时,必须加以认真的分析。
2、汉人的秦史观
鹤间揭示秦始皇统一事业的虚构性,其目的是为了秦代史的再构成。这是一个牵涉面很广、难度很大的课题,仅仅依靠对某些史实的辨析,是无法达到预定目标的。正因为如此,鹤间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虚构性”的成因作了深入的剖析,并且提出了汉人的秦史观。在阐述《史记·秦本纪》的史料构成时,突出司马迁本人的史观。他说:“司马迁在各种传说中,选择了最可信的传说,记录在史书中,在将这种口碑传说文字化的过程中,确立了司马迁本人的秦始皇帝观或者说秦帝国观。当时司马迁在诸多传说中,挑选特定传说的标准,一方面是回避征服者秦国的立场,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开东方六国反秦的立场,采取的是一种与秦朝保持一定距离的汉朝史学家的立场”。但这还不是鹤间所说的汉人秦史观的全部内涵。他在《汉代的秦王朝史观的变迁——以贾谊〈过秦论〉和司马迁〈秦始皇本记〉为中心》一文中,对汉人秦史观的形成、变迁作了系统的辨析与论证。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分析司马迁是在什么历史背景、站在什么立场上撰写秦王朝历史的。
鹤间指出,《史记·秦始皇本纪》是由四部分组成的:即(1)本文(编年、传说、故事、刻石等);(2)太史公论赞(《过秦论》下篇);(3)《过秦论》上、中篇;(4)历代秦侯、王、帝在位年数和葬地(《秦纪》)。他首先注意到贾谊的《过秦论》对司马迁的影响。汉代特别是西汉初年的确存在过一种“罪秦”、“过秦”的社会思潮,贾谊的《过秦论》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的代表。这种思潮不止是一种思想和观念,而且有着深刻的政治动机和功利目的。西汉王朝是在推翻秦朝之后得以建立的,为了论证汉朝取代亡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一般的老百姓和上层的统治者都自觉和不自觉地会“罪秦”和“仇秦”,而政论家和思想家则会依据这种感性认识和政治需求构筑一种思想和观念形态的东西,由此必然会突出秦朝的暴政和“二世而亡”的悲剧。但另一方面,汉朝统治者在推翻秦朝的同时,又在体制和政治运作方式上大体承袭了亡秦的基本格局。这样,在“过秦”和“罪秦”时就必须掌握一定的分寸,不致于在泼脏水的时候将孩子一起泼出去,给汉朝自身的统治带来麻烦。应该说,贾谊的《过秦论》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过秦论》名为“过秦”,实际上对秦朝的统一之功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对“功”“罪”都作了肯定;更重要的是对秦朝的兴和亡没有简单地以个人的善、恶进行解释,而是归之于历史的必然。这样,在以“过秦”论证汉朝代秦的合理性的同时,又从历史发展的趋势论证了这种袭替的必然性。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显然受到这种理论的重大影响。他一方面站在汉朝的立场上“过秦”,在《史记》中取材关东地区的传说以论证秦朝的暴虐,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了秦朝的统一之功,对汉朝的基本制度承袭秦朝这一点作了正面的评价。这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司马迁作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很好地将两者统一起来。考虑到这些因素,鹤间指出,我们在阅读《史记》关于秦史的记载时,一定要注意汉初“过秦”、“罪秦”思潮的影响,汉初统治者巩固新王朝的政治需求,以及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的自身立场。为此,我们对《史记》的秦史观有加以重新认识的必要。
3、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如果我们撇开其中否认历史客观性的内涵,那么,这句话还是有其合理因素的,即人们在编纂过去的历史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受到自身所处的时代的影响和局限,更深入地说,也不能不受到作者的功利目的和心理动机的影响。鹤间在揭示和分析“虚构性”的时候,不但指出汉人的秦史观对司马迁的影响,而且剖析了司马迁描述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及其个人形象的心理动机。他注意到,司马迁的秦史观虽然受贾谊的影响,但由于两者所处时代的不同,仍有明显的区别。在贾谊的笔下,秦始皇的形象只不过是秦王政的沿续,是一位继承秦国原有传统的君主;而司马迁描述的秦始皇,其气势和神态已经与秦王政有很大不同。因为贾谊所处的西汉初年,汉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秦制,而汉武帝则另外创立一番新的格局了。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撰写《史记》,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歌颂汉武盛世,由此对秦始皇所开创的大一统局面给予高度的评价,这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到了汉武帝统治的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化,司马迁逐渐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加之本人无端地遭受屈辱的待遇,使他对武帝本人也感到一种失落以至怨愤。这种心理状态大起大落的变化,不能不对他的史书编纂产生影响。所以鹤间认为,在《史记》对秦始皇形象的贬损中,可以窥测到司马迁的这种心理变化。因为司马迁是汉武帝的同时代人,作为臣民,他不能直接指责武帝,因而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间接地从秦代史的描述中反映出来,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以上,我们花费了不少笔墨评析对秦统一事业和秦始皇形象的“虚构性”问题的由来,以及鹤间和幸教授为秦代史再构成的努力。从学说史的发展而言,应该承认,50年代鎌田重雄、栗原朋信等学者对《史记》有关内容的批判,对秦汉史的整体研究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秦代可以信赖的史料太少之外,两位学者在当时主要采用本证的方法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这种批判的力度和影响。因为,既然对《史记》的有关内容持保留、批判的态度,那么,用来证明讹误的另一部分记载的确凿性也自然难以界定,有时不免给人以先入为主的印象,即以“水德说”的批判而言,两位先生用了不少笔墨论证此说之误。但据说,目前出土文物资料中确实表明秦采用过“水德”。果真如此,鎌田和栗原两位看似严密的论证就都成了“水中之月”了。然而,现在与三四十年以前相比,我们无论是对秦代史资料的掌握,还是对秦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鹤间和幸研究业绩最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于文献本身的辨疑,而是他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所进行的实地调查踏勘,以及在这一基础上所作出的论析。他所提出的秦代史“再构成”,既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有他个人辛勤劳作的因素,因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至少,他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对于秦代历史文化的再认识,除了藉助新的出土文物资料从事新课题的研究之外,对历来的传说成说(前人的记载,后人相沿成习、奉为正统的观点)也要作一番认真的清理,但这种清理应该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唯古是疑”。只要将这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秦文化和秦代史的研究一定会独秀一枝。
标签:司马迁论文; 秦始皇论文; 史记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秦朝论文; 过秦论论文; 秦本纪论文; 考古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大日本帝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