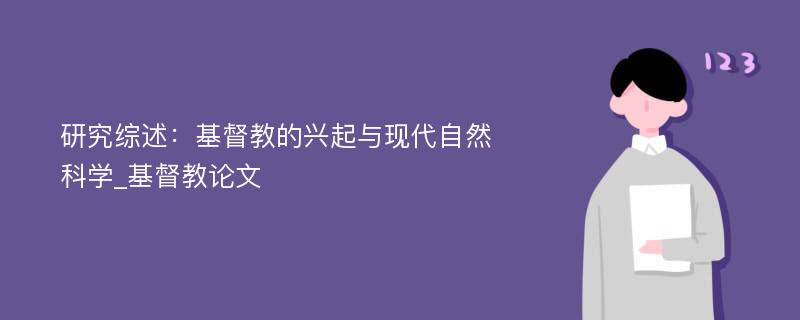
研究综述:基督教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自然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在世界几大地域并存着高度发展的文明,并各自曾有灿烂的古代科技成就,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规范化的自然科学却只产生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西部地区。一旦人们认识到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和其它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社会历史现象,那么,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当时西欧社会最强有力的社会规范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就会引起普遍的关注,而这正是当今研究的一个热点。
长期以来,对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的关系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二者一直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在本质上具有不相容性。基于这种思想的广泛研究给出了基督教阻碍科学发展的大量证据。他们认为:首先,科学精神在古希腊时期即已萌芽并有所发展,但是到了欧洲中世纪,由于基督教在社会上取得统治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科学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基督教神学说教完全背离了古希腊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科学活动被严格禁止,新的科学观点被斥为异端邪说,科学家遭到残酷迫害。基督教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把整个自然界描绘成一幅天堂地狱的宇宙图景,上帝创造并推动一切。他们抬高信仰,贬低理性,使自然科学屈从于为神学信仰做论证的地位。另外,科学的每一发展都包含着与基 督教的严重对立,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不断战胜基督教的结果。例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曾激起教会的激烈反对,加尔文就曾威胁:“有谁胆敢将哥白尼的威信高驾于圣灵的威信之上?”①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由于和基督教经典相矛盾而导致科学家们和教会的直接冲突。而且,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日益展露出其自身无限扩张,蔑视任何权威的本质,而基督教则把教义经典视为确定无疑的真理,是不容更改的。于是,二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最早系统阐述这种宗教—科学冲突观的当推美国历史学家德莱伯(J·w·Draper),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欧洲理智发展史》(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1863)和《宗教和神学的冲突史》(Historyof the Confo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1874)。其后怀特(A·D·White)写了另一部重要著作《基督教国家科学和神学的战争史》(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1897)。本世纪三十年代罗素的《宗教与科学》(1935)所受到的普遍好评显示了这种冲突观仍然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后来基督教会方面鉴于科学的日益强大而用价值性来强调宗教和科学之间具有互补性以及用物理学革命后一些基本科学思想的转变来做文章,试图调和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但是这些在学术界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冲突说首先按俗见把科学和宗教分别设定为革命的和保守的两种敌对势力,因而具有很强的倾向性和情感色彩,并有图式化和简单化倾向,阻断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性。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使人们有可能从一种新的视角更加深入地考察宗教和科学的关系,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直接论及这一问题。在发表于1904-1905年的《宗教社会学论集》第一卷亦即《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提出经过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具体地说,他认为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和上帝之选召的教义,导致归正教徒也包括清教徒采取一种和中世纪那种主张远离尘嚣苦身修行的禁欲主义十分不同的“现世”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引导人们在世俗职业中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中寻求蒙恩得救的可能性。这样就把世俗的职业看作“神召”和“天职”,于是商业和羸利成为神圣的事业,与此相联系的是勤勉、节俭、营利这样一些“美德”。这一切都和资本主义精神相契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②
受韦伯的启发,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Merton)在其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一书中讨论了清教对17世纪英国科学制度化的影响。他的基本设是:“科学的重大而顽强的发展只能发生在一定类型的社会里,该社会为这种发展提供出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③而事实上,在近代早期,组织化的宗教是欧洲社会最强有力的范式,于是17世纪后期英国科学技术的繁荣一定有着当时的宗教即清教的支持。
为了论证清教促进了17世纪英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默顿提出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社会学证据:其一是职业变迁的情况。默顿根据英国《国民传记辞典》和德国《科学技术史手册》所作的统计结果表明:17世纪后期,对科学感兴趣的英国人有明显的增加。这一现象背后肯定存在着某种原因。第二是比较新教和天主教的科学出产率。他指出英国皇家学会中清教徒占较大比例(70%),欧洲大陆国家也同样如此。并且,普鲁士新教徒的孩子进实科学校就读的比例较大,等等。其三,默顿论证了清教伦理和科学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他注重的是清教伦理的社会功利主义倾向,其中诸如宣扬自助、关心社会福利、敬仰上帝的作品,清醒、勤勉、对理性与经验的信心,关心实际和应用等等都会促发科学实践的兴趣,为科学实践披上神圣合法的宗教外衣,并为科学认识活动提供方法论支持。特别是清教摈弃权威使得理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近代科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认为自然界万物存在秩序,科学的任务即认识这种秩序。这正是和加尔文教预定论相互契合的。
默顿的观点引起了社会学界和科学史界的许多讨论。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默顿命题”显然提供了一个分析文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互助的案例;从科学史的角度看,“默顿命题”提示了宗教和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段历史,特别是对近代科学在欧洲的诞生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见解。有许多文章指出了默顿在论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有人认为,默顿在行文中始终没有对“清教主义”(Puritanism)“清教的精神气质”(Puritan ethos)给出过准确的定义,以致于使得历史上的某一群体(比如英国皇家学会)的宗教倾向是否为清教变得难以确认,因而削弱了其统计数据的说服力。还有人认为,默顿试图论证清教文化氛围比天主教文化氛围更适于科学的成长,这种比较是有失公正的。因为,伽利略、托里拆利、格里马蒂等科学家是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而帕斯卡尔、笛卡尔则是法国天主教文化的产物。④美国科学史家哈里斯还指出,虽然默顿在书中也论证社会经济因素对科学的崛起所起的作用,但对它和宗教价值观二者的态度并不是不偏不倚的。在默顿书中:“清教的精神气质在促使社会兴趣转移到科学上之后,便不再影响科学、技术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兴趣分布,而经济和军事则不被看成对一般文化兴趣向科学的转移作出过重要贡献”。⑤
更根本地,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A·Sorokin)指出韦伯和默顿将新教因素和科学因素(或经济因素)划定为“刺激者”和“受刺激者”在方法论上是幼稚的。作为默顿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索罗金在给默顿的信中指出:“尽管帕累托有着诸多的不是,但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件聪明的事中,他强调了他的下列图式:甲是乙的原因,乙是甲的原因。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甲和乙都是第三个更深、更大的‘原因’丙的功能。韦伯—默顿是沿着第一图式进行的。我在这些问题上沿着第二图式进行。而且,我认为我比你具有更牢固的基础。”⑥索罗金为克服文化考察中寻求要素之间单一的因果关系的缺陷而提出了他的文化类型论。
索罗金的文化类型论是在他的文化整合概念基础上加以阐发的。他认为,分析文化整体的最主要方法不是寻求各文化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在于规定文化整体的逻辑意义。他说:“只要文化是在逻辑上整合的,那么,区分出文化中的一个变量,就能使我们合乎逻辑地构造出其他变量之间相互联系的大网络,并且预言这每一变量的性质是什么。”⑦根据这一原则,索罗金把自古希腊、罗马以降至现代的西方文化划分为三大类型:理念型文化(Ideational Culture)、感官型文化(Sensate Culture)以及中间型,主要是理想型文化(Idealistic Culture)。这每一种类型的文化都是在逻辑上有意义的整体。
于是,在索罗金看来,这种文化类型的变迁就构成了单一文化要素变迁的大背景,也就是各种文化要素“共变”的更深层的原因。一旦文化类型发生变迁,则“所有主要的文化价值,连同占支配地位的人格类型,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⑧所有貌似无关的过程、事件,如果放在相应的文化类型中来审视,就不难发现其中相互连结的纽带。宗教改革和科学的兴起同是文化类型发生变迁的结果,它们是在同一框架中共生的现象而并非象默顿试图论证的那样互为因果。
就索罗金的基本思路——把握文化整体的类型及其变迁是理解文化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前提而言,在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他无疑要比默顿更具有历史感并猜到了问题的本质的一面。然而简单地把文化划分为一些先验的理想范畴,并试图据此统领一切细节上的文化变迁。显然易流于大而化之,而且也遮蔽了文化变迁的真正动因,这使他无力对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探讨。索罗金的做法明显地因袭了自圣西门、孔德、斯宾塞以来的社会进化三阶段论传统,并且受斯宾格勒文明种类划分的影响,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
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更深的原因无疑应当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宗教改革也是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结果。恩格斯说:“十三世纪发生的一切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在宗教幌子下进行的与此相关的斗争,从它们的理论方面来看,都只是市民阶级、城市平民以及同他们一起参加运动的农民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改变了的经济条件和新的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反复尝试。”⑨“加尔文的信条更适合当时的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于个人的活动和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⑩另一方面,“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11)韦伯和默顿的研究构成这段话的最好脚注。然而恩格斯接着写道:“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12)按照唯物史观,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变化的框架下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如何在默顿狭隘的因果论和索罗金空泛的文化类型论框架之外对宗教和科学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后来的学者无疑形成真正的挑战。应战者中,荷兰学者R·霍伊卡(R·Hooykaas)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代表作《宗教和现代科学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视野开阔而又细节翔实的画面。
霍伊卡指出,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相遇,经过若干世纪的对抗之后,孕育了现代科学。这种科学一些不可或缺的部分(数学、逻辑、观察和实验方法)固然是继承于古希腊遗产,但指导它们的社会观念和方法论观念,却导源于基督教世界观。他把科学喻为人体,其肉体部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13)这一结论大胆地赋予基督教最为积极的意义。
具体地,霍伊卡比较了在形成对待自然的科学态度的过程中,希腊的因素和《圣经》的因素究竟各自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着先,《圣经》上帝造物的思想有助于破除希腊人对自然的神化,推动了自由探索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学的自然观的形成。霍伊卡指出,圣经宗教之前和以外的许多宗教和哲学,无论是前苏格拉底时期还是后来,往往把整个大自然视为具有神性,甚至把具体的自然物奉若神明。正如埃斯库勒斯所说:“宙斯就是以太,就是大地,就是苍天。宙斯就是一切,是一切的一切。”于是对大自然或某些自然物的探索和利用,就会被视为冒犯或亵渎。希腊哲学虽然意味着古代诸神的死亡,但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这种宗教世界观必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妨碍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但是圣经宗教促成了宗教世界观方面的一个巨大转变,即把世界视为上帝的造物,它本身并不具有神性,上帝已将它交给人类去“管理”,将它“赐给”人类。这就为人类探索自然从而利用自然提供了神圣的“道德上的核准”(马克思语),从而放开了人类发展科技的手脚。
另一方面,霍伊卡批驳了认为现代科学是希腊理性精神的产物这样一种片面的说法。理性固然是科学的重要工具,但是现代科学的根基却是对事实的尊重。基督教思想极大地支持了理性经验论对唯理论的胜利。理性经验论承认,人类作为上帝的摹本,能够发现自然中的某些秩序,但人类还必须接受客观实在,即使当客观实在在人类看起来并不具有理性时也是如此。这一思想来源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认为,上帝的创造不受任何限制(其中包括人类理性的限制),因此人类必须接受事实(其中包括自己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事实)。人只有承认事实,承认自己不理解,才能去探索以求得理解。基督徒和科学家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在他们的思想中都存在某种不信任的成分。霍伊卡引证了宗教上的不可知论者T·H赫胥黎的一句话:“在我看来,科学似乎是以最崇高、最有力的方式来传授伟大的真理,而这种伟大的真理正是体现在完全服从上帝意志的基督教观念之中:像幼童般面对事实,随时准备放弃任何先入之见,谦恭地跟随自然的引导,即使是坠入深渊也在所不惜。否则,你就将一无所获。(14)
除此之外,古典时代关于人的技艺不能胜过自然以及人同自然竞争乃是罪过的观点,被圣经关于人可以支配自然(神使人“修理看守”伊甸园)的观点所取代,遂为服务于人类的科学向技术转化提供了宗教依据;古典社会对手工工作的轻视,被犹太教基督教对手工工作的尊重所取代,也为现代科学不可缺少的实验工作解开了观念禁锢。最后,霍伊卡详尽地分析了宗教改革对现代科学的正面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是改革后的宗派林立造成了相互宽容和自由辩论的环境,从而使新的科学思想很容易为那些作好了充分准备以接受任何类型变革的人们所接受。这里霍伊卡并不认定是宗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他说:“人们会问,在评价技术和实验科学方面,是宗教的、还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归正神学(甚或清教神学)对新科学起了促进作用呢,抑或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是引发科学与宗教改革的原因?对于这些两难问题要择一而答近乎不现实,因为上述诸多因素极为紧密地错综交杂在一起。”(15)简单地说,他回避了此类问题。他只是以翔尽的史实证实“清教以及禁欲主义新教,从总体上来说……为唤起人们对科学的持久兴趣而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6)虽然在这里霍伊卡从总体上接受默顿的观点,但对于默顿提出的加尔文教预定论和上帝之选召的教义增强了从事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兴趣与才能的说法提出了怀疑。(17)所有这些观点,都是霍伊卡以大量的原始资料(这些史料的组织显示了作者超越俗见而具有的深邃的洞察力)自身向我们展现的结果。
如果就再现历史事件的发生——现代自然科学如何经历古希腊、中世纪之后在近代基督教氛围内发展起来,霍伊卡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但是历史的进程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索罗金所追问的更大、更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霍伊卡没有去追问。“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因此,它们也只能这样发生。”(18)
迄今为止,除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对于基督教和现代科学的兴起的最深刻反思只见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由于他是从一更深的层面触及这一问题,以至于今天他的思想还没有被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充分地消化吸收,还没有被纳入他们的话语结构。不过,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于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消解性,就象索罗金猜测到的,一旦人们通过海德格尔认识到基督教和科学同属于世界历史的日益对象化的进程,并且基督教已先于科学进入技术座架并为技术展现扫清道路,即对非神化起了决定性作用,从而为现代科技的发动作好准备,支持这一研究的背后的一般心理学假定(为论证基督教有益或有害于科学,寻找二者在现象上的关联)就丧失了它的重要意义。
海德格尔毕其后半生追问技术问题,揭示技术的本质。这里我们无力全面展示他的思想。他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并不仅是手段性的东西,而是一个座架,是以算计的眼光,限定、强求的方式展现世界(科学即寓于技术的本质之中)。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自然在现代科技这个座架中是作为可计算的能量储存库而出现的,一切事物的展现过程是同人对自然能量的索取、发掘、储藏过程相一致的,是作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被限定的。他认为一旦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在古希腊形而上学中建立起来,现代科学的产生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的技术不仅在古代有其基础和前提,而且基督教的中世纪在某些形而上学的形态上是新时代科技的基础和温床。
虽然中世纪不是技术性的,但是通过一切存在者的“非神话化”,通过把神圣性置入超验的创造的神,它还是为现代技术缩减、降格事物和世界打下了基础。事物本身不再是生机勃勃和神圣的,从自己的自身存在中自在地推导出自己的本质性,而是它们通过一个第三者才得到这尊严:它们是由超经验的绝对的东西创造出来的。当新时代中这个神成为某种单纯彼岸的和非实在的东西,那么事物也丧失了来源于神的保护,就被降格成为现代科技探索和加工的对象。海德格尔在《世界图景的时代》一开始列举了新时代的五个基本现象,如下一段话表达了这一思想:“新时代的第五个现象是非神化。这个说法不是指单纯地排除神灵,不是指粗暴的无神论。非神化是双重的过程:一方面宇宙观基督教化,这是就世界的根据被规定为无限的东西、无条件的东西、绝对的东西而言的;另一方面基督教把它的基督教信仰重新解释为一种世界观(基督教的世界观)因而使自己适合于新时代。非神化是对上帝和神灵的无决断状况。对这状况的产生,基督教起了最大的作用。”(19)这段引文是说,新的科技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逝所决定的。基督教对这种非神化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这个过程才使事物的纯技术构造具有了可能性。反之,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上帝在场于世界和事物中,不能达到世界的技术的构造,即不能产生现代科学。
而且,在基督教所强调的救世信念中,海德格尔也看出了在为现代科技的主体论作准备:“在新时代的历史中,并且作为新时代人性的历史,人随时随地试图从自身出发,把自身作为中心和尺度而置于统治地位,即从事于确保统治地位。为此他就必须日益保证他自己的能力和统治手段,并总是使它们成为无条件地可加支配的。新时代人性的这一历史(它的法则直到在二十世纪才完全进入不可抗拒和有意识地可把握的东西的公开活动)是间接地靠具有救世信念的基督教的人作准备的。(20)”
另一方面,基督教本身在历史中的变化:上帝成为客体,成为某种单纯彼岸的和非实在的东西,从而使人获悉自己是主体,是基础的东西,同样从属于不可抗拒的对象化的普遍进程。海德格尔指出:“由于人腾飞为他的意志的唯一的自我意愿而产生的一切存在者本身的对象化是存在史的过程的本质,并通过这过程人在主体性中完成他的本质。按照这主体性,人在由主体性所承托的主客关系中调整自身并调整他想象为世界的东西。一切的超越,不管是本体论的或神学的,被相对地根据主客关系加以想象。由于腾飞为主体性,神学的超越并因而存在者中最具存在者——人们用存在足够典型地说出这一点——也进入了客体性的方式,即进入道德实践信仰的主体性的方式。”(21)这样,基督教和科学一样,从属于普遍的对象化进程,这一进程把一切东西置于它不可抗拒的力量中,没有什么能逃脱它,连基督教的上帝也是如此,上帝也要从新时代的信仰的人的主体性中获得自己的本质。
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可以理解宗教和科学的帕累托图式:看起来是甲是乙的原因,乙又是甲的原因。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甲和乙都是第三个更深、更大的“原因”丙的“功能”。
注释:
①罗素《宗教和科学》商务印书,1982年,第10页。
②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41页。
③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④⑤⑥Scicncc im Contcxt(SIC)Vol 3 N 1 Spring 1989,Combcridgc U-nivcrsity Prcss。第34-35页、第9页;第36页;第295页。
⑦⑧Sorkin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Vol.1,第34页、第68页。
⑨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5-546页。
(10)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11)(12)恩格斯《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第506页。
(13)(14)(15)(16)(17)(18)霍伊卡《宗教和现代科学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第64页、第118页、第185页、第121页、167页。
(19)海德格尔《林中路》,法兰克福,1972年,第70页。
(20)(21)海德格尔《尼采》第2卷,弗林恩,1961年,第426-427页、第378-379页。
标签:基督教论文; 科学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宗教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