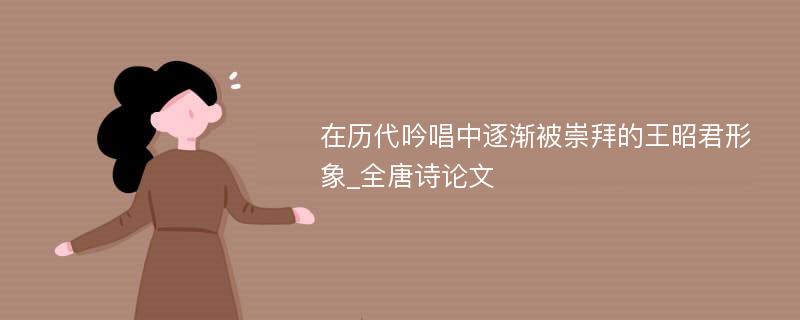
在历代吟咏中逐渐偶像化的王昭君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代论文,偶像论文,形象论文,王昭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汉书·南匈奴传》: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有关王昭君的原始资料在正史记载中,以此条最为详尽,昭君给人的印象也不过是美貌,入宫不得见幸及和亲诸事而已,其形象甚为单薄。作为一个女子,她不可能像王侯将相、才人学士们那样在史书中得到较为详备的记述。然而,自有昭君和亲,历代吟咏不绝,诗人们纷纷以自己的体悟来再现昭君当时的心境,遂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较之正史远为丰富生动的形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昭君形象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在吟咏中越来越丰满,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单薄到丰满,又从丰满归于单薄的过程,当然后一个单薄不是前一个单薄的重复。考察这一过程,不仅可使我们对昭君形象有更全面的了解,而且,透过这一个不断得到改造的原型,也可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
两晋南北朝时期
在汉代,王昭君主要还只是个历史人物,至两晋南北朝,才开始走入文学的殿堂,这一时期诗人笔下的昭君,自伤自悼,柔弱无助,完全是一个被当作牺牲品的弱女子形象。现存最早的咏昭君诗是晋石崇的《王昭君》,诗中的昭君充满了对嫁与胡人的悲叹,自伤昔日之“匣中玉”成了今日的“粪上英”,除了对自我命运的伤悼,并未涉及其他人。此外如“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庚信《王昭君》,《乐府诗集》第427页,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谁堪览明镜,持许照红妆”(萧纪《昭君词》,《乐府诗集》第432页)等,多描写其瘦影、残妆、啼泪、细腰,表现其远嫁的悲切、哀惋,在他们笔下,奠定了王昭君泪别汉阙的形象。至于梁代施荣泰的“唧唧抚心叹,蛾眉误杀人”(《王昭君》,《乐府诗集》第427页)和梁代沈愿满的“早信丹青巧,金货洛阳师”(《昭君叹》,《乐府诗集》第434页),则为昭君远嫁添加了两个很重要的内容:美貌误人及画师可怨。不过对此也仅以一个“叹”字了结。
故此,两晋南北朝时期诗人笔下的昭君,似乎全部心思都投注于对自身命运遭际的叹惋,其心理世界极为狭小,诗人仅涉及其体态、容貌、服饰及胡边环境,意在描摹她凄楚的心境。纵有那么一句“猗兰恩宠歇,昭阳幸御稀”(庚信《王昭君》,《乐府诗集》第427页),其间所包含的怨意也显得那么朦胧隐约,若有若无。我们注意到,这个时期以昭君为题材的诗,多题为《王明君》、《王昭君》、《昭君词》,抑或《昭君叹》[①],而没有“怨”字出现,这或许并不是偶然的。南朝168年间(421-589),历四朝,政权更替频繁,在这种纷乱的大势下,人们无法找出一个具体的责任承担者,人的命运沉浮似是整个社会使然。因此,人们只能对生命的悲剧作无可奈何的叹息。
隋唐时期
经过两百多年的分裂,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王朝——隋朝,这是一个短命的朝代,故它留下的咏昭君诗也极少,但这篇数极少的几首却已透露了一点新的气息。薛道衡的诗在承袭前人感叹昭君薄命的基础上,已明确触及了君王,即:“专由妾命薄,误使君恩轻。”(《昭君词》,《乐府诗集》第433页)侯夫人则断然写出:“毛君真可戳,不肯写昭君。”(隋侯夫人《遣意》,《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第1725页,中华书局1959年5月版),可见,在隋代诗人笔下,吟咏的眼界已逐步打开。首先,君王形象的增加使昭君原来一味自怨自艾的心灵世界增添了波澜;其次,侯夫人对画师的“判决”与前代那种轻描淡写的叹惜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原先那个朦胧的主题彻底挑明,这些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启发紧随其后的唐代诗人开始进行更为大胆的开拓。
在唐代诗人笔下,昭君是个情感复杂的昭君。
首先,对于美貌误人,前人仅仅一句“蛾眉误杀人”,这一命题唐人亦有承袭者,如李中“蛾眉翻自累,万里陷穷边”(《王昭君》,《全唐诗》第1868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版),但如白居易的“特报后来姝,不须倚眉首。无辞插荆钗,嫁作贫家妇”(《青冢》,《全唐诗》第1044页上),则已宕开一笔,以自身为借鉴警示来者,从一己的命运扩至对所有女子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在“蛾眉误杀人”的背后,唐人增加了十分丰富的内涵。他们通过“何事将军封万户,却令红粉为和戎”(胡曾《汉宫》,《全唐诗》第1632页中),“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戎昱《和番》[亦作《咏史》],《全唐诗》第674页上),这些或讥刺、或指斥的诗句表示了他们对昭君和亲的新解:于昭君,美貌铸成个人悲剧;于国家,赖得红颜暂保安靖;于朝臣,恰恰表现了他们的无能。这就是唐人在蛾眉误人背后赋予的深层含义,其实质就是对和亲政策的否定[②]。
其次,对于画师的态度。与侯夫人态度相同,唐人也每把指责的矛头指向画师。“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书斩画师。”(崔国辅《王昭君》,《全唐诗》第1932页下)进而发展至怨恨画工之时掺杂了对君王误信的埋怨。故王涣有句:“肠断君恩信画工”(《明妃》,《全唐诗》第1739页上)。如果说此论尚守怨而不怒的原则,白居易的“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昭君怨》,《全唐诗》第84页下),则是直斥君王,至于画师的责任,反在其次。
第三,关于君王。在白居易之前,沈佺②期“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尚将昭君的悲剧之因归于匈奴主和画师;杜甫诗中“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三,《全唐诗》第568页上),也只是模模糊糊的怨恨二字而已,至于郭元振“闻有南河信,传言杀画师。始知君恩重,更肯惜蛾眉”(《王昭君》,《乐府诗集》第430页),更是感念君王杀画师为己出气。从目前所见的诗歌来看,明确将矛头指向君王是自白居易始,也是他,首标《昭君怨》之题。此论一出,吟咏之意顿时大为拓展。本来诗中凡是言及胡边便不免凄凉[③],自从认为汉君不值得留恋,昭君在胡地也就有了新的感受。于是王睿言道:“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解昭君怨》,《全唐诗》第1278页上)沿着这一立意,引起后代无数发挥。
总之,昭君咏在唐代其内涵及外延有了极大的拓展,为后代开辟了广阔的吟咏空间,尤其在时间上的开拓使咏昭君诗开始具有了历史感。白居易“唯有阴怨气,时生坟左右。郁郁如苦雾,不随骨销朽”(《青冢》),写出了这一形象的历时性价值。至于杜甫“千载琵琶作胡语”,李白“死留青冢令人嗟”(《王昭君》,《全唐诗》第66页上),则已勾起千载共鸣之意,为宋人在这一意旨上进行进一步的开拓开了先河。
王昭君的形象在唐人笔下最为丰富光彩,唐代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给诗人们提供了自由的想象空间,在他们的塑造下,昭君忧喜交集,怨恨难遣,以昭君一人引带汉君、画师、朝臣、胡人、胡主等一群人,构成一幅出塞和亲的立体画卷。
宋代
唐人开拓了咏昭君诗,宋人则将其归拢。唐人各呈异思,破前人旧意而竟立新意,宋人则对唐人的各种意旨归纳并合,有继承也有创新,其特点是失去了唐代那种百家争鸣的盛况,吟咏的立意逐渐被规范于几个固定的方面。
宋人咏昭君最有名的是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等诗人的一次唱和。王安石作为首唱者,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见解:“人生失意无南北”和“人生乐在相知心”(《明妃曲》,清吴之振、吕留良辑《宋诗钞》见《诗歌总集丛刊》第106页下,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1月版),这一崭新的见解,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相和的诗人们,而且还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从这些诗中,不难看出其中深深的追求知音强调相知的意愿。宋人将这种对知音的寻觅放在广阔的时空之中,从胡边到中土,从当世到后代。然而,在这一寻求相知的过程中,对求得知音的慰藉(即使仅仅是希望)却显然冲淡了怨的成份。欧阳修的“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宋诗钞》第564页下),这自嗟二字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前代诗人笔下昭君难遣的怨恨,在一种轻轻的叹息中开始了某种理性的思考。因此,上述诗人们在表示人生贵在相知的同时,几乎都对君王提出讽谏之意,最明显的是司马光诗:“妾身生死终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发萧太傅,被语仰药更无疑。”王安石固然对君王进行了怨而兼怒的斥责,与他相和的诗人们却并未沿着此意继续,相反笔锋一转,显示了一种不限一己恩怨的抱怨。昭君以一种参政的责任心对朝政及国家前途表示担忧,并为遭受陷害的忠良之士抱屈叫怨,使昭君的怨具有儒家诗教中怨的意味。
宋人笔下的昭君胸襟显然较唐人开阔,由此,诗人们更偏离了王安石的诗意,开始在昭君远嫁这事上对君王表示体谅:“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文同《王昭君》,《宋诗钞》第605页),并发出“长城不战四夷平,臣妾一死鸿毛轻”(高似孙《琵琶引》,《宋诗纪事》第14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版)的豪语。同时出现如“西京自有麒麟阁,画向功臣卫霍间”[刘子翚《明妃出塞图》,《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以下简称《选注》)第10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1月版]之类的诗篇。在这些诗中,昭君不再悲叹埋没胡尘,而欲在胡边有所作为,对汉主作出“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黄庭坚《水调歌头·游览》,《全宋词》第386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的保证。
宋人赋予昭君承当国家政事的胆略和豪气,同时又对其在边地切实的凄苦加以种种慰藉:
例一:“野狐落中高台倾,宫人斜边曲畴平。千秋万岁总如此,谁似青冢年年青。”(费文雷《昭君行》,《选注》第105页)这是对王睿诗的一个拓展。
例二:“倘于国有益,尚胜守空房……得为胡阏氏,揣分已过当。”(郭祥正《王昭君》,《四库全书·青山集》第1195-89页)安慰之余甚而庆幸不已了。
至于苏轼的“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昭君村》,《选注》第84页),则已经上升到哲理性的高度来涵盖人事的变迁。
慰藉之意冲淡了怨怒之气,昭君对画师的态度亦有极大转变。在唐代,人们就已认为画师不该承担主要责任,到宋代,已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王安石《明妃曲》)。那么,怪谁呢?有认为“自是君王先错计,爱将耳目寄他人”(徐均《王昭君》,《选注》第111页),但也有认为“君恩厚,空怜命薄”(周密《杏花天》)。我们注意到,后代的吟咏是沿着后者的意思发展的。
总之,在宋人笔下,昭君出塞的悲剧意味已大大减弱。宋人喜做翻案诗在文学史上是有名的,可惜在咏昭君诗上,其翻案可谓极不高明,到了宋代,君王不必怨,画师无可恨,都是自己的命不好,似乎重归自怨自艾的形象,只是这一形象开始具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宋人这种颇带道学气的论点却深为后世所喜爱,为明清两代诗人们所津津乐道而进一步理想化。
元代
也许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中第一个为异族统治的王朝,故这个时代诗人的昭君咏极具时代特色。在强大的外族统治下,他们痛感前朝(宋朝)因羸弱而亡国,因此,元人几乎将昭君的悲剧完全归于外族(匈奴)的强大。马致远的《汉宫秋》里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但柔弱无能的汉元帝,这个形象是元人笔下君王形象的典型代表。因其柔弱,昭君非但无可怨,相反倒平添为主分忧的情怀。于是,她由衷表示“恨不别君未识时,免使君王怜玉质,君心有忧在远方,但恨妾身是女郎”(刘因《明妃曲》,《选注》第125页),并很深明大义地认为:“汉廷自此恩信重,美人身比鸿毛轻。”(陈旅《明妃出塞图》,《四库全书·安雅堂集》第1213—40页)非但如此,元人还为昭君出塞设置了一个令汉廷理直气壮的理由,即红颜祸水,不如远远离去,反于国有补,这样,画师无过,反而有功。就连昭君都很自觉地承认:“自售悬知非静女,汉家当论画师功。”(《刘因《昭君扇头二首》,《四库全书·静修集》第1196-627页)
此外,由于处在外族统治的特殊环境下,人们渐渐需要为自己的处境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于是不少诗人纷纷描述昭君在胡地受厚遇而满意的心情:“旃车百辆入单于,不恨千金买画图,争似山中插花女,傍家只嫁一丈夫。”(马祖常《昭君》,《选注》第132页)在元人看来,就昭君个人而言,远嫁已非悲剧;然于国家而言,“寄语汉飞将,此计诚太拙”(周权《明妃曲》,《选注》第136页),对和亲仍抱否定态度。这种矛盾心理是否正体现了在异族统治下人们的某种心情呢?即一方面迫于形势不得不隐忍偷安,而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始终不服外族统治。
明代
“爱恶爰有命,不在妍与媸。名花萎芜秽,小草植轩墀。古今皆如此,悲叹亦奚为。”(何乔新《王昭君》,《选注》第154页)正如诗中表现的,昭君在明人笔下,以一种通达的情怀来看待世间的悲欢离合,表现出一种更为理智的境界。
较之元人,明人严守胡汉之防,认为“毡裘肉食本异俗,不如但嫁巫山村”(高启《王昭君》,《选注》第144页),然对于汉家的一切,昭君则极尽其体谅和宽容。
对于和亲政策,明人的态度很模糊,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作为奉行和亲策略的昭君,则体现了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精神,这较之宋人更为进步。她自豪地声称:“将军仗钺妾和番,一样承恩出玉关。死战生留皆为国,敢将薄命怨红颜。”(汪循《明妃》,《选注》第159页)并很大度地表示:“但使此身能报国,何妨恩宠属他人。”(霍瑛《青冢吊明妃》,《选注》第178页),充分体现了一种舍己为国,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
对于君主,明人在承继元人立意的基础上,更进而让昭君替君王所采取的造成其悲剧的政策辩白:“征夫不复顾乡井,天子岂肯私婵娟。”(张宁《赵松雪昭君图》,《选注》第148页)并对君王表示出依依不舍的情意和矢志不渝的情感:“下阶一顾恩,犹使终生恋。”(李蔉《昭君怨》,《明诗卷》第581页上)明知此生不再,于是希望“他生誓相见,幸得被恩私”(顾鼎臣《明妃词》,《选注》第157页),安慰君主“妾命薄,冒黄尘。慎勿劳,吾皇神”(魏偁《王昭君》,《选注》第190页),甚至自责“空将艳质恼君怀,何似当时不相见”(李东阳《明妃怨》,《明诗卷》第1429页下),那份胸襟,那种温情,也许这就是明代文人心目中理想的女子形象,昭君充当了这种理想的载体。
至于画工,在明人笔下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但这画工已不特指误昭君的毛延寿,而代指一切欺君误国的弄臣。就昭君而言,画工误己犹可忍,且无可恨,“佳人自有命,画工何能有?”(文征明《明妃曲》,《四库全书·甫田集》)故自慰:“当时不遇毛延寿,安得芳名播千古。”(李学道《反昭君怨》,《选注》第173页)
昭君在明人笔下,以一种无怨无悔的担当精神出塞和亲,并以途中切身的体会,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说道:“晓来马上寒如许,信是将军出塞难。”(屠大山《昭君怨》,《选注》第166页)在这个时代,虽然也不乏凄凉语调,然总而言之,这些声音是极微弱的。诗人们认为昭君承受“千载文人笔,当年圣主情”,当然是“抚弦应破涕,那是断肠声”(薛宪岳《昭君》,《选注》第197页)。昭君轻抛个人恩怨,重视国家大义,是一位温柔善良,德容具佳的女中楷模。如果说前代诗人笔下的昭君尚有儿女之态,还能让人可亲可近,到了明代,昭君的形象则已成了道德教化的象征,完全泯灭了作为血肉个体的自我。
清代
唐人咏昭君诗的辉煌灿烂已不可再,在宋人设定的藩篱中,后代诗人们亦步亦趋,只求锦上添花,再不敢发出异语狂论。这在清代也无例外,不过除了基本蹈袭旧意,清代还是涌现了一大批立意很特殊的诗篇。他们一反明人笔下昭君的温柔敦厚,塑造了一个刚烈女子的形象,这成为清代昭君咏的最大特色。清人可能深感明人笔下的昭君太缺乏个性色彩,故赋予其强烈而鲜明的个性特征。明人少学乏识是清人的笑柄,作为一个反动,清人特别强调学识的作用,即使做诗,也是“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袁枚《忠雅堂诗集序》)。作为诗中的昭君形象,便也具有了卓越的见识和超凡的性情,于是清人笔下的昭君慨然表示“君恩不可再,断绝彼中肠,丈夫各有志,女子亦有行”(顾景星《王明妃》,《选注》第211页)。那么,是什么“行”呢?“才貌岂是定闺贤,总观大节知臧否,……宁为鸡口不牛后,谁识女子真英雄。”(升寅《青冢行》,《选注》第269页)这些见解从未见诸前人笔端,到清代却成为诗人们的共同观点,昭君俨然是一位慷慨激昂,节义凛然的侠女,正是基于对昭君形象的这样一种定位,清人对其不赂画工的举动和辞别汉君的情态也进行了新奇的描绘:“不把画金买画工,进身羞与自媒同。始知绝代佳人意,即有千秋国士风。”(吴雯《明妃》,《选注》第259页)“艳色自骄矜,安怪它人为,……所愿在一见,去之无所辞。”(李锴《王昭君》,《辽海丛书·含中集》第8页A面)清人笔下的昭君情志决然,极少缠绵的儿女情态,她不像元明诗人笔下的昭君那么隐忍自谦,而是毫不讳言自身价值,珍惜自身价值,耻于乞求自媒,只要价值得以实现,其他的恩怨荣辱均可置于身外。
此外,清人对和亲的态度已与前人截然不同,而表示了根本上的赞同。诗中多见“敢惜妾身归异国,汉家长策在和蕃”(刘献廷《王昭君》一,《选注》第205页)之类的论调。同时昭君也得意地言道:“寄言侍寝昭阳者,同报君恩若个多。”(袁枚《明妃曲》,《袁枚全集·小仓山房诗集》第3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版)显然她已将出塞和亲视作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途径,那么相对于明代那个隐忍个人辛酸的昭君,清人笔下的昭君则是保国家安宁,树自己青名,从理智到情感都是一个无悲有喜的形象。
清人塑造了一个远见卓识的昭君,昭君也终于褪尽了最后一丝汉宫女王嫱的残余。在明代她还是“我本弱女子,被选当雄兵”(陈子龙《王昭君》),到清代则完全是一个敢于进取,有思想,有主见,具有很强个人原则的强者。
从两晋南北朝凄哀无助的弱女子昭君,到隋唐柔肠百转恨怨难释的昭君,到宋代自嗟自慰的昭君,到元代随遇而安平心静气的昭君,到明代温柔宽厚、取义成仁的昭君,最后到清代义烈清刚,识见非凡的昭君,汉宫女王嫱由一个悲悲戚戚,伤感于一己忧乐的弱女子到被塑造成千秋景仰的和亲使者。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吟咏,我们看到的是“巾帼英才”(邓拓语,见《昭君无怨》,《选注》第324页)这样一尊偶像怎样被逐渐树立的,我们是否也能在这一过程中约略看到中国文人在历史演变中的一点心路历程?也许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更关注个人的生命,在自身狭小的生命空间内吟咏琐细的服饰,微妙的心灵感受;隋唐大国的恢宏气度则使诗人们能在一个广阔的自由空间里发挥充分的想象;宋代的积贫积弱使人们不能不忧虑于国家的前途安危,于是王昭君也被赋予一定的参政意识,具有全忠保义的思想;元代昭君咏是元人在承受外族统治这一大冲击下的心理调整;明人则以其前所未有的道学气和迂腐思想塑造了一个毫无生气的王昭君,其形象的暗弱沉闷尤如有明一代的风气;清人对此作了一个积极的反动,清代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使王昭君也追求才以致用,而公羊学派的重新兴起,那种“夷狄”可以进而为“中国”、“诸夏”可以退为“夷狄”的民族融和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清人的心理压力。故同为异族统治,清人便一反元人的态度,大唱和亲的赞歌。
注释:
①王明君即王昭君,因触晋文帝司马昭的讳,故晋人谓之明君。
②虽然张仲素有:“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王昭君》,(《乐府诗集》作令狐楚作,第431页)]但这种赞同和亲的论调在唐代是一个很微弱的声音。
③储光羲诗中虽表现“胡王知妾不胜愁,乐府皆传汉国辞”,胡王可谓体贴关心,然昭君却是“傍人相劝易罗衣,强来前帐看歌舞”,极为勉强。引诗出自《王昭君》,《乐府诗集》第4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