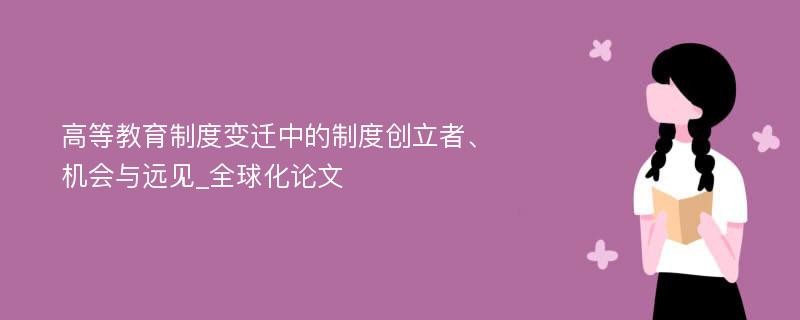
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的制度创立者、机遇和预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高等教育论文,机遇论文,创立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6)01-0158-15
本文关注的是制度变迁中机遇、长期趋势和理性预见这三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种类似“宽银幕电影”的方式,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人类设计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那么关注长期变化比关注每天起伏不定的改革,更可能获得有益的结果。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评价细致周密的人类设计:
1.通过比较外生的、内生的和预见这三种相关因素影响的相对大小;
2.争取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增加我们对所有这三种变迁形式细节的理解。
简言之,这里笔者所持的观点是:只有很少的制度变迁是由人类的理性预见和干预所带来的。大量的制度变迁要么是机遇(外部力量)所造成的,要么就是内部的变化所带来的,其中机遇所起的作用比我们通常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假如当人类理性干预的机会出现,我们又希望能更好地把握并加以利用的话,就需要更好地理解那些出现在历史纪录中的理性变迁的机制。以下是笔者的主要发现:
1.内部因素。象“理性化”、“现代化”、“全球化”或“世界体系”的机制,不仅不像制度变迁主流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在导致制度变迁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要少很多,而且他们的解释力也不像通常设想的那样好,因为将这些内部因素带入日常生活的局部的因果机制还没有被很好地揭示出来。
2.比起人们在制度文献方面有限的讨论基础上所形成的见解而言,历史偶然和机遇在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3.为了理解人类设计对制度变迁的作用,研究者应该对制度各相关参与者具体的文化构成及其活动的制度约束予以更多的关注。
笔者所引用的数据来自一项对德国和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比较研究,时间跨度大致是从20世纪早期到60年代。本文将首先找出这两个国家高等教育历史上的主要转折点,然后试图考察机遇、预见和内部变迁这三者的作用。
二、导致德国和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原因
在这部分,笔者将大致勾画德国和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主要历史转折点(这里的介绍是基于对两个系统的一本研究著作,但是本文无法举出必要的证据,来解释笔者对制度变迁时点和/或原因的选择)。
表1 德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转折点
制度变迁
背景
1806/08年耶拿(Jena) 拿破仑在耶拿击败普鲁士,大大削弱了君主
洪堡和他的朋友们以“教养”(" Bildung" ) 政体。普鲁士国王威廉指派一群激进的改
和“科学研究”(" Wissenschaft" )以及“教学 革分子与洪堡重建了德国的教育系统。
和科研的自由”(" Lehr-und Forschungs-
freiheit" )等理念为基础,成功地建议并实施
了一套新的高等教育系统。这套系统来自军事战败/
于一套完备的设计,反映了现代教育的理念 预见
(裴斯泰洛齐/卢梭),并建立了国际声誉。
1871年俾斯麦(Bismarck) 俾斯麦领导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打败了法
在俾斯麦领导下的高等教育集权制削弱了国。德国国家主义兴起导致了对制度化生
德国各州高等教育之间的竞争;各学院和大 活的“军国主义”重建。
学被军国主义思潮所笼罩;开始了科层制战争/
(Mandarins)①:而自由精神和大学间的竞争 德国民族国家的建立。
(续表)
制度变迁背景
1933年之后德国大学遭受了持续的“智力外流”,大量
纳粹主义的骚扰和迫害,使得犹太学者包括的研究精英逃离德国(很多到了美国)。
很多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离开了自己的工作 法西斯主义革命。
1945/47年 教授—学阀(mandarins)恢复了权力。教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开始“民主复 学/科研自由(Lehr-/Forschungsfreiheit)削
兴”(democratic renewal)。新宪法将“教学 弱了大学要求其教授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和科研自由”(Lehr-und Forschungsfreiheit) 能力。
置于宪法的保护之下。 军事/国家战败。
1965年之后经济增长、技术和教育发展扩大了对受过大
大学入学人数增至三倍。学生和年轻的大 学教育人才的需求。
学教师以及一些政客侵入德国以阶级为基 经济增长
础的教育系统,并试图推翻它。 激进的—民主运动。
2000年德国大学在声誉、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科
大学被赋予局部的自治。私立高等教育的 研的绩效等方面遭受了空前损失,尤其是当
开始出现并引入了竞争。美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成为德国大学所
参照的“基准”之时。
全球化/互联网技术
表2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转折点
制度变迁 背景
1865年 内战结束;北方各州工业化带来空前的经济
研究生教育的开端(康乃尔,约翰·霍普金
增长;新教资本家获得大量的个人财富。
有重要意义的美国对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学
习移民。大批美国人留学欧洲,尤其是德
国。在1850~1890年之间,大约有10000 造成的原因:
美国人在德国的大学学习,很多拿到博士学 战争/工业化
位后回国。 “全球化”
1870~1900年
查尔斯·艾里奥特(Charles Eliot)将哈佛学
院改造成现代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以斯拉·康乃尔、卡耐基、
李兰德·斯坦福(Llelland Stanford)、约翰·
洛克菲勒、波士顿·布罗明(Boston Brah-
预见
mins)都捐献巨款资助创立大学。
(续表)
制度变迁背景
1862年尽管新大学是公立,但是他们却效仿了东海
赠地法案(默雷尔)将现代大学扩展到美国 岸私立大学的模式
的“心脏地带”。 预见(国家水平)
Ca.1910年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之间以及内部的权力
“教师革命”。新的美国大学(包括研究生 平衡关系开始变化,并倾向于教师。
院)完全的制度化,导致“博士培养”爆炸性
(威廉·詹姆士1903:“博士章鱼”) 组织扩张
1932年,爱因斯坦及其数百名追随者迁居 纳粹主义采用暴力夺取权力。
到美国,他们主要是大学中的德裔犹太教
1940~1945年,大学和政府合作;大家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
到基础研究的战略作用。
1944年
退役军人法案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向中产阶
级开放。 二战结束
预见(国家水平)
20世纪60年代 组织增长,博士培养规模爆炸性增长②
南北内战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同时也大大促进了经济繁荣,并为新教的经济和文化精英创立私立学校提供了机会。普鲁士郡主政体被法国击败,之后在俾斯麦与法国对抗的“铁血”政策下,一个统一的德国产生;纳粹主义走上政治舞台;二次世界大战……很多这样的历史事件产生了国际反响,例如纳粹驱逐大量德裔犹太科学家,加强了美国的科研实力。战争通常导致经济的破坏和增长。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对职业化的专门知识、技能的需求也在增加。随着高等教育从面向上流社会转向中产和下层阶级,它的规模在扩大,并改变着自身的文化。
从美国学生到德国留学开始,全球化就促进了大量的制度变迁。从德裔犹太科学家的大批离去到今天德美两国师生的频繁交流,全球化已经成为导致大西洋两岸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
技术革命:互联网技术之前的技术革命仅仅是提高了对高等教育毕业生专业技能的需求,相比之下,互联网有可能(而且现在已经开始)改变教学和科研的本质。成人继续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即时”(just-in-time)学习和弹性教学模式。有些人认为,互联网将带来类似于印刷术出现所导致的制度变迁。
对德美两国高等教育中主要制度变迁和转折点的描述是很简要的,下面归纳了导致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原因:
● 战争和政权更替(10次)
● 经济或组织增长(4次)
● 预见(4次)
● 全球化(2次)
● 技术(1次)
如果把经济或组织增长、全球化和技术都归为内生的变迁这一类,我们可以得出外生、内生和预见三者之间的一个大致比例是40∶40∶20③。很显然,其他国家的历史轨迹很可能产生不同的比例。这里只是想对机遇、内生变化和预见的相对权重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可以说,机遇和内生变化构成了主要的原因,其比例基本相等,而预见则解释了剩余小部分的情形。
三、偶然事件——建立在“冻结的事故”之上的制度
下面将对偶然事件在解释制度轨迹中被低估的现象进行评论。社会科学家向来低估机遇或偶然事件对人类的影响。然而,偶然事件开始的地方,往往也是因果解释(意味着社会科学家的权威)终止的地方。此外,有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为了帮助领导人进行变革。轻易地把知识生产转化为“如何去做”的政策方案,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夸大决策者的能力(甚至无所不能),而其能力的局限却被忽略。
偶然事件经常是制度发展路径的开端。举例来说,一种制度的形态及其影响通常依赖于它何时以何种方式产生。顺序很重要。在德国普鲁士,普通教育机构(K-12)是在高等教育之前制度化的。而在美国,情况则正相反,在贺瑞斯·曼于麻省首次建立正规的普通教育系统之前,私立的教派学院已经形成。这反过来对美国人如何看待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他们不愿意通过税收支持公立教育)。美国高校牢固建立的事实,也解释了“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作为两种不同而又是一体的美国高等教育的特色。
的确,学院在正规的K-12学校之前就大量存在,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特殊而又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仅仅在笔者有限的专业知识范围内,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像德国和美国“幼儿园”的(kindergarten)发展轨迹、德国和美国大规模公立和私立学校创立的不同顺序。当然,一旦这样的历史事件成为一个更大的制度建构过程的一部分时,它们就成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轨迹中开始处的“被冻结的偶发事件”(frozen accidents)——斯蒂芬·杰伊·古德(Stephen Jay Gould)使用这个词来说明自然演化中的突然中断。就好像不同国家的制度发展可以在任意时刻或事件开始一样。西摩·李普赛特(Seymour Lipset)遵循马克斯·韦伯的思路,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像掷骰子游戏一样开始,一开始没有号码,但是接下来它的方向都要受到过去结果的影响……每次骰子都会有一个给定的号码,并且再次掷到那个号码的概率会增加”。[1]
通过这种方式,起初很小的差异会导致后来选择路径上很大的分别。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斯·韦伯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研究。韦伯在他成熟的社会学理论中问道:“哪一个特有的互相联系的环境”(which singular concatenation of circumstances)[2] 导致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这一显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他的解释是理性规律中的历史机遇、现代科技和新教伦理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而且仅仅出现在西方社会。④ 这种发展模式中的个别因素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都存在(例如,中国拥有很先进的技术),但是这些地方没有将这些因素凝结成一个特定的构造:理性法保证了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科技驱动了大规模组织中技术手段的平稳进步;新教伦理创造了一种激励性的文化信仰,那就是尽可能地把人的精力用在工作和生产上,即使生产超过了人们实际的需求。
当然,一旦新的制度形式在一国建立,其他的国家都可以模仿之。
四、内生的变化:没有轮子的强力引擎?
笔者注意到几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中内生因素的问题:
首先,大部分相关研究将自身限制于“通常的猜想”(usual suspects,诸如理性化、科层化、现代化、分化、全球化等),往往忽视更为具体和有趣的内在因素。
其次,上述这些通常猜想的因素被认为是导致特定制度变迁过程的有效因素而被接受,但是却没有人注意那些还在讨论中的机制和特定因素。这就使得那些解释从根本上看是目的论的。历史被视为是有一个终极目的。社会系统的主要驱动和活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像熵是自然系统的终极一样。内生变迁模型分享了人类理性中启迪教化的信念和“无限完备性”(infinite perfectibility)。
“内生因素”都被概念化为“零和”过程;“更多的现代性”意味着“更少的传统”,更多的全球化意味着更少的本土化等等,直到最后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水晶宫。在经验事实的层面上,新模式的建立往往并没有废除旧模式。它更像是一个嫁接,在已有的东西中增加新的内容,而不是替代或使已有的东西废止。混合要比崭新更为常见。
自发驱动内生因素的早期支持者之一是塔克特·帕森斯。他所构建的理论认为,社会总是朝着“更强的适应性”(greater adaptability)进步变化,这可以增加有效适应变动环境的机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已经有很多国家朝着“更强的适应性”发展。
相关的实例有约翰·迈尔(John Meyer)的全球化理论。迈尔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与现代化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现代化理论认为,一些常见的内生性因素像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民主化推动了现代制度的全球扩散,这些制度日益相互模仿,导致了一种全球制度趋同的结果。⑤ 既然“现代化”已经使所有的孩子产生了对阅读和计算的“需要”,那么迟早我们会发现在组织和教育特点上各国相似的“大众教育制度”都会使孩子们那样做。迈尔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全球化存在一种将西方式的教育模式“扩散”到全世界的长期趋势。这是因为普鲁士德国发明、后来被美国采用的学校系统是一种民族—国家的创造,它通过强制性的大众化教育来实现政治社会化和稳定。既然民族—国家是世界各地所有政治团体不得不采用的制度形式——只要能确保其安全——他们必定会建立相同类型的教育体系。的确,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和沟通的能量已经在最近爆发出来,而且很有可能进一步增长。
尽管迈尔等人在全球化和“世界社会”出现的条件下提出了制度变迁的重要问题,但他们论述得太抽象,造成读者无法用可辨识的经验事物与实际的教育制度相对应。⑥ 我们看来那些用来连接中心思想和结论的句子。例如,扩散到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模型的特征是什么呢?根据约翰·迈尔的说法,“各种角色都需要接受高等教育,并且大多数年轻人可以从中受益”,高等教育系统“承载着我们共有世界的文化框架”,[3] “大众教育的现代形式已经迅速地遍布现代世界体系的各个角落”。[4] 措辞笼统和模糊到这种程度,很难用经验事实来推翻它。
由于缺少特定的背景和因果特征,约翰·迈尔的理论中唯一的因果机制就是,理性化这样一个主要因素就像无人驾驶的引擎那样,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任意驰骋⑦。唯一进入视野的“参与者”是非描述性的“国家精英”,而且这些精英在他们的理论中也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些世界性的国家精英之间的相互影响,比受到来自地方传统和文化的影响更大,并且,尽管这些精英同地方和国家的状况不同步(至少在大部分的非犹太教—基督教地区),他们有能力对其国家制度施加影响,以适应他们世界性的、游移的思想:“所有的国家都有很多巨大的被学校制度化了的精英部门,这些部门有很多文化上的共通之处。”
类似地,前面提到的由全球化引致的历史事件是一种不连续的、不稳定的模式,而非稳定的长期发展趋势。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渐进的变迁过程,而是一个“变动均衡”(punctuate the equilibrium)的阶段性事件:如美国学生在19世纪留学德国;大批德裔犹太科学家被迫离开到了美国;20世纪末出现全球化的师生流动(美国是最大的流入国),当他们回到自己国家时,确信改变自己所在的社会是可能的。问题在于,即使当我们已经分辨出很多内生变迁的原因,证明的重担仍然在研究者的肩上,他们需要说明引起变化的原因不仅有引擎、而且是有轮子的,是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着陆的。
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
除了质疑内生变迁的连续性和必然性观点外,我们还需要挑战它们的深度和广度。即使世界各地构建制度的精英们被源自欧美想当然的理念和规则所指引,结果的相似性事实上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迈尔等人给人们的印象是,任何指标,如一个以年龄来分等级、采用授课形式的公立义务教育在特定国家被采用,就说明全球化又前进了一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的综合性高中、德国的大学预科(German Gymnasium)、德国的双轨体制和美国职业教育、美国的研究生院和法国的大学校(French Grandes Ecoles),⑧ 它们都是具有相同要素的正规教育模型扩散的例证。在理论高度抽象的水平上,上述观点可能是正确的。谁愿意接受如此抽象的结论呢?
约翰·迈尔的主要兴趣在于追踪和解释多数情况下用入学人数来表示正规教育的增长。以这样有限的指标为根据,他们得出了很宽泛的结论,包括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扩展“反映了一国社会共有的全球化模式,而不仅仅是一国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差异”。他们不问一个高等教育系统是否构成一国创新系统的一部分,或者服务于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统治系统再生产;也不问大学所培养的毕业生对国家的总体发展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妨碍。
因为迈尔等人的研究是在匿名的、“无人的”情况下做的,他们并不需要看到谁在促使制度变迁。在他们的研究里,没有可供辨认的个体或集体参与者、集团或阶级。我们认为,决策者行为使得每个地方都是摇摆不定的,这些决策者被一群思维相似的专家所影响,这些人持有相同的范式、出席相同的国际会议等等。迈尔等人试图把解释趋同的迹象作为说明具体的制度对于地方而言具有相同的符号和技术含义的证据。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Stiglitz)的话来说,迈尔等人忽略了编码的技术信息、隐性的文化知识和再定制技术文本的制度框架之间的区别:“技术手册、蓝图和指导书都是技术知识经过编码后的信息,它们可以被看作是整个冰山的山尖。编码后的技术信息假定了背景知识和实践在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是不完备的。”使技术发挥作用要求“隐性知识的慢慢积累,而无法简单地转移或‘下载’到发展中国家”。
斯蒂格里茨继续讨论了嵌入制度或组织输入更大的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即使一国可以建立一个与美国高中“一模一样”的制度。结果很可能是有一个和人家很像的外壳,但是文化意义上——课程、大型雇佣制度的后果、升入高等教育以及很多其他问题——很有可能是地方性和独特的。
如果想要确定制度复制过程中文化意义和技术输入,我们就需要采取同时引入历史和地方性的事实的视角。[5]
内生变迁在制度变迁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定的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是由内在的冲突或矛盾(韦伯称作“理性化”,黑格尔称作“理性的狡诈”)驱动的。杰斐逊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通过一些连续的美国革命阶段得以实现,通过这些缓慢渐进的变化,制度逐渐接近了“他们思想的理想”(ideal of their idea)。尽管这些趋势看起来不可抑制,但是它们既没有平衡地发挥作用,也不能在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在这些长期趋势的末端,是那些将理想与现实相比较并且只是二者不协调就会致力于变革的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缩减不和谐”的过程。即使一代的政治参与者耗尽心力尽量减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未竟使命,下一代仍然会奋起抗争。尽管变迁的压力始终存在,变化本身仍然是不连续的。将“创造平等”的公理从一句承诺变成现实需要独特的事件,如在部队和学校废止种族歧视,投票箱前的平等投票等等。
一个内生变迁动力的极好例子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它有内在的发展趋势。黑格尔说明,一个人对其他人而言要成为主人,只有当其他人本身也是主人并且认可他的时候才能实现。主人被奴隶认可并非毫无意义,仅从主人的看法来区分主人与非主人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的判断。因此,“主人—奴隶”的关系就有解放奴隶的内在趋向,这几乎同作为个体的主人的意愿相反。黑格尔把它称作是“理性的诡谲”,因为制度的理性程度的增长遵从的是无意识的、不可抑制的力量。
德国和美国制度变迁中存在两种内生性的力量,一种是全球化,另一种我们称之为大学的“科学化”(用来表明某种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那些研究者的影响力日益超过大学领导、行政人员和资助者)。很显然,建立在扩散知识和进行研究发现基础上的机构内在地会由从事发现工作的研究者所领导。但是,这种趋势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地方性的条件会压制、延迟或疏散内生的压力,通过目前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委员会的权力再分配或者尚未发生的中小学“教师革命”来起作用。
综上所述,内生的变迁过程是在已经建立的制度安排下进行的,已有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易于对内生变迁作出反应,并有利于它的。伊朗或沙特阿拉伯的教育系统明显处在“全球化”驱动的压力下。但在目前,内生变迁的净效果似乎减缓而不是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五、人类设计的作用
在本部分,笔者讨论用以改变制度的两类理性干预,分别来自在第二部分所提到的政府或公共政策代理人和“奠基人”或“创立者”。笔者认为,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者的能力。最好的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支持由后者发起的成功的制度创新,并促进它们向全社会传播扩散。每当政府试图创立新制度或者改革效率低的制度时,结果通常事与愿违。
创建者
一个制度的建立当然是说明由人类理性和细致的实践所诱发的制度变迁的最好例子。在这两种情况下,制度的创建者拥有经过仔细考虑的制度计划,这种计划来自于长期的集体反省和对话。但是,如不能打开机会之窗,这些制度计划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要打开机会之窗,一个例子是军事失败和国家崩溃,另一个例子是惊人和空前的经济腾飞(也同战争相关连)。没有这些外部的冲击来打破已有的制度均衡,个人或群体就很难成功地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创建的行为会留下创建者在思维方式、信仰、价值观和利益方面的深刻烙印。为了理解一个制度的文化,就需要进入到“集体道德”和创建参与者的环境当中。就美国的情形而言,制度创建者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富有、信奉新教,并且在政治上很有影响,他们真诚地相信,建立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起到文明开化的作用——他们就是东北海岸的一些贵族。
例证1 不同类型的制度创立者——贵族和学者
贵族对新制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果没有他们的经济支持和智性领导,现代美国大学就无法建立。贵族有学问(或者至少是对有学问心存敬意)、有实际经验,并且富有。他们居住的波士顿是一座“同时是文化、金融和社会中心的城市”。[6] 以他们尊贵的地位和公民的奉献和影响,他们更接近于美国人所认可的贵族——他们是一群兼有高等社会血统和经济独立性的人,他们对优秀文化和艺术存有真诚的敬意。但重要的是,他们也有商人创建和运作大型组织实际的经验,而且他们拥有(或可以动员)空前规模的金融资源。
在德国,与美国贵族相对应的是围绕在威廉·洪堡周围的那些人。洪堡是少数拥有高深学问而又有实践感觉(man of affairs)、并能够建立新制度的人。普鲁士对德国其他州的统治(正如韦伯后来所说,政治空气一直是更易于呼吸的)使得像洪堡这样的人能够扮演制度角色,并且把德国的大学推到了专制大臣和教授(科层,the“mandarins”)的手中。后者虽然可能有与贵族相同的知识鉴赏力,但是总体来说,他们缺乏对实际制度构建的感觉和调动公民参与的能力。他们也缺少资源和公民自治,来推行任何从政府和科层干预中要求自治的主张。实际上,由于缺少普鲁士各州的科层机构,他们完全无法将改革付诸实施。尽管洪堡周围有很多学者和作家团体支持新的德国市民和社会文化,但是他们既没有像美国同行那样的金融资源,也没有大学独立于国家这一共享的文化信念。
在比较美国的贵族和德国的学者以及市民参与者如何塑造现代大学时,有人可能会将主要差别归于美国贵族可支配巨大财富。要建立和资助现代研究型大学,当然需要巨大的财富做后盾。但金钱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对知识和教育价值的信念、对作为市民领袖和先驱在一个社会范围内(不仅仅是商业事务)所扮角色的信念以及为公共事业动用私人资源——这些信念都像金钱那样具有实质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20世纪早期美国商业阶级态度的描述与此相关:“因此我们在欧洲面临着大资产阶级所特有的缺陷,这些大资产阶级来自19世纪的产业成功,不久前看起来还是全能的主人。现在这个阶级中的个人面临如此巨大的恐怖和胆怯,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对社会有机体的必要性如此缺乏信心,以至于他们很容易被胁迫。在25年前的英国以及现在的美国都不是这样。那个时候资本家相信自己对社会的价值,在充分享受他们财富和无限的权力时,他们的存在是适当的。”[7]
在美国创立巨型大学,是一种狂傲的自信。毫无疑问,没有什么预测可以阻止美国伟大的贵族领袖将他们个人的意愿变成一种社会制度。
例证2 商学院的合法化——制度创立者的案例
所有的信念都是有效的,只要它们已经隐藏在成功而受人敬仰的制度里。哈佛法学院的存在对创建商学院的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创建研究生商学院得到多数商业团体的强大支持。但是,美国的学术—商业关系并不协调。很多美国学者对于“商业管理”科目表示怀疑;而商业团体的成员则对学术教育对真实世界领导的价值持保留态度。有人会说:“你可以教会计……但是没法教铁路建设……”(意思是,领导一个像西太平洋那样的大型组织)。毫不奇怪,一些著名学者和大学教师反对在大学里设立职业性的商学院。保护学术纯洁的先锋——芝加哥大学年轻的校长罗伯特·赫钦斯(Robert Hutchins)发起运动抵制商学院对学术理念的扭曲。
相反,尊敬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N·怀特海(Alfred N.Whitehead)和法学家洛厄尔(Lowell,也是后来的哈佛校长)就赞成设立商业管理专业学院,并且将这种想法放在美国实用主义的背景里寻找其哲学基础。但是,如果怀特海和洛厄尔未能利用法学院并把它作为专业学院的典型,他们建立商学院的想法也不会成功。尽管法学院偏于“应用”方面,但是仍然赢得了学者和从业人员的尊敬和威信。洛厄尔认为,商学院通过帮助学生成为职业经理人,同样可以赢得学者和商业团体领袖们的敬意。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明智地指出:正如法学院是帮助学生做好进入法律界的准备(不是成为法学教授)一样,新的商学院就是让学生做好商业管理的准备(不是成为经济学教授)⑨。两类学院外表的相似性——在商学院可以重复法学院的成功这一承诺下——将使商学院采用案例教学法。正像法学院的主要教学工具那样,撰写大量经理们实际遇到的真实问题,既可以作为工具让学生熟悉他们将来会遇到的问题,也可以帮助他们在做决策时形成成熟的判断。案例法成为一条虽然狭窄但是可行的通路,它使商学院的支持者们缩短了一个全新而受人质疑的专业学院获得合法性所经历的战斗历程。
两类政府的制度制定
一种有准备、有目的的制度变迁是通过建立法案实现的。另一类就是政府干预。第二类中的两个例子是赠地法案和退役军人法案,前者为贫穷的中西部各州创立巨型大学提供了“启动”资源,后者开启了高等教育使之面向之前被拒绝接纳的中产阶级学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政府干预都没有修补制度设计本身,而“仅仅”扩展了其范围和规模,同时保持制度的文化完整无缺。我们可以将之与其他国家政府试图进行的无休止的科层修补和改变高等教育本身内在运作相比较。例如,德国政府执行的名额限制(Numerus Clausus,NC),是一个政府配给方案,它决定一个学生在哪里学习、什么时候学习和学习什么东西。
德国政府采用名额限制是解决在70年代遇到的所谓“学生过剩”问题。事实上,问题出在德国大学无法控制学生的入学量——法律强制大学接收已经通过高中毕业考试(具体而言,就是有“高中毕业文凭”⑩)的学生。然而,赋予大学学生选拔权又违反了宪法对平等的保护。问题通过创建一个卡夫卡式的(Kafkaesque)科层(11) 得以解决。通过可输入学生个人的考试成绩并可对成百上千的学生进行排序的一个中心机构,一些学生被安排在鲁尔萨克森地区(Lower Saxony)学习一年社会学,在汉堡学习两年工程或者在慕尼黑(学生的首选)学习五年医学。在这种科层专制中存在大量的黑市交易,一个拥有在汉堡的社会学入学权的学生(住在或想要住在德国南部)会同一个有在慕尼黑的社会学入学权的学生做交易,这项交易通过为汉堡学生提供未知数量的钱财得以实现。
在德国最近的改革努力中,政府试图重新设计大学年轻教师的职业路径,引入了新的绩效标准以及其他很多措施。20世纪60年代,政府强制大学转变内部治理,遵从一种细致的、政府控制的计划。就所有这些科层的经验来说,政府控制的微观干预都是负面的。美国的例子表明,试图改变制度的有效预见应集中在扩展大学工作范围的简单干预方式上,而不是改变其内部运作(一个类似的微观管理的科层干预是K-12领域里的“不让一个儿童落伍”法令(12))。
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人,创业者要比政府更为重要:创建者像以斯拉·康乃尔、约翰·霍普金斯或激进的改革者像查尔斯·爱略特或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正是他创建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如果没有创立者担当起创新和变革的重任,政府是虚弱无力的。赠地法案和退伍军人法案都是有效的,因为它们都对通过私立方式运转良好的制度模式给予公共支持。在赠地的各州还没有获赠土地之前,不会(或没有那么快地)想到要创建大学,赠地使它们有了向前努力的积极性;而退伍军人法案则使过去没有钱上大学的人们有机会上大学。上面这些干预都没有修补制度本身,它们仅仅是扩展了运作的基础而已。
六、概要和政策意义
目前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互联网迅速普及是打开有效且理性的人类干预的机会之窗的两个条件。就这点而言,我们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政策结论呢?
在制度创立方面,由制度创立者发起和传播的深入的(战略性的)制度创新和变迁,最好是由政府机构予以财政支持,而不宜颠倒两者的顺序;集中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行动,与其说是构建或转换已有的制度实践,不如说是妨碍和抵制变迁;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战略干预,其成功往往在提供资源支持和加强运作良好的方面,而不是“改善”较差的运作。
在制度运行方面,不要做完美主义者。通过制度设计开拓内生的变迁,制度可以逐渐自我完善。不要因为所需要的参数不完备,就处于等待状态;促进制度的多样性。既然很多变化都是偶然发生的,多样性可以使成功转化的机会大大增加;使用多种政策标准。不公平不是教育制度中所遭遇的唯一问题,同样重要的是科层主义(大学被使用知识来强化自身的权力而不是促进创新的教师管辖)、文凭主义(学历文凭成为“向上流动”的唯一路径)等等;允许高等教育采取多样化的入学标准。允许大学使用自己的招生标准选拔学生,标准化的、普适的大学入学标准会窒息创新;定义和使用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优秀标准;向学位结构(本科、硕士、博士、MBA)的国际化和采纳国际绩效标准(学位攻读的时间、教师的生产力、薪水等等),使学术制度向国际标准开放;采用多样化的制度学习渠道。把学生送到国外学习,并帮助他们返回。吸引外国学生来本国留学,但也要提高教员处理文化多样性的能力。
注释:
①富里滋·瑞格尔(Fritz Ringer)在他的《德国学阀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1969)中使用“mandarins”一词来描述1870~1918年之间的德国大学教授。他的用法遵循了马克斯·韦伯对中国“文人”(literati)的研究,韦伯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联合传统的、卡里斯马和理性三种权威的阶层。狭义上,mandarins是一个统治阶层,他们使用文件命令作为对非文化阶层权力的来源。
②美国高校每年的博士“产出”大概是48000人,中国2003年是48000人(1995年是8139人),德国是20000人。
③有些人更倾向采取一种历史决定论的看法,他们认为,战争和政权更替遵循着某种因果规律,他们不接受上面的计数方法。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即使这些战争和革命发生的背后隐藏着某些规律,但是只要其规律是事后才发现的,这些战争和革命仍然是偶然事件。
④需要重申的是这里所说的出现(emergence)不同于可转移(transferability)。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并不排除它向东方的转移。
⑤一个对“趋同”模型的说明可参见John W.Meyer.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No.1,1977:55—77.一个最近的批评可参见William K.Cummings.The Institutions of Education:Compare,Compare,Compar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vol.43,No.4,1999:413—437.
⑥趋同和路径依赖的支持者双方之间的论战,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著作里关于非理性对制度持续的影响。例如,他在对现代行政的分析中沮丧地预测,理性科层的推行会把其他所有非理性的行政制度排挤出去。在韦伯的估计中,觉醒的力量要比再度沉迷的反作用力运转要困难得多。笔者以为这种预测只是韦伯的尼采式(Nietzsche)传统的一个结果,在经验上得不到证明。
⑦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韦伯都是这类变化的支持者。黑格尔认为,存在一种内在的动力,引导人们用平等替代不平等。马克思在内生变迁理论的基础上,做了大量预测。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从长期来看会下降,贫富差距会扩大,对人类需求的侵害将导致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反抗。韦伯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公务员系统以及选举系统都处在“欧化”(europeanized)的过程中。
⑧法国高等教育机构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学(UNIVERSITIES),法国有公立大学87所,私立大学4所,实行“宽进严出”的管理办法,淘汰率较高,有教学质量保证。另一类是大学校(GRANDES ECOLES),这类学校属“精英教育”性质,实行“严进宽出”。——译者注
⑨可以通过比较美国和德国的发展来测量这种区别,其中后者无法做这种区分。在德国,商业管理被制度化以失败告终。而在美国,商业管理作为一个应用和交叉性的研究领域被制度化却逐渐兴盛。
⑩“Abitur”考试是指德语考试和结合专业所选的3~4门科目的考试,通过考试证明是否符合大学的入学资格。——译者注
(11)Kafkaesque除了在文学意义上理解为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外,一般是指人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荒诞神秘的景况中,内心充满恐惧、焦虑、迷惑、困扰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那任意摆布人的力量是出自那样庞大复杂的机制,它又是那样的随意,它无所不在,又无所寓形,人受到它的压抑却又赴愬无门。——译者注
(12)2002年1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2001年的“不让一个儿童落伍”(NCLB:No Child Left Behind)法令。它深刻影响了美国教育,促进各州建立一套相应的评估考核体系,并导致学校很大程度围绕成绩和“不合格”的主题展开教育活动。——译者注
标签:全球化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大学论文; 德国教育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