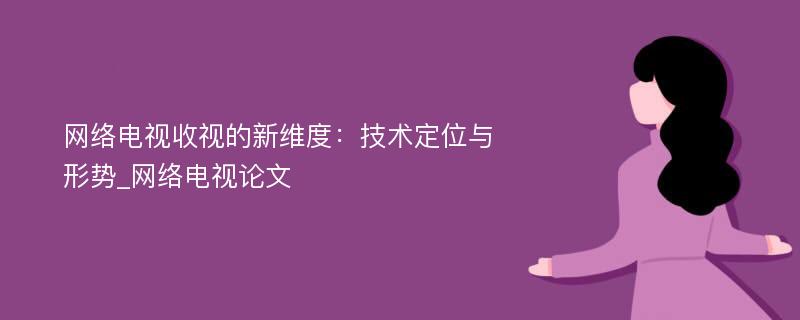
网络电视收视的新维度:技术和情境的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网络电视论文,情境论文,取向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前关于互联网能否取代电视的争论犹在耳边,媒介最终将走向融合的话语已经甚嚣尘上,不过其中批评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北欧学者Fagerjord and Storsual指出所谓“媒介融合”只不过是一个迷人的理论主张而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①在国内,学者张立伟认为媒介融合无论在内容层面还是组织层面都举步维艰。②理论上的争论其实也映射了媒介融合在现实中的尴尬。以通过网络观看电视节目为例,一组调查数据表明,在美国已有超过20%的电视收看是通过网络进行的。③但也有数据表明其实美国人平均每天观看网络电视或视频的时间只有两分钟左右。④尽管如此,互联网以及网络视频仍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在我国,CNNIC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网络视频网民达到3.89亿,网民中上网收看视频的比例为65.8%,半年增长率为4.5%。网络视频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电视用户的收视习惯,这对于传统电视机构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危机。在寻求变革之路上,传统电视媒体机构纷纷开始寻求和视频网站的合作,例如,依托传统电视媒体的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开播,PPLive网络电视以及PPS网络视频客户端的流行,还有以优酷网、奇艺网、酷6网等为代表的视频分享网站的后来居上,都见证了传统电视媒体顺应媒体趋势大潮的决心。
然而,需要思考的是,观众为什么会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下选择互联网而不是电视机来观看电视节目呢?网络电视相比于传统电视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限制呢?从以单向传播为主的电视到以互动传播为主的互联网,观众在认知审美、收视经验、情感和需求上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媒介内在技术属性的差别。但从遥控器到鼠标的过渡绝不仅仅是技术的转变那么简单。媒介研究中从技术决定论到社会构建理论的转向已经提醒我们对于这种属性的比量是需要从技术、社会文化经济、管理政策、媒介组织建构以及人本身多方面来考虑的。既然确实有一部分受众目前正通过网络来收看传统的电视节目,那么研究网络电视的传播特征以期寻找出满足网络电视观众需求的方法便成为传统电视媒体和互联网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John Pavlik曾将互联网电视(Internet TV)的节目来源分为四类,一是基于提高重复播出率和推广而将传统电视节目转化为网络电视节目的有偿输出。例如湖南卫视2013年度重磅出击的综艺选秀节目《快乐男声》就将其独家网络版权售卖给爱奇艺网站,爱奇艺负责网络平台的全面推广。二是各大电视台或者新闻机构通过建立自己的新闻网站,无偿提供从国际到国内到地方的各类新闻视频。三是作为内容供应商的第三方传媒机构将节目出售给传统电视台或各大视频网站。四是个人制作或原创频道的加入,草根民众通过自我创作或在新闻现场的拍摄上传,为网络电视源源不断地输送节目。目前也出现了专门为草根民众的视频上传和分享提供平台的网络电视网站。⑤
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由传统电视媒体制作并在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节目,经同步或者滞后上传到互联网并通过各类视频分享或者经媒体网站播出而形成的网络电视。这一界定排除了那些由电视台制作却只在网络平台播出的各类专门节目以及为推介某一电视节目而制作的各类节目预告片、宣传片和片花等(鉴于目前网上存在的各类可下载观看的电视节目大多存在版权问题,亦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同一内容在不同平台播出,可以方便我们做对比研究,从而可以更好地探寻两种传播媒介的媒介特征以及如何满足观众收视需求的诸多途径。
一 技术的取向
从电视到网络的转换,最大的挑战可能是来自于如何改变传统电视观众的媒介消费习惯。从历史的角度看,观众改变媒介消费习惯具有很强的惰性因素。从报纸到广播,再从广播到电视,外在的媒介符号的革命性变革是强大的推动力。那互联网依赖什么进行变革呢?电脑最初是以文字和数字处理工具的面目出现在家庭当中,和大众传播似无太多瓜葛。尔后,互联网所大力宣扬的从被动到主动,从单向到双向的传播方式变革也没能把网络电视推向大众传播的风口浪尖,反而在某些方面造成了电视收看的不可替代性。技术的进步使互联网赋予了观众更积极的角色和更互动的权力,也造成了互联网更加“工具化”而非“仪式化”的使用导向。因此,在以休闲和消磨时间为目的的媒介使用上,电视平台比网络平台更具有优越性,网络电视也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电视。另外,目前互联网技术对于播放电视节目来说仍存在诸多限制,比如画幅大小、画面清晰度、视频链接、缓冲速度以及声画同步等问题。
考虑到互联网技术的特点和限制,电视上网也应当首先从视听语言方面考虑观众的收视和审美需求。例如,从网络链接速度方面考虑,网络影像应当尽量减少内部被摄物体的运动以及外部镜头的运动,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视频的链接和缓冲速度。另外,计算机屏幕尺寸的限制使得特写镜头比中远景镜头更适合网络电视。但令人尴尬的是这些理论层面的诉求却和网络电视的发展现状并不完全吻合。以体育节目为例,一直以来,赛事直播都在网络电视中占有重要地位。电视向网络进军最早就是从体育节目开始的。1999年9月26日的美国职业橄榄球赛(NFL),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与明尼苏达维京人(Minnesota Vikings)的对决,NFL.com通过网络实时视频传输技术,让芬兰和奥地利三个具有高宽带接入技术的地区球迷与美国球迷同时观看到了比赛,最早实现了网络电视直播。此后,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的网络视频转播也在网络体育视频节目的发展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1999年11月2日,美国职业篮球联盟趁新赛季拉开大幕之际,同时推出了自己的在线网络电视(NBA.com)。NBA总裁David Stern曾形容,“NBA.com网络电视是网络、电视和篮球的融合。为球迷们提供NBA过去和现在的篮球赛事,及时而具有深度的球赛信息,全方位,24小时不间断的篮球报道”。在我国,PPlive是网络视频媒体的先行者,从2005年成立开始便不遗余力地推广赛事直播。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PPLive的全程直播所吸引的全球同时在线用户突破了500万。而到了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在线观看的受众人数更是创纪录地达到了1000万。新闻方面,CNN.com,MSNBC.com,CBSNews.com以及ABCNews.com都是线上视频新闻的引领者,CBS在波士顿地区的下属机构WBZ和西雅图地区的下属机构KIRO首先提供了地区网络视频新闻。1999年9月ABCNews.com更是首先推出了常态化的网络新闻节目,提供以网络为唯一播出平台的独家新闻视频。逢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中午12:30播出,时长15分钟。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传统电视机构都会同时在线发布自己的新闻节目视频。因此,体育节目和新闻节目一起构成了当今网络电视最大的细分市场。
然而,体育节目和新闻节目从电视拍摄和观众收视需求的角度看,都有着各自的在视听语言方面的要求。影视思维的核心是镜头,而作为银幕叙事的基本意义单位和构图方式,画面中“形”的质感决定了视听语言整体感知的力度。例如,体育节目自身特点决定了拍摄时会有大量的镜头内外部运动;而电视新闻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画面信息量,往往要求大量使用两极镜头。很显然,如上所述,这些镜头都不适合网络影像的要求。因此,带给我们的问题就是,在技术瓶颈暂时无法突破的情况下,网络电视必须发展出一套全新的符合网络传播规律和特点的视听语言。
其次,从观众收视经验和心理来看,英国学者威廉姆斯曾经提出过一个“流”的概念用以说明电视的连续播出对观众收视的影响。⑥当观众在某一时间段内持续收看同一频道的节目时,称为顺流;当观众从本频道转往其他频道时,称为溢流;若观众从其他频道转往本频道,则称为入流。⑦但不管是哪一种“流”的方式,电视收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线性传播,瞬间传达,被动接受的过程。对于在视频分享网站观看电视节目而言,相互独立存在的视频片段显然已经不存在于威廉姆斯所说的“流”之中了。不过可以设想,当观众一口气在网站上连续看上好几集电视连续剧的时候,由于没有了插播广告的干扰,没有了看电视时一天只能看一到两集的限制,观众反而会处于一种更加沉浸的状态中。因此,“互动”一定是网络传播中必不可少的诉求吗?可能对于某些类型的网络视频节目而言,在整个的观看过程中,更多的还是一个被动的“反应”过程而不是一个“互动”过程。此外,电视剧在生产的时候往往会按照最后的文本呈现方式来考虑他的叙事,因此,镜头视角和编排顺序成为文本转化为视听语言的重要环节,而铺陈、转折和高潮等等的情节构想往往会根据插入广告的时间设置以及按天播放的形式来设计安排。那么,网络电视无间断的收看是否又会使得节目内容本身所既定的叙事策略徒劳无功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虽然网络电视收视在时间维度上不存在于“流”之中,但在空间上却很容易形成Brooker所说的“溢出”(overflow)现象。⑧根据Brooker的理论,由于网络电视的视频窗口在空间上与其他网页的窗口十分接近,所以很容易促使观众从主视频窗口跳到其他相关的网页窗口,比如讨论组或者社区等。这其实也有效地推动了电视观众对于所谓“后观看”(post-viewing)的参与。Brooker论述中没有提及的是很多互动聊天功能在网上直播节目中的设置,例如,一些电视节目所进行的在线调查,搜集节目反馈或向观众征集节目互动话题等等,区别于在网络上观看新闻或是连续剧等节目,这不但大大地加强了“溢出”而且还有效地发挥了网络技术的互动功能,由此可见对技术的思考也要根据节目类型而变化。
最后,对于网络电视收视的思考不能忽略一个传播环境的问题。传统的电视节目以图像和声音信息为主要载体。然而,当电视上网以后,在一个网络页面中,视频窗口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周围充斥着各种文字、图片和动画等信息。当然受众可以把视频窗口全屏化处理。但是,也有很多受众不会这么做。因为,复合信息形态正是网络传播的一大优势和特色,文字和图像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但如果处理不当,围绕在视频窗口周围的文字图片等信息就会成为传播学中所说的“冗余信息”和“噪音”。因此,已经有学者通过对网络弹出视频广告的研究得出结论,因为网络传播环境要比电视有更多的干扰信息,所以上下都带有黑色遮幅的16︰9格式要比4︰3格式更适合网络电视。⑨两条看似简单的黑色拉边能很好地把视频窗口与其他信息间隔开,从而可以迅速和集中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如上所述,不管是优势还是限制,互联网平台在传播技术上确实显现出诸多独特之处。因此,把电视节目不加任何改动地照搬到互联网上播放,无论是同步还是滞后播出都明显不符合网络传播的特点,也肯定无法满足观众对网络观看的需求。简单地利用网络观看在播放和收看上的功能优势,比如暂停、重播、存储和定制等等,并没有使得网络电视比DVD观看更高一筹。相反,很多时候网络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在办公室用网络看体育节目直播就好比在旅途中用手机看电影一样,甚至还要付出容忍低劣影音质量的代价。因此,我们并不能奢求在电视机和网络同时可供选择的前提下观众会完全对电视弃之不理,但至少可以做到让观众在打开电视偶尔瞄上一眼的同时又能守在电脑屏幕前观看网络直播或者浏览其他相关内容。这在观众收视习惯层面是有可操作基础的。2000年10月8日,美国的Starz Channel在播放电影《第六感》(The Six Sense)的同时又在网络上同步推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内容,包括电影制作的花絮和过程集锦并开放了网络聊天室,同时提供了大量关于幽灵的背景资料。而制定这一方案的观众基础正是基于美国所拥有的近四千四百万的“telewebbers”。(“telewebber”是指在观看电视的同时通过计算机上网的人群,上网的内容可以与电视内容无关,称之为“视网迷”。参见http://computer.yourdictionary.com/telewebber)⑩如今,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年轻一代的快速成长,国内也出现了大量的视网迷。近几年“台网联动”“多屏互动”等概念的热推不仅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合作的有益尝试,也肯定了视网迷潮流的发展。例如,每逢春节联欢晚会或者选秀比赛等大型活动,边看电视节目边用互联网参与该节目的微博话题讨论已经成为年轻人新的收看习惯。就连一向高高在上的《新闻联播》如今也走上了台网互动的发展道路,尽管只是在30分钟节目的最后加上了一句“如果您还想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央视新闻”,却已强烈地表明新旧媒体之间的互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媒体的文化空间以及受众的物理和精神世界。视网迷作为一群可贵的先锋,他们对于交互式应用具有很强的接受能力,能够帮助新旧媒体寻找到电视与电脑协同工作的可能性和突破口,从而挖掘出更大的商业前景,得到广告商和内容提供商更多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交互式传播策略虽然近年来在国内外已经十分流行,但更多的是从内容层面着手,通过发挥网络多语言符号传播以及大数据库存储方面的优势形成对主体节目的有效补充。若从技术层面来看,电视节目如何适应互联网视听语言和收视体验等问题却仍待探讨和解决。虽然网络电视有自身的技术特点,但很多时候依旧作为电视收看的可替代性选择,所以,有人认为收看网络电视仍然是处于一种“广播”的情境当中。
二 情境的取向
如本文开头所言,观众对网络电视的使用最终要落到网络或者说是新媒体的本质属性层面来考虑,对新媒体的理解不能只从技术层面着手,还要看新媒体技术引起的使用情境的变化。Livingstone认为,“所谓新媒体,最主要还是新在媒体消费的社会情境方面,而不仅仅是技术”(11)。而对于情境的考量,过去对传统媒体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毕竟新与旧只是相对概念,“新媒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持续发生的旧有的技术和新的理念之间的杂交化过程”(12)。
在电视时代,我们已经知道电视使用的社会文化情境对观众的文本解读以及收视行为都有很大的影响,代表性的研究有欧洲观众研究的民族志转向和Roger Silverstone的“驯化”研究。(13)这些研究主张研究者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入到家庭这一电视消费的主要场所中去探究家庭生活实践如何塑形观众的媒介使用行为。在对观众需求的认知上,这一范式弥补了麦奎尔所指出的以使用满足理论为代表的美国经验研究因为功能主义而造成的在解释观众需求和实际使用模式上的无力。同时,对“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和实践(practice)的强调也因为其后结构主义和二元性的理论色彩而克服了完全用个人主义来解释观众需求所产生的一些弊病。由此可见,电视观众对网络电视的需求不仅仅取决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一些技术和审美层面的改变,还需要考虑“情境”对这种改变所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从本质上来说是施加于观众对计算机或者是互联网的使用,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对网络电视的消费产生作用。这也为我们思考网络电视的观众需求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更加细致的思考方向。
人的交流体验总是处于一定的情境之中,一件事情或者一个文本也总是在某种情境中发生和产生影响。因此,无论我们是使用电视或者互联网收看视频,情境都像一个无形的框架一样规定了我们“观看”这个屏幕的方式。Schilit等人将情境划分为三类:计算情境、用户情境和物理情境。(14)而McCreadie and Rice则进一步对context和situation作了区别。(15)(根据字典字面翻译,context指脉络或背景,但此释义多用于文本分析;situation是情境,多针对具体的动作和事件。McCreadie and Rice则认为二者本质区别不大,context更宏观更为宽泛一些,而situation则更具体。本文则统一使用“情境”。)笔者认为目前我们对网络电视消费的“情境”研究可以从互联网整体消费上借鉴思路。那么,从“驯化”研究出发,再结合网络电视自身的特点,本文将“情境”主要定义为物理的情境和人的情境两个层面。首先,物理情境是指网络电视收看发生的时空条件和一切技术基础等等。电视“驯化”研究已经指出电视在家庭里不同的空间配置,例如空间的开放性和闭合性、空间的使用权等问题会对观众的收视行为产生影响。而在计算机以及互联网进入家庭后,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新媒体时代的家庭媒介环境要比过去复杂很多。媒介融合理论强调相同内容在不同媒介平台之间的流动性,而多媒体的家庭环境正为这种流动性提供了时空上的便利性。虽然,电视、电影和计算机屏幕仍然在家庭空间里各自相互独立,但这种流动的过程也使得观众在这些屏幕上所看到的画面越来越丧失了他们本来应有的媒介特征(medium-based specificity)。(16)同时,媒介种类和数量上的多元化使得媒介消费与家庭时间空间分配以及使用权等因素的协商上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局面。如上文所述,可以想见当计算机和电视机在家庭里处于同一空间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电视和网络电视的同步使用。根据美国一项对互动电视消费模式的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家庭在客厅以及餐厅这一公共区域内会同时摆放至少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和电视机,而电视和电脑之间的平均距离是1.5米到2.4米,并且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同时开机状态。(17)相比之下,我国大部分家庭的电脑被放置在书房这样较为私人的空间环境中。因此,个人化的网络使用也决定了它在塑造观众集体身份上的无力,导致某些电视节目并不适合在互联网平台上播放,比如那些具有仪式化色彩的各种选秀节目。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在使用上的弥散化,“驯化”研究已经开始尝试突破家庭范围的限制而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来研究网络电视在公司、学校乃至其他公共场所中的使用。实际上,由于电视机在上述空间中的普遍缺席,以“替代者”身份出现的网络电视可能会更有用武之地。
对空间的考虑当然也不能忽略时间的维度。空间和电脑的功能在一天不同的时段里都会发生变化。例如,电脑和互联网相对于电视在功能上的最大变化就在于前者可以被用来工作。所以当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一个家庭办公室的时候,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白天电脑会用来工作,而到了晚上则成为了孩子们和家人娱乐的工具。所以,Ellen Seiter认为,对于媒介研究者来说,我们对网络电视观众身份的认识不仅仅要从消费者或者是家庭成员的角度出发,还需要把他们看成是工人或者是生产者。(18)随着时间而不断产生的身份变化也必然会影响到观众对网络电视的接收。实际上,电视节目的编排经过长期的摸索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时段计划,可以用来适应不同收视人群在一天不同时间内对节目的需求。身份变化在网络电视中的体现不再是时段计划而是节目分类,在这方面网络电视做得还不够细致,尤其是那些以播放电视节目为主的视频分享网站。
关于人的情境,主要是指观众的媒介素养水平和发生在家庭成员身份之间的互动协商关系给网络电视消费带来的影响。媒介素养研究是观众研究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的一次重要转折和复兴。这一框架在思考消费者和媒介关系时主要从观众的技能和知识水平入手,研究他们如何接触、分析、评价乃至生产新媒体文本。(19)虽然这一范式仍属于批判研究范畴,但是新的变量的引入也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新媒体的消费机制。例如,Vengerfeldt等人在爱沙尼亚做的一项调查表明,互联网用户(尤其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水平和互联网的使用积极程度密切相关。(20)在另一项研究中,Ribak通过对三个家庭计算机使用情况的细致观察发现计算机专业知识和使用能力与家庭两代人之间的权力身份的建立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双向关系。既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父亲——专家和儿子——普通用户的正常对应关系,也有父亲——普通用户和儿子——专家的错位关系。更为重要的后一种对应还存在一种反向作用力,也就是父辈力图通过提高计算机能力重新获得男性应有的权力和地位象征。(21)这实际上也提出了因为媒介素养造成的家庭代际差别以及由之而来的对家庭成员身份建立和媒介使用的影响问题。比如,Mesch的研究发现父辈往往会通过限制孩子对互联网的使用来体现父权,而且这种情况大都发生在孩子被赋予了计算机专家这一角色的时候。(22)这也进一步引发了我们对于网络电视使用人群年龄分层的思考。Ribak的研究本质上是遵循Giddens“结构化”理论框架从而探讨年龄与相关消费实践的动态关系。(23)这一理论框架也可以指导我们去探寻其他和网络电视消费相关的“人”的因素,例如性别、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社会资本等等。一言以蔽之,由于新媒体所呈现出的“个体消费特征”,过去电视节目对受众传统的地域划分和笼统的年龄段划分已经不适应新媒体的市场规则。营销学之父Philip Kotler经典的STP市场定位理论,包括市场细分(Segmentation)、目标市场(Targeting)和市场定位(Positioning)三部分,其实也可以作为对网络视频“人”的情境思考的基本理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维度的研究多是基于宏观层面的整个互联网消费,还缺乏与网络电视消费相关联的具体研究。
三 结论
本文从技术和情境的取向来讨论,切合了Manovich所提出的“文化界面”(cultural interface)的概念。Manovich的“文化界面”(cultural interface)概念认为,进入新媒体时代以后,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应当被内容与界面的对立所取代。(24)界面不是电视荧屏和计算机显示器在技术特点和可能性上的外在差异,而应是定位于在社会文化与媒介内容之间能够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和相互生成的“技术传递代理人”(technical transmission agent)。新媒体的文化界面在本质上体现了后工业时代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而对网络电视的思考需要我们在更深的层面,也就是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整个社会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一角度来认识它与观众需求之间的关系。正如Manovich所说,“正是文化界面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性和用户消费经验,文化界面即使是微小的变化也需要我们对工作进行全面的整体的重新思考”(25)。
电视向网络进军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新媒体内容层面相对于技术层面发展上的落后决定了本文所探讨的这一类网络电视仍将继续长期存在。从长远来看,对于网络电视的思考,首先仍要从互联网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观点出发,但同时又要兼顾其作为一种人际传播媒介的创新性。其次,我们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互联网上的电视已经不再是电视。最终的方向应该是互联网从本质上影响到电视节目的制作方式理念以及电视产业结构的变革。在这一点上,我仍然同意所谓“内容为王”的观点,优质内容仍是核心价值所在。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的一样,在数字时代,媒介本身已经不是讯息了,而是讯息的具体化和体现。(26)
①Fagerjord,A.and Storsual.T.(2007) 'Questioning convergence' in T.Storsual and D.Stuedahl(eds.)Embivalance towards convergence:digitalization and media change,Gotebog:Nordicom,P19-31.
②张立伟:《媒介融合:哪些无能为力?》,《新闻记者》2010年第8期。
③Emigh,J.(2008) 'Surveys:many people are now watching TV online',Beta News.Retrieved from http://www.betanews.com/article/Surveys-Many-people-are-now-watching-TV-online/1217453732.
④Zackon,R.(2009) 'Ground-breaking study of video viewing finds younger boomers consume more video media than any other group',Council for Research Excellence.Retrieved from http://www.researchexcellence.com/news/032609_vcm.php.
⑤Pavlik,J.(2000) 'TV on the Internet:dawn of a new era?',Television Quarterly,30(3),31.
⑥参见[英]威廉姆斯著(1974)、冯建三译《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原著:Williams,R.(1974),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London:Fontana.)
⑦刘燕南:《关于观众流动分析的一些探讨》,《收视中国》2001年第5期。
⑧Brooker,W.(2001) 'Living on Dawson's Creek:teen viewers,cultural convergence and television overflo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14(4),P 456-472.——(2003).Overflow and Audience in D.Jermyn(eds.)The audience studies reader,Routledge:London.
⑨Cossar,H.(2005) 'Taking a wider view:the widescreen aesthetic in online advertising',The Journal of New Media and Culture,3(1).
⑩Neel,K.C.(2000)Starz! Targets web viewers,CableWorld,12(41),P28.
(11)Livingstone,S.(1999)New media,new audiences?,New Media and Society,1(1),P62.
(12)Livingstone,(2002) 'Introduction' in L.A.Lievrouw and S.Livingstone(eds.)Handbook of new media: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London:Sage.P8.
(13)参见Moores,S.(1996)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articulating technology,Luton: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Lull,J.(1990).Inside family viewing: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television's audiences,London:Routledge.Silverstone,R.and Hirsch,E.(1992)(eds.)Consuming Technologies: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Silverstone,R.(1994)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New York:Routledge.
(14)参见Schilit,A.,Adams,N.and Want,R.(1994) 'Context aware computing applications',in A.Schilit,N.Adams and R.Want(eds)Proceedings of IEEE Workshop on Mobile Computing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Santa Cruz,CA: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P85-90.
(15)参见McCreadie,M.and Rice,R.(1999) 'Trends in analyz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35(1),P45-76.
(16)参见Friedberg,Anne.(2000) 'The end of cinema:multimedia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C.Gledhill and L.Williams(eds.)Reinventing film stud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参见Carey,J.(1996)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interactive television,Edinburgh,Scotland: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nivEd.
(18)参见Seiter,E.(1999)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audiences,New York:Clarendon Press
(19)Livingstone,(2008).Engaging with media-a matter of literacy?' 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1(1),P51-62.
(20)Kalmus,V.,Pruulmann-Vengerfeldt,P.,Runnel,P.and Siibak,A.(2009) 'Online content creation practices of Estonian school childre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3(4),P331-348.
(21)Ribak,R.(2001) 'Like immigrants:negotiating power in the face of the home computer',New Media and Society,3(2),P220-238.
(22)Mesch,Gustavo S.(2006)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over the Interne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9(4),P 473-495.
(23)参见Giddens,A.(1984)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Cambridge:Polity.
(24)(25)参见Manovich,L.(2001)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Cambridge:MIT Press.,P58.
(26)参见[美]尼葛洛庞帝著(1995)、胡泳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原著:Negroponte,N.(1995)Being digital,London:Hodder & Stoughton.)
标签:网络电视论文; 网络新闻论文; 互联网电视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新媒体广告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收视论文; 媒介融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