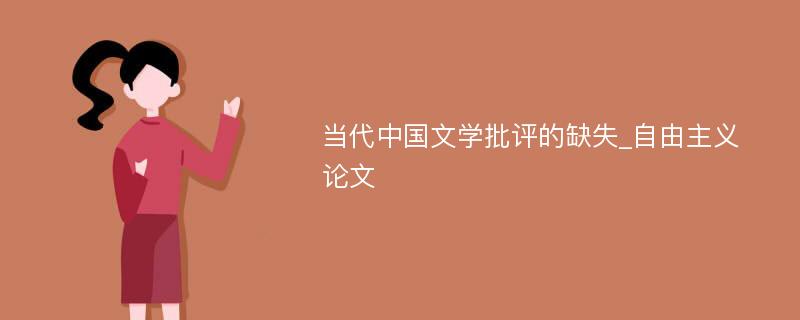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缺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缺什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1)01-0073-07
文艺批评是当代中国文化最活跃和富有影响力的部分。虽然它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但其功能却不仅仅限于反思、调校、总结文艺创作,而同时担当着思想启蒙、消解传统意识形态、建构新的人文精神乃至谋划中国文化之未来等重要使命。正因为文艺批评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对文艺批评本身进行批评就更加重要。冷静地审视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现实水准与它所担当的多种功能之间的关系,笔者发现它时常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这既表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使命是超重的,也意味着它必定存在某种欠缺。本文从3个视角探寻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欠缺,并以此表达对它最深沉的期待。
一、对后现代性的片面解读与批评视野的狭隘
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是20世纪人类生存方式发生的根本革命。迎接、理解、筹划、培育正在诞生中的后现代性是当代人的当代性使命。中国文艺批评界先于哲学界、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将后现代性纳入自己的视野,对之进行了富有激情的讨论,这对于培育中国的后现代文化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然而正是在迎接和理解后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文艺批评界表现出了因无法充分同化对方而产生的迷惘、犹豫、多变:后现代性忽而被当作后现代文化的特性,忽而被当作后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忽而被当作现代性在当代的变形。一种未被充分同化的主义从根本上说还是他人的主义,对他人的主义的茫然迎接表征着迎接者丧失了自己的立场。为什么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界在解读后现代性时会如此游移不定?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艺批评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现代性内化而成的视野观审后现代性的,必然无力把握后现代性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后现代性的言说就会直接转化为中国文艺批评家对后现代性的言说,甚至使之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性)当作后现代的总体特征(后现代性)。这在逻辑上就存在明显的错误。
后现代性究竟在哪些方面越出了绝大多数中国文艺批评家的视野?这就是它对作为现代性核心的人本主义的超越。如果说现代性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那么,后现代性就是对于这种主体主义的超越。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难以理解的:我们尚在现代化的途中,还沉浸在发现人的狂喜中(“文学是人学”仍是中国文艺批评十分流行的命题),依然把人本主义当作解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体系,因而内蕴于后现代性中的超越人本主义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必然是陌生乃至荒诞的。但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往往更能说明后现代的本质,因为后现代对于现代主义者乃是一种超越性力量。超越人本主义的核心是消解主体中心主义。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德和福柯)主要是从人与人关系的向度上消解主体中心主义的。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主体不仅是对于他人而言的,更是对物、自然、世界而言的,所以,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向度上的主体中心主义已成为更具当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超越目标。这样,后现代运动对主体中心主义的消解就展现为两个维度:(1)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消解作为绝对中心、权威、整体性象征的主体和与之相应的同一性、整体主义、领袖/群众的二分法,代之以多元共生的、个体化的、平等的生存逻辑(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叙事,就是因为启蒙叙事设定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不平等关系,而对平面化、碎片化、主体零散化的迷恋则是消解主体中心主义的激进方式);(2)在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层面上,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被征服的二分法、无限制的消费主义,主张人应该由征服者升华为存在的守护者,用“人和其他物种的亲情关系”代替“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把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怀与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1]所以,最为后现代的后现代精神追求的是人文关怀与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的统一。然而,由于中国文艺批评界仍囿于以人为绝对中心的人文视野,这种更全面地揭示了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尚未被绝大多数中国文艺批评家所注意,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在谈及后现代性时仍在重复平面模式、碎片化、主体零散化等语词,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结合起来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情怀。
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意识的缺乏表征着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视野的狭隘:仍停留在只见人而不见物、自然、宇宙的人类中心主义层面上。这使得中国文艺批评家一方面对已经具有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意识的文本视而不见,一方面对文艺创作中缺乏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的现象未给予必要的批评。华人作家高行健在80年代创作的戏剧《野人》中就表现出了对世界多层面的关怀:在剧中受到关注的不仅仅是人,更包括被人的征服欲所伤害的野人、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与作为生命之母的自然界,所以,这部作品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人文关怀视野,追求人文关怀与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的统一。这正是高行健超越绝大多数中国作家之处:他是汉语作家中极少数同时具有人文关怀意识和生态关怀意识的人,《野人》是中国最早的生态戏剧。也许高行健对汉语的细致把握能力并不是汉语作家中最高明者,但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鲜明的生命关怀意识、生态关怀意识、宇宙关怀意识在汉语作家中是杰出乃至独一无二的。令人遗憾的是,高行健的独特之处正是中国文艺批评家们所忽略的:评论者在论述《野人》时将注意力聚焦在其多声部的复调结构,集唱、念、作、打于一体的总体戏剧样式,舞台时空的自由变换,而忽略其中的生态意识。这种视野的狭隘也体现在对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的评价上:批评家批评和赞美的都是他们在电影中蕴涵的文化意识,而未认识到展示特定地域文化中的人在“地球村”时代已经不是艺术的最高使命——我们是地球人、世界人、生态人,而不仅仅是“文化人”。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局限不仅在于他们对东方文化的片面展示,更在于他们只有文化视野而缺乏生态视野,未能将人放到更广阔的生态视野中去呈现。这使得他们的电影理念实际上已经落后于世界电影的先锋形态——“地球村”时代的世界电影关注的中心已提升为人类整体和人类所生存于其中的生态整体(如被中国文艺界所屡屡嘲笑的好莱坞电影就以灾难片、恐怖片、科幻片的形式表达了对于人类命运、生态系统命运、宇宙命运的关注与警觉)。但对于张艺谋和陈凯歌等顶尖中国电影人的这种欠缺,文艺批评界几乎从未提及。这说明批评视野的狭隘决定了批评主体无法发现批评对象的视野的狭隘,自然也无法提升后者。由此而产生文艺批评的失职与渎职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中国文艺批评界最为偏爱的命题是:文学是人学;但人既是具有私人性的个体,又居住在逐级递升的家园系统中:他既是“文化人”,又是世界人、生态人、宇宙人,所以仅仅将人放在文化的语境中去评价和研究,则必然将人狭隘化了。如此被限定的人既不完整,也不当代。即使承认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仍然建立在人学的基地上,我们也有权要求扩大人学的视野:由文化到世界,由世界到生态系统,由生态体系到宇宙整体。只有经过这样的视野扩展,中国文艺批评才能在足够高的高度上进行工作。令人高兴的是,这种自我提升在新旧世纪之交已经悄然开始,少数批评家正在进行扩展视野的后现代转折,如鲁枢元等人着手筹划建构生态文艺学,力图建立以生态系统为整体话语空间的文艺体系。[2]这是中国文艺批评自我提升的重要标志。
二、对经验论的自由主义的偏爱与批评理性的残缺
自由主义舶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内在构成,乃是20世纪中国最富有解放性的文化运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渐成潮流。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肯定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事物,可以为了相互得益而彼此订立契约”,认为“除了个人的自由外,再没有什么别的自由”。[3]它对于以圣化绝对主体和集体主体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无疑是彻底的解构性因素,因而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而言是绝对的建构性力量。通过引入和弘扬自由主义来消解被过度圣化了的绝对主体和集体主体,确立个体的主体地位和个体自由的至高无上性,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策略,也是其最内在的生命需求。中国的文艺批评自70年代末便开始或自发或自觉地培育创作和批评中的自由主义,从对朦胧诗的辩护到对晚生代作家个体化写作方式的礼赞,个体的自由和解放都是中国文艺批评最为关注和珍爱的存在。
然而自由主义是内涵复杂的精神体系,它必须探讨自由与限制、自由与契约、自由与权利的复杂关系,有关自由主义的书往往是枯燥而繁琐的,单是对以自由为目标的游戏规则的思辨就足以令缺乏思辨传统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感到头疼。面对自由主义的多义性,中国文艺批评界实际上采取了避难就易的策略:相对回避以理性主义(立足于“我思”)为依托的自由主义,而更多地吸纳了英美式的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回顾一下70年代末以来的文艺批评,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文艺批评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意味:将自由与最基本的生存经验联系起来,凡是能给人的生活经验之流带来解放、快乐、陶醉之感的,就是善的,反之则恶。对于经验论的自由主义的采纳在我们尚无力建构出新的理性精神体系之前是十分有效的策略:经验总是我的,它是我的亲在本身,用我的当下经验去证实/证伪某个抽象的命题、原则、“真理”或“正义”乃是对我的个体性的最直接肯定;信任我的经验就是信任我的个体性和我的自由,所谓的自由若不能给我带来经验上的自由之感,便是虚幻的;自由最终将落实为我的感觉,以我的当下经验为绝对尺度正是自由主义对于我而言的真谛。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实在的解放功能——它将人从历史目的论的牺牲品还原为体验着本我历程的生活之流,实际上是将一切落实为个体本位,在消解传统意识形态的同时为个体创造、体验、享受自由提供了简单而实用的策略。这种对感性经验的推崇贯穿于大批文艺批评家对新状态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市民文学乃至对晚生代作家的“私人化”写作的评价中。这种选择实际上被传统和当下语境等多重因素支撑着:(1)中国的自由主义自胡适开始走的便是经验论的道路,认定经验就是生活,此思路经顾准和王小波等推崇经验主义的自由思想家的弘扬,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2)它既暗合了“世界图景时代”(海德格尔语)的逻辑,又与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经验主义倾向不相抵触,因而容易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存在下来。正因为如此,经验论的自由主义才成为中国文艺批评果乃至中国知识界未曾言明的主流话语。
虽然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中国文艺批评本体的残缺却在对它的推崇中凸显出来。经验论至少具有如下局限:(1)拒绝言说经验之外的事物,反对形而上学和乌托邦,缺乏远见和激情,容易走向文化保守主义;(2)经验论将经验当作最终极的实在,认为所有的命题、理论、信仰只有与经验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忽略了个体经验与人类经验的有限性,因而其原则的彻底实现会使文化最终陷入贫乏状态。这种局限现在已转化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局限: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在追随经验论的自由主义之时大多遗忘了或未意识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起源和向度——奠基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以笛卡尔式的我思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体以理性为自己立法的自由主义,忘记了自己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仅仅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对建构完整的以自由主义为目标的批评理性缺乏热情。与此相应,主流文艺批评放弃了对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有引导意义的价值体系,超越理想、信仰的建构,拒斥“崇高”、“英雄主义”、“使命”、“终极价值”、“远大目标”等具有超越意义的范畴,转向认同当下文艺创作中的深度模式削平、反宏伟叙事、碎片化、袒露欲望等经验主义走向,其结果就是当代文艺批评理性的日益残缺。本文所说的批评理性的残缺最集中地体现为以经验主义的“当下经验之流”拒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我思”。实际上,“我思”与“我的当下经验之流”合一,才构成完整的个体,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综合起来,方可建构出健全的批评理性——既不背弃当下的经验之流,又坚守我思的立法权的批评理性。“我思”的最重要功能是在将个体置于中心地位的同时使个体成为立法者,这从笛卡尔推论“我思,故我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切都是可怀疑的,惟有我在怀疑不可怀疑,而怀疑是思,所以,只有“我思”是不可怀疑的;既然“我思”是不可怀疑的,那么,原则、体系、理论的出发点只能是“我思”,“我思”是观照着世界的立法者。强调个体为自己和世界立法对于中国文艺批评乃至中国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具有立法能力的人才是真正的个体。维护个体的立法权是理性论的自由主义的核心。立法权中的“法”只能是理性之思的产物,故个体要成为立法者,就不能拒斥经验之外的存在,而要在吸纳各种主义、学说、信仰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主义、学说、信仰。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如果不具有自我立法的能力,那么,他至多只能是个分类者和描述者,而非真正的批评家——以自己的理性尺度评价文学艺术的个体。在各自具有立法能力的个体之间,才存在真正的对话和因对话而生成的保障集体自由的契约。自由的极境不是“众声喧哗”,而是“诸神共唱”——众多具有自我立法能力的个体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共生、共事、共乐。当下中国文艺批评的半失语状态乃是文艺批评家缺乏自我立法能力的结果和表征。克服这个欠缺的方法之一就是建构理性论的自由主义。如果说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因其通俗易懂和简单易行而引导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走上自由主义之路,那么,理性论的自由主义的建构则将使之成为更高层次的自由主义者。将经验论的自由主义与理性论的自由主义整合为一体,中国文艺批评就会克服批评理性的残缺状态,自我提升到更宽广的境域。
三、对体系性建构的逃避与批评本体的孱弱
文艺批评的最高境界显现在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和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诗学问题》等原创性著作中。通过创造新的批评体系,将批评对象纳入自己独特的批评视野,乃是伟大批评家的共同特征。在这种批评中,世界因他们独特的符号系统转化为他们的视界,他们在此视界中对批评对象进行观照——阐释——评估。最高境界的批评都具有创世纪的性质。
然而,20世纪中国文艺批评从未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思想家和批评家的名字,却不敢说20世纪中国文化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系。即使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这三位最有自立意识和建构精神的文化大师,也存在原创性不足的欠缺。原创性的缺乏使得20世纪中国文艺批评始终无法超越或回归传统或借鉴西方的贫困状态。由于传统话语体系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中已不能满足中国文艺批评家的精神需求和工具性需求,因此,倾听和转述已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西方话语就远远遮盖了回归传统的呼吁而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界的主流价值取向。这种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淹没了中国内地批评界,使得内地的汉语批评成为西方批评的汉语化,所谓的后殖民语境自此全面形成。与此相应,汉语批评本体则日益孱弱: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还有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有自立精神的文化大师敢于创立自己的体系和主义(他们虽然不是文艺批评家,但其思想乃是当时汉语批评的重要精神资源),那么,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文化人至多只能提出个别有创新性质的命题(如“美是自由的象征”和“性格组合论”等),大部分前卫批评家只能以率先引进某种西方话语为荣。而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艺批评最为活跃的20年间,汉语批评本体的建构又呈现出前强后弱的态势:80年代有刘再复等人提出“性格组合论”并一度表现出宏大的建构雄心,90年代后就少有人再提建构二字了,建构汉语批评本体的雄心让位于对后殖民语境的暗暗喝彩和无奈议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批评已经呈现出实实在在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状态。汉语在某些批评家那里沦落为翻译西方理论的工具。毫不夸张地说,汉语批评本体已孱弱到了我们有可能丧失汉语批评本体的地步。
如果说前新时期中国文艺批评缺乏原创性的体系建构更多地归因于文化生态的恶劣,那么,在文化生态已大有改善的80-90年代及现在,汉语批评本体的孱弱则只能说明批评主体的失职,即对重建汉语批评缺乏信心和使命感,因而有意或无意地逃避以汉语为本体的体系性建构。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剖推动并支撑此行为的心理动因:(1)对于改革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改革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完整的历史发生论—历史动力论—历史目的论为内核,在形成一个大全式的解释体系的同时将个体置于被先验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目的所规定的被动境域,此解释体系在文化走向个体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全球性的拒斥,中国知识分子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伤痛记忆而积极地参与了拒斥行动,但这种拒斥却泛化为对任何体系性建构的拒斥并使中国知识分子盲目追随解构主义;(2)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其反体系、解构、碎片化等主张对上述拒斥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支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理直气壮地拒斥任何体系性建构的借口,仿佛惟有如此,才是跟得上时代节拍的后现代人。然而这二者都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1)构成改革前主流意识形态核心的历史发生论—历史动力论—历史目的论体系实际上也是从西方借来的(前苏联文化也属于欧洲文化范畴),解构之的最好方案是以新的开放的体系来替代它,而不是以无体系论对抗所有体系,否则,解构者在成功地进行了解构之时将丧失任何形态的精神家园;(2)后现代主义的反体系/解构意向的产生是由于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后积累了太多的体系(其中有不少是黑格尔式的封闭体系),文化本体过于沉重,需要解构恢复其活力,而中国文化自“五四”以来几乎没有诞生原创性的体系,文化本体极度孱弱,如果再进行任性的解构,只能使之由孱弱走向孱弱,其结果不难想象。所以,中国当代文化急需的是建构而非解构。既然中国文化当下最需要的是体系性的建构,为什么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以各种理由拒斥体系性建构呢?根本的原因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进行体系性建构的能力和毅力,当仅有的建构尝试给自己以失败之感时,便开始以各种借口逃避体系性建构。从中固然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但更有超越意识形态和人格层面的深层原因支配着他们作如此选择。其中,两个因素是内在而关键的:(1)汉语文化自先秦时期建立自己的特质起就缺乏亚里士多德《诗学》式的纯逻辑建构,在秦至明清的两千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逻辑建构能力并没有质的提高,真正将纯逻辑性的理论建构提上议事日程的是“五四”时期,而“五四”至今尚不到100年时间,且其间又充满动乱和不利于纯逻辑建构的意识形态因素,真正能让中国知识分子从容地进行体系性建构的时间实际上少得可怜,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逻辑建构能力自然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提高,纯逻辑建构能力不足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欠缺。在实际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善于从一个或几个原初概念推论出整个体系,而主要采用带有原始思维特性的分类法进行建构——将分类以后的诸因素综合在一起。有的文艺批评著作篇幅很长,但不是个推理体系,而是将已有的东西陈列起来(如钱钟书的《谈艺录》)。这种陈列式的建构无法造就原创性的体系,只能成形为知识的陈列馆。(2)我们进行体系性建构是在汉语空间中进行的,而现代汉语的深层逻辑和意义迄今尚未充分地显现出来,这是造成汉语知识分子体系性建构能力不足的本体性根源。现代汉语的生成本身就是汉语文化与西语文化对话的产物(如现代汉语对系动词的使用),因而现代汉语既保存了传统汉语的特性,又在结构和意义上发生了根本的革命,由此形成了现代汉语全新的意义空间。如果说传统汉语不适合纯逻辑建构,那么,已完成了结构革命的现代汉语则不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现代汉语不适合原创性的体系建构,而是现代汉语知识分子未能将现代汉语的可能性空间充分地呈现出来:现代汉语在代替了传统汉语以后还缺乏深层的语言学游戏,乃是导致现代汉语在体系性建构方面生产力低下的具体原因。缺乏对现代汉语深层意义的领受,没有深层的语言游戏(如老子在说“道可道,非常道”时所做的那样),汉语的内在力量就无法进一步显现和生长。我们如果仅仅用一种语言的表层含义和表层逻辑进行理论建构,还能指望建构出新的原创性的体系吗?所以,现代汉语知识分子应对汉语怀有罪责意识,而不应以任何借口逃避以汉语为本体的体系性建构。
建立以汉语为本体的文艺批评体系是完全可能的:现代汉语已经通过同化西方语言的转换生成结构而获得新的逻辑建构的可能性空间,是开放的系统,因此,只要汉语知识分子通过持续的深层语言游戏不断发现汉语的原初意义,让汉语的字与字、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按照其微妙而本真的本体论关系结成新的因缘整体,那么,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汉语批评体系就一定能够生成,汉语批评本体将从孱弱走向强大。[4]这就要求中国文艺批评家不仅要成为发现者—阐释者—评估者,更要成为发明家——通过发明出新的体系让汉语发光,照亮文化尚未被阐释的界域,并因此而获得自己独特的发现。能完成此功业者,将成为汉语文化的功臣乃至圣人,其意义莫大焉。
本文所揭示的当代文艺批评的3重欠缺归根结底源于现代汉语文化原创性的不足,因而这些欠缺只有在汉语批评建构出原创性的体系时才能被超越。这种建构的成功与否决定着现代汉语与从属于它的现代汉语批评的命运,因此,建构主义是当代中国文艺批评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唯一希望。现代汉语知识分子曾因未能以现代汉语为本体进行体系性建构而对汉语犯有渎职罪,现在则要通过虔诚的建构为自己赎罪,现代汉语批评的希望将在这个过程中生成并壮大。
收稿日期:2000-12-04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艺论文; 文化论文; 现代汉语论文; 读书论文; 野人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经验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