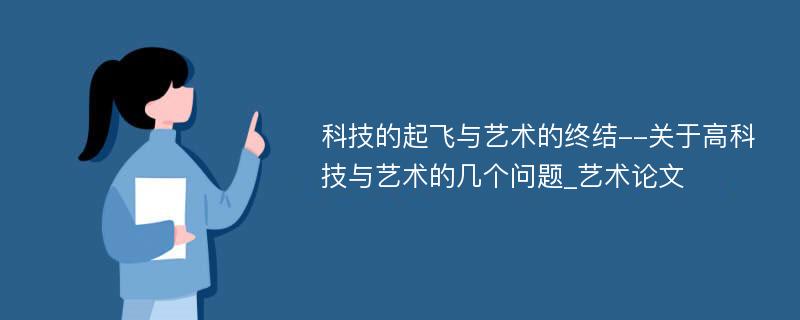
科技腾飞与艺术终结——关于高新科技与艺术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几个问题论文,高新科技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黑格尔的“艺术终结”预言在反黑格尔的语境(反线性历史总体意识)下得到应验式反响;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诗敌对”命题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全球胜利中再现。“终结者”话语,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文学时代不复存在”。美国当代美学家阿瑟·丹托认为,艺术会有未来,只是“我们的艺术没有未来”。在弗·杰姆逊,这是“诱导我们思考真正人类的最终形态和现有哲学已经达到的最终形态的瞬间”。
一、艺术进步的概念
艺术终结,杰姆逊指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由黑格尔的大小三段论演绎出来的(注:弗·杰姆逊:《“艺术终结”与“历史终结”》,引自《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4-75页。),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进步”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说“高新科技”时就意识到正面临着的“第一生产力”之腾飞。科学技术在根本上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力量。然而,“进步”这个概念没有比经过几千年发展之人类高科技文明的今天更陷入困境。进步史观既属历史哲学范畴又表现为一种科学哲学,如波普尔的线性渐进式科学进步观受到库恩之跳跃式“革命”的挑战。这不仅仅是科学史而是包括艺术史的整个文明史的问题,一方面是“后学”对“发展论(进步论)”的颠覆,对应于科学界的反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是庸俗进化论。
关于艺术“进步”,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如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把艺术的发展作为人类对自然征服的历史。启蒙主义者把科学精神代表之进步化为历史理性。这种思想便成为艺术进步概念的基石。在当代美学中,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完形”作用肯定了主体审美心理与客体有一种“同形同构”之进步上的一致性。冈布里奇所说不同风格艺术流派以各自的方式向预定图式之世界真实的接近被作为进化的艺术史观,如此等等。种种进步史观无论其缓进渐变还是激进革命的方式,因属线性发展的史观一概被后现代主义作为唯心主义“目的论”彻底颠覆了,甚至连资本主义作为封建主义之进步也遭到否认,遑论艺术史的进步。
然而,在与反发展论相反的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至少在中国还有相当市场,美学庸俗进化论是其在美学上的代表。一种集以上各种“进步”说之中国特色的著名美学理论,叫“积淀”,20世纪80年代至今流行和应用还非常广泛。按照这种理论,“审美作为……心理结构是感性与理性的交融统一,是人类内在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它是人的主体性的最终成果,是人性最鲜明突出的表现。”(注: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积淀说涉及的问题,如理性怎样积淀为感性等等,这里且不论,就其以人的(审美)心理结构所描绘的一种发展观完全是庸俗进化论的,如其所云:“只要相信人类是发展的,物质文明是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最终(而不是直接)决定于经济生活的前进,那么这其中总有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类的心理结构是否正是一种历史积淀的产物呢?……心理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的积淀作用最直接地通过艺术等审美形态表现出来,即所谓“美的历程”(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11-213页。)。这样,审美心理结构、艺术的发展与社会及相应生产力之间便有着一种完全整合式的同步关系,而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的不平衡”。
马克思在谈到不平衡原理时有一句不被人们注意的告诫:“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抽象的意义上去理解。”美学庸俗进化论之“庸俗”在于把“进步”这一历史现象平面化,也就是在审美与艺术的发展上简单化、线性化了,即所谓“心理结构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历史的进步在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是同步前进的。如马克思所说,艺术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人类社会发展主要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志与衡量标准的。生产力的发展呈线性上升,即科技含量由低向高,从而生产从低效率向高效率,从低产值到高产值,所显示的是一条上升曲线。生产力可以通过种种精密准确的数据计算出其高低来,如同样产品的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之差额。科学可以凭借难题的解决、理论的创新、资料的占有与积累来测度其进步。艺术生产发展并不是与生产力一致的上升曲线,而是更为复杂。如马克思所指出,在艺术史上,一种艺术生产的形态出现并消失之后便不可能在后来的发展阶段重复。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因此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的某些形态如神话与史诗,却好比人类历史的儿童时代的反映,因为这一时代之“永不复返”而具有“永久的魅力”,其价值并不因社会发展的成熟而降低。人类在生产上的低水准与在神话和史诗创造的高度魅力,即两种生产在历史发展进步的一致性中的不平衡,是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最大难点。
童年时代的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肯定比中青年时代低,资本主义肯定比封建主义进步,晚期资本主义在科技生产力、民主化管理等许多方面比早期有所进步,但艺术就不是这样,在拉斐尔与毕加索之间能比出谁高谁低来吗?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诗人“积淀”着比屈原、李白、杜甫更优越的“审美心理结构”呢?从个体发生来看,我们可以举出大量例子证明,一个诗人青年时代的作品并不一定低于其中晚年。毕加索一生经历了“古典时期”、“立体主义”、“蓝色时期”和“玫瑰时期”,在这些风格变化中能比较出高低来吗?为什么科技走向“高新”发展的今天却处处响起“艺术死亡”的声音呢?
绘画史上一向把与文艺复兴时代几何学的发展有关的“透视法”之发明作为重要进步,然而20世纪初的立体主义与未来主义率先打破了这一法则,它们最初借“工业”表达的观念却是“世界革命”。以画家视觉远近为准,建立在“模仿—逼真”基础上的透视画法在东方传统中没有地位,如中国、日本艺术,所以丹托说,“把空间再现仅仅当作习惯问题,进步的概念就消失了”。虽然他受“后学”影响有反达尔文主义倾向,并过于强调艺术史的非连续性。但他也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那样一概反对“进步”概念。他以下的提法是有道理的,即区分艺术的发展(进步)与风格的改变,从而在高新技术下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技术”带来“什么样艺术手段”的改变,这种改变并不能简单说是“进步”。他注重艺术“再现”与“表现”的区分,把艺术史线性的进步观改写为:当艺术“再现”的对象成了对与之有关事物“表现”的理由,我们就沿着这些新的途径“重建艺术史”(注: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第83-85、187、93、105页。)。这就是说,在以“再现”为方法和风格的艺术种类或流派的作品与“表现”特点的艺术之间,不是进步而是变化的问题。“比过去模仿得更逼真了”,我们可以说“再现”或“表现”的技巧、手段和效果进步了,而不能言“表现”比“再现”进步,或相反。同样,对于“超文本写作”与传统写作、“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也同样不存在谁比谁进步的问题,其相互异同需要比较与研究。
以科技这把尺来测度,当20世纪初其他艺术已经越过其光辉时期,电影却刚刚从婴幼开始其历史。三四十年代,甚至60年代人们决没有可能看到坦泰尼克号下沉时遇难者在斜插海面的甲板上纷纷坠落的画面。电影从卢米埃兄弟的《工厂的大门》到当前的《角斗士》表现为无可争辩的进步的话,那么嫦娥奔月的故事无可避免因阿波罗登月而黯然失色。高新科技完全可以塑造一个当代维纳斯具有生命活体的触感——肌肉皮肤的弹性、血液的温度等等,那么冰凉的大理石的米洛纳的维纳斯是否因此失去魅力?艺术“进步”的概念只有在同一种类、样式、风格与同等技巧、甚至传播媒介之下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同意丹托所说“艺术史对抗着进步的范式,即它一个接着一个地散落在一连串的个别活动中,所以艺术史决无某种可推测的未来”,但不同意把这种观点推广为一种泛化的后现代历史观。
丹托更不无深刻地认为,艺术不可能是人类进化的首要手段,只是在某一时期如此,但这种进步作用与“积淀”说恰恰相反,如丹托指出,它“丝毫没有发生在遗传学层面上,而只是发生在思想层面上”(注: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第83-85、187、93、105页。)。在历史的一定阶段,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同步而进,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艺术与科技生产力同表现为进步(人性解放)手段,但这不是什么“积淀”,而是思想上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
“终结(end-)”一字在德文与“解脱”、“引出”(ent-)相关(80年代我国哲学界曾有关于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终结”是否应译为“出口”之争)。黑格尔《美学》中的“艺术终结”一方面是“出口”,如古典—象征型艺术的终结引向浪漫型的起端;另一方面,又与黑格尔的体系之“回到起始”相关,如在其《美学》第二卷第二部第三章“古典型艺术的解体”之第二节“神由拟人而解体”中谈到,因为抽象的“神”化为“人”便意味着从僵死的偶像返回“意识”(惟人才有意识)。艺术最终消失于哲学(杰姆逊则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论艺术代替了哲学)。这样,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我们得到了乐观与悲观的统一的“终结”观念。从原始时期带有永恒魅力无名者的神秘涂鸦起始,在伴随着人类受难,因挣脱枷锁的呼唤而伟大的历程,艺术是少数殉道者精神火花所奉献出的精萃。它将以这种形态的终结而终结,其伟大高贵形态将变成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东西。我们所熟悉的艺术形态将封存于博物馆中,其委琐鄙俗之形态只能弃之于垃圾堆。正如人类历史在终将到来的最后一次宏大话语之后,艺术将变成我们从来不认识的叙事形态,并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返回”原始(如没有专门的艺术家,即人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
二、超真实、符号生产与虚拟性
20世纪以来,以现代科技媒介与制作(生产)方式带动艺术直接出现的新品种为电影—电视—电脑(包括网络文化)之三级跳。一种以电脑视窗体制支持的超负荷信息载体文本出现了。“超文本(hypertext)美学”把代码式信息尽可能地转化为“可视”信息,以多媒体的链接之网状、弹性、开放结构代替单一文本的线性、刚性;封闭结构(注:黄鸣奋:《电脑艺术》,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97页。)。电影的特技制作为想象开放了更广阔的空间。以影像感光—复制技术起步的摄影是以对真实世界的真实记录为特点和目的。这种音像视听的虚拟到电脑的动画制作、画面的任意切割、粘贴与捕捉移动达到登峰造极。高新技术给艺术带来的这一切无非是人的想象借助不同媒体制造虚拟真实能力的扩大与变换。尽管四五十年代的许多黑白片的精品并没有失去魅力,而大多数人仍然宁愿选择有声片与更高清晰度的影片。高新科技为借助高新科技诞生的艺术无疑增加了表现力和观赏性。然而,高新科技手段的利用过度却又使艺术冒在科学主义遮蔽下丧失自身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卧虎藏龙》的主人公在竹梢上打斗并不比李小龙的真功夫“进步”。另一方面,高新科技对艺术作为消费品生产、保存、传播的便捷性,使艺术愈益趋向大众化与消费化,艺术在“生产”与“消费”的意义上改变了过去的“经典性”、“传世性”和“永久性(魅力)”而成为“泡沫”、“快餐”和“一次性”文化消费品,最后是文化垃圾;感官刺激、娱乐的商业性代替了“诗意的思”、“沉醉”和“迷狂”。
以工具理性批判为特征之批判的非理性在后工业文明时代进入了“后学”阶段,取得了新的形态,这些新形态恰恰是与后现代高新科技产业相对应的。在高新科技与艺术的较切近的关系上,艺术真实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这种艺术真实问题与高新科技的联接表现为新手段、新形态、新媒体之“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即通过以电脑为主的种种高科技手段制造出一种对各种感官刺激和综合的“浸淫环境(immersive)”之“赛博空间(cyberspace)”(注:翟振明:《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的本体论对等性》,《哲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4页。)系统。哲学上有人提出,虚拟真实与自然真实本体论上是“对等(原则同格)”的(注:参见(1)翟振明:《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的本体论对等性》;(2)张怡:《虚拟实在论》,《哲学研究》2001年第6期。);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虚拟真实与自然真实是不同的,虚拟真实只是事实或实际,而不是真实。艺术事件与真实事件之间的直接性关系,它们在理论上被鲍德里亚称为“超真实”。鲍德里亚从加拿大传媒研究家迈克鲁恩那里引来“内爆(implosion)”一说,认为在后工业高科技文明中,由于科技虚拟仿真的功能,艺术品成为无穷增殖的“类像(simulacra)”的复制式生产,使得符号、虚拟仿真图像与真实世界之间发生“内爆”而界限消失了,我们正面临一个模型与符码所决定与支配的“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注: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2-154页。)。英国社会学家斯各特·拉什在对以“符号生产”代替“物质生产”的所谓“符号经济学”中,研究了语言(文字语言)向形象(图像)的转化之后现代文化特点,即以“图像”与其指涉的无差别〔“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表达了“内爆”与“超真实”同样的意思(注:周宪:《符号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视觉转向》,《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第19-22页。)。图像本来因其直观性具有反符号之特点,但它为传媒作为一种文化商品之消费符号便带有与文字语言符号(作为“存在的家园”)之敌对形态。在鲍德里亚的批判中,“超真实”不仅模糊了真实,代替了真实,甚至比真实更真实。实际上不同于自然与社会客体的真实,艺术真实也正如艺术虚拟,两者都是因流派而不同的历史范畴。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在历史的斜坡上充满张力地互动着。
其实,超真实是后现代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变体。真与假,有与无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的,它们统一于惟一的客观的真实。任何时代不同种类的艺术都要借助于虚拟,只不过手段、方式和程度有异。如鲍德里亚所举的例子:影视人物身份(医生、侦探)被当成演员的真实身份(注: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2-154页。),虚拟真实的逼真性,乱真性在前电视、电脑时代也有类似的问题。在中国40年代的解放区上演歌剧《白毛女》时观看的战士就当作真实情境,当场掏出枪来要打恶霸黄世仁。在西方《奥赛罗》中雅各扮演者也有过同样遭遇。“超真实”与真实的界限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如鲍德里亚所说那样被夷平了,这样说只不过把高新科技媒体制造的虚拟真实的“新”的逼真性夸大以生产出理论上的陌生感。高新科技并没有改变真实与虚拟的本质,只是改变了艺术虚拟的手段与形态。“超真实”对“现实真”的代替用一句老俗话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傻”就“傻”在把虚拟的真实当作现实的真,把银幕上倒现拍摄现场从高墙下跳当作真正的“飞檐走壁”来看,又把双子大厦被撞当作卡梅龙大片之“超真实”。所以“超真实”就是让虚拟(虚假或欺骗)尽最大可能,不惜一切,包括高科技手段,被看成现实的真。当银屏上的暴力与恐怖化为现实的真之时,虚拟的超真实便哑然了。"9·11"事件后,由于影视节目有关内容被查禁、删除,以此为长的美国影业面临着危机。虚拟真实与客体真实没有“对等性”,一句话:电脑不可能代替人脑,无论“人工智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其之所以是“人工的”表明人的作用仍然是主体。人类终结的方式不可能是被它创造的东西消灭,人的世界不可能被虚拟世界最终摧毁,尽管不可无视科学技术及其滥用。对高新科技理论上批判的非理性的基础为一种“技术决定论”,尽管这种批判是有深度的。正如贝斯特、凯尔纳指出的那样,它以科学技术生产力范畴掩盖了人们的社会关系范畴(注: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52-154页。)。而社会关系的批判却在前卫艺术中以身体的直接性同样非理性地展开。
三、存在的时间性与商品拜物教
在高新科技时代,虚拟的“超真实”之另一极端是“艺术的直接性”。艺术的“直接性”即是对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弥,也就是取消了艺术虚拟(假定)性真实与生活原型真实的界限。这种“直接性”艺术形态与借助高新科技媒体制作之虚拟真实在相反的极端上“内爆”以达到另一种“超真实”。它们往往也以精英性文化与大众文化中的科技新潮流相对峙。这种直接性以世纪之交达到高潮之“行为艺术”为代表。行为艺术虽然产生于高新技术时代,但与高新科技没有太多直接关系,而作为一种“末世的反叛”与60年代“左派”运动却有着内在的关联。政治过激的行动向艺术转移,使之取得“性”、暴力(伤残)、调侃(恶作剧)之内涵,并从人体模型、动物的肢解到伤残自己的身体等等。“无意义、无形式”即是一种与解构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艺术上彻底的“虚无化”。在行为艺术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性”、“身体”与商品的一体化。以身体传达的“性”主题的行为艺术正是对以女性为代表的人自身商品化的末日之反叛(注:美国《时代周刊》(中文)1998年4月24日报道,伦敦将举行史无前例的惊人画展:来自洛杉矶的美国女画家马歇尔到伦敦办展览,每次只让一个顾客进入画廊,然后她即席挥毫作画。如果双方成交,那顾客便可以与她进行一项性行为。一幅小画卖25英镑(约40美元),顾客可获得口交;一幅中等画值50镑,可与性交;一幅大画75英镑,购买者可与她干“任何变态性行为”。这个画展在伦敦东南部的德西玛画廊“性事与淫媒”馆举行。该馆馆长查普尔表示“最重要的,是顾客与马歇尔的性行为,令艺术变得完美,只有画像的主人这样干了之后,那才算艺术”。他说,已咨询过律师,律师向他保证这次展览是合法的。他说:“这是艺术,所以合法。”据悉,见报上周末十多场为期1小时的展览,已全被预订。这位女画家以自贱方式表达了女性主义对女性商品化的抗议。)。
今道友信把艺术与技术作为两种相反的时间性过程。人通过技术所追求所要达到的是提高效率,即缩短时间的过程。而艺术则相反,是人追求永恒,审美的艺术通过尼采所说的“梦”与“醉”,使作为生命的时间无限绵延的过程。今道友信这种不无正确性与深刻性的论说使我们想到关于艺术是“白日梦”的比喻,确实两者都有着不同于真实世界的时间性。时间作为客观物质运动的形式,它在主观上取得相应的感觉形式,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这种感觉形式效应往往决定于主客体相处的某种特定状态,审美的时间也相似于这种效应。进入柏拉图所说的审美的“迷狂”状态中,时间在主观上仿佛停滞了,生命似乎在瞬间进入类似无限与自由状态。
时间既是生命运动的形式,也是思维运动的形式,人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运动究竟是节约了生命还是浪费了生命呢?如果是节约了生命,为什么机械与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不仅没有消除剥削,而且使人的片面化更甚,使人们普遍感到生活的节奏更快,时间更少,精神更紧张,压力更大了呢?高效率节约下来的时间跑到哪里去了呢?
在商品拜物教统治时代,时间本身商品化了,生命与时间都可以买卖。一方面,时间本身因为普遍商品化的规律——“时间就是金钱”,“以更少的时间生产更多的商品”——时间成为商品增值的意义而失去自身与生命联接的意义;另一方面,与之相应的是商品化的消费文化使消费符号化,商品成为消费符号,艺术也成为一种消费符号,在超饱和的图像-符号化消费世界与美学世界中,意义被淹没,人们被迫接受着超饱和的符号-图像。垃圾般的“审美文化”信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主体失去了审美所必须的时间,也就失去了审美思考,失去意义与存在的价值。文化消费以“一次性”节约(艺术欣赏)时间的形式,以“暴力”性强制,剥夺了审美时间,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变成无意义的符号流,瞬息万变,目不暇接。这种烦躁、焦灼和忧虑影响到艺术,产生了现代-后现代艺术通过“零散化”、“平面化”、“精神病写作”、“类像-复制”等达到犬儒式的“去圣-解魅”之反审美效果。
在万物商品化的时代只有一种宗教:拜物教;只有一具偶像:金钱。1994年行为艺术家朱东发有一幅作品:一男性青年穿着中山服手提旅行提包在街上行走,其照片左上端标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字样。整个社会的无所不可变钱,正是金钱以其不可抗拒的邪恶性腐蚀着整个社会之恶性循环。劳工出卖的苦力与朱东发的“此人出售,价格面议”之间艺术的直接性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界限全然消失了,“内爆”了。所以问题归根结底不是高新科技,而是把人当作物来生产的商品拜物教的生产方式与人和人的艺术相敌对。高科技与高效率缩短了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正面效应上,这节省下来的时间没有以审美艺术的形式转移到人的诗意存在的意义上去,提高生命本体的价值,却在一定地域和历史阶段造成产品与劳动力的过剩,而导致人与产品的素质和价值的双双降低(如当前的中国)。
在生活中,为了避免实际操作的危险性,虚拟真实已经用于驾驶与手术训练。有人预想2300年“人类的大多数活动都在虚拟实在中进行。在其基础部分进行摇距操作,维持生计;在其扩展部分进行艺术创造、人际交往,丰富人生意义,通过编程改变世界的面貌”(注:翟振明:《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的本体论对等性》,《哲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4页。)。虚拟的“赛博空间”主要是通过实验者感觉器官存在的,感觉是人对现象世界认知的最表层部分,感觉常常造成假象,即现象与本质的脱离;并且真实世界的多维性的许多方面是超感觉的。如果在家庭赛博空间虚拟五岳真境我们就可随时随地游遍天下了。但是免除了攀登劳累与惊险是否能得到“无限风光在险峰”之真趣呢?正如在“虚拟真实”中的劳工能免于如此苦力享受“小康”的话,中国还有五六千万贫困户,上千万失业者可否看成“对等性”的虚拟呢?这个问题是否在2300年前就能解决呢?
四、身体直接性与精神分裂症
无论在任何意义下,商品所代表的都是物的虚拟,即反映人们社会关系的神秘性,一种与“天物”相分裂的“神性”力量。人们在对虚拟之物当作神来崇拜中失去了自身尊严、品格和价值。在《资本论》意义上的“物神”便是“剩余价值”,即商品所揭示无偿占有的劳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发生了某些变化。一方面在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中,“剩余价值”被“科学技术独立地创造价值”消解;另一方面它又被“公有”的意义消解,掩盖在“国有资产流失”与“分配不公”之下。高新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以空前的高效率创造着人类社会财富,然而,剥削与压迫的社会贫富两极之基本社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1960-1990年期间世界贫富差别扩大了约1倍。当今世界20%最富的居民占有世界收入的82.7%,而20%最穷的居民只占有世界收入的1.4%。思想者与创作家的根本使命是彻底改变这种结构。当对科技的批判成为一种科技—艺术单一关系的批判,这种批判本身就成了问题。当然阐释的理论行为可能把艺术对科技的批判转化为对体制的批判,批判理性的最后任务是把对法兰克福以来到鲍德里亚的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转移到历史理性上来。
一位行为艺术家在餐桌用膳,旁边放着一具“死婴”标本的餐碟,象征“食人”的行为艺术,行为艺术家发表的“食人”宣言为:
“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那就是人为什么不可以食人?
“只要非犯罪手段,食人行为是完全不受人类社会中宗教、法律之约束的;现在是我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并拿我自己的食人行为来对抗关于不可食人的人类道德观念的时候了。”(注:杨盅:《以艺术的名义:中国前卫艺术的穷途末路》,《文艺报》,“艺术周刊”(4)。)
当然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已经把这种“吃人筵席”写得淋漓尽致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本来就是“大吃小”的法则,不合理分配与不公平竞争使得吃人更为残忍。所谓“不可食人的人类道德观念”只不过是对这些“吃人筵席”的遮掩。行为艺术对高新科技掩盖下的“非人化”现实关系的批判是激烈的,但这种批判的非理性对艺术之犬儒式的“去圣化”与“解魅化”使艺术成为反审美的,而改变了艺术的美学本性,艺术的死亡,使艺术成为“非人”与“反人”的艺术的原因归根到底是与使人成为非人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
雅斯贝尔斯说:“在这些众多愿作狂人,却过于健康的人中,只有凡高一人是崇高的出于无奈的狂人。”凡高死了,凡高那样“崇高的出于无奈的狂人”也不再出现;现在“愿作狂人,却过于健康的”也不“众多”。正如行为艺术家张洹所说:“你似乎生活在一个有‘病’的时代,每个人都有病,你会发现自己也是一个‘病人’。”福科把疯颠作为一种“文明产物”。精神分裂在德鲁兹和加塔尼《反俄狄普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一书中不是作为一种疾病或一种生理状态,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枷锁下物质生产和欲望解放的力量之潜在状态——一种既知道行程中止,又要为自己设定目标;在一种激起灵与肉的最终毁灭的无尽虚空中要把既有的欲望生产投向某种新的生产行为的人格状况。他们写道:“当我们说精神分裂是我们的个性的病症、时代的病症时,我们的意思不仅仅是说现代生活使人发疯。精神分裂不是一个生活方式问题,而是一个生产的过程。”(注:Delluze,Gilles & Guattari,Felix: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New York:Viking Penguin,1977,p.22-35.)如此来阐释行为艺术倒比有些批评家和刊物义正辞严地挞伐行为艺术家(注:见《美术》杂志2001年第4期。),却本末倒置地对非人化的社会现实不予触动,要来得深刻,也更有些说服力。新世纪初有报道称:广东省精神性病患者人数100万,发病率上升1.5%,高于1.2%全国平均值。据分析,这与“人欲”、“物欲”增长成正比。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1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精神障碍患者达4.5亿,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在其一生中某个时段发生某种精神障碍。在这个意义上,不仅精神分裂,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在内的整个地球的癌变都是这种生产的产品。如福科所说:“正是人类的精神错乱导致了世界末日。”(注:福科:《疯颠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第13页。)真实的狂人与艺术虚拟的狂人化为同一的超真实。现实人的商品化与艺术的“卖人”的直接性,现实社会的吃人与艺术“吃人”的直接性,现实生活中的病人与艺术家作为病人之间的界限被行为艺术抹去。在大众化虚拟真实中,暴力与性以数字化标准化生产成为血淋淋、赤裸裸的,而在行为艺术中这种血淋淋、赤裸裸化为身体的直接性纳入同一之“超真实”。对于行为艺术之非理性批判是应加以理性批判的,但是更需要批判的是生长这种艺术的现实关系。
人类创造之“超真实”使命不是以高科技下的虚拟的逼真性与身体的直接性,而是完全不同于现有生产关系维系着的新的真实,这一使命也不是由精神分裂者作为解放的潜在力量来完成,而是一代新人把既倒之解放旗帜重新高高举起。在远离后现代之后的“新人”绝非今天所谓什么“新新人类”可比拟的。艺术的固有形态正消失在“超真实”之虚拟与“直接性”中。我们已经不认识艺术了,它的可能性再生也不会是馆藏东西之再现,正如人类整个历史正面临着的千年剧变。
“科技腾飞与艺术终结”这个永不衰竭的命题正表达了新千年人类命运中大喜大悲之悖论。当黑格尔“美妙的歌已唱完”之语音刚落,伟大现实主义运动正起。但是黑格尔在浪漫型艺术终结中已经说出:“主体性活动消除”这样的后现代话题,这是因为人的主体性总是在天人的分合关系中起落,其中交集着悲喜情怀。丹托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没有专业艺术家(人们早晨可以干这个,午间干那个……)的畅想中引出“艺术终结即死亡”之否定性结论:“永远会有帮助演示艺术的服务,如果艺术家喜欢这种情形的话。自由终结于自身的实现。从属的艺术永远与我们同在。”(注: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第83-85、187、93、105页。)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在人的个别性与普遍人性的统一、个别人的意识与绝对理念的统一之中,见之于有限内容之绝对精神并不绝对可以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并且艺术也并不再表现被认为是绝对的东西,“而是一切可以使一般人感到亲切的东西”(注: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80-381页。)。所以,永远同在的艺术已经不是那个艺术,正如我们已经不是那个我们,尽管山水也许还是那个山水,宇宙肯定还是那个宇宙。
标签:艺术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终结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虚拟商品论文; 科技论文; 后现代理论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