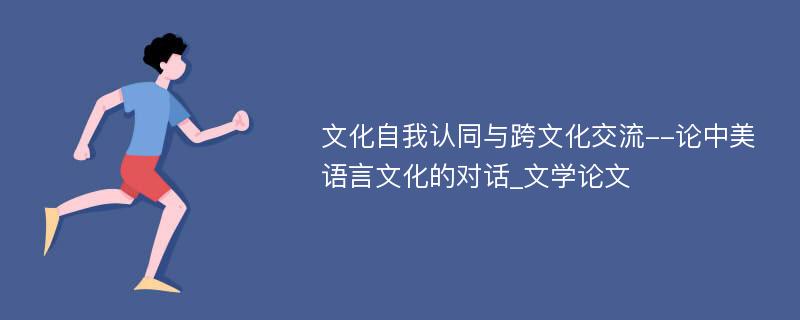
文化自识与跨文化交流——关于中美语言、文化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文化论文,跨文化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与经典
王晓路 司马教授好。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流。作为当代美国研究中国学的女专家之一,女专家真是不多呢(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余宝琳(Pauline Yu)应当是和您同期的学者吧。我曾拜读过她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解读》(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s Tradition)和其他一些有关比较文学的文章。你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视角都很有意思。我想了解一下您当初在求学时期,为什么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文学感兴趣呢?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后来在文学研究中又是如何转向积极推广汉语教育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我想这一点也是中国学界感兴趣的。
司马德琳 我们可以用中国人边喝茶、边谈话的方式来进行,你知道我的好茶叶很多,每年都从中国国内买新茶呢。我其实在攻读研究生之前就对语言、主要是外语感兴趣。当时在俄亥俄就学习了好多门欧洲语言,当时对中文只是感兴趣而已,开始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而是比较集中在法文和法国文学方面的学习。后来我申请到去巴黎学习的机会。我在巴黎得知有到台湾系统学习中文的机会,于是又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富布莱特项目到了台湾。顺便说一句,我曾经三次获得这个项目,其中一次是博士研究项目。我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集中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这的确为后来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然而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我才非常深入和系统地对中国语言文学进行了学习和研究。华大有一批十分优秀的中国语言文学的教授。我的导师是康达维(D.R.Knechtges)先生,你大概知道这位学者,他花了多年的心血翻译和研究《文选》,出版了《〈文选〉美文精选》(Wen xuan,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此书共八卷。这是目前英语世界中对《文选》最为权威的研究成果,非常受学术界的推崇。我当时比较偏爱中古时期的散文,所以我当时在他的悉心指导下,也选择了中国中古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以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修辞风格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即《唐代古文文体研究:以韩愈和柳宗元的修辞为例》。这种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对我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传承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其实,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一直很浓厚。当然在美国出于职业的考虑,有时候你不能只凭自己的兴趣做事,或只做一个领域或一个专业。特别是现在,中文语言教学的需求也增长得很快,大学里大多设有相关的课程。所以我在语言和文学两个方面都得做事。事情是做不完的,慢慢做吧。
王晓路 我听说过康达维先生,他对《文选》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对中国骈文和赋也很有研究,其文章或专著,如《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骈”》(“Bing”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文宴:早期中国文学中的美食》(A Literary Feast:Food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汉代的铺采之文:扬雄之赋研究》(The Han Rhapsody,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以及《扬雄、赋与汉代修辞》(Yang Shyong,the Fuh,and Hann Rhetoric)等都很见功力。我觉得,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学典籍中有两部书在英语世界中得到了很好地研究,一部就是康先生的《文选》,还有一部就是马瑞志(R.B.Mather)先生对《世说新语》的研究,即他的《〈世说新语〉——对世界的新述说》(Shi-Shuo Hsin-yu,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1976)。他还对当时的文学权威人物沈约进行了传记研究,即《沈约传》(The Poet Shen Yueh,1988)和一些论文,如《六朝时期关于一致性和自然性的论争》(The Controversy Over Conformity and Naturalnes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1969-70)等等,这些文章都很有意思。四川大学中文系的张永言老先生多年前曾对马瑞志先生所翻译的《世说新语》进行了商榷,并提出了一些英文处理方式的建议,构成学界的一段佳话。张先生虽然是研究汉语语言学的,但对文献、文学和文化有非常深入的体察,加上他的外文极好,不仅是英文,对俄文和德文都很有修养。我当年想了解陆机《文赋》的英文翻译,曾登门求教。先生不辞辛劳帮我找出自己留存的英文文献,真是让后学十分感动。现在这样的学者的确不多了。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中国三四十年代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学者。
司马德琳 这的确很有意思。中国有一批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们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尤其是“文革”期间都能将荣辱放在一边,排除干扰,坚持自己的人格信念并坚持问学。我听说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当年在下放劳动时都在想她的《唐吉诃德》的翻译。这种精神真是中国文人传统中一个非常宝贵的遗产。
王晓路 当时您的博士论文主要涉及到中国古文的修辞,那么您主要的方法是什么呢?
司马德琳 我首先花了不少功夫读文本。你知道,在美国读博士一般要读四个相关领域的文献,每一个领域需要至少六个月整。我当时是攻读《诗经》、楚辞、唐代散文和传奇,还加了现代汉语语法。但是我一共用了两年就完成了这几个相关领域的文献研读。那个时期是非常艰苦的,觉睡得很少,因为我还在华人的餐馆里打工,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学到地道的中文口语和一些方言,另外也可以补贴生活。我的博士论文涉及中国古文的修辞,但由于是用英文书写,所以我除了仔细研究有关的文本外,也将英文语言修辞中的一些分析方式运用到写作当中。分章节将修辞方式,如直接论争或说服、间接论争或说服、虚构中的修辞以及景物意象等等。正如你所看到的,里面有许多地方是对词、句、篇章等详尽的统计和中英的对比,用这样的方式将自己的观点在分析中逐步展开。
王晓路 我所认识的欧美学者都非常强调文献和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这的确是首要的工作,第一手文献是没办法绕过去的。如果只是看二手材料,或将别人引用过的直接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形成伪注,科研的水平也是永远无法提高的。目前,这在中国国内的学术界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因为国内对人文社科的量化式评估愈演愈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一些人急功近利。例如一些所谓做比较文学的学者或研究生就极少看外文材料,而主要根据翻译再做一些所谓的比较。每次我到美国来,美国学者都会问我,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界一说比较文学就是钱钟书和王元化,当代人在做什么?怎么一直没有什么新成果呢?我说“成果”多极了,这个专业的博士生每年毕业的都很多,只是没有出现真正超越性的成果。可能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沉下心来潜心问学,另外也有语言和文献的问题。我注意到您的代表作《唐代书写中的动物寓言》,除了选题很有意思之外,文献工作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从《战国策》、《博物志》、《列仙传》等等一直到后人对唐代文献的研究全部都进行了极其认真的爬梳整理,其中还包括了有关钱钟书父亲的相关成果。这种处理文献的方式现在还是美国汉学界一以贯之的传统吧?
司马德琳 这个问题是一个既老又新的问题。在古文和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其实在人文社科几乎所有的领域,离开了文献就没有办法说话。当然,如何看待和处理文献是另一回事。但文献是研读、分析、分类等工作的基础,因而总是第一位的。这个传统在美国很深。如加州圣巴巴拉分校的伊甘教授(Ronald Egan)对中国宋代文学的研究就是十分深入的。你可能会发现美国的学者和欧洲的学者有一些区别。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比较小,学校也少,一些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联系很紧密,当然这一点和欧洲知识界的沙龙传统也有关系。所以欧洲的一些学者有什么观点容易形成公共文化事件或媒体报道的文化新闻。而美国大学很多,地域太大,学者也多,所以不可能像欧洲学者那样频繁地面对面地交流,除了学术研究和跨校讲座外,大多是各自做学问。知识分子,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关系也和欧洲大学不太一样。但是,美国和欧洲的共同之处是,普遍采用跨学科的方式,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很紧密,观点需要大量可靠的事实或第一手材料的支撑与严谨的分析。那种论题宏大、内容空疏、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方式并不被学界所看好。因此研究生的训练首先就要提高研读文献的能力。当然也有不少美国学者是研究现当代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美国中国学有注重实用的传统,这和美国进入汉学领域较欧洲晚、并与20世纪自身的发展有关系。研究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在材料上好像要容易一些,其实不然,因为你使用材料的背后是研究者的思想、洞察力和研究能力的体现,你用一种什么样的观点看待事实是研究成果必不可少的。
王晓路 是的,您提到的伊甘教授的研究的确是非常严谨的,目前最为权威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北宋文学”("Northerm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ed.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条目就是他撰写的。四川大学最近召开了一个国际宋代文学研讨会,听说有两百多学者参会,可能伊甘教授会去吧。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文学专家真是人才济济。我所知道的,除了康达维教授外,还有王靖献(Ching-hsien Wang)等著名教授,王先生的《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The Bell and the Drum:Shi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m,1974)也有了中译本。其实,中西文学中均有大量的动物、山水、景物等等描写与寓言式叙述,背后总是有一些当时文学环境的要素。您选择唐代文学书写中的动物形象或意象,是否出于什么考虑呢?
司马德琳 同一种现象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肯定有一些类似的呈现方式。中国古人喜欢借一事而意指另一事。这包括一些作家借动物来述说自己的境遇或对世事的感慨,也有作家用动物的本性来谈人的本性等等。其中每一种动物,如鹿和马、老鼠等,在文学寓意性的书写中并不尽一致,这些都与一个时期的文化观念很有关系。但其中也有一些人在采纳一些动物时并没有明显的寓意,或言外之意。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后来者如何看待前人的书写方式以及如何将自己的理解放在注释之中,形成的这种阐释循环。因为这涉及到文学文化的规定性或惯例性书写。中国文学中有一个现象,就是把许多作家和作品放在固定的范畴中进行重复定位和解说。如一想到杜甫,肯定是他的诗歌创作,而不去仔细挖掘他的其他文类的创作。说韩愈,肯定就大说其古文,而不说他的骈文写作。刘禹锡也是多说他的诗歌,而不怎么谈他的散文。许多文学史和选集也大多将作家按照这样既定的方式分类。我觉得这种方式在《古文观止》后比较明显。编选者不断地重复收入一些作品,不断地阐释和再阐释,如《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选集所形成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这种按照既定的分类方式本身是值得探讨的,很有文化语法的含义。
王晓路 我同意您的观察,也注意到您的一些观点。刘禹锡由于和白居易和柳宗元的交往,被称为“刘白”和“刘柳”,有“诗豪”美誉。虽然《四库全书总目》对刘禹锡的散文有定评,如“古文则恣肆博辩”等,但人们的确主要还是谈他的诗作,并大量引用。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经典化的方式。我当年学英文,大看诺顿文选(Norton Anthology)系列,如《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诺顿英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以及《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等等。因为好的选集中大多有每一时期的总体介绍,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和作家等等,加之选入有定评的作品篇章,并且有比较好的注释,这样就比看单篇作品集中,也容易获得总体印象。当然诺顿系列现在还有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先生编辑、翻译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from Beginning to 1911)。但选集一般容量有限,大多将有定论的作家和作品选入。由于许多选集都用作教材,所以影响比较大,也容易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再加上选集若没有一定的理论支撑或编选者的理论分析和说明,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阅读定势。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时期的一些作家在反复被收入、反复得到解说的同时,同一时期的另一些作家或作品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忽略,或被“无意”遗忘了。
司马德琳 经典形成(canon formation)或被经典化(canonization)的过程往往是文化史中的重要问题。这个过程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如我们说到的编选文集、各级教育的教材、教学过程、测试引导、文学史以及当代媒体对传统文化的解说方式和呈现方式等等。所以我比较注意中国文学中,特别是中古时期那些不被主流看重的层面。
王晓路 我很同意。我自己在教学中,尤其是本科教学中一般不太使用统编教材,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教材是多人合写,观点不尽一致,大同小异,缺乏新意的比较多。如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大多是将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与王朝史并置,好像文学没有自身的演变逻辑一样。所以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串讲中提出一些必读的书目,尤其是作品,让学生自己通过读书、讨论甚至辩论的方式,去得出一些结论。文学总是要有文学感觉的,若都从观念出发,就有哲学课的意味。我自己因为也在外文系带研究生,所以也同时看英美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书。我曾看过两本有关美国文学有意思的书:《我们的非主流文学:犹太和南方作品选中的文化调解》(Jules Chametzky.Our Decentralized Literature:Cultural Mediations in Selected Jewish and Southern Writers.1986),《我们是如何被他人解读的:美国文学的国际视野》(Huck Gutman,ed.As Others Read Us: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Literature,1991)。两本书的特点都是关注非主流,并注意他者的文化语境。我注意到今年出的一本新书也很有意思,《美国新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它以第一手材料的方式,将许多原来主流文学界嗤之以鼻的材料,如书信等,纳入形成美国文学的范围。我正在写一篇与此书有关的书评。其实你们做的工作就是中国文学如何在他者文化中被解读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只有操母语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其实,古代的作品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一种“隔”。阅读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成果往往可以看到许多新意,如材料、方法和视角等等,将两种语境下研究的成果进行相互参照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司马德琳 是的,中国学者中也有许多人在研究我们美国和欧洲的文学和文化,但是可能他们大多在用中文做研究,他们的成果还不被欧美学界所客观地了解。另外中国的学术论述方式也和我们的不太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不懂中文,所以也基本上不看中国学者用中文写的论述。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王晓路 我常常在想,美国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人比中国研究美国文学和文化的人少得多。但美国学者的研究往往很有新意,也很深入,经常转而对中国学界形成影响。相反,中国学界研究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学者尽管人多,开会经常是上百人。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真正有洞见的成果很少,许多成果是一种依据英文材料的汉语转述或跟进式(echoing)的研究。一些学术会议也往往是按照所谓学者身份等级制安排大会专题发言,而不根据会议主题和论文质量。其中一些发言实在是没有认真准备。我现在极少参加这些会议,因为收获不多。这可能是科研体制的差异所致。因为美国参会论文是算科研成果的,而中国大陆是不算的。另外美国期刊评审制度和中国大陆的更是有很大的差别。美国是同行匿名评审,工作量在各单位计算,而中国大陆不是这样。
司马德琳 中国人口多,所以各个专业的人数也多。而且中国喜欢“国际”会议,有时候只要有外国人就是“国际”,这很有意思。不过每一个领域都有深入做研究的,可以召开一些小型会议,可能讨论就会深入一些。
语言文化教学
王晓路 是的。我在南京大学高级人文研究院参加过几次小型会议,就特别好。您在俄勒冈大学时就是中文领航项目的主任,我记得前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客座教授时您曾经来做过讲座,您当时还没有转到这里来。目前中国国内对美国中文领航项目还不十分了解,您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司马德琳 领航项目是美国国家面对全球化所开展的高级外国语言文化学习项目,主要在美国的大学里,当然主要是公立大学开展语言和相关文化的深入学习。现在美国大约有七所公立大学开展了中文领航项目,具体的展开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例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文领航项目主要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两年系统学习中文的课程和有关培训,学生不仅要学到较高水平的普通话,而且可以用该语言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其他的专业,拥有更强的职业能力,用英文说就是:create global professionals,培养全球性专业人才。
王晓路 在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确实是未来不可或缺的。从就业的指导思想来看,我感觉美国的大学在专业和能力的培养上是面对今后五年以上的发展着眼的。但目前中国国内一些专业的设置总是跟着社会上所谓“热”的东西跑,即有所谓的紧俏热门专业,什么“热”就急着办什么专业或方向,几年下来却发现重复设置很多,资源浪费也很严重,这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反而就业很难。
司马德琳 其实美国的大学也是相当实际的,而且受到经费很大的牵制,常常会因为经费问题砍掉一些单位,如研究机构或系所。如美国有关比较文学的设置就消失得很多。你上次来工作时还在的那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最近就被取消了。你知道美国的大学有很长的一个时期分科分得比较细,例如搞语言学的就根本不会做文学或文化,而文学和文化的老师也基本上不搞语言学。甚至做文学的也根本不和文化领域的搭界。语言和文学、文化分得太开了。其实两者是密切相关的,虽然这分别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目前我们主要的研究文本还是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的传播和接受等等本来就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形成文学文化。后来美国在许多专业的设置上都意识到跨学科的重要性,同样的对象,多了一些视角就可能见到有意思的东西,跨学科的趋势也是必然的。所以作语言教学项目并不影响我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而且在很多时候对我的研究还极有帮助。我经常在想,学习语言的美国学生,在语言能力有比较高的水平时,他们应当如何深入。我同意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的说法,这的确很重要。在美国的中文教学项目开始也比较小,后来在一些地区和学校开始逐渐扩大。我当时在科罗拉多时,中文项目就是比较小的,后来到俄勒冈大学经过自己的努力,做成了领航项目。现在又把领航项目做到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现在这个大学的中文项目,除了语言教学有领航项目外,在古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等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引进了一批美国一流的人才,例如你所熟悉的奚如谷(Stephen West)、高德耀(Joe Cutter)等教授等。这在美国西部的阵容应当是数一数二的了。
王晓路 奚先生在欧美学界当然是很知名的学者,我曾经和他详谈过好几次,后来访谈的主要内容发表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文艺研究》上了。高先生也是十分了得的中国文学专家,他对建安时期的文学有非常独到的研究。他在中国的中华书局还出过中文版的《斗鸡与中国文化》,其研究的视角和观点十分有意思。他有关建安时期的诗歌研究也应在中国介绍。我知道在美国,目前最大的外语教学是西班牙语,这当然与大量的墨西哥族裔有关,尤其是亚利桑那州。但我感觉在美国学习中文的人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点除了中国在新时期取得了一些经济方面的成就引起了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兴趣之外,与美国对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的现实逐步了解以及对中国的态度转变有关吗?
司马德琳 美国对中国的兴趣当然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关,市场的全球功能日益突出和成本核算的流向都会使其他发达国家注意到中国大陆的。而且经济和文化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产品在不同文化区域的有效接受和有效利用该地区的文化资本是分不开的。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公司、组织都肯定对中国感兴趣。美国人看的可能远,他们考虑需要对这个世纪有所准备。其他的原因也许还有一些,如有不少中国人移民到美国,他们的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在语言能力上应当保持。也有许多美国人领养了中国孩子,他们都十分愿意送孩子学习中文。另外一些美国人也认为自己的孩子有必要了解中国,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一下中文。所以,现在美国除了大学有中文学位项目,一些社区大学、中学甚至小学和幼稚园都有不少开设了中文课程。现在对中文的需求真是很大。
王晓路 我注意到前几周您主持的中文教学研讨时,有那么多中文教师来参加。大家认真听讲、做笔记、提问和讨论,真是印象深刻。中国国内若大学主办语言教学研讨,中小学不会有教师来参加的。可能体制不一样。就语言教学而言,中文与英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语言背后又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观念形态、群体行为与生活习俗。在美国教中文和在中国教英文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的文化误读和文化互识的问题需要处理。比如在中国,英文是最大的外语,而且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教学市场。许多中国学生,特别是城市里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学习英文,考大学或者大学毕业时,英文都是必需的课程。学习时间十分漫长,学习成本也很高。我觉得他们学习英文所花的功夫比学中文还要大。但我经常看到一些博士研究生写的论文英文摘要都很成问题时就会想,为什么他们花那么大的功夫结果会是这样呢?可能中国的英文教学大多针对考试,主要集中在语言的构成性成分的学习上,没有花同样的功夫去教会学习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许多学生都以为背了一定数量的词汇并了解了语法,就等于学会了英文。现在国内市场有许多急功近利的书籍或视听商品,好像可以在一个晚上就可以学会一门语言。其实语法的正确性并不等于文化的正确性。例如,虽然我们可以用一定的词汇放在语法的框架中,但在实际交流中可能并不符合表达习惯,因为不同语言间的交际必定是跨文化交际。您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您觉得在推广中文的过程中,其中比较难处理的文化问题是什么呢?这对于中国大陆的英文教学也许会有启发意义。
司马德琳 我也注意到来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的是学了多年的英文,一些人,特别是外文系出身的,他们一般性口语还是可以的,只是在学习方法上还很被动,还没有拥有一种学习能力,知识面比较欠缺,书读得不多,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也比较弱。知识都是一个时期对经验的总结,所以知识的结论总是暂时性的。学习的重要性在于拥有学习的能力,如拥有多的语言能力,看到知识可能的发展,由此才能对知识有所推进。但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方式,人才总是人才,他们总是会十分突出。所以一些中国学生可以直接进入这边的系所参加研究生的学习。当然教学问题也和每一个时期的主流教学指导思想以及教材的编写思路有关。例如许多中文教材都采取了课文、生词表、语法结构、文化背景介绍等等。但其中有不少缺乏每一个单元究竟要让学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要求。教师为中心的讲解并不能代替学习和领会的过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认为你讲完了,学生也就学会了。学生出现跨文化交际盲点是不奇怪的。所以我极力主张要提升美国的中文教学水平的方式之一,就是聘请一些学者直接用中文对高年级的美国学生进行古文、文学、宗教和文化的教学或研讨。直接教学法完全可以用在高年级和高水平的学生当中。
王晓路 这和中国大陆的英文教学情况有类似的地方。有一个时期是结构主义教学思想盛行,于是句型操练得到很大的普及,特别是美国教材《英语九百句》流行的时候。但我总体的感觉,在中学和大学的英文课堂上,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还是很普遍的,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教学班比美国大得多,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实践上有一定的难度。另外在学习语言构成所花的功夫比在语言运用上要大得多。加上考试对语言处理等因素的干扰,许多中国学生英文实际交际的水平还比较低。五分钟包打天下的情况很普遍,即谈话前五分钟还可以,接着就无法深入话题了。另外对英文背后的文化把握也比较欠缺。
司马德琳 我认为语言文化有两类需要处理,一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语言有一些大文化问题需要整体上了解,如区域历史、习俗、节庆等等,即所谓的文化背景简介。这也是很重要的概况性了解。也有一些中文教材还编写得不错,例如Integrated Chinese.Cheng & Tsui Company,Boston,里面每一章都用“Cultural Highlight(文化焦点)”的方式处理跨文化理解的问题。另外在了解宽泛文化的基础上,一个文化区域的群体大多有一个文化思维的定势,即他们的观念系统和由此对事物的所形成某种自然或必然的看法,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的教材里都没有反映出来。但我觉得,这一点是语言文化教学在当代需要认真思考的方面,尤其在高水平和高年级需要以多种形式进行探讨。这在世界联系如此紧密的情况下,对于避免负面的文化误读是十分重要的。
文化互识与跨文化沟通
王晓路 这一点很值得认真思考。文化的成长往往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在自身文化语境中的自我成长;其二是在外来的影响下产生文化互动,进而促进文化的成长和更新。这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有不少实例,如佛教、传教士以及近现代等外来因素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当代中国目前正是处于一个从受外来文化影响到主动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并试图影响他者文化的一个过程。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双重的,一个是自古到今的精神层面的传统,另一个是与外来文化对抗、冲突、汲取、融合的传统。而后者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新格局中更显得十分重要。所以中国需要处理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与自身传统的关系,二是与世界其他文化区域的关系。前者需要静心和仔细地清理自身文化的元命题,需要当代人认真看待、审视、反观自身的传统,使其在当前的转型中可以生产出对自身以及对世界其他文化区域有所帮助的东西。而后者需要虚心、平和并全面地了解他者文化的优势,从中体察并汲取文化推进的作用力。这两个关系互为系统,而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均与此有关。我一直以为,文化的传统有两个层面,其一是以文献为主的精神层面,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十分突出。其二是制度文化传统,即从民族建制到国家建制的过程中,需要汲取所有人类智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生产出合理和有效的公共方案。其实这也是中国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的一个方面。您作为美国人身处中国之外从事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这对于中国之外的世界,尤其是美国学生,更能有效地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而您在中文领航和孔子学院项目的实际推广中,以及自己的研究中也可能会看到更为有意思的东西。
司马德琳 中国人总能非常智慧地处理许多问题,这也是我心仪中国文化的原因之一。我自己的感觉是中国人在当代比较看重与美国的关系,不是原来冷战时期的敌我二元思维,而是有效理解和合作,这很重要。中国人对美国和美国人对中国,在今天的确越来越了解,但依然有,以后也肯定会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美国在20世纪虽然发展很快,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超级大国,但问题也是不断的。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轻松下来。但是欧洲和美国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就是不断地自识和反省。每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太一样,他们所实行的管理方式不可能一样。但是一些人不太明白,所以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这并不奇怪。在中国肯定也有人一想到美国就是帝国主义的感觉。文化间的互相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和一个具体的渠道,而目前中文项目就是非常有效的渠道之一。这也是我热心于此的原因吧。
王晓路 是的,其实越是文化大国,其包容性就应当越强,民族心理就越宽容。中国传统是一个不断汲取外来文化,与不同文化相遇、融合和互动的过程。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思维是有很大的危害性的。中国被说成“不差钱”之后,就有一些这一类的出版物出现,例如采用简单逻辑宣讲民族情绪的非学术书籍,这其实对年轻人是有负面影响的。中美文化教育合作的方式会有很多,如教学层面,通过派出和引进,中美就中国语言文学教学的合作已经大大扩展。对不同层次的教学问题也成为教学研究的一些正在探讨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成立相应的学会,定期以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研讨,以及共同编写一些教材并出版论文集。与此同时,在文化研究领域也有许多可以进行的事情。如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包括文学,和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其实都会有广阔的领域可以深入探讨。您对此有什么建议吗?在孔子学院这种形式之前,其实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都有中文项目。原先的中文项目和当代以孔子学院为形式的项目有什么差异和联系?现在世界各地都先后建立了一些孔子学院。就我所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孔子学院是最有特点也是最为成功的。您能否就孔子学院这一形式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为中美两国的语言、文化和人文学术的深度合作谈一谈?
司马德琳 正如你所了解的,领航项目和孔子学院是很难完全分开的,经常会有一些课程和活动在一起进行。美国现在有不少学校到中国大陆学习,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每年都有不同批次的学生到南京、青岛、成都等地进行形式多样的学习。中国大陆的老师也常年定期到学校来参与直接的教学活动,同时也有一些学生以双学位或联合培养的方式过来。一些研讨会也有不少学者参加。比如你这一次来,做了好几场有意思的讲座。我想合作的形式可以逐年展开,争取深度合作。
王晓路 请问您现在主要的研究项目是什么?
司马德琳 我有一些文章需要整理,其中既有教学的,也有文学方面的。教学的主要是关于语言和文化习得,如包括一些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课程设置上所应考虑的理论问题,因为大多数教材都集中在初级和中级阶段,对高级的考虑得不够,对其中的cultural literacy,文化性识别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均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
王晓路 谢谢您,我们以后可以继续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交谈,同时也欢迎您有机会多到中国走走看看。
司马德琳 好的,谢谢。
作者简介:
王晓路教授,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四川大学985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研究员。英文刊物《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副主编。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麦吉尔大学(McGill)、多伦多大学(U of T)访问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U of Chicago)访问学者、杜克大学(Duke)访问教授;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 of HK)、城市大学(City U of HK)、香港浸会大学(HKBU)访问教授。2007年起担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近期成果主要有《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以及译著《文化研究指南》等。
[美]司马德琳(Madeline K.Spring)教授,毕业于安提俄克大学(Antioch College)和华盛顿大学(UW),获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U of Colorado)、俄勒冈大学(U of Oregon)任教,兼任科罗拉多大学中文语言项目主任、俄勒冈大学中国领航项目学术主任。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文化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etters & Cultures,ASU)教授、兼任语言学和语言项目主任(th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rograms)、中文领航项目(ASU Chinese Language Flagship Partner Program)主任、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at ASU)院长。司马教授同时在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化教学两个领域进行工作和研究。前一领域集中在中国先秦诗歌、中古时期散文、六朝和唐代小说以及修辞和现代中文语法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同时对现当代中国小说和电影也多有涉及。后一领域主要集中在第二语言习得,教师培训、课程设置、教学评估以及文化教育研究等领域。其主要论著有:《唐代书写中的动物寓言》(Animal Allegories in T'ang China)、《唐代古文文体研究:以韩愈和柳宗元的修辞为例》(A Stylistic Study of Tangguwen:The Rhetoric of Han Yu and Liu Zongyuan)、《沟通:中文听力理解》(Making Connections:Enhance Your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n Chinese)以及大量的论文等。司马教授同时担任一些学术团体和学会常务理事和委员,如美国东方学会(AOS)、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美国大学指导委员会外国语言项目主任(AAUSC)、亚洲电影研究学会(ACSG)、中国语言教师协会(CLTA),中国语言国际教育咨询委员会(CIEE),美国外国语资源中心(NFLRC)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