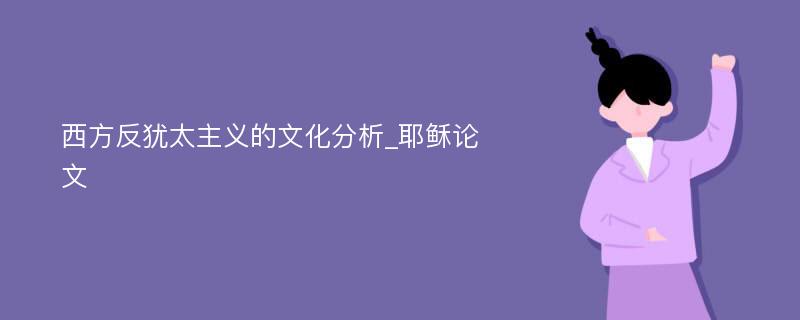
西方反犹主义的文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反犹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是一种有普遍性特征的历史文化现象。西方反犹主义的发生最初导源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学冲突,随着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基督教的神学观念逐渐演化为西方社会的文化观念,“犹太人”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综合情境中则被赋予了“恶”的文化品性和身份特征,反犹也往往成了某些西方人的不自觉的思想定势。同时,西方反犹主义的形成还与欧洲传统的种族主义思想相关。特别是犹太人超越性的现实行为以及与西方人的经济联系、经济冲突,更是导致西方反犹主义的世俗性、行为性契因,这种契因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更为直接和更有根本意义。
有人说,在西方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反犹主义。伴随着犹太人对西方世界的进入,形形色色的反犹主义几乎从未间断过,以至反犹主义不仅成为西方犹太人历史上的一种恒定性的生存压力,也成为西方历史上一种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历史一文化现象。西方反犹主义的发生、演变及其膨胀,显然不是偶然的和自发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一个现代词汇,一般认为是由德国现代作家威廉·马尔(Wilhelem Marr)首创,但历史上具有“反犹”性质的现象完全可以追溯到希伯来人的埃及时代,今天人们所说的反犹主要是指犹太人进入流散时期(The dispersion Period)特别是基督教兴起后所遭受的各种排斥和敌视。犹太人何以要历史性地承受外部世界的“矢石交攻”,早在希伯来《圣经》的一些篇章中就已进行了一定的探究,当然这种探究主要是神学意义上的。在《圣经》的论述中,犹太人的一切现世苦难(无论是来自外族还是来自本族或者来自自然界),其最终根源往往都被归纳为犹太人自身的罪责——犹太人对上帝的各种悖逆,由此上帝将诸种苦难加罚给犹太人。摩西在《申命记》中曾告诫以色列众人说:“你当记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①《诗篇》在追念了上帝的古昔之恩后,又向上帝陈述了“己身今时之苦”:“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作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②在《圣经》中,犹太人受外族所辱以及其它磨难,无疑都被解释为上帝的惩罚,因而犹太人的识罪意识和赎罪意识成了贯通《圣经》的一种重要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圣经》中被一贯地保持着,而且在《圣经》后的犹太生活中也得到了持续的延展,事实上,后世的犹太人常常都是以这种识罪、赎罪意识去解释、消减和对抗他们在现世生活中的苦难经验的。但犹太人为上帝受难的解释终究是一种神学信仰的解释,在现实与理性面前,特别在犹太人负罪受难的日子一再延宕、不知何时为完满终期的时候,犹太人自然会对《圣经》的这种神学解释发生疑问。其实这种疑问在《圣经》文本中就曾多次出现,犹太先祖曾向上帝诉道:“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③《圣经》中诸如此类的抱怨在后世的某些犹太人中甚至发展为对上帝的谴责,抑或最终导致了他们对上帝观念的彻底背弃。但同时,犹太人在西方世界所遭致的各种排挤和敌视,又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的受难及西方排犹主义的兴起又确实与“上帝”观念(相关的神学传统及神学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反犹主义在历史上以种种不同形式出现,并掀起了几次有代表性的高潮。罗马帝国的反犹以相当典型的武力强暴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业已蕴涵了特定的神学信仰因素。一方面,在犹太人看来,罗马统治者对犹太人宗教信仰的蔑视是对犹太人的最大侮辱,为此在犹太人的心中埋下了对罗马统治者极端愤恨的种子,犹太人也表现出为捍卫宗教信仰而宁死不屈的精神;另一方面,在罗马统治者看来,他们无需尊重犹太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特殊习惯,因而在犹太人因其反对偶像崇拜的神学思想而拒绝参与对罗马之像的崇拜时,犹太人便被视为缺乏应有的爱国心,遭致屠戮是其咎由自取。虽然罗马统治当局因其政治需要曾一度对与犹太人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某些调适,但犹太人的反抗及罗马人的武力镇压无疑构成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犹太人历史的基本旋律。在罗马帝国的反犹主义中,宗教神学因素的引入主要表现在罗马统治者对犹太教的玷污及犹太人对其宗教的捍卫上,这与后世反犹主义中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对立有着明显的不同。
基督教兴起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宗教歧视和宗教迫害成为反犹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在中世纪,剥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权利、强迫犹太人改宗是欧洲反犹主义者的重要目标。在强迫犹太人改宗的运动中,众多犹太人因不愿受洗而被杀;而那些在“死或者改宗”的抉择面前违心改了宗的犹太人中,也曾有数千人因被视作异端分子而受到异端裁判所的严厉制裁,有的被活活烧死。在十二、十三世纪,伴随着残酷的宗教迫害和尖锐的宗教对立,还在西方基督教世界衍发了一系列反犹太的谣传,谣传不仅为反犹主义制造了新的“理论根据”,其本身也成为反犹主义的一种恶毒而有效的工具,象“犹太人喜欢在逾越节期间宰杀基督儿童作献祭牺牲”之类显然又在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中加进了某种“公义”和“道德”的世俗性情感理由。1321年前后在欧洲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十分普遍的说法,即犹太人收买和唆使了众多麻疯病患者将病毒投入水井,从而导致了麻疯病在欧洲的蔓延。1348年欧洲流行黑死病,有的地区几乎每三至四人中就有一人因此丧命,格托中的犹太人因与外界联系有限,故染疾者较少,但犹太人的这一幸运又恰恰导致了他们的不幸,因为人们很快便制造和相信了这一谣传:犹太人是带来黑死病的罪魁祸首。接下来便发生了新一轮肆无忌惮的反犹。与“谣传”的反犹方式相呼应,中世纪另一种流行的反犹方法是为所有犹太人强制性地佩戴黄色标记,犹太人无论到哪里,都必须戴着这一耻辱性的象征。诸如此类的反犹表现将中世纪推向了反犹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黑暗的高峰。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曾给欧洲带来了一定的宗教自由,但在此之前,即使是人文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反犹主义也一直在不间断地或周期性地发生着,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对立在莎士比亚、克里斯托夫·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等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笔下都有生动表现。启蒙运动曾一度为欧洲犹太人带来了境遇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既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因为反犹主义业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19世纪欧洲反犹主义有了新的和综合性的发展,在德国等国反犹甚至成为其帝国政策的一部分。往日不断出现的自发性的反犹往往演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规模性运动,反犹主义亦从中世纪时期以宗教歧视、宗教迫害为主发展为以种族歧视迫害为主,反犹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剥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更在于剥夺犹太人的基本公民权利。因而在反犹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上,宗教歧视、经济制裁、种族迫害、人身自由限制、人格侮辱等等都有突出和综合的表现,反犹主义在19世纪形成了新的汹涌之势,这也为20世纪反犹主义的恶性膨胀制造了内在的必然机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反犹主义得到极端化表现的年代,德国纳粹主义在反犹动机、反犹方式等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根本目的已从剥夺犹太人的宗教权、公民权而发展到彻底剥夺犹太人的基本生存权。希特勒法西斯使用了一切最为恶毒、“有效”的屠杀方式,包括建立屠杀工场、使用化学毒气等等,米克洛什·尼斯利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犹太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幸免于难的一位犹太医生(在集中营的编号是A·8450),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了犹太人在地下室被毒死后的惨景:
尸体并不是乱七八糟地平躺在地上,而是簇成一团,堆成塔状,一直垒到房子的顶部。
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只能是毒气首先在大厅的底部蔓延开来,继而逐渐上升、扩散到天花板,因此,这些不幸的人们就被迫互相践踏,向上蹿起,一些人踩在另一些人的身上往上爬,爬得高一点,毒气就晚到一会,——这是人们本能的求生欲望使然,多么触目惊心、令人毛骨悚然的垂死挣扎!
我发现,尸体的底部是一些婴儿、小孩、妇女和老人,而顶部则是一些体格最强壮的男人,他们的身体一般都是紧紧地抱在一起的,身上、脸上和胳膊上布满了搏斗时留下来的斑斑血印,鼻子和嘴里流着污血,脸部肿大、变形,脸色铁青死灰,今人难以辨认。④
犹太人就是这样被一批批地毒死后再送进焚尸炉的,象奥斯威辛这样的大型集中营还有海乌姆诺、贝乌热茨、贝尔根一贝尔森、布痕瓦尔德、达豪、马伊达内克和特雷布林卡等。纳粹分子的反犹是历史上反犹主义发展到极端的结果,数百万犹太人的丧生不仅是犹太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一幕。在1945年纳粹灭亡之后,西方的反犹主义业已消减,但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和领域,反犹主义仍时有抬头。
西方反犹主义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其中起着根本和关键作用的首先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神学冲突,这种冲突在公元1-2世纪原先仅属犹太教下层支派之一的基督教派逐渐脱禽正统犹太教而发展成为影响巨大的新的宗教时就已开始。基督教虽然在其宗教典籍及学说等方面都直接承继和借用了犹太教的重要材料和思想,但无论在一般教义还是具体的神迹事典诸方面,基督教不仅较犹太教有了质的演变,而且生成了诸多对立性的观念,以致这两种原本一脉相承的亲缘宗教最终呈现极端对立的关系状态。基督教以普世宗教的形式出现,消减了犹太教中强烈的民族色彩,特别是它认为犹太人与上帝立约的失效、上帝已另立“新约”,以及由此而演发的救世主基督耶稣的学说等等,在观念深层否定了正统犹太神学的基本教义。而且,演绎基督教学说的一系列神迹事典,尤其是耶稣受难的传说,既为基督徒埋下了仇视犹太人的神圣种子,也是以更为生动、具象的方式表述了犹太人在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世界中的不良品性。在基督教学说中,作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因见利忘义而出卖了耶稣基督:
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作的事,就作吧!”于是那些人下手拿住耶稣。⑤接下来便发生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惨剧。上述故事是否可以作为信史解读的确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尽管在犹太史学家约瑟弗斯·弗拉维(Jasephus Flarius,公元37~约98)的《犹太古事记》和罗马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公元55年~公元118年)的《编年史》等几乎与耶稣同时代史学家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耶稣的问题,但不少学者经过研究还是认为能否作为确凿史料仍然值得怀疑,退一步讲,即使其时确有一个被称作“耶稣”的人,那么此“耶稣”亦未必可以等同于《新约》中的耶稣。19世纪在研究耶稣方面影响极大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F.Strauss,著有《耶稣传》)以及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等都认为《新约》中的耶稣实际上是一种神话的耶稣而非历史的耶稣,是经过《新约》作者塑造后形成的神话人物,虽然在该人物的生平经历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某种历史素材。即使姑且承认《新约》中的耶稣基本上是历史的而非神话的,那么耶稣被钉的责任是否可以象基督教所说的那样统统归纳到犹太人身上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马太福音》中,直接将耶稣送上十字架并将其钉死的,是罗马驻犹太巡抚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及其手下的罗马士兵,罗马史学家塔西陀在《编年史》中也明确写道:耶稣“在提比留(Tiberius)皇帝时被巡抚本丢·彼拉多处死。”巡抚的士兵不仅将耶稣作为犹太人来戏弄,而且在耶稣的罪状牌上指明耶稣的罪状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⑥但在《马太福音》中,作者显然淡化了彼拉多在杀死耶稣问题上的罪责,而将彼拉多这个极为残暴的罗马巡抚塑造成一个无主见、多善心的巡抚,他之所以决定将耶稣送上十字架,原因在于受到犹太祭司及众人的怂恿和压力,彼拉多甚至还试图为耶稣开脱,但“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⑦强暴的罗马巡抚竟然受制于普通“众人”,这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同时这也清楚地表明《马太福音》将犹太人视作杀死耶稣的罪魁祸首是经过了作者一定的主观演绎的。《新约》中的耶稣及其被犹太人杀害的有关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神话”的叙述。当然,在这种“神话”的背后,无疑又相当真实地写照了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背叛者而与犹太教之间固存着的深刻的现实对立。但这种现实性的对立一旦以耶稣受难的宗教神话形式再现出来,它所产生的“耶稣效应”就不仅超越了历史的客观限度,而且还借助宗教思想的传播而产生着难以估量的社会文化影响。在这种“耶稣效应”中,罗马巡抚的罪责荡然无存,“犹太人必须对耶稣之死负责”便成为一种神圣不可动摇的信念嵌入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徒的内心深处,《马太福音》在耶稣被杀时,就让包括犹太祭司在内的众人“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这无可估量的责任,众人说:“他(耶稣)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上。”⑧这样,在《马太福音》的“神话”中,犹太人不仅是杀死耶稣的罪人,而且在杀死耶稣时就已自动承认并担负了这一杀害耶稣的罪责。《新约》中诸如此类的神话故事也许远较基督教与犹太教在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更多地为后世的犹太人带来了不利,带来了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憎恨,这也使得犹太人在神学上必定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永恒的被疏远者。⑨
同时,还需指出的是,当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尖锐的神学对立伴随着宗教对文化的浸染而逐渐生发成一种文化对立时,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犹太人面临着的便不仅是宗教的压力,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压力。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信奉基督教并立基督教为国教以来,基督教就逐渐在欧洲文化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致基督教最终与欧洲文化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形成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历史建构中,基督教中的神迹典故便不仅仅是一种神学事典,同时也是一种传统性的“文化传说”,基督教的某些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神学观念,而更可以生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规范。特别是那些寓意深刻的“故事”,如“犹大之吻”、“最后的圣餐”、“基督受难”、“基督复活”等在民间作为一种传说而代代传诵的时候,它们所发生的影响就决不止于宗教范围,而更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文化领域,而且这种影响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甚至是从其尚未成年的时候就已开始发生作用的。同时,基督教的某些重要事典在西方文化中往往还以节期习俗的形式固定下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等),并在周而复始的循环呈现中演变为一种文化习规。基督教中的神迹典故无论以何样的形式、方式传递下来,它所传递的都不仅仅是“故事”,而更是一种形象化的观念,这些观念连同基督教的体系学说一起,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特别制约着人们对“犹太人”的观点和看法。所以,当宗教神圣要素(神迹典故、观念等)深化为一种文化要素时,它对人们的思想言行所发生的制约力肯定远远超过其原有水平。人们在接受这种制约时,其实也并非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而常常是一种自然性的吸纳并伴随着能动的运用,人们在以“犹大”表示“变节者”、“叛徒”,以“犹大之吻”喻指口蜜腹剑的卑鄙伎俩时,便是这种运用在日常语言中的表现。当然,更重要的运用还是在观念、思想等文化深层的运用。
这样,在基督教文化的综合情境中,在西方世界对基督教思想的文化运用中,“犹太人”不仅有了特定的文化语义,也被固定为特定的社会角色。在这里,“犹太人”被等同于“恶”,并被作为“恶”的意象、象征和载体而呈现在基督教世界的社会文化结构中。萨特在《反犹太者的画像》中曾指出,在西方反犹主义者的眼中,犹太人
……是根本坏的,是根本犹太的;他的长处,设若有,也因为是他的长处而变为短处,他的手所完成的工作必然带有他的污迹:如果他造桥,这桥就是坏的,因为它从头到尾每一寸都是犹太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所作的同样的事情,无论如何绝不相同。犹太人使得他触摸过的每种事物都成为可恶的东西。德国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犹太人到游泳池;对他们来讲,一个犹太人的身体投入水中就会把水根本弄脏。正确地说,犹太人由于他们的呼吸而污染了空气。⑩
萨特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西方世界对犹太人的认知和观念——这样的观念在基督教世界中已不是个别人的观念,而是一种有普遍性的观念,是人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它甚至还作为一种不自觉的深层意识融进了一般人对世界、对生活的基本看法当中,并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定势。因此在1894年法国发生的一次“泄秘事件”中,难怪犹太人德雷福斯首先被人们怀疑为泄秘者,也难怪当德雷福斯被指控为犯有叛国罪时,绝大部分法国人(包括贵族和平民)都不仅坚信不移,而且群起攻之。一个多世纪后重新回顾这一事件的缘由和发展,有许多方面是令人深思的:一位清洁女工在德国驻法国使馆的废纸篓里偶然拣到一封写有法国军事秘密的匿名信,引起法国特工部门的高度重视。炮兵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首先成为怀疑对象,怀疑的根据仅在于德雷福斯是个犹太人。法国原本是个具有法律传统的国度,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写下了不朽著作《论法的精神》,他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伟大思想——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曾对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的时候,法律的崇高和庄严恰恰在这个“法律王国”遭受了损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在法国有关当局对诉讼审判工作的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及对证据和事实的全然不顾。虽然德雷福斯始终否认自己犯有罪行,法院也未得到任何有效证据,但法院仍以卖国罪判处他终身监禁。当时只有作家埃米尔·左拉等个别人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但左拉为此也遭到判刑,甚至有人要烧死左拉。人们不约而同地声讨德雷福斯,还有人为未判德雷福斯死刑而深感遗憾和愤慨。德雷福斯的冤案在他被判刑十多年后的1906年才得以平反昭雪,真正的罪犯被查出,案情真相大白后,法国和世界都为之哗然。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国历史和犹太历史上都是值得记取的重大事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当时还是新闻记者的西奥多·赫茨尔后来写道:“德雷福斯案件不仅是个司法错误。它反映了绝大多数法国人的心理:判处一个犹太人并借此宣布所有的犹太人有罪。当有人从德雷福斯上尉的军服上扯掉军官符号时,一群人高喊:杀死犹太人!从此‘打倒犹太人!’就成了一个战斗口令。这一切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法国!发生在共和的、现代的、文明的法国,而且是在人权宣言发表一百周年以后……。”(11)在反犹意识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时,人权、平等的理想和理性的力量都显得那样的脆弱。法国哲学家萨特以其亲身经历表明不少西方人都患上了病态的“反犹太怪癖”:“我曾询问过上百的人关于他们反犹太人的事。他们之中大部分人一般归罪于犹太人的错误。‘我恨他们,因为他们自私、阴险、难打发、油滑、粗拙等等’——‘然而至少你与某些犹太人接触过吧?’——‘当然没有!’一个画家曾对我说:‘我敌视犹太人,因为由于他们的批评习惯,他们使得我们的仆人变得不顺从。’还有更为确定的经历:有一个没有才份的演员确言犹太人常常用卑下的角色使他不能在戏院出头。一个年轻的妇人曾对我说:‘我跟毛皮商有过可怕的经验,他们强夺了我,他们烧了我托给他们的毛皮。对的,他们都是犹太人。’然而为什么她恨犹太人更甚于毛皮商呢?因为她有反犹太的怪癖。”(12)萨特的分析是生动而深刻的。
无论是德雷福斯案件还是日常生活中,西方世界的“反犹太怪癖”都不是针对某一个犹太人而是针对“犹太人”整体的。人们早就发现西方世界中的犹太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典型的种族问题。(13)西方反犹主义的发生和猖獗除了与基督教文化传统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以外,也与欧洲传统的种族主义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反犹主义在另一种视角下也是一种典型的种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表现。在欧洲,种族主义曾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种族歧视不仅针对犹太人,也针对非洲和东方的其他有色人种,甚至欧洲人内部也有所谓优劣之分,东欧斯拉夫人种昔时就常遭西欧诸人种的歧视。英国自诩为“爱国主义作家”的吉卜林曾在一首题为《东方和西方》的诗中写道:“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就是东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永不会变/直到神的最后审判……。”(14)这是白人优越论的集中表白。欧洲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种族歧视和暴虐行径曾引起了包括西方正义人士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著名作家雨果、马克·吐温、托尔斯泰等都曾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向中国人民发出过声援。犹太人作为流浪客民寄居在欧洲各地,而这块土地原本就有着诸多对犹太人十分不利的宗教因素和文化背景。单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而言犹太人与其居住地就已形成了一种对立否定的文化构成,如果加上欧洲种族主义的催化作用,反犹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就有了更为适宜的膨胀机制。也可以这样说,种族歧视与宗教排斥两股力量的拧合势必使得反犹主义产生难以估量的现实效应。在此不能不指出的是,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思想不仅存在于一般的狭隘人士,甚至也存在于那些富有智慧、“照亮”他人的启蒙思想家。法国启蒙运动的著名理论家,曾以传播知识、批判宗教蒙昧著称的百科全书派领袖伏尔泰就曾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无知和野蛮的民族,他们长期以来将难填的欲壑、最可恶的迷信和对所有宽容并使他们致富的人们最隐密的仇恨结合在了一起。”(15)富有理性、开明的启蒙思想家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偏狭、愚昧之人。诚然,犹太人同世界上的任何民族一样也有其自身的弊端和劣根性,犹太人自己对此并不否认,因而自古而来不仅随时都在产生着犹太传统的背叛者(其中相当部分是出于对其传统阴暗面的不满),也随时都在涌现着犹太生活丑陋方面的揭发者。但这显然不能成为种族歧视和反犹的正当理由。况且,在西方反犹主义者的眼中,只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分,而无好的犹太人和恶的犹太人之分。在欧洲种族主义将其利刃指向诸多“劣等民族”时,也许犹太人是首当其冲的,这除了上述分析的宗教文化等原因以外,另一个“刺恼”西方人的重要原因或许就在于犹太人自认为“上帝的选民”并“坚信不移”,这无疑是西方“优等民族”所不能容忍和答应的,惟其如此,犹太人就必须被证明是“劣等的”和“野蛮的”。
如果说种族主义思想虽然超越了宗教神学范畴但毕竟还是一种观念因素的话,那么犹太人的现实活动、与欧洲人的经济联系等则又是导致反犹主义盛行的世俗性和行为性契因,这些契因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最为直接的,也是有根本意义的。生活在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因其生存环境的天然压力,只有以百倍的努力方能换得相应的生存保障,有时即使这样也难以从根本上解除生存中的后顾之忧。犹太人的这种无以消解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动力和潜能,对犹太人的现实行为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激发,事实表明,散居中的犹太人在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其它一些领域都常常制造出了超越性的行为事实和成就。但这对犹太人而言并不总是一种有利的优势设定,因为这同时也使得犹太人更易受到攻击,甚至在犹太人内部也有人抱怨犹太人的不幸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那些“拚命往上爬”的犹太人步子迈得太大的缘故。在犹太人与欧洲人发生诸种直接的联系时,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犹太人因其特定的传统和经历而形成的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身份特征——商人。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商人,也非所有的犹太商人都是富人,但商业性活动的确在犹太人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的历史与现实契因笔者将另作专文探讨。在犹太人的商业活动中,犹太人靠商业天赋和技巧常常获利甚至发财,这种商业行为及获利效应无疑极易造成商业阶层与非商业阶层之间的差距、隔阂和不信任。经济行为的一切参与者都是运用有利原则来发生其经济联系的——无论是商人与商人之间还是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犹太人作为这种经济活动的一方,无疑也是这样从有利和利己原则出发与西方人发生着直接而对立的经济联系。讨价还价的吵杂声、吵杂声背后的利益纷争,以及潜存在内心深处的心理冲突在何样的情境下会得以平息和安抚,在何样的程度上会使双方共同认可并予以接受,而这种认可和接受又不至于在短期内重新反悔,这些都是没有把握和令人怀疑的。这只是犹太人与西方人经济联系(或曰经济冲突)的一种浓缩化的象征景象,更为复杂的世俗功利冲突还渗透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活空间、就业,升学等等内容。其实,诸如此类的利益冲突即使在同族人之间也会存在,但发生在犹太人与西方人之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经济纷争在反犹主义者看来决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纷争,而更是一种“是非之争”,就象萨特在《反犹太者的画像》中所描述过的那样,一个鱼贩若被犹太鱼贩的竞争所激恼,便可拿起笔来去状告犹太鱼贩,藉助社会力量的“伸张正义”来打击和消灭他的竞争对手——犹太鱼贩。与犹太人发生直接联系者如此,甚至那些未与犹太人发生直接联系的人有时也会将其挫折归罪于犹太人,从申请奖学金的失败到就业机会的丧失,等等,人们在追究原因时,往往会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一切罪责的永恒的首要原因。
犹太人与西方人在世俗功利上的冲突是西方反犹主义的重要现实契因,犹太人与异族冲突的世俗性质在希伯来《圣经》中曾有集中反映,但在流散后的相当历史时期里往往被强烈的神圣化因素掩盖了。这并不奇怪,因为神圣化理由更能蛊惑人心。西方反犹主义的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藉助于神学文化之力而得以实现的,但在其深层的文化机理中,无疑融合了宗教与世俗的多种因素及其相互促发。当然,西方反犹主义的文化根源还远不止于这些,还有来自欧洲文化及犹太文化自身的更为隐蔽和复杂的因素。
反犹主义有着难以估量的危害,希特勒纳粹分子将西方的反犹推向极端,触目惊心地向世界展示了反犹主义的恶果,这也提醒着人们要警惕反犹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滋生的土壤。纳粹反犹既是西方反犹主义发展的自然结果,又有其特定的时代文化因素,遗憾的是某些学者在考察这一历史现象时,有时未能运用一种历史的、综合的文化观点去进行全面的分析。有人曾从心理学的角度发掘希特勒的“变态心理”,说希特勒曾与犹太妓女睡觉染上梅毒,因而滋生对犹太人的报复心理;亦有人说希特勒当年爱上的一位美貌女子被一位有犹太血统的青年人拐走,从而产生了对所有犹太人的愤慨,他本人曾在《我的奋斗》中说过“成百上千个姑娘被可恶的罗圈腿犹太杂种引诱”之类的话,等等。(16)希特勒是否确曾有过上述经历和心理特征是难以证实的,但即使有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方面,难以将其视为希特勒反犹的根本性文化原因。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表白,他“在反犹主义方面的看法是随着时代逐渐起变化的”,这表明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思想是在社会时代的培养下逐渐成熟并最终走向极端的。19世纪欧洲盛行的白人优越论、社会有机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希特勒,这些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将人类划分成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白人自然是优等民族(尤其是亚利安人),其它则是劣等民族,人类社会亦必须遵守生物学优存劣汰的生存竞争原则,而战争则是生存竞争的最高形式。等等。在德国,19世纪后期(1891年)就成立了泛德意志协会,泛德意志思潮四处泛滥,这些都直接成为德意志帝国扩张野心的酵母。此外,欧洲的反犹传统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得到了新的“光大”,人们在津津乐道地传涌和运用犹太人的诸种“古典神话”的同时,又制造和运用了犹太人的诸种“现代神话”,如犹太人导致了世界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困境,犹太人中隐藏着共产主义分子等等,这些无疑都对希特勒反犹主义的孕育和成长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早在希特勒还是个无名之辈时,他就树立了坚定的反犹思想,他曾在1919年写过一篇《关于犹太人的意见书》,提出反犹主义的“最终目的乃是坚定不移地除掉全部犹太人”。当希特勒大权在握以后,“全部解决犹太人”便成了他的重要奋斗目标,甚至他还把反犹主义思想融进了对纳粹党旗的解释当中:“红色是运动的社会思想,白色是民族主义,带钩十字代表斗争使命,即争取亚利安人的胜利以及过去和现在永远是反犹主义的创造性劳动思想的胜利。(17)
被特定社会、时代培育出来的一个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屠戮了600万犹太人的生命,也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一历史的深刻教训是后人不应忘记的,人们有义务以极大的责任感深刻反思这一历史悲剧。在希特勒肆无忌惮地施行反犹暴虐的时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保持了沉默,甚至不给逃难中的犹太人提供一个避难场所,从而在事实上加重了犹太人的灾难,这不同样需要后人的深刻反省吗?关于希特勒的身世在西方甚至还一度流行着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说法,说希特勒自己就带有犹太血统或是一个四分之一的犹太人!这一传说声称希特勒的祖母早年在一犹太富人家里做女佣时与主人的少爷发生关系生下了希特勒的父亲。人们未能找到任何有关这一传说的确切证据。这一“传说”被某些人故意渲染是不是反犹意识的另一种表现——一种迎合了某种心理的、恶毒的表现呢?
反犹主义的幽灵和文化观念在不同时期不仅有表现形式的不同,而且有表现程度的不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会淡化或沉寂,而一旦遇到适宜的机制,便会被随时唤醒。美国经济萧条时期,曾有人把经济衰败、农民受到城市的压力等都归罪于犹太人。在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有人认为是犹太人发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将犹太人与社会主义者等同,从而对犹太人进行种种迫害和监禁;而在冷战的另一方,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许多曾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流血奋斗的真正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却又成了权势斗争、党内路线斗争及种族歧视等奇特混合物的牺牲品。冷战的双方严重对峙着,但在冷战双方的内部,又发生着理由不同但事实和结果极其类同的反犹事件,这是对“世界政治”的一种检验和一大讽刺。
所以,许多敏锐的思想家、哲学家都将反犹视作一部超越了犹太问题的“历史”和“标本”来解读,从中发现理喻人类一般生活的独特视角和特殊参照。哲学家萨特在这方面是有见地的。他在分析了反犹太者的种种心态、完成了对反犹太者的画像以后,深刻地将“反犹主义”视作一种对人类自身的惧怕,将反犹者视为一个“惧怕者”:
现在我们已经懂了他。他是一个惧怕者。当然不是惧怕犹太人,而是惧怕他自己,他的良心,他的自由,他的本能,他的责任,恐惧孤独,变迁,社会及世界;除了犹太人以外,他惧怕一切……犹太人不过是个借口:到了其他的地方就会变成黑人,黄种人;犹太人的存在只不过使反犹太者将焦虑的胚芽及早掐断:他使自己相信他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是被别人霸占了,世界在等待他,而他由于传统之名有权去占领它。反犹太主义,总之一句话,是对人类命运的惧怕。反犹太者是一种想变为无情的石头,倾盆暴雨,怒吼的雷电的人。总而言之,是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人。(18)萨特的论述是否可以认为实际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反犹太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反人道主义。我们说,作为一种种族—文化歧视的反犹主义以及不管来自何方、以何种形式出现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从本质上上说都是反人道的。犹太人不应再为“犹太人”而受难,人类不应再为人类自身的种族多样化和文化多样化而受难。
注:
①《新旧约全书·申命记》第9章7-8节。
②③《新旧约全书·诗篇》第44章,9-14节、18-23节。
④米克洛什·尼斯利《奥斯威辛集中营秘闻》,许家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42页。
⑤《新旧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6章47-50节。
⑥⑦⑧《新旧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7章,37节、24节、25节。
⑨Joscpn L.Blau,Modcrn Varietics of Juda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css,New York and London,第2页。
⑩(12)(18)萨特《反犹太者的画像》,W.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2页、第286页、第300-301页。
(11)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79-280页。
(13)Paul R.Mcndcs-Flohr and Jchuda Rcinharz,cd,Thc Jow inthe Modern World,Oxford Univcrsity Prcss,1980,第273页。
(14)见弗·恩·鲍戈斯洛夫斯基等《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傅仲选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15)查姆·伯曼特《犹太人》,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33页。
(16)(17)胡其鼎《希特勒》,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27页、第29-86页。
标签:耶稣论文; 基督教论文; 中国犹太人论文; 反犹太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犹太教论文; 马太福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新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