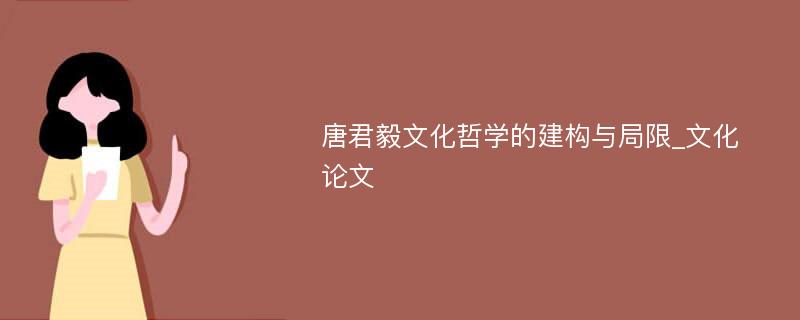
唐君毅文化哲学的建构及其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文化论文,唐君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深切苦难,表明了我们民族已处于一种难以回避的生存危机之中。满怀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以对文化的反省来寻求克服生存危机的良方妙法。正是对中西文化的反省及抉择的不同,构成中国现代哲学各种流派的纷争。本文所要论析的是,被誉为“文化宇宙中的巨人”、“超越的唯心论者”的现代新儒学巨擘唐君毅的文化哲学。
一
作为“超越的唯心论者”,唐君毅并不是泛论文化,而是在其心本论基础上探讨文化意识。在《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中,他系统地建构起他的文化哲学体系。其目的在于:“一方是为中国及西方之文化理想之融通建立一理论基础,一方是提出一文化哲学之系统,再一方是对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之文化,予以一彻底的否定,以保人类世界之长存而不坠。”①其文化哲学的中心意旨在于:“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②对于这一基本思想、唐君毅是通过以下几方面而展开的。
1.文化活动的义涵及其自觉性
唐君毅以为,文化现象既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单纯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文化即人之精神活动之表现或创造”③,即文化现象在根本上乃是精神现象。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活动,文化活动“乃为一自觉的理想或目的所领导者,亦即为自觉的求实现理想或目的之活动”④。但唐君毅认为他的以文化为精神的表现的观点,并不同世俗所想像的主观唯心论。因为他承认自然生命、身体物质、社会生活是实现理想的必需条件;肯定精神的实在,同时也必须肯定这些物质条件的实在。更重要的是唐君毅还强调精神活动的超越性,认为人的日常生活,处处充满理性的向往,处处有“超越意识”、“超越自我”之呈现。
在唐君毅看来,文化活动不仅为一精神活动,同时亦由精神活动之故而表现出自觉性。他认为:吾人欲了解人之文化活动,必先透过对于人的精神或人的理想之本身之了解,视此精神理想为决定人之文化活动之第一因,而不能以人所接触之现实环境,为决定人之文化活动之第一因。⑤他还说:“一切现实环境,皆不能真决定吾人之理想之形成,决定吾人之精神活动。而唯吾人之理想与精神活动之自己生发与形成,可以逐渐决定此一切现实而表现为文化。”⑥唐君毅承认,如果从外部世界去考察人的文化活动形态,可以发现,有不同的现实环境,就有不同的文化活动,但他认为,这只是“吾人之精神受现实环境之规定,而表现为不同文化活动”而已。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规定”不同于“决定”,它只是消极地“规定”人的文化活动不属于何种何类,而不能积极地“决定”人的文化活动属于何种何类。他还说,即使是受“规定”者,亦可有自动自决其如何活动之自由。由是唐氏主张:“一切谓现实环境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皆实只是规定而非决定。而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⑦
2.文化活动与道德活动
唐君毅以为真正的文化理想是依“理性”或“性理”所生发创起的理想。它必具有如下基本特征:超越性、客观性、内在性、主宰性、普遍性。人的真正文化理想,可依其所包含的价值目的观念而分为十二种形式:成就科学哲学为目的的理想、成就艺术文学作品之理想、宗教理想、道德理想、技术理想、经济理想、政治理想、家庭伦理之理想、体育之理想、军事之理想、法纪之理想、教育之理想。他进一步将这十二种文化理想归纳为三类:前四种文化理想为人类理性最纯正的表现;中间四者表现的是人的“理性条理”对“人的自然生命之欲望”的规范,而后四者统称为“维护人类文化存在之文化”。
在这十二种文化活动中,道德活动是其中的一种。但唐以为,文化活动在本质上乃是精神活动,它根植于人的超越的道德理性,即超越的“本心”。一切文化活动皆可称为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道德活动与文化活动最关键的联系在于:“道德活动内在于一切文化活动”。文化活动就其自觉层面上实现的乃是文化价值。“自觉的其他文化活动,只不自觉的实现道德价值,而自觉的道德活动,乃自觉的实现道德价值者。”唐君毅以为文化活动是在自我与客观对象的关系中实现文化理想,并成就一客观的文化表现。所以,“文化活动之本质,吾人亦可言其为表现的。”与此相对,“道德生活之本质,吾人以为乃反省的。”其差别在于:“表现只是自发的创造,反省则是批判的重造。”然而“在最高之人格理念中,文化与道德合一,反省与表现合一,而一切皆为天机天性之流露。”⑧
值得注意的是,唐君毅承继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良知“知善知恶”的思想,并把它扩大到文化领域。唐以为道德意识可以知文化活动之“过”和“不及”。“过”,易造成文化的偏枯;“不及”,则使文化活动难以持续。“过”,需要道德意识加以抑制,以成就各种文化活动的向内的协调意识、向外的开拓意识。“不及”,则需要道德意识激发人的生命力量以使文化活动得以持续,由此成就在外的保护意识与在内的延续意识。要之,道德意识不仅成就文化意识,同时亦超越和涵盖一切文化意识,故道德意识为一特殊的最高的文化意识。
依据道德自我的超越性、涵盖性,唐氏认为,道德活动具有自足性,文化活动具有相依性。具体说,道德活动实现于人格内部,求诸已而无待于外,文化活动则实现于人格与外界的关系之中。但我们能否因此认为唐君毅是狭隘的道德主义者?不能。他申明:“吾人不能谓人只须道德生活而排斥其他之文化活动。因吾人之自觉的道德理想中,即常包含文化理想。而促进文化活动,使之继续,并协调之使不相冲突,以求吾人之文化活动可久可大,即吾人之道德责任,而为道德生活中之内容。”他认为,如果不在文化活动中实现道德活动之道德价值,则道德价值之实现即成为不可能。“最高之道德活动,应包含为促进道德而从事实现文化理想、文化价值之文化活动。”⑨故道德与文化实在是统一而不可分,道德活动对于文化活动具有宰制作用,而文化活动对社会道德活动也具有促进作用。文化与道德的这种统一,实际上就是传统的“内圣外王”的理想。在唐君毅这里,“内圣”即道德,不再局限于人伦之中而扩展到整个文化之中;“外王”亦不再局限于政治事功,而扩展为整个文化活动。也可以说“内圣外王”统一于文化之中,而这个统一是以本心,即道德自我的无限超越性为基础的。
3.本心和文化的地位及兴衰之道
唐君毅明白表示:他的文化哲学不以自然主义、唯物主义为据,而从“理想主义的立场”立论。他指出,在自然宇宙的变化历程中,“贯于自然宇宙者,实自始为一超越物质世界或使物质世界自己超越之‘原理’或‘道’或‘生命精神’在不断显现。”通过对宇宙进化历程的透视,唐认为“人类文化活动之所自生,诚深根植于自然与宇宙之形上实体生命精神,实皆由自然之事物之在进化历程中不断自己超越而最后显出者。”⑩故文化生命位于自然世界之上,它超越自然世界,并涵盖、规范自然世界。因文化依据于人的超越的“本心”而有,故唐认为文化在宇宙中有其至高至上的地位。
关于文化兴亡之故,唐氏认为,如果视文化为宇宙之特殊有限之物,则任何民族文化都不能逃毁灭之命运;但若人能自觉地体现无限之精神,则人类文化可致不毁。可知文化崩坏的原因不在外在之自然,而在人类文化精神自身之堕落。文化之兴,实在于精神之向上。唐氏进一步分析文化堕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自觉其本原之所在,而忘其本以离其体”,造成天人分离,天心与人心分离,使天心、人心皆归于空虚而致文化之毁灭。因而,文化“不毁之道无他,即凡所成之末皆返于本,而末皆为本;斯可致生生之业。”(11)
二
唐氏对文化的研究并不仅仅停留于抽象的文化哲学的层面。他进一步把这种探求扩展到中西文化比较的领域。
关于西方文化精神,唐概括为四点:(一)向上、向外的超越精神,肯定在人之上、人之外的超越的理想、超越的实在;(二)理性客观的求知精神;(三)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精神;(四)学术文化分途的多端发展的精神。在唐看来,此四种精神体现了西方文化精神的两个层面,即体现在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文化中的追求、向往超越现实的宗教精神和体现在近代文化中的探求自然之理、改造自然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的科学精神。这两种精神分别代表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宗教的传统和科学的传统。
相对于西方文化的这种特点,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亦有其自身的精神价值。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有内在与外在的两方面。所谓外在的就是“存在本身即一价值”。所谓内在的方面,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是这样体现的:充分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12)。具体言之,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之特点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天人合一 唐氏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核心内容。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他指出“孔孟之精神,为一继天而体仁,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之仁于人伦、人文之精神。由孔孟之精神为枢纽,所形成之中国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说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13)唐氏以为人的内在善性之根据在于“天道”,即“德”。而此“天道”,又不是外在于人的异己之在,而是内有于人的人性中。这样,“天德”之流行而下至于人心,人心之弘伸可上达于天德”,从而人心与天心可以交贯融通。
内在超越的实践理性精神 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之核心内容,那么内在超越的实践理性则是这一精神内容的践行和超越方式。这一方式使中国文化与西方的上帝观念有所区别。在唐氏看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内在的超越,既有着宗教的超越感情,又超越了宗教的神人分离的外在超越。这样的精神即重理想又不脱离现实,是一种“实践理性”精神,依理性为指导,在道德实践中实现道德理想,其功用在于“见中和之情之致于万物”。他认为“孔子之精神为全面文化之精神,而又求直接实现之于全面社会之精神。其言其教,皆系属于其行事。”从而使理性契入现实生活,而至学用一致,相即相入。
道统意识 唐氏以为“中国文化有其一本性,政治上有政统,故哲学中即有道统。”这样的文化道统意识,并不因政治上的分合而有所变化,作为“政统”的对立面,它代表了中国士人独立自守的学术人格。在他看来,正是由于道统的存在,中国文化才有五千年的历史。唐氏断然认为:这一“存在本身即一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未来的民主建设需要把道统从它和政统的纠缠中独立出来。
对于中国文化,唐氏认为其精神价值尚有其它表现,如他在《文化宣言》中所倡:(a)“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情怀;(b)圆而神的智慧;(c)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d)使文化悠久的智慧;(e)天下一家之情。这几种精神价值,都是上述几种文化精神的引申或发挥。
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精神的疏释,唐氏更进一步指出了中西文化差别之所在。他认为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而非自觉地求表现。”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则是“自觉地求表现的,而未能真正成为自觉地求实现的。”在唐君毅看来,所谓“自觉地求实现”,其含义是将超越的精神理想化为内在的主观精神,并落实于现实生活以成就文化的各个层面,借以滋养人的精神生命和自然生命。这就是中国文化精神。至于“自觉地求表现”,指的是以人的自然生命力和精神活动,不遗余力地追求超越的精神理想,以成就客观的人文世界。(14)这就是西方文化精神。这样,中西文化的两种形态,在唐氏看来,则分别是理想精神的主观进路和客观进路。所谓理想精神,就是超越的本心。因而主观进路和客观进路,即是本心的两种“势用。”这就是说,中西文化都是根植于人超越的本心。对此,唐君毅分别用“圆而神”和“方以智”来表述。“圆而神”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是不偏执任何文化理想,而能会通其理想,即无执的精神。“方以智”则代表西方文化的精神,即执着于理想和理智的精神。
因此,“圆而神”与“方以智”的区别,即“无执”与“有执”的区别。二者都是超越本心的两种“势用”。“圆而神”体现了本心的生生精神,却不等同于本心自身。而“方以智”虽为有执,亦是根植本心,是本心的显发,而不是离体而外在。由此可见,在唐君毅文化理论中,中西文化问题并不再是抽象的体用问题,而是本心的两种势用,是理想精神的主观进路和客观进路。因而,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已大致显现出摆脱体用之争的端倪(尽管他自己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唐君毅的体用已是纯粹哲学本体论上的体用,而不是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体用,和洋务派相比,虽同样强调中国文化,但是在体用观上已大大不同了。这表明唐氏已经开始在更为超越的层面审视中西方文化。
三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的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唐君毅对中西文化的研究,必然落实为克服这一文化危机,重建我们民族文化的实践理路。
通过对历史文化的反省,他并不讳言中国文化的缺失。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缺失在于仅只弘扬了内在的主观进路,而未能充分地在客观层面上加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缺少实即由此而致。他以为重建民族文化就是要引入西方文化的客观化进路。如果说在中国是否需要引进科学和民主这一西方文化的精神的问题上,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唐君毅和西化论者都持有肯定的态度,那么在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则表现出他和西化论者截然不同的思想理路。他反对西化论者在吸收西方文化之时,对传统中国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西化论者的“以打倒中国文化之传统,作为接受西方文化之代价”的作法,绝不能真正吸收西方文化精神,反而会将中国精神丧失殆尽。他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以功利的动机来鼓吹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自由,完全忽视或否定中国文化的道德形上智慧所具有的精神价值。
唐氏以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和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基,亦即是在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前提下,主张吸收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这样一种文化重建方式,并不是要以“自觉地求表现的”西方文化精神来取代“自觉地求实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同时也不是利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进行修修补补。他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就其大本大源而言,是圆满自足的,只是它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没有充分展现而已。
唐君毅把这样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方式称之为“纳方于圆”,也就是说要以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来融摄西方文化中的“方以智”精神。这种文化接受方式,表明了唐氏作为新儒家的特有文化心态。表明他既要接受西方文化又要超越其特有的局限性,而这一局限性的超越则又要本着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才能得以完成。“纳方于圆”即是“返本开新”,即反求超越的本心以开出新文化的格局。其深层本质是“由中国文化之圆中,化出方来。”唐氏以为中国未来文化将呈现出作为人性人道的“人极”、作为天道的“天极”、作为多方面表现客观精神的人文世界的“皇极”并立发展,无一偏废的局面,从而建立一全面展开的“人文中国”。此即唐君毅所谓的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发展。
唐氏认为,世界人文主义的主流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人文思想,他对人文与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反人文等概念作了析疏。所谓人文是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的文化以及人的价值的肯定与尊重。与人文相对,非人文是指对人文的存在与价值未能全部加以肯定尊重;反人文是指对人文的歪曲与抹杀。唐氏认为人文思想为文化的主流与正流,非人文思想与超人文思想为人文之辅翼,同为一文化系统所不可缺少者,次人文思想为抵消人文的消极力量,而反人文思想则与人文精神根本对立,为文化逆流。
唐君毅以为中国文化“在本源上即是人文中心的文化”,它偏重于正德、利用、厚生和审美情趣方面。至于纯粹客观的自然精神和生死临界的超越意识,则只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层面而无以发挥,因而非人文思想和超人文思想极端缺乏。也正因为如此,儒家人文精神也就难以得到扩充和发展,以至到了近代,开始萎缩、衰落、大有一蹶不振的趋势。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要重建儒家人文主义之文化统绪,就必须以西方文化来扩充。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尽管也有人文主义的传统。但它所发展的则主要是超人文的宗教和非人文的科学,而人文精神所体现的道德和艺术则非常不完满。中国人文精神则关注于人本身,成就了道德和艺术,而缺少超人文的宗教和非人文的科学。由是,他强调指出,人文主义的重建与发展,“是要直接承接中国的人文思想,而加以开拓,以摄受西方的思想。而此中所要摄受的,却并非以西方的人文思想为主,而是以西方之超人文非人文的思想为主,这样才能截长补短。”(15)即要以儒家人文主义为根基去摄取西方的超人文宗教和非人文的科学。对科学和宗教,敞开接纳的胸怀,这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缺失体察的真切;以人文主义精神去摄取科学和宗教,则表明他体察到科学和宗教的局限性、偏执性,并试图以人文主义精神化解之。
唐君毅认为中国人文思想中,缺少非人文的科学。因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科学,以使中国文化在现实层面有所发展。他以为科学和人文思想并非绝对矛盾和完全排斥的。科学可以造福于人类,但是“如果真正一往运用科学的理智,去分析一切,而绝不回头,最后便会落到否定一切人生直接经验,与一切人生价值的绝对怀疑主义、虚无主义。”而要化除此冲突之局面,则需确认人之仁心为科学理智之主宰,同时也需确认科学理智之发展,对于中国文化之发展,及仁心之流行开拓,所表现的价值。由此可兼肯定纯理论科学与实用科学的价值。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另一大缺失是宗教精神的相对薄弱,儒家人文主义的宗教化取向,是他的人文主义重建的重要一环。高扬宗教的超人文理想,表现了他和前辈新儒家的不同。他以为宗教的超越精神,可对治科学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泛滥。他所肯定的宗教,并不是西方坚执不舍的绝对信仰,而是面对人生苦难和罪恶存在,以人的超越的本心,去体认“道德文化实践的精神。因而他并非要把西方宗教(如基督教)的具体内容加以引进,而是对西方古典宗教和现代宗教精神的超越意义给予现代诠释。他认为,天地人三才中,儒家人文主义只成就了人文,而对天道与自然有所忽视。但这并不意味儒家人文主义就排斥宗教,相反,儒家人文主义并未割断天人的联系;自我反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使伦理人文与宗教有着本质的契合。宗教精神可“由吾人道德文化精神之充分表现而自觉建立”(16)。作为道德自我之内在依据的超越本心内含了超越有限而趋向无限的意向。通过人伦人文之爱可以确立宗教精神,同时宗教也是道德力量之源。
再者,儒家人文思想重建的另一取向,即人文自身之充扩。这一充扩需要一客观的架构,这就需要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融摄。在唐君毅看来,中国百年来民主建国所经历的挫折和歧途,关键在于仅仅从现实层面和功利的视角来看待民主政治。因而要成功地完成民主建国(即所谓外王),就必须将民主政治归依于个人理性心灵、道德心灵,即归依于超越的本心。同时,唐氏亦清醒地认识到唯有民主,才能使个体主体充分发挥以成就儒家的人文主义,并给予拓广。由是儒家重德性的人文思想,与西方重个人自由、重国家、重社会组织等各种政治思想的冲突可以得到化解。他还进一步认为,唯有儒家人文主义才可化解抽象的民主政治所造成的泛政治主义的弊端。因而努力从事于民主建国,也就是在实际中发展中国的人文精神。
总之,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系于中国德性之发展,科学之发达,民主建国之成功,宗教信仰之树立,并使这一切并行不悖,相依为用。而所有这些,又都根值于对人的超越本心的确认、体察和充扩,亦即肯定儒家心性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家心性思想在唐氏看来,连天、地、人三才为一体,天道与自然内在于人的超越的本心和本性。此本心充沛无滞,贯通天地人之中,其上达于天道而具宗教意义和形上智慧;其下落实于自然,而形成认知科学,以发达非人文之精神;其中充实于人文之道德生活而必然要求个人自我主宰的自由与民主政治的确立。故此,唐氏认为,儒家心性之学为一圆满无缺的形上学。它内在地将人文、超人文、非人文融于自身,因而可摄取超人文的宗教,非人文的科学,以扩充自身的人文精神;又可由人文开显(或客观化)自身,以呈现宗教、科学等各种文化的分殊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说唐君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与发展,实质是超越本心的自我发展以及超越本心的客观化、外化而已。
四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新儒家的领袖之一,唐君毅极力反对“五四”以后西化派的民族文化虚无论和价值虚无论。不同于“国粹派”,他并不完全否认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缺失。也不同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者,他认为文化的复兴和建设,并不能仅仅利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文化加以修补,而应该是体用并重,道器共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不加以拒斥,而是加以认同的。不同于西化论者为引进西方科学与民主而对整个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唐君毅对民族文化有一种执着之情,他认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应持有“同情”和“敬意”,他说:“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
唐君毅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表明了他对现世文化危机的反省。在现世之中,价值的虚无化和人的“物化”,使人处于“存在的迷失”之中。为对抗价值虚无的世界,唐君毅付出一片心血。从积极的层面说,如果说西化派看到了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并以其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方式而进行思想解放,那么唐君毅所作的一切则是要表明,若想使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不能仅仅使其在“价值虚无”的世界中存在,而必须使其与中国文化内在本源接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唐君毅力图弘扬中华文化,确立人的道德主体,重建“人道尊严”,在形上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克服“人的存在迷失”,其内在动机和选择的虔诚都是值得同情的,并且不乏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是唐君毅的文化哲学体系也有其内在困境,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他的整个文化哲学体系都和他所谓的“超越的本心”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切文化都是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从而为客观的文化活动找到他所谓的内在的、主观的、形上的根据。他希冀由主观精神中开辟出一个客观的人文世界,以此使人的主观世界更加充实。这样一来,真实的客观人文世界只是作为主观精神的外化才得以存在,人的经验层面上的文化活动也被归结为超验的主观活动。“人的一切活动,都可说是精神”,在这一观念支配下,一切文化都依道德自我、“超越本心”而建立,客观的人文世界的内在结构、真实内容和独立价值就无法真正呈现。这样的立论基点,纵然唐氏自己不承认其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但又怎样自圆其说?
第二,唐氏的文化哲学,落实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上,就必然把主体性和实践看作一简单的蕴涵关系。他不是如马克思所开启的实践哲学及批判理论那样,把“思维能否达到客观真理的问题”从“认识问题”转化为“实践问题”。相反,他却把“实践问题”归结为抽象的“理论问题”。问题在于他把个人与社会,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当作同一范畴,简单地套用“吾欲仁,斯仁至矣”的抽象的意志自由选择模式,从而把儒家的“良知”无限制地扩展到整个社会历史实践中,而没有意识到人的自我意识(或良知)是根植于人的社会存在及生存实践之中。这样一来,他的“吾欲重建人文”,“斯人文重建至矣”的理论,在实践上必然是苍白无力的。
第三,唐君毅的整个文化哲学体系的根基是儒家的心性理论。在他看来,所谓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其实质就是认为人的道德理性、超越本心是自足自立、不假外求的,是一切文化创造的内在源泉和形上根据。这就关涉到对人的存在和人性内在结构如何理解的问题。笔者以为,不能把人理解为纯粹的超验存在,人的存在应是经验存在与超验存在的统一体。一方面,人是在现象中产生和形成,受到自然因果律的支配,永远承受着客观必然性的制约。另一方面,人性的超越本性又使人力图超越现象界,以表现心灵的自足、自由。经验与超验、自由与压抑永远是人性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二者统一于人的生活实践中,它们在人的生存实践和文化创造过程中得到沟通和体现。
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的危机实质上是我们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超验层面上对于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体系的危机,一是在经验层面上的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危机。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以及向西方学习,大都是在这两方面展开。因此,克服民族文化危机,重建文化传统,也就必然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唐君毅也同样看到危机的两个方面。但对人性、人心所谓绝对无待的自足性的体认,使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缺失仅仅是经验层面上的,在终极的超验领域,儒家心性之学是圆满自足的,并且可以由这一形上层面“推出”形下层面。他沿袭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把民主和科学统统置于“外王”的范围内探讨,天真地以为只要人心的一念“提升”和“超越”,就可以解决整个文化危机的问题,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虽然看到了科学理 性的限制,却没有真正洞察民主的本质,民主只被理解为政治模式。其实民主本身也是一种广义的人文精神,是形上层面的心灵自律。民主与科学共同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精神中的超验层面和经验层面。所谓向西方学习,就是指在这两个层面上学习西方的文化精神,以重新全面整合和再造我们的文化。当然,唐君毅也抽象地谈,“全套”学习西方文化精神,但落实为人文精神的重建,他的文化哲学体系则只是在超越本心的基础上谈论文化,而对文化的经验层面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文化自身也难以确立其独立的价值和地位。笔者以为仅仅从超越的本心,而不是从统一于人的生存实践的超验和经验两方面来审视文化,是难以真正明了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危机的症结所在的。
由此可见,以儒家心性论为基础、以“内圣外王”为架构的唐君毅的文化哲学,虽然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寻找传统和现代化的接榫,防治“民族文化虚无”和“价值虚无”,以及克服人的“存在迷失”等方面都给我们深刻的启迪,并且具有时代的意义;但由于他缺乏对人性及其内在结构的真正理解,因而无法真实地透视我们民族的生存实践方式,也就不能真正把握近百年来我们民族危机的真确症候。这样的文化哲学在形上层面既无法为我们民族确立真正的“终极关怀”,以免重蹈“价值虚妄”和“价值虚无”之覆辙;也无法在现实层面为我们民族克服生存危机提供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
注释:
①《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5页。
②《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5页。
③《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0页。
④《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5页。
⑤《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⑥《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第38页。
⑦《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第38-39页。
⑧《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第521页。
⑨《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第583页。
⑩《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第652页。
(11)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唐君毅全集卷二十),第671页。
(12)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476页。
(13)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478页。
(14)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363页。
(15)《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54页。
(16)《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536页。
标签:文化论文; 唐君毅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天道论文; 科学论文; 道德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