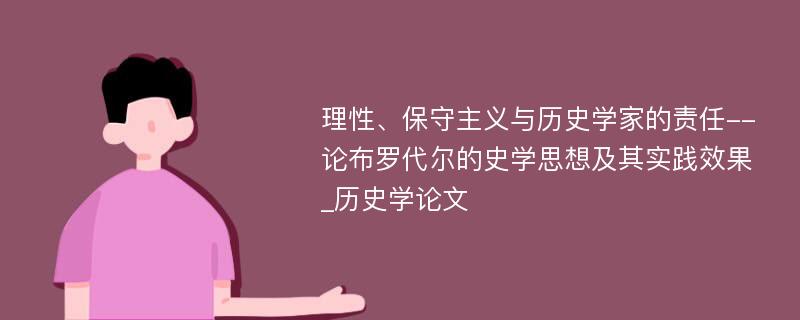
理性、保守主义与历史学家的责任——初论布罗代尔史学思想及其实践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史学论文,历史学家论文,布罗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其主要论著有:《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注:中文译者将本书名译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吴信模、唐家龙、曾培耿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笔者认为,应该译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该书名原文为: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Ⅱ.而中译本译名没有反映出作者的长时段理论。因为布罗代尔首先关注的是深层历史,即作为一个时空整体的地中海,他希望以此为基础来阐述具体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另一个证据是,最初,布罗代尔在阿尔及利亚教中学时准备写一部菲利普二世时期西班牙外交史,后来经过艰苦的资料准备,他将选题定为《菲利普二世与地中海》。1937年11月,他被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收为弟子,并给他的第一个重要建议便是,应将《菲利普二世与地中海》改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后者恰当地展现出长时段思想的意蕴。布罗代尔显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最后以现名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下面关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引文皆出自中译本。)、《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法兰西的特性》、《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以下简称《长时段》),他还与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共同主编了《法国经济与社会史》。布罗代尔提出的地理历史结构主义与历史时间的多元化思想,对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高度的启发性。然而,他的思想中包含的保守主义成分招致了人们的批评,这种批评所触及的问题直接关涉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甚至与我们在现实中的生活态度息息相关。本文试图通过阐述布罗代尔史学的基本特征、其著作中的理性思想、保守主义倾向及其可能给读者带来的效应,分析布罗代尔的理论与其积极的史学实践之间的矛盾,并力图说明作为社会实践者的历史学家应对历史和现实承担的责任。
一、布罗代尔史学的基本特征
布罗代尔史学的基本特征非常明显。只要翻开其三大部代表作的目录,便能看到文本的结构层次异常分明,所有事实毫无例外的遵循结构主义时空观的要求,并分别得到安排;也没有什么地方暗示过,作者准备越出自己依据这种时空观而预先划出的边界。这样,相同的史学思想和叙述布局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如地中海、物质文明史和法国史)内被利用,甚至越来越被强化,布罗代尔也就给读者留下了一条较为清晰的逻辑思路。我们尝试在理论的层面,描述出这条思路,追踪布罗代尔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史学实践。
对于原来不知布罗代尔为何许人的读者,开始阅读《地中海》、《物质文明》和《法兰西的特性》时,能看到些什么呢?我们必须从这种接受史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应该说,这是布罗代尔要求的角度。布罗代尔写作最初的目的并非纯粹是向专业学者提供这一研究领域内的另一种论述,更不是刻意等待着史学史家来研究其中的学术思想,他想要告诉人们,他理解的历史和历史学是怎样的,这样理解为什么更合理。也就是说,这位大历史学家心中的理想读者,正是那些更注重文本而非作者的普通人,他们是一群历史爱好者,只关注历史,无所谓谁是作者。在《地中海》的序言中,布罗代尔开卷即说:“愿意以我希望的方式阅读本书的读者,最好带着他自己对这个内海的回忆和想象,并赋予我这部作品以色彩,帮助我再现这个巨大的存在。”(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3页。)布罗代尔知道,一部作品只有在读者富有感情地接受时,才能迸发出更大的生命力。历史实在的显现,是在阅读历史文本时伴随而来的想象中,而非呈现在文本的字面意思上。面对茫然无知,或者感性多于理性的读者,布罗代尔首先要告诉他们,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是如何构思的,必须在宏观上把握它,从整体上理解它,其细节和局部才能变得更有意义,融合成一种结构的美。于是,布罗代尔必须尽快让这群富有感情的历史爱好者们,以总体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并用总体史的成果来解释现时,这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最根本的特征,是其灵魂所在。
布罗代尔惯用总体史这个概念。如果说结构主义时空观是其史学实践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最终成果,那么总体史观念则既是这种实践的理论前提,又是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布罗代尔看来,总体史应该是一首多声部唱出的能听见的歌,能够表现历史的不同层次,而每一个层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们相互重叠、牵连,共同构成人们难以恢复其丰富纷繁图像的总体史。为了实现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设想,《地中海》便成了最初的实验场地。他的写法是:“把历史事实按照三种具有连续性的记载来写,或者说按照三种不同的‘楼梯平台’来写。我更愿意说是按照三种不同的时间计量单位来写。这样写的目的在于抓住过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间有最大差别的节奏;在于提出它们的共存、互扰、矛盾以及多种深广丰富的内容。”(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976、975页。)在三部宏著中,布罗代尔分别设计了总体史的框架。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作者坚信真正的总体史应该由多元化的局部融合而成,总体不仅大于局部之和,而且多元化的表达更能体现历史在时间上的纵深感和空间上的层次感,进而捕获多样化历史运动的不同节奏。为此,布罗代尔必须找到恰当的理论支柱支撑起总体史的框架。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比较,历史学的特征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无一在时间和空间中诞生、成长和消亡,但是,这些对象所受到的历史影响却是有层次的。我们在解释某个事件时,习惯寻找导致其结果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或者发生影响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等等;我们也知道,各种有效原因、因素越是远离事件本身,其形成所耗费的时间也就越长久,在空间上就越广大。从由此产生的层次性中,不是可以看到一个由多元时间和空间构成的总体史结构的吗?
历史学家们承认,历史的意义不得不根据时间的顺序来解释。那么,总体史中包含的对象各式各样,是否都必须遵从同一种时间节奏呢?传统史学(本文中主要指20世纪20年代前,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的叙事史学)关注的叙述对象往往是单一的事件与人物,因此,史学家们通过安排短时间内的情节,生产出一种单一的线性历史。可是,单一的政治、军事事件不能构成总体。布罗代尔告诉我们:“近百年来的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注重短时间、个人和事件的传统史学已使我们习惯了它那匆促、紧张的情节叙述。”(注: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176页。)情节的激荡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但它很难将读者引入深思之境。要想真正将现实形成的根源说得透彻,就必须将它置于更悠长的时段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于是,总体史的要求促使布罗代尔提出了系统的时段理论与问题史学意识。作为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读者从三部宏著中都不难发现。
时段理论在《地中海》中首次运用,到1958年《长时段》发表时,已经完全成熟,并作为史学重大成果全面影响着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在作品中,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三种,分别指示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在不同时段的舞台上,分别上演着结构史(地理环境演变史)、情势史(社会史)和事件史(政治、军事史)。布罗代尔认为,结构史擅长定性,情势史擅长定量,而事件史不过是燃烧着激情的历史,值得怀疑(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10页。)。
《地中海》中,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地理环境在长时段里缓慢地演变,其速度使短暂的个人生命难以察觉。对待这种宏观结构,时间好像静止了。然而,在布罗代尔看来,长时段的历史对总体史具有决定性作用。地理条件,如陆地、海洋、气候等等,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基地,同时设定了人类运动的边界。《物质文明》中,长时段被用来解释日常生活结构,即物质文明。食品、服饰、住房、工具、货币、城镇就如《地中海》中的陆地、海洋、气候等等要素。此处,布罗代尔也想找到一条边界,而这条边界必须划在人们可能得到的与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之间(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法兰西的特性》在结构上更像《地中海》,长时段首先要说明的是法兰西的多样性,它们涉及地理形态、方言、人口分布、边界等等。
在几乎静止的结构之上,是中时段节奏加快的情势史,经济、国家、社会和战争的各种形式共同组成了《地中海》的社会结构史。《物质文明》关注的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等是其中的主题。在短时段中发生的事件史缤纷繁杂,以布罗代尔的眼光看,它虽是总体史形式上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本质上并不重要。他认为,事件虽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但不过是海面上的湍流、泡沫,与长时段中形成的深海潜流相比,我们必须学会不再信任事件(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On History),芝加哥1980年版,第21页。)。
布罗代尔继承前人成果,系统提出时段理论,并在史学实践中硕果累累。这使他愈加相信,这种理论正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在20世纪中期,相对其他人文科学,历史学研究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布罗代尔在掌握了时段理论后,意识到,历史学应该打一个翻身仗了。既然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那么时段理论应该也适用于这些研究。布罗代尔挑起争论,向学术界宣布:“经过反复的历史观察,历史学家发现了关于时限的辩证法,即瞬时与缓慢流逝的时间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深刻的和反复无穷的对立;我们认为,在社会现实中,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比这一对立更加重要。无论研究过去或研究现在,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时间的这种多元性,这是人文科学共同的方法论。”(注: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第175页。)时段理论是实践布罗代尔总体史理想的一把利刃,用它挑战别的人文学科或许能带来方法论的革命,但要想让这些学科服膺历史学,共同建构总体史,那么,时段理论就显得捉襟见肘了。而布罗代尔史学思想中的另一基本特征——问题史学意识有效地担负了统率其他学科、建构总体史的任务。简单地说,问题史学意设就是要求历史学家根据事先设想的问题选择历史文献,而不是通过整理文献,按照编年顺序摆出历史事实。实际上,这是承认和倡导历史研究的观念和理论先行。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和费弗尔的著作中问题史学意识非常浓厚,这也是他们超越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法宝之一。在布罗代尔史学思想里,这种意识也已深深扎根,体现在总体史建构中的各个角落。
现时是建构总体史的轴心。既然史学实践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不再遵循兰克的名言——“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那么,史学实践(在布罗代尔这里便是建构总体史)的目的也就从描述过去转移到了说明现在。在史学实践中,问题的产生源于现实的需要。布罗代尔写道:“现实是一张方位图,我甚至敢说,是一张真值表。”“历史的秘密目标和深邃动机不就是要说明现时吗?当今的历史学在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接触中,正逐渐像其他人文科学一样,成为一门不完善的、近似的科学,但它随时准备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充当衡量现时和过去的尺度。”(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21页。)强调史学实践的问题意识与服务于现实的目的,表明布罗代尔对史学实践的意义经过了深思熟虑。他以一名参与者的身份积极投身到社会总体实践中,要使史学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不再沉迷于传统史学那种对某些人的丰功伟绩或个别事件的简单描述。例如《地中海》面对的根本问题并非只与地中海历史相关。文本中的地中海历史更像是一种解释工具,意在促成史学思想上的破旧立新。其中的根本问题属于史学思想的范围,全书都在论证“人们能否采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同时抓住一种迅速变化着的、又因其变化本身及其场面而引人注目的历史,和一种隐蔽的、几乎不被见证人和主演者觉察的、终究抵抗时间顽强的磨蚀并且始终保持原状的历史?这个始终有待阐明的决定性矛盾,是认识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它适用于生活的一切领域,并根据不同的比较条件,必定以不同的形式而出现”(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15页。)。在此,布罗代尔想通过《地中海》寻找到一种超越短时段而理解生活(包括现时生活)的有效方式。
《物质文明》倾向于引导人们从长时段的物质文明中,去寻找现时资本主义各种表现的渊源。它要澄清的问题是:用时段理论来审视资本主义会得出什么结论?资本主义与长时段结构的关系如何?资本主义能否继续存在?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有何异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将与现时代的社会经济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例如,若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等同视之,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排斥资本主义,也就会同样排斥市场经济,这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按照经济规律发展经济,最终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
《法兰西的特性》拟在说明法兰西文明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是如何在长时段中逐步形成的。这部未完成的遗稿将问题直指法兰西的现实。它要证明:“昨日和现今矛盾着的力量彼此交织,不断地生发演化,成为一部深刻的历史,法兰西正是它的衍生物。”(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第13页。)
问题史学意识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也表现得很突出。只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研究就应该越过传统史学在时间、空间、研究方法等诸方面设置的界限。全局史(histoire globale)观念(注:法语"histoire globale"一词,亦有总体史的意思,但它的实际含义与"histoire totale"有所区别。我们在此译为全局史。全局史主要是与问题相联系。当然,全局史与总体史之间更为明确的区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是以问题史学意识为核心表现的具体观念之一。布罗代尔在《作为结论》一文中说:“全局史并不意味着要写一部完整的世界的历史……它仅仅是一种愿望,即当人们面对一个问题时,必须系统地超越它的局限性。”(注:费尔南·布罗代尔:《作为结论》(Braudel,"En guise de conclusion"),载《评论》(Review)1978年第1期。)在《地中海》中,全局史要求研究从空间上走出海洋,进入撒哈拉沙漠和北欧大陆,从时间上摆脱菲利普二世时代的限制进入长时段;在《物质文明》中,全局史要求研究从欧洲扩展到世界:《法兰西的特性》同样如此,只有从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人们才能在比较中体会到法兰西的独特魅力。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问题史学意识要求超越传统史学有限的技术,广泛采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各学科的方法和工具。总之,只要能够解决预设的问题,一切研究的传统界限都不复存在。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研究是否是一种历史学研究担心的话,只要这种研究结合运用了时段理论,它就注定了自己的历史学性质。而此时的历史学已经成了全体人文科学的总和。
上述阐释,从总体史观念到时段理论、问题史学意识,均是布罗代尔在史学实践中表现出的主旨或基本特征,它们直接组织、建构了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文本。从现象的层面阅读布罗代尔的文本,肯定能丰富读者的知识,使自己了解布罗代尔的基本史学观念和方法。可是,读者只有进一步询问诸现象产生的原因,才有可能深入布罗代尔的意识内部,寻找到意识深处的潜流,这样读者才能看清,现象的小船是如何在这种潜流强有力的涌动下,驶向布罗代尔史学实践的目的地——现实与未来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将布罗代尔的史学实践成果融入到现实生活中,用他的论说作为读者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实践的参照。
二、理性与保守主义的有机结合
每一个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他希望经过自己的努力,能改变自身、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布罗代尔正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历史叙述是他参与社会实践的有效方式。因此,我们能够通过分析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与内涵来透视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反之,通过了解布罗代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史学思想的脉络与不同特征之间的联系。我们将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作为切入点,尝试着进入布罗代尔的观念世界。首先吸引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布罗代尔坚持要把总体史树为自己的理想与目标?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一,是出于当时西方史学落后状态和布罗代尔寻求变革的心态考虑;其二,是布罗代尔个人学术成长经历中各种偶然因素共同构成的必然结果。这两个方面都体现布罗代尔在认识事物时,力图在理性的层面上为事物寻求一种超越情感的解释。
19世纪是西方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历史学世纪”的美誉。历史学在这个世纪逐渐走向专业化,被大众接受。尤其当19世纪后半叶欧美各大学设立历史学专业以后,历史学已经成为人文科学中一门不可缺少的学科。19世纪同样是一个学科分立的世纪,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新兴学科都像历史学那样,有了自己独特的领域。然而,人们很快觉察到,学科分立造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隔阂。面对近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和日趋复杂,单一的学科成果无法满足人们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变化。一些怀着忧患意识的历史学家认识到,要想让历史学更具时代特征,就必须改革传统叙事史学,进行学科综合,扩大历史学的领地。
实际上,从19世纪中期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历史研究中就已经具备了宏观视野与综合研究能力;到20世纪初,亨利贝尔、赫伊津哈、斯宾格勒等人的学科综合、文化/文明史研究方法(尤其是比较方法)进一步刺激了那些反传统青年史家的勃勃雄心。1929年,年鉴学派顺应变革的呼声而诞生。他们在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前提下,重写历史,为现实答疑解惑。例如,布罗代尔对以往关于地中海的有关著作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他说:“这些论著中需要修订,需要推倒重写,需要加以提高使之复活的地方委实太多了。”对于整个历史学科,布罗代尔认识到,“历史学也许并不注定只能研究围墙内的菜园子。否则,它肯定完不成其现时的任务之一,即回答当前使人焦虑的问题以及保持它与各种十分年轻而又咄咄逼人的人文科学的联系。”(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5-10页。)显然,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状况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史学变革迫在眉睫(注:关于年鉴学派的学术渊源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可参考张广智、陈新著:《年鉴学派》,台湾扬智文化公司1999年版,第1-81页。)。另一方面,关于历史与现时的关系问题,历史学家经过批判客观主义史学“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迂回之后,普遍承认史学实践必须服务于现时的要求。布罗代尔曾经宣称,“为了认识现时,必须研究迄今以来的全部历史”(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时》,载《资本主义论丛》,第121页。),这句话也道出了追求总体史的目的与要求。
在布罗代尔那里,总体史必须具有稳定的结构和层次。他认为:“有了历史层次,历史学家才能相应地重新思考历史总体。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被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注: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第183页。)布罗代尔的总体史观正是通过将历史划分成多种层次,并将长时段、中时段中呈现的历史层次认定为总体历史运动的策源地,这样才为总体史找到了立身的稳定结构。将历史视为多元、多线、多因素的发展使诸者认识历史的眼光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简单地相信“眼见为实”这个机械实在论原则,而是更多地学会综合各种因素思考历史和现实。人们由此认识到,要想了解历史的意义,真正用“过去解释现时”,就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停留在描述历史现象的层面,关键在于解释。总体史其实也是布罗代尔为读者提供的一种历史解释工具。布罗代尔意在提醒人们,要从本质上理解历史,就必须在宏观上把握那些长时段、中时段中形成的稳定结构,任何拘泥于细节或短时段中的激情都将以失败告终。在布罗代尔的概念系统中,他毫不讳言地推崇稳定、静止(或半静止)、结构、深层,蔑视激情、瞬间即逝、表层,与传统叙事史学的对立由此表露无遗。这同时也是深沉与肤浅的对立,理性与感性的对立。
既然总体史观不过是诸多历史解释工具中的一种,那么布罗代尔为什么单单对它如此推崇呢?总体史观不是布罗代尔首创的,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布罗代尔之所以能够接受总体史观,并使它有更大的发展,这与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有着一定的联系。
布罗代尔在完成大学学业时,获得了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任教资格。从1923年到1932年,布罗代尔到阿尔及利亚任中学教师近10年。在此期间,布罗代尔积极地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准备资料,遍历地中海周边国家,培养出一种开阔的视野。他的论文选题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外交史有关,属于传统史学的题材。1929年,费弗尔与布洛赫创办了《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这份充满着史学革命气味的刊物很快打动了布罗代尔。他本来就热爱地理学,年鉴学派创始人的跨学科和总体史设想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这位青年人的前程。布罗代尔从此更加关注和学习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希望自己有能力实现年鉴学派创始人的理想。1935-1937年,布罗代尔任教于巴西圣保罗大学。站在南美洲大地上,接受另一种文化的熏陶。在巴西的经历使布罗代尔有机会以一种旁观者的眼光,从总体上审视着整个欧洲大陆。命运还为布罗代尔安排了一次巧合。1937年,布罗代尔在从巴西回国的船上遇到自己仰慕已久的费弗尔。交流之后,费弗尔当即收布罗代尔为弟子,这个机会使他迅速地融入年鉴学派的小圈子。费弗尔对其博士论文选题的建议非常及时,它决定性地促成了布罗代尔在思想上从传统史学向年鉴学派总体史学的转变。从此,布罗代尔的博士论文便按照这种思路重新酝酿。
《地中海》的主要篇章是二战期间布罗代尔被德军俘虏后,在集中营中完成的。当时,战争的惨痛经历,尤其是自己的亡国之辱,使布罗代尔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注:这种反思,读者可能从《法兰西的特性》中更能品味出来。参见《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的导言。)。集中营的生活与心境加深了布罗代尔思想中的总体史倾向。在研究中强调宏观历史与深层历史的意义,有助于摆脱现实带来的痛苦。后来,有学者向布罗代尔指出,《地中海》在结构上的安排应从事件史开始,以地理环境史来结束。布罗代尔简单地回答说:“沙漏肯定可以翻转,正、反两面都可以使用。”(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418页。)然而,彼特·伯克的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他认为:“对布罗代尔来说,从‘表层’的事件史开始是不能忍受的,因为在他被监禁而仓促完成这项研究的环境中,对他而言,超越短时段是一种心理上的要求。”(注:彼特·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Peter Burke,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es School,1929-1989),斯坦福1990年版,第40页。)尽管这不是促成《地中海》现行结构的惟一要求,但是,当人们认为短时段中惨痛的现实是长时段形成的必然结果时,心中的郁闷确实能得到释缓。《长时段》中的布罗代尔承认了这个事实,他谈到:“就我个人而言,在那百无聊赖的被囚期间(1940年至1945年),我曾拼命去摆脱这些困难年月的漫长时间。拒绝接受当时的事件和时间,就是明哲保身地站在一边,以便能高瞻远瞩和不过分着眼现实。从短时间过渡到较长的时间和很长的时间,接着便暂时停下,重新考察一切和重新建设一切,看到一切都在自己周围转动:这种处世之道确实值得历史学家一试。”(注:费尔南·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第199页。)这的确是一种处世之道,只是它不仅仅适用于历史学家及其研究,通过《地中海》等著作,布罗代尔显然希望读者们都能领悟这种源自历史学思考的处世之道。它是一种人生观,一种通过历史进入现实表象深处的人生观,一种要求理性制服情感、分析替代幻想的现实主义人生观。而对现实生成的必然性过分强调,便会给自己的思想添上一笔浓重的保守主义色彩。
倘若读者像布罗代尔所主张的那样,完全以一种过滤了情感的眼光来观察人类的历史,观察身边的事物,那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一种怎样的态度呢?从布罗代尔的作品中,读者能看到作者针对不同事物做出的各式各样的判断。我们籍此来了解布罗代尔希望自己的作品给读者带来的效应。
首先,面对纷繁复杂、变幻多端的现实,布罗代尔提醒读者,应该有一个由理性支配的冷静头脑,才有可能深化对事物的认识,从而把握总体史中“基本的原则和事实”,并真正认识到在这些原则的推动下,个人命运涌动的方向。在《地中海》中,布罗代尔已经证明,事件史占据的现实世界(包括历史人物生活的现实世界和读者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个“充满激情的世界,是个像任何其他活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那样盲目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就像最轻捷的小船在激流的表面飞驶而过。这也是个危险的世界。为了躲开它的魔法和巫术,我们必须事先弄清这些隐蔽的、往往无声无息的巨大水流,而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提示它们的流向”(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418、10页。)。就追求历史实在这一点,布罗代尔与传统实证主义史家没有两样,他相信历史实在存在于现象的彼岸,如果人们能够“摒弃个人的感情,也就是超脱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激忿或留恋,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的毕生经历及时代给予我们的种种影响”(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第2页。),我们就能成为一位超脱的“观察家”。比较一下现实生活中的经历,读者很容易接受布罗代尔的观点。在生活中,人们都希望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而布罗代尔为此提供了学理上的证明。它有助于读者更多地思考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进入复杂的历史关系中。这样,读者有效地避免了认识的简单化,更不会轻易为激情所动,以至最终具备一种历史的眼光,理性地思考问题。
其次,布罗代尔强调结构与长时段的价值,势必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强化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强化一方面表现为突出稳定而变化缓慢的地理环境结构或集体命运,另一方面忽视转瞬即逝的个人命运。其最终结果是,个人在总体历史中显得无足轻重。如果全面接受这种观点,读者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必然性的陷阱,产生一种保守主义、宿命论,甚至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因为读者始终是一个个体,他的命运在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中,永远只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瞬间。布罗代尔的著作中,保守主义的痕迹随处可见,而且随着作者年岁的增加,这种痕迹也日渐深刻。作者在《地中海》中除了强调地理环境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而忽视个人的价值之处,毕竟还是认为社会时间中的历史,即表现出集体命运和趋势的集团的历史“是一部社会史,其主角是人,人类,……即人类在物的基础上建造的东西”(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528页。)。在此历史仍然是人类的创造物。而在《法兰西的特性》中,作者已经发出这样的感叹:“长时段的历史从遥远的过去开始,今后还将顺着平缓的斜坡长期发展下去。因此,在长时段历史中,人的自由和责任具有局限性。人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反倒是历史造就着人,并且为人卸除责任。”(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第411页。)在现实中,人类,尤其个人,他们生活在长时段形成的历史中,要想立即改变这种历史似乎不太可能,也不现实,于是,他们只有听任历史趋势无情地宰割。
另外,尚不必说改变总体的历史,甚至人们要想改变总体历史结构中的万千个要素中的某一个都异常艰难。例如,涉及具体的历史事实,布罗代尔在《物质文明》中讨论了资本主义的命运,他声称:“除非我从头到尾全都搞错,我确实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由于‘内在的’衰败而自动垮台;为使资本主义垮台,必须有极大的外力冲击和可靠的替代办法。社会中强大的习惯势力,时刻保持警惕的少数统治者的抵抗(他们今天已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唇齿相依的关系),决不是几篇夸夸其谈的演说和纲领,决不是几次暂时的选举成功,就能轻易动摇得了的。”(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729页。)的确,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已经与历史中的其他要素,如世界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制度、科技进步、心理及价值观念等等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任何针对资本主义的剧烈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除非有一种系统的替代体制与巨大外力冲击相配合才能成功。
布罗代尔看待问题往往力求全面、深入,这也使他的保守主义以一种冷静而理智的姿态出现。当一些史家欣喜地称赞17世纪的法国物产丰饶,完全自给自足,是“普天之下物产最齐全的王国”时,布罗代尔就会劝同行们不要太乐观。他不仅将法国当时食物供应不足、不断从国外进口农业产品的实例、统计数字罗列出来,说明法国仅仅是非常勉强地做到食物自给,而且列举那时由于粮食匮乏而频频发生的饥馑、骚乱、暴动等等社会动荡,证明历史的真实往往比某些激进史学家的简单结论更具复杂性和多样性(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第131-157页。)。这样的观点使读者更容易从布罗代尔的作品中看到社会体系各要素之间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客观存在着,它不但阻止了社会迅速发展,对它的清醒认识更令激进历史学家的幻想破灭。
保守主义思想还使布罗代尔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怀乡病。当他评述旧时代的法国农民时,一反传统史家对旧时代农民悲惨遭遇表现的同情心理,而是:“面对旧时代的法国农民,我确实没有理由流露悲天悯人的感情,因为回过头看,维护这些旧平衡在当时只可能是明智的和合情合理的办法。相反,今天朝着技术进步和移风易俗方向发展的农业却不一定都很合理”(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第410页。)。在保守主义思想的缠绕下,布罗代尔在晚年终于说道:“我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今日世界的90%是由过去造成的,人们只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摆动,还自以为是自由的、负责的。”(注:转引自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中译本代序,第18页。)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人们闻到了保守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气息,感到的只是人的渺小和无奈。此时,我们已经能理解为什么布罗代尔会如此推崇保守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将他视为精神上的教父(注: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第1页。)。在布罗代尔那里,理性与保守主义相依并存,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在历史认识或日常生活的认识中,理性的思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实践中的保守主义,甚至悲观主义的结局吗?历史的眼光是保守主义者的独特眼光吗?这样,面对总体史观与长时段,我们对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思考已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态度发生了密切联系,我们不得不步入另一个核心问题的语境之中。
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面对自认为不可更改的现实,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他的思想完全是悲观的、消极的、保守的,那么他似乎什么都不应该做,而是保持沉默。从布罗代尔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不仅仅他的史学实践给西方史学、世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我们同样能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他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所做的一点一滴的努力。这种努力是一个积极的史学家参与社会总体实践所应做的。从布罗代尔的实践及其效应看,他所做的与他所说的之间确实存在着矛盾,也就是说,他的理论与他的实践之间并不吻合。那么,为什会这样呢?布罗代尔的理论有极多的可取之处,而且,以长时段为意义之源的总体史结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相反,它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也许布罗代尔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通过寻找一个核心问题的解答,我们能将这个开放的结构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人(尤其是个人)始终是被历史造成的,那么,谁又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这个问题有许多类似的形式,它困绕着诸多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甚至每一个思考自身存在的人。我们从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寻求解答,这并不意味着相信自己能够获得确定的答案,或许询问本身便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三、布罗代尔与历史学家的责任
阅读布罗代尔著作的学者们在评论其观点时,批评主要集中于作者表现出来的决定论思想。他们认为,这种思想中存在的消极因素,不利于一般读者正确地认识历史与现实的生成,以致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到读者承担自身责任与义务的态度。我们从布罗代尔晚年的谈话中的确已经了解到,对转瞬即成为历史的现实生活,他心存保守观念,认为个人在其中已经没有多少自由意志可以施展了。
一位英国评论家带着讥讽的口气说:“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是一个对人类的控制毫无反应的世界。”(注:埃里奥特所撰书评,载《纽约书评》(New York Book Review)1973年5月3日,转引自彼特·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40页。)布罗代尔无法逃避这种“责备”,因为它涉及的不再是一种学术观点,而是个人的世界观或布罗代尔所说的处世之道,因此,这种“责备”也就只能表现读者与作者之间在处世之道上的差异,而不具有价值上的优劣之分。
个人在长时段中的自由意志问题,是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时常考虑的问题。1965年,当布罗代尔为《地中海》第2版重写结论时,他必须回答读者在这方面的异议。他写道:“指出行动范围的狭窄有限性,就是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吗?我认为不是这样。……我将作出这样不合情理的结论:伟大的实干家是有自知之明的、能够准确地量度自己的能力的狭窄有限性的人,是选择把自己保持在这个狭窄有限的范围之内,甚至利用不可避免的事物的重量以便把它加到自己的推力中去的人。任何反对历史的主流——这种主流并不总是明显的——的努力都是预先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当我想到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很想看见他被囚禁在他自己勉强制造出来的命运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后构成了‘长期’的无限的远景的风景画中。在我看来,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这样说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统统由我来承担。”(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984页。)
布罗代尔的话让我们想起一句名言:服从上帝的人,上帝领着走;不服从上帝的人,上帝拖着走。布罗代尔虽然指出历史上的伟人往往是那些能够认识自身局限性的人,但他们在获得这种认识之后,却只能顺应历史潮流。换句话说,只有当人们自觉地将自己的意志与历史发展的长节拍吻合起来时,他才有机会成为历史中的伟人。布罗代尔并不在乎他的解释是否消除他在读者眼中的决定论者和宿命论者的形象,而事实是,它更加证实了批评者的看法。
有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双方的争执在本质上是不可协调的。同情者伯克说道:“布罗代尔的决定论并不是简单化的。他坚持需要多元解释。……关于自由的限度及决定论的讨论与历史写作的历史一样长久。在此,无论哲学家怎样说,对历史学家而言,超越他们自己处境的简单声明都是极困难的。”(注:彼特·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40页。)作为史学界的一个伟人(注:1946年,布罗代尔为《地中海》第1版写的序言的结尾说:“法拉尔在1942年写道:‘对伟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伟大的历史学。’但愿这种伟大的历史学复活!”(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第11页)从这句话中,我们已经能看到布罗代尔的抱负。),布罗代尔相信——至少希望——自己的实践顺应历史潮流。但我们也不时看到,布罗代尔仍有超越自身处境,置身于历史及其潮流之外来观察历史的愿望。由此可以说明,超越自己的处境以获得更大的自由始终是布罗代尔实践的驱动力,尽管要实现它的确困难重重,但他在不断尝试。
按照布罗代尔的保守主义观点,历史造就了他。他成长在西方史学的传统之中,一定带着传统的印迹。这一点,我们不难证明(注:布罗代尔继承德国历史主义传统,试图在研究中摆脱意识形态偏见,追求客观的历史实在等等,都与传统实证主义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论证参见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章);《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3章;张广智、陈新:《年鉴学派》,第4、5章。)。但我们同样能够证明哪些是布罗代尔的独特贡献(注:至少布罗代尔时段理论的独创性是大家公认的。伯克说:“布罗代尔无与伦比的贡献是,他比本世纪任何别的历史学家都强有力地改变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观念。甚至它的批评者都不能否认这是一部杰作”(《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第41页)。利科也认为:“把不同时段垒放在一起,正是法国史学界对历史认识论的最杰出的贡献之一”(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显然,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思想是20世纪史学发展的主流,而且也是构成20世纪末史学现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从现在回顾过去,历史总是必然的。在史学发展的必然性之中,有布罗代尔主观的努力,他成功地应对了自己面对的现实(我们已经将它称为历史了)提出的挑战,担负起史学革新的责任。布罗代尔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史学实践中积极地改造传统史学。无论是在求学、教学生涯,还是在被俘入狱期间,或是充当法国史学巨擘时期,布罗代尔都笔耕不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活、实践态度及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影响了几代学者。这便是布罗代尔的自由意志真正的体现。
如果以一种社会实践的眼光来看待布罗代尔积极投身史学实践的一生,我们就不得不说,这种实践恰恰证明,布罗代尔宣扬的保守主义、悲观主义结论并不意味着一种消极的人生观,而更多的是一种忧患意识和焦虑。布罗代尔注意到,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具有了在瞬间摧毁整个世界的能力(注:在《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导言中,布罗代尔忧心忡忡地说:“假如人们在明天不滥用其魔鬼般的摧毁力量,法国将比我们的焦虑、比我们的个人生命、比我们经历的充满曲折事迹的历史寿命更长。”)。正是对法国的未来,乃至人类未来的忧虑,加重了布罗代尔思想中的保守主义色彩。而他积极的实践旨在说明,只要文明还有一线希望,就必须努力延续。
也许布罗代尔没有看到,长时段构成的总体史正向未来开放着,即长时段中形成的历史能够通过长时段的努力被改变,只不过最终的改变,必须凝聚无数人千百年的努力。每一代人也许难以看到自身努力的明显效果,但历史确实在缓慢地变化着。任何变化都是人双手创造的,人类对它负责。如果说历史中的长时段已经成为必然,那么,尚未展开的未来的长时段却是偶然的王国。个人在其中可以不断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使理想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虽然未来不可预料,但人的理性必将为此做出积极的贡献。显然,布罗代尔在实践中承担了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承担了一个普通的个体生命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布罗代尔并没有意识到,他心中深蕴的忧患意识与积极实践完全可以在自觉中融洽协调,那样将更有利于自由意志的发挥。这一缺陷,也使布罗代尔不可能由此深入到人类如何创造历史这一问题的深层。伊格尔斯是对的,他在评价包括布罗代尔在内的年鉴学派史学家时说:“由于极力强调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他们忽略了考察人类在创造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而且把研究人类是在什么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工作留给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注: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85页。)
从正反两方面,布罗代尔史学思想及其实践效应给人们的最大启示是:人们不仅要认识总体——长时段历史给人类生存制造的局限性,还应该探索人类超越传统的界限而创造历史的途径。否则,缺乏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正确了解和评价,历史学甚至人文科学都将失去自己的意义之源。
标签:历史学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年鉴学派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西方历史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物质文明论文; 法兰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