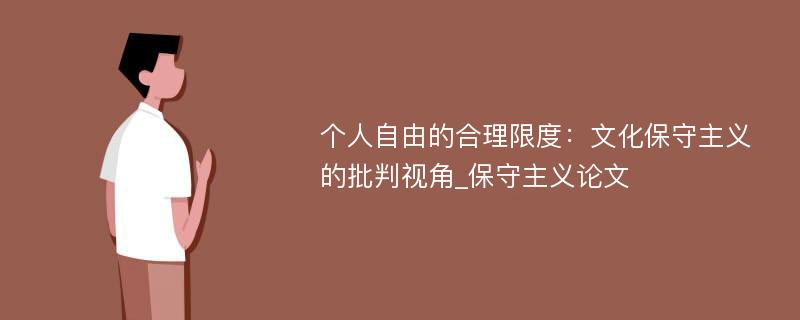
个性自由的合理限度———种来自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限度论文,透视论文,批评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追求个性自由、捍卫个人权利,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变迁的主导潮流。如果联系其历史起源,将这一潮流同封闭的和压抑性的中世纪禁欲主义传统作对照,谁也不怀疑它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所起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性作用。所以直到今天,人们仍习惯于把解放当作自由的同义语。若换一个更朴实的说法,所谓解放也就是释放,亦即疏通一切淤塞的渠道,顺乎自然,让每一个人的幸福渴望和生命潜能在最少限制的自由环境里畅畅快快地排释。这或许是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典型心态。但是,纵令充分认可个性解放的历史进步意义,并把它作为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原则予以接受,从道德秩序的良性建构来看,也仍然有理由,就这一原则的正当性的合理限度提出追问。这一追问在今天显得相当迫切。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强调约束、督导和教化为特征的传统力量日益萎缩,而个性自由在解脱传统的压抑束缚之后,不但作为价值理念成了具有文化霸权意味的“主义”话语,而且还好像某种获得性社会遗传一样,融入普通男女的精神血液,启动了一场开拓欲望边疆的时尚竞赛。倘说这场竞赛的无节制进行潜伏着破坏道德生态平衡的危险,那么,审视一下文化保守主义对个性自由负面效应的批评,便具有某种建设性的启发意义(注:将文化保守主义同现代个人主义或现代自由主义作比照,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沟通联结。事实上,我们既难找到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更难找到纯粹的保守主义者。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严格说来是一种文化问题上的保守取向。本文在讨论中把伯克、托克维尔、韦伯、熊彼特、贝尔、麦金泰尔等人归于这个取向之内,并不是给他们盖棺定性,而只是说,他们的文化观包含着明显的保守主义思想因素(不论他们是否自认为,或通常被别人认为是保守主义者);而这种思想因素对反省个性自由的负面效应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座标。)。
一
作为一股社会思潮,现代保守主义起源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性反应。它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思想家伯克。在《法国大革命感想》一书中,伯克基于对传统价值的偏爱,对法国大革命彻底打烂旧秩序的过激行为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曾被法国复辟时期的贵族保守派思想家加以极端发挥。他们指责启蒙哲学对个人理性的弘扬和法国大革命对个人权利的滥用,将国家和社会瓦解成“个体性的尘埃和粉末”,因而在否定的意义上最早明确使用了“个人主义”一词(注:参见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他们的一个极端立场是,要为个人主义的泛滥纠偏,必须恢复神权和王权的绝对权威;而要使这种权威获得至高无上的尊严,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嗜血的刽子手来整顿纪律(注:梅斯特尔宣称:“一切权威、一切秩序都要依赖刽子手。他是人类社会中的恐怖力量,是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纽带。”进步思想家认为,如此极端的保守主张,实乃呼唤白色恐怖的反动。(参见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但是后来的保守主义者,大都不再持如此张狂的复仇心态。而且他们认为,传统秩序的瓦解也不单单是一场政治革命的后果,毋宁说,它是一个更为广泛和更为持久的社会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近代随着城市的崛起而开始,因世俗化潮流的涌动而扩展,最后在声势浩大的现代化浪潮中完成了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改造。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一概否认由此产生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他们强调,现代化进程在使个人挣脱传统纽带束缚的时候,也使他丧失了任何“必然的社会身份”;它不仅教会个人怎样设计和实现一个独立的“自我”,而且也鼓励个人消解原本为他提供终极归属并据以判断其行为的道德准则的限制(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5页。)。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正是问题的后一个方面使他们有理由对个性化浪潮发出批判性的质疑。他们的第一个追问是:个人自然欲望的释放应不应该接受必要的约束?
当敬重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发出这一追问的时候,他们心目中已经有了相当确定的答案。麦金泰尔指出,传统道德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目的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与“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重要对照。伦理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对人之为人所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进行阐释,并以伦理戒规来约束人的行为,用道德教化来塑造人的品格,从而使人由偶然形成的现存状态向本该如何的真实目的转化(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此乃传统道德体系的基本特征。
但是,这样一种道德体系在近代文明浪潮的冲击下逐步瓦解了。一方面,由实证科学的成长所带动的理性化过程,首先为自然“解除魔咒”;而它在认知和征服自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又鼓励其信奉者进一步否弃了人性问题上的目的论观点。结果,“认识到自己真实目的后可能成为的人”的概念被冲淡或取消,而未经教化的人,即受本能欲望支配的自然人,则成了伦理学所面对并由此出发的经验事实。另一方面,由商品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世俗化过程,不仅把个人从传统归属纽带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自主行为者;而且以反禁欲的方式,将功利谋划提升成了个人现世生活的至上目标。这样,传统意义的超验价值关怀遭到否决,而感性欲望的公开排释和物质利益的自由追逐,则被合乎逻辑地宣布为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
由此不难理解伯克与启蒙思想家的争论。启蒙思想家从反禁欲的立场出发,对个人感性幸福追求的正当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他们来说,“个人利益是个人行为价值的唯一而且普遍的鉴定者”(注:爱尔维修语,见《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60页。 )。但是伯克却强调,一旦取消偶然形成的现存状态同本该如何的道德关切的重要对照,对个人自然权利的张扬将不可避免地危及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基础。因为,“文明社会的最早的起因之一,也是它的基本的法则之一,就是不容许任何人为自己判断是非。”(注:见《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34页。)按照伯克的理论逻辑, 仅当人们愿意生活在蒙昧状态之下的时候,才可以谈论不受约束的天赋自由;而要在文明社会也保全这样的自由,则办不到也不容许,除非想让整个文明拱架在纷争中被炸毁。因此,只要有起码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责任心,那就必须承认抑制个人自然欲望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伯克甚至认为,“约束应该和自由一样,被看作人类的权利。”(注:见《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35页。)
伯克把约束提到人类权利的高度,就其基本意向来说,并不是渴望恢复中世纪那样严酷的社会控制。随着历史的进步,恢复那种社会控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问题在于,反对一种特定形式的独断高压,是否可以理解为取消任何公共权威和道德约束的充足理由?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如果作这样的推演,至少在逻辑上意味着文明法则的崩溃。由于这一极端状态十分可怖,一些理智的个人主义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个性自由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与范围。但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接下来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约束个人自然欲望的无度释放是使进步变得稳妥而有效的一个必要因素,那么,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否包含提供这种约束的文化资源?
二
对于这个问题,个人主义思想家给出过两种典型的回答。第一种回答诉诸的是理性谋算。它把趋乐避苦看作人的自然本性,而把社会生活理解为一个广义的交易场所。因此可以作出如下推论:当个人进入这个交易场所的时候,基于对切身利害的左右权衡,他会适当收敛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损失的过度贪欲,理智地坐下来和竞争对手谈判,以互利的方式达到自利。第二种回答诉诸的是共同情感。这种回答以人所共有的某种怜悯、同情之心作为人的自利倾向的必要校正。斯密称:“人,不论一般认为如何自私自利,在他的本性中总明显存在某些因素,这些本性的因素使他关怀别人的祸福,使别人的幸福成为他本人的必需,即使他在这别人的幸福中,除了看到这幸福而引起的快慰以外,并无丝毫利得。怜悯或者同情,便属于这一类性质。”(注:见《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75页。)所谓“悲人之所悲、 哀人之所哀”的情感共鸣,表明人不仅有自私之欲,而且有利他之心。这是施仁爱、行正义的道德基础。
但是,以上两种辩护,在麦金泰尔看来非但不充分,而且暴露出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因为按照功利型个人主义的理论逻辑,一当认为人具有本性利己的倾向,则利他主义就立刻成为社会所必需的,但又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问题的关键在于, 个人主义一方面执着于原子式的独立自我,另一方面又将利益追逐看作个人的自然本性和正当权利,这使它在论证公共道德标准的必要性的时候,只能诉诸一种“利益交换中的相互性互惠之场”(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但是, “如果诸如正义和守信这类规则是因为且仅仅因为它们有利于我们的长远利益而应遵守,那么当它们不能使我们得到,并且违反它们没有任何不利后果时,违背这些规则为什么不能证明为正确呢?”(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这是个人主义伦理无法穿透的一个理论盲点。它不仅使乞灵于同情、怜悯之心的努力显得十分幼稚,而且根本就是一种遮掩问题实质的虚构。对于以自我为轴心的个人主义来说,一种客观、普适的公共道德标准是很难成立的。
一些为个人自由辩护的思想家曾以退为进,干脆对超个人的社会权威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个人利益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使他们的追求不可能与任何单一的道德目标相吻合。如果借助某种社会权威来强行实现这种吻合,那将不仅对个人自由选择形成可怕的极权主义约束,而且会由此伤害个人的道德良知。哈耶克指出:“只有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负责并且有牺牲它们的自由时,我们的决定才有道德的价值。”因此,在必须作出选择的范围内,我们“有安排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有责任依照自己的良心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道德观念能够成长,道德价值能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逐日得到再造的唯一气氛。”(注:《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02页。)
确实,如果不是倡导盲目服从,道德责任的承当必须以人格的独立为前提。对于这一点,现代大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一概否认。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始终强调,道德是在自由中被接受的,却不是被个人自由意志所创造的。个人主义伦理的一个难题在于,它主张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那种他想成为的人以及他所喜欢的生活方式,从而支持了一种价值相对主义立场。但是这个立场一旦流行开来,人们的道德判断就随之成为不可通约的了。在这种前提下推崇自由选择,其实践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演化为随心所欲。托克维尔批评个人主义“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最后沦为利己主义”(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25页。),原因即在于此。 贝尔指出:“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其好的一面是维护个人自由,其坏的一面则是要逃避群体社会规定的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为社会应做出的牺牲。”(注: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8页。)从这个意义来看, 个人主义作为组织良好社会生活的原则和方法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倘若个人自然欲望的释放确有施以道德约束的必要,那就应该到个人主义之外寻求某些富有建设意义的文化资源。但是个人主义本身能够做到这一点吗?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于是发出了进一步的追问:假如个人主义不包含或不充分包含提供道德约束的文化资源,它的负面效应将会达到什么程度?
三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反思历史。由于现代文明的成长,特别是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潜能的自由迸发,所以,当一个个“小我”摆脱传统纽带的束缚,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进步思想家都对此表示了肯定。历史进步等于自由创造,等于个性解放,等于反禁欲、反传统,成了一种流行的思维定势。但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却认为,这种思维定势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在他们看来,即使个人自利的原则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创造能量,若将这种能量的释放纳入一个健康的轨道,也必须借助另外一套原则的积极配合。这另外一套原则来自传统伦理。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以个人自利为原则的市场体系的最初运行,是稳固地靠在前市场社会的精神气质的肩上的。正是传统伦理所强调的责任、义务、信用、承诺、勤劳和节俭等等,通过对个人贪欲的限制,给初创阶段的市场体系的合理化和有序化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一种健康的市场规则的确立,与其说是纯粹的个人作品,不如说是对无拘无束的个人施以督导的产物。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那些世俗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人们接受而较少考虑其负面效应,就起源来说,也部分地在于它受到了影子一般的传统道德遗产的约束或支撑。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曾或多或少地把这种约束或支撑视为理所当然,因而未对它作过多的评论。但其后继者们却在传统道德遗产受到严重侵蚀因而也是最为需要的时候将它忽略了。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先于资本主义存在而被带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传统道德遗产,由于约束个人贪得无厌的需求和欲望,因而以弥补个人自利原则之缺陷的方式为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提供了限制性保护。就此而论,它不仅是市场体系的初始条件,而且是其持续存在的条件。“自由主义这些年来一直能不断存在下去,是因为它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始终是不完全的,得到古老的戒律和忠诚,以及地方的、伦理的、宗教的稳定模式的调节。未经此调节的自由主义是无法长期存在的。……自由主义对其历史性限制的胜利将是一场危机。”(注:参见《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8页。)
但难以逆转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勇猛地突破了在它看来不过是绊脚石的一切传统边界。它不仅把个人的自然欲望公开释放出来,而且动用各种各样的舆论宣传手段,给追求世俗幸福的功利原子式个体人提供缓解焦虑的祷文,进行洗刷负疚意识的心灵蒸气浴。经过不断地蒸发,个人主义逐步耗尽曾对其予以限制的传统道德遗产,它变得纯粹了,单一了,也缩小了,或者不如说膨胀了。结果,“我们的欲望成为一种我们必须尊奉的神谕圣言。”(注: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承认个人利益有一个专属于他自己的正当范围,但是,由于其批判矛头主要不是指向个人的过份自由,而始终是由社会督导和约束所带来的个人的过份不自由,因此,他们在生活实践中激起的文化效应,将趋向于一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托尔维尔指出:“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 ”(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 625页。)
文化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在封建体系和传统道德之间作出审慎的区分。按照他们的看法,以自由竞争为基本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打破封建体系的禁锢,但其合理、有序的运作,却离不开传统道德遗产的隐性支持。可是问题在于,当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主导性的价值观念获得文化霸权之后,不断膨胀的自负使它对于传统道德遗产提供的给养压根就缺乏意识。在它的心目中,传统戒规最好不过是某种不必要的负担,而最坏则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此要么对其漠然处之,要么就是有意的敌对。这样,在愈益偏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驱动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打破封建禁锢的同时,也把传统道德体系负载的价值意义一并抛弃了。于是它就按照自身逻辑卷入了一场“创造性的毁灭”的风暴(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5页。)。对它来说,任何创造都是对旧有界限的毁灭, 而且不毁灭旧有的界限就无法进行创造。虽然由于其使物质财富滚滚而来,这股风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但是熊彼特指出,成功背后隐藏着负面。因为它砸碎的前资本主义文化镣铐,同时也曾给它以必要的支持和庇护。而一当完全摒弃这种庇护,资本主义终有一天无法消受它成功的美酒,不仅醉倒,甚而中毒,以致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将因为自己的成功而一步步走向衰败:“在破坏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时,资本主义就这样不仅破坏了妨碍它前进的障碍,而且拆掉了阻止它崩溃的临时支架。这个以其残酷无情的必然性而予人以深刻印象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消除制度上的枯枝败叶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赶走和资本主义阶层共生的老伙伴们的过程,和它们共生在一起,原是资本主义图式的本质要素。”(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4页。)
四
从表现形式上看,文化保守主义者大都有一种浓郁的怀旧情绪。他们崇尚传统,敬重权威,对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显示出一种特殊的价值偏好。这种偏好使他们常常发出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中业已沦丧的感叹,因此,同那些迷恋独创性和新奇性的时髦男女比较起来,显得有些老派固执。但是,如果注意到个性自由浪潮已从经济领域的功利追逐扩张为日常生活领域的不断翻新的先锋实验,以致亵渎神圣演化成了一种流行的社会时尚,那么,我们又该承认,一种信护传统的稳重守成,在今天恰以不合潮流的方式彰显了自己的独特价值(注:现代个人主义有“功利型”和“表现型”两种基本样态。本文主要讨论了文化保守主义对“功利型个人主义”的批评。有关“表现型个人主义”的问题,留待另一篇文章作专门分析。)。
就否定的意义来说,这种价值主要表现为对个性自由的过份张扬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的批评。在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这种批评相当尖刻,甚至带有浓重的偏见。但这并不是勾销其历史合理性与价值正当性的充足理由。可以打个比方:文化保守主义像一个汽车制动器,它审慎地守护着道德边界;而希望达到充分自由的功利追逐和个性表现,则趋向于不断加大马力,冲破这一道德边界。塞西尔对两者相互关系的表达十分确切:“虽然乍看起来守旧思想似乎是同进步直接对立的,但它却是使进步变得稳妥而有效的一个必要因素。守旧思想的审慎态度必须控制追求进步的热情,否则就会招致祸害。人们在整个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首要的,虽然确实不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以正确的比例来协调这两种倾向,既不致于过份大胆或轻率,也不致于过份慎重或延迟。”(注:赛西尔:《保守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9页。)
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样一种良性的均衡?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对个性自由的正当督导,而且也涉及对专制强迫的有效防范。后一方面要求保守主义摒弃以极端方式整顿纪律的偏执诉求,对各种类型的外在强制和独断高压保持警觉。如果把这看作是一种思想上的老道与成熟,那么,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它不仅得益于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对话,而且有赖于对个人尊严及其正当权利的基本认同。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只有作为一种后个人主义或后自由主义哲学才能得到恰当的认识。其“约束自大狂”的主张,既不是政治偏激,也不是回到前现代,而是协调过去与未来,在个性自由和道德约束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一如贝拉所说:“虽然分离化和个体化对于摆脱过去的强权制度、解放自己是必要的,但为了避免走向事物的反面、引起自我毁灭,就必须用新的责任心和社会感去制衡分离化和个体化的倾向。”(注:贝拉:《心灵的习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16页。)说到底, 对传统的凝聚力保而守之,是为了使个性自由发展得更合理,更健康。“如果分离化和个性的精华即个人尊严和自主要得以维持,就必须实现一种新的社会聚合。”(注:贝拉:《心灵的习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29页。)这大略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实质所在。
标签:保守主义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道德论文; 商务印书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