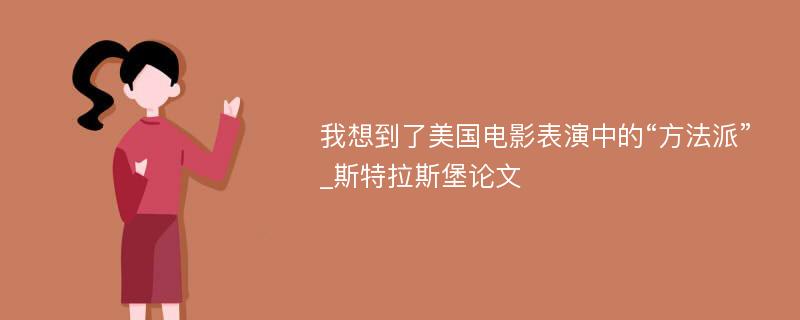
想起了美国电影表演中的“方法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电影论文,方法论文,想起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7月,我应邀作为中国评委参加了第十五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长故事片评委会(亦即所谓“大评委”)的评奖工作。担任这个评委会主席的是美国著名影星罗伯特·德尼罗。当时正处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倡“改革与新思维”的时期,苏美两国历经多年“冷战”之后,关系似乎有较大好转,美国就派出了包括众多影星、导演、制片人、影评人等共130余人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我感到,苏联当局将这一历来只由苏联人担任的“大评委”主席的职位让给美国人,可以视为对美方如此踊跃参加该电影节的一种“回报”,与此同时,也是对罗伯特·德尼罗本人的高度重视。罗伯特·德尼罗对我国电影界和广大电影观众说来并不陌生,他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主演的许多名片如《美国往事》、《猎鹿人》、《不可饶恕》等等曾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还感到苏方给予他如此殊荣,还因为他当时是美国“方法派”演员最重要的代表。
美国表演学派中的“方法派”是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原理培养出来的。其成员中,较年长的有马龙·白兰度、保罗·纽曼、詹姆斯·迪恩、简·方达等,较年轻的有罗伯特·德尼罗、达斯廷·霍夫曼、杰克·尼科尔森、萨利·菲尔德、梅丽尔·斯特里普等,这些演员主演的影片有相当大的数量都在我国公映过或“内部”观摩过,而他们不止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一殊荣,更为我国戏剧、电影和电视剧界所共知。时光荏苒,这些较年长的“方法派”演员多已先后作古,而所谓“较年轻的”如今也多已年近古稀,再不能为广大观众贡献其精湛的技艺了。然而,美国“方法派”的诞生、发展过程及其如何在电影表演中运用斯氏体系的精神和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的创作经验,仍然值得我国影视表演界加以研究和借鉴。
“方法派”的由来可远溯至上一世纪二十年代。1923—1924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率领莫斯科艺术剧院到美国巡回演出后,留下了剧院的两位年轻成员波列斯拉夫斯基和渥斯本斯卡娅,他们后来就在美国实验剧院开班讲授斯氏体系。按照斯氏体系当时的发展阶段,所着重的是心理技术,而外部技术及体现问题则很少谈论,更不用说进入三十年代后才得到发展的“形体动作方法”了。这个班上有一位学生,即李·斯特拉斯堡,他在1951年接任了创建于1947年,有“方法派的大本营”之称的“纽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研修所”的所长,在任长达31年之久,直到1982年去世。
李·斯特拉斯堡在他的回忆录《一场激昂的梦幻》中曾明确地指出:“(美国的)‘方法’是对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延续和补充。”他认为,多年来盛行于美国剧坛和银幕的“表演通病”有二:其一是凭“本色”表演,让观众看到的始终是演员本人的个性特征:其二是“装腔作势”,动作设计虽甚华丽,却缺少“生活的暗示”。所以,他像斯氏一样,强调演员在舞台上首先要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和行为举止,为他化身为角色准备内外部条件。
“方法派”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其焦点在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晚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对形体动作逻辑和形体动作方法的强调——在“方法派”表演和训练中应占什么样的位置。
争论主要是在波列斯拉夫斯基和渥斯本斯卡娅的两位高足,即李·斯特拉斯堡和斯泰拉·艾德勒之间进行的。在1931年创建团体剧院之后,斯特拉斯堡就把激情(情绪)记忆的运用当作体系的主要方面。他坚持要去探索下意识情感以寻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内心真实。团体剧院的另一创建人哈罗德·克莱曼曾说他“在情绪问题上简直像发了疯,任何其他东西与它相比都是次要的”。1934年,艾德勒在巴黎遇见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并在一个多月时间内不断向他求教。回到纽约后,她通过一系列的示范表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把重点摆在动作、剧本的情境和演员的想象,而不是演员的个人情感之上。因此,她和克莱曼都得出结论说:斯特拉斯堡对体系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准确”的。
然而,1951年斯特拉斯堡接任演员研修所所长后,他仍然继续注重于下意识的分析性探索和个人强烈经验的运用。据美国的一位斯氏体系研究者说,“体系的形体方面在这种修正中完全被抛弃了,而这种修正现在就以‘方法’而闻名”。
由此可以看到,斯氏体系与“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想象是表演的核心,并从剧本原文中寻求情绪的真实。斯特拉斯堡则从演员的下意识中寻求情绪的真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原先对内心技术和理性技术(剧本分析)的强调被吸收到“方法”里来了,而体系的形体部分则完全被忽视,并代之以分析性的考虑。照斯特拉斯堡看来,演员必须不受约束才能够达到情绪的真实。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这同样的情绪的真实是通过有内心根据的形体动作逻辑达到的,这一点,斯特拉斯堡却从来没有加以探究。
据这位研究者说,六十年代中期曾有一批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前来纽约举办过讲习班,着重说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38年去世之前就已放弃了激情记忆练习并认为形体动作方法是他晚年工作的高峰。他晚年追求的是内部技术和外部技术的统一。
与此相对照,斯特拉斯堡保持它对激情记忆以及心理分析探索的重要性的强调,因而被认为是“硕果仅存的对早期斯氏体系的美国式解释”。
纵观斯特拉斯堡所著《一场激昂的梦幻》一书,我也感到他所津津乐道的确实是体系早期讨论过的东西。但与此同时,我又不断地自问:“方法”既然与体系的后期成果有一大段距离,为什么却能训练出这么一大批优秀的电影演员呢?
此中原因,可能有这样一些:
一、在崇尚商业化、标准化、类型化的好莱坞的表演界,以内心体验为核心的斯氏体系毕竟给它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对情绪记忆的强调,对演员下意识生活的探索,演员自我与角色的融合(“生活于角色”)等等,所有这些体系早期阶段对演员所提出的要求对于增强银幕形象的可信性和深度显然都是有益的。
二、从演员的下意识中寻求情绪真实的方法,尽管很值得争论,在电影中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因为特写镜头表演会使场面的亲切性得到强调。
三、“方法派”演员们对于《演员自我修养》第一部《情绪记忆》一章所论述的内容都极为熟悉并身体力行。他们一般都能从“深入生活”中取得情绪材料。例如,罗伯特·德尼罗为准备拍摄《愤怒的公牛》,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拳击手一起生活。为准备《猎鹿人》,他在俄亥俄河谷的钢铁工人中生活,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为了演《慢击鼓》,他观察在一场棒球赛中职业选手是怎样放松的,并“在自己的房间里练习,体验他们的吊儿郎当”。
斯氏体系不论在前期或后期,体验问题始终是其核心。“方法派”掌握了这个基点,是他们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保证。如果他们也能运用形体动作方法,是不是可以使他们更快、更有效地接近角色并进入角色呢?
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美国戏剧和电影表演中,“方法”已成为一股主流,在美国整个剧坛和影坛占据主导地位。
这首先应归功于演员研修所领导人之一、著名戏剧和电影导演艾利亚·卡赞。他运用“方法”执导的《欲望号街车》(1947)和《推销员之死》(1949)均获巨大成就,前者同时获普利策奖和评论界奖,并于四年后搬上银幕即获奥斯卡金像奖。剧评界认为,这些演出风格的特点是“表演中的近似自然主义与布景中的风格化相结合”。此后,由着重于强烈的心理真实的表演和删除枝蔓而保持现实主义轮廓的视觉元素这两者构成的“戏剧化的现实主义”风格,在美国演剧界风行一时,并造就了诸如马龙·白兰度等一批杰出演员。
在整个五十年代,“方法”在现实主义的演出中起了主导作用。“方法”已从三十年代的“低调自然主义”演进为五十年代演员研修所时期的“火爆”风格,从“散文式的精确”发展为“有节奏的力量”;这对于上演田纳西·威廉斯、阿瑟·米勒、威廉·英兹等当时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作品是十分合适的。
然而三十年代下半期以后,美国戏剧划分为百老汇与地区剧院的商业性演出和外百老汇与外外百老汇的非商业性实验。与此同时,法国安托南·阿尔托的“残忍戏剧”和波兰耶日·格洛托夫斯基的“贫困戏剧”也开始对美国非主流的实验性演剧产生影响。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分析剧本和人物的概念相反,阿尔托寻求通过冲击去净化观众的情感。而格洛托夫斯基虽然声称自己是“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成长起来的”,“他对他自己早期工作的辩证关系使他成了我个人的理想”,但他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提出的主要的方法论问题,解决的途径却大不相同,有时甚至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格洛托夫斯基的演员与其说是表演“传统的角色”,毋宁说是表演他自己,但仅仅通过形体技术来创造各种假面,并寻求一种使他自己和观众都卷入的神秘的经验。
在这二三十年间,与戏剧实验的非现实主义恰成对照,电影和电视却仍然讲求自然逼真性,甚至是“自然主义”的。这使得“方法”的技术对于现实主义表演盛行的影视媒介完全适用。以卡赞的工作方式为例。他严格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要求,先是分析剧本的结构,然后通过对那种分析型结构的认识来构成各个场面。他就此作出解释说:“‘方法’的想法就是把剧本当作伸展着众多树枝的树干来考虑,然后你让一根树枝把你引导到另一根树枝,慢慢地你达到剧本的第一个高潮。这个想法就是,如果你是心中有数地执行所有的任务,你就终究能执行这些任务。……所以当我准备拍摄影片时,我也试图通过词语来抓住那主要任务是什么,并用一个句子把它概括出来。”他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中有一个基本元素在他导演影片中的演员时最为有用,那就是抓住“想要”这个关键性字眼。“你为何来到这里?”“你走来走去想要得到什么?”他指导演员时总是要强调在这个场面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不仅谈论它,有时还进行即兴创作。于是,“当那场面开始时,他们就完全进去了,而不单纯是讲出指定给他们的台词”。
卡赞及其他“方法派”导演和演员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相当出色的影片,除《欲望号街车》外,《码头风云》(1954)、《无因的反抗》、《伊甸园东方》(1955)、《十二怒汉》(1957)、《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8)等影片都很有名,并使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等红极一时。
六十年代的好莱坞着重于表现更可认同的主人公和反英雄。从表演角度看,这是达斯廷·霍夫曼、杰克·尼科尔森、艾尔·帕西诺等人的时代,他们大都其貌不扬,用霍夫曼的话说,“曾经是明星制度的牺牲品”。达斯廷·霍夫曼在《毕业生》(1967)中首先为“长相平常”但自然可信的表演者踏上影坛打开了大门。从《毕业生》一直到前些年获奥斯卡奖的《雷曼》(又译《雨人》),他创造的许许多多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对我国影剧界说来并不陌生。霍夫曼认为,他的这种适应性是“‘方法’训练的直接结果”,因为就学于李·斯特拉斯堡使他成了这样一个多面手:“我在李·斯特拉斯堡那里学习时,受到他很大的影响:他总是不断地说:‘不存在什么翩翩少年或天真少女或流氓或英雄式领袖人物这样的东西。我们是所有的性格……’”
长相平常或其貌不扬的演员与英俊漂亮的明星的对立在六十年代达到了高峰,而且延续至今。“方法”的运用对这两种实践的冲突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没有“方法派”观点的影响,七十年代诸如脸上长着雀斑的芭芭拉·史翠珊(曾主演《回首当年》)和被称为“丑小鸭”的塞茜·斯帕塞克(曾主演《矿工的女儿》)等恐怕很难在好莱坞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方法”派演员中并不乏漂亮影星,如保罗·纽曼、萨利·菲尔德等,这里主要问题是:按照斯氏体系和“方法”的观点,任何演员都应创造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不是热衷于表现自己或只演一定的“类型”。
说“方法派”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电影表演界已占据统治地位,是一点也不算过分的。仅从1970年至1984年,演员研修所成员就获得过七十次以上奥斯卡最佳表演和最佳导演金像奖的提名。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成员由于在电视剧中的优秀表演而获得由五十多个国家的新闻记者每年一度投票评选的金球奖,以及美国电视艺术科学研究院的持续不断的提名。“方法派”虽然人数不多(据1984年的统计数字,各个时期“在册”的共六百余人),但能量极大,已足以决定当代美国电影表演的基本面貌。
“方法派”在当代美国电影表演中取得特别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斯氏体系的一些基本原理比较符合电影表演中现实主义的需要。体系为演员在特写镜头表演中达到内心现实主义和创造一种个人的亲切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础,适应了近三四十年来许多影片中体现戏剧性主题和塑造人物性格的风格的要求。“方法”虽然对体系作了若干修正,但体系的一些基本元素仍然完整无缺地在“方法”中延续了下来。演员的核心体验仍然是以原先的朝向剧本规定情境的想象为基础。“方法”后来强调对来自演员个人生活的情绪进行推理性的体验,这与斯氏晚期的工作方法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差别,而对于注重演员个人亲切感和个人魅力的银幕表演则更为有效。
在当今美国表演界,斯氏体系的一些原理也被演员研修所以外的大量演员、导演和表演教师所广泛运用。从纽约到洛杉矶,表演教师和职业演员们都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观点为基础的“剧本分析”和“人物发展”的某些方面提供训练。他们对体系原理作出了各自的解释,有时与“方法派”的解释颇有一段距离,这是很正常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生前就告诫过人们:绝对不要把他的体系奉为“金科玉律”,应该根据本民族和艺术家个人的特点而灵活加以运用。
然而,“方法派”演员们由于受过系统训练毕竟更接近于斯氏体系的精神实质,也在电影表演中取得了更多的成就。我们可以引述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言论来说明“方法”对他们的意义。继斯特拉斯堡之后出任演员研修所所长、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保罗·纽曼,把他“关于表演所知道的一切东西”都归功于研修所。达斯廷·霍夫曼认为“方法”在他的所有工作中“灌输了注意力集中和控制”。简·方达宣称她本不想去继承他父亲亨利·方达的事业,“一直到就学于李·斯特拉斯堡时才改变初衷”,她发现“方法”具有深刻的解放作用。雪莉·温德斯认为研修所是“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表演训练资源”。
关于具体运用“方法”的经验和体会,他们也有颇多论述。达斯廷·霍夫曼提到,在准备《克莱默夫妇》(1979)时,为他的角色作了大量的即兴创作和激情记忆练习,从而使他对角色有完整的内心视像。霍夫曼在接下来的一部影片《宝贝》(1982)中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即兴创作时期去探索他所扮演的女性人物的复杂性格,这个即兴工作阶段在编导参与下延续了三年之久。简·方达在准备《归来》(1978)、《中国综合症》(1979)、《金色池塘》(1981)等片中的角色时,运用了“方法”所提供的情绪卷入和性格化的技术。她采用的激情记忆技术和个人替代物帮助她进入角色的内心生活:“说到我处理表演的方法,就是要把你的全身心都贯注到纸上所写的东西里去,给它带来生命。”保罗·纽曼在扮演《冷面路克》时在农村生活了很久,“沉浸于周围环境之中。最后我跟一个卖土豆的商人到处转悠,来观察他的讲话和行为方式”。纽曼的妻子提到“他读的剧本上总是满篇注解,他把什么东西都写下来进行分析”。纽曼总是设法找出他的角色的动机和动作的真实性,然后用激情记忆技术“轻轻敲进他的情绪储备库”。
很显然,不同演员都会以不同方式处理创造角色的问题。每个演员都会找到独特的东西以便在探索形体和内心真实时发生作用。“方法”所运用的技术为这种探索提供了一整套合乎逻辑的路数。有些演员从分析剧本和角色开始他们的准备工作,以找到形体化和行为现实的提示。他们可以运用观察的技术勾勒出对角色形体和言语上的探索,最后,他们还可以通过个人替代物和激情记忆技术的结合来使行为现实内心化。各种艺术手段都听凭他们调遣:他们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技术来应付每次新的挑战。
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一再强调要反对“一般的情绪”、“一般的动作”等等一样,“方法派”也很注重角色创造工作的“选择性”。例如,罗伯特·德尼罗谈到需要从“方法”的总体中作出最有效的选择时就说,“这就像任何别的事情一样。开始时你学习规则,然后你认识到这些规则什么地方可用或不可用,认识到实际上存在着几百万种行事方式。”他认为,演员应该做出选择,而最后的选择将决定最后的表演效果。达斯廷·霍夫曼也强调,选择和实验应在准备阶段充分加以探讨,这样,结果才会显得自然,而不是“表演出来”的:“我说演员们不应该去‘表演’。场面应该构成这个样子——你不必去‘表演’……就像黄油那样,他已经摆在那里了——所有工作都必须事先做好——所以你就不必坐在那里去硬挤情绪。它应该自然而然地流泻。”
总的看来,“方法派”电影演员们接近角色的方法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制定的那些发展的技术基本上保持一致:理性工作——即深入分析剧本和角色:内心技术——即探讨情绪记忆、想象、观察、注意力集中和自我感觉等等的运用;外部技术——即通过身体运动和声音使角色形体化。最终结果就是所有心理和形体行为的有效的、统一的表达。
斯氏体系为演员们达到在舞台和银幕上的真实表演提供了坚实的框架。七八十年来它在美国虽得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毕竟通过“方法”影响了美国电影表演的进程。“方法”及体系的其他变种已被吸收进美国电影的主流,成为美国那些最著名的演员、导演和教师们的创作催化剂。
标签:斯特拉斯堡论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 演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