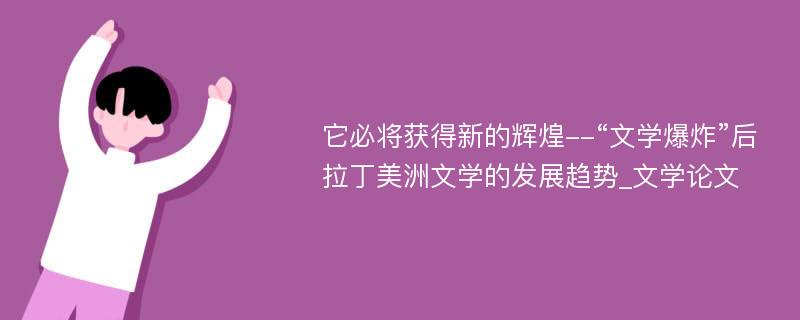
它必将获得新的辉煌——拉美文学在后“文学爆炸”中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拉美论文,发展趋势论文,辉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小说创作向内转
60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震撼了世界文坛,令世人刮目相看,然而拉美文学到了七八十年代即后“文学爆炸”,是仍大放异彩,光辉四射,还是夕阳的余辉,黄昏的灿烂?
70年代,拉美的政治形势明显地向右转,乌拉圭总统进行“自我政变”,镇压左派政党;阿根廷的庇隆上台,倒向右派;智利总统阿连德被军人推翻,阿连德本人以身殉职;奉行“西方主义”的巴西军人遂与美国结盟,投靠美国。独裁政权和轮回的怪圈死灰复燃,出现了局部性的倒退局面。虽然有些国家如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抵制倒退的浪潮,但拉美的政治气氛是沉闷压抑的,仿佛乌云遮住了大半个天空,生活在这种氛围中的拉美作家,其心境与欧美现代主义大师颇有同病相怜之感,对欧美现代主义表现的生活空虚、精神苦闷、前途渺茫、信仰丧失、理想破灭有一种认同的取向,他们更多的是寻找自我,发泄内心的苦闷,表述人生的感触,对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的关切心情在淡化、减弱,他们不再像60年代作家那样以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为其作品的主题或创作的题材。这种政治局势的向右转,引发作家创作的向内转,这是后“文学爆炸”不同于“文学爆炸”的重大变化。
在拉美文学的嬗变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常被人忽视,这就是宿命论。宿命论作为拉美人的集体无意识已深深地烙印在拉美人的灵魂中,就以60年代“文学爆炸”精英们的作品而论,宿命论仿佛时隐时现的幽灵摆布着人物的命运:《百年孤独》中身经百战的奥雷良诺上校,晚年在做小金鱼和熔化小金鱼的百无聊赖中渡过自己的余生,五代世家赖以生存的马贡多小镇,“被飓风一扫而光,并从世人的记忆里永远消失”;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中克罗斯之死;略萨的《世界末日之战》中与政府军抗衡的村民们男女老少全部壮烈牺牲;鲁尔福的《彼德罗·巴拉莫》中科马拉村的居民全部死光;多诺索的《淫秽的夜鸟》中的主人公翁伯特仿佛在迷宫中顽强地追求,却永远不能如愿以偿;柯塔萨尔的《彩票》中乘船航行的人们,不知道前往何方。这些作品在对社会无情批判、严厉谴责的同时,流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宿命论思想,这就是表现在作品中的悲观主义。“人被禁闭在模糊的迷宫里,被无情的、不可逆转的时间所吞噬。”这不仅是对《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的说明,也是对拉美新小说中悲观主义的有力诠释。克罗斯、翁伯特、布恩底亚家族、村民、乘客,无不是生活在迷宫里迷惘、惶惑的匆匆过客,他们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社会的腐败、道德的堕落,只能听之任之。他们最终将被时间所吞噬。这种宿命论思想无疑将对处于彷徨、徘徊中的后“文学爆炸”作家产生消极的影响。
后“文学爆炸”作家在创作上的向内转,和他们固有的宿命论观点使他们的小说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地沉湎于个人的痛苦、骚动与不安,他们在孤独中不能自拔,与寻觅中找不到出路。但他们仍直面人生,坚持不懈地探寻,终究没有成为欧美文学大师笔下的甲壳虫,尽管他们中有些人的结局是悲哀的。
二、富有生命力的多样化文学流派
后“文学爆炸”的小说虽向内转,但作家对文学探索的势头并未减弱,各种文学流派依然各呈异彩,小说种类之庞杂不逊于文学繁荣的60年代。在种类繁多的小说中,成绩斐然的有墨西哥作家德尔帕索的历史小说、阿根廷作家普伊格的性小说、戴维·比利亚斯的政治小说、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雷斯·加尔德亚萨尔的谴责小说、古巴作家阿雷纳斯的幻想小说、萨多依的语言实验主义小说、智利作家斯卡尔梅达的诗意现实主义小说、秘鲁作家孔格拉因斯和委内拉作家冈萨雷斯的现实主义小说、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德尔帕索的《墨西哥龙虾》是后“文学爆炸”的一部杰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不同视角反映墨西哥的现实生活。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浑名“龙虾”,不慎掉入海中,未被大海淹死,却死于警察对学生示威游行的镇压。但这部小说有两个显著的特点:语言实验和黑色幽默。卡彭铁尔在《探索与差异》一书中写道,“拉美小说的正统风格是巴罗克。”《墨西哥龙虾》的语言正体现了拉美的巴罗克风格。这种语言实验是在“拉美新小说反对我们虚假的、封建的起源和虚假的、不合潮流的语言长期板结中出现的”。《墨西哥龙虾》的黑色幽默又不同于《百年孤独》的幽默,后者的幽默是加深对人、人的生存条件的认识,前者是一种愤慨,对镇压1968年学生运动的抗议。这部小说虽然重在从宏观上对墨西哥社会做全面的描写,但对人的生存方式也作了有益的探讨。小说中的人物瓦尔特的儿子认为,“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世界还不算坏。”可是医生的看法却与此相反,他觉得生活在捉弄人,谁也逃脱不了孤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使在生活的剧变中仍显出不同人物各自不同的心态。
《墨西哥的龙虾》出场的人物有128人之多,其中不乏世界大文豪莎士比亚、大仲马、巴尔扎克、左拉等。然而,德尔帕索的近作《帝国轶闻》(1987)涉及的人物有数百人,远胜过《墨西哥龙虾》。这部六十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在拉美文学史上实属罕见,不愧为是一幅色彩斑斓的伟大画卷。《帝国轶闻》是一部历史小说,叙述墨西哥第二帝国的兴衰史,但作者的真正用意是通过历史描写活动于历史舞台上的人:被拿破伦派往墨西哥的奥地利大公、墨西哥第二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亚诺和他的妻子卡洛塔;战胜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墨西哥英雄华雷斯。这些人物在历史的演变中扮演他们各自的角色:马克西米利亚诺被捕、处死;卡洛塔去欧洲求援,失败后变疯;华雷斯在战争中赢得胜利,成了民族英雄。历史是无情的,失败者,抑或胜利者均由历史来裁定,而人是有情的,在全书23章中,作者用了12章叙述疯女人卡洛塔对随着帝国的覆灭而被处死的马克西米利亚诺的拳拳之心,她的爱、她的恨、她的悲喜、她的悔怨使冷酷的历史变得丰富、多彩,增添了些许的人情味。这是因为作者是作家,他用他的感情,他的真诚去写历史上的人,而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冷眼旁观、无动于衷地叙述历史。然而,小说中的另外11章完全是纯客观的叙述,按照时间的顺序叙写了墨西哥第二帝国兴衰的全部过程。小说的中心人物不是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亚诺,也不是民族英雄华雷斯,而是疯女人卡洛塔,通过卡洛塔之口,娓娓动听地道出19世纪墨西哥一段奇特的历史。全书在卡洛塔的声音中开场,又在卡洛塔的声音中结束。卡洛塔的独白,她的意识流动,她的幻觉,她的奇想组成了“多声部”的乐曲。这种形式的多样、内容的庞杂,全方位地再现了墨西哥社会的方方面面。各种人物和历史事件穿插在小说中,绘声绘色的人情世态把历史小说化了。
如果说《帝国轶闻》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表现了社会中的人,阿根廷作家普伊格则从性的视角来把握社会。普被西班牙视为禁书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1973)的手淫、性虐待和鸡奸、《蜘蛛女之吻》(1976)的同性恋、《天使的阴阜》(1979)的性欲折射了社会存在的问题。
性描写在拉美新小说中随处可见,不足为怪。普伊格无视性的禁忌,把人的性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达到抨击社会弊病的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中的女主人公受“高等人的操纵和主宰,他们在她身上拥有一切的权利,包括对她的性虐待”;《天使的阴阜》中的安娜感觉到“大腿间的软弱点”,因而受到男人的统治,故天使没有性欲,不受他人伤害;《蜘蛛女之吻》展示人的性压抑和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在普伊格小说的性描写中蕴含着一种性的对抗、受侮辱受损害的人的追求和愿望,反映了作者对弱者的深切同情,普伊格的小说通俗易懂,情节引人入胜。《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用侦探小说的形式抒写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蜘蛛女之吻》中贯穿全书的六个电影故事使小说异彩纷呈,读来兴味盎然;《丽塔·海华斯的反叛》(1968)用日记、书信、对话、独白等创作手法叙述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红红的小嘴巴》(1969)以连载小说形式描写一个患肺病的青年的恋爱生活。普伊格的小说既有高雅文学的严肃,又有通俗文学的情趣,它的高雅体现在主题和题材的严肃性,通俗则在于技巧的多样性、情节的丰富和语言的大众化。雅中见俗、俗中有雅是普伊格创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文学创新的一种尝试。无庸讳言,普伊格小说的性描写过于具体,渲染一些色情的情节,对同性恋这一现象似乎同情多于批判,以至给人一种为同性恋辩解之感。
在创作风格上与普伊格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是墨西哥作家豪尔赫·伊巴尔贡戈依迪亚(1928-),他用通俗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他的小说《八月的闪电》(1964)、《杀死的狮子》(1969)、和《两桩罪案》(1979)等幽默、风趣,情节复杂、多变,既有题材的惊险,又有作者的大胆想象。这种熔雅与俗于一炉的小说在后“文学爆炸”小说向内转时,不啻是一种新的创作动向。这类小说与现实主义流派的小说有着某些差异,它迎合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激发了读者的阅读热情,在调侃、讥讽现实的同时反映了现实。
阿根廷作家戴维·比利亚斯熟悉军人的生活,他创作了以军人为题材的一系列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阿根廷社会变化关键时刻的人与事,反映了阿根廷军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心态和失落感。
《正视》(1962)描述了1919年1月军队对工人罢工的镇压。门迪布鲁是以智慧、豁达著称的将军,杨托诺是个心地善良的记者,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点:对现实的不满。将军对军队、婚姻和他的子女感到沮丧;记者对报纸感到失望。他们都是诚实的人,诚实使将军站出来反对庇隆,诚实使记者继续他的民意测验,尽管受到上级的威胁。小说的基调是痛苦的,因为“某种东西”在侵独着将军,也侵独着记者。《骑在马上的人们》(1967)叙述一个军人家庭的衰亡。埃米利奥·戈多伊作为军人家庭的一员,目睹他的父亲、军队的首脑,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都是“一些幸福的机器人”。埃米利奥和阿根廷军队参加在秘鲁的军事演习,这场演习以巴拉圭几名士兵的死亡而告结束。对此,埃米利奥深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他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适逢他的兄弟马塞洛因离开军队而自杀。这使他惘然若失,不知如何对待面临的现实。《狗群》(1974)则描述了巴拉圭战争期间军人的嫉妒的仇恨。
哥伦比亚作家阿尔瓦雷斯·加尔德亚萨尔(1945-)的谴责小说与戴维·比利亚斯的政治小说相比,更贴近现实,对现实的反映也更为深刻。阿尔瓦雷斯是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大多以他的故乡图鲁亚镇为背景,反映图鲁亚镇在不同时期发生的事件,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社会性,小说中的人物也来自他的出生地图鲁亚镇。
他曾创作了描写政治暴力斗争的三部曲《博亚卡的公园》、《秃鹰并非天天埋葬》和《教皇的毒蛇》,以后又创作了反映社会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暴力斗争的《哈里斯科》。阿尔瓦雷斯自称,“我很难摆脱暴力,如同我不能摆脱我的小说主题孤独和死亡一样。”阿尔瓦雷斯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精确地把握了哥伦比亚的脉胳,并加以出色的描绘。他的名作《达贝瓦》(1973)描写一个偏僻的小镇在发生自然灾害后陷入孤立无援的悲惨境地。他的另一部小说《莱昂·马丽亚回来的日子》(1969)因涉及图鲁亚镇莱昂·马丽亚家族的丑闻,其子女要控告作者,迫使阿尔瓦雷斯离开了家乡。阿尔瓦雷斯对文学的追求矢志不渝,积极参加到社会生活中去。他对一些人把文学当作消遣嗤之以鼻,他认为他创作的是谴责小说,“我不想在谴责中让人们开心,而是使他们觉悟……”他认为他是艺术贵族坚定的敌人,“文学一刻也不能离开生活的社会。”对于文学的模仿和影响,阿尔瓦雷斯也自有高见,他认为“事物都是不相同的,至于影响,我们永远也不能否定。因此,需要对文学进行研究,不去重复既有的东西。必须避免落入俗套,清除以前作品中无用的东西,不至于重蹈复辙。”阿尔瓦雷斯虽然受到他的同胞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但他另辟蹊径,同时又汲取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从而加强了小说的深度和力度。
古巴作家雷纳尔多·阿雷纳斯(1945-)的小说创作完全不同于上述作家的文学风格,他的小说是他想象的产物,故他以幻想小说而声名远播。阿雷纳斯的第一部小说《黎明前的赛莱斯蒂诺》(1967)描写少年的赛莱斯蒂诺贫穷饥饿,生活中缺乏爱。但他喜好在树皮上写诗,精神上的富有与生活的穷困形成鲜明的对照。阿雷纳斯虽以想象而著称,然而塞莱斯帝诺这一人物形象并非毫无根据,与作者的少年时代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阿雷纳斯从小就酷爱文学,16岁来到首都哈瓦那,结识了诗人埃利塞奥·迪耶戈和小说家莱萨马·利马,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的文学创作才得以提高。《黎明前的赛莱斯蒂诺》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但真正全面地展开他的想象力的小说则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迷惘的世界》(1969)。这部小说以墨西哥著名爱国教士塞尔万多·特雷莎·德·米耶尔(1763-1827)为典型,描写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墨西哥社会。塞尔万多在墨西哥独立战争前后为民族的独立、为“被欧洲人奴役的美洲”而奋不顾身。他曾从几所不同的监狱里逃跑,但最终逃不出自己的生活,成为自己生活的囚徒,流露出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作者把历史现实变为想象的寓言式的现实,因而《迷惘的世界》被视为一部反现实主义的小说。为了不囿于历史的时间顺序的约束,作者使用了三个平行的叙事者;一是“我”,塞尔万多本人;另一是“你”,想象中的人;再者是无所不能的第三者,对第一、第二人物叙述的补充和评说。这样,作者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任意驰骋他的想象力。他的第三部小说《雪白的臭鼬宫殿》是《黎明前的赛莱斯蒂诺》的续篇,作者用塞莱斯蒂诺长大成人后的眼光,看待自己家族和历史,重新组合已消失的现实和活动于美洲殖民地时期的人物,表现了作者惊人的想象力。
在后“文学爆炸”中,有些作家,在创作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古巴萨多依的“语言实验主义”、智利作家斯卡尔梅达的“诗意现实主义”是后“文学爆炸”作家在文学探索中的创举,尽管这两种新的文学流派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大。
萨多依语言实验主义的力作《眼镜蛇》(1972)是语言的一种实验,作者追随法国符号学家巴尔特研究语言的产物。小说描述了“眼镜蛇”变成了女人后在游览西班牙和摩洛哥时被人阉割,后在远东死于非命。这部小说不仅内容是荒诞的,而且形式也是变形的,没有悬念,没有情节高潮,内容与形式形成反传统的统一体。这种形式的变形也反映在语言上,萨多依认为,语言可以在作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既能反映人对世界事物的感受能力,又能表达文本中所没有的含义。
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1940年出生于智利,原籍南斯拉夫。斯卡尔梅达曾积极支持阿连德政府,并在文学部门担任要职。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政权被颠覆,斯卡尔梅达被迫流亡德国。斯卡尔梅达于1967年从事文学创作以来,发表了十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最为著名的有短篇小说《热情》(1967)、《屋顶上的裸者》(1969)和长篇小说《我梦见白雪在燃烧》(1975)。前两部小说均获得古巴美洲之家文学奖,后者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学。斯卡尔梅达主张作家的创作要贴近现实,反映现实。他作为一个流亡作家,尽可能地向世人介绍智利军人违背人民意志的倒行逆施,抨击政变当局镇压人民的暴行。《我梦见白雪在燃烧》从不同的视角生动地剖析了智利社会各个阶层在动荡的局势面前的复杂心态。斯卡尔梅达认为,为了尽善尽美地叙事状物,表现现实,作家要用优美的文笔,酣畅地把生活的底蕴表达出来,既要忠实生活,又富有诗意,这便是斯卡尔梅达的诗意现实主义。
在后“文学爆炸”中,致力于现实主义创作的有两位作家,一位是秘鲁作家恩里克·孔格拉因斯(1932-),他以叙写拉美的贫困化问题见长;另一位作家是委内瑞拉的阿德里亚诺·冈萨雷斯·莱昂(1931-),他塑造了拉美小说中不多见的城市游击队的形象。拉美的贫困化和城市游击队是拉美屡见不鲜的现象,但专以这两个社会问题作为题材写出的小说可谓凤毛麟角。在拉美小说中,德尔帕索的《何塞·特里戈》、多诺索的《加冕礼》和《这个星期天》、加门迪亚的《居民》都有对拉美贫困化的描写,但只有阿格达斯的《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才真正深入到拉美贫困化中去。恩里克·孔格拉因斯的《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的死亡》(1958)与其他描写拉美贫困化小说所不同的是它没有其他作家流露出来的悲观主义,而是给人们一种希望。这部小说以秘鲁首都利马的一个大垃圾场为背景,这个背景象征着人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小说主人公马鲁哈在垃圾场附近的一家洗瓶子店里当炊事员,店主从利马街头绑架一些疯子作为他的劳动力,马鲁哈则想利用一帮无赖,在适当的时机攫取这片商店的财物和这些疯子。她认为人的自身可以达到某种平衡,作出“完善和超越自己的努力”。这就是马鲁哈的人生价值。所以,她对金钱、对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感兴趣,也不满足简单的性欲,她要成为洗瓶子店的主人。为了发挥她内在的潜力,锻炼她的性格,肯定她的人生价值,曾有所动作,但都失败了。然而,她并不气馁,运用她的智慧和勇气征服了那些无赖们,从而发现她自身的力量。小说描写的虽然是垃圾场里以废品为生的人们,但作者的意图并不在对这种状态的描写,而是通过对马鲁哈抓住机遇的叙述,证明自身的价值。作者在叙事过程中,过多的评论和人物的心理描写,削弱了艺术的感染力。这部小说对拉美新小说的贡献在于运用了恐怖主义,这在拉美新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拉美新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城市游击队的形象,这是因为城市游击队是拉美现实的客观存在。在卡彭铁尔的《追踪》和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中都留下了城市游击队的痕迹。但对城市游击队进行深入描写的却是冈萨雷斯的《携带的国家》(1968)。小说以一个下午和部分的夜晚开始,并逐步向刚刚的过去延伸。主人公安德烈斯在刚刚过去的政治游行中接受了战斗的洗礼,然后时间又向更遥远的过去发展。叙述了在遥远的过去里,安德烈斯数代人的境况。小说从安德烈斯的旅行开始,通过他在城市和农村生活的转换,情节的不断发展,把安德烈斯心理的(旅行中的感受)、社会的(政治行动)、历史的(城市与平原的联系、农村向城市的移民)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个城市游击队员的完整形象。安德烈斯作为一名有追求的热血青年,对统治者的卑鄙行径义愤填膺,但在行动中又有一种害怕、孤立、失败的感觉。这反映了作者对城市游击队是否能取得成功产生了怀疑。小说还叙述了政治压迫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这正是作者内心的坦露和对社会的批判。
拉美特有的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在60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使拉美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七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流派并未向下滑坡,跌入低谷。因为继马尔克斯之后,又涌现出一些魔幻现实主义新秀,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短短的数年内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幽灵之家》(1982)、《爱情与阴影》(1984)、《月亮部落的夏娃》(1987)、《月亮部落的夏娃故事集》(1990)。《幽灵之家》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回忆录。因为这部小说原是作者写给外祖父的书信,后来才汇编成书;书中的人物大多以自己的亲属为原型,书中第一个出场人物罗莎是作者的姨婆,书中的克拉拉是作者的外祖母,正如作者所言,这部小说“讲着我们一家人的故事”。《幽灵之家》是《百年孤独》的再现,描绘了伊·阿连德称之为“近年来,我们美洲的历史”。因而作者故意省略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使读者从拉丁美洲的整体来思考拉美的现实,向读者说明《百年孤独》中的马贡多小镇不仅存在于哥伦比亚,在智利、在拉美其他国家也有类似马贡多那样封闭、落后、“从世人的记忆里永远消失”的小镇。这种整体的认同感也见于《幽灵之家》与《彼德罗·巴拉莫》情节的相似性。《幽灵之家》中的埃斯特万·特鲁埃瓦的《彼德罗·巴拉莫》中的彼德罗·巴拉莫都是十恶不赦的人物,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凌辱妇女,有不计其数的私生子。但他们不是生就的恶人;特鲁埃瓦对反对过他的彼德罗第三在危急时给予救援,帮助他逃出国外;巴拉莫小时是个顺从、听话的孩子,对欺人的行为有逆反心理。但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不足以遮掩他们给人间带来的黑暗。
伊莎贝尔·阿连德承认曾受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但她并不刻意地去摹仿《百年孤独》,“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作家是不会有意识地接受他人的影响的。”她的名作是在炽热的感情、强烈的愿望促使下写成的。《幽灵之家》写了她的家庭、她的祖国、她过去的世界。书中的魔幻情节如克拉拉的意念和《爱情与阴影》中埃万赫利娜的癫痫所产生的某种特异功能不是作者的凭空编造,而是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的,“这里所展示的一切都是事实。”《幽灵之家》是继《百年孤独》之后的一部魔幻现实主义杰作,伊莎贝尔·阿连德不愧为魔幻现实主义在后“文学爆炸”中的杰出代表。
在后“文学爆炸”中,一大批文学新人沿着前人的足迹,继往开来,创作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其实,这些新秀并非初出茅庐,虽然其中不少人出生于40年代前后,他们在拉美文学辉煌的60年代便有作品问世,但当时泰山压顶,名家的光辉遮住了他们的亮光。
可以相信,在后“文学爆炸”中,笔耕不辍的老作家和具有创新意识的新作家的共同努力必将使拉美文学获得新的辉煌。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智利总统论文; 小说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蜘蛛女之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普伊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