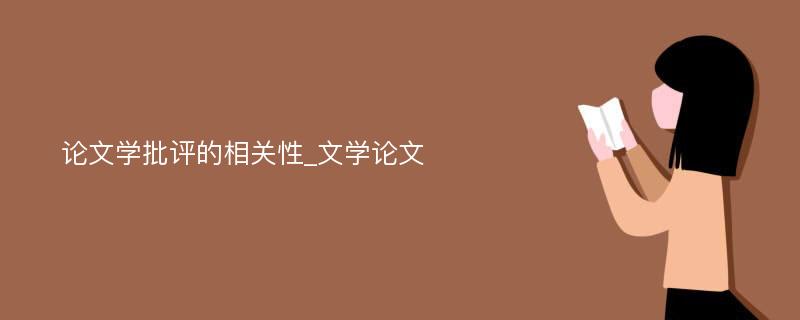
论文学物性批评的关联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性论文,批评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理论批评悄然展开了物质性转向运动。理论批评的内容发生了深刻转换,从语言、话语和文化的内容转向了“物质性、生物学和特别政治性的内容”(Elliott and Attridge 3);而从物性维度阐发诗学问题,已然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趋势之一(张进146)。来自不同理论谱系和批评传统的研究者从各自角度聚焦文学的物质性,彰显出文学物性批评的若干向度,并引发了对各种物质向度之间关系问题的重新考量。已然取得的研究成果,或阐发文学语言“能指的物质性”和文本本身的物质属性,德·曼的“铭写物质性”理论批评是其代表;或探讨新马克思主义式的唯物主义物质性,强调文学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事实条件之间的关联,其理论要旨在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论”中得到拓展;或讨论文学感知主体的物质性,即审美经验藉以发生的主体身体的物质性,其主要倾向在当前的身体美学和“赛博形象”研究中得到集中呈现;或考察文学表征对象、经验客体以及经验于其中得以发生的对象世界的物质性,其观念取向在当前声势浩大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得到全面表达。本文旨在梳理剖析初现端倪的文学物性批评诸向度的内涵特征,研究其间复杂的“事物间性”关联,彰显新世纪文学观念从“人性的表征”向“物性的体现”转换的理论轨迹。 一、文学语言能指和文本的物质性 自古以来,词与物一直被视为“致命的天敌”,但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新式文学理论则认为词与物“能够融合”,“每个人”都“能够读懂物”(孟悦 罗钢 83)。“物”不是因为反映于话语而被人读懂,而是由于物已然自行安置在人类精神之中而成为一种“物话语”,这种话语本身具有物质性。这一观念转变,开启了从物性维度解释文学语言能指的新路径。 能指和语言本身的物质性的观念,在索绪尔语言学、俄苏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理论批评中都得到了持续的强调。索绪尔的语言学反对语言仅仅具有描述性(语言仅仅是事物的名称)的思想,认为“语言是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可以被理解为能够产生那些一度被认为仅仅能够理解的事物”(麦高恩17)。俄苏形式主义集中关注文学作品自身的“物质现实”(the material reality),像检查机器一样检视文学文本的运作和功能(Eaglton “Literary” 2—3)。英美新批评则着力将诗歌转变为物恋的对象,并使之重新物质化(rematerialized),强调作品在物质性方面的自足性和作品自身的物质真实性(张进13)。这种将“词”作为“物”来对待的批评路径,在后结构主义以来的文学研究中体现为:具有物质性和实践性品格的“话语”(discourse)和“文本”(text)概念逐步取代“语言”、“言语”、“能指”和“作品”(work)等术语而成为文学研究的聚焦点;将文学的“形式”作为“内容”来把握,将文学“媒介”作为“讯息”来对待,将文学的“文本”作为“事件”来阐释。 索绪尔语言学有关语言“反映”现实与“打造”现实的悖论,皮尔士古典符号学有关“记号”与“模拟”之间的张力,成为不断生发新文学观念的策源地。皮尔士认为,“借由‘记号’(semiosis)而进行的指涉反映事物,而借由‘模拟’(mimesis)来进行的指涉则促发冲动”(拉什 291—92)。正是语言“打造”和“促发”现实的功能,推动20世纪的文学研究在物性批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奥斯汀有关语言“施事功能”的论述与之呼应,将文学语言“打造”现实的能力推向极致,引发了文学理论批评进一步从语言的“所说”(constative)研究转向话语的“所做”(performative)研究。这一系列观念,不仅强调了文学语言文本以及相关的书写行为的物质性,而且强化了语言书写行为介入和打造语言之外的物质现实的能力,突出了书写行为参与并抵抗历史的潜能。因此,历史书写不仅在“报道”历史事件的意义上具有物质性,其述行行为本身就足以构成一种物质性的历史“事件”。德·曼“铭写的物质性”观念全面释放了历史书写的“述行功能”。对他来说,述行行为可以意指实际的历史事件(这是不可逆转的),也可以意指述行行为。“进行‘物质性’阅读,意味着使阅读涉及并抵抗铭写及铭写模式,寻找这种模式开始进入另一参考、中介、理解、即时性等体系的踪迹”(Cohen viii)。在他看来,任何一个被铭写的文本都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映”或“表达”,文本本身即是一种物质性“事件”,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也是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能指的物质性,一方面可以指向朴素的物质网络,如一般所谓的“物质”能指即字母、声音、文字记载等,它们维持着语言记忆和程序感受(或阐释);另一方面,这个物质能指自身又引发和产生各种物质性的指涉、价值或相关体系。两个方面会通于“文本的物质性”(Textual Materiality),聚焦于文本的“语言意义”与“物质意义”之间的“互动关联”(Allen,Griffin & O'Connell 2),并形成一个多学科综合治理的学术领域。其工作假设和解读方法可以概括如下:文本的意义解读紧密关联着文本的物质形式(physical forms);文本及其潜文本(paratexts)体现着文本的物质性(physicality)意义;文本与其物质形式之间的关系对意义具有构成作用;文本表述的物质形式影响阅读接受和理解态度。这些基本设定,试图在文学文本自身的物质性和文本的社会历史物质性之间、在文学的“记述”物质性与“述行”物质性之间架起飞桥。 在具体文学批评实践中,被塞尔登视为“后理论”表征的“版本目录学研究”(textual bibliography),即是文学物性批评的重要分支。“版本目录学考察一个文本从手稿到成书的演化过程,从而探寻种种事实证据,了解作者创作意图、审核形式、创作与合作中的修订等问题。它“一方面受新历史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以及解构论的影响,可它另一方面也颇像从文本档案馆中钩稽那些潜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的研究”(塞尔登 332)。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批评,其实意味着“回归对文学文本的形式主义的或传统的读解,或者回归到那些实质上对理论厌烦或淡漠的文学研究中去”(Seldon 272)。其所谓“传统的读解”,其实正是20世纪以来强调文学物质性的种种批评方法。 “文本物质性”观念扩展到艺术领域,引发了艺术家和批评家对“物质材料的价值”的“重新评估”,使“美学体系重新重视物质”并从新方向探索可能的形式。于是,对当代大多数艺术家来说,物质不再只是作品的“载体”,也是作品的“目的”。“有时候,艺术家听任材料自由发展,听任泼上画布的颜色、粗麻布或金属自由发挥,直接由一个随机或出乎意料的裂口代言。艺术品每每仿佛不求任何形式,让画布或雕塑几乎成为自然物体,是机缘巧成之作,如海水之画沙,雨滴之铃泥”(艾柯 402—05)。探索艺术的材料,发现它们内里隐藏的美,当代艺术家从“抽象形式”走向了对“物质的深度”的探测,不自知是在恋物拜物。“今天,精密的电子技术使我们在物质深处发现出乎意料的形式层面,一如我们从前一度在显微镜下赞赏雪花结晶之美”(Eco 409)。 总之,物质性观念从语言能指蔓延伸展,逐渐渗透到文学形式、文本、媒介、素材和语境等要素环节,进而与文学活动的其他物质维度会通融合。 二、文学限制条件和语境的物质性 这是新马克思主义所阐发的唯物主义物质性,它强调文学与起限制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世界的事实和条件之间的物质关联。伊格尔顿运用这一思想阐发了文学的物质事件属性。他认为“诗歌语言愈是密集编织,它就愈能成为拥有自身特权之物,也就愈能指向自身之外”(Eagleton “The Event” 205)。从“语言”与“自身之外”的结合部来考察物质经验的来龙去脉,成为理解文学物性的基本途径。这一理论将唯物主义观念注入“精神”本身(事实上承继了“语言论转向”的新传统),模糊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至关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分界线,“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架起桥梁”(Eaglton “Literary” 199)。因此,伊格尔顿等人尽管承认文学语言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文学之外”的物质条件和语境,也不否认文学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之间的血肉关联(Bennett 3)。 这种唯物主义文学观念重视“艺术作品无可逃避的物质性”。然而,像威廉斯和伊格尔顿这样的批评家,却并不强调艺术作品作为意识形态与物质社会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认为文化本身就是植根于社会的“物”,文化是一套物质实践(Brooker 57)。威廉斯并不认为文化具有独立于物质世界的自足身份,而是承认文化本身的物质性,承认文化秩序生产的物质特性。他因而推动了艺术和文化的“再物质化”进程,主张“艺术作品无法逃避的物质性即是各种经验的不可替代的物质化”(Williams 162)。受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影响的更为激进的唯物主义文化理论家断言:不仅物质对于观念具有优先性(primacy),而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物质的,语言、表征、身体、文学和文化文本本身具有物质性;无论是躯体生产的历史工艺品,还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本凸显其自身物质身份的方式,都是物质性的。当然,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与铺路石的物质存在不可等量齐观,后者完全根植于它的“自然实体”(physical matter)。相反的情况表明,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看来,当今媒介社会被分离的和自由流通的影像信息之流主宰着,人们的身体是移动的能指,人们的性别身份是延展性的,而非实体物质的(Brooker 158)。因此,“物质性”并不等同于“物质实体”。 沿着这一路径,文学和文化被解读为“物质实践”,“意识形态”不只作为“观念体系”而且作为“物质装置”在发挥作用。因此,文学和文化研究就不仅要考察文学和文化的“文本”,同时还要考察文学和文化文本的物质“实践”;不仅要研究文学和文化的精神内涵,还要将其作为物质性的“特定生活方式”来研究,考察海滨度假、法定节日和宗教庆典中的意识形态,从监狱、疯人院和临床医学等物质实践的形式中逆向考察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不过,尽管一般的唯物主义都重视物质的重要性,但它总是倾向于设定:主体创造了历史,主体把世界变成了整体;而客体则是“羞耻的、龌龊的、被动的”,客体只是作为“主体异化的、被诅咒的部分”才可以理解。而近年来兴起的“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则把客体作为当然的东西来接受,“赋予它们以潜在性——表明它们是如何组织我们的私下和公开情感的。”它认为,物的世界向人类推进,与人形成了“亲密的纠缠”,人与物之间构成一种“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孟悦罗钢82)。这种新唯物主义强调物的延展性和生产性,留意物的自我构成和通过主体间互动得以构形的多种方式,从而使人和物各归其所(Coole and Frost 7)。同时,当它构想出物的充满活力的能动性之时,它也以“后人文主义”立场重新定义了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 这种新唯物主义,既是当代自然科学和物质领域巨大变迁的反映,也是对新物质新技术大量涌现所导致的伦理问题的回应,同时也是对漠视物质性而走向强弩之末的“文化转向”的反拨。这一新学术思潮重新理解和阐发物质性,强调物质化是一个复杂的、复数的和相对开放的过程,坚持认为包括理论家在内的人类,都陷身于物质生产的偶然性之中。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发展是这类新物质观念得以出现的物质基础。19世纪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哲学思想,都受到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有力推动;然而,当代新物理学和新生物学使得经典科学所激发的理解方式不再能够解读物质的本质。对于各种旧唯物主义来说,尽管牛顿的机械论异常重要,但是在当代物理学看来,物质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刷新”理解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互动的方式(Coole and Frost 5)。今天,我们已经超越了机械论的宇宙模型,“进入了以量子论为基础的范式”。在这种范式看来,“辩证过程的结果并不能先期确定:系统可能崩坍,但它也许能自我再生,在过程中自我组构,从而具备更高水平的行动成熟度”(沃尔弗雷斯 131)。 因此,新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性批评尽管强调文学与起限制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世界的事实和条件之间的物质关联,但它并不在线性因果论的维度上,而毋宁是在非线性的维度上开掘文学的物质性,并将文学的语言物质性与社会物质性联结起来。其典型的表现形式即是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论”。在他看来,诗歌的意义与物质性并肩工作,“诗歌的物质躯体通过其内部运作向其外在的世界开放。所有的语言都是这样,但它在诗歌中更为明显。诗歌语言的文本编织越是细密,它就越能成为一个拥有自身特权之物,也就越能指向自身之外。可以说,人类躯体与之类似,其物质存在只是其与世界的关系,即是说,躯体更根本的是作为实践的形式而存在的”(Eagleton “The Event” 205)。因此,“文学事件”使能指的物质性与能指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之间形成了物质性互动,从而展示出文学中的物质事实。 作为“事件”的文学本身,即是人类物质实践的组成部分;文学文本不仅在“反映”历史的意义上拥有价值,文学作为事件本身即是历史的组成部分。看待一个事件不是凭其内在意义和重要性,而是凭它与各种社会性控制力量的关系。文学文本作为文化“事件”,其意义并不限于自身“之内”;但意义也并不在该文本“背后”或作者“思想”,而在于它与其它文化文本之间的流通交换过程,“因为这个意义并不在于文本的‘外部’(结构或意识形态),而在于诸文本和诸事件的领域”(Colebrook 74)。“事件”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具有“创造性”,它不仅从原有的事件和前提中创造自身,而且对后继事件施加作用并对未来产生创造性的影响(格里芬 66—67)。“文学事件”以其向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双向开放的潜能,在语言文本的物质性与社会世界的物质性之间架起了飞桥。 三、文学感知主体和身体的物质性 文学感知主体是文学活动得以展开的主体依托,考察感知主体的物质性,即考察审美经验藉以发生的主体身体的物质性,其主要倾向在当前的身体美学和文化研究的“身体转向”中得到了集中呈现。任何审美活动,都不仅需要通过精神性的意识而发生,而且必须通过物质性的身体而发生,身体是审美经验得以发生的物质基础。当然,美学文艺学对身体的研究古已有之,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主体身体在审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重视不够,阐发不足。近年来,文艺审美领域所发生的身体转向是对这一偏颇的有力纠正。然而,当前身体转向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依然像以往的研究那样从精神的、隐喻的和符号的方面研究身体,而在于从考古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物质性方面研究身体,将身体不仅作为“隐喻”而且作为“生理现实”来研究(Fahlander and Oestigaard 19)。在一些具体而微的研究中,人们甚至可以考察审美活动与主体身体的“内脏器官”的活动之间的物质性关联(Machon 14)。因此,当前身体转向因其对审美主体身体物质性的开掘和凸显而汇入了物性批评的洪流。 “身体”成为近来文化理论强烈关注的课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视其在文化研究议程中的地位而变化,诸如女性身体与消费主义和身体保健之间的关系、普通大众对于健康(fitness)问题的关注、学术界内外对于性属问题的广泛兴趣、围绕同性恋和艾滋病的争论、后殖民理论对种族身体的概念化而产生的后果,以及当前人们对于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发展的关切,等等。在所有这些理论批评活动中,人们对身体物质性方面的重视不断加强。新锐理论家号召人们要更加充分地认识“身体作为物质的和生理的现象”(the body as a material and physical phenomenon),充分认识身体作为“物质事件”在话语和意识形态领域所起的作用。这种唯物主义身体观既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相关,也与近来新生物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后者提出了人的生理身体和人类身份的“延展性”问题(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即是最轰动的例子)。理论著述、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中的“赛伯格”(Cyborgs)主题或隐喻,即是对“后”人类身份的技术和伦理的一种反映(Brooker 21)。 人的身体正逐渐被看成有差异的、需要特殊对待的机体(entity),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消费文化通过节食、化妆品、锻炼、维生素把人的身体分解为一系列身体部件。从身体保健的目的来看,人不是带病的躯体,而是需要按照X光、血压与血液检测、扫描检查、体内检测技术提供的证据进行评估的一系列“症状”。把人的身体分解为身体部件的组合,这是后现代理论特别关注的、当代世界大范围“碎片化”过程的一部分,它对“人类到哪里结束、机器从哪里开始提出了疑问,并有助于我们将关于人类身份的身体基础的传统理解相对化”(鲍尔德温 318)。后现代物质“入侵”身体,使这个“恐怖的身体”不再是原来意义上“自然的”身体,而拥有了非自然物质的“物质性”,并与意识形态之间展开了新的共谋互构关联。文学批评不仅需要正视身体的物质性,更应该正视身体之中“非自然”物质的物质性。哈拉维对于赛博形象的研究,代表着身体物质性研究的这一方向。赛博形象的大量涌现使我们的一些轻松的、把身体和自然密切联结的概念发生了彻底动摇。 然而,这一切并未将身体从既成的文化话语中驱除出去,而是使身体成为当代思想的聚焦点,使身体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紧密关联起来。哲学家费恩指出,“人生的旅程之中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动了好几次手术——幼年时期发育形成的神经组织,年老后它又开始衰竭、萎缩。”人的身体一生中所经历的变化正像那艘不断更换船板的“忒修斯之船”(费恩 17)。据古希腊神话记载,大英雄忒修斯杀死克里特岛的米诺陶之后,他的战船每年都要开往提洛岛做一次致意之旅。随着时间的流逝,船桁纷纷腐坏溃烂,于是渐次被换成新板,到最后原先的木板都已不复存在。看起来此船仍是忒修斯拥有的那一条,但我们也许会感到疑惑:现在它还是“同一条”船吗?在当代新技术和生物工程的推动下,人的身体不仅被非自然的物质一次性地、部分地“入侵”,而且有可能像“忒修斯之船”那样被彻底“置换”,我们身体和身份的同一性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学会与这些非自然物质的物质性“亲密纠缠”。当前,人机合一的“赛伯格”形象充斥各种文艺形式之中,反映出人们对于身体中的非自然物质入侵的极大恐惧和困惑。文学理论批评也迅速介入这一新的物质空间,理论批评的新话语和新范式正在这个新物质空间滋生成长。 人类物质生产的实践不仅改变着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改变着人们感知并承载精神世界的躯体;躯体作为人的精神的“直接现实”在普通的物质与精神之间充当着中介桥梁。人类在物质实践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往往通过直接地改变人类躯体而间接地改造人的精神世界,文学研究应该能够通过研究身体的物质性而深化对文学问题的理解阐释。 四、文学表征对象和经验客体的物质性 文学表征对象的物质性,即经验的对象以及经验于其中得以发生的对象世界的物质性。这个意义上的“物”无所不在,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它们,就是研究表征对象的“物性”。在中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无论是“物恋”“物化”“物联”还是“物感”“物色”“物役”“物象”“物语”“物哀”,无论是“与物为春”“神与物游”“以物观物”还是“物秩序”和“物体系”,这些问题的研究都触及“物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个被文艺文化所表征的对象,都有其物质性的层面,文学理论批评不仅应该考察“物”在表征系统中的精神含义,更应该考察它在物质世界中的“物性”内涵。由于近代以来缘于西方“物化”概念所包含的否定性意涵,理论批评对于“物性”的兴趣有所减弱。我们处身于物的包围之中,却对物的“物性”漠然视之。 物质领域的变迁刷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时空观念,新物质和新事物的出现,其特殊的“物性”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多样化的表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艺术地呈现了作为新事物的汽车对人们造成的“震惊”。“汽车虽已离去,但它仍留下一丝余波,回荡在邦德街两侧的手套、帽子和成人店里。半分钟之内,每个人的脸都转向同一个方向——窗户[……]要是这种事情单独出现,那真是微不足道,即使最精密的数学仪器也无能为力,尽管它们能记录来自中国的地震,却无法测定这类事情的震动。[……]那辆汽车经过时引起的表面上的激动逐渐冲淡了,骨子里却触动了某种极为深沉的情感”(伍尔夫 18)。重量、速度、震动、声音等,都是汽车之“物性”的重要方面,这一新事物之物性特征的集中呈现,改变了人们的情感方式和时空观念。汽车的意义在于它重组了公民社会,导致了西方在“汽车时空”社会中居住方式、旅游方式和社交方式的重构。汽车是一个典型的“物”,“它的轨迹与对象的批量生产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到20世纪中叶,它在现代晚期的消费、生活风格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发展中变得意义重大。汽车作为一个客体塑造了大部分社会生活,这一点只有到了21世纪初才得到承认”(Dant 9)。 文学理论批评转向那些得到表征的具体之物,考察诸如“电灯”和“电话”等物在中国近代以来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以及这种新型之物在各类文学作品中的“表征”情况,探讨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活动之间的多样化关联(Dikotter 148)。不仅如此,新事物的物性特征通常也是文学理论批评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基本触媒。研究发现,在美国超验主义诗学理论中,“电”充当了多数作家运用科学的、社会政治的和精神的术语想象审美经验的工具。“电”作为新物质的某种貌似“超验”的特征,正是美国超验主义浪漫主义理论批评阐发文学本质功能的物质依据(Gilmore 5)。欧洲浪漫主义时代自然科学所发现的“化石”,作为一种“有生命之物”,成为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和批评的灵感源泉。当前,“生物学又一次站在了科学的前沿,新的非人类的生命形式举目皆是,一部新的物质客体的历史似乎正在孕育。克隆羊,自动繁殖的机器人,以及西伯利亚猛犸冷冻的DNA,都成为头条新闻,从死者身上复苏的绝种怪物的形象占据了电影的影像世界”(孟悦 罗钢 535)。人们只有在与物的亲密纠缠中,才能把握文学作品的真实内涵。 这里存在一个异常复杂的相互表征的关系网络。比如“电视”作为“物”,既可以成为表征和播放文学作品的媒介,也可以成为文学描写、反映和“被表征”的对象。我们惯常是在电视所反映的内容和对象的意义上研究其对人类生活活动的影响,却每每忽视电视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的“物”本身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命生活方式(无论电视节目播放了什么内容)。比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电视屏幕的大小薄厚、轻重黑白以及在家庭空间中的摆放位置,都在表征并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等等。 不同时代的思想者用那个时代新出现的“物”来进行理论联想,试图运用最新的技术模型去理解人的心智活动。美国哲学家塞尔写道:“在我的童年时期,人类总自信满满地断言大脑就是一部电话交换机[……]伟大的英国脑神经生理学家谢灵顿认为大脑的活动方式类似于一个电报系统。弗洛伊德多次将大脑与水力系统和电磁系统相提并论。莱布尼茨则把它比作是一碾磨,还有人告诉我不少古希腊人认为大脑运转起来跟石弩没什么两样。而现在,很明显,人们将它比喻成了数字计算机”(费恩 41)。这些物不仅是哲学思想的运思模型,而且是文学理论批评解剖文学活动的参照模板。这些物进入了文艺作品,成为其表征对象,也成为文艺实践的鲜活生动的“物境”。然而,长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对于这类物的物性方面的研究却并不充分,导致文学批评“言之无物”。 文学理论批评正在“与物为春”的新型“人—物”关系系统中重新思考那些在文艺中得到表征的“物”,研究其“物性”特征,以及这些物性方面与理论批评之间的复杂关联。“物的世界除了对人性和人类生活形成外在压迫之外,还以空前亲密的方式深入人的内在空间。物不仅对人形成压迫,还与人形成亲密的纠缠”(孟悦 罗钢 2)。以往的文学理论批评,对物与人之间的对立有很多论述,但对物与人之间的亲密纠缠很少论及。那些被长期赋予贬义的“物”和“物性”,正在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大显身手的新空间。 文学研究在如上向度上彰显出的文学物质性,构成了文学物性批评的基本内容。这些维度上的物质性相互联系、彼此互动,共同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网络(Gilmore 9—10)。理论批评密集转向文学的物性和物质现实,引发了文学研究焦点从“文本间性”向“事物间性”的转移,与之联袂而行的,是“文学作为人性的表征”的传统文学观念正在让位于一种可称之为“文学作为物性的体现”的新型文学观念。 文学理论批评必须认识到,它所讨论的,不仅是单一向度和要素意义上的文学物性,而是综合向度和系统意义上的。这是一种“关系物性”或“物性关系”(material relations),是一种“活态的实践性关系”。研究者指出,“消费研究一直强调事物之社会身份的‘意思’或意义,但忽视了与事物的活态的(lived)实践性关系”(Dant 10)。人与周遭事物之间的“物质关系”,使得情绪和感情得以通过物而由内到外地展开,从心理到身体,进而超越到身体之外。“物质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就是由人与物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是一种物质性的互动关联(material interaction)。汽车的意义在于它重组了公民社会,导致了西方在“汽车时空”的社会中居住方式、旅游方式和社交方式等的显著变化。我们只有从物质性关系的维度,才能够认清“汽车”的“物质性”和“社会性”。 把握“物性关系”系统的枢纽,一在于“物性”观念的调整,当代西方哲学越来越强调物性的“事物间性”品格(张法 53),强调物与物之间的“间性”关联,这种新的物性观念是我们阐发文学物性问题的重要理论参照。二在于“人—物关系”的重新规划,在于从积极的意义上重绘人与物之间亲密纠缠的构图,这在庄子的“与物为春”的“物化”思想中得到了系统表达。文学物性批评,就是要在“事物间性”观念下,在人与物的亲密纠缠中,在“与物为春”的“人—物”关系中,在“物—物”关联的历史具体性中,对自身做出定位。 文学物性批评促生了一个跨学科、跨媒介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空间,在这里,人—物之间“与物为春”的生态关系得到强调,“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界限得到重划,单一学科视野之外的“物”的多样维度得到阐发;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和生物学研究的一系列新成果在这里会通融合,共同勾画着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新景观和新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