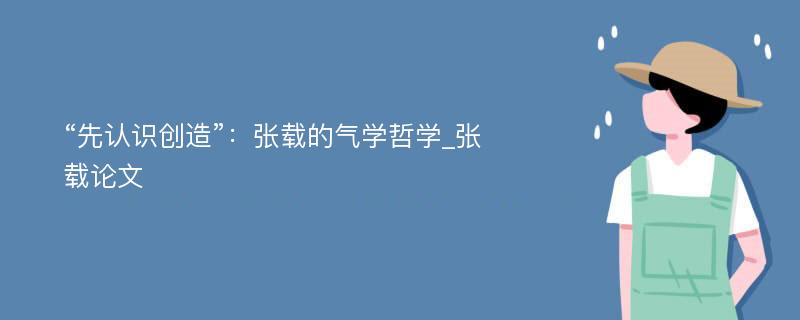
“先识造化”: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造化论文,哲学论文,张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吕大临作《横渠先生行状》云:张载“少孤自立,无所不学。与邠人焦寅游,寅喜谈兵,先生说(悦)其言。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此中“年十八”当依《宋史》本传作“年二十一”。《张载集·文集佚存》中收录了《边议》九条,其中有云“今边患作矣”,当即写于边患初作之“康定用兵时”。《行状》云:“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可乐”据《宋史》本传补)范仲淹的这次警策,乃“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三年之后,即庆历二年(1042),张载作《庆州大顺城记》,记述范仲淹在庆州率军筑大顺城,击败西夏军,文中有云“兵久不用,文张武纵”,此与范仲淹同年所作《上吕相公书》批评“文之弊”而“忘战日久”,“一旦夷狄叛”则将帅乏人,主张朝廷命官要“文武参用”、“使文武之道协和为一”的思想相符。观此可知,范仲淹所谓“何事于兵”的本意不是否认军事的重要,而是激励张载成为“明体达用”的儒者。迄至熙宁初年,张载仍作有《与蔡帅边事画一》、《泾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等,可知张载在“入圣人之室”、乃至嘉祐初“讲《易》京师”后仍高度关注边关防务。
就儒家的“明体”而言,《中庸》无疑是重要的经典。范仲淹在《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中就已对《中庸》之“自诚而明”和“自明而诚”有所阐发,在其执掌睢阳书院期间作有《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余英时先生谓“此文全就《中庸》发挥,充分表达了由修身、齐家而建立理想秩序的意识,而且也含有‘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观念”①。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是深有其意的,但张载对《中庸》“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行状》)。张载之“爱”《中庸》并非虚言,他曾说:“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经学理窟·义理》)说此话时起码已在嘉祐五年(1060)以后,即张载之学已初具规模时。但在康定、庆历年间,张载读《中庸》而“犹未以为足也”,此中原因就是《中庸》的义理还不能满足张载建构其“本体一宇宙论”思想体系的需要。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在“反而求之《六经》”之后云:“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乃尽弃异学,淳如也。”后一句原作“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曾对此批评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程氏外书》卷十一)无论“尽弃其学而学焉”还是“尽弃异学,淳如也”,两说都不符合张载思想的实际②。《宋史·张载传》云:“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此据程门弟子尹焞所述(见《程氏外书》卷十二),其中虽也有对张载之学的贬抑,但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当是事实。
张载在嘉祐二年(1057)与程颢等同年中进士,其“讲《易》京师”并与二程“共语道学之要”当在此期间。张岱年先生认为:“张载在开封讲《易》时,可能已经开始写《易说》了。”③ 这一推断是合理的,即《易说》可能是张载在开封讲《易》时的“讲稿”。张载的《正蒙》乃作于熙宁三年(1070)他“谒告西归,居于横渠故居”之后,《行状》记其“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正蒙》完成于熙宁九年秋,一年后张载即病故于从洛阳返陕西的途中。《易说》中的许多文字又见于《正蒙》,可知《正蒙》是在《易说》的基础上“简编”(“简”者择也)、扩充而成。《易说》是张载之学的奠基,《正蒙》则是张载的晚年定论。张载之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宋史·张载传》),即张载的思想是以阐发《周易》为基本,而又涵容了《中庸》、《论语》和《孟子》的思想。由此可知,张载早年读《中庸》而“犹未以为足”,其累年参究释、老的思想后“反而求之《六经》”,他主要是从对《周易》的理解和诠释中建立了其思想体系的基础(王夫之《正蒙注》:“张子之学,无非《易》也”)。
二
张载诠释《周易》的一个特点是“观《易》必由《系辞》”。他说:
不先尽《系辞》,则其观于《易》也或远或近,或太艰难。不知《系辞》而求《易》,正由不知礼而考《春秋》也。(《易说·系辞上》)
《系辞》所以论《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则《易》象在其中。故观《易》必由《系辞》。(同上)
此说与二程的易学有同有异。《程氏遗书》卷二上载:“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明)”“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须先看卦,乃看得《系辞》。”这里的第一条为程颢所言,特重《系辞》,与张载相同;第二、三条,未注明谁所言,可能出自程颐,其重视《周易》的义理也与张载相同(他们同属于宋代易学的义理派),但其强调先求卦义,后看《系辞》,则与张载的“观《易》必由《系辞》”相反。
张载诠释《系辞》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先识造化”。他说:
易,造化也。圣人之意莫先乎要识造化,既识造化然后其理可穷。彼惟不识造化,以为幻妄也。不见易则何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则何以语性?(《易说·系辞上》)
不见易则不识造化,不识造化则不知性命。既不识造化,则将何谓之性命也?(同上)
有谓心即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尽易之道!(同上)
释氏之言性,不识易。识易然后尽性。(同上)
张载所谓“造化”,就是气之“一阴一阳”的变易。他说:“一阴一阳是道也”,“易即天道”(同上)。此“一阴一阳”之道“范围天地之化”、“弥纶天地之道”、“通乎昼夜”,故云“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谓也”(同上)。张载提出“先识造化”,然后可以穷理、知性命,这显然主要是针对佛教的以心为本、以天地万物为幻妄的思想而发。其累年参究释、老之说,反而求之《六经》,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要“先识造化”,即首先在本体—宇宙论上与释、老划清界限,然后才可以穷理、知性命。
“先识造化”的思想又见于《正蒙·太和》篇:
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体虚空为性,不知本天道为用,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明有不尽则诬世界乾坤为幻化。幽明不能举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阴一阳范围天地,通乎昼夜,三极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庄混然一途。语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恍惚梦幻,则定以“有生于无”为穷高极微之论。入德之途,不知择术而求,多见其蔽于诐而陷于淫矣。
所谓“深于《易》者”,就是“知虚空即气”(气即阴阳),知道“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都统一于气,对于“聚散、出入、形不形”(气聚则“出”而有形,气散则“入”而无形④)能够“推本所从来”,这就是“先识造化”。所谓“此道不明”,就是“彼惟不识造化,以为幻妄也”。“幽明”即气之“聚散、出入、形不形”,如果对此“不能举其要”,先言“体虚空为性”等等,那就是“躐等(超越等级程序)妄意而然”。正因为不悟一阴一阳的变易“范围天地,通乎昼夜”,乃天地人(三才)的普遍法则,所以才使儒、佛、老庄的思想发生混淆。那些“不识造化”而“语天道性命者”,不是迷惑于佛教的“恍惚梦幻”之说,就是将老庄、道教的“有生于无”视为至高极妙之论。在张载看来,“入德之途”就是“先识造化”,若不知此而求道德,则往往被偏颇之辞(“诐”)所蒙蔽而陷于不中、过度(“淫”)之荒谬。
《正蒙·太和》篇言“虚空即气”,又言“太虚即气”: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故圣人语‘性与天道’之极,尽于参伍之神,变易而已。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非穷理之学也。
这段话也首见于《易说·系辞上》。“太虚”一词在《庄子·知北游》和《黄帝内经·天元纪大论》等著作中早已使用,其义指广袤无垠的空间。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即气是充满空间的(王夫之《正蒙注》所谓“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在此意义上说,“太虚即(就是)气”,“无无”即宇宙间没有气之外的空无。“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太虚与气的关系就如同水与冰的关系,水之凝固就是冰,冰之融释就是水(水是冰的本然状态),气之凝聚就是有形之万物,万物之消散就反归无形之太虚(太虚是气的本然状态)⑤。张载认为,圣人讲“性与天道”的最根本道理,就是讲到一阴一阳之“参伍错综”的神妙变化⑥。“诸子浅妄,有有无之分”,主要针对老庄的“无生有”而言,张载指出,这不是“穷理之学”。在以无为本还是以气为本的问题上,张载以前的儒家没有分辨儒、道的自觉,至张载则明确提出了“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易说·系辞上》,这两句又分别见《正蒙》之《太和》与《大易》)。所谓“不言有无”,就是“气能一有无”(《易说·系辞上》),即将“有无”都统一于气之实在,没有气之外的空无。张载由此而与释、老的宇宙观划清界限(改变“儒、佛、老庄混然一途”),他说:
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正蒙·太和》)
“有无混一之常”,就是“气能一有无”;物与虚“相资”,就是万物与太虚的关系不过是气之聚散的变化。
“幽明”一词源出《易传·系辞上》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⑦。张载说:“显,其聚也;隐,其散也。显且隐,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荡所以妙乎神。”(《易说·系辞上》,又见《正蒙·大易》)气聚而有形,则为“显”“明”;气散而无形,则为“隐”“幽”。气之聚且散,是因为“一阴一阳”相互推荡的神妙变化,“阴性凝聚,阳性发散,阴聚之,阳必散之,其势均散”(《正蒙·参两》)。张载又说:
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则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万物相见乎离,非离不相见也。见者由明,而不见者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处。彼异学则皆归之空虚,盖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见一边耳。(《易说·系辞上》)
“因明而知之”,即因气聚有形之“显”“明”而知之;“非明则皆幽也”,即气散无形而“隐”,则为“幽”。“万物相见乎离,非离不相见也”,此本于《易传·说卦》的“离为目”,“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即万物都依人的视觉而相见,若没有人的视觉则不相见。人所见者是由于气聚有形而“明”,人所不见者并非无物,而是有气散无形之“隐”“幽”,这乃是天之根本。“彼异学”(指释、老)把不可见者都归于无物之空虚,盖其只知道“明”,而不体察“幽”,所见是片面的。张载接着说:
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同上,又见《正蒙·太和》)
这段话承上而言,就是说:气之凝聚则人的视觉可以施之于有形之物⑧,气之不聚则人的视觉不能施之于无形之气。当气聚有形时,怎能不称其为“有”?当气散无形时,又怎能说其是“无”(空无)?意谓无形之气(太虚),虽然人的视觉不可见,但仍是客观的实在⑨。此即“气能一有无”,知道“有无混一之常”。张载的“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正是由此而提出。
牟宗三先生解“气聚则离明得施”一段,谓此“离明”之词“不实指目言,乃直指神体之虚明照鉴而言也……此是言‘心’之‘本体、宇宙论的’根据,而此神体之明亦可以说即是‘宇宙心’也”⑩。此说与张载的本义相差甚大。张载由“先识造化”得出的是气本论的思想,无论在《易说》还是在《正蒙》中,张载屡言“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易说·复》),“天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易说·系辞上》),“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正蒙·诗书》),“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正蒙·气质》),其批评佛教亦言“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正蒙·大心》),他哪里会有世界本体之“宇宙心”的思想?而且,如果以“离明”为“神体之虚明照鉴”,那么“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此句根本解释不通(11)。
上引文中“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有”,在《正蒙·太和》篇改为“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12)。这一改动是承接上文之“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对张载思想的误解,常因此句之“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而起。牟宗三先生亦将此句误解为“气以太虚——清通之神——为体”,从而亦将“太虚即气”理解为太虚(神体)与气之“相即不离”(13)。其实,“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是说太虚之无形乃气之本然的象态(14)。“其聚其散”的“其”字,即指“太虚无形”之气(若无“气”,则“其”不能聚散;下言“至静无感,性之渊源”,亦承上指“太虚无形”之气乃“性之渊源”,说详后)。“本体”是相对于“客形”而言,气之本然的象态是太虚,而气之聚散则是其变化之“有去有来”的暂时状态(王夫之《正蒙注》:“有去有来谓之客”)。“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太虚即气”可以说太虚与气“通一无二”(15),而不可理解为太虚(神体)与气是“二”而“相即不离”或“不即不离”(16)。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牟宗三先生把“太虚不能无气”理解为太虚神体“不能离气”(17),但后一“太虚”分明就是指气,因为万物之散只能散为无形之气,而不能说散为“太虚神体”。
三
张载说的气之“聚散”,就是指无形之气与有形之物的相互转化。此因一阴一阳的变易而起,故曰“易,造化也”,“易即天道”。张载又说:“一阴一阳是道也。”“一阴一阳不可以形器拘,故谓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易说·系辞上》)张载由此而区分《易》之形而上、下,他说:
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易说·系辞上》,又见《正蒙·天道》)形而上是无形体者,故形以上者谓之道也;形而下是有形体者,故形以下者谓之器。(《易说·系辞上》)
有变则有象……有此气则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则直无而已,谓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但于不形中得以措辞者,已是得象可状也。(《易说·系辞下》)
张载认为,气之一阴一阳的变易就是“道”,“形而上”就是气聚成形以上,“形而下”就是气聚成形以下。此说成为张载的气本论与二程的理本论的一个根本分歧。二程所谓“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程氏遗书》卷十一),“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程氏遗书》卷三),就是以“理”为气之根本。而张载则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太和》)“理”就是天地之气运动变化的秩序、规律。牟宗三先生对“其为理也,顺而不妄”的解释是:“言其聚之所以为聚,散之所以为散,攻之所以为攻,取之所以为取,皆有其形上地必然之道……‘为理’是此事之所以为此事之理……此‘理’字是虚说,其实处是通于太虚之神。”(18) 然而在张载的思想中,“形上地必然之道”也就是“一阴一阳不可以形器拘”的“道”,换言之,此“道”也就是“有此气则有此象可得而言”的“形上者”。除此之外,若无气的形上者则“直无而已”,张载否认在“一阴一阳”之上还有“所以阴阳”的理、道,更否认在“阴阳不测”之外还有“太虚之神”(“宇宙心”)。
《易传·系辞上》云:“神无方而易无体。”张载说:“神与易虽是一事,方与体虽是一义,以其不测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体,然则易近于化。”(《易说·系辞上》)又说:“体不偏滞,乃可谓无方无体。偏滞于昼夜、阴阳者,物也;若道则兼体而无累也。以其兼体故曰‘一阴一阳’,又曰‘阴阳不测’,又曰‘一阖一辟’,又曰‘通乎昼夜’。语其推行故曰‘道’,语其不测故曰‘神’,语其生生故曰‘易’,其实一物,指事而异名尔。”(同上,又见《正蒙·乾称》)张载对“神”的理解没有超出“阴阳不测”的意义之外,所谓“神无方”、“易无体”、道之“兼体而无累”,大致都是从“一阴一阳不可以形器拘”的意义上讲,“其实一物”(此“一物”当作“一气”来理解,而非偏滞于“昼夜、阴阳”某一方面的形器之物),只是言之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张载说:“太虚之气,阴阳一物也;然而有两体,健顺而已。”(《易说·系辞下》)此即张载的气之“一物两体”的思想。此处言“太虚之气”犹如言“太极”,“阴阳一物”即前引“其实一物”的“物”,“有两体”即道之“兼体”的意思。张载说:
一物两体者,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参也。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若一则有两,有两亦一在,无两亦一在,然无两则安用一?不以太极,空虚而已,非天参也。(《易说·说卦》,其中部分文字又分别见《正蒙》之《神化》、《太和》)
一物而两体者,其太极之谓欤!(《易说·说卦》,又见《正蒙·大易》)
《易传》的最高范畴是“太极”,张载以“一物两体”之气为“太极”。此“太极”与“太虚之气”是同等的概念,“其实一物”,亦言之角度的不同而已。言“太极”犹如有最高的“一物”,其生两仪(天地)、四象(四时),主要具宇宙生成论的意义;言“太虚”则其“至大无外”(19),在空间上“范围天地”,在时间上“通乎昼夜”(20),不仅生成万物,而且为人与万物的性命之源,遂已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意义合一。合而言之,“太极”之“一物两体”之气充满空间即是“太虚”(21),而“太和”就是指作为世界本原的“太极”或“太虚”的最高和谐。
《易说·系辞上》在“易有太极……”之下注云:“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时之象,故下文云‘变通莫大乎四时’。”此处必有阙文,据《易说·说卦》,张载必以“一物两体者,气也”注解“太极”,而对“两仪”当有注云:“两仪即天地,乾坤之体,故下文云‘法象莫大乎天地’。”
《易说·系辞下》在“天地絪缊……”之下注云:
气块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絪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欤!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通聚结,为风雨,为霜雪,万品之流形……
这段话又见于《正蒙·太和》。“气块然太虚”,就是气充满太虚,亦即“太虚不能无气”的意思。“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此言由太虚分化为两仪(天地)。“其感通聚结”,也就是“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太和》篇的首段云:
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絪缊,不足谓之太和……
这段话不见于《易说》,当是写《正蒙》时的新作,而又是从“气块然太虚”一段发展而来。“太和”是言“太虚”之和谐。“中涵浮沈……之性,是生絪缊……之始”,大致是“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的意思。“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本于《易传·系辞上》的“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是讲天地化生万物的秩序,即《正蒙·动物》篇所云“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从“几微易简”到“广大坚固”,包含五行生成之序的意思。
上引《太和》篇首段中最引起读者误解的是“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牟宗三先生把张载的“太虚”理解为“太虚神体”主要根据这句话(22)。就“散殊而可象为气”而言,这的确是张载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表述,《易说》中无与此相类者,只《正蒙·乾称》篇有两例:
至虚之实,实而不固……实而不固,则一而散……
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其散无数……虽无数,其实一而已。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也。形聚为物,形溃反原……
“至虚之实”就是太虚之气为实有,“一而散”就是从统一的(连续性的)太虚之气“散”分成万物之殊。“气有阴阳”,即是“一物两体”。“其散无数”、“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与“一而散”同义。另外,在《张子语录·下》有一条:“大凡寛褊者是所禀之气也。气者,自万物散殊时各有所得之气……”这是讲人物所禀的“气质”。参考此三例,可知“散殊”是相对于“合则混然”即无形的太虚之气而言,它与“形(气)聚为物”是一个意思。准此,《太和》篇的“散殊而可象为气”,只是指气之“客形”的有形象,它不是指气之“本体”。《太和》篇云:“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前句是言气之“本体”,后句“感而生则聚而有象”也就是“散殊而可象为气”,此中的“象”是指有形可见的形象,“气”则指万物所禀的“气质”(形气)。与“散殊而可象为气”相对为言的“清通而不可象为神”,此“象”也是指形象(23),而“神”只与有形的“气质”相对待,并非与“一物两体”、“湛一无形”的气相对待,亦即并非如牟宗三先生所说“毕竟神是神,而不是气……神与气可分别建立”。
牟先生对《正蒙·参两》篇“一物两体,气也”的解释是:“‘一物’即太极、太虚神体之为圆为一,‘两体’即昼夜、阴阳、虚实、动静等,属于气。”(24) 但《易说·说卦》和《正蒙·大易》明言“一物而两体者,其太极之谓欤”,仅只“一物”而无“两体”,并不能称为“太极”或“太虚”。《易说·说卦》云:“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然无两则安用一?不以太极,空虚而已,非天参也。”《正蒙·太和》篇亦云:“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可见在张载的思想中,“气有阴阳”才能称为“太极”,如果没有“阴阳”,那么“一”只是张载所否认的“空虚”而已。张载说:“太虚之气,阴阳一物也”,如果没有“阴阳”,那么“太虚”也只是张载所否认的“空虚”而已。张载说:“一物两体者,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此天之所以参也。”“然无两则安用一?”“不有两则无一”,如果没有“两故化”,那么“一故神”也只是“空虚而已,非天参也”。
张载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正蒙·神化》)如果没有阴阳之“合一”,那么也就没有“不测”之神。张载说:“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同上)“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正蒙·乾称》)阴阳之外无“太极”、无“太虚”、无“神”;因为“气有阴阳”、“一物两体”,所以才有“神”“化”;“太虚”就是“气”,“神与性乃气所固有”。这是张载所固有的思想,而非张载的所谓“滞辞”(25)。如果理解成“太虚神体”与气化“相即不离”或“不即不离”,那么这只是理解者的偏滞。
吾学友丁为祥教授对张载的思想亦持“虚气相即”的观点。他解释张载所谓“神”,认为“从气的角度提出的神正是作用义的神,而从太虚角度提出的神则是实体之神……也可以说就是太虚本体之‘清通而不可象’自身”(26)。他的“虚气相即”之说显然是受到牟宗三先生的影响,而在他新举证的史料中有一条“言虚者未论阴阳之道”,他论证说:
所谓“言虚者未论阴阳之道”,显然不是一个宇宙论—时空向度的提法,因为“太和”一开始就内含阴阳这一点也不容许将太虚与阴阳从宇宙源始的角度分开,只有从本体论的角度才可作这样的表达。所以,这里的“未言”所表现的只能是逻辑上的关系,是太虚超越于阴阳、超越于太极元气的表现。(27)
我认为,在张载的思想中宇宙论与本体论是统一的,当我们从这两个角度解释张载的思想时,不能轻易地以二者之“对翻”或“对扬”而容许其间有思想的矛盾。就“太虚”、“神”与“阴阳”的关系而言,无论在《易说》还是在《正蒙》中都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太虚”、“神”超越了“阴阳”或“太极元气”(丁为祥对张载之“太极”的理解与牟先生不同),而“言虚者未论阴阳之道”只是《张子语录》中与前后文断开(另为一段)的单独一句话(28),此句与张载所说“太虚之气,阴阳一物也”、“不有两则无一”明显相矛盾,因此,“言虚者未论阴阳之道”只能是张载对“未论阴阳之道”而“言虚者”的批评(如《正蒙·乾称》篇批评佛教“彼欲直语太虚,不以昼夜、阴阳累其心,则是未始见易”)。
四
张载对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一个简要的概括,即:
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正蒙·太和》)
“天”既是指哲理意义的最高存在,又具有中国古代天文学之“宣夜说”的理论背景,所谓“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晋书·天文志》),把此中的“虚空”与“气”统一,就是张载所谓“太虚即气”的“天”。“气化”即张载所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化,天道……一于气而已”,也就是说,气之一阴一阳的变化过程就是“道”,此变化过程“顺而不妄”就是张载所说的“理”。
“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此表述极易引起误解。朱熹解释此句:“‘虚’字便说理,理与气合,所以有人。”(《朱子语类》卷六十)这是用理气二分的观点来解释张载的思想。后来主张理气统一者如明儒吴廷翰,也批评张载“言之未精”,“其以‘虚与气’两言之,犹未免于理气之失也”(《吉斋漫录》卷上)。其实,“合虚与气”的“气”也应理解为“自万物散殊时各有所得之气(质)”。张载说:
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纳不二也。……性其总,合两也。……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正蒙·诚明》)
以上是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思想。其中,“天所性者”、“天性在人”、“湛一,气之本”、“性于人无不善”等等,都是讲“天地之性”;“气之昏明”、“受光有小大”、“攻取,气之欲”、“气之偏”等等,都是讲“气质之性”。“性其总”当即“有性之名”的“性”,“合两也”当即“合虚与气”,也就是合太虚与气质。张载说: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正蒙·太和》)
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反清为浊,浊则碍,碍则形。凡气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同上)
太虚之无形、“至静无感”(29)、清通无碍,是“天地之性”的渊源;气之“反清为浊”,壅蔽锢塞,是“气质之性”所由生。“太虚为清”即是“气清”,亦即“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故“合虚与气”即是合太虚之气与气质,“有性之名”即是合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其总,合两也”。此句虽然表述上有“未当”,但不可作“理气二分”或“理气二元”解。至如牟宗三先生批评“横渠此语决是不谛之晦辞”,这是依其理解:“太虚神体根本不可以气言……不能将神混作气……性之名只能超越分解地偏就太虚神体之体万物而建立,不能由‘合虚与气’而建立。”(30) 这种理解与张载所说“太虚为清……凡气清则通……清极则神”是根本相违的。
“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此可见“性”与“心”之区别。张载说:“由气化,有道之名”,“天道即性也”(《易说·说卦》),“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在这里,无论“天地之性”还是“气质之性”都是没有“知觉”的,而“知觉”之产生则如周敦颐《太极图说》所云“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亦即“形具而神生”,“气须形而知”,朱熹也说“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朱子语类》卷五)。张载说:“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开塞,所以有人、物之别……”(《张子语录·后录下》)可见,人之所以有区别于(高于)万物的“知觉”,也是因为人禀赋了天地间的清通之气,这里也有《太极图说》所谓“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的意思。天地间的清通之气不仅是人所禀赋“天地之性”的渊源,而且其与人之“气质”相结合,便可“形具”而“神”发为“知觉”,此即人之“心”。因此,“心”的属性统含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与知觉,此即“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形具而有“性与知觉”,则“性”感物而发为情感,故张载又说:“心统性情者也。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性理拾遗》)
“知觉”是人心所有,这是人特有的主体能动性。所以,张载说:“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正蒙·诚明》)心之所以能“尽性”,人之所以能“弘道”,是因为人心有“知觉”的主体能动性;反言之,性之所以“不知检其心”,道之所以不能“弘人”,是因为“性”(即天道)没有人心之“知觉”。张载认为,知觉可分为“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他主张“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而“不以见闻梏其心”(《正蒙·大心》)。虽然见闻对于“合内外之德”也有开启的作用,但只有“大其心”的“德性所知”才是充尽了心的功能。如何“大其心”或“尽其心”?张载说:“思尽其心者,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谓因身发智,贪天功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同上)所谓“心所从来”,也就是人之身心由“天”之造化所成。“神,天德;化,天道……一于气而已”,这是人之身心(以及万物)的本原。知此,才能“尽心则知性知天”,才能“体天下之物……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才能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的境界。反此而为,徒知“大其心”,则未免流于张载所批评的:“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凝冰者与!”(《正蒙·大心》)张载主张的“大其心”,仍是以“先识造化”为前提,其基点是与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划清界限。张载认为,如此才能尽心、知性,才能达到“体天下之物……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仁”的境界(31)。
张载由“先识造化”所建立的哲学体系,就是以“太虚之气”为世界本原的气本论。“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此四句为张载哲学体系的概念层次、逻辑架构和理论纲领所在。牟宗三先生把张载思想强纳入“心体与性体”为一而与气“相即不离”的心学谱系,则未免把张载的许多关键语句都视为“滞辞”。以上四句中的后两句尤为牟先生所诟病(32),但若依牟先生所解,“问题只是心性合一否”,“宇宙之生化即是道德(心)之创造”(33),那么张载必反言之:“有谓心即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尽易之道!”
五
张载的“先识造化”,其宗旨也是“推天道以明人事”。朱熹说:“横渠说得好。‘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此是总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是就人上说。”(《朱子语类》卷六十)所谓“总说”就是“推天道”,所谓“就人上说”就是明人之心性。从“太虚即气”推演到“心统性情”,类似于《太极图说》从“无极而太极”推演到“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接着,便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而《正蒙》在《诚明》、《大心》之后,便是《中正》、《至当》,所谓“至当”即是“人极”,亦即最高的价值标准(34)。
《正蒙·中正》篇的大意是:“中正”乃君子立身行事的准则。“士希贤,贤希圣”,君子学做圣人,就是要将“中正”弘扬至“大中至正之极”。能够知道“大中至正”是最高的价值标准,也就知道了“止于至善”。“择中庸而固执之”,“知学”然后能奋勉日进,此为努力达到圣人境界的“工夫”。与周敦颐的“主静”不同,张载更强调了道德实践的长期修养和“知学”的重要(以后二程更强调了“主敬”与“致知”)。
《正蒙·至当》篇云:
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无入而非百顺,故君子乐得其道。……安所遇而敦仁,故其爱有常心,有常心则物被常爱也。……上达则乐天,乐天则不怨;下学 则治己,治己则无尤。
“至当”就是最高的应当,亦即最高的价值标准。“至当之谓德”,此“德”就是仁义,就是“大中至正”。张载对于德福关系的见解,建立在“穷理”而“知性命”的基础上,体现了“德福一致”、“义命合一”的思想。“命”一方面指“天命之谓性”,即人之性善,德为至当,知道了“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大人能尽性,“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另一方面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知此为人生必然的命运,则大人“安所遇”而顺应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正蒙·乾称》)这是宋代新儒家将道德确立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并且超越对于个人之贫富穷达的计较和生死之牵挂的仁者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君子乐得其道”,“乐天则不怨”,“治己则无尤”。于是,儒家有了一种不同于佛、老的安身立命之地。在范仲淹激励张载,提出“儒者自有名教可乐”,“因劝读《中庸》”之后,张载经过“先识造化”,建立了“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的哲学体系,从而最终为范仲淹提出的“名教可乐”或“道义之乐”(35) 提供了“性与天道合一”的哲理基础。
张载的哲学体系是以气为本而“天人合一”。以气为本,就是“先识造化”,也就是首先在世界本原的问题上肯定天地万物、人的生活世界是实在的。张载说:“诚有是物,则有终有始;伪实不有,何终始之有!故曰‘不诚无物’。”(《正蒙·诚明》)按,《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此“诚”即是“真实无妄”之实在(reality)的意思。张载以“一物两体”的“太虚之气”为世界的本原,此为“至虚之实”,人与万物由气之聚散而为“终始”,因太虚之“实”而人与万物亦为“诚有”(真实的存在)(36)。如果太虚是虚幻的“伪实”(假有),那么“物之终始”也就不过是依“心法”起灭的幻相。“不诚无物”,张载的气本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肯定天地万物、人的生活世界为真实的存在,由此而为儒家的道德论奠定本体—宇宙论的基础。张载的气本论亦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因此,“太虚无形”不仅是气之本然的象态,而且其“至静无感”亦是性善的渊源;“天道”不仅是一阴一阳的屈伸相感,而且“天道即性也”,“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在这里,“诚”不仅是天道的客观实在,而且是人道的道德主体性的“诚之”。张载哲学由“先识造化”而建立气本论,其理论的归趋、思想体系的完成则是“天人合一”。
就中国哲学的普遍架构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而言,“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总体趋向、主要特点。但在不同哲学家的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具体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张载是“天人合一”这一成语的首发者,在他的思想中,“天人合一”主要是用来批判佛教,而阐明儒家的实在论与道德论的统一。他说:
释氏语实际,乃知道者所谓诚也,天德也。其语到实际,则以人生为幻妄,[以]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彼语虽似是,观其发本要归,与吾儒二本殊归矣。道一而已,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固不当同日而语。……彼欲直语太虚,不以昼夜、阴阳累其心,则是未始见易,未始见易,则虽欲免阴阳、昼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见,又乌能更语真际?舍真际而谈鬼神,妄也。所谓实际,彼徒能语之而已,未始心解也。(《正蒙·乾称》)
佛教所说的“实际”,就其抽象的“真实”意义而言,如同儒家所说的“诚”或“天德”。但佛教是以“性空”、“真如心”和“涅槃”为终极真实,而把人生看作幻妄的,把人的“有为”看作有害而多余的“疣赘”,把人所生活的“世界”看作黑暗污浊的,因此,佛教主张“厌而不有,遗而弗存”,即主张“出离世间”,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涅槃”境界。假使佛教真得到了“实际”,那也只是“诚而恶明”,即只把“天德”看作真实的,而把人生、有为、世界视为应该厌弃的。儒家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在这里,“诚”是天道之真实,“明”是人道之明理(“诚之”或“思诚”),“天人合一”也就是“诚明合一”(王夫之《正蒙注》:“诚者,天之实理;明者,性之良能。性之良能出于天之实理,故交相致,而明诚合一”)。张载强调,儒家学说不像佛教那样“诚而恶明”。佛教以人生为幻妄,儒家则以人生为真实;佛教以“有为”为疣赘,儒家则主张“致学”可以成圣;佛教以人的生活世界为“荫浊”,儒家则认为人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道德的;佛教主张厌弃人生,归于涅槃,儒家则认为“天人一物”(《正蒙·乾称》),故“得天而未始遗人”,明德成圣就是人生最高的应当。张载进一步指出,佛教学说虽然“似是”,但“观其发本要归,与吾儒二本殊归矣”。“本”就是对世界本原的看法,“归”就是人生之归趋、价值之理想,儒家与佛教在这两方面都不同。正确的“道”只有一个,“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故儒与佛应划清界限,“不当同日而语”。在张载看来,“大率知昼夜、阴阳”(亦即“识造化”)然后才能知性命、知圣人、知鬼神,而佛教“不识造化”,“彼欲直语太虚”(“太虚”在佛教的思想中就是“性空”、“真如心”和“涅槃”),则其“未始见易”,想要超脱人世,免于“阴阳、昼夜之累”,这是“末由”即没有途径可行的。“易且不见,又乌能更语真际?”只有先识“易”(造化),才可以知道什么是“真际”或“实际”。如果不知道“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那么其“谈鬼神”就是虚妄之谈(37)。因此,佛教所谓“实际”,只是空言而已,不是“心解”即发自内心的对“实际”的真正解悟。
张载所谓“心解”,有发自内心而又发前人所未发的意思。他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经学理窟·义理》)此“心悟”就是“心解”。他又说:“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同上)张载充分认识到,他的思想也有孔孟未曾言而自己言之的“心解”成分,这是因为与佛教“较是非,计得失”而不得已也。他说:
自其说(佛教)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乃其俗达之天下,致善恶、智愚、男女、臧获,人人著信……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自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正蒙·乾称》)
可以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思想正是为了与佛教“较是非,计得失”而激发起来的一种理论创新。张载对于自己的理论创新虽然不谓之“至理”,但基本上自信。他说:“某比年所思虑事渐不可易动,岁年间只得变得些文字,亦未可谓辞有巧拙,其实是有过。……然某近来思虑义理,大率亿度屡中可用,既是亿度屡中可用则可以大受……”(《张子语录·下》)这段话必是《正蒙》著成后所说,可谓张载的临终遗言,对吕大临、范育等弟子寄予厚望。所谓“岁年间只得变得些文字,亦未可谓辞有巧拙,其实是有过”,当是指从《易说》到《正蒙》而有所改动,其“有过”可能如《易说》中有“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是也;‘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则异矣”,在《正蒙》中已没有对老子言“天地不仁”的肯定。尽管其间“变得些文字”,但从《易说》到《正蒙》,其思想是一贯的,《易说》奠定了《正蒙》的基础,张载认为此中的基本思想是“不可易动”的。
张载的《正蒙》原未分篇,在他死后由其弟子苏昞“离其书为十七篇”。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苏昞将编成的《正蒙》十七篇交由范育作序,当时范育“居太夫人忧……泣血受书,三年不能为一辞”,三年之后写成《正蒙序》。范育早在熙宁十年即张载临终前“受其书而质问焉”,在十三年之后他已“痛乎微言之将绝也”,当时二程对张载所谓“清虚一大”的批评已经风行(38)。范育是认真读过《正蒙》且有深切理解的,他对先师张载也抱有深厚的感情,故在张载去世后,迄至王夫之写《正蒙注》,真正给予张载思想以中肯评价的莫过于范育的《正蒙序》。其文云:
惟夫子之为此书也,有《六经》之所未载,圣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盖不必道。若“清虚一大”之语适将取訾于末学,予则异焉。
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图、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天下靡然同风,无敢置疑于其间,况能奋一朝之辩,而与之较是非曲直乎哉!
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千载之间。闵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将灭也,故为此言与浮屠、老子辩,夫岂好异乎哉?盖不得已也。
浮屠以心为法,以空为真,故《正蒙》辟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老子以无为为道,故《正蒙》辟之曰“不有两则无一”。至于谈死生之际,曰“轮转不息,能脱是者则无生灭”,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辟之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夫为是言者,岂得已哉!
使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则吾何为纷纷然与之辩哉?其为辩者,正欲排邪说,归至理,使万世不惑而已。……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
范育的《正蒙序》主要围绕着道学内部的理论分歧而为张载的《正蒙》作辩护,其要旨是阐明《正蒙》之言“与浮屠、老子辩”乃不得已也。文中叠言“不得已”,盖不如此,则不足以为张载之学作辩护,也不足以真知张载之学。然而,同样主张“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认为“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程氏文集》卷十三)的二程,为什么对张载之学不能肯认而有所批评呢?此中原因盖由于二程认为佛、老之学的要害在于“自私独善”,从而主张“先识仁”(《程氏遗书》卷二上)。于是,洛学与关学在建立道学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上有所不同。如果说张载的“先识造化”首先强调这个世界是实在的,然后讲这个世界的本质是道德的,那么二程的“先识仁”则首先强调这个世界的本质是道德的,然后讲这个世界是实在的。实在与道德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倾向,这个基本倾向也正是宋明道学的主题。
[作者附识:本文是我正在完成书稿中的一小节。回顾二十年前,我写有《“先识造化”与“先识仁”——略论关学与洛学的异同》,发表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曾呈张岱年先生教正。张先生在1989年12月18日的信中说:“你论述关洛异同的文章写得很好!很久没有见到这样好的文章了……我看了很高兴!”这一鼓励对于我以后的治学有重要影响。值此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谨以此文遥祭先师也。]
注释:
①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9页。
② 至熙宁初年,“神宗问明道以张载、邢恕之学,奏云:‘张载臣所畏,邢恕从臣游。’”(《程氏外书》卷十二)按,邢恕是程门弟子,而“张载臣所畏”则是程颢对有殊于洛学的张载之学的尊重。
③ 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5页。
④ 《正蒙·太和》:“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⑤ 冰水之喻,源于汉代王充所说:“人之生,其犹冰也。水凝而为冰,气积而为人。”(《论衡·道虚》)“人生于天地之间,其犹冰也。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论衡·论死》)
⑥ 《易传·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⑦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幽谓天上地下不可得睹者也……明谓天地之间万物陈列,著于耳目者也……”韩康伯《周易·系辞注》曰:“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
⑧ 《正蒙·神化》篇所谓气之“蒸郁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又见《易说·系辞下》),《正蒙·大心》篇所谓“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几万里之高也”,亦是此意。
⑨ 张载说:“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出实。”“太虚者,天之实也。”“诚者,虚中求出实。”(《张子语录·中》)因为“凡有形之物即易坏,惟太虚无动摇”,所以张载又说太虚为“至实”(同上)。
⑩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11) 牟宗三先生说:“‘离明不得施而无形’即(神)因气不聚而隐也。……隐显就神之明言。聚散就气言。”同上书第401页。此与张载所说“显,其聚也;隐,其散也”相矛盾。
(12) “安得不谓之有”是《易说》之原文,宋方闻一编《大易粹言》和古逸丛书之《周易系辞精义》均作“有”,只是《正蒙·太和》篇将“有”改为“客”。
(13)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380、393、403页。
(14) 张载认为,无形之气虽然不可见,但亦有“象”。他说:“所谓气也者,非待其蒸郁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苟健顺、动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正蒙·神化》)在张载的用语中,“象”既可指可见的形象,如云“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正蒙·太和》),又可指虽然不可见但可以言说的无形之气的变化,如云“有变则有象……故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但于不形中得以措辞者,已是得象可状也……有气方有象,虽未形,不害象在其中”(《易说·系辞下》)。
(15) 张载说:“太虚之气,阴阳一物也”(《易说·系辞下》),此明言太虚就是气,而不容说“太虚神体之气”。
(16) 牟宗三先生除对“即”作相即不离的理解外,又说:“依横渠之思想,体用圆融即是神体、气化之不即不离。”见《心体与性体》上,第392页。
(17) 同上书,第392页。
(18) 同上书,第383页。
(19) 张载说“天大无外”(《易说·系辞下》,又见《正蒙》之《太和》、《大心》),此“天”即太虚,《太和》篇云“由太虚,有天之名”。
(20) “昼夜”不仅指白昼和黑夜。张载说:“昼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昼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气易……气交为春,万物糅错,对秋而言,天之昼夜也。”(《正蒙·太和》)作为“天道春秋分”的“昼夜”,即相当于“两仪”之下的“四象”(四时)。
(21) 《正蒙·神化》:“象若非气,指何为象?时若非象,指何为时?”故“太虚”概念不仅统一了气的运动与空间,而且统一了气的运动与时空。
(22) 牟先生说:“神固不离气,然毕竟神是神,而不是气,气是气,而不是神,神与气可分别建立。”“‘太虚’一词,是由‘清通不可象为神’而说者。吾人即可以‘清通无象之神’来规定‘太虚’。”见《心体与性体》上,第379、380页。
(23) 张载说:“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矣。神为不测,故缓辞不足以尽神;化为难知,故急辞不足以体化。”(《正蒙·神化》)阴阳不测之“神”即是“形而上者”,“缓辞不足以尽神”,然则“急辞”庶几可“得辞斯得象矣”,此“象”与“清通而不可象”之“象”意义有别。张载说:“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故神之应也无穷……虽无穷,其实湛然……”(《正蒙·乾称》)此“神之应也无穷”的“湛然”即是“得辞”之“象”。
(2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388页。
(25) 牟先生说:“‘气之性’即气之体性。此体性是气之超越的体性……此‘固有’乃是超越地固有……”但又说:“‘气之性’则容易使人想成气之质性,此即成误解。此其所以为滞辞也。‘神与性乃气所固有’句尤其窒碍不顺,尤易使人想成气之质性。”见同上书,第379、410页。
(26) 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27) 同上书,第60—61页。
(28) 《张载集》,第325页。
(29) “至静无感”并非绝对静止,《正蒙·乾称》云:“至静之动,动而不穷……动而不穷,则往且来。”此处“无感”是相对于有形之物的“客感”而言,《张子语录·上》云:“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
(30)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424—425页。
(31) 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程氏遗书》卷二上)
(32) 牟先生说:“由‘合虚与气’以说性之名之所以立,此根本是滞辞。”“‘合性与知觉’好像是说性体中本无知觉,性是性,加上知觉才有‘心之名’。此句由‘合’字表示心,与上句由‘合’字表示性,皆是不精熟之滞辞。”见《心体与性体》,第424、454页。
(33) 同上书,第488页。
(34) 朱熹说:“若‘皇极’之极、‘民极’之极,乃为标准之意,犹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答陆子静》)又说:“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阜极辨》)
(35) 范仲淹有《睢阳学舍书怀》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锺君恨即销。”(《范文正公集》卷三)此与周敦颐所说“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通书·志学》)意旨相同。在范仲淹晚年,“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范文正公集·年谱》)
(36) 太虚之气与由此产生的天地万物、人的生活世界均为实有,此即中国哲学的“一个世界”、“存有的连续性”思想,而没有“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的“自然之二分”。
(37) 张载认为,“鬼神”不过是阴阳二气的屈伸聚散之“良能”,“鬼神之实,不越二端而已矣”(《正蒙·太和》)。
(38) 吕大临在元丰二年(1079)东见二程,此时二程对张载之学已有“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等批评(《程氏遗书》卷二上),此距范育写《正蒙序》十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