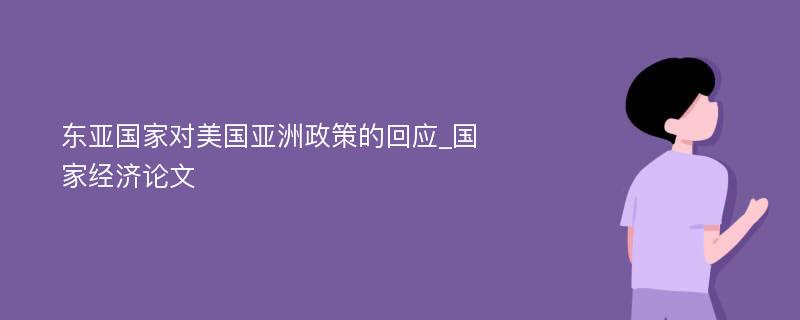
东亚国家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亚洲论文,美国论文,政策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的亚洲政策由三大要素构成:经济上,力促亚太国家尽快撤消贸易上的保护措施,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极力推行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提高美国对亚太市场的占有率;安全上,调整从亚太撤军的战略收缩政策,重视美国的存在,确保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意识形态方面,极力推销美国式的“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观念”,企图以自己的模式重新塑造亚太国家。
美国的亚洲政策执行两年来,在许多方面几乎陷入困境,受到国内外众多的批评和指责。
东亚国家积极寻求适合亚太地区的发展道路。他们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回应,表现在三方面:互相配合,力争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主导权;安全上减少依赖性,增强自主防务意识;弘扬民族文化,提倡传统价值观。
近一两年来,“新亚洲主义”、“亚洲独特的道路”、“亚洲政治和社会模式”、“离美入亚”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等议论骤然而起,反映了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意识和独立自主的倾向增强,其趋势广受瞩目。自80年代起,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生机持续高速发展而在世界经济领域内独领风骚,加之多极化的发展,使东亚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和扩大。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当中许多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也在提高,改变了以往忖度大国意图,被超级大国左右的局面,开始独立自主地主导自己的内部事务。东亚国家独立自主程度的提高和联合自强势头的增强,将决定亚洲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力量配置。举世公认,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政治中一个新的力量中心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所以,研究和探讨东亚国家如何应对美国的亚洲战略,是研究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趋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一
关于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详细内容和对其评论和剖析,已有众多专文陈述,但为更好地探讨东亚国家如何应对美国的亚洲战略,简要回溯一下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后所制定的亚洲政策似有其必要。
1993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东京时曾强调“太平洋地区能够并且必将成为美国人民就业、收入、合作、思想以及经济增长的巨大来源”。美国商务部长布朗在谈到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亚太地区不仅是我们命运的归宿,也是我们目前财富的来源”。事实表明,克林顿政府重视亚太并将亚太地区置于“外交和经济政策的中心地位”之一的意向已定。从美国政府领导人的言行和官方发表的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亚洲政策由三大要素构成:经济上,力促亚太地区国家尽快撤消贸易上的保护性措施,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极力推行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积极参与本地区的经贸活动,开拓市场以争取贸易先机,提高美国对亚太地区市场的占有率;安全上,调整从亚太地区撤军的战略收缩政策,维持其前沿战略部署和较高水平的军事存在,以确保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及政治和经济利益;意识形态方面,极力推销美国式的“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观念”,企图以自己的模式重新塑造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为达此目的,美国常借“人权”等问题进行威胁,如用人权换最惠国待遇,或以经贸制裁等手段相要挟,胁迫有关国家接受其“人权观”和“民主观”以及美国其他一些政治上、安全上、经济上的要求。
从本质上讲,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政策是美国全球政策的派生,基本上是萧规曹随,与前任所奉行的政策实无原则区别,而只是受国内经济和亚太地区大环境的驱使,作了些重要调整,把开拓市场和促进贸易置于优先地位。美国的战略步骤是,着力推进由它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内部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借支持东盟地区论坛,展开“多边”安全对话,实现其安全战略构想,即政治上既可推行美国价值观,又可对一些国家进行牵制,防止出现任何新的所谓“霸权大国”。
二
综观克林顿政府执政两年多来所奉行的亚洲政策,其困难多于成功,忧虑多于喜悦,铸错多于决断。在诸多方面几乎陷入困境,并受到国内外众多的批评和指责。
众所周知,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把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联系在一起,并给中国规定了一些“人权”问题的具体条件,声称要根据中国的“人权”表现来决定是否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达此目的,美国政府和国会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打的这张牌并没有使中国屈服。相反,它遭到中国、美国商界和前政府高级官员及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事态发展表明,美国把“人权同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已走到尽头。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在1994年5月26日宣布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这无疑是明智之举,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从此不再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了,而只是改变策略而已。
由日益剧烈的经贸竞争产生的日美贸易摩擦及日本在购买美国汽车零部件和购买外国车的“数值目标”问题上的不妥协政策,并敢于向美国说“不”,使日美经贸关系更趋恶化。美国政府重施故伎,宣称要对进口日本的豪华汽车征收100%的关税,以示对日本制裁,而日本为此决定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日本决定要与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对簿公堂”,反映了冷战后日美经济实力发生变化,改变了过去唯美马首是瞻的模式,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以经济实力作后盾,争当政治大国。
另外,泰国和菲律宾政府公开拒绝美国装军需品的舰只在它们的海湾停靠的要求,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关于外籍劳工权力的龃龉以及新加坡政府不顾美国压力对犯有损害他人财物罪的美国一青年处以笞刑等,均反映了这些国家的独立自主意识的提高。特别是从马哈蒂尔总理拒绝出席1993年11月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到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提出和《亚洲可以说“不”》一书的问世,体现了东亚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自强自立的信心。
情况表明,美国推行的亚洲政策阻力大,曲折多,进行得很不顺利。这些在冷战期间是无法想像的。诚然,亚洲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领土争端、制度的差异以及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交往尚不深、或出于某些特殊需要和利益考虑,它们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在某些方面有认同感。例如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问题,认为目前尚有其必要性。但应该看到,亚太地区多数国家要求以亚洲国家认同的方式处理地区内部事务和解决矛盾与争端,以及积极寻求适合亚洲地区的发展道路。
三
东亚国家对美国的亚洲政策作出的相应对策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1994年《华盛顿邮报》援引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给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信中曾指出,亚太领导人已经和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和措施抵制美国对亚洲国家单方面施压政策。
(一)互相配合,力争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主导权。东亚国家近几年经济发展成果显著,区域内贸易迅速扩大。据《日本经济新闻》4月17日发表的该报记者竹冈伦示的一篇报道,1994年东盟各国对本地区的出口比前一年增长20%至80%,大大高于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增长率。美国商务部长布朗也承认,就在过去的一年(1994年),美国的商品出口26%出口到西欧,29%出口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这一事实表明,东亚国家间经济合作和发展不仅使市场容量和竞争力增大,而且也会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方向有较大发言权。毋庸讳言,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主导权之争的核心是,谁来掌控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在这方面,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反对有的国家借经济合作之名,行抢夺经济合作组织主导权之实。在该经济合作组织的定性问题上,它们明确表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只能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不同意将该组织搞成内向性贸易集团,否则它会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自主性、竞争性和开放性。因此,东亚地区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为防止出现该组织有可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方向去发展,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为代表提出成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构想,来牵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保护它们的经济主权和提高掌握经济主导权的抗衡能力。该构想得到了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赞同,因为这些国家对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母体”,来确保某个大国创设区域内自由贸易圈主导权的做法抱有强烈的警惕心理。美国却为此担心并认为如该构想一旦成为现实,就会架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样美国的战略构想就会落空。所以美国坚决反对。日本虽然没有否定由亚洲国家创立属于本身的经济组织的构想,但又不愿得罪美国,有其难言的苦衷,故态度暧昧,甚至拒绝出席原定今年4月在泰国举行的东盟、中、日、韩参加的负责经济事务部长会议(与拟议中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相同)。故该构想仍在运筹之中。此外,一个由东盟倡导的将要启动、旨在加强亚、欧双方政治经济联系和经济合作,并就经贸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政策交流和协调的亚、欧首脑会议正是从另一个层面拓展其回旋余地和国际空间。
面对主导权之争和日益频繁的贸易保护主义,东亚地区国家意识到,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和影响力,必须改变那种单枪匹马各自为战的局面,才能在剧烈的竞争中取胜和掌握经济主导权。东盟国家提出建立“东南亚十国共同体”,正是为了加强次区域内经济合作,增强对欧、美等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抗衡能力,保护其经济主权。
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问题,去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发表的《茂物宣言》规定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尽管这是成员国领导人所作的一项政治性承诺,但由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与美、日相比较尚有校大差距且发展也不很平衡,因此,多数成员国对此采取了有保留的态度。它们担心,美国会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机会而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行经济扩张。对美国来说,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产品和资金将不受边界限制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倾销产品,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廉价的生产基地,而不是共同开发人力和自然资源和发挥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最终实现平等发展及缩小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所以,美国急于敦促有关各方拟定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时间表,其目的也在于此。墨西哥超前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诱发的金融危机对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面可以引以为戒的镜子。今年2月日本福冈部长级会议上因意见不一而未能落实。4月在新加坡召开的高级官员会议上又由于东盟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反对定出具体时间表,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笔者认为,《茂物宣言》宣布2010年和2020年分两个阶段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本身反映了亚太地区国家经济水平的不平衡性,并在时间问题上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赢得了主动权。
(二)安全上减少依赖性,增强自主防务意识。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冷战军事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冷战期间遗留下的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完全的解决。本地区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关系到亚太地区安全和长期稳定的大事。各国对此提出了许多建议和主张,但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安全构想不尽相同。美国提出保持前沿军事存在和维系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及多边安全对话三位一体的安全战略构想。中国表示愿意同亚太地区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展开“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东盟国家则主张通过“东盟地区论坛”构筑亚太安全新框架,试图平衡美、日、中、俄几个大国在亚太的力量均势。想法不尽相同,但从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主张和建议看,其基本点是协商和对话,反对用武力或制裁施压等手段来解决分歧和争端。这是亚太地区国家战略意识提高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7月25日,由东盟国家倡导和主持世界主要大国在内的18个与会方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顺利召开表明,由东盟国家主导的亚太安全对话开始启动。这是冷战后首次由亚太发展中国家出面组织并按亚太方式就安全等问题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这同冷战期间由某一两个大国操纵,说了就算数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就安全保障而言,东亚国家的自主防务意识也在提高。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明确表示,“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处于危险状态。假如出现险情,显然也不能全靠美国来维护东亚的安全”。这与有些国家的看法大相径庭,但也反映了大多数亚太地区国家想说而没有说出的想法。当然,现在谈论由东亚国家支配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还为时过早,因为美国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和科学技术上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亚洲的“变革之风已经朝那个方向强烈地吹起”。现在,美国虽然还将继续从战略上参与亚洲的安全事务,但其出发点是以军事存在为依托,谋求贸易和经济利益。因此,同冷战结束前相比较,其参与性质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可以肯定,东亚地区的安全战略将会越来越多地由本地区国家来作出决断。
(三)弘扬民族文化,提倡传统价值观。亚洲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文明,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先导作用,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带动了西方文明的进步。不同的民族其文化表现形式和内涵有所不同。中国历来主张在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的同时,进行文化交流,特别是要从西方文化中吸取有益的部分,来丰富和繁荣本民族的文化。我们承认,一定的文化会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这是我们反对和抵制腐朽文化的出发点。新加坡李光耀资政谈到文化影响时,有一段精彩的表述:“西方媒体,它们的报纸和电视,从中发挥影响力。它们的产品充斥我们的电视、广播和印刷媒体。美国漫画、纪录片,以及电缆电视新闻广播网(CNN),把外界发生的大事带进了我们的客厅,而美国舆论,则从美国的角度和看法,向我们解释这些事件的含义。当东亚开始发展,人民成为自己媒体的主人时,亚洲漫画、亚洲纪录片和亚洲评论员,将从亚洲人的眼光,向我们解释这些世界大事的含义”,“因此,当西方传媒企图把自己的意愿和价值观,强加在我们身上时,我们敢抗拒他们是因为这场仗,我们不一定会输”。
价值观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现今谈论价值观离不开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问题。但近几年来,美国与中国和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在人权观念上出现明显对立。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宣扬价值观念的普遍意义,并强调个人人权,用自己的政治标准去裁判别国的人权状况,对认为不符合其人权标准的国家,动辄就实行制裁,甚至迫使他国改变政治制度。其实,人权状况的发展是受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因素制约的。同时,由于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对人权的理解亦有所不同。我国认为人权问题的核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互相尊重的精神增进了解,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促进国际人权领域中的合作,反对在人权问题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人权问题只能根据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靠这些国家自己来解决。强制推行某个国家的“人权观”就是用人权来干涉别国内政。
事实证明,大多数亚太地区国家不喜欢美国的“人权观”,即使是日本这样的国家也没有完全站到美国一边反对一些亚洲邻国的人权观念。日本前首相细川在人权问题上与美国的态度就不同。为此,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指责他“在人权问题上拆我们的台”。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明确表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是徒劳的。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公开批评美国使用“贸易杠杆促进中国人权的策略”,反对把人权问题与贸易挂钩的做法。越南副外长黎梅最近也指出,人权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强加干涉的,并批评某些人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马哈蒂尔总理强调维护自己的价值体系的重要性,他说,“亚洲若能在继续保持其原有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超越欧美,将创造出世界上史无前例的伟大文明圈,在产业及一切文明方面重新走在欧洲前头。有意识地努力维护自己的价值体系极为重要。否则,亚洲就会再次处于欧洲统治之下”。因为,“时至今日,他们仍坚持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政治体系是最优秀的,并将它们强加给别人。他们所说的‘民主’和‘人权’,只是出于他们唯我独尊和利己主义的考虑与解释”。他精辟地分析了弘扬民族文化和维护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宣扬的“民主”和“人权”的实质是强权主义,企图将不符合其人权标准的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四
美国的亚洲政策连连受挫,不能如愿贯彻自己的意志是由其国际和国内因素决定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亚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必然导致独立自主性的提高。60年代,东亚经济实力只占全球4%,到90年代其经济实力增至25%。据统计,1993年日本和中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出口贸易总额为6210亿美元,美国为4650亿美元。进口方面美国为6000亿美元,而日本和中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进口总额与美国或欧盟相当。如果加上东盟进出口额3000多亿美元,则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规模已超过了美国或欧盟。近年来,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方向发生了变化,即区域外贸易比重有所下降,区域内贸易比重在增加。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决定行动。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比重增大,必然导致亚太地区国家发言权增大,在分享经济权益中的筹码增加及独立自主处理内部事务和地区事务的愿望增强。所以总的趋势是,由原来的依附关系向自主独立趋向发展。但美国对此反映迟钝,仍习惯于用冷战时期“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来贯彻自己的意志。一旦自己的目的不能达到,就采取高压政策施行经济贸易制裁乃至以武力相威胁。连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这种对抗作风“即使不是恶霸,也像是个国际保姆”。这是美国的亚洲政策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克林顿政府的决策者错误地认为,美国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仍具吸引力,对发展中国家仍可像几十年前那样鹰啄雀燕,任意摆布。因此,他们认为今天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最好的办法是,对不顺遂者施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这种傲慢自大和对抗作风不仅缺乏兼容性和包容性,而且低估了东亚崛起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诚然,从美国总体实力看,它仍然是超级强国,但其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明显下降,从军事看,美国要想继续充当“世界警察”已力不从心,需要借助盟国的支持。然而,冷战后美国国内民众情绪趋于内向和孤立主义。这种现象无疑对即使由盟国掏腰包美国出兵充当“警察”,也会起到掣肘作用。这也是美国的政策频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的亚洲政策在遭受到一系列挫折之后,也作了某些微调,如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与一些国家淡化争议,使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巨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参与本地区的经济和安全事务是既定方针。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人权、贸易逆差、生态环境、工人的最低工资、武器控制和核开发以及台湾等问题为由干涉亚洲国家内部政经事务也不会变。因此,美国想要顺利推行其亚洲政策,还会有困难和阻力,甚至会遭到挫折和失败。亚洲对美国说“不”的次数可能会增多。
